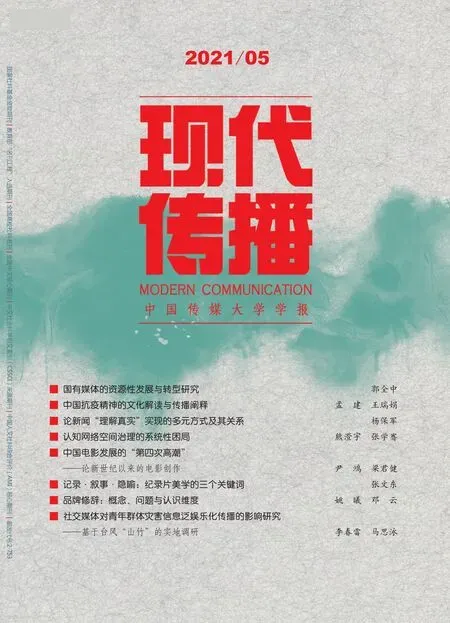品牌修辭:概念、問題與認識維度*
■ 姚 曦 鄧 云
人類在經歷了農業革命、工業革命后,正在經歷著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飛速發展的信息革命。在當前第四次工業革命時代背景下,隨著以信息交流、共享、共創為主要特征的數字傳播技術的革新進步,品牌傳播認識圖式也正經歷著結構性調整,并逐步形成新的框架體系。這集中體現在“品牌傳播研究內容的更新與范疇的擴大”①。其中,品牌傳播的修辭問題是新的時代背景下品牌傳播研究領域的新議題之一。本文將以品牌傳播實踐面臨的問題為切入點,引入修辭的思維與手法,再結合品牌與修辭的經典理論,探索品牌修辭的基本問題和認識維度,以期為理解品牌修辭,以及如何通過品牌修辭更好地提升品牌傳播效果與價值提供新的路徑方向。
一、品牌傳播的修辭問題
(一)品牌傳播的修辭需要與修辭可能
數字技術的發展給以效果為導向的品牌傳播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機遇與挑戰。一方面,信息爆炸帶來了信息傳遞邊際效應的弱化,消費者注意力資源日趨稀缺,品牌的光環逐漸黯淡;另一方面,品牌信息的傳遞更具個性化、精準化與立體化,傳播效果有了大幅提升的可能。如何以內容為核心講好品牌故事,強化創意表現,以技術為手段精準定位目標消費群體并帶來全息的品牌體驗,是抓住機遇迎接挑戰的最佳舉措。而修辭能夠將藝術化的內容創意與科學化的形式展現統一于品牌行為之中,使得技術的發展優勢與信息內容的生產、表現、傳播產生疊加效應,彌合因為過于注重形式、忽略內容而產生的技術與內容的割裂,全面提升傳播的效力,為企業品牌與國家品牌的傳播提供了新的思考。此外,數字技術的快速迭代,造成新的品牌傳播現象與問題層出不窮,原有的品牌傳播研究體系在尚未完全發展成熟之時,又面臨著更新擴大的需求,跨學科汲取發展的養分成為當務之急。
起源于古希臘時期的西方修辭學以話語實踐為核心,有著龐大、成熟且完善的知識體系,可為品牌傳播研究提供豐富的理論資源與方法論資源。自二十世紀以來,修辭以一種廣泛的意識向其他學科領域擴散,并參與到全部學科的演變過程中,以此完善各個學科理論體系。這一修辭學的轉向也為修辭意識介入品牌傳播研究領域提供了前提條件。與此同時,伴隨著技術的發展,修辭意識日益凸顯,修辭表現形式趨于多元與立體,修辭的重要性愈發突出,修辭既無處不在地存在于品牌傳播實踐領域,也逐漸成為可獲取、可觀測的現象。品牌傳播的修辭問題研究兼具了理論與實踐的可能。由此,以修辭為視角形成品牌傳播與修辭的結合兼具了歷史的必然性與未來的可能性。
(二)品牌修辭的概念“生成”
品牌既是品牌信息的載體也是品牌關系的集合。在數字化時代,品牌傳播的本質在于努力搭建品牌本身與貫穿傳播活動始終的一切利益相關者的關系,使其形成不可分離的共生關系,并在此基礎上實現價值共創。②修辭的本質在于以一種抽象性的思維,付諸于“勸服性”的手法技巧,實現同一性的目的,其中同一既是修辭的動機,也是修辭的目的。具體來看,修辭的本質與功能存在千絲萬縷的關系。“修辭的功能是調節思想以適應人;調節人以適應思想”③,具備社會功能;修辭是認識世界,形成知識,以及創造性地再現知識世界的工具,人類運用修辭的過程即為知識產生的過程④,具備認知功能;修辭著眼于消除分歧與隔閡,以尋求解決社會政治問題的和平方法,具備政治功能。修辭的社會功能、認知功能與政治功能統一于修辭的目的之中,修辭本質上便具備了認識論與方法論的特性。
根據德勒茲(Gilles Louis Rene Deleuze)的觀點,“生成,就是從(我們所擁有的)形式、(我們所是的)主體、(我們所具有的)器官或(我們所實現的)功能出發,從中釋放出粒子,在這些粒子之間建立起動與靜、快與慢的關系——它們最為接近我們正在生成的事物,也正是通過它們,我們才得以進行生成。”⑤品牌傳播是關系連接的過程,而修辭具有實現連接、達成同一、完成認識的功能,以“連接”“同一”為相似性關系的節點,可將修辭嵌入品牌傳播的過程之中,形成品牌與修辭的結合。鑒于“生成”的目的是為了實現主體“生命”力的提升,也即品牌傳播效果的提升,修辭僅以一種思維意識與認識方法融入品牌傳播的過程,并不涉及到一個新的研究領域。品牌修辭是品牌傳播研究領域里的一個新的認識視角與知識概念,它以品牌傳播過程中的修辭現象為研究對象,即品牌傳播如何經由修辭的作用實現提升效果的目的,其最終落腳點仍然在于品牌傳播本身。具體來看,品牌修辭包括了品牌信息表達的修辭化與品牌信息傳播的修辭化,以實現品牌利益相關者的同一。在這個過程中,修辭是一種同一性的思維方式,符號是品牌信息最基本的表現元素,技術則是提升修辭能力、實現修辭融合的主要驅動。品牌主體運用修辭的思維、原則與手法,通過技術對符號進行策略化的組合、呈現與傳播,并與信息接收者一起構筑品牌信息傳播的場域情境,形成關于品牌理念感知、交流與協商的釋義框架,最終協調與利益相關主體間的關系。其內部應該包含以下研究問題:主體問題、策略問題、情境問題以及受眾問題,這四個問題是從過程的角度對品牌修辭的細化與解析,是品牌修辭這一概念的基本問題情境。
二、基本問題:主體、策略、情境與受眾
科克斯(David Roxbee Cox)將問題定義為“在特定歷史時期對某些事件的意識。”⑥問題的特質就在于其對于理解本身所具有的方向指引性的意義,要對品牌修辭形成深刻認識,首先需要形成品牌修辭的問題。本文將主要從以下兩個層面來形成品牌修辭的問題:一是立足于傳播學的學科傳統,從信息傳播的理論脈絡中提煉出品牌修辭的本體問題;二是立足于品牌本身,從品牌形成與發展的最終目的出發,分析出品牌修辭的核心問題。本體問題與核心問題共同構成了品牌修辭的基本問題。
品牌修辭的本體問題源自于對品牌傳播本質——品牌信息傳播的認識。弗洛里迪(Luciano Floridi)認為,信源將信號經由符號系統傳遞給信宿,信宿在共享的符號范式內,對信號進行理解,只有對信宿理解有效的信號(消息)才能稱為信息。結合品牌的符號特性,品牌相關信息是其符號化的前提與基礎,而符號的策略化組合則體現了修辭的思維與技巧。回到傳播學的研究視域,以交流為核心的問題域強調的是傳播現象的“嵌入性”特征⑦,傳播無法脫離主體的作用。因此,品牌修辭的本體問題應該是品牌信息的修辭化呈現與傳播,為品牌修辭的策略問題;品牌信息的修辭化源自主體行為,為品牌修辭的主體性問題。本體問題回應了品牌修辭是什么,而核心問題則對應了品牌修辭的為什么。自品牌以商業化的市場概念出現,其最終目的便在于品牌價值的實現,隨著品牌觀念的發展,品牌不僅關乎于品牌所有者的利益,也與品牌相關者的利益緊密相連。那么如何實現品牌利益相關者的價值增值?通過品牌主與各利益相關者進行互動、共演,從而形成關系系統的共通與優化,品牌傳播則是通往品牌價值的重要途徑。品牌傳播效果實現的關鍵在于與品牌利益相關者實現品牌理念的共享共通,其中理念的交流與協商需要依賴于具體的感知環境與社會經驗,由此品牌修辭的核心問題一是傳播的情境問題,二是傳播的受眾問題。
(一)主體問題
主體問題屬于品牌修辭的本體問題,指涉的是品牌修辭主體間的關系及其運行機制。“真正的主體只有在主體間的交往關系中,即在主體與主體相互承認和尊重對方的主體身份時才可能存在。”⑧哈貝馬斯(Jürgen Habermas)從交往行為理論的角度對主體間性進行了界定,認為主體間性就是作為社會主體的人與人之間的相互性與同一性,主體在對話與交往過程中表現出以“交互主體”為核心的一致性,強調的是主體間的理解與溝通。
隨著大數據及人工智能技術的介入,品牌傳播關系發生變化,品牌信息傳播的主導權逐步讓位于受眾,受眾一改往日被動、消極、松散的信息接收者角色,成為品牌社群中有組織的信息創造者、協商者與傳遞者,從而影響著品牌價值與意義的建構。品牌主體與客體之間的關系部分轉化為主體與主體間的交流合作,主體行為不再是單一的工具性行為,還應當包括主體體系內部多主體交流互動的主體間性行為。品牌修辭行為中往往存在多個價值主體,這些價值主體之間以符號為介質,通過編碼與解碼的方式,經過多次“主體-主體”“主體-客體”之間的意義生成與協商,從而達成觀念的同一。
數字技術驅動品牌傳播主體間關系走向復雜化,品牌修辭的主體認識應該進入一個更廣闊的分析空間,既要看到單獨的傳播主體,也不能忽視了傳播主體間、傳播主客體間的意義交流與關系構建。可以說,傳播主體間關于品牌符號意義協商的一致性,是進行品牌有效傳播與價值理念同一的前提。“主體間性”觀念的引入,為理解數字技術環境下的品牌修辭主體關系提供了切入點。而主體的形成,以及主體系統的解構與認知,則與符號、技術緊密相連。符號是主體身份建構、表征的前提與基礎,正如巴赫金(Bakhtin Michael)所言,“我”和“你”都是對話的產物,沒有和“我”對話的“你”,“我”也不復存在⑨,作為主體的“我”是一個符號化的相對概念。符號也是主體間交流協作,并形成一致性關系的關鍵因素。經由符號的溝通與協商功能,主體逐漸成為一個完整的體系。技術則是驅動品牌修辭由主體性走向主體間性的重要推力,它將多個利益主體納入同一體系范圍,并建立關系連接,為達成多元利益的滿足以及品牌傳播效果的最大化創造了條件。此外,技術還增強了符號的表意能力,為符號連接主體與主體、主體與客體形成完備的主體體系提供了可能。
(二)策略問題
品牌信息的在場屬于品牌修辭的本體問題,對應的是品牌信息選擇與呈現的修辭化策略。佩雷爾曼(Grigory Perelman)在《新修辭學:論論辯》一書中將在場定義為“對一些因素的呈現,而正是這些因素言者希望集中注意以占據聽者意識的前景。”⑩喬治·坎貝爾(Campbell,G)則認為,在場源于說話者所呈現事物的一些情況,這些情況能夠喚醒或激發受眾的熱情。可知“一些因素”或“一些情況”在行為發生之前便預設了某種選擇,而呈現是選擇之后的展現與加強,具有一定的策略性。言者(說話者)與聽者(受眾)為修辭的雙方,前景(熱情)則體現了選擇與呈現的目的,故而在場的定義實際上搭建了一個關于品牌修辭的初始性框架。
在場實際表現在兩個語義層面:非缺席的在場以及增效性的在場。其中前者的實現途徑為“選擇”,后者對應的是“呈現”。品牌修辭的主體出于一定的目的,選擇部分信息進入受眾視野,而受眾也會有選擇地允許信息進入到關注的范圍。這些最終被選擇的信息便獲得了一種在場的效果。“呈現”既包括了信息內容如何通過符號系統被順利表征,也表現在編碼之后的信息如何經由符號載體更好地接觸到受眾,這是一種事實意義上的在場。佩雷爾曼認為呈現的增效性可以通過辭格的使用進行體現。伯克(Edmund Burke)則重點突出了四種常用修辭格——“隱喻”“轉喻”“提喻”“反語”,認為它們存在于人的思維與言語交際之中,對于人的溝通交流具有極強的促進作用。隱喻是最為常見的辭格,其本體與喻體之間的相似度極低,也就是說作為亞像似符的表現形態,隱喻關注的是兩者之間的意義關聯,并以一種通約性的共識機制來協調與構建兩者之間的關系。因此,以隱喻為代表的辭格實際上促進了符號解釋項的推演,增強了符號的可衍義性,擴大了符號體系。可見,修辭策略化的裝置體現了符號意義生成的內在機理,符號的意義生成與意義擴散則增強了修辭手法的表現能力。
在“呈現”的過程中,其增效強度通常會受到技術的影響,也就是說,技術通過作用于符號形式的變化,不斷生成新的符號或完善已有符號的意指關系,擴充符號系統,使得信息可以被更好地呈現。在數字技術的驅動下,品牌修辭的符號形式由單純的語言符號,轉向多元的視聽符號、科學符號以及虛擬符號,實現了由平面到立體,單一到多維,游離到浸合的轉變,符號的表意能力得到了極大的增強。與此同時,技術豐富了傳播的渠道,符號與渠道更為適配,甚至可以根據個人的信息接觸習慣,形成更為個性化與針對性的傳播接觸點,信息的呈現得到了全方位的提升。
(三)情境問題
情境問題屬于品牌修辭的核心問題,旨在形成品牌修辭釋義的情境規約,同時也為品牌修辭的意義生成與錨定提供了某種回應機制,引導受眾在情境規約下的共識性框架內完成修辭意義的解讀與接納。其中情境為符號的指涉實踐提供了意向場所,賦予了符號意義生成的框架與規則,幾乎每一個符號的意義生產都是特定情境規制與理解下的產物。符號的出場則使游移在情境內的意義有了外化形態,意義得以被固定與表征。技術增加了情境的類別,擴大了情境的意義裝置范圍,使得情境既可以是物理的空間場景,也可以是抽象的釋義氛圍,更可以是虛擬的感知空間,從而加強了情境與符號之間的錨固,意義的表征與釋義也更為順暢。
比徹爾(Bitzer)指出“情境”為“一個由人物、事件、物體及關系組成的復合體,該復合體呈現出一種缺失,它可以完全或部分地得到解除”。其中缺失、受眾和限制是“修辭情境”的三個基本要素,“缺失”為具有一定緊迫性與復雜性的非完善狀態,指向修辭的目的,是“情境”的中心;“受眾”是受話語影響以改變缺失狀態的人,具備一定的能動性;“限制”將“修辭情境”控制在了特定的范圍,“意義”的進入是“限制”形成的條件。比徹爾修辭情境的觀點,還體現了修辭話語、修辭情境以及修辭意義三者之間的關系,即修辭話語經由修辭情境生成并確定意義。意義是話語的核心、情境的靈魂,具有不確定性、動態性的特征,符號則是修辭話語的外化形態,情境受多種因素影響對符號意義進行了規約與限定。當話語以符號的形式進入有限的情境,本身便具備了某種意圖或動機。受眾受認知語境的影響,對符號進行釋義的過程,實質上也是關于符號意義交流與協商的過程。其中認知語境是意義傳達時所激活的存儲于主體大腦中的語言語境、情景語境和文化語境,這些被固定化、系統化的語境再經由轉喻、象征等手法產生或解讀出新的語境意義,則屬于社會語境。語言語境與情景語境關注的是修辭話語發生的文本結構與情境邏輯,而文化語境與社會語境強調的是超脫于修辭本身更為廣闊的范圍,包括社會文化背景以及基于共識性約定的規則。因此,通俗意義上的修辭情境通常表現為修辭主體與修辭客體在特定情境內發生的意義交流與協商行為,以期彌合情境中的主要缺失,其中意義交流的載體為符號。
品牌修辭實際上包括兩個行為階段:一個為品牌信息修辭化的呈現與傳遞過程;另一個則是品牌信息修辭化之后的意義生成與協商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主體出于某種傳播目的,將信息符號化地展現并賦予其意義,受眾綜合語言語境、情境語境和社會語境激發認知后,順利完成意義的解碼與交流,從而與品牌主體產生觀念的互通,由此實現品牌傳播的目的與價值。進入數字時代,隨著增強現實(AR)和虛擬現實(VR)等技術的出現與發展,情境的范圍在不斷擴大,符號意義的生成與情境的聯動更為密切,符號再現體與對象之間的聯系也更為穩固與貼切。以虛擬技術與數字符號為基礎構筑的虛擬空間作為情境的物質載體,在恰當的時機、以適宜的場景(互聯網使用場景或現實生活場景)連接到消費者。消費者則充分調動自身所有的感官,對品牌形成相關理念的認知,這種情境感知與理解模式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以話語情境為主導的線性交流、認知模式,走向了以人的身體為核心的立體化、多元化、復雜化甚至全能化的“浸合”,品牌傳播效果得以大幅提升。可以說,技術是情境形成并得以不斷擴大的動因,對技術的把握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理解情境的物理裝置;而符號是情境意義的外顯形式與外部通道,也是情境的內容與靈魂,對符號的理解使得認知情境的意義生成與配置過程得以被認知,反過來也作用于品牌信息的傳播效果。
(四)受眾問題
品牌修辭的另一個核心問題為受眾問題,闡釋的是受眾身份構成與釋義機制,以此明確受眾在品牌修辭中的地位。品牌符號解釋項的推演和符號意指關系的最終確定都需要依賴受眾意識。而受眾意識往往由受眾群體內部的共識性規約與個體自身的經驗習慣共同構成。也就是說,受眾通過作用于符號系統,成為實現品牌修辭目的的關鍵因素。技術的發展加劇了受眾的復雜程度,與此同時受眾的主動性增強,符號在溝通受眾與受眾、受眾與傳播主體間關系的能力得以強化。佩雷爾曼在“新修辭”理論中,強調受眾決定了論辯的質量以及言說者的行為,言說者必須要考慮到受眾。但受眾是一個復雜且多元的群體,在性格、背景等方面均存在差異,故而言說者要與受眾產生智力(思維)的接觸。
可從兩個層面對受眾的結構進行剖析,一是受眾的個體層面。杜威(John Dewey)認為,“每個人都是一個聯系體,這個聯系體包括很多細胞,每個細胞又都是一個獨立存在。”阿馬蒂亞·森(Amartya Sen)則發現,我們每個人其實就是一個“復雜的多元結構”,特定的身份不可避免地是多元的,這也就決定了個人身份的確立具有復雜性與非固定性。單一受眾身份的形成,既與個人經歷、特質相關,也與其所處的群體相聯系。經由受眾群體內部的個體符號交流,以及受眾個體與傳播主體之間的符號互動,個體不斷修正被賦予的“構筑”。其中群體內部共同的思想空間與認知環境幫助塑造了受眾的“思想地貌”,使得同一受眾在不同的群體中具有不同的個體身份。二是受眾的社會層面。從受眾的內部構成來看,受眾身份具有層次性,復合受眾有次群體,次群體有單一受眾,單一受眾又有復雜多元的身份結構。佩雷爾曼認為受眾是“說者有意通過自己的論辯加以影響的所有那些人構成的一個組合”。每一個單一受眾既是獨立的個體,又彼此存在關聯,個體的受眾基于群體內共享的符號意義,在相互傳播與交流的過程中逐漸彌合了次群體成員之間的信仰沖突,也消解了獨立受眾的個性沖突,形成具有彼此認同感的意義探究社群。而意義探究社群內部則往往存在規約性的符號意義機制,符號成為聯結群體內部各部分的紐帶。
數字技術的發展,實現了由“傳統人”到“數字人”的轉變,受眾的權力明顯增強,并逐漸成為屬性多重、身份多樣、構成多元、功能復雜的群體。這些群體以共同的品牌話題形成虛擬化的聚集——品牌社群。社群內部存在多種符號行為,包括個體受眾與傳播主體、個體受眾與個體受眾間的符號互動交流行為,個體在社群內部逐漸完善了其身份特征。數字傳播時代,品牌價值實現的關鍵在受眾,而受眾需求的充分滿足,由內容與需求的適配程度所決定。雖然大數據、云計算等數字技術能極大地實現需求的精準匹配,但關于受眾本身的分析,是實現傳播效果的關鍵。因此,受眾的身份問題仍是關乎于品牌修辭效果實現的核心問題。其中技術是促使受眾關系變化的主要推力,符號則是表征受眾,解構受眾并逐步完善受眾身份特征的重要手段。
三、認識維度:符號與技術
通過對品牌修辭基本問題的分析,發現符號與技術幾乎貫穿于分析的全過程,那么符號與技術在品牌修辭的形成與發展過程中起著怎樣的作用?對于這一問題的回答,首先應該回到符號與技術的本質,以及符號與技術間的關系層面,以此厘清品牌修辭的內在發展邏輯與基本規律。
符號學家皮爾斯(Charles S.Peirce)認為符號由“符號形體”“符號對象”“符號詮釋”組成,其中“符號形體”是符號的外在形象,為符號的可感知項;“符號對象”是符號的內容,為符號所代表的“另一事物”;“符號詮釋”是符號的解釋項,也是符號使用者對符號所作的解釋。三者的關系表現為:“符號形體”表征“符號對象”;“符號對象”是“符號形體”所傳達的思想或意義;“符號詮釋”經由符號主體(解釋者)的意識作用,在“符號形體”與“符號對象”之間不斷建立新的意指關系,形成新的價值與意義。在解釋項的作用下,符號具有了可衍義性與可再生產性,呈現出動態、開放的意義結構。因此,“符號被認為是攜帶意義的感知:意義必須用符號才能表達,符號的用途是表達意義”。符號主體賦予符號某種特定的意義,或在已有符號意指關系的基礎上,根據具體情境完善、調整其意義體系,以減少交流中的不確定性。在意義的生產過程中,符號始終在主客體之間起著聯結、交流的作用。
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用“座架”來形容技術,認為技術是自然、世界和人的構造方式,彌散在人類的生活之中。也就是說,技術以整體性的形式存在并聯結著社會的每一個個體,決定著人與時間、空間、其他個體、物質世界的關系,是社會生活的環境與圖底。技術進化的邏輯在于人類的需求驅動,技術進步最終導向的是人類關于物質世界的解蔽。因此,技術既構造了人的生存方式與關系世界,也提供了介入物質世界內部的思路與手段,后者體現了技術的工具性特征。
(一)符號:基本表意單位
修辭是一種抽象的思維,本身不具備實體化的外在形態,需要符號進行具象化的詮釋。符號是修辭具象化表現的基本元素與載體。品牌是一種具有任意理據性的特殊符號系統,內部承載著豐富的意義與意義生產機制。因此,符號連接著品牌與修辭,是品牌信息修辭化的基本表意單位。
作為意義的載體,符號是修辭進行具象化呈現、感知的主要方式,也是促使修辭由“勸服”轉向 “同一”、由語言修辭走向多維修辭的內在驅動,更是實現修辭目標的重要介質。傳統修辭學著力于單向性的“勸服”研究,主要表現方式為語言符號,修辭即為運用語言符號實現主體意圖的過程,修辭主客體之間缺乏交流互動。在古典修辭時期,符號系統的發展速度緩慢,符號的功能受到制約,反過來也影響了修辭“勸服”的效用。19世紀與20世紀之交,修辭開始復興,并向新修辭學轉化,修辭的本質由單向的“說服”走向雙向的“交流”。新修辭學奠基人肯尼斯·伯克(Kenneth Burke)將修辭學的研究對象從基于單一線性認知邏輯的語言修辭領域轉向復雜多維的新修辭學領域,突破了傳統語言修辭的束縛,而體現一切“象征行為”的符號系統是修辭擴散的基礎。在伯克看來,“人是制造象征的動物”,而修辭就是“用符號誘使那些本性能對符號作出反應的動物進行合作。”符號系統擴大的前提是人的象征能力的提升,而符號系統的豐富使得修辭突破了語言修辭的范圍。修辭需要通過符號進行展現,因此,修辭是一種思維、一種手段,也是一個過程,而符號是修辭表征、感知的手段與方式。區別于古典修辭學,新修辭學以“同一”為核心,強調了主客體間的雙向交流,客體意義的反饋為符號意義的協商提供了條件,相對穩固的符號意指關系在主客體協商的過程之中得以完善,不確定性進一步消除,修辭的目標得以最大化地實現。
符號是品牌相關信息的載體,意義是符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信息本身具備意義,因而品牌具備了符號的屬性,是制造消費者認同的重要介質。“品牌”一詞源自古挪威語“brandr”,意為“打上烙印”。古代人們在牲畜或工具上打上烙印,用以宣示其所有權,這個烙印本身就是一種符號標記。隨著社會生產的漸次發展,商品交換日具規模,品牌作為商標印記迅速被普及,并產生了無形的附加價值,逐漸成為市場競爭中的一個重要概念,品牌由單純的符號標記開始具有了表意的功能。技術的快速迭代使得市場競爭愈加激烈,品牌的概念內涵趨于復雜,根據傳統品牌階段對品牌的界定,品牌是信息的有序集合,這些信息包括了名稱、標識、圖像、服務承諾以及文化內蘊等要素。其中名稱、標識、肖像是品牌符號的形式,也是品牌符號化的基礎,與產品(服務)一起構成了品牌的再現體。而品牌圖像、服務承諾、品牌精神、品牌營銷方式以及品牌文化等則是品牌符號的內容,品牌符號的解釋項需要由品牌利益相關者共同發揮作用形成。區別于自然符號、文化符號或約定符號,品牌是一種被人工創造出來的純符號,僅具有符用層面的理據,即符號與對象之間的理據。品牌本身并不具備意義以及意義生成的功能,其意義的形成與確定均需要依賴以人為中介的意識系統。步入數字傳播時代,品牌逐漸成為品牌利益相關者的關系集合,即以品牌價值為核心的關系社群。其內部成員在遵守社群內部共同交際規則的基礎之上,彼此進行關于意義的互動協商行為。如此品牌由純符號走向具有成熟意義生產機制的符號體系。
(二)技術:根本驅動力
技術的根本驅動體現在技術的發展從根本上增強了品牌信息的修辭能力,提升了品牌傳播的效果。修辭能力指的是修辭對于品牌的裝置能力,包括了修辭表現能力與修辭組合能力,其中修辭表現能力需要以符號為載體進行具體體現,修辭組合能力則是對個體的符號進行策略化組合的能力,也即修辭的技巧與手法,是修辭的“句法”。
技術以一種底層的思維圖式,構筑著人的精神世界,通過促進媒介形態的變化,賦予符號新的表現形式、意義機制與組合配置,幾乎每一次的技術變更都能帶來新的修辭裝置和修辭的能力不斷增強。在技術發展的初期,商品所有者以身體、實物等為媒介進行信息的傳遞,語言符號是最主要的符號表意系統,信息組合的方式為同一媒介形態內符號的簡單疊加,品牌信息的修辭能力極為有限。在大眾媒介技術時期,人們以報紙、廣播和電視等為媒介進行信息的傳播,符號系統從語言符號擴散至語言、圖像與聲音等結合的視聽符號領域,并形成了相應的表意、釋義機制與裝置規則。符號的表意能力增強,符號與符號之間的聯結開始具有了策略性與技巧性。在“萬物皆媒”的互聯網技術時代,互聯網媒介從傳統媒介平臺開始向著平臺媒介的方向迅速升級,介質與應用之間實現分離。符號與符號之間可以跨越同一媒介形態、同一空間維度進行多元化的組合(新媒介修辭)。這一時期的技術以一種精神化的實質為符號的表意與組合提供了更廣闊的裝置空間,修辭的能力得以空前提升。
(三)演進邏輯:符號與技術的聯結機理
技術構建了人們感知、溝通現實世界的底層思維,技術物是這種思維方式的外化實體,而符號則是解蔽現實世界的主要介質與渠道。技術的外在表現形式是技術物,技術內部則蘊含著隱性的符號結構,符號結構使得技術物可被人們所感知。符號系統指涉信息意義,技術物充當著儲存與傳播符號的中介工具,是符號載體的物質類別,符號需要依附于技術物進行意義的傳遞。符號系統隨著技術與文化系統組織形式的發展而產生階段性的變化,其中技術對于符號的變化發展起著根本性的推動作用。技術的發展帶來傳播關系的變化,符號系統的衍義能力增強,原有的符號意指關系斷裂,而后又通過象征與交流的方式實現新的意指關系的重聚,新的符號層出不窮并迅速獲得理據性與規約性,符號系統內部不斷調整與擴充。作為實體的技術物并不存在于人們的感知世界,必須要通過符號這個介質作用于人的感知系統,從而對相應的技術內容進行認識,其中感知環境是技術認識形成的背景環境。當開始感知到技術功能的不足,出于自身發展的需要,人們便開發新的技術或完善已有技術的功能,技術得以進步,人們的符號表征、感知以及釋義能力也得到了極大的提升。
在技術發展的早期,人們主要以身體、實物等為介質進行商品信息的單向傳遞,技術載體與符號內容的界限模糊,如吆喝販賣,市聲廣告以及實物標志等。其中吆喝販賣通過口頭吆喝傳遞商品信息,市聲廣告通過樂器發聲吸引消費者注意力,實物標志則以陳列實物或以實物為器具鑄就相關印記。這一時期,技術被視為一種特殊的符號,直接作用于商品信息的生產與傳播,其表現能力、傳播能力有限,品牌的意識尚未正式形成,修辭的滲透更傾向于一種無意識的介入,修辭技巧和符號印記的運用往往缺乏規律性與系統性。當技術逐步發展,技術的力量開始顯現并日益強大,以技術物為物質載體進行的符號表現及傳遞變得普遍與靈活,品牌認知得以形成。技術物與符號系統開始分離,主要體現在物質載體與意義內容的分離,這一現象極大地提升了信息傳播的能力,傳播開始突破時間與空間的限制,效力得以增強,影響也逐步擴大。技術成為推動品牌修辭發展的顯性因素,一方面,技術使得品牌由單純的符號印記,成為相關信息的集合,品牌符號的意義生成機制逐漸成型;另一方面,符號為了適應技術的發展框架,以相應的形式進行信息的呈現與傳播,符號系統得以擴大,符號形體與媒介渠道更為契合,符號表意能力增強。這一時期,品牌主體開始在品牌行為中有意識地運用修辭的手法與技巧,以實現勸服消費者的目的。品牌與修辭的融合程度加深,但修辭的滲透仍然停留在修飾技巧的介入層面。
自人類步入信息化時代以來,數字化的高速發展帶來了技術的進一步革新,品牌成為關系、信息等多方要素的集合,品牌生態系統的概念形成。與此同時,符號載體不斷更新,符號系統愈加豐富而立體,符號表征能力空前強化,技術與符號內容之間愈加分離。技術通過增強符號形式的表現力而強化品牌信息修辭化的效果,這是一種間接促進作用。符號載體與實際應用之間逐步分立。符號借助靈活的數字技術,以不同的形態在不同軟件(平臺)完成多種傳播應用,信息傳播的渠道增多,符號形式愈加靈活,并與渠道充分契合。隨著5G技術的發展,技術逐漸成為內含許多人類信息符號密碼的物的存在方式。它以一種數據化、科學化、虛擬化的形態介入信息的傳播,構建與信息接收者交互的虛擬場景,通過場景內立體化、全能化的多維符號形態,與其產生感官與意識的聯動,形成物理的離身與意識的沉浸,以此完成在場的溝通。這一階段,人的身體成為信息傳播的重要節點,并以此為核心融合多種符號,進行跨媒介、跨場景的組合。已有的符號出現外在形態的更新,新的符號持續涌現,修辭以更為抽象、泛化的思維方式融入品牌行為,粘合了品牌利益相關主體,實現了品牌傳播效果的突破,品牌與修辭實現了更深層次的交融。
隨著技術的不斷發展,技術與符號的聯結由融合走向分立,技術由直接促進到通過作用于符號形式提升修辭的技巧與能力,這是一種間接性的作用方式。在這一過程中,品牌認知由單一的符號印記轉化為復雜的品牌生態系統,品牌與修辭的融合由技巧的無規則介入擴大至思維的全面滲透,品牌信息的表現能力與傳播能力得以極大地提升,品牌修辭逐漸演化為一個密不可分的整體。
四、結語
修辭以一種抽象的思維方式與技術手段介入品牌傳播實踐領域,并開始走向融合,最終演化為一個全新的知識概念——品牌修辭。品牌修辭專注于品牌信息的內容生產與傳播實踐,目的在于提升傳播的效果。如果說,概念的形成是理論維度構筑的基礎,那么基本問題則限定了理論維度的范圍,構成了品牌修辭的主體部分,品牌修辭以主體問題、策略問題、情境問題和受眾問題為基本問題,幾乎涵蓋了品牌修辭的整個過程。符號與技術是品牌修辭的認識維度,也是通往品牌修辭內部的路徑方式,其聯結方式的變化充分詮釋了品牌與修辭融合演進的內在邏輯和規律。因此,概念、問題與認識維度共同構成了品牌修辭的理論分析框架。
注釋:
① 姚曦、鄧云:《品牌傳播研究的新范疇與新內容——基于發生學的認識圖式》,《武漢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0第4期,第74頁。
② 單波:《傳播創新藍皮書:中國傳播創新研究報告(2020)》,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0年版,第76頁。
③ Corbett,E.P.J.& R.J.Connors.ClassicalRhetoricfortheModernStudent.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p.21.
④ 鞠玉梅:《修辭的本質與功能——兼論修辭與和諧社會的構建》,《福建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版),2007第6期,第79頁。
⑤ [法]德勒茲,加塔利:《資本主義與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姜宇輝等譯,上海書店出版社2010年版,第37頁。
⑥ 幸小勤、馬雷:《“問題”理論研究及其未來走向》,《重慶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第6期,第133頁。
⑦ 許松:《從灰色地帶邁向問題域:論后現代思潮中傳播理論整合》,《國際新聞界》,2019第5期,第14頁。
⑧ 郭湛:《主體性哲學———人的存在及其意義》,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53頁。
⑨ 米哈依·洛特曼、湯黎:《主體世界與符號域》,《符號與傳媒》,2013第1期,第15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