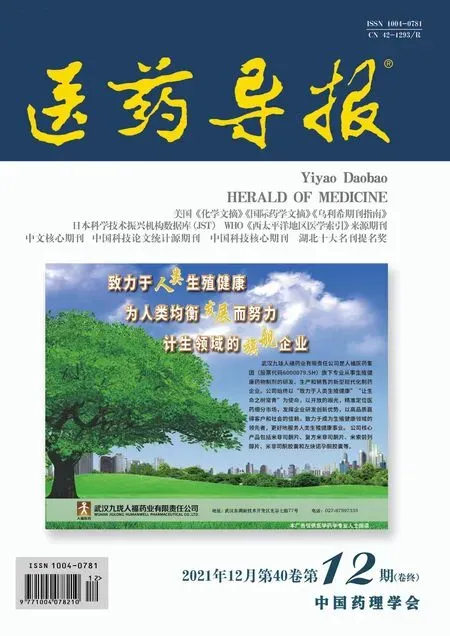丙戊酸鈉聯(lián)合拉莫三嗪致中毒性表皮壞死松解癥1例
趙亞錚,李婷婷
(華中科技大學(xué)同濟(jì)醫(yī)學(xué)院附屬同濟(jì)醫(yī)院藥學(xué)部,武漢 430030)
1 病例介紹
患者,女,31歲,抑郁癥病史3個(gè)月余,自述規(guī)律口服丙戊酸鎂治療,半個(gè)月前改為丙戊酸鈉(一日2次,上午1次250 mg,晚上1次500 mg)和富馬酸喹硫平(每晚1次,每次200 mg),10 d前加用拉莫三嗪(初始劑量為每日12.5 mg,第7天加量至每日25 mg)。加用拉莫三嗪第7天,患者頸部出現(xiàn)片狀水腫型皮疹伴瘙癢,體溫最高39.6 ℃,皮疹數(shù)小時(shí)內(nèi)蔓延至顏面部、軀干、四肢,部分皮疹融合成大片并出現(xiàn)散在破潰和滲液,口腔黏膜糜爛,無法進(jìn)食。2019年10月8日在外院就診,予以馬來酸氯苯那敏、注射用維生素C及復(fù)方氯化鈉(林格液)等對(duì)癥處理,病情未見明顯好轉(zhuǎn),2019年10月9日到我院就診,所有藥物已停用3 d,門診以多型紅斑收入院。患者無食物藥物過敏史。
入院體格檢查:患者神志清醒,體溫39.4 ℃,脈搏110次·min-1,呼吸20次·min-1,血壓99/67 mmHg(1 mmHg=0.133 kPa)。皮膚科情況:面部、軀干見較廣泛分布大小不一片狀水腫性暗紅斑、斑丘疹,部分紅斑基礎(chǔ)上見散在小水皰;四肢見散在小片狀紅斑、斑丘疹;口腔黏膜腫脹,見散在糜爛面,上覆較多黃白色分泌物;眼部、外陰、肛周見片狀糜爛面,眼部結(jié)膜明顯充血。實(shí)驗(yàn)室檢查:白細(xì)胞計(jì)數(shù)14.60×109·L-1,中性粒細(xì)胞百分比87.2%,中性粒細(xì)胞12.73×109·L-1,淋巴細(xì)胞% 4.2%,單核細(xì)胞1.22×109·L-1,血鉀3.48 mmol·L-1,血鈉135.2 mmol·L-1,血鈣2.09 mmol·L-1,高密度脂蛋白0.82 mmol·L-1,碳酸氫根20.2 mmol·L-1。肝功能無明顯異常。血糖測(cè)定6.48 mmol·L-1。超敏C反應(yīng)蛋白265.9 mg·L-1,鐵蛋白238.6 μg·L-1,白細(xì)胞介素6(IL-6)311.50 pg·mL-1。降鈣素原3.41 ng·mL-1。凝血功能:D-二聚體定量1.12 μg·mL-1FEU,凝血酶原時(shí)間14.9 s,纖維蛋白原5.27 g·L-1,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時(shí)間51.6 s。尿常規(guī):紅細(xì)胞(隱血)2+,尿蛋白2+,尿葡萄糖4+,尿酮體2+,紅細(xì)胞計(jì)數(shù)159.9·μL-1,白細(xì)胞計(jì)數(shù)46.60·μL-1。CT-胸部及心臟平掃檢查診斷:右肺中葉及雙肺下葉感染,右側(cè)胸膜增厚、粘連,心包少量積液。皮膚創(chuàng)面分泌物細(xì)菌培養(yǎng):肺炎克雷伯菌檢出。患者反復(fù)高熱,病情進(jìn)行性加重,紅斑融合成大片,其上發(fā)水皰、大皰,尼氏征陽性,出現(xiàn)大面積表皮松解。口腔糜爛加重,面積擴(kuò)大。臨床診斷為大皰表皮松解型藥疹、肺部感染、低蛋白血癥、電解質(zhì)紊亂、貧血、角膜炎、抑郁癥。治療方案:①糖皮質(zhì)激素+抗感染治療,給予甲潑尼龍琥珀酸鈉40 mg×2 d→100 mg×8 d→逐步減量、2次·d-1靜脈滴注,替考拉寧200 mg、qd,靜脈滴注2周,比阿培南300 mg、3次·d-1靜脈滴注2周的抗感染治療;②入院第4天加用丙種球蛋白20 g、qd,5 d,靜脈滴注的大劑量沖擊治療調(diào)節(jié)免疫功能,后減量至5 g、qd,5 d,靜脈滴注;③對(duì)癥支持治療:靜脈給予復(fù)方甘草酸苷、維生素C、葡萄糖酸鈣、人血白蛋白、氯化鉀的對(duì)癥支持治療;④對(duì)癥局部治療:同時(shí)外用魚爐洗劑、夫西地酸、苯扎氯銨溶液、康復(fù)新液、重組人表皮生長(zhǎng)因子外用溶液、普拉洛芬滴眼液、重組人表皮生長(zhǎng)因子滴眼液進(jìn)行局部治療。入院第5天,患者體溫下降至36.8 ℃,炎性指標(biāo)及凝血功能好轉(zhuǎn)。第15天,患者肺部感染較前吸收,停用抗菌藥物。第22天,患者面頸、軀干、四肢見散在淡紅斑,其上見細(xì)碎及片狀脫屑;眼部、肛周糜爛面已愈合;舌部、外陰見散在片狀糜爛面,無明顯分泌物。予以出院。患者出院后1周,調(diào)整抗抑郁癥用藥為:丙戊酸鎂緩釋片(一日2次,每次0.25 g),奧氮平片(每晚1次,每次2.5 mg),奧沙西平片(每晚1次,每次15 mg)。后未見不良反應(yīng)發(fā)生報(bào)告。
2 討論
本文病例為雙相障礙抑郁發(fā)作患者,藥物聯(lián)用的具體用藥史為:使用丙戊酸3個(gè)月余后合用富馬酸喹硫平,1周后又加用拉莫三嗪,使用拉莫三嗪第7天即發(fā)生嚴(yán)重皮膚不良反應(yīng)。丙戊酸在本案例中用于治療與雙相障礙相關(guān)的躁狂發(fā)作,其相關(guān)皮膚不良反應(yīng)常見的有超敏性、一過性和(或)劑量相關(guān)的脫發(fā),指甲和甲床的疾病,罕見引起中毒性表皮壞死松解癥(TEN)、Stevens-Johnson綜合征(SJS)、藥物性皮疹等嚴(yán)重皮膚不良反應(yīng)[1]。一項(xiàng)丙戊酸與SJS的系統(tǒng)回顧性研究顯示[2],在所有相關(guān)的19例病例中,只有7例為丙戊酸單藥治療引起SJS,且SJS發(fā)生在丙戊酸治療1個(gè)月內(nèi)(多為1~3周);12例為聯(lián)合用藥引起SJS,且都聯(lián)用了拉莫三嗪。喹硫平為多種神經(jīng)遞質(zhì)受體拮抗劑,在本病例中作為丙戊酸的增效治療藥物用于雙相障礙患者,其最常見的藥物不良反應(yīng)為困倦,頭暈,口干,輕度無力,便秘,心動(dòng)過速,直立性低血壓及消化不良。與丙戊酸聯(lián)合用藥時(shí),兩者的藥動(dòng)學(xué)不會(huì)發(fā)生有臨床意義的改變。拉莫三嗪是一種電壓敏感型鈉離子通道拮抗劑,精神科常用于雙相障礙維持期的治療,有臨床試驗(yàn)表明,在喹硫平療法中加入拉莫三嗪可改善雙相障礙患者的治療結(jié)局[3]。拉莫三嗪臨床上主要用于部分性和全身性癲癇發(fā)作的單藥治療或輔助治療,其非常常見的不良反應(yīng)有皮疹,惡心,嗜睡等。拉莫三嗪的皮膚不良反應(yīng)一般發(fā)生在開始治療的前8周。一項(xiàng)關(guān)于亞洲人對(duì)抗癲癇藥物的嚴(yán)重皮膚不良反應(yīng)研究顯示[4],拉莫三嗪為第三大引起SJS/TEN的抗癲癇藥物,誘發(fā)率為10.4%,僅次于卡馬西平(carbamazepine,CBZ)的67.8%和苯妥英鈉(phenytoin sodium,PHT)的17.4%。臨床治療中,多用拉莫三嗪與丙戊酸聯(lián)合使用以增加癲癇患者的療效[5]。但丙戊酸會(huì)抑制拉莫三嗪代謝酶UDP-葡萄糖醛酸轉(zhuǎn)移酶的活性,使拉莫三嗪的平均消除半衰期由24~35 h增加至近70 h。該病例中,患者在丙戊酸和喹硫平療法中加用拉莫三嗪用于延緩新的抑郁發(fā)作,該治療方案中拉莫三嗪的推薦加量劑量為:前2周25 mg隔日一次,之后2周25 mg·d-1,第5周50 mg·d-1,第6周增至目標(biāo)劑量100 mg·d-1。患者的初始加藥劑量為12.5 mg·d-1,第7天加量至25 mg·d-1,加量后即發(fā)生嚴(yán)重皮疹。根據(jù)上述分析,該不良反應(yīng)的發(fā)生與患者在使用丙戊酸基礎(chǔ)上加用拉莫三嗪劑量過快相關(guān)。另外,該患者入院檢查時(shí),皮膚創(chuàng)面分泌物有肺炎克雷伯菌檢出。根據(jù)經(jīng)驗(yàn)用藥[6],選用糖肽類抗菌藥物替考拉寧和廣譜抗菌藥物比阿培南使皮膚和軟組織感染得到控制。
影響拉莫三嗪血藥濃度的因素主要包括給藥劑量、合并用藥和患者肝腎功能等[7]。臨床上為降低嚴(yán)重皮疹的風(fēng)險(xiǎn),拉莫三嗪給藥劑量遞增應(yīng)循序漸進(jìn),切勿加量過快、過大,并盡量避免合用影響其葡萄糖醛酸化的藥物,如抑制拉莫三嗪葡萄糖醛酸化的丙戊酸鹽,誘導(dǎo)拉莫三嗪葡萄糖醛酸化的CBZ、PHT、苯巴比妥、利福平等。如需合用丙戊酸鹽,應(yīng)比拉莫三嗪?jiǎn)嗡幗o藥的劑量遞增更加緩慢[8-9]。但在丙戊酸基礎(chǔ)上,以推薦劑量加用拉莫三嗪仍能誘發(fā)嚴(yán)重的皮膚不良反應(yīng)[10],推測(cè)不良反應(yīng)的發(fā)生也與個(gè)體易感性相關(guān)。
一般認(rèn)為,拉莫三嗪引起嚴(yán)重皮膚不良反應(yīng)是由于個(gè)體對(duì)藥物的超敏反應(yīng)所導(dǎo)致的,基因水平研究發(fā)現(xiàn),人類白細(xì)胞抗原(HLA)基因與其相關(guān)。目前發(fā)現(xiàn)的相關(guān)HLA基因包括HLA-B*1502、HLA-A*2402和HLA-B*3303。HLA-A*2402是2017年發(fā)現(xiàn)的芳香性抗癲癇藥物引起皮膚不良反應(yīng)相關(guān)基因,在拉莫三嗪引起的SJS中,HLA-A*2402是檢測(cè)到的唯一顯著相關(guān)的等位基因[11]。另有研究顯示,在中國(guó)人群中,HLA-B*1502是拉莫三嗪誘導(dǎo)SJS/TEN的風(fēng)險(xiǎn)等位基因,HLA-A*2402是SJS/TEN和斑疹丘疹爆發(fā)(MPE)的重要風(fēng)險(xiǎn)等位基因,而HLA-B*3303被認(rèn)為是中國(guó)人群MPE的保護(hù)基因[12]。這為預(yù)測(cè)和預(yù)防拉莫三嗪誘發(fā)的嚴(yán)重皮膚不良反應(yīng)提供了支持。
拉莫三嗪主要作為精神科常用藥物,臨床應(yīng)用廣泛,但嚴(yán)重皮膚不良反應(yīng)屢見報(bào)道。在使用前需詳細(xì)了解患者用藥史和過敏史,高風(fēng)險(xiǎn)患者可進(jìn)行相關(guān)基因監(jiān)測(cè)。在使用過程中嚴(yán)格遵循劑量遞增的原則,特別是在合用丙戊酸時(shí)。定期檢查肝腎功能,特殊人群進(jìn)行血藥濃度監(jiān)測(cè),如低齡兒童、妊娠期患者、哺乳期患者和母乳喂養(yǎng)的嬰兒及合并用藥患者。癲癇患者用藥過程如出現(xiàn)皮疹,應(yīng)立即停藥,不推薦再次使用,同時(shí)應(yīng)慎用芳香類抗癲癇藥物,建議選擇安全性較高的非芳香類抗癲癇藥物,如丙戊酸、托吡酯和左乙拉西坦等。
(志謝:特別感謝華中科技大學(xué)同濟(jì)醫(yī)學(xué)院附屬同濟(jì)醫(yī)院皮膚科段銥醫(yī)師提供的本文病例患者不良反應(yīng)信息及治療信息,感謝武漢市精神衛(wèi)生中心心理治療師彭雪卉子提供的患者前期用藥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