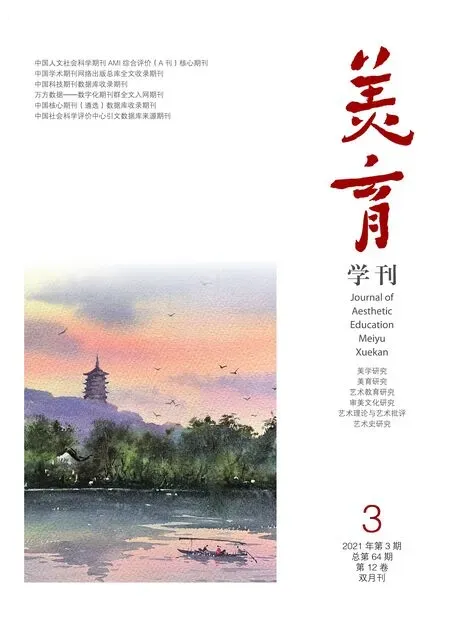中國當代藝術(shù)“中國化”問題的批評脈絡(luò)
時勝勛
(北京大學 中文系,北京 100871)
隨著全球化的不斷深入,中國文化自主性的加強,中國當代藝術(shù)民族化、本土化、中國化訴求日益強烈,并集中體現(xiàn)在中國當代藝術(shù)批評話語中。在歷史上,陸續(xù)出現(xiàn)了“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中國氣派”“中國化”等話語,它們之間的關(guān)系不是相互取代的,而是不斷深化的。雖然表面看“中國化”更加科學化,更能表現(xiàn)出中國思想的特質(zhì),而“中國氣派”則更多地側(cè)重于外在形象[1],但是“中國化”的結(jié)果必然是“中國氣派”,但不能因此就說“中國氣派”僅僅是形象的,因為“中國氣派”本身也包含精神性的內(nèi)涵,二者不應(yīng)割裂。
“中國化”的出現(xiàn)并不晚,毛澤東早在1938年的《論新階段》中就提到了。在20世紀50年代也不時出現(xiàn),比如潘梓年提出“哲學必須要有中國化的哲學”[2]。不過,此后關(guān)于“中國化”的討論并不多見,直到80年代,關(guān)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討論才越來越多。“中國化”不僅發(fā)生在馬克思主義哲學領(lǐng)域,也發(fā)生在西方哲學領(lǐng)域[3],在中國當代藝術(shù)領(lǐng)域,探討“中國化”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方面,但時間上看則更為后起。[4]但是,筆者認為,中國當代藝術(shù)批評中的“中國化”并不局限于“中國化”這一顯在的提法,也是對冠以“中國”的諸如“中國特色”“中國方式”等提法的總稱,以此呈現(xiàn)中國化的豐富性與復(fù)雜性。對其成因、內(nèi)涵、問題的分析,不僅有助于促進中國當代藝術(shù)文化與審美自覺走向深入,也有助于中國當代藝術(shù)批評話語權(quán)的提升,推進新時代中國特色當代藝術(shù)話語體系建設(shè)。
一、“中國特色”:從政治考量到學術(shù)拓展
“中國化”系列話語中最為突出的就是“中國特色”,與“中國化”相比,“中國特色”的“特色”就是政治性、意識形態(tài)色彩濃厚,尤其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樣的著名提法。在20世紀80年代,文藝界就使用“中國特色”,比如“中國特色的詩歌”。[5]這明顯是受到了主流話語的影響。在文藝領(lǐng)域,“中國特色”一般就是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美術(shù)”等。[6]受制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一政治話語的內(nèi)涵,藝術(shù)界使用“中國特色”也多著眼于意識形態(tài)方面,而單獨的中國特色藝術(shù)則使用頻率并不高,探討也不深入,在學術(shù)界影響并不廣泛。[7]今天也很少有“中國特色美術(shù)”這樣的話題。不過,近幾年“中國特色”的討論則在更為學術(shù)化的藝術(shù)學領(lǐng)域有充分展開,諸如“中國特色藝術(shù)學理論”等。[8]這源于當代對“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的重視,與前述政治性的考量是一致的,不過更加偏重于學術(shù)性,尤其是相對于西方的話語權(quán)問題。
實際上,從語言使用角度而言,單純的“中國特色”并無不可,只是在中國特定語境下,提到藝術(shù)的“中國特色”必然涉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藝術(shù)(批評、理論等)”,它鮮明地表達了中國藝術(shù)及其理論自身的主流性、政治性、意識形態(tài)特色。這并不意味著“中國特色”缺乏學術(shù)性,而是意味著它自覺的意識形態(tài)以及話語權(quán)建構(gòu)。不過,從內(nèi)涵式發(fā)展而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藝術(shù)(批評、理論)”這一稱謂還有更多的內(nèi)容需要加以充實,尤其需要兼顧政治性與學術(shù)性兩個維度。
二、“中國方式”:策略的中國化及其爭議
相比“中國特色”,“中國方式”就更為民間,也有很大爭議。20世紀90年代初,栗憲庭用“中國方式”來概括當時出現(xiàn)的“玩世現(xiàn)實主義”“波普主義”。除此之外,還有“中國智慧”“中國形象”等提法,都可以歸屬于“中國方式”模式。但是,以“玩世現(xiàn)實主義”“波普主義”等為代表的中國當代藝術(shù)在主流藝術(shù)界遭遇了持續(xù)的批評,“中國方式”的中國當代藝術(shù)是真正的中國當代藝術(shù)嗎?這引起了學者們的討論。
批評者如邱志杰、王南溟等認為,“中國方式”屬于“后殖民”,“中國方式”只不過是“中國符號”(“春卷”“打中國牌”等)而已,受制于西方中心論,這是在總體上否定了“中國方式”。[9]除此之外,對“中國方式”的負面評價還有“后東方主義”“細腰的國際主義”等提法,大部分將其納入后殖民譜系加以批評。支持者有肖豐等人。2004年,肖豐、任建軍將“中國方式”的技術(shù)前提概括為“借用”和“轉(zhuǎn)換”。“借用”,就是“借用中國傳統(tǒng)文化資源作為新的審美意象的起點或基礎(chǔ)”。“轉(zhuǎn)換”,就是“把原有文化資源中的某些具有‘符號性’特征的審美元素轉(zhuǎn)換成另一種形式的視覺語言,在保留原有的審美特性的同時,顯示出新的精神指向”,使人們在欣賞當代藝術(shù)的同時,又能領(lǐng)悟作品中文化的根源和脈絡(luò)。[10]2006年,肖豐、任建軍又進一步分析了“中國方式”的策略性價值,也回應(yīng)了當時對“中國方式”的批評聲音。[11]肖豐所在的華中師范大學美術(shù)學院也開展了中國當代藝術(shù)的“中國方式”的研究,有不少其指導(dǎo)的碩士論文涉及此問題,構(gòu)成一個小型的“中國方式”研究學派。無論是批評還是支持,從學理性角度而言,“中國方式”既然已經(jīng)存在,那就有其生存的某種合理性。批評家楊衛(wèi)則將其與中國傳統(tǒng)的退隱山林聯(lián)系起來,區(qū)別在于前者朝向西方,但又表現(xiàn)了當代性,這就是當代藝術(shù)的“中國方式”,也可以說是一定程度上的“中國化”的當代藝術(shù)。[12]在筆者看來,遭遇了全球化之后,退隱山林就一定要變成“中國方式”,恐并非如此簡單。
“中國方式”是80年代中國現(xiàn)代藝術(shù)西方化之后的一種新策略,兼顧了西方當代藝術(shù)規(guī)則與中國藝術(shù)特色,并非一無是處。實際上,中國當代藝術(shù)家?guī)缀醵忌孀氵^“中國方式”,如谷文達、徐冰、蔡國強等。[13]“中國方式”就是將傳統(tǒng)性、西方性、現(xiàn)代性(當代性)結(jié)合起來,其基本精神是現(xiàn)代性的,在其發(fā)展中,意識形態(tài)對抗性逐漸減弱,文化性、藝術(shù)性逐漸增強,因而具有較強的時代意義。可以說,“中國方式”是中國當代藝術(shù)國際化與本土化階段性的實踐經(jīng)驗和理論概括,并且影響到藝術(shù)設(shè)計等領(lǐng)域。[14]可見,“中國方式”對于中國當代藝術(shù)的創(chuàng)作與傳播都是有一定借鑒意義的,雖有這樣那樣的問題,也不可一概否定。
此外,孫振華以吳為山的雕塑為例闡釋了中國雕塑的“中國方式”,將“意”視為吳為山雕塑的核心詞,通過“意”,吳為山“改變了20世紀以來中國雕塑的觀念方式,使中國雕塑在重新發(fā)現(xiàn)傳統(tǒng)的基礎(chǔ)上,為建構(gòu)當代的、本土的雕塑方式提供了可能”。[15]吳為山的雕塑表現(xiàn)將傳統(tǒng)寫意精神融入藝術(shù)實踐的創(chuàng)作經(jīng)驗,體現(xiàn)“尚意”的中國藝術(shù)語言方式。這與當代藝術(shù)的“中國方式”(即玩世現(xiàn)實主義)并不完全一致,應(yīng)該屬于名同實異的“中國方式”。
三、“中國經(jīng)驗”:現(xiàn)代性的精神追求
如果說“中國方式”多對應(yīng)于玩世現(xiàn)實主義、波普藝術(shù),那么“中國經(jīng)驗”則對應(yīng)于西南當代藝術(shù),二者的矛盾性是比較明顯的。“中國經(jīng)驗”原不用于藝術(shù)領(lǐng)域,而是指包括中國政治、社會實踐在內(nèi)的“中國經(jīng)驗”,主要是社會主義經(jīng)驗,后來用于藝術(shù)領(lǐng)域,這是王林倡導(dǎo)的,起始于1993年在成都舉辦的“90年代的中國美術(shù):‘中國經(jīng)驗’畫展”。這一展覽在當時并沒有產(chǎn)生什么影響,直到王林的闡釋,才開始引起注意,屬于典型的批評話語。
“‘中國經(jīng)驗’畫展”共展出葉永青、張曉剛、毛旭輝、王川、周春芽五人的作品。當時展覽主題定位“中國經(jīng)驗”。所謂“中國經(jīng)驗”,王林解釋說就是“藝術(shù)家獨立精神的體現(xiàn),即對既定的生存環(huán)境和文化現(xiàn)狀的批判”,“是深度的批判的個人經(jīng)驗在藝術(shù)中的呈現(xiàn)”。[16]“中國經(jīng)驗”的提出是針對當時的政治波普以及消費文化興起對精神性的讓渡而言的,是對不滿于拷貝、復(fù)制西方當代藝術(shù)以及關(guān)注精神性、批判性的中國藝術(shù)實踐的理論概括。在20世紀90年代初,藝術(shù)界已經(jīng)感受到市場經(jīng)濟、后殖民文化帶給當代藝術(shù)的挑戰(zhàn),提出基于批判性、現(xiàn)實性、精神性的“中國經(jīng)驗”自然是藝術(shù)界對現(xiàn)實的一種反應(yīng)。批評家何桂彥指出,此次展覽的美學訴求,“首先它力圖與‘政治波普’和‘玩世現(xiàn)實主義’拉開距離,拒絕調(diào)侃化、消費化的文化態(tài)度。其次,倡導(dǎo)‘深度繪畫’,即關(guān)注藝術(shù)和人的聯(lián)系性,不放棄終極理想和精神追求,把對現(xiàn)實情境的體驗不斷轉(zhuǎn)換為精神發(fā)展的歷史標志”。[17]顯然,在中國當代藝術(shù)界始終存在著“中國經(jīng)驗”(西南當代藝術(shù))與“非中國經(jīng)驗”(玩世現(xiàn)實主義等)的沖突。
1998年,王林以裝置藝術(shù)為例提到中國當代藝術(shù)的“中國經(jīng)驗”問題,中國當代藝術(shù)開始“關(guān)注問題本身以及在藝術(shù)中關(guān)注中國經(jīng)驗和世界文化的關(guān)系”。正是在此意義上,中國當代藝術(shù)的實踐才具有“中國經(jīng)驗”的特質(zhì)。“中國經(jīng)驗”是“當代中國人作為個體存在的生存經(jīng)驗,它是局部的、具體的”,“中國經(jīng)驗”是對西方現(xiàn)代性的反思,強調(diào)多元性、多樣性的價值。“中國經(jīng)驗”重視藝術(shù)家個性、個體思維、個性創(chuàng)造,而90年代興起的觀念藝術(shù)就是“中國經(jīng)驗”的一個突出體現(xiàn)。[18]
王林一直致力于對“中國經(jīng)驗”的研究與傳播,進入21世紀之后也繼續(xù)詮釋“中國經(jīng)驗”。2003年,王林以西南當代藝術(shù)為例解釋了“中國經(jīng)驗”的四個特征:一是“始終具有濃厚的人文情懷,注重生命意識、生存境遇與藝術(shù)的關(guān)系”;二是“重視內(nèi)心體驗和主觀表現(xiàn),和即時的、流行的文化現(xiàn)實保持一定距離”;三是“看重歷史性、時間性,以中國人的歷史經(jīng)驗和個人經(jīng)歷作為資源”;四是“具有深度感和多義性,不以直接、表層、時尚的藝術(shù)效果為歸旨”。王林理解的“中國經(jīng)驗”還包括強烈的問題意識與媒體變革,“90年代西南藝術(shù)家在觀念藝術(shù)創(chuàng)作中對當代問題和媒介方式做了深入的研究,不僅擴展了西南當代藝術(shù)的領(lǐng)域,而且深化了西南當代藝術(shù)的人文精神”,“西南藝術(shù)家的創(chuàng)作不棄人文關(guān)懷、歷史責任和主體追求”。在王林看來,當代藝術(shù)有很強的思想智慧與個體自由。[19]王林的“中國經(jīng)驗”訴求有很強的現(xiàn)代性內(nèi)涵,與“五四”啟蒙精神一脈相承,并非執(zhí)著于對傳統(tǒng)資源的恢復(fù),注重的是當代中國藝術(shù)對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中國與西方復(fù)雜關(guān)系的創(chuàng)造性轉(zhuǎn)化。
2005年,王林的文集《從中國經(jīng)驗開始》出版,使得“中國經(jīng)驗”成為一種較為系統(tǒng)、自覺的本土化話語。在文集前言,王林批評了東方主義,認為中國當代藝術(shù)表面繁榮的國際化可能墮入了東方主義陷阱,“西方選擇和東方迎合的共謀性,將取消或改寫東方文化的自身特質(zhì)”。但是,王林對東方主義的批判并不會重回傳統(tǒng)的民族主義或保守主義,而是促進文化多樣性。[20]在此背景下,王林強調(diào)的是“中國經(jīng)驗”,是本土精神的當代闡揚,而非復(fù)古。“本土文化、中國經(jīng)驗和東方智慧”在東方主義視野中并沒有自己的位置,有的話也只是邊緣地位。王林強調(diào)的“中國經(jīng)驗中的文化智慧”對于回應(yīng)中國當代藝術(shù)的后殖民傾向與西方中心論是有積極意義的。
在藝術(shù)界討論“中國經(jīng)驗”,并未局限于西南當代藝術(shù)流派。比如畫家楊渝詮釋了90年代末以來中國藝術(shù)介入社會現(xiàn)實問題的“中國經(jīng)驗”,藝術(shù)創(chuàng)作也更加關(guān)注個體經(jīng)驗。[21]林世賓通過對“溪山引”展覽作品的分析,探討了中國當代藝術(shù)的“中國經(jīng)驗”呈現(xiàn)與中國文化表達。他明確反對那種戲謔的、潑皮的、艷俗的、時尚包裝的方式來進行“中國經(jīng)驗”呈現(xiàn)。關(guān)于中國文化表達,林世賓認為應(yīng)該從林風眠、趙無極等人開創(chuàng)的道路出發(fā),“中國藝術(shù)的現(xiàn)代性道路就是在現(xiàn)代背景下尋找中國藝術(shù)主體身份的努力,是中國開創(chuàng)具有人類未來文化意義在藝術(shù)上的表達”。[22]
此外,“中國經(jīng)驗”也溢出了藝術(shù)界,有一些學者介入“中國經(jīng)驗”的討論,比如傅謹關(guān)于戲劇的“中國經(jīng)驗”的討論[23],張檸關(guān)于莫言小說的“中國經(jīng)驗”的討論[24],大抵都是強調(diào)中國藝術(shù)的本土性、民間性價值,但都還沒有明確“中國經(jīng)驗”的理論價值,更多的只是一種口號。
“中國經(jīng)驗”不是一種封閉的、固定的,而是一種開放性的狀態(tài)。關(guān)于“中國經(jīng)驗”的階段,王岳川將其分為三大階段:一是“純粹古典高雅、逍遙自足的中國傳統(tǒng)經(jīng)驗”;二是“經(jīng)歷了歐風美雨痛苦和希望交織的中國現(xiàn)代性經(jīng)驗”;三是“整合傳統(tǒng)文化經(jīng)驗和百年西化經(jīng)驗變成自身的文化資源,納入國際化學術(shù)文化資源和知識資源空間,用人類普世化的知識表達中國立場和中國經(jīng)驗”。[25]這三個階段的“中國經(jīng)驗”可以概括為傳統(tǒng)性經(jīng)驗、現(xiàn)代性經(jīng)驗和當代性經(jīng)驗。傳統(tǒng)性經(jīng)驗是原汁原味的,現(xiàn)代性經(jīng)驗是西方化的,當代性經(jīng)驗是一種新的生成,是在西方化與中國性中找到適當?shù)钠胶狻?/p>
“中國經(jīng)驗”作為中國當代藝術(shù)本土化的一種體現(xiàn),多數(shù)并不是將其引到傳統(tǒng),而是更強調(diào)現(xiàn)實性。這種現(xiàn)實性與中國的現(xiàn)代性經(jīng)驗特別是特定的個體生命經(jīng)驗密切相關(guān)。當然,后來隨著“中國經(jīng)驗”的泛化,一些與現(xiàn)代性內(nèi)涵較遠的內(nèi)容也加入進來,比如社會主義、民族性、傳統(tǒng)性的文學藝術(shù)本身的“中國經(jīng)驗”問題等。[26]這導(dǎo)致了“中國經(jīng)驗”自身的復(fù)雜性和矛盾性,同時也可能意味著“中國經(jīng)驗”的無限擴大而面臨著話語權(quán)的爭奪,甚至概念本身的自我消解。
四、“中國版本”:立足文化血脈的自主性嘗試
“中國版本”是2003年由陳孝信提出來的一個概念,強調(diào)傳統(tǒng)性與當代性的融合,在一定意義上是“中國方式”的升級版,但弱化了意識形態(tài)沖突的內(nèi)容,相反增加了文化的內(nèi)容。與這個概念相關(guān)的還有“文脈”“超寫意”等詞,共同構(gòu)成了“中國版本”的完整內(nèi)容。
在陳孝信看來,“文脈”是中國藝術(shù)實踐長期積累、傳承的“內(nèi)核”,這一內(nèi)核主要就是中國藝術(shù)精神。當然,“文脈”并不是單一的,而是多元的,諸如儒、釋、道、民間等。這個“文脈”在現(xiàn)代中斷了,出現(xiàn)了三種情況,一是西化,二是中西融合,三是重復(fù)傳統(tǒng)。西化自不必言,完全沒有“文脈”,繼承的是西方的“文脈”。中西融合也是缺乏“文脈”的,只是國際版本的“中國變體”,缺乏原創(chuàng)性。重復(fù)傳統(tǒng)雖有“文脈”,但卻是死的,不是開拓型的。陳孝信在否定了這三種傾向之后,提出自己的“中國版本”,所謂“中國版本”,就是對西方、傳統(tǒng)的超越,這個超越強調(diào)創(chuàng)造性。這個“中國版本”的突出方面就是“文化個性”,即“一個民族或一個國家當代藝術(shù)總體上的差異性和豐富多樣性”。[27]即便在西方,國家與國家之間的當代藝術(shù)也不一樣,所以陳孝信提倡要“國別化”,而不是一味國際化,這是一種既超越狹隘民族主義的開放的民族主義的立場。
至于如何“國別化”,如何體現(xiàn)“文化個性”,陳孝信提出“扎根、利用、轉(zhuǎn)換”三原則。扎根是深入傳統(tǒng),是前提,利用是途徑、過程,關(guān)鍵是轉(zhuǎn)換,實現(xiàn)對接、創(chuàng)化。轉(zhuǎn)換就是對傳統(tǒng)、西方的雙重超越,從他策劃過的“中國版本——超寫意新藝術(shù)邀請展”(2003)、“中國版本——滬、寧、杭超寫意藝術(shù)現(xiàn)象展”(2004)、“中國版本——2005北京邀請展”、“文脈當代·中國版本”大型綜合藝術(shù)展(2007)等可以看出,這些展覽的關(guān)鍵詞是“中國版本”“超寫意”“文脈”等。“文脈”是根,“超寫意”是實踐,“中國版本”是最終呈現(xiàn)狀態(tài)。
“中國版本”是西方藝術(shù)本土化也是傳統(tǒng)藝術(shù)精神當代化的雙重體現(xiàn),這種思路就是從“國際版本的中國樣式”走向“中國版本的國際樣式”。為了詮釋這一“中國版本”,他做了很多個案的分析,比如谷文達、申偉光等,顯然“中國版本”的當代性、藝術(shù)性要更強一點,而且文化性又是經(jīng)過當代性、藝術(shù)性過濾的,因此才容納了一些當代藝術(shù)類型。
五、“中國風格”:審美多樣性的呈現(xiàn)
“中國風格”與“中國氣派”接近,但“中國風格”更加強調(diào)美學風貌,且屬于后起話語。“中國風格”是2010年前后提出的概念,具有很強的主流性。2010年,“中國風格·時代丹青——全國優(yōu)秀美術(shù)作品展覽”在廣州藝術(shù)博物館隆重開幕。這是首次以“中國風格”為主題的中國當代美術(shù)展。
為什么要提出“中國風格”?張曉凌認為有兩個背景,一是20世紀90年代“瀆神、潑皮、解構(gòu)、艷俗之風廣為流行”,這就是前文提及的“中國方式”,二是“晚明以來中國數(shù)代美術(shù)家所積累起來的現(xiàn)代性經(jīng)驗”,主要是徐悲鴻、劉海粟等人的中西融合風格。可見“中國風格”不是空中樓閣,而是有深刻的現(xiàn)實針對性與文化動因。“中國風格”的提出,也必然使得中國當代藝術(shù)自覺審視自我本土的現(xiàn)代性經(jīng)驗,同時應(yīng)對西方化的沖擊。因此,張曉凌認為在此背景下的“中國風格”其文化戰(zhàn)略意圖是明確的,一是反對后殖民風,二是總結(jié)中國百年現(xiàn)代性經(jīng)驗,三是建構(gòu)有東方美學意蘊的中國當代性經(jīng)驗,最終“在全球化語境中,做大做強中國美術(shù)主體,并使其價值觀具有普世性”。[28]
“中國風格”提出后得到了積極的學術(shù)回應(yīng),主要集中于文化立場與美學內(nèi)涵兩個方面。在美學立場上,盧禹舜認為“中國風格”“是美術(shù)的國家形象,體現(xiàn)了主流文化在當下創(chuàng)作上的指導(dǎo)意義,優(yōu)秀的民族文化、傳統(tǒng)精神在美術(shù)創(chuàng)作中具有主導(dǎo)作用,弘揚民族文化精神,增強民族文化自信,在當代傳承創(chuàng)新發(fā)展中縱向延伸為中國風格,有其歷史意義”。張江舟認為“中國風格”“體現(xiàn)了中國文化主體意識的回歸,是當代美術(shù)發(fā)展歷程中對民族立場、國家意識的一種自覺選擇,體現(xiàn)了一個東方大國對本民族優(yōu)秀文化精神傳統(tǒng)的尊重”。在審美內(nèi)涵上,王鏞認為“中國風格”體現(xiàn)為兩類,一是寫實風格,二是寫意風格,抽象風格則很少。相比寫實、抽象風格,王鏞認為“寫意精神是一種高度自由的創(chuàng)造精神,在某種程度上來講,它應(yīng)該是構(gòu)成中國風格的核心”。不過,王鏞也強調(diào)不能唯寫意,他認為現(xiàn)代藝術(shù)有兩個基本特征,即“強化個性”“簡化形式”,這實質(zhì)上就是當代藝術(shù)的基本精神。陳池瑜則認為“中國風格”主要是寫實風格,“打造中國美術(shù)的民族風格或者時代風格,現(xiàn)實主義是一個很好的、不可或缺的點”。尚輝認為“中國風格”就是“中國特色”,“是古今中外的一次整合,是一次新的更高程度的整合”。(1)關(guān)于“中國風格”參見《第九屆中國藝術(shù)節(jié)“中國風格·時代丹青——全國優(yōu)秀美術(shù)作品展”研討會綜述》,載《美術(shù)報》,2010年6月26日。尚輝的觀點應(yīng)該是毛澤東“中國氣派”在美術(shù)上的體現(xiàn),在某種程度上表明了二者的邏輯脈絡(luò)。
此外,與“中國風格”接近的是“中國風”,強調(diào)中國當代藝術(shù)要融入“中國因素”。聶琦峰將中國風分為三類,即傳統(tǒng)觀念+現(xiàn)代形式(如吳冠中)、非傳統(tǒng)符號+當代社會性(如張曉剛)、傳統(tǒng)符號的當代化(如呂勝中)。[29]由此可見,“中國風”本身就是復(fù)雜的。多數(shù)國人還處于第一類的欣賞層次,但就藝術(shù)家而言,要積極進行第二類甚至第三類的創(chuàng)作,這有利于中國當代藝術(shù)進入世界藝術(shù)潮流,同時又彰顯了本土的創(chuàng)造性。
六、“中國精神”:對傳統(tǒng)價值的藝術(shù)激活
對“中國精神”的討論可以追溯至20世紀90年代民族精神或者“精神性”,比如文學界關(guān)于人文精神失落的討論,[30]以及油畫界關(guān)于“精神性”(涉及時代精神、民族精神)的討論等,[31]不過還沒有上升到“中國精神”高度。21世紀初以后,“中國精神”的討論逐漸出現(xiàn),[32]也有相應(yīng)的展覽,比如2012年,“中國精神——油畫風景學術(shù)研究展”在中國藝術(shù)研究院中國油畫院舉行。到了2014年,情況有了顯著的變化,“中國精神”成為主流話語。
2014年,習近平《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提到,“中國精神是中國社會主義文藝的靈魂”。這一命題突出之處在于對文藝社會主義政治、道德維度的強調(diào),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提出“中國精神”的背景是受到消費主義、全球化的挑戰(zhàn),本土價值觀開始滑坡這一嚴峻的社會現(xiàn)實。關(guān)于文藝如何做到有“中國精神”,習近平在講話中提到四點,一是愛國主義,二是對真善美的追求,三是汲取傳統(tǒng)文化資源(2)傳統(tǒng)文化資源又集中體現(xiàn)在中國美學精神上:“中華美學講求托物言志、寓理于情,講求言簡意賅、凝練節(jié)制,講求形神兼?zhèn)洹⒁饩成钸h,強調(diào)知、情、意、行相統(tǒng)一。”見習近平《在文藝座工作談會上的講話》,http://culture.people.com.cn/n/2014/1015/c22219-25842812.html,2014年10月15日。,四是學習借鑒西方優(yōu)秀文化。由于習近平講話是一個政治文本,因而具有很強的政策引導(dǎo)性,這對于扭轉(zhuǎn)當前過于西方化、商業(yè)化的當代藝術(shù)趨勢是非常迫切而重要的。
隨著習近平總書記提倡“中國精神”之后,此觀念迅速上升為國家文化戰(zhàn)略,相應(yīng)的展覽、討論不斷涌現(xiàn)。“中國精神”也不再僅僅局限于風景油畫,而擴展至更廣泛的領(lǐng)域。2015年、2016年、2017年,“中國精神”第四屆中國油畫展分別以“心像”“真像”“抽象”為題展覽,分別對應(yīng)表現(xiàn)性、寫實性、非具象性油畫作品。油畫三大形態(tài)與“中國精神”的關(guān)系是中國藝術(shù)對油畫的百年篩選的結(jié)果,并非寫實一類。楊飛云在肯定三大形態(tài)的價值之后,也反思了三大形態(tài)自身的某些問題,“寫實油畫泛起的圖像化、精工化,媚俗(媚雅)化的實形主義,而冷靜甚至缺乏真正的激情;表現(xiàn)性油畫興起的求怪求異的蒼白表象與恣意宣泄,而弱化甚至放棄了情感的高貴而率直表達;抽象油畫泥于語言之放,缺失形而上的內(nèi)質(zhì)追求,放言而忘意趣,空泛玄虛等,出現(xiàn)了在繪畫語言和語言背后的文化觀念、精神內(nèi)涵、個人情感、民族傳統(tǒng)積淀的關(guān)系失衡的現(xiàn)象”。[33]2015年,當代藝術(shù)家韋申個展舉行,他也強調(diào)中國當代藝術(shù)“應(yīng)該是注重中國精神的,應(yīng)該注重東方文化的價值觀”。(3)參見《韋申個展開幕 稱中國當代藝術(shù)應(yīng)注重中國精神》,http://www.chinanews.com/cul/2015/05-30/7311512.shtml,2015年5月30日。他的作品在荒誕怪誕、超現(xiàn)實主義中隱含了東方的自然自由精神。2016年,“‘中國精神’2016·中國百家金陵畫展(中國畫)”在江蘇省美術(shù)館舉辦,彰顯中國畫面向現(xiàn)實、服務(wù)于中國社會主義文化建設(shè)的藝術(shù)態(tài)度。2018年,朱樂耕在政協(xié)全國會議上提議要將“中國精神”融入當代藝術(shù)創(chuàng)作之中,并注重國家層面的導(dǎo)向機制。[34]這應(yīng)該是比較明確地強調(diào)當代藝術(shù)融入“中國精神”的看法。
“中國精神”體現(xiàn)在兩個方面:一是文化資源上的發(fā)揚傳統(tǒng)。尚輝強調(diào)要“塑造當代美術(shù)的中國精神”,他認為“儒家的天人合一、道家的有無相生、釋家的虛齋坐忘,從來都是中國藝術(shù)的文化魂靈”,中國當代美術(shù)應(yīng)從此再出發(fā)。[35]邵大箴強調(diào)當代油畫的“中國精神”的綜合路徑,即“運用毛筆作畫的,力圖從國外藝術(shù)潮流中吸收營養(yǎng),進行藝術(shù)變革;執(zhí)油畫筆與刮刀的,卻在精神的旅途上,渴望向著民族傳統(tǒng)回歸”[36],這是中西融合的新創(chuàng)造。二是“中國精神”的美學內(nèi)涵,邵大箴認為劉文進的“意象油畫”尤其能夠體現(xiàn)“中國精神”,使得“中國精神”更具體地落實在“寫意精神”上。林笑初認為“靳尚誼探求中國畫的筆墨形式與油畫書寫性表現(xiàn),用油畫語言探討中國畫的寫意性與意境,對不同風格技巧和技法進行嘗試,表現(xiàn)一種特有的‘中國寫意水墨油畫’”。[37]靳尚宜的“寫意水墨油畫”是“中國精神”的嶄新體現(xiàn)。徐里不僅強調(diào)油畫中國化的意象性、寫意性實踐,還吸納了蔡國強、徐冰等人的藝術(shù)實踐,放置在“中國精神”之下,進一步擴大了“中國精神”的空間,也使其更具包容性、當代性、生命力。[38]
從總體上說,這些討論都還比較籠統(tǒng),都是宏觀討論,將“中國精神”引向傳統(tǒng)、引向?qū)懸?但具體如何操作,還是缺乏細致的分析。這一方面說明“中國精神”是一個極為龐大的理論命題,另一方面說明“中國精神”的藝術(shù)化呈現(xiàn)也是一個長期而艱難的過程,并非一時一地所能解決。
七、結(jié)語:“中國化”話語的成績與問題
以上對中國當代藝術(shù)“中國化”問題批評脈絡(luò)的梳理,說明中國當代藝術(shù)批評界都試圖給中國當代藝術(shù)尋找某種“中國性”的價值,這種“中國性”不僅涉及意識形態(tài),也涉及學術(shù)、審美、文化,這說明近年來中國當代藝術(shù)批評日益涌動的多層面的政治、學術(shù)、審美、文化自覺。在21世紀“中華民族偉大復(fù)興”的時代語境中,“中國化”無疑彰顯了文化的自我反思意識,為中國當代藝術(shù)的健康發(fā)展營造了較好的批評氣氛,形成了21世紀以來中國當代藝術(shù)中國化的時代潮流。
當然,中國化并非完美無缺,其問題也存在:第一,命名之間并不統(tǒng)一,關(guān)系錯綜復(fù)雜,比如“中國特色”的政治性如何與“中國精神”等的文化性融合為一,而“中國經(jīng)驗”與“中國方式”之間的明顯對立如何整合,還有像“中國經(jīng)驗”“中國版本”的偏當代性與“中國精神”的偏傳統(tǒng)性如何整合,等等。第二,“中國化”系列的主要問題是過于寬泛,切割不清,容易相互混淆。這些提法中的“中國”究竟是文化的中國,還是政治的中國,或者是藝術(shù)的中國?特色、方式、經(jīng)驗、版本、風格、精神,內(nèi)部究竟有何差異?更突出的在于,這些話語幾乎缺乏美學的定位,過于抽象,與“魏晉風骨”“盛唐氣象”相比,特色、方式、經(jīng)驗、版本、風格、精神,仍然缺乏文氣,靈動與韻味不足。用中國命名,更應(yīng)該體現(xiàn)獨特的審美風貌。因此,如何將“中國化”的美學內(nèi)涵不斷充實、完善、細化、豐富,是中國當代藝術(shù)批評不得不思考的問題。第三,中國化與世界化、國際化的關(guān)系如何處理,如何克服狹隘民族主義、文化相對主義弊端以及東西方二元對立的慣性思維,尋找一種既能堅持本民族血脈,又具有跨文化性、世界性、人類性指向的中國化當代藝術(shù),尤其是在推進人類命運共同體進程中,以藝術(shù)的方式貢獻自己的智慧,是中國化實踐所無法忽視的問題。
無論是成績還是問題,有一點是明確的,中國當代藝術(shù)已經(jīng)走過40年的歷程,中國整體的內(nèi)外部環(huán)境也發(fā)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在“中華民族偉大復(fù)興”不斷深化與中國當代藝術(shù)本土化訴求日益強烈的時代語境里,“中國化”對中國當代藝術(shù)內(nèi)涵式發(fā)展與全球性推進都是積極而重要的。在某種意義上說,只有中國化的中國當代藝術(shù),才能以它獨有的特色、精神、氣韻,實現(xiàn)其時代性與世界性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