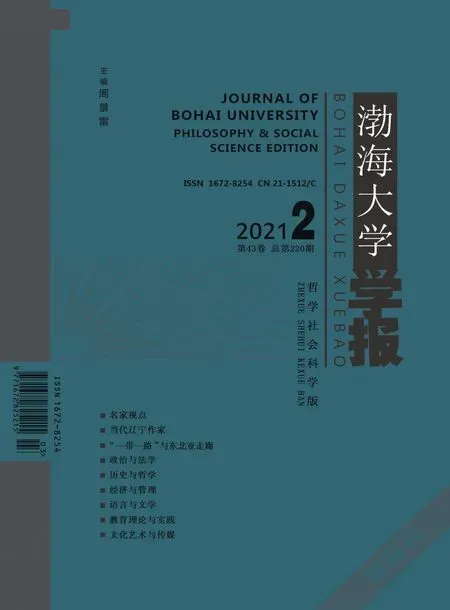農村金融效率
——一個文獻總結與展望
苗長青 閆星潼 朱寧薇(渤海大學經濟學院,遼寧錦州 121013)
2012年,中央一號文件明確指出加快農村金融體制轉變、完善農村金融服務體系是當今農村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重要保障,也是我國未來農村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有力支撐。農業是國民經濟發展的根本,在維持國民經濟的平穩運行和社會秩序的穩定等方面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與其他產業發展一樣,農業發展同樣需要大量資金支持,相較于城市地區金融服務業發展,農村地區的金融服務發展依然滯后,金融機構網點少、農村金融產品單一、服務效率低等問題長期存在,農業經濟發展缺少必要的金融服務供給。因此,農村金融效率的高低對加快我國現代農村建設、農業產業轉型升級、實現農民增收致富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農村金融效率提升直接關系到我國現階段農村主要矛盾能否順利解決。
一、金融效率的總體回顧
最早提出金融效率觀點的是美國經濟學家JG Gurley &ESShaw,1960年,在其著作Money in a Theory of Finance 中指出金融效率是在既定技術水平條件下,金融生產要素投入與效益產出之間的關系。國外對金融效率的研究始于20 世紀50年代后期,Koopmans(1957)從社會資金資源的配置與運行機制(宏觀經濟運行層面)和資源配置效率(微觀視角)來解釋金融效率的內涵[1]。從宏觀層面上來看,1973年,RIMckinnon& E S Show 提出金融抑制論和金融深化論過于強化金融自由化的發展戰略,而忽視金融效率對一國金融體系完善的促進作用。Robinson(1974)把金融系統效率分成操作效率和配置效率,操作效率是指資產資源操作過程中發生的成本效率比,配置效率是指有效引導資金資源流向生產性用途[2]。雖然Hellman 等人在20 世紀90年代提出了金融約束論,但其研究內容僅限于統計方法,整體上來看還不夠全面。就微觀層面來看,不僅包括單元或個體的資源配置方式(如對銀行或者股票市場效率的研究),還應包括金融工具的范疇、證券價格與利率的關系、收益與風險分析等方面。Charnes (1978) 運用DEA 法對不滿足利潤最大化假設條件下,公共部門或非營利部門的經濟效率進行了研究[3]。Stiglitz(1981)根據股票對信息量反映強弱程度,分為弱有效、半強有效和強有效等三種市場類型,其研究結果表明:即使在強有效競爭條件下,帕累托最優結果也不一定會出現[4]。Annim(2010)根據雙重目標將金融效率分為財務效率與社會效率[5]。
從宏觀層面上來看,對金融效率的研究主要側重于社會資源配置與社會資金運行兩方面。Ang A,Bekaert G,M Wei(2008)指出金融效率高低在一定程度上取決于金融系統資源配置功能完善程度和社會金融資金運用的合理程度[6]。對于宏觀金融效率的測度方面,Wurgler(1999)運用自身計量模型對金融效率進行測算,得出一國金融自由化的程度越高,越有利于其資本市場的發展,且能優化其資本市場配置效率的結論[7]。Allen & Gale(2000)指出市場主導主體的差異會導致金融資源配置效率的全然不同,一方面,金融政策運行空間、金融發展水平等因素會導致金融效率差異;另一方面,政府金融政策則直接導致資金市場的分割[8]。
隨著金融效率研究的逐步深入,國內學者圍繞金融效率展開分區域分層次研究,從宏觀層面來看,可分為金融資源視角的金融效率和福利經濟學視角的金融效率。白欽先(2001)認為金融效率是金融資源在經濟系統及各子系統之間配置協調程度[9]。王振山(2000)認為在優化成本前提下,有效的金融效率能夠實現帕累托最優[10]。從微觀視角上可分為制度經濟學視角下資本市場金融效率和金融要素功能視角下金融效率。李建軍、曹雁翎(2003)從市場有效性、資源配置效率及市場信息效率三個方面探討金融效率的內涵[11]。楊德勇(1999)認為金融效率是各金融要素在國民經濟運行中所發揮的資源配置功能程度[12]。
從研究基礎上來看,國內對金融效率的研究多基于內生金融理論的投入產出模式基礎上,如戈德史密斯的金融結構理論、白欽先的金融可持續發展理論等。而金融系統協調理論則是把金融資產運作能力當成整個社會經濟運行中宏觀層面和微觀視角均實現帕累托最優的衡量指標。也有部分學者從金融效率不均質分布狀態原因,著手分析研究金融效率與經濟發展水平的關系。李雪琴、方先明(2010)運用1998—2008年我國七大區域的相關經濟金融指標數據, 建立固定影響的變截距的面板數據模型,從銀行業、證券業和保險業詮釋區域金融支持與經濟發展之間的內在關聯,得出二者關系為正[13]。趙勇、雷達(2010)通過分析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影響,得出金融發展水平不同的地區,金融發展規模對金融效率的改善作用也不同[14]。陸遠權、張德鋼(2013)認為金融發展水平較低的地區,金融發展規模對金融效率影響相對較大,我國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的作用仍停留在粗放型擴張階段[15]。
二、農村金融效率文獻述評
歐美國家金融體系相對較為發達,對金融體系沒有城鄉之分。而我國由于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的存在,在對金融體系劃分時考慮城鄉金融融合發展,農村金融隨之而出,國內學者結合我國農村金融發展的具體情況,開始對農村金融及其效率、農村金融市場、農村金融市場效率等內容開展研究。針對農村金融效率的研究文獻,依然采用宏觀層面和微觀視角分開論述。從宏觀層面來看,一方面是對農村金融效率的內涵和外延的界定;另一方面是將農村金融效率融于農村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關系的研究之中,側重于農村金融支持地方經濟增長的效率分析。另外,還有部分學者對農村金融效率的影響因素、農村金融效率區域差異進行研究。而微觀層面上則主要是對農村金融機構效率評價及其指標體系、農村金融效率測算方法及分區域研究等。目的在于融合我國城鄉金融融合發展、提升農村金融支持農村經濟發展的效率,加快現代農村建設。隨著國內學者對金融效率研究的逐步深入,農村金融效率研究體系也逐漸形成,包括農村金融效率內涵與區域差異、農村金融效率方法與評價、農村金融效率與經濟發展的實證分析等方面。
(一)農村金融效率的內涵
趙洪丹、朱顯平(2015)認為農村金融效率是農村金融中介將農村居民儲蓄轉化為農業貸款的能力[16]。李建(2006)從制度經濟學角度衡量農村金融制度效率,認為現有的農村金融制度安排本身沒有考慮微觀農村經濟發展的現狀,與中國農戶的現實特征缺乏緊密聯系,在具體度量實施過程中脫離客觀情況,導致我國農村金融效率水平不高[17]。
(二)農村金融效率區域差異
岳意定、劉立新(2013)從經營效率與服務效率二維視角全面審視我國農村金融現狀及效率提升問題,研究結果發現農村金融效率低主要因為涉農資金投入不足、資本利用率偏低、農村金融組織不健全、農村金融機構單一等,改善農村金融生態環境和完善農村金融體系有助于提升我國農村金融效率[18]。孟兆娟(2013)對我國農村金融效率的省際差異以及東中西部差異進行測算,實證結果表明農村金融效率的省際差異呈先擴大后縮小的趨勢,區域差異主要表現為省際行政區域間的差異,省際個體差異和政府干預致使我國農村金融效率存在區域差異化[19]。向琳、郭斯華(2013)對中國各區域農村金融效率進行整體研究,發現各區域農村金融發展具有地域差異性,東部地區農村金融效率差異程度略低于中西部地區,整體上來看我國東中西部地區農村金融效率差異不大[20]。薛薇(2014)認為由于地理空間的分布差異,產生地區空間上的集聚效應和溢出效應,由于西部地區各種制度不夠健全和管理水平相對低下導致我國西部農村金融效率較低,也使得我國農村金融效率發展存在不均衡性[21]。武臻、羅劍朝、張珩(2014)借助于2007—2012年西部地區12個省域相關數據,通過對相關數據對比分析發現西部地區農村金融市場資源配置效率較低和全要素生產率不斷下降。另外,研究結果還表明技術進步成為影響農村金融市場資源配置效率的關鍵所在[22]。張永剛、張茜(2015)以資源配置效率為研究視角切入,實證研究山西省農村金融技術效率和規模效率歷年變化趨勢,并與全國農村金融市場效率進行比較,研究結果表明山西農村金融的發展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經濟發展。山西省各地區之間農村金融效率存在區域差異,農村金融資源的發展促進了山西資源經濟的轉型,影響農村金融效率的高低的因素主要有農村金融政策制度、農村金融機構數量、生態環境等[23]。薛薇(2016)指出我國農村金融系統效率的復雜性主要是金融系統的復雜性、農業產業特殊性、二元經濟結構典型性三個因素共同疊加而成,并從微觀與宏觀兩個方面對現有研究成果進行綜合述評,最終得出了農村金融效率低下制約了農村經濟的進一步發展之結論[24]。鄭博陽、張冬平(2016)從“三農”問題現狀出發,以河南省及其下屬17 個地市為樣本進行數據分析,研究結果一方面顯示河南省農村區域的金融資源配置是有效率的,另一方面,農業城市的全要素生產率高于工業城市,全要素生產率整體上呈上升態勢[25]。耿劉利、黎娜(2019)從金融領域的供給側改革入手,對2016年安徽省16 個下屬地級市樣本數據進行分析,研究結果表明安徽省整體農村金融效率偏低并且具有較強的區域差異性,農村金融供給側改革等方面仍有較大改進空間。另外還發現安徽省農村金融市場、農村金融資源等利用率相對較低,農村金融經營效率不高[26]。董春麗(2019)通過對比分析安徽省2003—2017年間農村金融機構改革前后的支農效率,得出2012年前農村金融機構的支農效率呈下降趨勢,而隨著金融機構改革的不斷推進,2012年之后農村金融機構的支農效率呈現回升趨勢,整體上來看表現為正U 型發展態勢。就目前現實情況來看,一方面增加農村金融機構數量;另一方面提升農村金融機構經營效率,切實提升安徽農村金融機構支農效率水平[27]。
(三)農村金融效率測算
崔紅(2008)通過測算我國農村金融市場的行業集中度和赫芬達爾指數,結果表明農村金融機構具有較強的單一性,農村信貸市場效率低下[28]。鄧奇志(2010)通過我國農村金融效率測算,得出我國農村金融效率水平較低的原因是農村金融制度的有效供給不足、政府對金融市場的管制、國有銀行信貸管理體制不健全、農村金融結構的單一性、農村金融生態環境較差等[29]。溫紅梅、姚鳳閣、常晶(2014)以2010年全國2001個縣級數據為樣本,通過建立自身計量模型對上述縣級市投入產出指標及外部環境進行實證分析,研究發現我國農村金融效率整體水平偏低,造成這一局面的根源在于我國農村金融資源利用率較低和農村金融市場效率不高,建議通過深化制度改革,轉變經濟結構,改善經營環境等發展外部環境因素的措施促進農村金融效率的發展[30]。蔣志強(2014)對現有文獻研究下的農村金融效率測算方法進行了梳理與歸納,發現目前研究農村金融效率測度的方法主要是回歸分析法、數據包絡分析法以及指標體系分析法[31]。
(四)農村金融效率方法與評價
效率測算方法可分為前沿法和非前沿法,前沿分析法在國外文獻中運用較多,Battese(1995)運用隨機前沿生產函數法對政府主導型的農業信貸效率進行了實證分析[32]。國內文獻在研究我國農村金融資源效率問題時則更多采用數據包絡分析方法和面板數據的回歸分析法。而對我國農村金融機構的經營效率與影響因素研究大部分運用指標體系法、排序多元選擇模型。常晶(2014)通過對我國農村金融效率的整體性研究,提出運用創新戰略,推進農村金融組織體系創新、服務功能創新,同時構建信用評價體系,加強農村誠信數據庫建設的方式建設農村信用體系,并加大農村教育投資以及加強監管體系等多領域措施提升農村金融效率[33]。馮永琦、嚴萍(2015)以金融生態環境的視角研究了農村金融主體的經濟環境因子、法制環境因子、金融發展環境因子、信用環境因子以及政府治理因子對農村金融效率的影響,提出完善法律法規與執法體系,提高地區農村金融市場化程度,采取差異化的貨幣政策等措施改善金融生態環境,提升金融效率[34]。劉淑紅(2016)運用描述性統計分析與因子分析對甘肅省14 個地州市進行農村金融效率分析,研究發現甘肅各地區儲蓄投資轉化率水平較低,整體呈現下降趨勢,甘肅農村整體經濟水平較低,農村經濟區域差異導致農村金融效率區域差異,建議各區域實施因地制宜的差異性區域性的農村金融發展策略[35]。李常武、蔡永衛、甘泉(2018)通過對定西市農村金融效率的研究發現定西市農村金融效率總體呈現下降趨勢,農村地區儲蓄率和農業投資效率是影響農村金融效率的主要因素,提出通過深入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優化農村金融組織,深化科技金融創新驅動,加快制定農村金融法等措施提升農村金融效率[36]。李枷宇、李智(2019)通過對重慶市各區縣農村金融效率研究發現重慶全要素生產率整體效率值不高,各區縣之間差異不明顯,技術進步效率的制約影響較大,且改善力度不夠,并建議引進先進的金融設備,金融機器,金融終端產品來替代人工辦理業務以提升業務工作效率,針對性地把政府的資金支持用于先進技術方面,適當擴大偏遠地區農村金融機構的投入,更好地促進重慶整體農村金融效率的發展[37]。莫媛、陳張霞、易小蘭(2020)建立DEA 三階段模型,在測算江蘇省農村金融效率的基礎上,得出江蘇省農村金融效率整體水平較高,農村金融效率水平與區域經濟梯度一致,農村金融效率較高的原因在于江蘇省農村金融制度較為完善。因此應積極發揮農村先進管理制度和經驗溢出效應,加大農村金融資源投入力度提升農村金融效率[38]。
(五)農村金融效率實證分析
彭陽、王燕(2011)認為,農村金融效率的影響因素主要有農村金融發展水平、農村金融結構、農村經濟發展水平及結構,其中農村金融結構、農村經濟發展水平與農村宏觀金融效率呈負相關,農村金融發展水平與農村金融效率呈正相關[39]。吳躍、劉影(2012)根據DEA 模型對廣西崇左農村金融效率進行研究,實證結果表明崇左市區農村金融效率偏低下,原因是投入冗余大,樣本研究中的投入變量距離達到DEA 有效的目標值還有很大差距,即決策目標生產點在有效前沿面上的投影還有待改善[40]。孫玉榮、陳奇(2013)選擇農村合作金融機構從業人員、機構數、總資產作為農村金融投入指標,選擇農村合作金融的存款、貸款和稅前利潤作為農村金融的產出指標,應用DEA 模型對我國2011年30 個省份的農村金融效率進行研究,研究結果發現我國大部分省域農村金融投入產出效率低下[41]。阮華、翁貞林(2015)以江西省各設區市作為決策單元,選取農村信貸余額與城鎮固定資產投資為投入指標,以第一產業增加值、第二產業增加值和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為產出指標,以Malmquist 指數形式的全要素生產率測度農村金融的投入產出效率[42]。張一青、彭非(2016)運用四階段DEA-Tobit 方法分析了我國31 省份農村金融效率,實證結果表明四階段DEATobit 方法同經典DEA 方法所測算結果存在差異,農村金融效率受外部因素影響顯著[43]。耿玉璧、夏詠、焦學偉(2016)利用1995—2014年間新疆農村金融與經濟統計數據,并運用因子分析法與回歸分析法對影響新疆農村金融效率的因素進行分析,研究結果發現新疆農村金融發展能夠促進農村經濟發展與農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同時使用因子分析法與回歸分析相互印證了結果的一致性[44]。李鳳嘉、項繁繁(2018)運用DEA 模型三個評價值技術效率、純技術效率和規模效率實證分析江蘇泰州農村金融效率,為提升農村金融效率提供參考路徑[45]。陳莉(2018)在模型指標的選取上,以每一年為決策單元單位選取1990—2014年數據進行模型構建,兼顧了決策單元數據選取的周期科學性與精簡性,同時選取農村涉農貸款、農村存款、農村保險費用收入及農村金融機構總量4 個類型數據為投入指標并以農村家庭平均收入和農村GDP 兩個類型數據產出指標進行模型的構建與數據分析,研究結果表明我國現階段農村金融效率除個別年份波動較大外,一直處于較高發展水平,并穩步朝向更積極的方向發展[46]。李彩霞、韓賢(2020)在對京津冀地區的農村金融效率測算評析時,設定京津冀地區為決策單元,選取農村金融機構營業網點數、農村金融機構從業人員總數和農村金融機構資產總額三項數據為投入指標,選取農林牧副漁人均生產總值和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為產出指標進而進行數據分析[47]。吳限(2020)以廣東省農村金融為研究對象,運用四階段DEA-Tobit 模型,剔除具有顯著影響的外部環境因素,合理評估了決策單元廣東農村金融效率發展水平,為有效推進廣東農村金融效率提供了借鑒[48]。
(六)述評
首先,國內部分研究文獻雖然提出農村金融效率評價方法和體系,但方法上多采用DEA統計法,由于DEA 統計方法的假設條件過于寬松,只強調生產要素的自由流通,這與我國農村的現實情況吻合度不高。從已經建立的農村金融效率評價體系來看,就評價指標的合理性缺乏有力的證明。其次,對農村金融市場效率的文獻更多地集中在有效或強有效市場情況,缺乏對弱有效市場的探討。而我國中西部地區由于歷史原因,大多數農村金融市場程度不高,機構單一,存在著不完全競爭,因此應在充分考慮區域差異的實際環境之后,綜合考量市場有效程度,提出有針對性的解決措施。再次,就目前國內外文獻多數從宏觀層面和微觀視角兩個方面對金融效率或農村金融效率分別進行研究,從整體上來看,沒有將二者有機聯系起來,研究具有片面性和單一性。從宏觀研究文獻來看,多數文獻以農村金融資源配置為出發點,通過對金融效率或農村金融效率的內涵和外延的界定,并對微觀農村金融效率分區域測評,得出我國農村金融效率存在區域差異和整體水平較低的結論。雖然這些文獻從空間上擴大了我國農村金融效率,但研究內容缺乏相應的微觀研究基礎,屬于單維度分析,相對來說理論基礎支撐不夠。另一方面,這些文獻只強調提升我國農村金融機構經營效率,單純地增加我國農村金融機構數量的粗放型增長方式,而忽視了對服務效率的提升,缺乏與服務對象的有效銜接,導致我國農村金融機構支農效率低下,只有提升農村金融機構的服務效率,才能有效發揮農村金融效率的宏觀微觀的整體協作性。因此,在未來的農村金融研究方向和領域應更多地結合金融服務擴大金融機構和金融資源,從經營效率和服務效率兩個維度綜合把控農村金融和支農效率的關系。
三、結論與展望
通過回顧和梳理以往文獻,不難發現致使我國農村金融效率低下的根源在于農村金融資金支持力度不夠、農村金融資源利用率不高、農村金融機構單一、農村金融組織體系不健全以及農村金融整體環境相對較弱。伴隨著我國“三農”問題逐漸呈現,如何深化我國農村金融改革、提高農民可支配收入、加快農業現代化建設、促進農村經濟快速發展,提高農村金融效率必然成為我國農村金融持續健康有效發展的當務之急。根據我國現階段農村經濟發展的瓶頸問題,應擴大中國農業發展銀行業務范圍、鞏固各地農村信用社的傳統業務、增強地方商業銀行金融機構服務農村效率、強化非銀行金融機構支農業務。未來一段時間內,我國農村金融改革的方向是通過政策引導、制度完善等提高農村金融機構的經營效率,更重要的是完善農村金融服務體系,提升農村金融機構服務水平和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