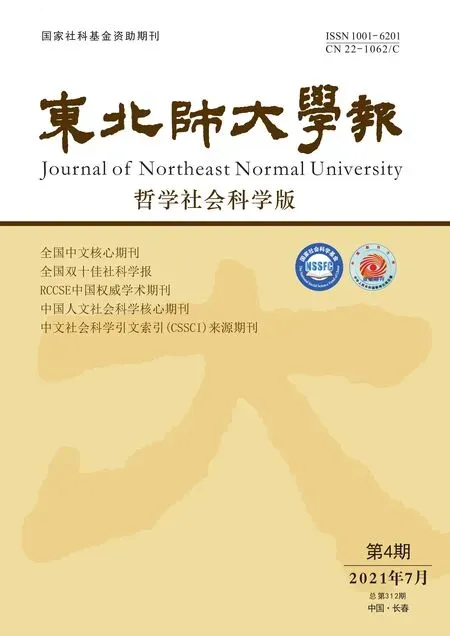張力中的女性烏托邦建構
——《克蘭福鎮》的女性主義敘事學解讀
夏 文 靜
(吉林大學 公共外語教育學院,吉林 長春 130012)
烏托邦(Utopia)一詞最初來源于英國人文主義小說家托馬斯·莫爾(Thomas More)所著的同名小說,莫爾利用希臘語中outopia(烏有之地)和eutopia(好地方)合成Utopia一詞,表示并不存在的美好之地。在之后的歲月里,烏托邦就成了人們逃避現實生活中痛苦的精神寄托,成為幸福、和諧的完美世界的代名詞。烏托邦小說自此成為一種傳統,描繪人們夢想中以道德完善為特征、人人安居樂業的理想社會。在這些小說中,“烏托邦遠遠不只是作為想象力的產物或愿望的滿足,它還是對現代社會困境的批判性彩排,同時還是關于解決這些困境的最佳途徑的指示性描述”[1]58。即便在這一類描繪未來理想社會的小說中,女性被安排的角色依然是傳宗接代、料理家務,女性自己的聲音仍然處在“缺席”的狀態。歸根結底,這類烏托邦小說仍然是男性價值體系的產物,它力求改變的是階級社會中階級之間的矛盾與斗爭,而女性作為平等個體的愿望和訴求仍然是被忽視的。正是針對這種情況,18世紀末19世紀初的一些英美女作家在西方傳統的烏托邦小說模式中融入了女性的愿望和訴求,創作了女性烏托邦小說。“女性烏托邦小說,顧名思義,即以小說為載體,反映女性主義思想,展現烏托邦精神,關注女性和人類未來的小說。”[2]以此為標準衡量,蓋斯凱爾夫人的《克蘭福鎮》當屬女性烏托邦小說之列。
一、《克蘭福鎮》故事與話語層面的張力呈現
蓋斯凱爾夫人將小說的背景設置為一個遠離塵囂的小鎮(克蘭福鎮),這是一個以年老貴族女性為主導的世界,作為對男權中心文化中女性職責的反撥,小鎮中居于主導地位的女性或終生未婚,或年老寡居。盡管伴隨著社會的發展,貴族階級退出歷史舞臺的趨勢無法挽回,但憑借女性性格中特有的善良、寬容、細致和堅韌不拔,小鎮上的女性不僅實現了觀念與身份的平穩過渡和轉變,也逐步與出現在她們生命中的男性實現了和解。這使得《克蘭福鎮》在故事層面不同于18世紀以薩拉·魯濱遜·司各特(Sarah Robinson Scott)的《千年圣殿》(MilleniumHall,1762)為代表的早期女性烏托邦小說為遠離婚姻傷害、撫平心靈創傷而對于男性的排斥,也不同于19世紀末20世紀初以夏洛特·帕金斯·吉爾曼(Charlotte Perskins Gilman)的《她鄉》(Herland,1915)為代表的女權主義階段烏托邦小說為解構男性話語、顛覆男性權威對男性的反抗。也使得小說受到來自讀者和文論界的質疑:女性被囿于家庭瑣事中的現狀是否代表著她們已被男權中心社會剝奪了謀生的能力,這是否承認了“她們無法自我救贖,唯有通過外來父權社會的力量才能被拯救出經濟困境”[3],這樣的女性烏托邦是否意味著走向解體。
在19世紀的英國維多利亞社會,社會生活和文學領域的話語權還完全掌握在男性手中,“作家的敘事地位是否在講述故事過程中得到權威認可,完全取決于該作家的社會身份,并非像早期那樣,取決于敘事作品本身摹仿現實的程度”[4]100。因此,當時的女性小說家通常在創作時采用男性或中性筆名,在作品中同樣選用男性敘述者與讀者進行直接交流,以期借用男性權威,使作品中的觀點更好地被社會接受。
由于蓋斯凱爾夫人在創作時以女性的真實身份直面社會,她在敘述故事時一貫小心翼翼。早在其第一部嶄露頭角的小說《瑪麗·巴頓》的序言中,蓋斯凱爾夫人就曾這樣聲明,“萬一我的敘述附和了或是觸犯了某種制度,那么,不論贊成或反對,都并非出于本意”[5]。以此方式求得男權社會的認同,這也成為她日后所有作品的敘述基調。我國學者申潔玲曾指出,在將小說的敘述者等同于作者的認知模式影響下,相當一部分作者為逃避對于敘事責任的承擔,往往采取“我聽故事”“我讀日記書信”的方式拉大第一人稱敘述者與所敘述故事的距離,使其成為故事中的超敘述者,而非故事的直接講述者,從而為代表了作者本人敘事權威的第一人稱敘述者推卸敘述責任。在《克蘭福鎮》中,小說敘述者瑪麗就因其客居小鎮的身份而缺席諸多重要故事情節,只能在女士們的閑談聚會中對小鎮上發生的種種有所耳聞,通過多重轉述的方式將故事呈現給讀者。而小說中的女性敘述者所承擔的敘事責任也就在這一過程中得到了弱化。不僅如此,在諸多由女性敘述者的間接引語轉述呈現的故事情節中,仍保留了以直接引語形式呈現的男性人物話語,這也使得本應在女性烏托邦小說中失語的男性有走上敘事前臺之嫌。但如果將蓋斯凱爾夫人置于英國女性文學發展進化的時間縱軸,便不難發現她正處于被美國女權主義文論家肖瓦爾特(Elaine Showalter)定義為內化男權社會標準的“女性”階段,這也就決定了她筆下的小說在敘事層面亦不同于處于推翻男權標準的“女權”階段,竭盡全力倡導觀念,大刀闊斧推行改革的女性烏托邦小說。
英國學者羅吉·福勒(Roger Fowler)將張力定義為:“一般而論,凡是存在著對立而又相互聯系的力量、沖動或意義的地方,都存在著張力。”[6]在文學作品中,“一切相互對峙又相互作用的原則、意義、情感、修辭、語詞,都可產生張力”[7]。《克蘭福鎮》中,囿于瑣事的女性、塑造為正面形象的男性、男女兩性之間的和解,與傳統女性烏托邦小說形成了故事層面的張力;在故事的敘述中,作為“女性”階段作家的蓋斯凱爾夫人的小心翼翼與“女權”階段女性作家的直抒胸臆,小說中男性人物聲音的浮現與傳統女性烏托邦小說中男性人物的失語都形成了話語層面的張力。
也就是說,無論從故事層面,還是話語層面,蓋斯凱爾夫人筆下的《克蘭福鎮》都不同于傳統女性主義批評和敘事學視域中的女性烏托邦小說,這也就引發了聚焦此處的諸多研究與爭議。維多利亞文學研究專家大衛·塞西爾(David Cecil)就曾因蓋斯凱爾夫人創作中看似妥協、關注瑣事的女性特質認為,她的“女性特質嚴重限制了她的成就,使她無法成為一流的藝術家”[8]154-155。而女性主義敘事學作為萌芽于20世紀80年代的后經典敘事學的分支,其關注的內容當屬倫理敘事學范疇,它與文化研究敘事學、馬克思主義敘事學、后殖民主義敘事學等其他以闡釋為主的敘事學一同成為經典敘事學的修正與補充。不同于女性主義批評對作品故事層面的特殊關注,也不同于經典敘事學對敘事話語的單一聚焦,女性主義敘事學的研究范圍包括故事和話語兩個層面,在女性主義敘事學視域下,研究內容不僅涵蓋了對女性敘事情節結構和女性敘事話語特殊性的關注,也涵蓋了對敘事過程和敘事形式如何建構性別的關注。也就是說,女性主義敘事學從敘事過程和敘事形式出發,探討二者如何作用于性別政治。女性主義敘事學作為文本闡釋的方式,意味著敘事與倫理的整合,因此透過女性主義敘事學的透鏡,文學作品的倫理意義與訴求被以新的視角全面透視后清晰地呈現在讀者面前。將在女性主義批評和敘事學視域下呈現出與女性烏托邦傳統存在重重張力的《克蘭福鎮》置于女性主義敘事學的視域下,可以幫助讀者理解敘事與倫理的相互作用,從而更好地解讀在女性被視為“家中的天使”的維多利亞時代,蓋斯凱爾夫人是怎樣在看似符合男權中心社會規約的表象下,透過故事與話語層面呈現出來的張力,實現筆下女性烏托邦的建構,使得《克蘭福鎮》成為“一部很多其他作品都無法與其抗衡的作品,顯然注定以其謙遜的姿態成為一部杰作”[9]。
二、“女性氣質”的解決辦法——《克蘭福鎮》敘事結構的倫理內涵
蓋斯凱爾夫人的《克蘭福鎮》是英國文學史上對第一人稱敘事嘗試較早的作品之一。在當時嘗試新型敘事方式的先行者中,不乏其他女性小說家,但不同于同時代其他女性小說家,蓋斯凱爾夫人在創作中由始至終以真實的女性身份直面讀者。因此,她不僅在小說中采用了女性人物作為第一人稱敘事者,以具有女性特色的敘事方式建構了整篇小說,而且她在小說中設置的第一人稱敘事者,“在德倫布爾與克蘭福鎮之間來來往往”[10]210的瑪麗·史密斯也成為在曼徹斯特與納斯福德鎮之間往返的她本人的代言人。
小說《克蘭福鎮》中有兩條并行的主線,相交于故事的主要人物瑪蒂小姐。但整篇小說中缺乏一個能夠統攝全篇的中心矛盾,各個情節分別呈現為相對獨立的故事,彼此之間的獨立性大于連續性,由共同的背景聯結成為一個彼此之間關系并不緊密的整體。
對于小說結構的松散,蓋斯凱爾夫人借敘述者瑪麗之口做出了解釋。瑪麗在談論每個人具有的不同癖好時所說的一句話被認為喻指她本人講述故事的方式。瑪麗曾說:“我得承認我自己也有這種毛病,我最舍不得的便是小繩子。我口袋里老是裝滿了線團,一有小段繩子就撿起來繞在上面備用,而實際上卻是從來都沒用上過。要是誰不肯耐著性兒一個結一個結地解開扎小包的帶子,而是一剪子剪斷它,我見到便覺老大難受。”[10]58毫無疑問,這也正是作為作者的蓋斯凱爾夫人在創作這部小說時所使用的敘事方式。正如米勒就此做出的解讀:“這本書就像是一系列短繩殘線,被收集,解開,拉直,連接為一體,最終成為講述單一故事的線條。”[11]179而蓋斯凱爾夫人正是“決意要充分利用情節的插曲增生和故事的非連貫性”[11]180,以小說非連貫性的結構與瑣碎、簡單的內容彼此呼應,達到故事與話語的統一。
作為一篇描述與世隔絕的小鎮生活的小說,《克蘭福鎮》中各個情節內容簡單、平淡,多以女士們的聚會閑談、關于服飾樣式的討論、對于貴族稱謂的商議等日常瑣事為主要內容,情節發展緩慢,其中并無凸顯張力的矛盾沖突;在涉及布朗上尉舍身救人、彼得離家出走以及強盜光臨小鎮的傳聞等略顯緊張的事件時,則作為女士聚會閑談的一部分,經由多層轉述的方式呈現給讀者。在整部小說中全無關于激烈沖突斗爭的直接描寫,即便在作為瑪蒂命運轉折點的“破產”一節中,也并未有激烈的矛盾沖突發生。
對于小說的這一特點,瑪麗也曾指出,“在克蘭福鎮,一些零零碎碎的東西只要有機會,都能派上用場。……許多人看不上眼的東西或者認為不值得做的小事,在克蘭福鎮卻是件件都有人留心”[10]22。暗示盡管她在小說中敘述的都是日常生活的小事,但并非毫無意義,而正是所謂細微處見深意,克蘭福鎮這個看似寧靜的小鎮潛在的生命力正蘊含在這些平淡無奇的細節中。這種關注細節、瑣碎、平淡的敘事方式不僅與女性敏銳、細致、善感的性格特征相一致,更為重要的是,正如凱特·弗林特(Kate Plint)所說:“《克蘭福鎮》中轉述各種軼事的段落也有一種預防性的功能,它們對細枝末節的追究似乎能夠抵御現代生活方式所帶來的變化和對現有狀態毀滅性的瓦解。”[12]小鎮女性并非進行暴風驟雨、大刀闊斧式社會革命的急行軍,正如女性主義敘事的創始人蘇珊·S.蘭瑟(Susan S. Lanser)所言,“在這些小說中,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女性社群,這些外在的或內在的理想之國,都為變革中的社會提供了‘女性氣質’的解決辦法”[4]272,將危機波瀾不驚地化解于無形之中。小鎮上故事發生的背景正如蓋斯凱爾夫人置身其中的維多利亞社會,彼時一度在社會中占據主導地位的貴族倫理道德觀念日漸式微,達爾文的進化論等新學說的涌現徹底動搖了宗教和上帝在人們心目中的地位,資產階級一貫推崇的福音主義和功利主義逐漸庸俗化,人們普遍面臨著道德危機和信仰缺失的困境。當男權中心社會中暴露出來的問題無法以男性倡導的規則和方式解決時,蓋斯凱爾夫人試圖以女性的特質作為化解危機的方式,這不僅是構成蓋斯凱爾夫人筆下女性烏托邦的基礎,也是其建構的女性烏托邦的特征。正是在這一意義上,小說的敘事方法與倫理內涵得到了完美的結合。
三、兩性和諧社會的建構——女性聲音的倫理訴求
在《虛構的權威——女性作家與敘述聲音》一書中,蘭瑟對“聲音”這一術語在敘事學和女性主義視域內的雙重內涵給出了區分。敘事學領域內的聲音“指敘事中的講述者(teller),以區別于敘事中的作者和非敘述性人物”[4]3,它強調的是敘述故事的動作由誰來完成。而“女性主義者所謂的‘聲音’通常指那些現實或虛擬的個人或群體的行為,這些人表達了以女性為中心的觀點和見解”[4]4,即強調所敘述的內容代表了誰的觀點。當我們在女性主義敘事學框架下探討女性敘述聲音對作者倫理觀念表達的作用時,上述雙重意義得到了完美的整合,即敘事過程中的講述者和觀點的主體在敘事作品倫理內涵的表達中均具有自己的功能和意義。
“在任何典型的烏托邦敘事中,總有一位局外人來充當文本表達的中介。此人意外發現這個群落,然后成為其人種史記錄者和文化倡導者。”[4]258在《克蘭福鎮》中,這個集局外人、記錄者和文化倡導者于一身的角色正是小說故事的敘述者瑪麗·史密斯,她來自距克蘭福鎮不遠處的大城市德倫布爾,卻時常會因為探訪朋友來到克蘭福鎮小住。米勒也曾指出:“瑪麗·史密斯的敘述權威源于她既處于克蘭福鎮之內,又處于該社區之外的雙重位置。她猶如一位人類學家,受邀進入某一部落或者社區,但忙于寫作一篇專題論文,旨在揭示該部落或社區的全部規律,講述其全部秘密。”[11]215正是瑪麗身份上的獨特性賦予了她獨特的敘事權威:她可以從外來者的角度客觀審視克蘭福鎮的風土人情,可以通過將克蘭福鎮與德倫布爾相比較而洞察這個小鎮的規則和紀律、人們的價值觀念以及小鎮里的奇聞怪事。在小說的開端,蓋斯凱爾夫人借用瑪麗的敘事權威聲明“克蘭福鎮是個女人王國”,“在不幸中互相幫助、互相慰藉……本鎮的太太小姐們已經綽綽有余了”[10]1-2,暗示了小說表達的克蘭福鎮這個女性烏托邦憑借女性美德走出困境這一倫理主題。
西蒙娜·德·波伏娃曾在《第二性》(TheSecondSex,1949)中說道,女性一直無法以“我們”自稱,因為她們“缺乏具體的辦法,不能把自己組織起來,形成一個與其他相關的統一組織旗鼓相當的整體……她們散居于男性之中,因為住房、家居、經濟條件和社會地位諸因素而附屬于父親或丈夫等等身份的男性。這種依附比起她們對其他女性的依附關系更為緊密”[4]255。蓋斯凱爾夫人在小說中對女性烏托邦的建構為女性缺乏組織的問題提供了解決辦法,將原本散居在男性中間的女性集中在克蘭福鎮這樣一個男性缺席的小鎮中,使女性成為彼此間的依靠,以此創造了能夠說“我們”的條件。在小說中,敘述聲音所代表的主體間或在指代敘述者個人的“我”和指代女性群體的“我們”之間切換,“敘述者固然保持‘第一人稱’敘事的句法,但她們的文本卻避開以私人化聲音為特征的個人性質標記”[4]274,通過女性群體共言的形式,使女性的集體意識得到體現。在布朗上尉來到克蘭福鎮之后,小鎮上女性們的態度由“我們喜歡高雅,討厭男性,幾乎相信男人天生就是‘俗氣’的”[10]9,向“我們有點兒可憐他,都說‘不管怎樣,從星期天上午那件事看得出來,他為人確實是厚道’”[10]16轉變,代表了克蘭福鎮女性抗拒男權但并不排斥男性的立場。這無疑是蓋斯凱爾夫人建構男女兩性和諧相處社會倫理期待的具體體現。
與此同時,為反撥女性在文學作品中的失語現象,使女性擺脫被言說的地位,蓋斯凱爾夫人使小說中的女性共同承擔了敘事的任務。從敘事學意義上講,盡管《克蘭福鎮》并不像艾米莉的《呼嘯山莊》一樣,具有多層框架的敘事結構,但小說的敘事同樣是由故事中的眾多女性人物共同完成的。小說中瑪麗作為第一人稱敘述者的身份決定了她必然采取有限視角,因此對于她無法親眼看見和親身參與的故事,同樣由小鎮中其他女性以敘述和書信的形式進行補充。而在這些由不同敘事者參與的敘事中,也都或多或少包含了敘述者對男性的評價。在小說第十章“驚慌失措”中,波爾小姐曾在她的敘事中對男性做出評價:“男人總是男人,他們裝得像參孫那樣力大無比,兇狠得別人不敢動他一根毫毛,又希望像所羅門那樣聰明,機靈得從來不會上當。您看好了,他們自吹凡事總有先見之明,但在出事之前又從來不肯打聲招呼,告訴別人一聲。我父親是男人,我對男人的脾氣是一清二楚的。”[10]134米勒曾從這一評價出發,認為這代表了蓋斯凱爾夫人對于男性虛假和衰弱的諷刺。但事實上,小鎮本無強盜,霍金斯大夫也并未撒謊,一切不過是波爾小姐自己的無中生有。當真相大白后,證明的只是波爾小姐本人的虛榮和可笑。至于宣稱“女性比男性要強多了”[10]18的狄布拉小姐,盡管評論多將她奉為女性權威的隱喻,但正是在她和曾任教區長的父親的共同反對之下,瑪蒂與地位低于她的心上人未能終成眷屬。由此可知,狄布拉小姐實為男權社會規范和倫理道德的支持者,她的這種用男權社會的規范來反抗男權、用女權簡單代替男權的做法到頭來只能加強現有的男權統治秩序。這與小說中建立兩性和諧社會的基調是不相符的。因此,蓋斯凱爾夫人在這些女性人物的敘事中所使用的反諷手段,與其說是對男性的諷刺,不如說是對盲目反對男性態度的不以為然。蓋斯凱爾夫人利用不同敘事者敘述聲音之間的差異產生的張力深化了小說建構男女兩性和諧的社會這一倫理主題。
《克蘭福鎮》女性烏托邦敘事的性質使得蓋斯凱爾夫人能夠在小說中選擇女性作為與讀者直接交流的第一人稱敘事者,而其看似推卸敘述責任,在敘述中采用的多重轉述的方式也有助于實現敘述者代替克蘭福鎮的女性群體發言的“單言”(singular)形式、復數主語“我們”敘述的“共言”(simultaneous)形式和女性群體中的個人輪流發言的“輪言”(sequential)形式的多種敘述聲音的并存。這種集體型敘述正如蘭瑟所說,“基本上是邊緣群體或受壓制的群體的敘述現象”[4]60,它不僅建構了女性的敘事權威,也有助于深化作者意在表達的倫理意圖。
四、女性烏托邦的情感凈化之旅——女性情感建構的倫理意義
烏托邦文學是人們對向往中的完美世界的描述,由于烏托邦所代表世界的完美性和難于實現性,它往往被等同于空想和白日夢。而事實上,烏托邦最大的意義并非在于它對未來的想象,而在于它“不妥協的批判精神”[1]60,即借助對理想世界的描述進行的對現實的批判性指向。就這一特征而言,女性烏托邦文學這一烏托邦文學的亞文類亦然。在蓋斯凱爾夫人的《克蘭福鎮》中,批判的矛頭試圖指向當時社會中存在的利己主義的倫理道德準則和男權中心社會對女性的壓迫和排斥。
姚建斌在他的《烏托邦文學論綱》一文中,對烏托邦文學的特征曾這樣總結道:“對烏托邦的描寫與找尋,主要是為了同探險者或航海家所從來的國家形成對照,給人以希望的指引或批判的理由。”[1]60這也正是烏托邦文學“不妥協的批判精神”的具體表現形式。蓋斯凱爾夫人創作《克蘭福鎮》的意義也正在于此。蓋斯凱爾夫人作為牧師妻子的身份使得她對于當時社會繁榮富足表象下深藏的矛盾了如指掌,在她的創作中,她始終在為這種社會困境尋找出路。她筆下的烏托邦雖然在空間意義上并非一個不為人知的神秘之地,但它的相對封閉性使它自成一體,臨近它的大城市德倫布爾作為克蘭福鎮的參照物存在。小說試圖通過瑪麗眼中德倫布爾與克蘭福鎮的對比,彰顯這個由女性構成的群體所奉行的倫理道德觀念的優勢。
與此同時,蓋斯凱爾夫人的《克蘭福鎮》作為女性烏托邦小說所引起的爭議也正在于此。在讀者的預期中,在一個去男權中心、解構二元對立的理想之地,女性人物本應擺脫婚姻的枷鎖和階級的壓迫,生活得如魚得水。但克蘭福鎮的女性生活似乎并非如此簡單如意,其對于現實的批判性指向又往往難以實現。按照經典敘事學解讀文本與讀者之間關系的方法,從讀者對文本接受的角度切入,蓋斯凱爾夫人建構完美烏托邦的倫理訴求似乎難以實現。但在女性主義敘事學的視域下,美國當代學者羅賓·沃霍爾(Robyn R. Warhol)提出,敘事形式能夠幫助建構讀者的社會性別身份,特別是能夠建構讀者的女性化社會性別身份。在敘事創作中,這是幫助敘事作品實現倫理訴求的重要維度。在當時男權中心的社會和文化背景下,女性作家可以將故事層面做出的讓步有效轉移到話語層面,服務于女性烏托邦的建構。
在沃霍爾的理解中,女性化性別身份并非受限于讀者的生理性別,而是取決于文化對其進行的規定或劃分[13]。也就是說,通過適當的敘事形式,可以幫助男性讀者成功建構女性身份。例如:在由男性主導的主流社會文化中,往往將以哭泣為代表的某些神態、動作、語調等視為女性化情感,與女性性別身份相聯系。參照亞里士多德的“情感凈化說”,敘事作品幫助讀者建構女性化性別身份的過程,也就是由作者主導的,敘事作品相伴讀者的一次情感凈化之旅。沃霍爾指出,諸如小說等通俗文學形式往往訴諸特定的、具有強烈性別化的情感模式和敘事類型,她曾歸納了七種建構女性化性別身份的敘事模式[14]45-51,以此標準觀照《克蘭福鎮》,讀者在小說敘事者瑪麗帶領下由德倫布爾至克蘭福鎮的烏托邦之旅,正是蓋斯凱爾夫人為讀者精心策劃的情感凈化之旅。
沃霍爾認為,采用人物內聚焦的形式,也就是用參與故事情節的第一人稱敘事者使讀者體會故事主體所經歷的磨難,尤其是歷經磨難之后的勝利,能夠有效地幫助讀者建構女性化性別身份[14]51。在《克蘭福鎮》中,瑪麗就是這樣一個參與故事情節的第一人稱敘事者。于是,伴隨故事情節的展開,讀者的情緒自始至終隨瑪麗的情緒起伏。
在整個故事中,作者以詼諧反襯悲傷,以喜悅彌補磨難,為讀者帶來了種種復雜的情感體驗。在前期種種不合時宜的舉動和言行的襯托下,布朗上尉最終的舍己為人顯得格外悲壯和令人動容,讓讀者也不免為自己早期在敘事者引導下產生的偏見心生歉疚。平和溫厚的瑪蒂遭遇人生中的悲劇,不能不讓讀者掬一捧同情之淚;但當她經歷了人生的低谷,最終得到了命運回饋她的善意,讀者也會隨之如釋重負地破涕為笑。這種“描寫痛苦和磨難,但常伴有歡樂和成功”[14]51的敘事情節,正是沃霍爾理論體系中催生女性化情感的敘事技巧。當讀者經歷了情感的凈化與升華,帶著柔軟善感的女性化情感回望作者筆下的克蘭福鎮,自然更能體會這個秉承愛與寬容,雖經歷挫折,終迎來希望的女性烏托邦的可貴之處。
塑造與傳統模式不同的人物形象也是女性主義敘事學視域下建構女性情感的有效途徑之一[14]51。在傳統的女性烏托邦小說中,男性人物或作為女性的陪襯出現,或成為作者指向的批判對象,小說《克蘭福鎮》不僅改變了男性的這種刻板印象,更在故事敘述中多重轉述的背景上保留了一些主要男性人物的聲音,這其中體現出作者不同于傳統的感情傾向。
小說中出現的第一個主要男性形象是上文提到的布朗上尉。他雖然有一定的不合時宜之處,但不同于其他高高在上、對女性頤指氣使的男性,他在與小鎮女性日積月累的接觸中表現出的友善、坦誠、“男人的卓越常識”[10]6以及對女性的尊重幫助他贏得了女士們的好評和愛戴。在表現克蘭福鎮女士對于布朗上尉的認可時,蓋斯凱爾夫人刻意將敘述者瑪麗的個人敘述聲音轉化為集體敘述聲音:“我們有點兒可憐他,都說‘不管怎樣,從星期天上午那件事看得出來,他為人確實是厚道’。”[10]16此外,就職于鐵路的布朗上尉同時具有另外一層身份的象征,即鐵路所代表的新興工業資本主義,克蘭福鎮女士們對布朗上尉從排斥到接納的態度也暗示了她們對于時代進步從拒斥到認同的變化。
小說中第二位重要的男性形象是瑪麗的父親,作為來自德倫布爾的商人,他有精明、實際、行事謹慎的一面。從瑪麗的敘事話語中我們可以看出瑪麗對父親務實一面的不以為然,她對父親來信的態度“一看就知是男子寫的,也就是說一點趣味也沒有”[10]165,正暗示了她的這種不以為然。但不同于傳統商人的金錢至上、唯利是圖,瑪麗父親的身上充滿了正義感。當預見了瑪蒂將要面臨的困境時,便告誡女兒不能棄瑪蒂于不顧;當瑪蒂破產后,他更是從自己并不順利的事務中硬擠出時間幫助瑪蒂處理事務。瑪麗此時對父親的描述“頭腦敏銳,處事果斷”[10]193,則表明了她對父親美德的認同。
小說中最后一位出場的重要男性是瑪蒂小姐的弟弟彼得。彼得是蓋斯凱爾夫人筆下具有女性特征的男性,他早年時多次的男扮女裝就暗示了這一點。他為人隨和,愛開玩笑,具有女性的善感與善良,在他重回克蘭福鎮后,“只要以前幫過瑪蒂一點小忙的……必定會熱忱相待,表示感謝”[10]209。同姐姐瑪蒂一樣,他擺脫了貴族階級的倫理特征,摒棄了貴族對于階級門第的狹隘觀念。在他的努力下,鎮上貴族的核心賈米遜夫人和平民出身的霍金斯家族不相往來的僵局得到了化解。毫無疑問,與傳統男性截然不同的彼得同樣代表了蓋斯凱爾夫人贊同的男性形象。
不論是為布朗先生的意外身故悲傷,還是被瑪麗父親的雪中送炭感動,又或是為彼得的善良和平安歸來動容,《克蘭福鎮》中異于女性烏托邦小說中常規男性形象的人物塑造總能在打破讀者預期的同時觸動讀者內心深處最柔軟的地方。正如沃霍爾在她的研究中所指出,“心理感受可以通過生理刺激來得到強化和訓練”[15],小說令讀者感動落淚的過程正是幫助讀者建構女性化情感的過程,而讀者的女性化身份也由此得到建構,《克蘭福鎮》作為女性烏托邦小說建構男女兩性和諧相處社會的倫理訴求由此得到實現。
女性主義敘事學的透鏡整合了女性主義和敘事學各自視域下零散的畫面,為讀者勾勒出蓋斯凱爾夫人構建的女性烏托邦的全貌。蓋斯凱爾夫人筆下的女性烏托邦,不是固守封建貴族制度的世外桃源,也不是盲目倡導女權的白日夢,而是面對現實、平和接受時代進步的設想。“在一個不惜任何代價強調理想女性特征的年代里”,她筆下的作品和她一樣“具備了理想女性的全部特征:溫柔,居家,得體”[8]152。作為“女性”階段的代表作家,蓋斯凱爾夫人創作的目的,是希望將在維多利亞社會中一向默默無聞的女性置于眾人目光聚焦之下,通過倡導女性特有的美德,幫助社會擺脫潛在的危機;與此同時,蓋斯凱爾夫人也呼吁為人正直、坦率、尊重女性的男性的出現,以此建立一個男女兩性和諧共處的社會。盡管在歷史進步的車輪下,克蘭福鎮面臨變遷的現實不可更改,但“作者告訴我們,如果有智慧的眼光,有寬容的襟懷,有真誠的友愛,也許能打破陳舊的思維定式,解除相互的隔膜與怨憤,建立一個和諧融洽的社會”[10]4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