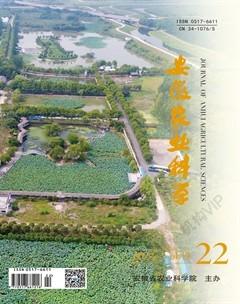整體性治理視域下農村基層社會治理層級體系構建
徐成洋


摘要 農村基層社會治理的研究是一項系統性研究。現階段,農村基層社會治理過程中存在明顯“碎片化”問題,整體性治理理論契合當下中國基層治理碎片化的現實需要。梳理農村基層社會治理過程中的已有研究,以整體性治理理論為基礎,在兩者邏輯耦合的基礎上,通過層級互動和組織互動,構建各基層治理主體間的整合和協調機制。再基于對山東省M鎮基層社會治理案例的分析,結合研究實際提出針對農村基層社會治理層級體系效能提升的整體性對策。
關鍵詞 整體性治理;農村基層社會;治理效能;層級治理
中圖分類號 D-422.6?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517-6611(2021)22-0262-04
doi:10.3969/j.issn.0517-6611.2021.22.066
開放科學(資源服務)標識碼(OSID):
Construction of Rural Grassroots Social Governance Hierarch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olistic Governance—A Case Study of M Town in Shandong Province
XU Cheng-yang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Zhejiang Ocean University,Zhoushan,Zhejiang 316000)
Abstract Rural grass-roots social governance research is a systematic study.At this stage,there is obvious “fragmentation” problem in the process of rural grass-roots social governance,and the whole governance theory meets the current needs of Chinas grass-roots governance fragmentation.In view of the realistic problems in the process of rural grass-roots social governance,based on the holistic governance theory,and on the basis of the logical coupling of the two,through the interaction of levels and organizations,construct the integration and coordination mechanism and interaction mechanism among the various governing bodies.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case of social governance at the grass-roots level in M town of Shandong Province,this paper put forward the overall countermeasures for improving the efficiency of the rural grass-roots social governance hierarchy.
Key words Integral governance;Rural grass-roots society;Governance efficiency;Hierarchical governance
“三農”問題是關系國計民生的根本性問題,我國政府向來重視“三農”問題。鄉村振興戰略指出“要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建立健全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加快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體現了黨和國家對“三農”工作的高度重視。農村基層社會治理是國家治理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將“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作為中心議題,這一舉措對農村基層社會有效治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鄉村振興和農村基層社會治理具有較強的耦合性,農村基層社會治理的現代化是鄉村振興的重要內容,鄉村振興又為農村基層社會治理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環境。因此,在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背景下,從整體性治理的角度研究農村基層社會治理層級體系的構建,對基層治理效能的提升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農村基層社會治理是國家治理的基層基礎,是綜合治理、源頭治理的重要組成部分[1]。不少學者對農村基層社會治理展開研究,黃愛軍[2]認為應該借鑒和運用新公共管理思想來開展我國的基層治理工作。劉金海[3]提出農村基層社會治理是一個綜合性的體系,分析了基層治理的三大前提條件,并探討了其模式的發展與創新。陳躍等[4]則從社會主要矛盾轉化為著手,分析了基層社會治理存在的系列問題,繼而提出創新基層社會治理的路徑。徐勇[5]從城鄉一體化進程的角度闡述了基層治理的概念,對于新時期研究鄉村治理具有借鑒意義。在不斷完善農村基層社會治理的同時,治理效能的提升尤為重要。提升基層社會治理效能,最重要的是發揮基層黨組織在農村基層社會治理過程中總覽全局的作用[6]。曹海軍等[7]借由浙江省A縣“矛調中心”的案例,分析了其組織結構和運行機制,有利于基層社會矛盾糾紛化解的流程再造與治理效能提升。林星等[8]以三治結合為著力點,分析了鄉村治理體系的目標、原則與路徑,通過優化三治結合鄉村治理體系的總體結構與子結構,以提升鄉村治理效能。
農村基層社會治理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不單指一個社會層面,它涵蓋了政治、經濟、生態、文化等多個領域;不單依靠基層政府進行治理,還要依靠村級組織、村民、企事業單位、民間團體等多方主體參與治理。目前來看,農村基層社會治理存在明顯“碎片化”問題,如治理層級體系機制碎片化、治理過程權責結構碎片化、治理方式理念環節碎片化等。如何化解這些治理“碎片化”問題成為學術界與社會關注的焦點。
綜上所述,對于農村基層社會治理及其效能提升的研究,學界已取得了較為豐碩的成果。然而,從整體性治理的角度分析基層社會治理及其效能提升的文章相對較少。筆者認為,整體性治理與農村基層社會治理存在較強的理論邏輯關系,兩者治理目標具有一致性,治理機制具有協調性,把整體性治理理論中的層級互動和組織互動應用到農村基層社會治理過程中,并在此基礎上構建各治理主體間的整合和協調機制。只有這樣,才能從整體把握農村基層社會治理的關鍵,助推基層社會治理效能的提升。
1 整體性治理:理論邏輯與互動模式
1.1 理論基礎
整體性治理理論(holistic governance)一詞源于20 世紀 90 年代中后期的英國。隨著數字信息技術的發展,以及傳統公共行政和新公共管理的衰微,西方國家試圖主張管理從分散走向集中、從部分走向整體、從破碎走向整合,以期更好地回應公民的服務需求[9]。該理論的主要倡始者是英國著名學者佩里·希克斯(Perri Hicks)。整體性治理就是在政策、規則、服務供給、監控等過程中實現整合,其針對的是碎片化治理帶來的一系列問題,整體主義的對立面是碎片化而不是專業化[10]。該理論強調以整體性為價值理念、以公民需求為導向,通過協調、整合、合作為治理機制,彌補傳統官僚制和新公共管理理論的缺陷,提供全方位、合作化、無縫隙的服務供給,構建整體性政府體制[11]。通過總結相關文獻,筆者認為把整體性治理理論應用在基層社會治理過程中,即:以滿足農民需求為導向,以現代化數字技術為手段,以整合、協調、合作為機制,通過整體性的價值理念對基層各層級、各部門等碎片化問題進行協調與整合,以構建一種基層政府與市場和基層社會通力合作運轉協調的基層治理模式。
1.2 理論邏輯 農村基層社會層級治理邏輯框架見圖1。
1.2.1 治理目標的一致性。
農村基層社會治理旨在通過多元主體、科學手段、互動過程等構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層社會治理體系,以滿足農村基層各主體的需求,建立良好穩定的社會秩序,其價值導向是促使政府公共服務部門向服務型政府轉變,不斷提升農村基層社會治理的治理效能和內生動力。整體性治理完全改變了以官僚制為理論基礎的“人治行政”思想,其重點在于通過協調各個部門的運作來擴大公共服務的覆蓋面,協調各層級部門的工作,提高治理水平和公共服務水平[12]。在治理的價值目標上,兩者有著共同的價值取向,只有吸收和借鑒整體性治理理論的理念與思想,才能更加系統有效地研究農村基層社會治理過程中存在系列問題,不斷提升基層社會治理效能和內生動力。綜上,運用整體性治理理論來化解基層社會的“碎片化”問題具有可行性。
1.2.2 治理機制的協調性。
農村基層社會治理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目前學界對基層社會治理機制的研究主要包括多元治理機制、協同治理機制、聯動治理機制等。整體性治理的治理機制為整合、協調、合作[13]。將整合、協調、合作運用到農村基層社會治理過程中,可為其提供整體性的治理思路:在整合層面上,整體性治理考慮的是不同的主體、層級、部門等在基層治理過程中的合作與配合;在協調層面上,整體性治理關注的是制定什么政策可以使基層社會獲得有效治理;在合作層面上,整體性治理著力于達成政府與村民之間的良好信任關系,將不同主體統籌協調起來參與基層治理。綜上,整體性治理理論與農村基層社會在治理機制上存在一定的協調性。
1.3 互動模式
1.3.1 層級互動。
我國政府結構屬于直線職能型,強調組織縱向層級間的相互節制以及橫向部門間的專業分工[14],這種直線職能型的政府結構體現在農村基層社會治理中即“中央—省—市—縣—鎮”5級治理層級體系,這種結構模式既有利于各層主體間的分工協作,但也存在單元分離、層級分散等碎片化問題。整體性治理理論提倡一種縱向層級治理與橫向功能治理的整合[15],這種綜合組織結構強化了中央對政策過程的控制能力,為跨部門聯系與合作提供了便利,有助于解決上下層級節制引起的制度碎片化問題。運用整體性治理理論加強各層級間的合作互動,有利于協調各層級黨組織和政府在推動基層治理過程中的具體分工,強化縣級在基層社會治理體系建設中的關鍵作用。
1.3.2 組織互動。
整體性治理的價值導向是滿足公眾的需要,以解決實際問題,其解決了新公共管理所帶來的相互轉嫁、相互沖突、缺乏溝通等一系列“碎片化”問題[16],強調政府通過運用整合與協調機制促進多元主體協調互動,不斷推進服務型政府的建設。農村基層社會治理過程中的組織主體包括基層黨委、基層政府、村級組織、村民、企事業單位、民間團體等,通過運用整體性治理,能夠構建多方主體協調參與基層治理的整合機制,以建立起良好的組織互動合作關系。既有利于激發農村基層社會各種治理主體的互動積極性,也有利于多元治理主體有效參與和協同推進農村基層社會各項事務治理,不斷提升農村基層社會治理效能。
2 山東省M鎮基層社會治理實證分析
M鎮位于山東省西北部,距市區30 km,鎮域面積83萬km 下轄62個行政村,常住人口4萬余人,是典型的農業大鎮。由于多種原因,該鎮在農村基層社會治理過程中存在嚴重 “碎片化”現象:主體參與單一、層級部門分散、過程手段冗雜、權責關系模糊、政策理念傳統等。近年來,該鎮依托精準扶貧政策的東風,不斷整合政策優勢,推進城鄉合作共融,創新網格化管理,促進多元主體協同參與,優化了農村基層社會治理的層級體系(圖2),極大地提升了治理的內生動力和治理效能。
2.1 整合政策優勢,驅動治理效能高質提升
在精準扶貧政策下,M鎮下轄的62個行政村中有9個省定貧困村,2017年在省派第一書記的幫扶帶領下,M鎮相對集中的5個貧困村的黨支部同心協力、共謀發展,共同創辦了以聯合黨支部為基礎的合作社。合作社帶動了組織振興、產業振興,充分發揮了基層黨組織協調整合能力,輻射帶動周圍多個村莊的農民興業、創業、致富。M鎮通過聯合黨支部合作社以組織振興推動產業振興,以產業振興帶動鄉風文明、環境衛生整治等各項工作,在脫貧攻堅的同時,不斷提升基層治理能力和水平。
2.2 城鄉協作共融,助推基層治理合作共建
M鎮積極探索村社聯建、城鄉共融的基層治理理念,在精準扶貧政策下,由市、區2級扶貧部門牽頭指導,與城區X街道結成互助對子,M鎮成立了由貧困戶為主體的物業勞務組織,組織貧困戶到X街道39個老舊小區從事衛生保潔服務,真正形成城鄉互動、互惠雙贏。貧困戶在進城服務的同時,依托X街道建立的扶貧便利店,把M鎮特色農產品,通過訂單的形式銷售到城區居民家中,增加了農民收入,帶動產業發展。在推進脫貧攻堅的同時,既促進了鄉村振興又創新了基層治理。
2.3 創新治理方式,推進基層治理網格化
為推進基層治理扁平化、網格化、數字化,2018年M鎮以原有的9個省定貧困村為中心村,在全鎮建立了以貧困村為載體的社區聯合黨委,在社區聯合黨委的基礎上構建了網格化治理模式,形成了“鎮—社區聯合黨委—村—村小組”4級網格治理體系。目前,M鎮基本實現了網格全覆蓋,推動了農村基層社會治理的精細化與專業化,真正打通了基層治理的“最后一公里”,進一步解決了基層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短板問題,不斷推動制度優勢向治理效能轉化。
綜上所述,M鎮在精準扶貧政策的引領下,既保障在貧困村的穩步脫貧,又因地制宜探索出一條適合本區域基層社會治理路子。在整合政策優勢的背景下,聯合貧困村黨支部創辦合作社,促進了基礎組織振興和產業振興,帶動了文化振興,進而提升了基層治理水平;不斷推進城鄉共融、合作治理,在帶動貧困村產業發展、增加貧困戶收入、參與城區街道物業服務的同時實現了村社治理雙贏;通過構建網格化治理體系,解決了基層治理所面臨的“碎片化”問題,有效促進了社會和諧穩定,營造出共建、共治、共享的良好局面。M鎮借助精準扶貧政策的東方,不僅實現了精準脫貧,還助推了新時代鄉村振興,切實提升了農村基層社會治理水平和治理效能。
3 機制建構:基于治理效能提升的整體性方略
3.1 優化層級結構,構建治理體系整合機制
整合是整體性治理理論最核心的機制,也是其組織構架的原則和首要制度性策略方法,是針對治理碎片化提出的策略路徑[17]。整體性治理理論所講的整合,與以往傳統公共行政和新公共行政所講的整合在概念上是不相等的,這里講的整合主要是合作性整合,既包括政府體系內縱向層級間、橫向部門間的整合,也包括政府與其他社會組織之間的合作所形成的整合。現階段,我國農村基層社會治理政策的制定和執行分屬不同層級管理,受限于多元化的層級管理體制,難以保證基層社會治理政策在執行過程中“無縫銜接”,因此整體優化各層級結構,深入維持基層治理政策制定與執行的整體聯動性至關重要。第一,縱向層級整合。應依托現代信息技術,整合“中央—省—市—區—鎮”5級治理層級體系,以及“區—鎮—聯合社區—村—村民小組”5級層級式網格治理信息平臺,縮減各個層級間的成本與時間,在節約行政資源的同時基層社會的治理效能也將不斷提升。第二,橫向職能整合。由于基層社會治理涉及多個部門,因此簡單地進行職能機構的合并不太現實,應構建信息化平臺整合各職能部門資源,將各職能部門的工作任務通過可視化的形式表現出來,以達到多職能部門的聯動治理。第三,監督機制整合。針對農村基層社會治理過程中的微腐敗,應打破干部內部相互監督的單一機制,在層級間、部門間監督的基礎上,整合完善村民等非政府部門監督,建立多元監督機制。
3.2 理清權責邊界,建立治理過程協調合作機制
在整體性治理的過程中,最重要的是協調階段,合作是建立在信任的基礎上進行整合與協調,進而實現多主體共建協作。協調與合作應用在農村基層社會治理過程中,即包括層級部門協作、政府內部協作、政府與社會協作。第一,層級部門協作。應理順并協調各層級、各部門在基層治理中的管理職能,在縱向層級上晨厘清基層治理的服務主責和履職邊界,界定區、鎮、聯合社區、村的責任關系,逐步走向法定化的權責配置;在橫向部門上,要根據縱向層級來劃分各部門理應承擔的相關責任,并通過平臺進行量化,實現各職能部門的合作治理。第二,政府內部協作。基層政府是農村基層社會治理的責任主體,是決定基層社會治理成敗的關鍵因素,因此要改變政府部門權責模糊的現狀,應依據部門權責一致的原則,厘清不同政府主體在基層社會治理過程中的權利與責任,加強各主體間的協調與合作。第三,政府與社會協作。基層社會治理是一項涉及面廣的系統工程,治理過程冗雜,在確保基層黨組織發揮總攬全局作用的同時,應不斷加強與其他主體的聯系,積極開展“黨建+”系列工作,把農村黨員干部和農民群眾的思想和智慧凝聚起來,形成推動農村基層社會協作治理的強大合力,不斷提升農村基層社會治理水平。
3.3 創新治理理念,推進治理方式數字化
整體性治理是以信息技術為治理手段的,即其在技術層面是以現代信息技術為支撐的。政府部門之間信息的互動、交流與整合,是構成整體性信息系統的基礎[18]。信息技術作為整體性治理的重要手段,能夠將農村基層社會治理過程中的主體有機地結合在一起,打破治理主體之間的壁壘,整合跨地區、跨部門和跨邊界的資源,統籌碎片化信息,從而實現信息的整體性治理,有利于消除功能分化所導致的治理碎片化弊端。 2019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數字鄉村發展戰略綱要》,指出要通過數字鄉村的建設,建立靈敏高效的現代鄉村社會治理體系,不斷推進鄉村治理能力現代化。第一,積極探索“互聯網+”治理模式向鄉村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領域不斷延伸,形成系統性的智慧網絡信息管理平臺,推進政府各部門資源和信息的有效整合,構建基于數字化的基層社會治理新體系。第二,打造專門為鄉村服務的符合鄉村具體實際的政務服務平臺,建立村級政務便民服務中心,使政務事務在村級實現“一站式”服務,走穩基層社會治理的 “最后一公里”,更好地通過智慧網絡信息管理平臺構建農村基層社會自治、法治和德治相融合的數字化治理體系以提升農村基層社會治理效能。推進數字技術在農村基層社會治理領域的應用,能推動基層黨組織、基層政府、社會組織、民間團體、村民等主體通過智慧網絡信息管理平臺參與到農村基層社會治理過程中,推進基層治理方式精細化和專業化,有利于農村基層社會治理效能的提升。
參考文獻
[1]
王海濤.大力提升鄉村治理水平[N].人民日報,2015-09-29(007).
[2] 黃愛軍.新公共管理與我國的鄉村治理[J].中國農村經濟,2005(2):67-72.
[3] 劉金海.鄉村治理模式的發展與創新[J].中國農村觀察,2016(6):67-7 97.
[4] 陳躍,余練.社會主要矛盾轉化與基層社會治理創新探析[J].理論探索,2020(4):81-90.
[5] 徐勇.城鄉一體化進程中的鄉村治理創新[J].中國農村經濟,2016(10):23-26.
[6] 李冬青.黨組織怎樣下好“基層治理”這盤棋[J].人民論壇,2016(24):96-97.
[7] 曹海軍,鮑操.系統集成與部門協同:基層社會矛盾糾紛化解的流程再造與治理效能:以浙江省A縣“矛調中心”為例[J].天津行政學院學報,2020,22(6):23-31.
[8] 林星,吳春梅,黃祖輝.新時代“三治結合”鄉村治理體系的目標、原則與路徑[J].南京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 21(2):96-103.
[9] 竺乾威.從新公共管理到整體性治理[J].中國行政管理,2008(10):52-58.
[10] PERRI ?LEAT D,SELTZER K,et al.Towards holistic governance:The new reform agenda[M].New York:Palgrave,2002.
[11] 王余生,陳越.碎片化與整體性:綜合行政執法改革路徑創新研究[J].天津行政學院學報,201 18(6):22-29.
[12] 邵巖.運用整體性治理理念推進服務型政府建設[J].中國黨政干部論壇,2019(9):71-73.
[13] 李峰.整體性治理:應對我國社會組織治理碎片化的新范式[J].學習與探索,2020(12):57-62.
[14] 李金龍,王英偉.整體性政府理論視域下省直管縣改革的碎片化及其整合研究[J].河南社會科學,2017,25(7):52-58.
[15] 袁坤.整體性治理視角下西部農村地區協同扶貧機制研究:以L鎮綜合扶貧改革試點為研究對象[D].武漢:華中師范大學,2016.
[16] 胡象明,唐波勇.整體性治理:公共管理的新范式[J].華中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0,49(1):11-15.
[17] 任維德,喬德中.城市群內府際關系協調的治理邏輯:基于整體性治理[J].內蒙古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 40(2):50-55.
[18] 韓兆柱,翟文康.大數據時代背景下整體性治理理論應用研究[J].行政論壇,201 22(6):24-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