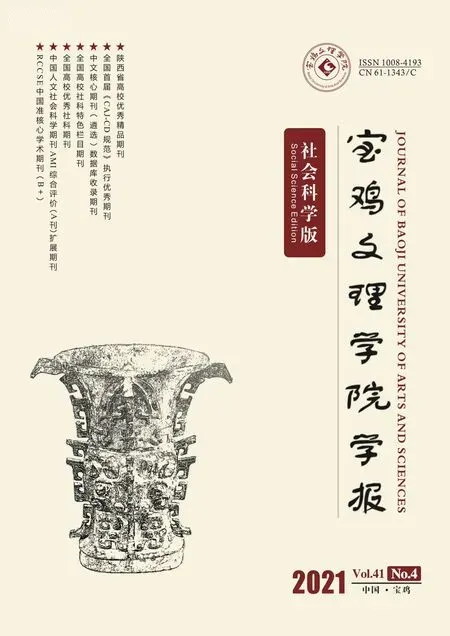技術·意識·文脈:文明競爭與文化共享背景下文化產業的文化邏輯*
李劍清
(寶雞文理學院 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陜西 寶雞 721013)
文化產業,是伴隨著大眾文化而興起的產業模式。西方理論家如阿多諾、霍克海默等人將這種大眾文化的生產稱為“文化工業”(culture industry)。阿多諾、霍克海默合著的《啟蒙的辯證法》一書中,就有一篇題名《文化工業,作為大眾欺騙的啟蒙》的文章。“文化工業”或“文化產業”是一種遵循現代商品經濟原則、在現代技術操縱下,為大眾群體或階層生產文化性商品的新工業體系。如果套用阿基米德的話,給文化產業一個支點——“技術”,和一根足夠長的杠桿——“意識”,就能撬動“文脈”這一文化資源。可以說,技術、意識與文脈是發展文化產業的文化邏輯。盡管文化產業是三級文明形態——現代工業文明高度發展的產物,但從人類文明進程來看,文化產業的文化邏輯要追溯到游獵、游牧的一級文明形態與農耕的二級文明形態,甚至需要將文化產業的文化邏輯放置在人類的文明競爭與文化共享背景中去理解。
一、技術:文化共享與文化產業的邏輯支點
技術,尤其作為一種藝術生產力的現代技術,是文化產業的邏輯支點。技術誕生于人類應戰自然環境的挑戰之中,或者說,原始先民為獲得賴以生存的物質能量,不得不借助非本能的——文化方式,運用原始而簡單的技術,改變自然界的物質形態。原始先民逐漸學會打制或磨制石器等技術,變成生產工具,如石鏟、石刀、石斧、石錛、石鏃、石臼、石磨、石杵、石硯等;逐漸學會磨制骨器等技術,如骨針等;逐漸學會用植物纖維、動物皮毛制作衣服的技術,抵抗嚴寒;逐漸學會使用鉆木取火等技術,用火恐嚇大型猛獸以及取暖;逐漸學會用水和泥,塑形、燒制各種陶器的技術,如陶鬲、陶盆、陶瓶、陶鼎等;逐漸學會烹飪技術與制作弓箭的技術;逐漸學會筑屋挖穴等技術,遮風擋雨;逐漸學會培育原始植物、馴服幼獸,發展原始農耕與畜牧;等等。
縱觀人類的文明進程,技術是推動人類文明的核心因素。原始先民所掌握生產生活方面的各種技術,往往滲透著原始巫術思維,也常常借助原始巫術儀式發揮作用。原始先民所掌握的生產生活技術,看似簡單,但也是經過上萬年的經驗積累。當與原始農業相關的技術與經驗,積累到一定程度,產生了質的飛躍,就大大提高了生產力。原始農業發展了,賴以生存的食物愈加充裕與之同時,從培育植物的過程中也掌握中草藥以及醫術。農業和醫學,導致人口迅速膨脹,為人類進入到文明奠定基礎。當原始技術通過空間共享和時間傳承積累到較高程度之后,人類進入以文字、青銅以及城市乃至祭臺為標志的文明階段。諸多核心技術如養蠶絲織、燒制陶瓷、冶煉青銅、占星觀象、天文歷法以及造紙、印刷、火藥、指南針等由國家嚴格管控,屬于國家核心機密。
技術具有文化共享性。所謂文化共享,是指人類某一族群所探索并掌握的生存經驗與技術觀念,在足夠長的時期中,隨著人類的遷徙以及文化交流,傳播至不同區域的其他族群,實現文化共享。文化共享性包括空間傳播,也包括時間承傳。在空間傳播方面看,據考古學發現,早在8000到5000年前,“繩紋陶的分布,北起西伯利亞(并向東達北美東北部、向西達到斯堪第那維亞半島),中經中國本部,南達中南半島、泰國與馬來西亞,甚至太平洋區域。”[1](P72)也就是說,早在彩陶時代之前的3千年內,燒制繩紋陶的技術已經文化共享到歐亞大陸乃至環太平洋地區。其實,豈止這種繩紋陶一種技藝具有空間傳播性,原始技術都具有空間傳播性。這就是我們能在不同區域的歷史博物館看到史前石器、骨器、陶器、玉器具有一定的共性特征的根源。從時間承傳上看,一種技術往往是根據某種物質材料的特性發明出來的,比如燒制陶器,就是根據陶土與火的特性而出現的。大地灣的彩陶燒制,與大地灣臺地前的渭河河道中淤積的極細河泥有關。當人類普遍掌握制陶技術之后,即使物質材料發生變化,同樣可以將燒制技術運用到新的物質材料之上。如青銅冶煉技術。也許人類早期在打磨石器的過程中,偶爾撿到天然銅塊等,當作石頭打磨,結果發現了銅質的鋒利與韌性等。也許在偶然機會,不慎將含有銅質礦石落入大火之中,發現了流化的銅。盡管考古學認為,青銅冶煉技術是經中亞傳播至中國,但我個人以為,中國的青銅冶煉技術是承傳了燒陶技術。因為中國古代的青銅冶煉技術,必須運用各種陶制的模具和范具,而模范的燒制就與燒陶技術相關。這樣才能將銅錫等礦石放進坩堝等容器進行冶煉,制作各種青銅器具,如銅簋、銅鼎、銅爵、銅豆等酒食器以及銅斧、銅鉞、銅劍、銅戈、銅戟、銅我等兵器。再比如說,人類在燒制紅陶等過程,根據某種審美或其他原始宗教觀念需要,在成型的紅陶坯上,用毛筆描繪花紋、草紋、鳥紋、魚紋、渦旋水紋、幾何紋等,這種繪黑色礦物質顏料的技術,承傳在漆器的制作上。人類將自身的身體做載體,用各色礦物質顏料繪成各種紋身。當絲絹、紙張出現之后,人類仍會將這種技術承傳在畫作的繪制之上。再比如說,原始人類會將契刻技術運用石頭、陶器之上,進而刻在美石之上——玉上,甚至將文字符號刻在龜甲獸骨、乃至青銅器之上,如中山國的契刻文字的銅器。這種繪刻技術,匯合著文字書寫器物之上。中國文字以毛筆書寫的技藝,一定與仰韶彩陶的繪彩(實際上是繪墨)有關。中國篆刻藝術一定與陶器刻符技術、刻玉技術、甲骨契刻技術、刻石藝術等有關。
現代技術,是以西方文藝復興啟蒙運動以來的近代科學思想為內核的,而近代科學理性是以數理邏輯為核心的。為了對抗中世紀的宗教意識形態,西方啟蒙思想家將近代科學思潮追溯到古希臘時代。正如卡西爾說的,“在偉大的古希臘思想家的時代以前——在畢達哥拉斯學派學者、原子論者、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以前,甚至連特定意義的科學概念本身都不存在。而且這個最初的概念在以后的若干世紀似乎被遺忘和遮蔽了,以致在文藝復興的時代不得不被重新發現重新建立。在這種重新發現之后,科學的成就看來是圓滿的無可非議的。”[2](P326)“在變動不居的宇宙中,科學思想確立了支撐點,確立了不可動搖的支柱。”[2](P326-327)“在畢達哥拉斯及其早期信徒的時代,希臘哲學已經發現了一種新的語言——數的語言。這個發現標志著我們近代科學概念的誕生。”[2](P331)也就是說,近代啟蒙運動以來的西方社會,帶著科學的眼鏡,在古希臘時代哲學中發現了一種數學語言或者數學的符碼意指系統,同時,創造出近代數理哲學——解析幾何,徹底建立起一種數形關系,即“一門數學哲學必須證明:……那種不能由整數或整數之間比例來確切地表達的量,由于引入了新的符號而成為完全可以理解的和可表達的了。”[2](P336)近代以來的科學,運用數學語言或純粹數學符號體系,給世界建構起數學模型,從而揭示宇宙奧秘。從此,以數學為核心科學,不再被“看成一種的神秘力量或事物的形而上學本質,而是把它看成一種特殊的獲取知識的工具。”[2](P344)以現代科學精神為支撐的現代科技,取代了前現代的經驗性技術,建立了以蒸汽為動力、機械化生產模式的現代工業體系,極大地提高社會生產力。從此,現代社會成了“為市場而生產,以交換為目的”商品帝國。現代工業生產體系往往以科技為崇拜,通過技術革新提高生產效率,試圖占據世界市場的最大份額,以企獲得豐厚的利潤回報。尤其當照相、攝像等現代機械復制技術出現之后,一種以商品消費的文化符號的生產體系如雨后春筍,紛紛而出。包括商品影像的廣告產業、電影產業等。如今,廣播、電視、電影以及網絡世界中,鋪天蓋地的廣告影像,在想象的影像世界創造出等級體系。現代影像技術業已成為一種藝術生產力,推動文化產業尤其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法蘭克福學派學者本雅明提出“文學技術是一種生產力”的觀點,這是來自于馬克思的物質基礎與上層建筑關系的論述。在本雅明看來,文學的生產力,即文學技術,是決定文學中的政治傾向和文學特質。于是,文學的生產關系,即一個社會的藝術生產方式,很大程度上制約了生產者和消費者等之間的社會關系,而這種藝術的生產方式就是“文學技術”——即形式的構成方式。正是這種作為藝術生產力的現代技術諸如照相技術、攝影技術、電子數碼技術等出現與大力發展,文化產業成為一種現實。
安置在現代工業生產體系之中的現代科技,不可避免地出現了標準化、批量化傾向。在馬克思以及西方馬克思主義學派看來,這是在現代技術崇拜意識的操作下,對“人的本質力量的異化”以及抹殺人的個性活動。早年馬克思(大約24歲前后)用了6個月時間,寫出了極端痛恨私有制、熱烈向往共產主義的《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馬克思一針見血,揭示出私有制社會的弊癥根于“異化勞動”。馬克思深受近代文藝復興人學理論的影響,從對抗超自然的“上帝”觀念的“抽象的、大寫的人”的理念,抽繹出“人的類本質”,從應然的理想狀態分析,認為人類的“正常勞動”是“人的本質力量”的對象化過程。從應然狀態上看,與動物的本能活動相比,人的“類本質”或“人的本質力量”是萬能的、自由的。而實然狀態上看,正是因為私有制、社會分工等原因,人的本質力量尚未實現“萬能”與“自由”,是一種異化勞動。正如朱光潛先生所說,“異化的勞動使勞動著失去了他的產品,他的產品‘異化’到資本家那里成為資本,而他自己創造出的商品愈多反而就愈貧窮,不但掌握不到生產資料,而且也被剝奪去維持肉體生產的生活資料。”[3](P80)“異化還表現在勞動者對生產勞動這種活動本身上。勞動者不但被剝奪去他的產品,而且他的生產活動也剝奪去它作為人的本質力量。”[3](P81)馬克思已經意識到近代“抽象的、大寫的人”觀念,忽視“個體的、現實的人”的弊端,才一再強調“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共產黨宣言》)。20世紀西方馬克思主義——法蘭克福學派延續了馬克思的理論傳統,發展出社會批判理論,“把批判的視線著重回轉到意識形態和文化領域中來”[4](P8)。這樣,法蘭克福學派認為,“商品生產中的標準化原則也成為大眾文化的原則,文化在這里不再標志著一種富有創造性的人的生命的對象化,而是體現為對個性的消滅。”[4](P51)當然,我們也應該看到,與“前現代社會”不計成本、手工化生產方式以滿足貴族階層所需的生產模式相比,以現代科技為主的工業生產體系以及技術革新可以大規模批量化生產商品,滿足了更多的大眾消費需要,是一種歷史進步。也就是說,正是機械化的工業生產模式,讓原來只能供特權階層使用的物品,“昔日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
二、意識:文明競爭與文化產業的驅動力量
盡管技術具有文化共享性特點,但是人類進入文明階段之后,技術同樣具有壟斷性。因為,技術的先進與否,決定著文明的等級。不同區域的“文化共同體”之間存在文明競爭。人類在應戰各種挑戰——包括自然的、其他族群的挑戰過程中,培育出了問題意識、創新意識、變通意識等文化意識。因此說,文化意識成為文明的競爭力,也成為文化產業的驅動力量。
從文明時間歷程上看,人類經歷了游牧(獵)方式的一級文明、農耕方式的二級文明以及工業方式的三級文明等三個階段。人類的游獵、游牧以及采集等史前文明階段,往往是以萬年來計年。人類經歷了三百萬年的時間,度過了漫長的舊石器時代。而人類的農耕時代則以千年計年,大約經過5千年的原始農業積累,人類進入到國家文明形態的“新紀元”。如今的現代文明日新月異,新事物層出不窮,新技術革新不斷。從生產能力上看,在一畝土地上進行農耕所獲得的莊稼能養活的人口數量遠比放牧所養活的人口數量大的多。“從舊石器時代的初期到后期,技術實際上有了很大的進步,這就導致人口的急劇增長。據估計,舊石器時代初期,原人的人口數為125 000人,而到了距今10000萬的舊石器時代末期,即農業革命前夕,人類的人口增為532萬人。人口增長42倍以上,可見比得上后來隨歷次技術革命而出現的人口爆炸。”[5](P76)因此,農耕方式的二級文明要比游牧(獵)方式的一級文明高級得多。而現代工業方式的三級文明農業生產,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變自然氣候的季節周期的制約,又可以運用現代化的生產工具,還可以通過高科技的人工雜交技術,推動農作物的基因選擇進程,甚至可以運用現代灌溉、熒光滅蛾、有機肥料等技術,提高單位面積上的農作物產量。尤其現代工業體系能夠以煤炭、石油和由水能、風能、光能等轉化成的電能,以及核能等新能源為動力,能夠機械化、批量化源源不斷地生產商品,以滿足人的生存生活需要。因此,以現代工業為生產方式的三級文明,社會生產力遠比農耕文明高得多。正如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不無感慨地說:“資產階級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6](P32)從全球區域空間來,人類所經歷的三級文明形態,但在同一歷史時段共存并生,相互競爭。盡管技術具有一定的文化共享性,但是技術與生存環境相關。人類生產、生活方式與所處的自然環境相關。就東亞腹地的中國而言,氣候溫暖,黃土沉積層深厚,又有黃河、長江以及無數支流,適宜農業耕作。早在距今5000年前就進入二級文明形態,成為東亞文明的文化中心。而青藏高原、蒙古高原等周邊等地區,卻因氣候、地理、植被等原因的影響,依然處在游牧或游獵狀態,屬一級文明形態。因此,盡管農耕文明區的各種生產技術文化共享到這些游牧游獵文化區,也存在著文化選擇的問題。另外,在華夏文明核心區的不同區域內部,也會出現因某些族群掌握某種先進技術,成為華夏文化核心區的主導力量。比如渭水地區的古羌人——姜羌,傳說時代的炎帝神農氏部落,因為掌握了原始農業技術與原始中草藥醫術,成為中華文明的始祖之一。比如生活在黃河中上游流域、具有半游牧、半農耕性質的黃帝部落,因能征善戰,諸侯咸來賓從。黃帝軒轅部落之所以能夠習用干戈,恐怕與其草原文化能征善戰的習性有關。取代神農氏的天下共主地位之后,黃帝依然改變不了游牧方式,所謂“遷徙往來無常處,以師兵為營衛”。從黃帝的名字“軒轅”,我們也許能夠明白這一族群掌握了當時最先進的車輪技術。車輪的發明,既改變了人類的運輸輜重方式,又加快了行進速度,因此,才能實現“遷徙往來無常處”的愿望。當然黃帝部落更懂得“修德振兵”,即使打敗神農氏——炎帝的同時,懂得聯合炎帝部落。最終,依靠著聯盟共同體人口上的絕對優勢,戰勝了東北方的紅山文化——傳說中的“蚩尤族”。至此,我們已經明白了一個道理:應對挑戰,形成問題意識,問題意識促生創新意識與變通意識,創新意識與變通意識促生技術更新。技術更新,推動世界文明中心形成。世界文明中心的爭奪,形成了文明競爭。
文化產業也是在問題意識下促生出來的。文化產業是為大眾文化生產文化性商品的后工業體系,與大眾文化的興起息息相關。大眾文化是在西方近代啟蒙精神下培育出來的,啟蒙精神實質上是一種問題意識,是一種創新意識與變通意識。同時,啟蒙精神培育了現代科學知識體系與現代工業社會,促生現代工業文明的三級文明形態。
“大眾文化”與“前現代社會”的“貴族文化”相對的概念,是美國民主制下發展起來的,業已成為“社會文化中壓倒一切的潮流”[4](P49)。所謂“前現代社會”,主要是指以巫術、宗教意識為主流社會意識的傳統社會。在前現代社會中,創造、掌握文化符碼體系的往往是貴族階層,如巫覡、薩滿、釋比、史祝、宗卜、教士、彌賽亞等。人類文化符碼體系,如文字、咒語、圖像、方術、巫術、醫術等,以及相關的物質載體如神殿、玉器、石像、青銅禮器、祭臺、觀象臺等等,均掌握在貴族手里。總之,前現代社會的文化符碼系統往往與神秘文化相關,具有原始宗教或宗教的神圣性、神魅性。而普通民眾則在從事社會生產、創造社會財富,維系個體生存與族群繁衍的過程中,遵循這些文化符碼體系,分享相關的文化意義,自覺不自覺地受到貴族階層的文化符碼系統的教化或凈化,并沒有屬于自己階層的文化系統,也就是說,在前現代社會,并不存在大眾文化。人類經歷了漫長的“前現代社會”,直到西方現代科學興起,才進入到現代社會。具體說來,16世紀以來的歐洲文藝復興啟蒙運動,為對抗中世紀基督教的上帝信仰,建構出“大寫的、抽象的人”,將“人的主體性”規定為理性、自由、平等的人。換言之,人是理性的動物,具有偉大的理性能力。正如康德所言“知性替自然立法”。從此,人類進入了以科技崇拜的現代社會。科學成為“人的智力發展中的最后一步,并且可以被看成是人類文化最高最獨特的成就。它是一種只有在特殊條件下才可能得到發展的非常晚而又非常精致的成果。”[2](P326)現代社會以啟蒙為特質,“啟蒙的核心就在于用科學化的、綜合性的、工具化的理性來控制自然,企圖把自然從多神教神話的紛亂中解救出來。”[4](P114)以科學理性為核心建構出的啟蒙知識話語體系,對“前現代社會”的宗教文化具有祛魅作用,還原巫術、宗教、神話等知識系統背后的因果邏輯,彰顯審美因素和觀念意識。以科學理性為核心的現代技術以及現代工業體系,成為獲得物質能量的最佳方式。巨大的社會財富掌握在資本家或布爾喬亞階層手中,進而要求更多地政治權力,通過革命或改良方式,打破了貴族社會結構,建立了平等、民主、自由等資產階級政權。貴族社會瓦解,文化話語權以及文化符碼體系下移。啟蒙不僅將“前現代社會”的文化符碼、知識系統開始從貴族階層下移至資產階級手里,也在一定程度上培育了更多的大眾群體。大眾文化是如何起源的?法蘭克福學派阿多諾給出了自己的解釋。他從啟蒙精神對現代人性結構的影響來揭示大眾文化起源。他先把啟蒙的觀念看作近代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再追溯這種啟蒙觀念的古希臘起源,認為荷馬史詩是人類最初擺脫神話,力圖理性地、自由地把握自然的記載。英雄奧德修斯就是“資產階級個體的原型”,“在他身上體現了啟蒙觀念的要素,出于自我保存的需要,他一次次地控制內心自然,犧牲自我的熱情,促使本能來擺脫自然的誘惑;由此他在逃離神話的同時也分裂了自己,他用否定自己的方式免除了懲罰,但同時他也失去了自身的自然。也就是說,啟蒙要求人強制忘掉生命,從而剝奪了自身血肉之軀的權利。”[4](P115)他將《奧德賽》的主題闡釋為犧牲與克制。啟蒙所張揚的理性在于克制和犧牲人性中非理性的東西,是一種自我自然的異化。阿多諾指出,“由啟蒙精神發展而來的藝術,就必然是一種同人的真實生命無關的,在人和自然分離之后所產生的幻想。”[4](P115)他借《奧德賽》中奧德修斯遇到海妖塞壬歌聲的情景來闡釋:當聽到代表著自然魅力的海妖們的歌聲時,奧德修斯讓水手們蠟封耳朵以抵制誘惑,因為他知道,勞動者——水手們必須集中精力向前看,必須擺脫一切自然的誘惑,努力將自然的力量移置與升華。這就是啟蒙理性對勞動者的要求。奧德修斯讓水手把自己綁在桅桿上,無力地傾聽海妖的歌聲,從而把自然的欲望與現實的克制割裂開來,海妖的歌聲變成了沉思的對象——藝術①。也就是說,藝術在近代啟蒙精神下,不再是人的內在自然的要求,而變成了遠距離的、冷冰冰的觀賞品。在現代工業社會中,大眾必須把肉體束縛在機械勞動之中,而所謂享受被分配在“閑暇”的娛樂中,是“資產階級式的險惡分割。”①大眾文化僅僅是人喪失了自身的自然之后,用幻想來補償擺脫勞役的快樂體驗。阿多諾遵循法蘭克福學派的社會批判理論剖析大眾文化起源,有其深刻性與犀利性,當然也難免有偏見。他沒有認識到,與“前現代性社會”只分享文化符碼背后的神性意義、并無自身獨立文化系統狀況相比,現代工業社會中,滿足勞動者——大眾來補償快樂體驗的大眾文化是一種歷史進步。
簡而言之,人類誕生在第四紀冰川時期的四次冰川覆蓋與三次間冰川時代,急劇變化的自然環境對人類先祖形成了巨大的挑戰。為了生存繁衍下來,人類先祖不得不主動應對環境的挑戰,形成了問題意識、創新意識、變通意識等人類的觀念意識,人類的觀念意識促使技術的誕生與運用,技術的廣泛運用,促使人類進入文明形態。從整個文明區域看,凡是不斷應對新的挑戰,充滿問題意識,不斷革新技術的族群或文化共同體,就成為世界文明的中心。不同區域的族群或文化共同體為了爭奪世界文明的中心,不斷進行文明競爭。這就解釋了古代中國農耕文明中心為何會不斷受到周邊游牧文化區的挑戰。恰恰因為古代中國的華夏農耕文明中心處在二級文明形態,能夠創造更多的物質財富,養活更多的人口,而周邊游牧文化區的族群處在較低的一級文明形態,雖然會在一定歷史階段,突入農耕文明區,甚至建立政權,但因其文明形態等級較低,無法創造出更多的社會財富,因此,游牧游獵的一級文明文化區必然地改變其生產生活方式,被二級文明同化,吸收到二級文明形態的共同體之中。同時,我們要意識到,西方近代啟蒙精神所促生的現代工業文明的三級文明形態,比農耕文明的二級文明形態的社會生產能力更大,因此,成為現代世界文化體系中的文明中心。因此,從農耕文明轉型而來的現代中國,同樣面臨著三級文明形態的挑戰,我們如何對應現代工業文明的挑戰呢?如何發展中國的現代工業體系以及后工業的文化產業體系呢?
三、文脈:文化表征與文化產業的意指實踐
如前所揭,文化產業是在現代技術的操縱下,遵循現代商品經濟原則,為大眾群體或階層生產文化性商品的后工業體系。文化產業離不開現代科技,尤其是感光膠片、電子成像以及數碼技術等現代高科技手段。文化產業尤其文化創意產業,就是運用感光膠片技術、電子數碼技術等,生產一種消費影像符碼體系的文化表征實踐活動。所謂“表征”,按照英國文化研究著名學者霍爾的解釋,“表征意味著用語言向他人就這個世界說出某種有意義的話來,或有意義地表述這個世界。”[7](P15)既然文化產業是一種意指實踐活動,表征文化命脈的意義的實踐活動,那么,中國的文化產業所要表征的正是中華民族的文化命脈,不僅要為國內的大眾群體生產出契合民族文化心理的文化商品,更要為全世界生產出既具中國特色、又具文化共享的文化消費產品及商品消費符碼體系。
既然我國的文化產業要表征的是中華文脈,那么華夏文明的文化命脈是什么?我們只有將中華文脈放置在華夏文明起源中來破譯理解。華夏文明與人類文明誕生一樣,都是在應對自然環境等挑戰的過程中產生的。當然,不同地理環境所帶來的挑戰,帶來了不同的應戰方式。不同的應戰方式所積淀的文化心理不同,塑造的文化命脈也不盡相同。就東亞大陸的氣候、地理等自然環境而言,當第四紀冰川期的冰川鋪天蓋地襲來的時候,遷徙而來的現代智人——人類先祖被阻隔在連綿起伏的秦嶺山麓之中。巍峨的秦嶺阻隔了冰川的入侵,秦嶺山麓的褶皺,成為冰河時代原始人類的搖籃。當第三冰川間歇期到來之際,地球氣溫回升,冰川消融,雪線退去。秦嶺以北的黃土臺地覆蓋在亞熱帶氣候之下,林木森森,水草豐茂,原始族群的生存范圍逐漸不斷擴展,雖然原始技術有所進步,但仍然過著靠采集野生植物與漁獵方式維系生存。距今1萬年左右,隨著磨制經驗技術的長期積累,原始族群已經能夠磨制出各種平滑光亮的生產工具,生產能力大大提升。從此人類迎來了新石器時代。也許是氣候的急劇變化,或許是人口的增長,采集或漁獵的食物難以維持生存。人類迫不得利用所掌握的有關植物生長知識經驗,過上了“刀耕火種”的生活。生活在東亞大陸黃河最大支流的渭水流域原始族群,培育出黍、粟等旱原作物,學會了燒陶技術,過上定居的農業生活。至今,渭水流域一帶還流傳著神農教民稼穡的傳說。從8000年到6000年前,隨著農耕技術的發展,以黍、粟為主的食物充足以及草藥為主的原始醫學發展,人口數量激增,原始聚落尋求拓展,形成甘、陜、晉、豫等為核心的仰韶彩陶文化。原始農業、草藥為主的醫術以及較為廉價的陶器制作,成為進入文明的加速度。因為,原始農業生產帶來充足的糧食;草藥為主的醫術,減少人類的死亡率;相對青銅等而言,陶器燒制成本較低,方便組建最小的社會單位——家庭;這一切的結果,導致人口成幾十倍的激增。人口的激增,促使仰韶族群不斷沿著黃河向東拓展。在與南下的紅山文化族群、與北上的良渚文化族群以及西拓的山東大汶口文化族群在河北、河南等地相遇,產生了激烈的碰撞,最終仰韶族群取得了勝利,奠定了華夏文明的基本格局。
盡管新石器時代原始族群還沉浸在原始巫術與宗教意識中,但仰韶族群卻選擇了一條“重人輕神”的“仰韶模式”。半坡墓葬遺址中的成人墓,只有較少的生前日用陶器作陪葬品,而在夭折的兒童墓中,則用繪制精美的人面魚紋的陶盆來蓋覆棺。這足以看出半坡人對死亡態度較為淡然,只是對夭折的兒童十分痛心與驚懼!人面魚紋盆上留有細小的孔洞,希望夭折兒童的靈魂能得以超生。因此,從半坡遺址的兒童墓葬制度所顯示出來重視兒童的意識。不由得讓人聯想起西周青銅器銘文中“子子孫孫永寶之”的套語,這不就是周人意識中重視兒童、關注人的另一種體現嗎?
仰韶族群為什么并不關心外在的神的存在,而關心族群內部的子息繁衍等現實問題?其原因或許是當時黃河流域的黃土臺地,盡管處在亞熱帶氣候之中,但不像秦巴山區及其以南的山林環境容易盛行巫術,也不像長城以北高維度的高原環境適宜游牧,經過烈山焚林、裸露的黃土層適宜農耕,低洼水澤,也可滿足漁獵,一切都不必外假于外在的神靈,養成了“重人輕神”的文化心理。暑假,我們單位十人一行,去漢中、寧強等地考察民俗遺存,發現這一帶依然保留著古羌人的儺術,儺師古稱“釋比”,今稱“端公”,經過敬神、作法,神靈附身,便可上刀山下火海。我一直想不明白,端公為什么要上刀山、下火海,直到參觀羌文化博物館,我才明白,當民眾得病,或者筑屋架梁等情況下,才會請端公做法,禳災祈福。一切都是為了人,所以端公十分受民眾的敬重。端公們不僅敬畏神靈,更看重在民眾中的影響力——德。試想,以古羌人為主體的仰韶族群,骨子里依然重視的是“德”。另外,考古學發現,仰韶文化類型從甘、陜等地擴張輻射到晉、豫、河套、河曲、內蒙古、湖北、湖南等地。我們不禁要問,仰韶文化是靠什么力量輻射至北中國呢?靠武力征服嗎?從目前的考古發掘看,仰韶區諸多遺址并未出現變革意義的武器。從情理上可以推斷,靠武力征伐不僅需要強大的物質保障,也需要更多的人口來組建強大的軍隊。仰韶文化區的文明程度遠遠不足以提供足夠多的物質保障,也不可能靠某一部族源源不斷的人口來支撐征伐所需。何況征伐本身也會讓人口銳減。如果我們循著“重人輕神”“仰韶模式”思考,有可能逼近歷史真相。在仰韶類型的部族內部,十分重視子孫繁衍。而在周邊的不同部族,仰韶文化的核心部族已經意識到與不同部族之間構成了一種原始意義的命運共同體。重視、尊重命運共同體的人的生命、生存。因此,選擇了一種柔性的文化同化的方式,不僅分享物質文化成果,如輸出陶器、紡織物等,甚至分享燒陶技術、紡織技術等。在分享文明成果的過程中,逐漸擴大區域的文化認同,使得仰韶文明區的范圍迅速擴展起來。同時,在趨同性的文化認同過程中,開始嘗試建構一種以核心區為中心、協同萬邦的政治格局。到了約6000-5000年前后仰韶廟地溝類型,河南成為文化中心,其輻射區已經達多半個中國。所以廟底溝文化最偉大之處就在于在那么早的時期,建立了一個類似于邦聯的超級聯盟,已經有能力來協同萬邦,預示了中國后來的統一形態。可以說這種超級聯盟的政治體制,是非常偉大的制度創新。雖然在物質形態上并不發達,但在社會組織形態上已經極為先進。通過這樣一種邦聯形式,促進了各部落的交融,文化間的交流更加頻繁,直接加速了堯舜禹、夏商以來的文明演進。其根本原因在于仰韶文化自身沒有過于強烈的宗教信仰,歡迎不同文化價值的方國或部落來溝通交流,共同發展。因此,我們隱約地可以感受到仰韶文化的“和”的精神,首先是和平,只有各部落之間“和”,才能達到平滿,才能不使更多的生命被無情地殺戮,才能迅速地占據更為廣袤的區域,發展人類文明。至今,中國人的思想深處依然強調“和氣生財”,恐怕也是仰韶文化的基因遺傳。其次是和諧共處、協同發展。雖然說通過暴力掠奪,可以集中社會財富,然而這種方式得到的是仇恨與報復,且并不能創造社會財富。只有分享先進的文明、技術——制陶等技術,使更多的部落或方國富足起來,才能使命運共同體更加強大。最后是融合,隨著先進的文化、觀念意識的滲透,部落之間的種族差異、文化差異逐步縮小,而文化認同逐步趨同,部落之間交融起來,故而形成了以炎黃族為主體的華夏文明。
從考古發掘看,在東亞腹地西部的仰韶類型的部族群體也已經進入農耕方式,如半坡遺址出土的原始石鋤、石鏟以及去谷殼的石杵等。也正是谷類等的培育與種植,讓仰韶類型的部族感知到春夏秋冬的四季輪回,同時感受到種子帶來更多的收獲,遠比采集狩獵的食物來源可靠充足,自然會生發出安樂之感。如果說進入農耕的史前人類,都會或多或少的生發一種安樂之感。那么,為什么說仰韶文化區的部族比其他區域產生更濃郁的安樂意識呢?這也許與仰韶文化區的地理環境有關。準確地說,適宜耕作的深厚黃土層,蓐燒灰燼化為原始肥料,讓仰韶文化區的農耕變得更加便利,收獲變得更加豐厚。這樣,收獲的喜悅比其他區域更濃郁強烈!仰韶文化區的部族更加依賴土地,更為關注實用與具體問題,而無需過分沉浸在濃厚的原始宗教氛圍之中。仰韶類型更為關心“吃飯哲學”,這就能理解“禹鑄九鼎”的真正內涵。當然,所鑄之“鼎”并非真要煮飯,而是象征著邦聯之首領將要負責所有結盟部族的吃飯問題,有權力調解聯盟內部部族之間的爭執與糾紛。滿足吃飯、維系生命存在之后,另一個問題突顯,那就是部族的生命繁衍問題。這也就解釋了大地灣、半坡等仰韶文化遺址中的器物上繪制“蛙紋”“魚紋”等,尤其半坡人為夭折的兒童制作最精美的彩盆。
我們可以大膽推斷,仰韶的半坡類型非常重視生命的繁衍和部族的延續,不愿意去相信虛無縹緲的神的存在。因此,仰韶文化多了未來的面向,對生活充滿了樂觀精神。這都積淀成后來的周文化與儒家文化的性格。更多地關注于現世,關注當下的人類社會,與西方宗教蘊含的罪感文化和悲劇文化完全不同。即使在后工業的今天,中國家家戶戶在過年的時候,貼對聯、貼窗花,不就在表達著對未來美好生活的期盼嗎?如果說樂的精神是一枚錢幣,那么對美好生活的向往與期盼是其一面,對自然災難、生活苦難與民族危亡的抗爭精神以及憂患意識則是其另一面。中國的文化精神更關注現實,強調人的作為更能起到積極的作用。在處理與外部世界的關系時,強調天人合一,和諧共處,也強調人定勝天。正因為對外部世界保持積極有為的態度,中華民族形成了樂觀的戰天斗地精神,堅信未來,渴望長治久安,對一切潛在的威脅因素保持著強烈的憂患意識。當深處危難的時候,奉行“天行健,君子當自強不息”的信念,絕不妥協、絕不悲觀,能夠積極應對,積極抗爭。
樂觀的戰天斗地精神與強烈的憂患意識脫胎于仰韶文化。仰韶半坡類型雖已經有了較為便利的農耕,但依然要面對自然災害、洪水、猛獸、疾病、戰爭等的威脅與挑戰。到了廟地溝類型,還要面對紅山-龍山類型的部族聯盟向西發展所帶來的沖突與戰爭威脅。然而,仰韶文化關注人、關注現實,重視人的主體性,往往采取積極有為的態度,而不是放棄人的能動性,匍匐在濃烈的原始宗教之中。即使借助宗教神學,也是為了凝聚人心,增加群體的文化認同意識。古史傳說中一再講述炎黃兩大部落結盟共同擊敗蚩尤部,這不就是重視群體的結盟力量嗎?當洪水滔天的時候,大禹聯合黃河中上游流域的諸多方國,一起鑿山治水。中國古代神話中的夸父追日、后羿射日、精衛填海等,無一不是在表現人的戰天斗地精神,無論成功與否,都絕不妥協。基于此,形成了中華民族積極向上的樂觀的文化精神。從中國歷史上看,農耕文明區始終受到游牧民族的威脅,以漢民族為主體的王朝總會居安思危,充滿憂患意識。因此,中華民族的文化血液中始終流淌著“居安思危”的憂患意識。尤其在近現代,西方列強環伺,虎視眈眈,在堅船利炮與大兵壓境的民族危亡之際,中華民族奮不顧身,抵抗外族入侵。可以說,越是在困苦不堪的時候,越是在民族危亡的時候,中華民族越是斗志昂揚,前仆后繼,拋頭顱、灑熱血,為民族獨立奮斗。試想如果不是對美好生活的憧憬與向往,如果不是為子孫后代創造良好的生活環境,誰還會不惜犧牲自我生命呢?
可以說,生生不息、和合天下、樂觀向上與憂患意識正是中華文明的文化命脈。當今的文化產業應該認真思考,如何運用極具民族特色的文化符碼來表征這些文化命脈?
綜上所述,人類文明經歷了原始游獵、傳統農耕、現代工業文明三級三個等級化的文明形態。技術,無論是以“巫-神”為內核的“術數”,還是以現代科學為內核的技術,在人類文明形態發展過程中都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因此,現代科學技術手段成為推動我國現代文化產業的重要抓手。意識、尤其是創新意識,是人類對應自然、社會等各種挑戰,不斷驅使技術革新,實現人類文明等級演進。也是我國現代文化產業的內在驅動力量。文脈關系一個國家、民族的文化心理,是文化產業的生命底蘊。現代文化產業更應該灌注中國文化命脈,創造既具民族特色、又具文化共享的文化消費產品以及商品消費符碼系統。由此可見,在文明競爭與文化共享背景下,技術、意識與文脈是我國現代文化產業發展的文化邏輯。
注釋
① 參見楊小濱《否定的美學——法蘭克福學派的文藝理論和文化批評》第四章的相關論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