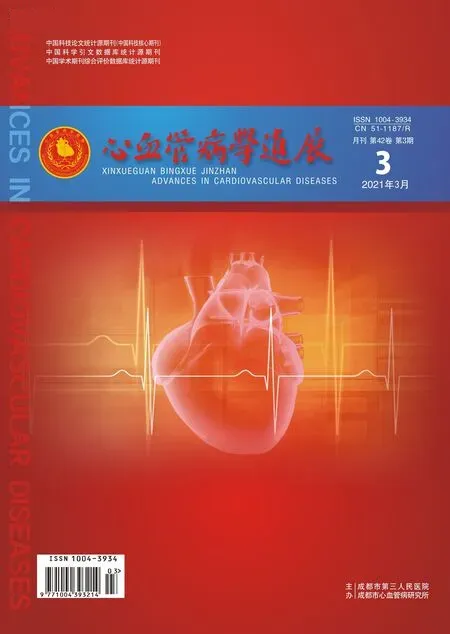腔內影像學在冠狀動脈支架內再狹窄中應用的研究進展
馬越 宋雷 喬樹賓
(中國醫學科學院 北京協和醫學院 國家心血管病中心 阜外醫院冠心病中心,北京 100037)
冠狀動脈支架內再狹窄(in-stent restenosis,ISR)是目前心血管領域的研究熱點,需靶病變再次血運重建的癥狀性ISR常表現為心絞痛或心肌梗死。冠狀動脈造影是評估冠狀動脈結構和指導介入治療的傳統手段,但二維管腔影像不能反映血管壁情況,無法準確地評估血管大小、斑塊特點和支架植入效果。腔內影像學技術可以幫助識別斑塊性質,早期發現薄纖維帽粥樣硬化斑塊等易損斑塊,為心血管介入醫師提供更為精準的病變信息,從而優化和指導ISR的介入治療。
1 ISR
ISR是指冠狀動脈支架內全程和/或支架兩端5 mm以內的血管造影提示直徑狹窄率≥50%的病變,Mehran等[1]根據造影特征將ISR分為4型:Ⅰ型:局灶性再狹窄(≤10 mm),可發生在支架內或支架邊緣;Ⅱ型:支架內彌漫性再狹窄(>10 mm,局限于支架內);Ⅲ型:支架內外彌漫性再狹窄(>10 mm,超出支架邊緣);Ⅳ型:支架完全閉塞。
ISR發病機制為血管內皮損傷、血栓形成、炎癥反應、血管彈性回縮及重塑等。其中,介入器械與血管壁的接觸導致斑塊破裂、血管內皮撕裂及剝脫等損傷是ISR的始動因素,繼而造成凝血和纖溶系統激活,導致血栓形成;支架植入后局部及全身炎癥反應形成,因球囊擴張而導致血管平滑肌過度增殖遷移在ISR的發生中也起到關鍵作用。支架內新生動脈粥樣硬化是近年來發現的ISR的重要病理生理學機制,特別是支架內新生薄纖維帽斑塊及大脂質核斑塊等不穩定斑塊[2]。由于新生動脈粥樣硬化與高血壓、糖尿病和吸煙等冠心病經典危險因素密切相關,故合并上述疾病者可加速ISR的發生和發展[3]。
支架植入后局部血流動力學因素的改變對ISR的發生有著密切的關系。支架鋼梁周圍壁面剪切應力較低及局部血液回流等因素可誘發炎癥反應,損傷內膜或內膜增生,從而導致ISR[4]。機械因素及技術因素也參與ISR的發生,目前普遍認為支架膨脹不全是導致ISR的重要機械性因素,支架斷裂、組織脫垂、病變長度和支架類型等因素同樣可影響ISR的發生。
2 腔內影像學
血管內超聲(intravascular ultrasound,IVUS)是一種心血管介入的腔內影像學技術,使用含有超聲探頭的專用導管,利用超聲波成像原理對冠狀動脈血管橫截面進行實時成像,用于觀察病變形態,量化斑塊負荷,指導支架尺寸,評估支架擴張效果,識別手術并發癥等[5]。IVUS在冠狀動脈造影的基礎上,選擇自動或手動回撤的方式,從血管內部對病變進行評估,可幫助改進血運重建策略的制定,從而降低患者支架植入后臨床不良事件的發生率[6]。
光學相干斷層成像(optical coherence tomography,OCT)是另一種心血管介入的腔內影像學技術,使用含有近紅外線光學裝置的專用導管,利用光的干涉原理,在不損害圖像分辨率的情況下對冠狀動脈血管進行成像,用于觀察管腔精細結構,描述斑塊組成成分,識別血栓性質,指導支架植入等[7]。與冠狀動脈造影指導介入相比,OCT指導可降低心源性猝死、心肌梗死和再次血運重建等事件發生率[8]。
IVUS與OCT的腔內影像成像原理不同,因此各具優勢與不足。IVUS具有更強的穿透力,在無需阻斷靶血管血流的情況下即可實現對血管壁內膜、中膜和外膜的全層評價,但IVUS存在軸向分辨率較低,斑塊亞型分類能力欠佳,導管回撤緩慢等不足[9]。OCT具有更高的分辨率,能更精確地顯示正常血管和病變部位血管的微觀結構,但OCT存在穿透力較低,成像范圍局限,造影劑用量增加,成像易受血液中殘余紅細胞干擾等不足[10]。多項研究顯示,IVUS與OCT在指導介入治療方面的臨床效果相當[8]。
3 腔內影像學應用于ISR的指南推薦
3.1 IVUS應用于ISR的指南推薦
2011年美國心臟病學會基金會、美國心臟協會和美國心血管造影介入聯合會聯合發布的經皮冠狀動脈介入治療指南推薦將IVUS應用于明確ISR的機制(推薦級別Ⅱa,證據等級C)[11]。2018年歐洲心臟病學會發布的心肌血運重建指南推薦將IVUS應用于優化冠狀動脈支架植入(推薦級別Ⅱa,證據等級B)[12]。
3.2 OCT應用于ISR的指南推薦
2018年歐洲心臟病學會發布的心肌血運重建指南推薦將OCT應用于明確導致ISR的支架相關機械性問題(推薦級別Ⅱa,證據等級C),同時推薦將OCT應用于優化冠狀動脈支架植入(推薦級別Ⅱa,證據等級B)[12]。2018年歐洲心血管介入學會發布的腔內影像學臨床應用專家共識推薦在明確冠狀動脈ISR發生機制中應用IVUS或OCT[13]。
4 腔內影像學對ISR的預測
4.1 IVUS對ISR的預測
大量研究發現,支架擴張效果和支架邊緣斑塊負荷是影響支架長期通暢性的重要因素。Fujii等[14]對15例西羅莫司支架植入后發生支架相關不良事件的危險因素進行分析,支架內血栓組的IVUS下最小支架面積(minimum stent area,MSA)明顯低于對照組,支架失敗的獨立危險因素是支架膨脹不全和參考段血管殘余狹窄。Fujita等[15]對223例應用依維莫司支架治療的ISR患者進行IVUS檢查,MSA≤5.3 mm2是患者發生反復ISR的獨立危險因素。HORIZONS-AMI研究[16]對36個中心的患者進行13個月的IVUS隨訪發現,支架失敗組患者的最小管腔面積(minimum lumen area,MLA)較小,平均MLA為4.4 mm2,兩組間MLA、殘余狹窄及支架邊緣斑塊負荷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
預測ISR或臨床事件發生的MSA臨界值在不同類型的藥物洗脫支架中相似。Song等[17]對912例藥物洗脫支架植入后行IVUS下MSA測量,經9個月隨訪證實MSA是發生ISR的獨立危險因素,預測西羅莫司支架發生ISR的MSA臨界值為5.5 mm2,佐他莫司支架的MSA臨界值為5.3 mm2,依維莫司支架的MSA臨界值為5.4 mm2。
4.2 OCT對ISR的預測
多項研究證實,支架擴張效果是ISR及反復ISR發生的較強的預測價值。Matsuo等[18]對69例在直徑為2.5 mm的小血管中植入依維莫司支架后的患者進行回顧性分析,9個月造影隨訪ISR發生率為7.2%,支架植入術后即刻OCT下MSA對ISR預測的敏感性為80%,特異性為71%,陽性預測值為18%,陰性預測值為98%,MSA<3.5 mm2時對ISR的預測價值較高。Miura等[19]對222例紫杉醇藥物球囊治療的ISR患者術后再次發生ISR的危險因素進行分析,再次發生ISR組患者MLA和MSA均較小,OCT識別的病變組織異質性比例較高。
冠狀動脈病變組織學性質及范圍也與ISR的發生密切相關。Ino等[20]對319例依維莫司支架植入術后即刻行OCT檢查的患者進行回顧性分析,OCT下脂質斑塊范圍及MLA是患者術后9~12個月發生ISR的獨立危險因素,脂質斑塊累及管腔范圍>185 °及MLA<4.1 mm2是預測ISR發生的最佳臨界值。
支架植入后不規則組織突入管腔提示ISR風險增加,其風險水平與脂質斑塊負荷相關。Soeda等[21]對786例支架植入后患者行OCT檢查,在1年隨訪過程中,OCT探及的管腔內不規則組織突出和MSA較小是靶血管相關心肌梗死、靶病變血管重建、ISR及支架內血栓形成等支架相關不良事件的獨立危險因素。Bryniarski等[22]對786例支架植入后即刻OCT檢查,對識別到不規則組織突入管腔的患者行支架植入前相關危險因素分析,發現此患者群體低密度脂蛋白膽固醇水平較高,IVUS下動脈粥樣硬化體積較大,OCT下斑塊脂質成分含量較高且合并血栓形成。
5 腔內影像學對ISR的評價
5.1 ISR發生機制的探討
ISR發生機制包括機械性因素和生物性因素。腔內影像學技術能提供比冠狀動脈造影更準確的病變特征,可對新生動脈粥樣硬化形成、支架變形斷裂及支架膨脹不全等進行評價,提高ISR病因的識別能力,從而改善ISR患者的遠期預后[3,23]。機械性因素如支架變形和支架斷裂可導致新生內膜過度增生,從而導致ISR[24]。
近年來研究證實,新生動脈粥樣硬化是ISR發生的重要生物性因素,新生動脈粥樣硬化是指支架新生內膜中出現脂質沉積、新生鈣化及斑塊破裂等[2]。IVUS檢查下ISR病變中的薄纖維帽斑塊及脂質成分為主的新生內膜均為新生動脈粥樣硬化的標志[25]。在ISR發生機制評價方面OCT優于IVUS,因為IVUS無法準確地評價血栓類型或新生動脈粥樣硬化成分[26]。
5.2 不同時期ISR的病變特征
不同時期ISR的新生內膜病變特征有所不同,晚期ISR患者IVUS下病變中脂質所占百分比及壞死核體積均高于早期ISR患者[27]。新生動脈粥樣硬化是導致晚期ISR的重要生物學因素,對早期ISR和晚期ISR的OCT病變進行對比發現,早期ISR與MSA<4.0 mm2密切相關,而晚期ISR中則是新生動脈粥樣硬化更為常見[28]。晚期ISR新生內膜大多為異質性組織,新生動脈粥樣硬化、薄纖維帽粥樣硬化斑塊和新生微血管檢出率更高[29]。
晚期ISR中新生動脈粥樣硬化也是導致支架內血栓形成及支架失敗的重要原因[30],在晚期和極晚期支架失敗患者中,OCT下新生動脈粥樣硬化與IVUS下血管正性重構具有一定的相關性,血管正性重構可幫助預測晚期和極晚期支架失敗患者中新生動脈粥樣硬化的形成[31]。
5.3 支架類型與ISR病變特征
不同支架類型的ISR新生內膜存在差異,借助腔內影像學技術充分了解病變特征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其發生機制。根據支架是否含有藥物涂層分為藥物洗脫支架(drug eluting stent,DES)與金屬裸支架(bare-metal stent,BMS),通過對DES與BMS植入后發生ISR患者的IVUS下病變特征進行分析發現,DES新生內膜面積明顯低于BMS,發生局限性ISR的概率更高[32]。OCT下特征亦有所不同,BMS早期ISR主要表現為均質高信號,BMS晚期ISR及DES植入后ISR均表現為不均質性混合信號[33]。與BMS相比,DES植入后新生脂質內膜和新生鈣化等新生動脈粥樣硬化性ISR的發生率較高,且新生動脈粥樣硬化的范圍相對局限,纖維帽更厚[34]。
DES根據其藥物涂層種類分為第一代和第二代,第一代DES主要包括紫杉醇和西羅莫司支架,第二代DES主要包括依維莫司和佐他莫司支架,第一代DES發生ISR主要是由于新生動脈粥樣硬化為主的生物性因素,第二代DES發生ISR主要是由于支架膨脹不全及支架斷裂變形等機械性因素[35]。從OCT對新生內膜的識別來看,第一代DES植入后ISR中具有衰減的非均質性病變為主,第二代DES植入后ISR中均質性病變為主,提示第二代DES新生內膜更為穩定[36]。
為避免金屬植入物永久留存體內,生物可吸收支架這項新技術近年來逐漸開始應用于冠狀動脈介入治療,對發生ISR的患者進行OCT分析發現,大多數ISR發生在生物可吸收支架植入后晚期,ISR以局灶性病變最為常見,主要累及支架近端邊緣,OCT下表現為不均質性或層狀病變的較多,在少數彌漫性ISR患者中,OCT提示富含脂質或層狀病變合并新生微血管,說明新生動脈粥樣硬化是生物可吸收支架發生ISR的主要機制[37]。
5.4 特殊血管及特殊人群的ISR評價
大量研究針對冠狀動脈ISR進行腔內影像學研究,但對于冠狀動脈旁路移植術后橋血管ISR的病變特征報道尚不多見。在對54例隱靜脈橋血管ISR患者進行IVUS檢查時發現,大部分患者是由于生物性因素所導致的ISR,其中包括19例新生動脈粥樣硬化、13例新生內膜增生和4例血栓形成;少部分患者是由于機械性因素所導致的ISR,其中包括10例支架膨脹不全、6例支架變形或支架斷裂和2例支架未覆蓋主動脈吻合口處病變[38]。
對于特殊合并癥人群ISR的腔內影像學病變特征進行研究有助于充分了解疾病間的相互作用,以期提高臨床診療。對合并糖尿病的ISR患者行OCT檢查,新生動脈粥樣硬化病變中的新生微血管的形成在糖尿病患者中更為常見。與血糖控制良好的糖尿病患者相比,長期血糖控制不佳的糖尿病患者ISR病變中薄纖維帽粥樣硬化斑塊的檢出率更高[39]。
6 腔內影像學指導ISR治療
應用腔內影像學指導ISR介入治療可降低反復ISR事件的發生率[40],在一項應用OCT指導DES治療ISR的研究中,發生反復ISR的主要原因為新植入的DES支架膨脹不全,而導致其膨脹不全的主要危險因素包括原支架膨脹不全、新生內膜體積、支架周圍新生鈣化及既往多層支架[41],有關腔內影像學指導ISR介入治療器械的選擇目前尚無統一定論,需更多研究進一步證實。
7 小結與展望
腔內影像學在ISR患者介入診療中發揮重要作用,結合當前影像后處理技術的進步,基于腔內影像學的冠狀動脈血流儲備分數計算可為ISR患者提供更為準確和全面的病變評估,在優化和指導血運重建策略的制定方面充分發揮腔內影像學的價值;其次,由于IVUS及OCT各具優勢,同時完成兩項腔內影像學檢查所需時間較長,目前有學者提出將兩種腔內影像導管合二為一,充分發揮IVUS與OCT結合的優勢;另外,目前有關藥物支架或藥物球囊在ISR介入治療方面效果的臨床研究證據尚不充分,未來需更多大型隨機對照臨床試驗來證實其優劣性,以更好地指導ISR患者的臨床診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