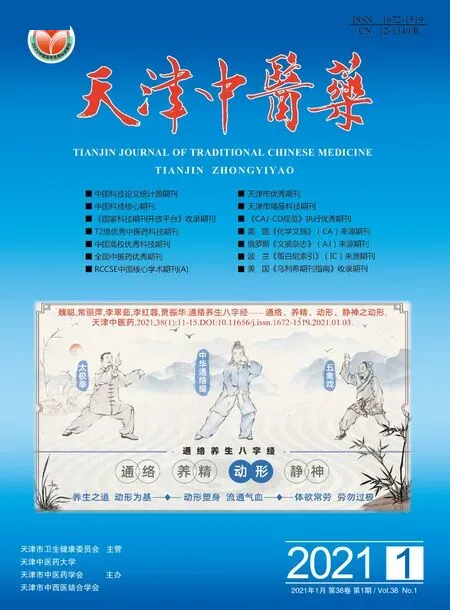截斷療法在防治新型冠狀病毒肺炎中的應用*
熊可,楊豐文,馮睿,黃明
(天津中醫藥大學,天津 301617)
2019年12月以來在全球爆發的新型病毒性肺炎是一種呼吸道病毒性肺炎疾病,被世界衛生組織(WHO)命名為2019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具有人群普遍易感性,老年人及有基礎疾病者感染后病情較重[1],中醫學將本病歸于溫病范疇,由于其傳染性極強,又屬疫病。本病臨床表現多樣,多為呼吸道癥狀,輕癥癥狀輕微,類似于普通感冒和流感,預后較好,但部分患者會轉為重癥,表現為肺炎,甚至出現急性呼吸窘迫綜合征以及多臟器衰竭,嚴重時導致死亡。其中中醫藥在COVID-19救治全過程全方位深度介入,發揮了重要作用,被譽為是中國方案的亮點[2]。2 000多年來中醫藥在與各類傳染性疾病斗爭的過程中,積累了豐富的經驗,總結了系統的理論。比如截斷療法在COVID-19疫情防治的全過程都起著很好的臨床指導意義。文章就中醫學的截斷療法在治療COVID-19中的應用和意義提出幾點思考,以作拋磚引玉之用。
1 截斷療法的理論源流
“截斷療法”主要包含了“截斷”和“扭轉”兩個方面[3]。“截斷”是指采用果斷措施和特效方藥,直接作用于病處,以求迅速祛除病原或攔截病邪深入,從而阻止疾病的進展和遷延。“扭轉”是指扭轉病勢,使疾病向愈發展。臨床上“截斷”和“扭轉”趨勢一致,統稱“截斷療法”。中醫理論中一直滲透著已病防傳、未盛防盛、已盛防逆、瘥后防復等截斷療法的治療思想。
追根溯源,“截斷療法”起源于《黃帝內經》。《素問·四氣調神大論》曰:“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亂治未亂,夫病已成而后藥之,亂已成而后治之,譬猶渴而穿井,斗而鑄兵,不亦晚乎?”尤其針對熱病,須及時抓住窗口期采用汗、泄兩法,及時截斷,跨越病機階段動態防守,其中“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亂治未亂”也提示醫家在治病時要明晰疾病的傳變規律,知其所犯,詳其進展,安其未病之地。
漢代張仲景的《傷寒雜病論》中對“截斷療法”又有進一步認識。在《金匱要略》篇首就提出“見肝之病,知肝傳脾,當先實脾”,強調要注重審“勢”堵截,已病防變;另外《傷寒論》中描述陽明三急下證,除“目中不了了,睛不和”外,其余癥狀似不危急,如“發熱汗出”“腹滿痛”,提出需急用大承氣湯通腑瀉下以制內熱,保真陰,較《黃帝內經》的“汗、泄”法有了進一步的提高,有了具體的方藥,這也表明張仲景熟知疾病的發展規律,深知病“勢”的嚴重性,宜先證截斷,逐邪于外,才能起沉疴,救危重。
明代溫病學家結合對瘟疫病因病機的新認識,突破了“燥屎內結”的下法應用原則的束縛,提出可不必拘于燥屎,可早治早下也。吳又可的《溫疫論》中曰:“欲為萬全之策者,不過知邪之所在,早拔去病根為要耳。”還有“客邪貴乎早逐”之說,這種“早逐客邪”的觀點體現了吳又可的“截斷療法”思想;書中的“數日之法,一日行之,因其毒甚,傳變亦速,用藥不得不緊”,也是對截斷療法用藥原則的補充。
清代溫病學家葉天士提出治以“甘寒之中加入咸寒”之藥以治療溫熱病斑出熱不解,胃津虧虛但未及下焦腎陰,亦是截斷療法的體現。
近代名醫趙錫武先生在20世紀60年代提出治療肺炎不能囿于溫病衛氣營血理論的束縛,應采用直搗病穴的方法,這也是扭轉病勢,截斷病情發展的思想體現[4]。20世紀70年代上海名醫姜春華結合臨床經驗具體提出了“截斷療法”的概念,主張對一些傳染性疾病應早期截斷衛氣營血的傳變,使疾病不再進一步發展,而不是因循等待。
至此,截斷療法的概念和理論得以確立。綜上可見,“截斷療法”的治療思想起源于《黃帝內經》,后經歷代醫家補充發展,到20世紀70年代由上海名醫姜春華先生提出總結,對治療多種急性傳染病有指導意義[5],截斷病勢,扭轉病程,控制疾病傳變,而不是單純的受制于疾病傳變,這就是本療法的核心。
2 截斷療法在防治COVID-19中的應用
“截斷療法”是從提高臨床療效出發而提出的一種治療學思想,對COVID-19的防治具有指導意義。COVID-19屬于疫病范疇,主要病性特點為濕毒,可稱之為濕毒疫。濕毒疫是以濕毒為典型特點的疫病,濕邪為患往往起病隱匿,起始癥狀溫和,傳變迅速,多生變證,纏綿難愈。主要證候要素為濕、毒、熱、閉、虛,主要侵襲肺與脾兩臟,濕毒壅肺為主要病機。因此把握COVID-19疫病的屬性,知道其傳變必定要經過某個階段,采取先行一步的方法,提前用藥,截斷其病程的發展,可以為中醫救治爭取主動。
2.1“四類人群”早期干預,先證而治,截斷傳變 先證而治是截斷療法思想的具體體現,對COVID-19防治具有現實意義和臨床指導價值。先證而治的含義是指機體已受外邪或疫毒侵襲,但無任何臨床癥狀,或僅出現少數非特征性的變化,臨床上對還無法明確辨證的患者進行治療。這也是《千金要方》中所說的“上工醫未病之病”“中工醫欲病之病”之說。截斷療法就是把握某些疾病本質的屬性,知道疾病傳變必定要經過某個階段,所以采取先行一步的方法,提前用藥,截斷其病程的發展。
根據《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診療方案(試行第七版)》[1]的流行病學調查,新型冠狀病毒的潛伏期1~14 d,多為3~7 d,具有普遍人群易感性。在疫情嚴峻時確診尚無癥狀者、疑似病例、密切接觸者、發熱待查人群有數萬人之多,西醫除了隔離尚無有效干預手段,但不干預會貽誤病情。因此張伯禮院士向中央指導組建議采用“中藥漫灌”普施中藥的建議被采納,對此4類人群進行早期干預,明顯減少了確診人數,截斷了其發病或由輕癥轉為重癥的傳變,取得了顯著的效果。
對于老年人、有基礎病等免疫力較弱的人群予以中醫藥早期干預也可截斷其發病。致病因素與體內正氣相爭是疾病邪正消長動態變化的過程,貫穿于溫病的始終,決定疾病發生發展及預后轉歸。對于此類人群早期予以扶正祛邪,根據《天津市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中醫藥防治方案》[6]予黃芪、白術、玄參、防風、桔梗、黃芩、桑白皮等藥物水煎服,再配合日常太極拳、八段錦等調護,增強正氣,可一定程度上截斷發病,如《黃帝內經》所云:“正氣在內,邪不可干。”
2.2 對于輕癥、普通型患者,截斷療法與辨病施治相統一 對于COVID-19的治療,首先必須辨明其病乃濕毒疫為患,屬疫病范疇,可通過呼吸道傳播,有其特定的發生、發展和傳變規律。所以在明晰病勢的基礎上對輕癥、普通型患者轉入方艙醫院采取隔離方式截斷病因,即《黃帝內經》中所說的“避其毒氣”,也是中國自古以來預防瘟疫流行最有效的措施。
根據WHO報道[7],大約80% COVID-19患者癥狀較輕,14%左右會轉為重癥,5%左右轉為危重癥。因此對COVID-19輕癥、普通型患者進行中藥干預,截斷病勢,顯得極其重要,降低轉重率就可以間接降低病死率。由于輕癥、普通型患者達數萬人,致病因素一樣,癥狀相近,證同則治同,所以采取的辨病治療,通治方給藥,取得了良好的治療效果。有報道顯示[8],江夏中醫方艙醫院采用宣肺敗毒或清肺排毒湯劑等中藥治療,收治的564例患者無1例轉為重癥,有效地截斷了病勢發展。
同時,治療時也可結合辨病結果及最新中藥抗病毒研究成果,選擇加用具有一定抗冠狀病毒作用又切合辨證病機的的特效藥物,如有研究顯示桑葉、蒼術、金銀花、連翹、浙貝母、生姜、草果7味中藥可能通過阻斷多個人體內血管緊張素轉化酶與新型冠狀病毒的結合位點[9],預測上述中藥可能具有治療COVID-19的作用,也有研究發現虎杖、大黃、山豆根等可能對新型冠狀病毒有抑制作用[10]。這樣有利于截斷病情傳變,收到更好的治療效果。
2.3 巧用下法,降低轉重率,截斷重轉危重癥,促進康復 《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診療方案(試行第七版)》[1]將COVID-19分為醫學觀察期和臨床治療期,其中臨床治療期分為輕型、普通型、重型、危重型、恢復期5型。在證型上輕型分為寒濕郁肺、濕熱壅肺型;普通型分為濕毒郁肺、寒濕阻肺型;重型分為疫毒閉肺、氣營兩燔型;危重型為內閉外脫證;恢復期分為肺脾氣虛、氣陰兩虛型。但是COVID-19具有發展快、病勢重的臨床特點,部分表現出的臨床癥狀會滯后于真實的病情進展,再加上疫情嚴峻形勢下中藥供給到患者服用的速度稍慢,若只見癥辨證會有渴而鑿井,斗而鑄錐的被動之勢,因此辨證論治不但要從“有”處入手,也要從“無”處揣測,明晰COVID-19的發展趨勢,提前用藥截斷。根據溫病“下不嫌早”的截斷療法思想,通腑瀉下可用于COVID-19的治療,既能祛無形之熱,又可除有形之滯,可先病機而至,截斷疾病傳變,符合吳又可提出的“勿拘于下不厭遲”之說。臨床實踐也表明[11-12],在治療乙型腦炎以及嚴重急性呼吸綜合征(SARS)時,早期即用大黃等中藥攻下蕩滌邪熱,能很好的控制疾病發展,預后較佳。因此在治療COVID-19時,注重觀察患者大便情況,辨證論治,巧用下法,截斷病勢,阻止輕型轉為重型,對于COVID-19的治療具有重要價值。
國家方案中的各證型都給出了推薦的方藥,其中濕毒郁肺證的宣肺敗毒湯體現了截斷療法的思想。宣肺敗毒湯是在麻杏石甘湯、麻杏薏甘湯、葶藶大棗瀉肺湯、千金葦莖湯等基礎上組方。全方共13味中藥:生麻黃、苦杏仁、生石膏、生薏苡仁、茅蒼術、廣藿香、青蒿草、虎杖、馬鞭草、干蘆根、葶藶子、化橘紅、生甘草。主要功效是宣肺化濕、清熱透邪、瀉肺解毒。其中加葶藶子、虎杖是為瀉肺泄下,先證而治,逐邪外出,截斷傳變。
根據劉清泉教授在武漢一線的治療經驗,對于新冠肺炎重癥有便秘癥狀的患者,也應及時采用通腑泄濁的方法,而且越早越好。予中藥湯劑通腑、瀉濁、促動力,生大黃 30 g,厚樸 15 g,人參 30 g,枳實30 g,玄參 30 g,生地 30 g,麥門冬 30 g,芒硝(另包)15~30 g,水煎300 mL,鼻飼分3次。若大便通,腸鳴音開始恢復去掉芒硝。以上立足于吳又可“早逐客邪,重視下法”的學術思想,早用泄下之法,及時泄下能夠防止邪入營血轉為氣營兩燔、內閉外脫等危重癥,降低轉重率,截斷病情傳變。
疫病治療前期以祛邪為主,但求中病即止,不可過用下法而傷正,因此在祛邪后要提前注重扶正,特別是在康復期需辨證調治,重視調補氣血陰陽,同時重視精神調護,避免傷正而生變證。康復期雖然核酸轉陰,但是新型冠狀病毒對臟器及免疫系統的損傷仍未修復,因此要重視臟器及免疫系統的保護,避免后遺癥的發生,促進康復。
3 截斷療法在COVID-19診療中的應用意義
COVID-19具有發展快、病勢重、威脅大的臨床特點,中醫學認為其屬于瘟疫范疇,主要病性特點為濕毒,可稱之為濕毒疫。濕毒疫是以濕毒為典型特點的疫病,濕邪為患往往起病癥狀不嚴重,癥狀看似溫和,但其傳變迅速,可突然病情轉重,且病情復雜,多生變證,部分重癥,纏綿難愈。因此把握COVID-19疫病的屬性,知道其傳變必定要經過某個階段,采取先行一步的方法,在“截斷療法”思想的指導下提前用藥,截斷其病程的發展,可以為治療爭取主動。對隔離的“四類人群”中早期干預,先證而治,可以截斷傳變;對于輕癥、普通型患者,截斷療法通治方給藥,可有效降低轉重率;對于重癥患者中西結合,中醫辨證論治,一人一策,早逐客邪,重視下法,同時注重扶正、臟腑功能保護可以截斷重癥轉向危重癥,降低病死率。對康復期患者也可根據病情積極辨證論治,促進早日康復,防止嚴重后遺癥出現。
總之,“截斷療法”是從提高臨床療效出發而提出的一種治療學思想,對COVID-19的防治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