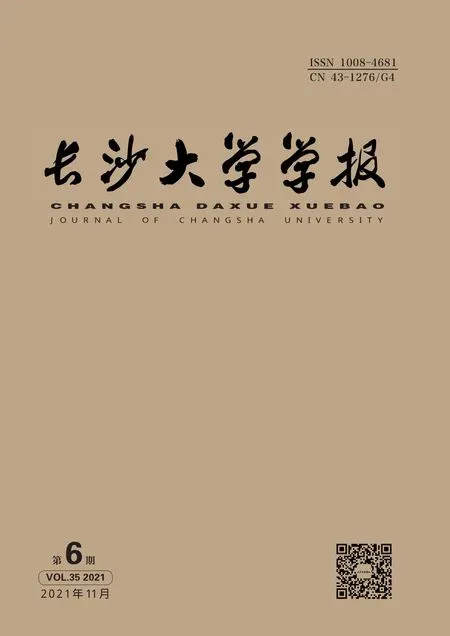文旅視域下湖湘名人故居的價值管窺
魏穎
(中南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湖南 長沙 410083)
一 文化旅游與湖湘名人故居的開發
文化旅游簡稱文旅,指通過旅游體驗各地傳統文化、民俗風情,追尋文化名人遺蹤,實現感知、了解、體察人類文化具體內容之目的的行為過程。文化旅游是一個包含了地方產業、生態建設和文化建設等諸多領域的綜合課題,其著眼點是經濟,而文化則是文化旅游發展的持久動力。習近平強調,要“努力實現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使之與現實文化相融相通,共同服務以文化人的時代任務”[1]313。隨著人們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人們對精神消費的需求也不斷攀升。深入挖掘名人故居的歷史文化價值,使文化旅游一方面成為開展愛國主義教育和優秀傳統文化教育的重要方式,另一方面成為推動地方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內生力量,這是實現中華民族文化振興,影響當地群眾和觀光游客文化自覺的重要舉措。
所謂文化自覺,按費孝通的解釋,其意義在于“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對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來歷、形成的過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的發展的趨向,自知之明是為了加強對文化轉型的自主能力,取得決定適應新環境、新時代文化選擇的自主地位”[2]403。費孝通的文化自覺論要求實事求是地認識某個民族、某個地區、某個共同體的文化,在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格局中“形成一個你來我去、我來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個性的多元統一體”[3]3。將文化和旅游有機結合,通過旅游感知文化、品味文化,不僅能夠弘揚民族精神和時代精神,普及歷史文化知識,而且能產生巨大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
湖南是湘軍的故鄉,是戊戌變法、辛亥革命、國民革命與農民運動的重要地區之一,產生過一大批對中國歷史有重要影響的人物。從魏源提出“師夷長技以制夷”的主張,到曾國藩、左宗棠創立湘軍、推崇洋務運動;從譚嗣同、唐才常獻身維新變法,到黃興、宋教仁在辛亥革命中引領風騷;從蔡鍔高舉護國討袁的義旗到毛澤東、劉少奇、任弼時、彭德懷、賀龍等走出湖南,奏響締造新中國的凱歌……這些湖湘名人的故居蘊含傳統文化的精髓和紅色文化的基因,不僅是湖湘文化的實物坐標,而且是鄉鎮經濟、文化發展的得天獨厚的優勢資源。隨著高鐵和高速公路的興起,出現了文化旅游熱。合理開發和利用鄉鎮名人故居,使名人故居所承載的思想價值和文化價值滲透到區域經濟發展中形成文化資本,從而增強地域經濟發展的競爭力,產生直接的經濟效益,是當下鄉村振興的重點。
以毛澤東的故鄉韶山為例,近年來大力發展文化旅游產業,依托韶山沖毛澤東故居,建設了毛澤東銅像廣場、毛澤東同志紀念館、毛氏宗祠、毛澤東紀念園、滴水洞景區、韶峰景區,促進了交通運輸、文化創意、鄉村民宿等產業在融合發展中同步升級、同步增值、同步受益。目前,毛主席像章、毛主席雕塑、毛主席畫冊、毛主席圖書等文創產品,毛公酒、毛記麻花等地方特產,“夢回韶山”等文旅項目已發展為特色文化產業,成為韶山增加收入的重要途徑。譬如,距離毛澤東故居20分鐘車程的銀田鎮銀田村,利用紅色文化資源,種植靈芝苗木、辦研學基地、開農家樂、發展田園旅游經濟,使曾經貧困的村民安居樂業,奔上了小康生活。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隨著紅色旅游的發展,韶山的基礎設施也日益完善,高速公路和高鐵四通八達,全國首個“國內—長沙—韶山”黨史紅色旅游線路“空鐵聯運”服務產品正式上線。當地政府部門將進一步依托毛澤東故居,與地方高校、科研院所、行業企業以及國際組織進行深度合作,凝聚海外傳播力量,充分發揮高校海外校友會、海外商會、學術交流會等平臺作用,促進經貿文化一體化,積極推進湖湘文化“出海”。
需要強調的是,文化旅游不單單需要創造物質文明,也同樣需要創造精神文明,精神文明是構成地域經濟社會凝聚力和競爭力的關鍵要素。仍以韶山為例,在黨和政府部門的大力倡導下,在開發旅游產業的同時,弘揚紅色文化和革命優良傳統,促進鄉風文明建設,努力營造積極向上、充滿活力的地域精神風貌。紅色文化所蘊含的崇高的理想信念、深厚的愛國情懷、積極進取的精神氣質潛移默化地影響了韶山人民,并成為引領生態宜居和生活富裕的內生創造力,使得來自五湖四海,去韶山學習、旅游、考察的每個人都能感受到韶山充滿活力、和諧有序的鄉村文明新風尚,這又進一步帶動了韶山紅色旅游產業的可持續發展。
簡而言之,充分開發湖湘名人故居資源,發展文化旅游產業,從而使文化成為實現人們美好生活的內生力量,帶動地方經濟、生態、交通運輸各方面的發展,讓廣大人民群眾實現精神層面和物質層面的富足與強大,是值得探討的課題。
二 湖湘名人故居的精神價值
湖南人杰地靈,特別在近現代涌現了許多影響中國,乃至世界的杰出人物。文化先賢、革命先烈、偉人前輩的故居在湖南星羅棋布,且主要分布在鄉村、鄉鎮。這些名人遺跡往往以故宅、楹聯、照片、器物等物質形式流傳下來,許多故居附近還建造有紀念館、文化園、風景區,對名人的精神、事跡進行更為具體的呈現和更為翔實的介紹,使得故居與湖湘歷史人物的光輝事跡、思想精神相互交織、相互作用,使故居成為湖湘文化精神的物質載體。在長期的歷史發展過程之中,“湖湘文化形成了以憂患意識和事功化人生價值取向為核心的精神內涵”[4]275。從具體的表現來看,湖湘名人故居所承載的思想價值和精神價值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矢志不渝的民族氣節
考察明末清初思想家、文學家和哲學家王船山(1619—1692)晚年隱居的湘西草堂(位于衡陽縣曲蘭鎮),可以感受王船山矢志不渝的民族氣節和學術追求。王船山4歲發蒙,伴大哥王介之讀書,7歲讀完十三經,14歲中秀才,24歲中舉人。清軍入關阻斷了王船山的科舉之路,他從一位飽讀圣賢書的讀書人轉變為反清復明的斗士。清順治五年(1648年),王船山在衡陽舉兵抗清,阻擊清軍南下,失敗后繼續追尋南明朝廷,投奔肇慶,任南明桂王政府行人司行人之職。后因彈劾王化澄等弄權亂國,王船山身陷囹圄,獲救后,投奔桂林瞿式耜繼續抗清。桂林陷沒,瞿式耜殉難,為避清廷緝害,王船山過上了流亡生活。他輾轉湘西、湘南,變姓名易衣冠為瑤人,借居于瑤人村寨、荒山古剎和山洞之中。永歷政權滅亡后,反清復明的事業已非常渺茫,王船山選擇在窮鄉僻壤衡陽縣石船山歸隱,并在此修建了三間茅屋,名曰“湘西草堂”。今天的湘西草堂,仍保留了原初的建筑格局,其中堂掛有王船山的畫像,畫像兩旁有一副對聯“六經責我開生面,七尺從天乞活埋”。此聯原為1669年冬王船山由敗葉廬遷往觀生居自題的堂聯,表達了王船山希望通過重建與再造中華民族經典,將中國傳統文化繼往開來的使命感,以及作為一代遺民,在社稷傾覆之際的悲憤心理。王船山在湘西草堂默默耕耘了17年,直至逝世。
江山的改朝易代,雖然給王船山的身心造成了巨大的摧殘,但也使他走出書齋,廣泛接觸社會現實,以及底層勞動人民的艱辛生活,為他晚年在湘西草堂潛心治學,關注并思考中華民族的歷史命運夯實了基礎。王船山不僅以錚錚鐵骨的民族氣節光耀千古,更以其學術思想遺澤后世。他一生著作約100余種,400多卷,近千萬字,學術研究遍及經、史、子、集各個領域。一直到今天,王船山依然是中國學術史上著作最多的學者之一。隨著“船山學”研究的深入,船山思想正逐步走向世界。日本、韓國、俄羅斯、美國、法國、德國、加拿大、英國、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國涌現了一批又一批“船山學”研究者,“西方有一個黑格爾,東方有一個王船山”越來越被世界文明之林所接受和認同。王船山晚年隱居的湘西草堂吸引了來自各地的中外游客,成為聞名遐邇的文化旅游勝地。
(二)經世致用的擔當精神
在湖南省邵陽市隆回縣司門前鎮學堂灣村,有一座建于清乾隆初年,兩正兩橫的木結構四合院,這就是中國近代史上著名的愛國主義思想家、史學家和文學家,“睜眼看世界”的最優秀代表之一魏源(1794—1857)的故居。魏源故居的兩棟正房和左廂房均為平房,右廂房則為兩層樓房,面闊七間,進深四間,底層五間為谷倉,兩端為樓梯間;二樓為讀書樓,正中三間為講堂,兩梢間為書房。在右廂房的二樓,魏源度過了他的童年和青少年時期。由于刻苦讀書,魏源常常足不出戶。魏源書齋中一塊木牌上的文字記載了“狗不識主”的典故:魏源7歲入家塾讀書,其勤奮刻苦遠超一般弟子。他喜歡把自己關在書齋中閉門苦讀,以至于偶一外出,竟引起家犬群嗥。
在魏源故居,懸掛有多副魏源親自撰寫的對聯,諸如“讀古人書求修身道,友天下士謀救時方”“功名待寄凌煙閣,憂樂常存報國心”“盡交天下士,長讀古人書”“學貴運時策,友交立德人”等,還有清代文學家龔自珍為魏源題寫的一聯:“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綜一代典,成一家言。”這些對聯傳達了魏源憂國憂民的胸襟抱負,以及為了運籌時政、經理世事而讀書的思想。根據故居的圖片及文字介紹,可以獲悉魏源生活在中國由封建社會向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急劇轉變的時期。鴉片戰爭的失敗,使魏源對國家和民族的命運憂心如焚,產生了強烈的經世濟民的思想,提出了向西方學習的綱領性命題“師夷長技以制夷”。魏源的代表作為《海國圖志》,其主體部分是介紹世界主要國家的歷史、地理、經濟和人文狀況。雖然魏源沒有機會走出國門,但到過當時尚在侵略者手中的香港和澳門。在香港和澳門,魏源看到了與內地不同的人文習俗和政治經濟情況,為他編纂《海國圖志》增加了感性認識。魏源經世,主要靠其著述影響當時及后代的經世者。此外,在為官期間,魏源也做了不少勤政愛民的實事,諸如“改建書院,儲卷籍,置義冢,設義學,整飭育嬰堂、恤嫠會,傳種牛痘,興水利,培地脈”[5]96。無論是治學,還是勤政,魏源都展現了經世致用的擔當精神,以及一代知識分子對國家和民族命運、前途的思考。
(三)心憂天下的使命意識
在湘陰縣樟樹鎮巡山村柳家沖,保存有晚清民族英雄左宗棠(1812—1885)早年的故宅柳莊。根據柳莊景區的介紹,1843年,左宗棠用主持教學所得的積蓄在湘陰柳家沖置田70畝、山地80畝,并親自設計建造了一座占地4畝多、有48間房屋的磚木結構庭院。由于左宗棠摯愛柳樹的不折品格,其在住宅周邊栽種了許多柳樹,并將此庭院起名為“柳莊”。
樸存閣為左宗棠在柳莊的居室,進門有一楹聯:“身無半畝,心憂天下;讀破萬卷,神交古人。”“身無半畝,心憂天下”說的是一種身處逆境而不挫其志的自強不息精神,一種憂國憂民的擔當精神;“讀破萬卷,神交古人”說的是胸有丘壑、借鑒古人,且能博古通今、經世致用。此聯表現出遠大的志向和格局,可以說是左宗棠一生修身勵志的座右銘——他早年科舉并非一帆風順,三次會試都名落孫山后,便絕意科舉,開始廣收博取,將自己的興趣放在農田、水利、地理等務實學問方面,經過多年刻苦自學,年逾不惑方踏上仕途,41歲出山任事,50歲擔任浙江巡撫,54歲籌辦福州船政局、創辦馬尾造船廠,68歲抬棺出征,71歲自請赴福建督師、抗擊法寇……憑借過人的天資稟賦,心憂天下的胸襟抱負,以及“讀破萬卷,神交古人”的積累,又遭逢崛起的機遇,左宗棠不僅在晚清時期成就了千秋功業,也成為身處逆境百折不撓,憑借真才實學立身揚名的典范。柳莊現已成為愛國主義教育的示范基地,柳莊越來越成為人們來湖南觀光旅游的必選之地。
(四)堅韌不拔的奮斗精神
偉大的教育家、革命家徐特立(1877—1968)先生的故居位于長沙縣五美鄉(今江背鎮)特立村觀音塘。參觀故居時,可以了解徐特立教育救國、孜孜不倦、艱苦奮斗、無私奉獻的一生。徐特立出生于五美鄉荷葉塅一個貧苦農民家庭,18歲開始從事教育行業,在五美鄉小塘灣開設蒙館,20歲制訂和執行“十年破產讀書”計劃,28歲創辦梨江高小和五美初小。此外,徐特立還創辦了私立長沙女子師范學校,擔任過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師范學校、長沙縣立師范學校的校長,在周南、長郡、明德、修業等學校都授過課,被稱為長沙教育界的“長沙王”。
在徐特立故居,至今仍保留左右兩間教室,簡單樸素的課桌、板凳、講臺、黑板,還原了100多年前徐特立在家鄉捐居辦學的場景——1915年,徐特立用自己在長沙教書所得的部分薪金對自家老屋加以改建,將其作為五美高級小學校舍,另外還擴建了兩間教室。徐特立故居還以文字介紹和圖片的形式呈現了不少關于徐特立的感人事跡:1927年5月,反動軍閥何鍵在湖南策動了“馬日事變”,瘋狂屠殺共產黨員,鎮壓工農運動,在投機分子相繼投敵的情況下,徐特立卻毅然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34年10月,徐特立以57歲高齡參加二萬五千里長征,成為黨和紅軍隊伍中年齡最長,以超人毅力克服難以想象的艱難險阻的楷模;1936年,59歲的徐特立在陜北保安推行新文字,領導廣大群眾掃除文盲;徐特立60歲生日時,毛澤東在祝壽信中寫道:“你是我二十年前的先生,你現在仍然是我的先生。”至今,在徐特立故居的門楣上還懸掛有一塊紅色的匾額“堅強的老戰士”,這是毛澤東為徐特立七十壽辰的題詞,概括了徐特立立志教育救國,并為這個理想奮斗了一生的堅韌不拔的優秀品質。
另外,寧鄉有劉少奇故居,瀏陽有譚嗣同故居,湘陰有郭嵩燾故居,邵陽有蔡鍔故居,婁底有曾國藩故居和蔡和森、蔡暢故居,懷化有向警予故居……這些湖湘名人故居既有共性,又有各自的特色,其共性表現為作為湖湘名人思想精神的物質載體,成為愛國主義教育、革命傳統教育和人文歷史知識教育的基地;同時,由于湖湘名人各自有獨特的人生經歷和個性,使得其故居所傳達的價值觀又各有所側重。深度挖掘并生動展現湖湘名人故居的精神價值,是提升中華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的有效途徑。
三 湖湘名人故居的文化價值與經濟價值
名人故居復原了革命先驅、文化精英當年生活的場景,陳列了反映名人生平思想的文物、歷史圖片,不僅成為旅游觀光的景點,讓游客受到崇高精神的感召,而且是鄉鎮經濟賴以發展的特色優勢資源,能為當地的文化振興提供精神動力和智力支持。鄉村振興既要把名人故居作為“一種促進鄉村發展活力釋放的資源要素,建立起文化與地理環境、經濟產業、制度政策之間的銜接,又要回歸‘人是目的’而實現美好生活的價值原點”[6]。將名人故居的資源優勢轉化為現實生產力,打造文化旅游品牌,發展文化旅游產業,促進文化建設、環境保護、商貿服務、交通電信等相關事(行)業的發展,增加當地居民的就業機會,提高人們的生活水平和文化素質,帶動城鄉經濟建設和文化發展,是當下許多鄉鎮實現文化振興與經濟發展的重要舉措。接下來筆者主要以寧鄉花明樓鎮為例,闡釋其發揮劉少奇故居的資源優勢,發展文化旅游產業,以點帶面,帶動花明樓鎮包括交通運輸、餐飲服務、商業貿易等在內的第三產業的發展,實現鄉鎮經濟建設與文化建設欣欣向榮。
(一)名人故居建設與愛國主義教育、歷史人文教育協調發展
寧鄉花明樓鎮是劉少奇同志的故鄉,先后獲得了“中國文明鎮”“中國環境優美鄉鎮”“湖南省最具發展潛力鄉鎮”等榮譽稱號。隨著國家紅色旅游事業的迅速發展,花明樓鎮著力打造花明樓景區,提煉花明精神,開展愛國主義教育和革命傳統文化教育。花明樓景區以劉少奇故居與劉少奇紀念館為主體,建設有劉少奇故里門樓廣場、劉少奇銅像廣場、劉少奇文物館、炭子沖民俗文化村、花明園、花明樓、劉少奇坐過的飛機、萬德鼎、九龍柱、修養亭、懷念亭、一葉湖等景觀。
劉少奇故居始建于清同治十年(1871年),系土木結構的四合院建筑,由正屋、偏廈、外坪、內院等組成,屋頂大部分為小青瓦,小部分為茅草,墻面是和了糠殼的黃泥墻,屋前有池塘,屋后為山巒。故居的房屋大大小小共計二十一間半,其中包括劉少奇的臥室、書房,劉少奇父母、兄長的臥室,還有堂屋、酒房、農具室、烤火房、碓房、廚房、飯堂、牛欄屋、豬欄屋等,再現了20世紀初江南農家民宅的典型風貌,以及劉少奇在這里讀書、生活、召開小型會議的場景。1961年,劉少奇偕夫人王光美回鄉調查農村情況,在故居住了一個星期,走訪了當地的許多農民及農村基層干部,看到不少農民住房擁擠,決定將舊居房屋及鍋灶桌凳全部分給農民。“文化大革命”時期,故居橫遭破壞,文物失散。20世紀80年代黨和政府組織相關部門對故居按照原樣進行了修復,在正門懸掛由鄧小平同志題寫的“劉少奇同志故居”的匾額,在故居里陳列劉少奇家用過的木屐、油傘、斗笠、農具等實物器具,以及相關歷史圖片數百張。
劉少奇故居附近建立了全國唯一一家系統、完整地介紹劉少奇生平業績的傳記性專館——劉少奇紀念館,其以劉少奇生平為主線,采用生平加專題相結合的形式,反映劉少奇光輝而偉大的一生。故居附近還修建了修養亭,修養亭得名于劉少奇的光輝著作《論共產黨員的修養》,其內陳列有劉少奇《論共產黨員的修養》提綱手跡,歷代名家對《論共產黨員的修養》的認識,以及黨和國家領導人對《論共產黨員的修養》的評價,以供游客參觀、學習、瞻仰。
(二)紅色文化與湖湘文化有機交融
劉少奇故居及紀念館目前是全國非常重要的愛國主義教育示范基地之一,革命紀念地和紅色旅游景點之一。為了充分發揮名人故居文化軟實力的優勢,花明樓景區在劉少奇故居附近建立了富有湖南典型農家特征的炭子沖民俗文化村和彰顯湖湘文化底蘊的花明樓,使人文風情和當地環境有機結合,促進了紅色文化與湖湘文化相互交融、融匯共進。
炭子沖民俗文化村以反映湖南農村生產、生活習俗為主題,營造一種典型的20世紀初湖南農村生產、生活場景,有織布房、農具房、煮酒房,陳列有極富地方特色的織布機、農具和各式生活用品。民俗文化村還有現做現賣的劉家老酒、劉家米糕、蘿卜糖、砂仁糕、冰姜、刀豆花、紫蘇梅,游客在參觀農耕時代小型作坊的同時也能購買和品嘗各式各樣的寧鄉土特產。
花明樓則以湖湘文化陳列為主題。第一層陳列有《花明樓記》,張掛有諸多名家撰寫的楹聯,以及配有古詩與山水圖的“寧鄉十景”(玉潭環秀、大溈凌云、香山鐘韻、飛鳳朝陽、湯泉沸玉、石柱書聲、天馬翔空、獅顧嵐光、樓臺曉色、靈峰夜月)的景觀介紹;第二層陳列有寧鄉出土的青銅器復制品;第三、四層為湖湘文化名人陳列,有對屈原、賈誼、周敦頤、魏源、曾國藩、左宗棠、黃興、蔡鍔等人的簡介,與岳麓書院的楹聯“惟楚有材,于斯為盛”構成了互文回響;第五層是青年劉少奇的雕塑。
通過策劃展覽,舉辦各種文化活動,大力加強旅游配套設施建設,花明樓風景區為觀光者提供了一個集旅游觀光、參觀學習、休閑度假為一體的交往空間,讓游客在濃郁的紅色文化與湖湘文化氛圍中體驗偉人成長的人文環境,與偉人對話,從而獲得心靈升華。
(三)文化生態旅游與經濟發展融匯共進
雖然以劉少奇故居及紀念館為中心的花明樓景區在紅色文化旅游上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但作為單一的旅游景點,難以形成集約型品牌,吸引更多的中外游客。目前,在鄉村振興戰略的引領下,依托劉少奇故居,圍繞花明樓景區,相關部門正在開發、建設芙蓉寨、雙獅嶺文化園、楚文化遺址大夫堂、道林古鎮等景區項目,打造旅游文化產品和品牌,努力創建文化與自然共生共榮的文化生態旅游產業。另外,花明樓鎮的居民不僅可以依靠餐飲、農副產品、文創手工等各種項目創收,而且在耳濡目染紅色文化的同時也與來自各地的游客交流、接觸,開闊了眼界,提高了文化素質。
值得一提的是,劉少奇故居距離韶山毛澤東故居僅37千米,距離烏石彭德懷故居也不過55千米,這三位偉人的故居構成了全國獨一無二的“偉人故里紅三角”,便于建立區域合作、線路對接、市場互動、互利共贏的共同體:以愛國主義教育、革命傳統教育作為主打產品,注重講好偉人故事,詮釋偉人精神,對參觀游覽者進行“潤物細無聲”的精神陶冶;以觀光度假、休閑娛樂作為補充產品,在傳播革命優良傳統的同時推動其他行業的發展,增強花明樓鎮、烏石鎮、韶山的整體財力,這反過來又有利于實現紅色旅游產業的可持續發展。
在湖南,除了在寧鄉依托劉少奇故居建立花明樓景區之外,還在汨羅依托屈子祠建立了屈子文化園,在永州依托柳子廟建立了零陵古城,在韶山依托毛澤東故居建立了韶山風景區,在烏石依托彭德懷故居建立了烏石峰村三十六坊……這些依托名人故居發展起來的文化產業,在推動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傳統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社會發展的各個方面的同時,一定程度上實現了城鄉互惠互利,由文化資源到文化資本的轉變。
綜上所述,名人故居不僅是名人思想、精神的物質載體,而且是地域經濟、文化發展的特色資源。湖湘杰出歷史人物所表現的矢志不渝的民族氣節、經世致用的擔當精神、心憂天下的使命意識、堅韌不拔的奮斗精神等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高度契合,并能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提供強大的內生性精神動力。深度挖掘湖湘名人故居資源,將故居所承載的精神價值和思想價值生動形象地呈現出來,并依托故居規劃有著文化積淀和文化傳承的鄉鎮形象,使名人故居建設與愛國主義教育、歷史人文教育協調發展,紅色文化與湖湘文化、生態文化有機交融,文化旅游與鄉村經濟發展融匯共進,不失為助力新時代鄉村振興的有效途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