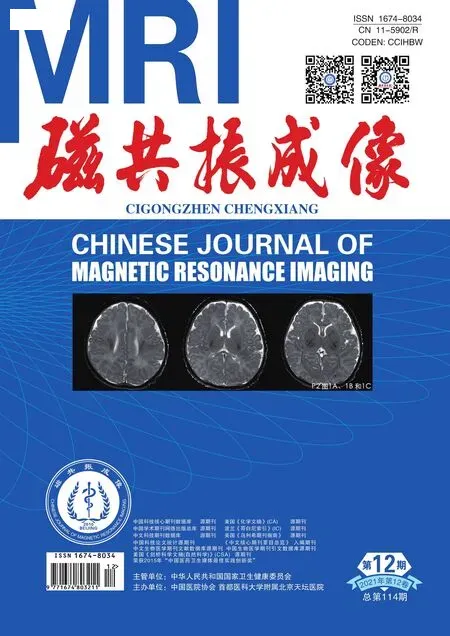MRI預測高級別膠質瘤術后復發模式的研究進展
劉毛毛,賀業新
作者單位:1.山西醫科大學,太原030001;2.山西醫科大學附屬人民醫院磁共振室,太原030012
腦膠質瘤是中樞神經系統最常見的惡性腫瘤[1]。高級別腦膠質瘤(high-grade glioma,HGG)惡性程度高,腫瘤細胞異質性高,呈浸潤性生長,手術難以徹底切除。通常術后需要輔助放療、化療或者同步放化療,但是術后復發率仍然很高。不同復發模式的HGG患者其生存預后也存在很大差異[2]。MRI是預測HGG復發模式的重要手段,其不僅可以通過對腫瘤術前位置、體積、形態的測量分析來預測復發模式,還可以提供組織代謝、化學環境變化等信息。準確地預測HGG復發模式有很大意義。因此,有關HGG復發模式的影響因素正在研究和探索中。
1 復發模式
目前,HGG 術后復發模式還沒有統一定義,使用的分類基于所研究的具體因素而定。有研究[3,26]根據復發腫瘤與放射治療目標的空間關系將復發模式分為野中心復發、野內復發、野邊緣復發及遠處復發。野中心復發為復發灶在95%的等劑量曲線內的體積≥95%;野內復發為復發灶在95%的等劑量曲線內的體積<95%且≥80%;野邊緣復發為復發灶在95%的等劑量曲線內的體積<80%且≥20%;遠處復發為復發灶在95%的等劑量曲線內的體積<20%。其中野中心、野內、野邊緣復發也稱局部復發。也有研究[4]根據復發灶距離術腔的距離將復發模式分為局部復發、非局部復發。普遍將局部復發定義為復發灶位于原術腔內、與術腔相連續或與術腔不相連且距離腔外2 cm 范圍內;非局部復發則是指與術腔不相連且超出腔外2 cm范圍[5,6]。非局部復發包括遠距離復發、室管膜下和軟腦膜播散。HGG 復發模式與諸多因素有關,包括基因、治療方案等臨床因素和腫瘤位置、體積、水腫程度等腫瘤因素。
2 通過臨床因素預測HGG復發模式
2.1 患者基因
HGG 具有生物異質性,分子遺傳學是HGG 復發模式的一個決定性因素[7]。Yoon等[8]認為局部復發膠質母細胞瘤(glioblastomas multiforme,GBM)具有原發腫瘤所攜帶的大部分突變基因,呈線性進化;遠距離復發GBM 僅攜帶一部分原發腫瘤的突變基因,呈分支進化。HGG不同復發模式的發生與患者體內某些基因改變有關。Yamaki 等[9]通過167 例GBM 患者的基因檢測和復發模式分析認為CD133 高表達與遠距離復發有關。Tini 等[7]研究認為表皮生長因子受體表達量越低,復發模式就越傾向野中心和野內復發。Ge 等[4]研究認為信號蛋白P53、細胞增殖抗原標記物Ki-67 表達增加與非局部復發的發生有著密切關系。Jiang等[2]研究認為O6-甲基鳥嘌呤-DNA 甲基轉移酶啟動子的甲基化是非局部復發的危險因素。Back等[10]研究認為異檸檬酸脫氫酶(isocitrate dehydrogenase,IDH)野生型膠質瘤患者局部復發比例明顯高于IDH 突變型。患者的基因改變也會影響腫瘤的表現,進而間接預測復發模式。Jungk 等[11]研究發現IDH 突變型患者更易出現室管膜下區(subventricular zone,SVZ)受累,SVZ 受累患者非局部復發率較高。
2.2 治療方案
目前,手術仍然是HGG 治療的基礎,神經導航技術和術中MRI 可實現腫瘤的可視化,能夠更準確地切除HGG。HGG 的標準術后輔助治療是聯合放化療,近年來分子靶向治療、免疫治療以及腫瘤電場治療均取得了一定突破[12]。治療方案的選擇和實施對復發模式及患者生存預后有著較大影響。有研究[13]認為擴大手術切除范圍可以增加非局部復發的概率。Jiang 等[2]認為擴大手術切除范圍、放療與復發模式并沒有明顯的相關性,化療是非局部復發的保護因素。而Choi 等[14]研究認為放療是非局部復發的危險因素。也有學者[4]認為與單純化療相比,術后聯合放化療能夠更有效地抑制局部腫瘤生長,非局部復發率更高。
3 通過MRI預測HGG復發模式
3.1 常規MRI技術
MRI 多序列、多方位成像,能較好地顯示腫瘤以及腫瘤與周圍腦組織的關系。尤其是近年來神經導航通過3D 薄層重建實現了對腫瘤位置、邊界、體積的準確評估以及對手術入路的精準設計,提高了切除的準確性[16]。神經導航結合術中MRI不僅能夠避免損傷重要腦功能區,還能提高腫瘤切除率。
3.1.1 腫瘤體積
腫瘤患者手術前后病灶大小是評估患者病情的基本量化指標。大多研究對術前腫瘤體積的測量采用二維公式計算和三維重建方法。神經導航通過3D 薄層重建能夠更加精確地獲得腫瘤大小及周圍浸潤生長的相關信息。Tejada等[17]研究認為術前T1WI 增強相上腫瘤體積高于54 cm3的患者非局部復發率為66.6%,FLAIR 相上腫瘤體積變化與復發模式之間無顯著相關性。術后殘留病灶體積的測定,主要是為了確定手術切除程度,而切除程度的大小對復發模式有一定的影響。目前術中MRI能夠使手術切除程度更精確化。
3.1.2 腫瘤位置
神經導航結合常規MRI 可以直觀地體現腫瘤位置和邊界,很好地顯示腫瘤體積和腫瘤灶多少。SVZ包含大量的神經原始細胞及腫瘤干細胞,腫瘤干細胞具有自我更新、無限繁殖、多向分化和遷移特性。Huang 等[18]認為腫瘤接觸SVZ 是腫瘤復發的獨立危險因素。有研究[2,19]認為HGG患者SVZ受累與軟腦膜播散、遠處復發和生存率降低有關。也有研究[9,11]通過分析SVZ、皮質雙重因素對復發模式的影響發現,術前SVZ 未受累、皮質受累組患者更易出現非局部復發;單純SVZ 受累不影響HGG的復發模式。膠質瘤根據病灶數目多少常表現為單灶性和多灶性,二者的治療方案、預后結果不同[20]。Rades等[21]認為多灶性HGG 患者生存率明顯低于單灶性HGG 患者。多灶性GBM 患者預后不佳與Ki-67 增殖指數增加有關[22]。Syed 等[23]也認為多灶性GBM患者預后較差,但單灶性GBM患者與多灶性GBM患者的復發模式相似。
3.1.3 水腫程度及形態
HGG術后復發易發生于瘤周水腫區[24],瘤周水腫促進了膠質瘤細胞的侵襲,明顯影響患者的預后。根據術前瘤周水腫可以預測HGG 術后復發模式,進而為準確勾畫靶區提供依據。HGG 復發模式與瘤周水腫程度和水腫形態相關。劉水源等[25]認為水腫程度較輕、水腫形態為類圓形患者,復發模式以局部復發為主;水腫程度較重、水腫形態為不規則型患者,復發模式多傾向非局部復發。瘤周水腫越重,水腫區的膠質瘤細胞數量越多、侵襲范圍越廣,復發模式就越傾向非局部復發。而Tu 等[26]認為瘤周水腫越重,野內和野邊緣復發概率越高。由此可見瘤周水腫對HGG患者復發模式的影響尚無定論。
利用常規MRI結合神經導航預測HGG復發模式具有重要的意義,然而其只能單純地反映腫瘤位置、體積、形態和水腫區等宏觀信息,不能提供代謝、病理生理和功能等多維度信息。
3.2 擴散加權成像
擴散加權成像(diffusion weighted imaging,DWI)是一種單指數模型,基于體內水分子的微觀運動僅受水分子擴散運動的影響,表觀擴散系數(apparent diffusion coeficient,ADC)值可對水分子擴散運動的受限程度進行量化評估。
DWI對于診斷急性腦梗死具有較高敏感度和特異度,已經成為診斷急性腦梗死常用的影像學檢查方法。Furuta等[27]認為GBM患者術區周邊圍繞DWI高信號提示預后較好,其總生存期和無進展生存期較長。腫瘤通過產生復雜的微血管網絡滿足其營養需求,術區血管損傷阻斷了周圍組織的血液供應,破壞了腫瘤生長的微環境,因此術區周圍梗死范圍可能與HGG復發模式有關。Thiepold等[28]研究認為術區周圍發生梗死的GBM患者比未發生梗死的患者更易發生遠距離復發。Bette等[29]研究也顯示術后梗死體積越大,患者越有可能出現遠距離復發,同時復發灶越易接觸到室管膜和硬腦膜。Curtin等[30]認為除了梗死造成的低氧環境之外,腫瘤細胞的固有遷移和增殖速率也是驅動非局部復發的關鍵因素。但也有研究[31]認為非梗死組和梗死組之間局部復發比例無顯著差異。
水分子的微觀運動受到水分子擴散和毛細血管內血液循環雙重影響。DWI僅可以反映水分子的自由運動,而雙指數模型擴散,即體素內不相干運動擴散加權成像(introvoxel incoherent motion-DWI,IVIM-DWI)可同時獲得水分子自由擴散運動和微循環灌注信息。腦灌注信息又與腫瘤血管生成程度密切相關,腫瘤生長所需營養主要靠微血管提供,因此通過檢測腦灌注信息就可以了解腫瘤營養狀態。已經有學者[32]證實IVIM-DWI 技術可以評估SD 大鼠C6 腦膠質瘤微環境缺氧狀態。這就為我們提供了思路,IVIM-DWI 技術能否通過術后乏氧程度來預測HGG 復發模式。目前相關文獻尚未見報道,故需展開新的研究來驗證上述假設。另外,雖然IVIM 較DWI 技術顯示出獨特的優勢,但由于b 值的選擇與分布尚未得到完全統一,研究結果可能存在一定差異[33]。
4 通過影像組學預測HGG復發模式
影像組學是一種通過計算機算法從醫學影像圖像中高通量地提取大量數字化影像組學量化特征的方法,通過結合機器學習方法,對特征進行篩選、分析,深度挖掘其代表的生物學信息,從而輔助臨床診斷、治療等工作[34]。
基于不同MRI 技術的影像組學在膠質瘤鑒別診斷、腫瘤分級、分子分型、療效監測及預后評估等方面有深入的研究[35]。近年來,影像組學在預測HGG復發模式方面也體現出一定價值。Yan 等[36]研究通過常規MRI 結合擴散張量成像、DWI的影像組學分析發現,采用影像組學分析預測復發模式的準確度為77.5%~82.5%,而采用卷積神經網絡法預測復發模式的準確度可以更高。Shim等[37]研究發現基于動態增強的影像組學能夠較好地預測復發模式,預測局部復發時AUC 為0.969,預測非局部復發時AUC 為0.864。復發模式聯合復發時間的可靠前期預測可能更有助于個體化治療。Fathi 等[38]研究發現腫瘤增強區、非增強區和周圍水腫區的影像學特征不僅可以預測HGG 復發模式還可以預測復發時間。這為HGG患者術后得到準確、及時、有效的治療提供了有力支持。
5 總結
綜上所述,從目前國內外研究中可以看出,基因、治療方案、腫瘤的位置、體積、水腫程度和術后梗死范圍等是目前影像學在預測HGG復發模式研究中的主要方向。MRI在預測HGG復發模式方面,可通過不同的MRI序列和影像組學評估患者腫瘤因素并結合臨床做出較為準確的預測。隨著技術進步,神經導航聯合術中MRI 已經越來越多地應用于腦功能區HGG 手術,在精準定位腫瘤、準確評估體積、提高手術全切率和降低術后并發癥等方面體現出明顯優勢。雖然MRI 在預測HGG 復發模式的研究中展現了較好的效果,但仍存在一定局限性:首先,相關研究尚處于初級階段,國內外對HGG 術后復發模式的定義缺乏統一標準,會在不同程度上影響研究結果。其次,以往對HGG復發模式的研究多局限于單一序列掃描,缺乏多模態成像技術對復發模式的研究。影像組學技術通過高通量提取圖像特征,為更加精準評估HGG患者術后復發模式提供了新方法。隨著人工智能的不斷發展,多模態磁共振成像技術與影像組學技術深度融合,將為臨床工作提供更加可靠的信息。
作者利益沖突聲明:全部作者均聲明無利益沖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