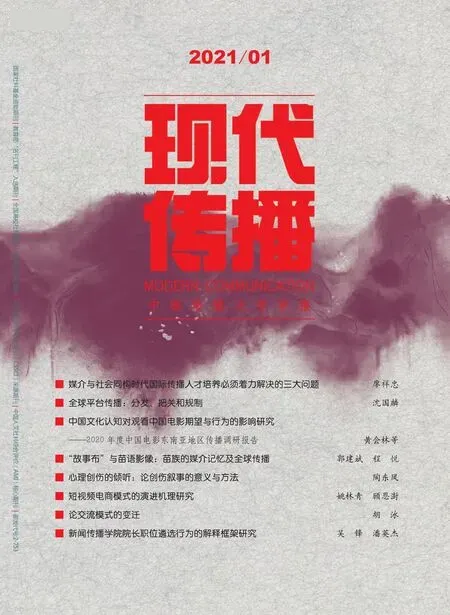心理創傷的傾聽:論創傷敘事的意義與方法
■ 陶東風
20世紀后期,隨著戰爭創傷神經癥在越戰老兵身上不斷出現,一大批來自不同領域的學者開始把目光投向創傷研究并不斷取得進展。①在眾多創傷研究成果中,如何通過受害者的講述進行創傷的治療和修復,是一個重要方面。比如,臨床心理醫生朱迪斯·赫爾曼(Judith Herman)的《創傷與復原》(Trauma and Recovery,1992)一書主張:個體的創傷可以通過向別人講述的方式得到復原。②這極大地改變了人們思考和治療創傷的方式,該著作一度成為心理創傷治療領域的暢銷書。
但是,講述不是獨白,不是講述者(創傷受害者)能夠單獨完成的獨角戲,而是講述者與傾聽者(包括但不限于心理醫生)之間的對話(即使聽者常常只是若隱若現地低調在場,這在場也至關重要)。創傷受害者是否愿意講述,講述什么和如何講述,都與傾聽者的在場及其傾聽方式密切相關。大屠殺幸存者、意大利著名見證文學作家普里莫·萊維在其第一部杰出的見證作品《這是不是一個人》的“作者前言”中這樣解釋大屠殺幸存者的創傷講述動機:“寫本書的意想和念頭在死亡營的那些日子里就已經產生了。出于把事實講述給‘其他人’聽的需要,出于想讓‘其他人’參與的需要,在從死亡營里出來獲得自由的前后,這種需要存在于我們中間,像有一股強烈而又直接的沖動,它并不亞于人活著的其它基本需要。”③
大屠殺的幸存者,也是20世紀最大的創傷受害者群體,其講述/見證的需要與被傾聽的需要是相互依存的。講述離不開聽眾,見證本身需要被見證。希望被傾聽是講述的基本動力。萊維還寫道:在戰后作為一家化工廠的化學家在來往于都靈(萊維的家鄉)與米蘭(萊維工作的地方)的日子里,他無法控制地、“隨心所欲地”和火車上那些不認識的人交談,向他們講集中營的故事。據萊維的訪談者馬可·貝波里蒂記載,萊維不止一次把一本書比作“一部能夠運作的電話”④。“電話”是一個交流而非獨白的工具,說話人知道在電話的那頭有人正在傾聽。
在回答安東尼·魯道夫的采訪時,萊維進一步把這種指向傾聽的講述和書寫大屠殺記憶視作一種治療/康復:“寫作《這是不是一個人》是一種治療,當我回到家中時,我絲毫不平靜。我感到徹底的不安。我對所有人,甚至不認識的人,講述這些故事。”這是因為,“通過寫作,我有了被治愈的感覺。我被治愈了”⑤。
一、創傷敘述者的困境
很多大屠殺幸存者都不愿意甚至斷然拒絕講述自己不堪回首的往事。耶魯大學心理學教授多麗·勞布用“對回歸的畏懼”(the dread of return)表達幸存者的這種心理,并提出了“二次傷害”的概念。⑥勞布指出,回憶過去、講述創傷很可能會成為對受害者的“二次傷害”:“對于命運重演的畏懼成為創傷記憶的關鍵,也成為不能言說的關鍵。一旦內在的沉默被打破,一直被回避的大屠殺可能會復生并被重新經歷。然而這一次創傷受害者再也沒有了忍受煎熬的能力。”好不容易九死一生活下來的幸存者,誰又愿意“再死一次”?“如果打破沉默的代價是再度經驗創傷,敘述行為就可能增加傷害。不是解脫,而是二度創傷。”⑦挺身而出見證大屠殺的作家、詩人,比如策蘭、萊維,最后都選擇了自殺,不能不讓人感慨系之。
為什么講述創傷會成為“二次傷害”而不是解脫或新生?在這里,有沒有傾聽者以及聽的方式至關重要。“如果講述創傷的人未能被認真聆聽,講述行為就會被經驗為創傷的復歸——重新經歷創傷事件本身。”⑧可見,未被認真傾聽是造成“二次傷害”的根本原因。這里涉及的情況非常復雜,值得分層次認真深入地予以分析。
首先,大屠殺幸存者在面對自己創傷性的過去時,常常陷于尷尬、分裂、矛盾、糾結的處境。對此,美國著名創傷研究專家、哈佛大學醫學院精神病學系臨床教授朱迪思·赫爾曼曾有如下描述:
對暴行的一般反應是將它排除于意識之外。某些反社會常態的事,會恐怖到讓人無法清楚表達的程度,而只能用難以啟齒(unspeakable)這個詞形容了。
一方面想要否定恐怖暴行的存在,另一方面又希望將它公之于世,這種矛盾正是心理創傷的主要對立沖突之處。暴行的幸存者通常會用高度情緒化、自相矛盾和零碎片段的方式述說他們的慘痛遭遇,但這種方式嚴重損及他們的可信度,因而導致出現到底是說出真相,還是保持緘默的兩難困境。
受創者所表現出來的心理癥狀是:既想讓人注意到那難以啟齒的創傷秘密,又想極力掩蓋它的存在。⑨
很多幸存者不愿意講述、見證大屠殺的暴行,是因為它實在過于殘酷血腥,太不堪回首、難以講述。幸存者不愿意再次揭開傷疤完全合乎情理。這里面既有加害者令人發指的罪與惡,更有受害者人性淪喪的恥與悔。集中營是一個讓人失去人性、蛻化為動物的地方(比如像動物一樣與其他囚犯爭食,趴在地上吸食別人的嘔吐物,為了自保而對自己的獄友甚至親人極度冷漠,等等)。正因為這樣,萊維認為奧斯維辛是讓人淪為畜生的大機器。用芝加哥大學教授布魯姆·貝托漢的話說:“我們希望遺忘它……希望忘記德國滅絕營的故事。如果可以的話,我們希望它壓根就不曾發生。我們最能接近于相信這個故事的辦法,就是不要再去想它,這樣我們就沒有必要去勉力接受其噩夢般的場面。”⑩集中營挑戰了我們對人的自信和樂觀,對上帝的期待和信仰,將人性的脆弱和幽暗暴露無遺。這樣,創傷受害者常常寧愿選擇沉默以便保護自己。
但是,這恰恰從另一個角度證明了大屠殺創傷見證的必要性。見證大屠殺的意義有很多,但筆者認為最重要的是豐富、深化對人性——尤其是人性之陰暗面的理解。用芝加哥大學教授布魯姆·貝托漢的話說,集中營“讓我們多了一個認識人類的維度,一個我們都想要忘卻的那個方面”。“想要忘卻”的方面正是人不愿意面對的人性之脆弱、陰暗:不僅是劊子手的極惡,也包括受難者在極權環境下的軟弱、茍活、奴性、自私、墮落。“滅絕營的獨特之處,并不在于德國人在這里滅絕了上千萬的人口……真正新穎、獨特、嚇人的,是數量如此之眾的人,他們就跟挪威旅鼠一樣,是自覺排隊走向了死亡;這是令人難以置信的事情,這是我們必須慢慢弄明白的事情。”在一般的情況下,這些陰暗面常常被掩埋在無意識深處,只有在集中營這樣的極端環境下才暴露無遺。它才是更需要見證的心靈創傷。
二、通過傾聽參與創傷
遺憾的是,盡管有些幸存者選擇勇敢地站出來作見證,但他們卻常常遭遇不被傾聽或不被相信的尷尬、失望乃至絕望的境遇。萊維本人就不止一次寫道:他的見證、他關于奧斯維辛的講述無法引起聽眾的興趣。在《這是不是一個人》中,他記載了聽者對自己的講述“無動于衷”“毫不在乎”,他們“談論著其他的事情,仿佛我不在場”。萊維對此感到心痛:“一種絕望的悲傷生自我心”,“為什么每日的痛苦如此不停息地轉化進我們的噩夢中,永遠重復著同樣的遭遇——沒有人傾聽我們的故事?”這就是說,這種不被傾聽的悲傷和絕望甚至變成了一種反復糾纏幸存者的噩夢,變成了另一種新的創傷。“我們經常覺得,自己是令人厭煩的講述者。有時甚至眼前出現了一種象征性的夢,好奇怪,那是在我們被囚禁期間夜里經常做的夢:對話者不再聽我們在說什么,他聽不懂,心不在焉,然后就走掉了,留下我們孤零零的。”
這里的“聽不懂”不能從字面意義上理解(幸存者證詞的文字并不艱澀),它實際上是指由幸存者講述的故事與聽者的常識(慣常化的知識和經驗)之間的鴻溝導致的難以置信。大屠殺實在太黑暗、太駭人聽聞、太令人匪夷所思,以至于超出了人類的理解能力和認識范疇,讓人無法相信。埃利·維賽爾在其《夜》的“作者序”中寫道:“憑心而論,那時的目擊者都認為,至今仍然認為,別人不會相信他們的見證,因為那樣的事件發生在人類最黑暗的地帶。只有到過奧斯維辛的人,身臨其境的人,才知道事情的本來面目,別人則永遠不會知道。”法國著名作家、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莫里亞克在《夜》的“前言”中也指出:“誰能想到世界上竟然有這種事情!把羔羊從母親懷中奪走,這種暴行大大超出了我們的想象。”莫里亞克將之稱為“詭異的邪惡”,認為它意味著“一個時代的終結”。相當多的研究成果證明:“心理創傷的研究不斷帶領我們進入不可思議的領域,并讓我們的一些基本信念瀕臨崩潰。”
除了知識上的斷裂之外,拒絕傾聽創傷的更深層原因恐怕來自情感上的抗拒和抵制。如上所述,集中營的故事駭人聽聞,暴露了大量存在的難題,蘊含了人性中最幽深、最深藏不露、羞于公開的奧秘。傾聽這樣的故事,固然是一個難得的深入了解人性、認識他人、認識自己的機會,但也是對聽眾心理承受力的挑戰。講述和傾聽這樣的創傷故事,不但對于講述者,而且對傾聽者而言都是一件極其痛苦、難堪甚至是難以忍受的事情,是一場充滿陷阱的冒險之旅(甚至自己遭遇創傷化)。正因為這樣,勞布指出,必須控制好傾聽者在聽的過程中可能會產生的種種抵制(心理防御),包括擔心被講述的暴行所淹沒,陷于滅頂、癱瘓的感覺,強烈的退出(不想再聽下去)欲望,等等。
這樣,傾聽創傷的人必須勇于在聽的過程中變成創傷的參與者與共享者,在自己身上部分地經驗創傷及其帶來的痛苦。也就是說,在聽的過程中,受害者與創傷事件的關系,會轉移到聽者那里。傾聽者如果想要發揮聽者的功能,如果想要讓創傷呈現出來,就必須分擔所有消極情緒,與受害者/講述者一起與過去的創傷記憶“搏斗”,與遺留的消極情緒“搏斗”。聽者必須從內心深處感受受害者的失敗與沉默。而這,正是見證得以形成的前提。
當然,傾聽者在參與創傷的同時卻無需也不應該完全變成受難者。傾聽也是見證,是對受難者的見證行為及證詞的見證。但他仍然是一個獨立個體,保持著自己獨立的位置和視野。“聽者在發揮創傷證人之證人的功能(function of a witness to the trauma witness)的同時,依然是一個獨立的人,體會到他自己的為難與掙扎。雖然與受害者的經驗部分交疊,他依然沒有變成受害者——他保持了自己獨立的位置、立場、視角。”傾聽者是分裂的,各種力量在他身上搏斗、撕裂,如果他要適當地執行其任務,就必須尊重自己的這種沖突和分裂身份。
由于傾聽者參與了創傷見證的發生,因此,傾聽者既是“創傷證人的見證者”(witness to the trauma witness),見證了證人的誕生(大屠殺的受害者并不都是見證者,他們中的大部分選擇了拒絕回憶、拒絕作證);同時也是自己的證人,見證了自己如何成為一個合格的傾聽者。通過同時意識到既存在于創傷見證者、也存在于他自己的內在的、持續的冒險,他的傾聽使得他成為使見證成為可能的人:啟動見證,同時成為見證過程和見證動力的維護者。
三、講述、傾聽與治療
創傷經驗的根本特點之一是:它總是像一個難以驅散的噩夢不斷返回來糾纏受難者。現代創傷理論的創始人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引論》(1917)中強調:創傷是一種突發的、人在意識層面無法適應的震驚經驗,且這種經驗具有持久性、頑固性和反復性。他給“創傷”下了這樣的定義:“一種經驗如果在一個很短暫的時期內,使心靈受到一種最高度的刺激,以致不能用正常的方法謀求適應,從而使心靈的有效能力的分配受到永久的擾亂,我們便稱這種經驗為創傷的。”在1920年出版的《超越快樂原則》中,弗洛伊德把創傷與“夢”聯系起來,指出:創傷對于意識而言是一段缺失的無法言說的經驗,人們常常在不知不覺間無法自控地重復傷害自己或他人,這種“重復強制”的行為,即我們所說的創傷;而其無法把握、難以言說的陌生性,被勞布稱為創傷的“他者性”(a quality of otherness)。
創傷事件雖然真實,但是卻在“正常現實”的范圍外發生,超越了尋常的因果、順序及時空,這使它處于相互聯系的經驗范圍之外,也缺乏界定它的現成知識范疇,難以理解、無法敘述(參見上文)。如果不能得到有效治療,創傷受難者就將帶著一個永遠沒有終結、也無法終結的噩夢活著。這一點在創傷文學的創作上也有反映。歐文·豪指出:經歷過奧斯維辛和古拉格的作家,“他們必須帶著給他們留下永恒傷疤的經驗而活下去。他們反復地、時常強迫性地回到這個主題”。有很多集中營的幸存者一方面拒絕回憶,拒絕談論(集中營的)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拒絕交往并陷于幽閉麻木;另一方面又無法忘記,長期被噩夢所折磨。依據朱迪思·赫爾曼的命名,前者為“禁閉畏縮”,后者為“記憶侵擾”,這兩個“相互矛盾的反應,會形成一種擺蕩于兩端的律動”,它是“創傷后癥候群”的最大特征。
精神分析理論在這方面開出的藥方是:為了擺脫這不可知、不可說而又無休止糾纏幸存者的創傷經驗,必須啟動一個治療過程,通過精神分析師的傾聽和引導,讓幸存者通過講述使創傷事件再外在化(re-externalizing the event);而再外在化的過程必須有醫生——可以理解為一種特殊的傾聽者——的配合:“這個事件的再外在化只有在一個人可以表達并傳遞(transmit)故事給外在的他人并再次收回于內的情況下,才能發生并生效。”
同樣,耶魯大學大屠殺音像資料中心收集的那些關于創傷的自傳性敘述,既是對創傷的見證,也是與心理分析類似的治療過程。與敘述的雙重功能(見證與治療)相對應,資料中心的研究者如費爾曼、勞布,也具有雙重角色:既是治療者,也是訪談者(傾聽者)。創傷講述、歷史見證與心理治療是同時展開的過程。
在這個過程中,心理醫生與創傷受害者之間的相互信任至關重要。醫生要和“病人”一起通過相互之間的“安全測試”:相互證明對方的持重、理性、沉穩、值得信任和尊重。只有這樣,幸存者才會把自己“托付”給醫生/訪談者。這意味著醫生/聆聽者與“病人”/講述者在通過“安全測試”后建立了“信任合約”:“其中一方持續地敘述創傷、展現其生命記錄,而另一方則暗示地對見證者說:在整個見證的過程中,我將盡我所能始終陪伴你。你到哪里我就到哪里,我將全程保護你。在旅途在終點,我將離開你。”一方面,這個傾聽者需要保持“低調在場”(unobtrusively present)的姿態,不能粗暴、輕易地介入見證過程,不能自我張揚、自以為是、喧賓奪主;另一方面,他又要敏銳感受并記錄證人言說中的蛛絲馬跡,在受害者猶豫、退縮時扶持、鼓勵他/她繼續講述下去。
第一次世界大戰后英國著名神經生理學家、心理學與人類學家教授里弗斯,與他的病人西格弗里德·薩松之間就建立了這樣一種“信任合約”。薩松原為一名驍勇善戰的軍官,但后來轉變立場成為著名的反戰詩人和獻身人類和平事業的公共知識分子。他因此而遭到極大的壓力甚至可能受到軍事法庭的審判。同為詩人的軍官同僚格雷夫斯安排薩松去里弗斯那里接受治療。里弗斯嘗試用人道主義的方法來治療薩松、并以此證明其比懲罰性的傳統方法高明。他以有尊嚴的、尊重的態度對待薩松,鼓勵薩松自由地說出戰爭的恐怖。對此薩松充滿感激:“他(里弗斯)讓我立刻有了安全感,他似乎了解我的一切。……我愿意用盡我收藏的留聲唱片去換取一點我和里弗斯的談話錄音。”
這再一次表明:見證不能由創傷受害者一個人在孤獨中進行,必須有可信賴的、合格的、樂于傾聽的“他者”,“見證創傷的過程是包含聽者的過程,為了讓見證過程發生,需要一個他者的、連接性的、親密的、完全的在場并處于傾聽的位置”。“證人是在和某些人說話,和某些他等待已久的人說話。”很多人就是因為缺少這樣的傾聽者、陪伴者而失去了見證的動力和勇氣。
從倫理角度看,創傷講述的最終目標是修復創傷者與他人及世界的信任和愛的關系。赫爾曼認為:在創傷事件發生之后,患者變得更加容易受到傷害,他們或過度警覺,對世界失去信任;或深受記憶侵擾,創傷經驗以強迫重復的方式不斷返回;或緊閉畏縮,對一切麻木無感。特別是,創傷事件粉碎了人與社群之間的連接感,受害者對社群產生普遍的不信任感,認為這是一個“虛偽”的世界。“它(創傷事件)撕裂了家庭、朋友、情人、社群的依附關系,它粉碎了借由建立和維系與他人關系所架起來的自我,它破壞了將人類經驗賦予意義的信念體系,違背了受害者對大自然規律和上帝意志的信仰,并將受害者丟入充滿生存危機的深淵中。”要解決這個問題,唯一的方法就是重建與他人、與社群、與世界的連接關系,使得“個人與廣大的社群有更多的接觸與互動”。如此,創傷的講述才必須指向聽者,它本質上必須是雙向的交流,只有交流才具有修復人際關系、修復創傷者與世界之關系的功能,才能恢復生命的“外部關聯性”。這一切通過獨白是無法實現的。但如果創傷者的講述不被傾聽、不被理解,就必然使得他長期缺乏“人類一家的感覺”(the sense of human relatedness),缺乏被愛的感覺,甚至出現錯覺,覺得自己愛別人不夠,認為自己才是要對災難負責的人。未被講出的事件在他/她的無意識中變得如此扭曲,以至于使得他/她相信是自己而不是加害者,要對其所親歷的暴行負責。這樣的受害者變得完全喪失了見證的能力,勞布稱之為“見證的崩潰”(collapse of witnessing)。
四、善于傾聽沉默,尊重知識局限
特別需要強調的是:在傾聽創傷見證的過程中,聽者不應該過分糾纏于細節的準確性,尤其不應該對真實性持有機械的、僵化的理解,而應尊重受害者在特定條件下的知識局限。如前所述,創傷受害者并不擁有對于創傷事件的完整知識,更不能透徹理解它。以大屠殺為例,幸存者對于大屠殺的記憶很可能在細節上不準確(尤其是從科學真理的標準看)。一個很典型的例子是:耶魯大學大屠殺見證錄像資料中心的一個訪談者、奧斯維辛集中營一個年近七旬的女性幸存者,在回憶奧斯維辛集中營暴動時出現了細節錯誤。她說暴動那天晚上“四個煙囪竄出火焰,火光沖天”。之后不久,有一個歷史學家在一個研討會上就此指出:該婦人所說“四個煙囪”不符合歷史事實。事實上當時冒火的煙囪只有一個而不是四個。他由此斷言這個證人的記憶不準確,其見證不可信。在他看來,細節真實具有絕對甚至唯一的重要性,否則就會被歷史修正主義者抓住把柄加以利用。
勞布本人也參加了這個會議。她不同意這位歷史學家的觀點。她的理由是:“這位婦人見證的不是爆炸煙囪的數量,而是某種更根本、更關鍵的事實。一個不可想象的事件的發生。”在奧斯維辛,一個煙囪的爆炸和四個煙囪的爆炸一樣不可思議。數量的多少不如發生的事實及其給犯人帶來的震撼重要,更不如它所代表的納粹無往不勝的神話的破滅重要。這個難以置信的事實的發生打破了關于奧斯維辛不可抗拒的主導認知框架,依據這個框架,犯人在奧斯維辛進行武裝抵抗這樣的事情根本不可能發生;而這位婦人見證的就是這個框架的破滅。這是一個比細節更為重要的真理。
勞布的觀點讓我想起蘇聯作家、諾貝爾文學獎獲獎者阿列克謝耶維奇的觀點。在《我是女兵,也是女人》(又譯為《戰爭讓女人走開》《戰爭中沒有女性》等)末尾附加的創作談《寫戰爭,更是寫人》中,她自稱“靈魂的史學家”,反復強調戰爭書寫中人性維度和情感維度的重要性,甚至說“我不是在寫戰爭,而是在寫戰爭中的人。我不是寫戰爭的歷史,而是寫情感的歷史”。與“戰爭的真實”相比,“人性更重要”。阿列克謝耶維奇將自己的上述見解提升為自己的記憶理論:“回憶”不是對已逝去的經歷作冷漠的復述或記錄。“當時間倒退回來時,往事已經獲得了新生。”因此,回憶也是一種創作、至少是一種重構。省略、補充、改寫是無法避免的。在其《切爾諾貝利的回憶:核災難口述史》的“結束語”中,阿列克謝耶維奇寫道:“我常常想,相對于簡單而機械的事實而言,人腦海中的那些模糊的情感、傳言、印象其實更接近事實真相。……令我著迷,念念不忘的也恰恰正是這些情感的演變歷程,以及人們再談及這些情感時無意之中表露出來的某些事實。我嘗試著去尋找這些情感,然后把它們收集起來,加以保護。”顯然,那位集中營幸存婦女心目的“四個煙囪竄出火焰”應該就是她“心中念念不忘”的“腦海中的印象”。
無論是歷史學家、精神分析學家還是作家,都應該尊重幸存證人的知識局限,不能以此為由其剝奪其講述的權利。比如,勞布得知這個婦人在奧斯維辛集中營屬于“加拿大突擊隊”成員。這個突擊隊是納粹從囚犯中選出的一些人組建的,其工作是挑撿被瓦斯毒死的猶太人的遺物,納粹要將它們沒收并運回德國。她在訪談中自豪地回憶起自己如何把一些比較好的衣服偷偷私藏并送給自己的囚犯同伴。但她根本不知道自己所屬的突擊隊,也不知道這些遺物來自哪里。這就是所謂的“受害者的知識極限”。這個時候,勞布知道自己不能再問下去,應該尊重這個極限。勞布就此闡釋道:“作為一個訪談者與傾聽者,我所嘗試的恰恰就是尊重——不要擾亂、逾越——婦人之所知與其所不知、所不能知之間微妙平衡。只有以這種尊重——對局限和沉默的邊界的尊重——為代價,婦人所確知的東西——也是我們一無所知的東西,她下決心加以見證的東西——才能發生并得到傾聽。”如果像歷史學家那樣抓住婦人的知識局限不放,并全盤否定其證詞的見證價值,這就必然導致只有她能傳達給我們的信息、只有她能講述的故事,也一起遭到清除。
傾聽者/訪談者不但不能以自己的知識(比如這次起義被無情鎮壓,起義囚犯被全部處決,而且在起義一開始就遭到了波蘭抵抗組織的背叛,等等)和預先見解干擾、妨礙見證人講述,或者質疑其講述的全部真實性,而且還要明白傾聽者的歷史知識、其既定的理解模式,反倒可能會干擾其傾聽,而且其自身也帶有很大的局限性。勞布對此始終保持了高度的自省和反思:“我可能會有證實自己所知的沖動,而提出使見證翻車(derailed the testimony)的問題。……不論我事先設定的議程是歷史的,還是精神分析的,都可能不自覺地干擾見證的過程。在這方面,有時候不知道太多反而有用。”
這絕非為無知辯護或提倡無知。為了能夠聽見、能夠覺察暗示,傾聽者必須有足夠的知識。但是這些知識不應該以既定結論或預先的拒絕來干擾或阻礙傾聽的過程,不應該遮蔽不可預見的、嶄新的、充滿分歧的信息。重要的是在見證展開的過程中發現新的知識。見證中的知識不是對現成的“既成事實”的復制,而是一個新的、有自己獨立存在理由的事件。受難者見證的是他/她的心中、他/她眼中的歷史,而且是只有她才能見證的歷史真理中的本質部分。比如這個婦人看到奧斯維辛集中營的煙囪在爆炸,也就是不可想象的事情正在發生,她所見證的就是她親眼所見之事的不可思議性,是對暴行的抗拒,是對生還的執著,是關于反抗行為的活生生記憶。這種記憶是歷史學家不具備的,盡管歷史學家所掌握關于煙囪的數量、暴動的失敗、反抗者的慘死等知識,是這個婦人所不具備的,但這并不影響其見證的獨特價值。這種“不可思議性”打破了奧斯維辛的神話,導致了既定的“奧斯維辛框架的突然破裂”(bursting open of very frame of Auschwitz);而歷史學家證實的事實(如只有一根煙囪爆炸,波蘭地下組織的背叛),并沒有打破這個框架。
萊維在其小說《扳手》中寫道:“正如講故事是一門藝術一樣——將故事千回百轉地嚴絲合縫地組織起來——傾聽也是一門藝術。它同樣古老,同樣精妙。”的確,傾聽也是藝術,而且傾聽的水平直接影響到講述的水平。交談是必須的,但交談也是艱難的。俄國著名詩人曼德爾斯坦姆有言:“一次談話的平臺是以登山運動員般的努力為代價創建起來的。”這句話被當作普里莫·萊維、喬瓦尼·泰西奧的對話錄《與你們交談的我——萊維、泰西奧談話錄》開篇的卷首語,值得我們深長思之。
注釋:
① 至20世紀90年代,創傷研究達到了其黃金時期。在此過程中,先后涌現出一大批歷史學家、人類學家、精神分析學家和文學—文化批評家,如勞倫斯·蘭格(Lawrence Langer)、阿爾文·羅森菲爾德(Alvin Rosenfeld)、杰弗里·哈特曼(Geoffrey Hartman)、朱迪斯·赫爾曼(Judith Herman)、多麗·勞布(Dori Laub)、凱西·卡魯斯(Cathy Caruth)、卡莉·塔爾(Kalí Tal)、多米尼克·拉卡普拉(Dominick Lacapra)等等。特別值得一提的是:1979年,針對“二戰”中猶太人被屠殺的歷史,心理醫生、大屠殺幸存者多麗·勞布與大名鼎鼎的文學理論家哈特曼等,啟動了著名的“大屠殺證詞福圖諾夫錄像檔案”(Fortunoff Video Archive for Holocaust Testimonies)研究項目,所有檔案均存放于耶魯大學的斯特林紀念圖書館。這一工程大大激發和促進了之后的創傷研究,也使得耶魯大學成為創傷研究的重鎮。
② [美]朱迪思·赫爾曼:《創傷與復原》,施宏達等譯,機械工業出版社2019年版。
④ [意]馬可·貝波里蒂:《我是一頭半人馬》,載[美]普里莫·萊維:《記憶之聲:萊維訪談錄,1961-1987》,索馬里譯,中信出版集團2019年版,前言第17頁。
⑥ 在研究如何傾聽創傷訴說的學者中,耶魯大學心理醫生多麗·勞布(Dori Laub)值得重視。在其與文學研究者肖珊娜·費爾曼(Shoshana Felman)合作撰寫的《證詞:文學、心理分析與歷史中的見證危機》(Testimony:Crises of Witnessing in Literature,Psychoanalysis,and History,1992)一書中,兩位作者從精神分析和文學批評的視角對大屠殺見證進行了深入研究。其中特別是勞布執筆的第二章“見證或聽的變遷”(Bear Witness or the Vicissitudes of Listening)與第三章“無見證的事件:真理、見證與幸存”(The Event without A witness:Truth,Testimony and Survival),就創傷見證與傾聽之間的關系、訪談者(作為特殊的傾聽者)與受訪者(訴說者)的關系等問題,提出了極具啟發的見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