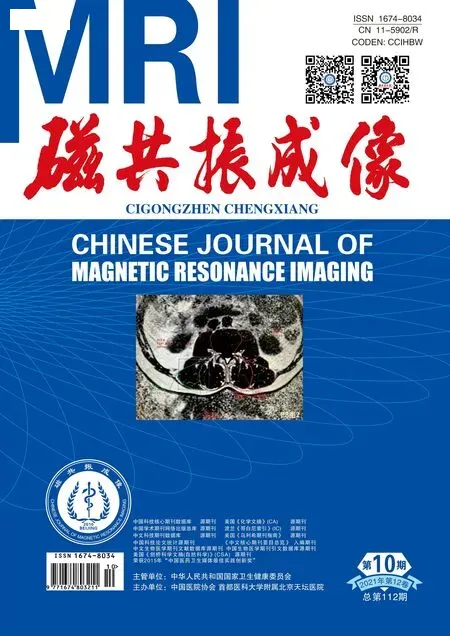MR擴散加權成像在軟組織腫瘤中的應用進展
陽艷語 ,張凱,張麗娜 ,王紹武*
軟組織腫瘤(soft tissue tumors,STTs)起源自間葉組織,組織病理學類型繁雜,各種類型腫瘤間和腫瘤內異質性高[1],初診時腫瘤情況、治療方法以及是否發生復發和/或轉移等都決定著STTs患者的預后。影像學檢查在STTs患者初診及隨診中都是不可或缺的環節。MRI因良好的軟組織分辨率已成為STTs診療評估主要輔助技術,常規MRI能提供腫瘤位置、大小、邊緣等形態學特征,但不能反映腫瘤功能性病理變化信息[2]。MR擴散加權成像能夠檢測活體組織水分子擴散狀況,分辨正常與病變組織、不同病變組織之間微觀結構的變化。本文就MR擴散加權成像技術在STTs中的應用進展綜述如下。
1 MR擴散加權成像常用技術類型及相關參數
MR擴散加權成像基于水分子的擴散特性,提供細胞密度、細胞膜完整性等病理生理改變信息。近年來,用于STTs臨床研究的技術類型主要有:(1)單指數擴散加權成像(diffusion weighted imaging,DWI),目前應用最廣泛的模型,其中單次激發平面回波成像序列具有采集速度快且保留相對較高信噪比的特點,成為獲取單指數DWI最常見的方法[1]。定量參數ADC值由兩個b值擬合得出,用來評估水分子擴散受限程度。而b值的選擇目前尚無統一標準,Subhawong等[3]建議最低b值取50 s/mm2,以減輕血液灌注對ADC值的影響。ADC值在感興趣區內測量,但考慮到STTs高度異質性,ROI的大小和位置在很大程度上影響ADC值,ADC值的可重復性也成為臨床工作中亟待解決的問題。Ahlawat等[4]在STTs中用3種ROI測量方法(腫瘤最大層面法、預定義的三層勾畫法和基于觀察者的三層勾畫法),并與全腫瘤勾畫法進行比較,發現4種ROI勾畫方法測得ADC值均有良好的觀察者間一致性(ICC:0.78~0.90),可重復性較好,且腫瘤最大層面法所需測量時間最短,在臨床實踐中最為便利。(2)體素內不相干運動(intravoxel incoherent motion,IVIM)模型即多b值擴散加權成像,通過雙指數擬合函數區分水分子擴散和毛細血管灌注效應,并用定量參數D值、D*值和f值表示,其中真擴散系數D值提供純水分子擴散信息,偽擴散系數D*值為微循環灌注對應信息,灌注分數f值代表微循環擴散占總體擴散比例。在b值較低(b<200 s/mm2)時,信號主要受微循環灌注影響;高b值時主要體現水分子真實擴散效應。軟組織腫瘤IVIM掃描中通常設置10~14個b值,范圍從0 s/mm2到1500 s/mm2[5-7]。(3)擴散張量成像(diffusion tensor imaging,DTI)兼顧水分子各向異性擴散特征,并以定量參數各向異性分數(fractional anisotropy,FA)和相對各向異性(relative anisotropy,RA)表示。DTI除了可獲得水分子擴散信息,還能通過纖維示蹤技術描繪腫瘤和纖維束的關系,觀察纖維束的受壓、移位、破壞情況[8]。(4)擴散峰度成像(diffusion kurtosis imaging,DKI)在DTI技術上延展,根據非高斯模型,用定量參數平均峰度(mean kurtosis,MK)和平均擴散率(mean diffusivity,MD)反映水分子擴散和組織微觀結構變化程度[9];水分子呈非高斯擴散越明顯,表明組織微觀結構越復雜,MK值越大。當b值較高(b>1000 s/mm2)時,信號衰減明顯偏離高斯分布,因此軟組織腫瘤DKI掃描大多設置3~5個b值,最高b值可達2100 s/mm2[6,10]。
2 MR擴散加權成像技術在軟組織腫瘤中的應用進展
2.1 軟組織腫瘤的良惡性鑒別
隨著STTs惡性程度增加,腫瘤細胞核異型增多、細胞密度增加、細胞外間隙減小,導致細胞內、外水分子擴散受限。大量研究表明[11-14],惡性較良性軟組織腫瘤ADC值低。同時,STTs異質性高,瘤內成分復雜,病灶內黏液樣基質能夠增加水分子擴散,導致ADC值升高,部分良惡性軟組織腫瘤ADC值重疊。Song等[15]對123例STTs患者行DWI檢查,當ADCmean和ADCmin閾值分別為1.348×10-3mm2/s及0.805×10-3mm2/s時,對其良惡性鑒別診斷性能最佳,而將黏液樣和非黏液樣STTs分組研究發現,當ADCmean和ADCmin閾值為1.132×10-3mm2/s及0.631×10-3mm2/s時,對非黏液樣STTs良惡性鑒別診斷性能最佳。此外,考慮到ROI對ADC值的影響,Bonarelli等[16]探討手動和半自動ROI定位方法對STTs良惡性鑒別診斷的影響,發現兩種方法測得ADC值觀察者間一致性均較好(ICC:0.71~0.87);但基于手動法測得的最小ADC值(閾值1.28×10-3mm2/s)具有較高的診斷敏感性和特異性(83%和63%)。IVIM較DWI能更好區分水分子擴散和微循環灌注,真擴散系數D值較ADC值也能更好地反映水分子的擴散。多數研究報道[7,17,18],IVIM的定量參數D值、D*值和f值均能反映STTs細胞密度及灌注特性,區分良、惡性STTs。Gondim等[19]對65例非血管性非脂肪性STTs患者行DWI、IVIM檢查發現,惡性較良性軟組織腫瘤ADC值和D值明顯降低,且在排除黏液樣腫瘤時,D值的診斷敏感度提高16%~21%。目前,DTI技術在STTs中主要應用于周圍神經鞘腫瘤,在其良惡性鑒別方面具有重要臨床意義;在DTI模型中,不僅能夠提供水分子擴散特性,還能觀察組織內纖維束受侵情況。Mazal等[20]研究報道,在周圍神經鞘瘤中,病側FA值通常低于健側;同時,利用纖維示蹤圖發現,惡性較良性周圍神經鞘瘤神經束斷裂嚴重,證明DTI有助于評估STSs周圍神經浸潤情況,對腫瘤切除計劃后保留神經功能有很大價值。DKI對組織微觀結構改變較敏感,有利于病變的早期診斷。Ogawa等[21]報道,MK值能夠準確區分肌肉骨骼腫瘤良惡性,惡性肌肉骨骼腫瘤MK值較大,且MK值和最小ADC值具有強相關性。Liu等[22]對58例STTs患者行IVIM和DKI檢查,發現惡性組較良性組D值、MD值和MK值明顯減低(AUC分別為0.859,0.765和0.676),且D值診斷特異性最好(82.93%)。同樣,在張曉莉等[23]對26例STTs患者行IVIM和DKI檢查的研究中,ADC值、D值、MK值和MD值診斷性能較高,在最佳閾值下其敏感度和特異度均能達到60%以上。同時,該研究還發現,D值與MK值和MD值聯合診斷價值更高(AUC分別為0.958和0.915)。綜上,DWI、IVIM、DTI和DKI在STTs良惡性鑒別方面均有探索,且各自具有優勢。同時,ROI的選擇在ADC圖上進一步研究,不同ROI測得ADC值可重復性較好,但在ROI勾畫時應盡量避開腫瘤組織囊變、壞死、鈣化等區域,減小對ADC值的影響。但由于STTs高度異質性,在最佳b值選擇、定量閾值確定等仍需要大樣本的研究來進一步提高診斷準確性。
2.2 軟組織腫瘤的組織病理學分級預測
腫瘤組織病理學分級常是預測患者預后和指導治療方案的重要因素。常規MRI可以利用腫瘤的形態學特征評估組織學分級。Crombé等[24]對130例STTs患者行平掃和增強MRI檢查,結果顯示腫瘤壞死、T2WI不均勻信號超過50%和瘤周強化特征與Ⅲ級軟組織肉瘤(soft tissue sarcomas,STSs)相關,并能將診斷準確性提高至50%以上。但病灶周圍炎癥反應、血管充血和過灌注等都會導致MRI瘤周高信號和瘤周強化表現。擴散加權成像通過觀察水分子微觀運動,對組織病理生理變化信息更為敏感。Chhabra等[25]對51例STSs患者行常規和增強MRI掃描以及DWI檢查發現,Ⅲ級較I、Ⅱ級STSs平均ADC值顯著降低,閾值為0.88×10-3mm2/s時,診斷敏感度和特異度達到62%和80%;閾值為0.98×10-3mm2/s時,辨別I級和Ⅱ、Ⅲ級STSs的敏感度和特異度為56%和88%;此外,DWI的診斷準確度與平掃和增強MRI聯合分析相當,對于不能進行造影增強檢查的患者,DWI可以增加常規MRI診斷特異性。不同級別的STSs在血流灌注上也有差別,理論上,高級別STSs較低級別新生血管增多、血供及血流量增高,IVIM在STSs分級評估中具有很好的發展潛力,且IVIM與動態增強MRI提供的灌注信息間的關聯需要更深入的研究進行探討。
2.3 軟組織腫瘤的浸潤評估和復發監測
外科手術切除是STTs治療的主要方法,術前借助影像學檢查確定腫瘤邊緣十分關鍵。MRI檢查在確定切除腫瘤邊緣范圍,輔助治療方法,患者預后等方面有重要參考價值。Lee等[26]在一項對253例淺表STSs的研究中,在MRI下將淺表STSs與周圍深筋膜的關系分為三類:無筋膜接觸組、筋膜接觸組和筋膜浸潤組,發現筋膜浸潤是導致淺表STSs的疾病特異性生存率降低的獨立因素。Yoon等[27]、Hong等[28]指出,在常規MRI基礎上增加DWI檢查,可以提高STSs筋膜侵犯和邊緣浸潤的診斷能力。瘤周信號改變為腫瘤細胞浸潤抑或單純反應性水腫,仍是臨床工作中爭議較大的問題。IVIM和DKI較單指數DWI更能反映組織微觀結構變化。Li等[29]對34例STSs患者行IVIM和DKI檢查發現,標準ADC值、D值、MK值和MD值均能可靠地區分瘤周陽性和陰性浸潤,其中MD值具有最好的診斷性能(AUC=0.85),閾值為2.35×10-3mm2/s時診斷準確度、敏感度及特異度分別為88.2%、94.4%及81.3%。腫瘤浸潤與否與外科手術切除范圍密切相關,若將反應性水腫、炎癥反應等過度診斷為瘤周浸潤,則會導致不必要的擴大切除;而忽視瘤周浸潤,又會造成切緣陽性,提高STTs患者局部復發率。據報道,切緣陽性患者局部復發率是陰性患者的5.9倍,但由于STTs多樣的組織病理學類型、復雜重疊的影像特征,仍有30%~50%的病例以非計劃切除的方式進行外科手術[30]。多項研究表明[31,32],在非計劃切除的STTs中,DWI較常規MRI更能確定STTs瘤床中的殘留腫瘤,以期進行再次切除或后續治療方案的調整。對于切緣陰性的患者,術后瘢痕、血腫等炎癥反應在常規MRI和靜態增強上常與復發腫塊呈現類似的信號改變。Grande等[33]對37例術后STSs患者研究發現,DWI檢查可提高常規MRI鑒別腫瘤復發和術后瘢痕的特異性,其中復發腫瘤的ADC值與術后瘢痕、血腫的ADC值均有差異。擴散加權成像技術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STTs的生物學行為,指導外科醫師制定個性化手術切除方案,同時監測疾病進展,對患者預后具有重要臨床價值。
2.4 軟組織腫瘤的放化療療效評價或預測
近年來,放射治療和化學治療在STSs中展示出較好的治療前景[34]。傳統的實體腫瘤評估標準依賴于治療干預前后腫瘤大小的變化[35],但形態學的改變往往滯后于細胞代謝和功能的改變。放化療后,因藥物的細胞毒性作用,誘導腫瘤細胞凋亡、壞死,導致細胞密度減低、細胞膜破裂,水分子擴散增加。Moustafa等[36]對9例接受放化療的STSs患者進行隨訪DWI檢查發現,治療后ADC值平均增加0.28×10-3mm2/s。Soldatos等[37]發現DWI可以提高常規MRI在STSs新輔助治療后區分治療反應相關炎性變化與殘留腫瘤的靈敏度,且最小ADC值為2.0×10-3mm2/s與平均ADC值為2.2×10-3mm2/s時可作為判斷治療反應良好的閾值。IVIM與DWI一樣,其參數值的變化能為治療過程中腫瘤細胞密度的改變提供定量分析,早期了解治療反應,Winfield等[38]對30例腹膜后STSs患者行DWI、IVIM檢查發現,ADC值和D值在放射治療后顯著增加,且放療前ADC值與細胞密度、間質類型和間質分級相關。近年來,組織病理學特征在STTs的評估中日益受到重視。多項研究表明[39,40],組織病理學指標不僅在STTs的形成、侵襲、血管生成等方面發揮重要作用,還能預測放化療療效,其靶向藥物也有望成為一種新興的治療策略。Li等[41]在一項40例STSs患者的IVIM和DKI與乏氧誘導因子(hypoxia-inducible factors,HIF)表達的相關性研究中,使用一種全新的影像-病理對照方法,實現影像和病理“面對面、點對點”精準對照,發現IVIM和DKI的定量參數D值、f值、MD值和MK值可用于評估軟組織肉瘤HIF-1α表達水平,其中MK值為0.604時,對HIF-1α表達程度診斷敏感度達到78.3%,特異度達到88.2%。此外,ki-67、VEGF等免疫組化指標有助于了解STTs惡性程度,其靶向藥物也在STTs治療中發揮出巨大潛力。擴散功能成像參數與組織病理學特征之間的關聯,有助于早期了解腫瘤生長情況,同時監測治療療效,起到早期預警和評估病情的作用,這可能成為未來STTs影像與病理精準對照研究的思路之一。
3 小結
在常規MRI基礎上,擴散加權成像技術對于STTs的臨床應用具有重要附加價值。但仍有較多問題需要解決,在最佳序列、參數的選擇和診斷標準上尚未統一,還需要進一步的研究。相信在不久的將來,MR擴散加權成像技術不斷的發展和完善,在STTs診療方面具有廣闊的應用前景。
作者利益沖突聲明:全部作者均聲明無利益沖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