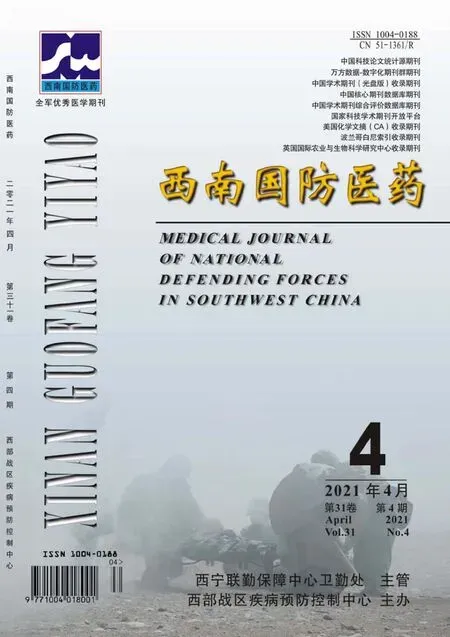CHIVA:基于血流動力學原理治療下肢靜脈曲張的臨床應用
張作林,郭曙光
下肢靜脈曲張是一種常見的血管性疾病,發病緩慢,到一定時期就會出現可見的靜脈曲張、水腫、疼痛、皮膚瘙癢及沉重感,不僅影響生活質量,甚至會使部分患者喪失勞動能力,浪費大量醫療資源[1],很多情況下都需外科治療,目前手術方式大致分為兩類,一是:消融或破壞性治療,如經典的大隱靜脈高位結扎剝脫術、射頻或激光治療、硬化劑治療,另一種是保留隱靜脈的血流動力學治療(CHIVA)[2]。針對CHIVA術式目前國內外爭議較大,有研究認為在過去的20年中該術式得到了一定的發展,目前是安全切除術后用于下肢靜脈曲張外科手術的第二種手術方式[3]。Bellmunt等[4]綜述了CHIVA策略可長期降低復發率的證據。在我國CHIVA被2019年中國慢性靜脈疾病診斷與治療指南中認為對于CEAP分級中的C3以下患者效果較好[5],同樣有學者認為,CHIVA實用范圍有限,在國外幾乎沒有開展,國內有些醫療機構對CHIVA有宣傳過度的嫌疑[6]。筆者對CHIVA手術的原理及特征進行綜述,望對臨床工作者有所參考。
1 CHIVA的原理
CHIVA:意為“門診治療靜脈功能不全的保守療法和血流動力學療法”,是一種保留下肢靜脈治療慢性靜脈疾病的方法[7]。該理論基礎認為增加的透壁壓(TMP)是造成慢性靜脈功能不全的原因之一,所謂的透壁壓即靜脈側壓(主要為重力靜水壓和曲張靜脈內血液由層流轉變為湍流作用于血管壁引起的壓力)與外部靜脈壓之間的差異(大氣壓和組織壓)。淺靜脈透壁壓的升高,由于沒有正向動力壓力分流和閉合分流的存在導致更高的水動力壓力,從而引起一系列臨床癥狀[8]。CHIVA的核心是正確的血液動力學評估,進行良好的血管B超檢查以正確確定壓力過載的來源,并進行準確結扎來中斷壓力逃逸點(反流開始),保留再入點,使血流通過正常穿支靜脈回流進入深層系統[9]。理論上沒有進行任何的靜脈剝脫,隨著透壁壓的減少導致靜脈曲張直徑的縮小,直至恢復正常。
2 靜脈反流與血管直徑的關系
在2006年國際靜脈學協會的共識文件[10]中認為大隱靜脈的直徑可作為靜脈疾病嚴重程度的指標。大隱靜脈的所有部位都可能發生靜脈反流,當發生靜脈反流時,大隱靜脈的直徑通常會增加,并且靜脈擴張的程度可能會根據大隱靜脈中反流程度和位置而改變。Mendoza等[11]在182條腿的研究中通過測量隱股瓣膜交界處(SFJ)及大腿近端(PT),距離SFJ約15 cm處的大隱靜脈(GSV)血管直徑,認為PT處大隱靜脈直徑對靜脈疾病的分類具有更高的準確性、敏感性和特異性。并且射頻消融和激光治療往往以SFJ直徑作為確定治療方向和隨訪的手段,而CHIVA大多包含PT處GSV直徑,因為該部位的GSV的血管壁相對平直,位于最近端分支靜脈的交界處,即使進行交叉切除術,其治療策略也可以將GSV干線留在原位,從而更好地進行干預評估。Kim等[12]在99例(198肢)患者中從SFJ到BK的4個區域中檢查GSV直徑:SFJ遠端2 cm,MT(SFJ和LT的中點),LT(膝關節上方5 cm)和BK(膝關節下方5 cm),研究認為有回流的GSV的直徑僅在LT區域顯著更大(P<0.01),是最敏感的擴張位置。當LT處的直徑以1 mm的增量從3 mm細分為10 mm時,當直徑<5 mm的反流率為37.9%,直徑>5 mm時反流率為56.3%,并建議對LT直徑>5 mm伴有癥狀的靜脈反流進行治療并通過檢查LT處的靜脈反流和直徑來評估復發率。
3 CHIVA術后血管直徑變化
根據CHIVA原理通過結扎反流點,減輕透壁壓導致靜脈曲張直徑縮小,直至恢復正常[8-9]。為確定靜脈直徑在術后是否增加或減少,Mendoza[13]對383例470條腿在術后8~25 w內進行隨訪,檢查對比大隱靜脈和股總靜脈的直徑,研究發現男女大隱靜脈和股總靜脈的直徑有統計學差異。女性組GSV直徑從術前6.1 mm縮窄至術后4.5 mm,男性組從6.8 mm縮窄至5.1 mm。女性組股總靜脈直徑從術前14.0 mm縮窄至術后13.7 mm,男性組從術后16.5 mm縮窄至16.1 mm,術后兩個月股總靜脈直徑顯著減少,從而證實了CHIVA不會使深靜脈系統超負荷,反而可以緩解深靜脈壓力。為了驗證長期效果Mendoza[14]在43例患者于GSV或SSV的CHIVA治療5年后進行評估,在整個組中,股總靜脈直徑從術前的15.4 mm經8 w后降至15.1 mm,5年后的14.2 mm。伴有GSV反流的患者中,股總靜脈的直徑從術前的16.1 mm減少到8 w后的15.3 mm(不顯著),5年后減少到14.3 mm(與術前和術后8 w相比顯著)。GSV直徑從術前的平均直徑7.0 mm減小到8 w后的5.0 mm,5年后減小到4.4 mm。而對小隱靜脈干預后,健康的大隱靜脈直徑變化不大。從而再次證明了CHIVA手術不僅短期療效是可以肯定的,并且長期療效一樣存在。
4 穿支靜脈在CHIVA術前評估的重要性
根據下肢肌肉筋膜的解剖將下肢分為3個不同的靜脈網[15](N1、N2、N3),N1:肌肉筋膜下的深靜脈系統;N2:深、淺筋膜間的隱靜脈系統(GSV,SSV,Giacomini);N3:淺筋膜外的血管(GSV和SSV分支)。通常情況下生理靜脈引流的等級順序通過穿支靜脈直接從最淺的網絡N3進入N1,或通過N2系統間接發生,即N3-N2-N1。因此,反流可以定義為靜脈排空分層順序的任何變化[8]。遵從CHIVA血流動力學原理,結扎處理逃逸點(反流開始),保留再入點通過正常穿支靜脈回流進入深層系統,可見穿支靜脈單向瓣膜功能,是靜脈正常回流的基礎,病變穿支靜脈能否有效解決,直接影響到CHIVA手術效果和術后的復發,根據王鑫毅等[16]研究發現在69例GSV患者中發現81支穿靜脈反流,楊文超等[17]在421條患肢中發現599條穿支靜脈功能不全。兩項研究共同認為,當穿支靜脈>4 mm時無論反流時間多長均應診斷為穿支靜脈功能不全,在術中積極處理,可有效糾正病變的血流動力學。由此可見穿支靜脈在CHIVA系統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術前準確全面的評估是該術的關鍵點,評估方式多種多樣,包括血管B超、下肢血管造影、CT靜脈造影、磁共振靜脈造影等[18],各有優勢和不足,血管B超無疑是最方便、快捷的檢查方式。但需要初學者投入大量的培訓和經驗積累,以及對血流動力學的完整理解。對CHIVA的不完全了解可能會產生比傳統療法更糟糕的結果。
5 CHIVA術后復發率問題
靜脈曲張術后復發一直都是一個不可避免的復雜而頻繁的問題,仍然是治療上的挑戰。目前CHIVA術式爭議較大,主要還是術后效果及復發率的問題。在Carandina等[19]報道的一項150例患者的隨機研究中平均隨訪10年發現,CHIVA組與傳統組相比,CHIVA組復發率為18%,傳統組為35%。在王華等[20]研究中CHIVA組1年復發率為1.25%,傳統組為8.75%。在Zmudzinski等[21]一項58條患肢前瞻性研究中平均隨訪16.4個月,B超檢查發現5條患肢再次反流,復發率為8.6%。一項2019年的薈萃分析中對消融,硬化劑療法,CHIVA,結扎和剝離術式術后治療率和復發率進行比較分析,認為CHIVA的擁有最高的治療率和最低的復發率[22]。但在2020年的一項225條患肢隨機對照試驗研究顯示[23]:術后兩年復發率分別為射頻消融:7.2%;高位結扎剝脫術:4.3%;CHIVA:14.7%。 相關研究結果的不同,更多的應考慮方案制定和技術上的問題,術前血管B超篩查情況,可直接影響方案制定,技術問題則更多的依賴于手術技巧,與術者密切相關。射頻消融或傳統手術,以完全閉合或剝離GSV為目的,所以方案制定方面誤差較小,CHIVA與二者的不同在于CHIVA每個患者都需要制定個性化治療方案,因各個研究者水平高低不同可能會出現更多的技術失誤,導致術后效果天差地別,因此應理性對待術后復發率等問題。
6 未來隱靜脈在旁路手術中的運用
冠狀動脈阻塞引起的心肌缺血是西方國家發病率和死亡率的主要原因[24],并且隨著年齡的增長而增加,除了通過改變生活方式進行一級預防外,經皮冠狀動脈介入治療(PCI)或冠狀動脈旁路移植術進行有創血管重建是其主要的治療方式。盡管PCI技術發展迅猛,具有創傷小、恢復快等優勢,但根據美國和歐洲的指南冠狀動脈旁路移植術仍然是治療復雜性多支冠狀動脈疾病和/或左主干疾病的金標準[25-26]。盡管移植管道的選擇一直存在爭議性,因隱靜脈具有可用性強、容易獲取、吻合期間容易處理、胸骨傷口并發癥較少等優勢仍然是移植時最常用的管道[27]。在CHIVA策略中隱靜脈的保留是其重要的一個環節,可能具有以后在旁路手術中進一步使用的優勢。由于CHIVA術后隱靜脈管壁病理生理及術后再次用于旁路移植研究較少,缺乏切實的循證學依據,其質量及遠期通暢率能否滿足臨床要求仍需進一步驗證。
7 小結
作為新興術式微創、局麻、低成本、疼痛輕是其獨有的優勢,可能具有神經零損傷、低復發率、隱靜脈的保留用于旁路移植手術等特點[9]。但學習成本較高,需要扎實的血流動力學理論知識,每個患者都需要制定個性化治療方案,但不同中心的醫療技術水平不同,易出現決策性失誤,術后效果不一,這也是爭議的原因。根據筆者的臨床實踐,部分C3以上患者術后曲張靜脈直徑收縮不全,外觀改善不明顯,但臨床癥狀如:酸脹、沉重、抽搐、潰瘍卻有著極大的改善。若對結扎后的無效曲張靜脈進行點狀剝脫,患者術后美觀滿意度較高。總之隨著微創外科的發展,日間門診手術逐漸成為臨床趨勢,CHIVA策略或許是一種全新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