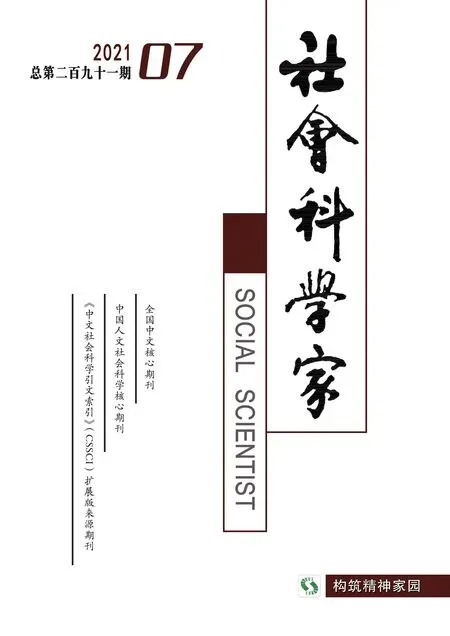社會網絡與居民消費支出
——來自中國家庭追蹤調查數據的證據
孫海剛,馮春陽
(鄭州銀行,河南 鄭州 450046)
一、引言及文獻綜述
(一)引言
后疫情時代,民粹主義升溫,貿易保護主義抬頭,我國國內外發展環境面臨深刻調整,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國際國內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勢在必行。因此,挖掘國內市場潛力,促進居民消費水平提升將是未來實現中國經濟增長動力轉換的關鍵環節。那么,如何促進國內消費水平提升呢?明確影響國內居民消費水平的原因至關重要。事實上,居民消費與居民的生活環境息息相關,其中“社交關系”是居民的生活環境的重要體現。中國作為一個傳統的關系型社會,每個個體都生活在基于社會交往的社會網絡①社會網絡是指個人或家庭所擁有的親戚、朋友、同事或鄰居等構成的關系網絡,居民通過家庭社會網絡擁有的社會網絡獲取資源,從而影響就業、福利和貧困。中,社會網絡對居民信息交流、個人行為等產生著較大影響。因此,社會網絡對居民家庭消費可能存在著影響。
(二)相關文獻綜述
社會網絡從多角度影響了居民經濟行為。首先,社會網絡對居民就業,對抗不確定性帶來的風險有著顯著積極影響[1],例如,家庭宗族網絡能夠為其網絡內成員提供勞動力流動的社會保障[2]。其次,社會網絡對居民金融行為的影響。社會網絡促進了農戶保險購買意愿和提高了金融參與度[3]。社會網絡的廣泛性與農村儲蓄率呈負相關,這種相關關系尤其在低收入家庭最為明顯[4]。社會網絡有利于農戶獲得民間借貸[5],同時也有利于其獲得正規金融機構貸款,與非正規渠道借貸相比,社會網絡對正規金融機構借貸行為的影響更為強烈[6]。再次,社會網絡增強了農民工的流動性,使其能夠跨越到經濟增長“核心”區,從而增加工資水平[7]。同時,社會網絡也縮小了城鄉居民收入差距[8]。最后,社會網絡的其他效應。
二、相關假設
就社會網絡對居民消費的影響而言。社會網絡促進了內部成員的信息交流,形成了一定程度的消費“示范效應”和“聯動效應”,進而造成了消費行為的趨同性[9]。例如,通過社會交往增加了酒精飲料的消費[10],來自坦桑尼亞、南非、印度尼西亞等國的數據也證明了社會網絡增加了居民消費[11]。因此,社會網絡對我國居民家庭消費也應當有顯著的正向影響,由此得到本文的第一條假設。
假設1:社會網絡促進了我國居民家庭消費,居民社會交往形成的社會網絡對居民家庭消費有顯著的促進作用。
以收入為代表的各種不確定性是居民儲蓄動機的重要來源,是抑制居民消費的重要因素。在流動性約束的情況下,社會網絡能夠為網絡成員提供風險共擔機制,為居民對抗收入波動風險和平滑消費提供保障[12]。這種社會網絡對居民防御性儲蓄的負向影響從而對消費的保險作用在我國同樣存在[13],特別是對低收入群體而言,通過社會網絡獲得流動性支持從而減少預防性儲蓄的作用更加明顯[4]。作為家庭收入分配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社會網絡既然對低收入家庭儲蓄有負向影響那么其對家庭總消費就應當有正向的促進作用。為此,本文提出第二條假設。
假設2:社會網絡對低收入家庭的消費有顯著正向影響,對較高收入家庭而言這一作用可能并不明顯。
處在特定社會網絡中的成員一般存在某種“特定的行為規范”,能夠影響網絡中成員的偏好和消費行為[14],即消費者同伴的當期消費能夠影響決策者的跨期消費決策[15]。此外,消費者在消費中感受到的“自卑感”促使其通過炫耀性消費來表現他們在物質領域的優越感。但這取決于比較對象與自我之間是競爭關系還是合作關系[16]。在消費結構上,通過購買能夠彰顯其經濟地位的消費產品,是在炫耀性消費動機下消費者最有可能的選擇。推而廣之,對于我國消費者而言,在發展與享受型消費的消費行為中也可能存在炫耀性消費的動機。為此,本文得出第三條假設。
假設3:在炫耀性消費動機及社會網絡中“規范”的影響下,社會網絡對中國居民家庭的發展與享受型消費存在正向影響。
本文可能的創新點如下:1.數據來源上,本文使用2014-2018年中國家庭追蹤調查數據組成的面板數據,研究了包括城市和農村居民在內的社會網絡與居民家庭消費之間的關系,進一步完善了樣本構成,盡可能克服因遺漏變量造成的結果偏誤;2.考察了不同居民收入水平下,社會網絡對家庭消費行為影響的差異;3.研究了居民家庭社會網絡對居民家庭消費結構的影響,明確了影響路徑。
三、家庭社會網絡與家庭消費的基本事實
本文使用了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調查中心于2014、2016及2018年開展的“中國家庭追蹤調查(CFPS)”數據庫中的合并數據。依據家庭編碼的唯一性,只保留了三年中均在調查樣本中的家庭。在家庭消費中,戶主往往對家庭消費有著絕對的話語權,本文以數據庫中家庭“財務回答人”作為家庭戶主,并依據其代碼的唯一性提取了其個人信息數據。在社會網絡的度量方面,本文選取由“禮尚往來”而來的“人情禮支出(元/年)”作為社會網絡的代理變量。在家庭消費構成方面,將居民家庭消費分為基本生活需求消費和發展與享受型消費。其中基本生活需求消費包括食物煙酒、衣著、居住及交通通信消費;發展與享受型消費包括家庭設備、文教娛樂、醫療保健及其他消費支出[17]。
樣本中,如表1所示,城市居民總消費遠高于農村居民,消費總量也沿東、中、西部地區梯次下降。與總消費支出相反,西部地區居民禮金支出最高,中部地區次之,東部地區最低,這也印證了社會網絡的作用可能隨著經濟發展程度的提高而逐步弱化,同時也意味著隨著正式制度的建立和完善,非正式制度的作用將趨于弱化[18]。

表1 城鄉和地區總消費及社會網絡變量描述(單位:元)
四、家庭社會網絡對家庭消費的實證研究
(一)社會網絡對居民家庭總消費的影響
1.基本模型的設定
理論上,家庭總消費支出和家庭的持久收入相關,較高的持久收入能夠帶來更高的消費水平,同時,家庭消費受到家庭資產帶來的財富效應的影響。基于此,設立計量模型如下:

方程(1)中,i代表居民家庭,t代表樣本調查時間。lntoconit表示居民家庭i在t年的總消費支出。lnsnit為居民家庭i在t年的禮金支出,其中禮金支出以問卷中“人情禮支出(元/年)包括實物和現金,過去12個月,您家總共出了多少人情禮?”為度量指標。除此之外,本文還控制了居民家庭收入lnincit及家庭資產情況lnastit。與家庭戶主相關的控制變量選取如下:家庭規模(Famsize),本文將家庭規模設定為3.5人以下家庭及大于3.5人的家庭;戶主年齡(Age)及其平方項(Age2)、戶主性別(Sex)、戶主的婚姻狀態(Marriage)、戶主是否接受過高等教育(Edu)、家庭居住地區是農村還是城鄉(City_cou)、是否為黨員(Party)及個人健康狀況(Healthy)。
2.內生性的解決
考慮到社會網絡與家庭消費之間的內在關系:首先,社會網絡可能通過信息傳遞及社會網絡中包含的共同價值觀(社會規范)影響居民家庭消費支出。其次,居民家庭消費支出水平也可能影響居民社會交往情況,進而影響居民家庭禮金支出。第三,雖然在模型設定中盡可能控制了影響居民家庭消費支出的相關變量,但諸如家庭傳統、偏好、能力等某些影響因素依舊會落入模型殘差中,因此,因遺漏變量而導致的內生性問題同樣值得關注。參考楊汝岱等[5]本文選用了每個居民家庭所屬區縣的戶均禮金支出作為家庭社會網絡的工具變量。原因在于:一方面,戶均禮金支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該地區的禮金支出習俗,對于家庭禮金支出而言具有較強的外生性,同時,地區禮金支出習俗將影響到家庭的禮金支出情況,但并不直接影響每個家庭的消費情況,此外,戶均禮金支出也與家庭不可觀察的傳統、偏好、能力等因素無關。另一方面,某一居民家庭消費情況基本上不會影響到地區戶均禮金支出,同時,戶均禮金支出也大大降低了測量誤差的可能性,因此也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反向因果、測量偏誤等問題。
3.實證分析結果
表2(1)-(6)列展示了家庭社會網絡對家庭總消費支出影響的基準回歸結果。其中,第(1)-(3)列使用了固定效應模型;第(4)-(6)列使用了固定效應兩階段最小二乘法,所有回歸均使用穩健估計方法(Robust Regression)。其中第(1)列為基準方程,第(2)-(3)列不斷增加控制變量,雖然社會網絡對于居民家庭總消費的影響有所下降,但仍呈現顯著的正相關關系。

表2 社會網絡對居民家庭總消費影響的基準回歸
第(4)-(6)列使用固定效應兩階段最小二乘法對方程(1)進行了估計,以每個居民家庭所屬區縣的戶均禮金支出作為居民社會網絡的工具變量。第(4)列為基準方程,第(5)列在第(4)列的基礎上控制了居民家庭收入和資產情況,結果顯示社會網絡對居民家庭消費的影響并不顯著。第(6)列增加了戶主的個人信息,結果表明社會網絡在5%的顯著性水平上影響了居民家庭總消費支出,同時,從系數上看,該列社會網絡代理變量系數為0.041,遠高于方程(3)固定效應的估計系數,說明普通固定效應模型低估了社會網絡對家庭消費的影響,也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了由于社會網絡與消費的內生性問題的存在確實造成了二者之間的不一致估計。從回歸方程的檢驗看,第(6)列中一階段回歸的Kleibergen-Paap-F統計量為62.983,高于10的臨界值,說明使用的工具變量與內生解釋變量存在較強的相關關系;與此同時,Hansen-J統計量的P值為0.737,超過了0.05的臨界值,證明了工具變量的有效性。
通過以上基準回歸,居民家庭社會網絡的確對居民家庭消費產生了顯著影響,其彈性系數為4.1%,即居民家庭社會網絡投資每增加1%,家庭總消費支出將增加4.1%,社會網絡對消費的刺激作用較為強烈。這一結果證實了假設1的猜想。除消費的“聯動效應”和“示范效應”外還有文獻認為擁有更多的社會資源可以使個體擁有更強的應對風險的能力,從而促進一般信任的發展[19],而社會信任的提升也能夠通過降低居民消費中的風險感受促進居民消費[20],這也是社會網絡對居民家庭消費有顯著提升影響的另一渠道。
(二)社會網絡對居民家庭總消費影響的穩健性檢驗
表3中通過替換樣本和替換變量進行穩健性檢驗。表3中(1)-(3)列使用交通通信費用(Ct)①交通通信費用(Ct)包括郵電通信費和本地交通費。作為社會網絡的替代代理指標進行了回歸,同時,在總消費中將該交通通信費用剔除(tocon_adj)。交通通信費用在很大程度上衡量了本地的基礎設施建設水平,衡量了居民家庭對基礎設施的依賴程度,同時,對于居民家庭而言,相較于一個年度內由親朋好友引起的不經常發生的禮金支出,交通通信費用衡量了居民家庭平時的社交情況,較高的通信交通費用支出在一定程度上衡量了居民家庭在日常生活中本地區的社交廣度、密度和社交距離。但是,與禮金支出一樣,交通通信費用支出與居民消費支出也可能存在一定的內生性聯系,所以,參考對禮金支出的處理方法,同樣采用每個居民家庭所屬區縣的戶均交通通信費用作為其工具變量。
表3第(1)列使用全樣本同時使用交通通信費用為工具變量進行了回歸,結果顯示,社會網絡對于居民家庭總消費(tocon_adj)的影響依舊顯著。第(2)列使用30-65歲戶主的家庭樣本進行了檢驗,該組別家庭是個人事業開始和尾聲階段,其對于社會網絡的依賴度高于其他組別。結果顯示社會網絡替代代理變量依舊有效,且系數有明顯改善。第(3)列剔除了消費最高及最低的10%家庭樣本,結果顯示社會網絡對其家庭總消費支出的影響依舊穩健。

表3 社會網絡對居民家庭總消費的穩健性檢驗
為了考察禮金支出作為社會網絡代理變量的穩健性,表3(4)-(5)列使用未剔除交通通信費用的總消費支出進行了回歸。第(4)列使用35-65歲戶主家庭組別進行回歸,結果顯示社會網絡對居民家庭消費仍然存在顯著積極影響,且在10%的水平上顯著。第(5)列同樣剔除了樣本中最高及最低的10%樣本,社會網絡對家庭總消費支出同樣在10%的水平上顯著。以上回歸證明無論是替換社會網絡的代理指標還是分樣本回歸,社會網絡對居民家庭消費的影響都是顯著的,證明了前文基準回歸結果的穩健性。
(三)影響的異質性分析
表4第(1)-(3)列展示了對樣本中家庭按照居民家庭收入水平進行劃分的情況,考慮到收入樣本基本服從正態分布,對樣本按照≤30%、30%-70%和≥70%三個階段進行了劃分。如表4所示,樣本中社會網絡只對收入水平較低的家庭產生了顯著影響并在1%的顯著性水平上顯著,其他樣本并不顯著。這證明了假設2的存在,即社會網絡對低收入群體的消費有更加顯著的提升作用。這可能是因為,如消費者在消費中感受到的“自卑感”是其進行“炫耀性”消費以獲得“優越感”的一大動因一樣,對于收入水平較低的群體而言,通過社交網絡不斷地進行信息交流和模仿他人消費行為可能是低收入家庭弱化其收入“自卑感”的一種方式。而這種消費模式是在社會網絡能夠向低收入居民提供“消費保險”的作用下進行的,考慮到居民收入通常用來儲蓄和消費,這可能也從另一個方面解釋了社會網絡對較低收入農戶儲蓄率有顯著負向影響的原因。對于處于中等和較高收入水平的群體而言,隨著收入水平提升,居民家庭消費的從眾心理開始減弱,更多的追求基于自身偏好的消費,從而使得社會網絡對其消費的影響減弱。

表4 社會網絡對居民家庭總消費的差異化影響及地區差異
表4第(4)-(6)列分別為對我國東、中、西部地區樣本進行考察的結果:社會網絡對東、中部地區居民家庭消費產生了顯著正向影響且在10%的水平上顯著。而對西部家庭而言,社會網絡對其影響并不顯著。表1中,家庭禮金支出沿西、中、東部地區依次降低,但是家庭禮金支出對其總消費的影響卻在東部地區最高,其次為中部地區家庭,而對西部地區家庭而言,家庭禮金支出對總消費的影響并不顯著。這可能證明了社會網絡作為一種非正式制度會隨著經濟發展程度的提升而不斷弱化。例如,東、中、西部地區經濟發展程度依次降低,交通通信、金融服務等基礎設施發達程度同樣依次降低,如表1中,東、中、西部地區居民家庭交通通信費用依次為2918.633元、2946.220元、3154.202元。所以,交通通信的便利性帶來更多的社會交往及社會網絡的擴大,社會交往的密度和廣度在東、中、西部地區有著顯著差異,而這種社會網絡中所蘊含的人脈信息、商業機會及新消費信息的傳播也是不同的,可能導致社會網絡對家庭消費的影響表現出地區差異。
五、對居民家庭消費結構影響的進一步分析
表5第(1)-(8)列匯報了社會網絡對居民家庭消費結構的影響。在基本生活需求消費中,第(2)和第(4)列分別為社會網絡對衣著支出、交通通信類消費的影響,影響系數為正,其系數分別為0.066和0.079且至少在10%的顯著性水平上顯著。在發展與享受型消費中,(5)-(7)列分別為社會網絡對家庭設備、文教娛樂和醫療保健支出的影響,其系數分別為0.134、0.08、0.06且至少在10%的水平上顯著。由此,社會網絡主要通過家庭衣著、交通通信、家庭設備、文教娛樂及醫療保健消費影響了家庭總消費支出。

表5 居民家庭社會網絡對于家庭消費結構的影響
值得注意的是,相較于衣著支出和交通通信費用,社會網絡對發展與享受型消費中的構成項目影響彈性更高。可能的原因在于,衣著支出及交通通信費用支出更為剛性,屬于經常性支出,居民日常交往中對這類消費的關注較少。作為非經常支出的發展與享受型消費,該類商品和服務的單價往往較高,是居民展示其社會經濟地位的主要表現形式,例如,家庭設備和文教娛樂消費在社會網絡中“共同規范”及可能存在的“炫耀性消費”的因素影響下,社會網絡對這兩種消費的影響也更為強烈。而這一現象也能夠從各影響系數中得到體現,例如社會網絡對發展與享受型消費的影響系數普遍高于衣著和交通通信費用,同時在最能彰顯家庭社會經濟地位的家庭設備消費上(主要是家庭耐用品消費),社會網絡對其影響系數達到了13.4%,顯著高于其他發展與享受型消費。以上研究結果證明了假設3,即社會網絡對居民發展與享受型消費的影響更為顯著。
六、結論與對策措施
(一)結論
使用2014-2018年中國家庭追蹤調查數據組成的面板數據,研究了社會網絡對居民消費支出的影響,同時,利用工具變量考察了社會網絡與居民家庭消費之間的內生性并得到以下結論:
1.家庭社會網絡正向影響了居民家庭總消費支出,在考慮社會網絡與居民家庭總消費內生性關系后該影響依舊顯著,在多種穩健性檢驗下該正向影響關系依舊成立。
2.考慮到不同收入水平層次及地域特征的差異性,社會網絡對收入水平較低的家庭消費具有顯著正向影響,而對于處于中等及較高收入水平的家庭而言,社會網絡對家庭消費并無顯著影響。同時,在地區差異中,社會網絡對處于東部和中部地區家庭的總消費有著顯著影響,對于西部地區居民家庭而言,社會網絡對其家庭總消費支出有負向影響,但并不顯著。
3.從居民家庭消費結構方面考察了社會網絡對家庭總消費影響的原因,發現居民家庭社會網絡主要通過影響基本生活需求消費中的衣著支出及交通通信費用影響了居民家庭總消費,同時,社會網絡也通過影響發展與享受型消費中家庭設備、文教娛樂及醫療保健支出影響了居民家庭總消費支出。
(二)對策措施
根據前文的研究結論,結合我國經濟現實,可以得到以下幾點啟示:
1.由于社會網絡對居民家庭總消費有著顯著正向影響,是提高居民家庭總消費的重要途徑,而這種影響是通過“聯動效應”和“示范效應”產生的。因此可以考慮加強建立不同形式的社交平臺,如充分發揮基層組織作用,引導居民良好消費理念,并通過消費的聯動及示范效應推動居民消費的合理化及理性化。具體來講,可以考慮建設良好社區氛圍為居民之間建立良好的社交網絡提供便利的環境,在相互交流和信息溝通中,形成良好的消費習慣,提高居民消費水平和生活質量。
2.鑒于不同收入群體的社交網絡對于消費的拉動作用存在差異,因此,需更加重視低收入群體和高收入群體的社交網絡的建立,對于低收入群體,應當加強社會保障功能,保障其基本生活需求消費,同時也應當引導低收入群體合理利用其社會網絡的消費保險功能,合理借貸和適度提前消費,杜絕消費者之間的不合理“攀比”。對于高收入群體而言,其消費能力較強,同時更加重視其社會網絡中人脈的建設,因此在供給端提供更加符合其消費理念和消費習慣的產品的同時還應充分利用高收入群體在消費中的“領頭羊”作用,引導高收入群體不進行過度的炫耀性消費從而避免形成不良的社會風氣,帶動其他消費群體形成“勤儉節約”及更加關注環保等社會議題的良好消費習慣。以此雙管齊下,充分挖掘城鄉居民各消費層次群體的消費潛力。
3.雖然居民家庭社會網絡能夠顯著提升居民消費水平和居民信任水平,但是居民社會網絡中對于消費的負面消息同樣值得關注。如對于傷害消費者權益的產品和服務,居民社會網絡對該類產品及服務的家庭消費將產生負向影響。因此,加強產品質量管控能力、建立失信行為曝光平臺、建立企業巨額罰款制度等有助于提升居民消費信心的措施同樣值得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