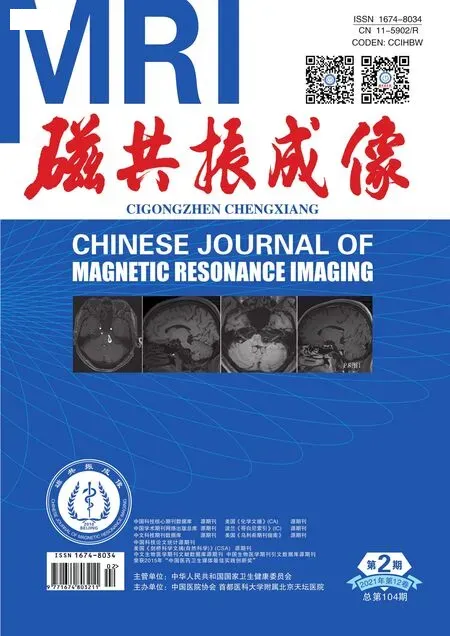缺血性腦卒中的神經影像學進展
盧予婕,李文美*,梁志堅
在臨床,盡管急性中風的治療取得了進展,但20%~30%的患者仍會在一個月內死亡,70%~80%會導致嚴重的長期殘疾[1]。目前基于證據的治療方法包括靜脈溶栓(intravenous thrombolysis,IVT)和機械血栓切除術(mechanical thrombectomy,MT),現代影像技術在鑒別患者是否受益于MT或IVT 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更先進的成像技術能更準確地評估局灶性損傷后大腦網絡結構和功能連接的損傷和重塑。功能性神經影像學數據分析的新進展使我們能夠在活體內評估單個腦區(qū)對功能恢復的特殊貢獻以及治療對皮層重組的影響。連接性分析可以用來研究中風對大腦網絡的影響,并幫助我們理解為什么有些患者比其他患者恢復得更好。這些系統(tǒng)水平的觀點提供了關于神經調節(jié)干預如何針對與不完全恢復相關的病理網絡配置的見解。未來,這些連通性分析有助于優(yōu)化基于特定神經功能缺陷的個體網絡病理學的治療方案,從而為患者分層開辟新的個性化道路。
1 基于擴散的磁共振技術
基于擴散的磁共振技術(diffusion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dMRI)是目前應用最廣泛的評價急性或亞急性缺血性腦卒中后灰、白質改變的神經影像學技術。MR 信號對細胞內水分子的擴散分布敏感且可在多個方向上迭代估計空間擴散率和擴散權重[2],由此不僅可以檢測到與疾病相關的擴散特性變化,還可以進行纖維束重建。大部分擴散模型都依賴于重建總體平均擴散密度函數(ensemble average propagator,EAP)來間接量化不同微觀結構特征改變,從而評估卒中相關神經網絡和病灶周圍神經細胞[3]的改變。纖維束追蹤能評估結構連接性(可用圖論進行降維分析,研究腦網絡拓撲結構,描述小世界屬性及其經濟性,量化大腦區(qū)域在腦網絡中的整體作用[4-5])。橫向研究可評估卒中神經網絡的潛在改變與卒中后遺癥功能的相關性,如運動(皮質脊髓束)[6]、失語(弓狀束)[7]、忽視(上縱束)[8]等,縱向研究可預測中風后的功能恢復情況。源于初級運動皮層的皮質脊髓束(corticospinal tract,CST)是大腦控制運動系統(tǒng)的關鍵下行束,其結構與卒中運動功能的損傷和恢復密切相關[9-10]。隨后的研究發(fā)現,不僅CST,其他的替代運動纖維網絡(alternate motor fibers,aMF)也與中風后的運動恢復情況息息相關,如皮質-紅核-脊髓束[11]和皮質-網狀-脊髓束[12]。在很長一段時間內,皮質-皮質間(cortical-cortical)網絡一直被忽視,擴散成像對其相互作用的研究大大擴寬了卒中恢復過程中腦網絡相互作用的概念,比如研究發(fā)現同側額頂區(qū)的結構連接與卒中后殘存的運動功能相關[13]。此外,應用非侵入性腦刺激技術和電生理研究表明,大腦半球間相互作用與中風恢復至關重要[14]。因此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這些重要網絡的結構功能狀態(tài)可能與中風后的恢復和殘余功能有關。未來的結構連接性分析可以探索這些網絡特性相互作用的機制,幫助更好地理解卒中后的大腦可塑性。
1.1 磁共振擴散張量成像
1994 年,Basser 等[15]提出張量模型,假設水分子運動分布符合高斯分布,根據水分子擴散的各向異性原理,利用3 個特征值λ1、λ2、λ3描述擴散張量D,在不少于6 個方向上施加梯度,再根據一幅參數相同而未施加梯度的b0圖像,計算出擴散張量的各向異性擴散方向信息追蹤白質纖維束。主要參數包括:平均彌散率(mean diffusivity,MD)、各向異性分數(fractional anisotropy,FA)、徑 向 擴 散 系 數(radial diffusivity,RD)及 軸 向 擴 散 系 數(axial diffusivity,AD)[16]。
大量研究證明,缺血性卒中的腦白質微結構有顯著變化,且磁共振擴散張量成像(diffusion tensor imaging,DTI)假設神經元信息流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結構的完整性,因此FA和其他擴散指標可作為敏感的定量指標[17-19]。Lotan 等[17]發(fā)現在原發(fā)性梗死遠端的下行錐體束中FA 值顯著降低,并伴有MD 增高或未改變。與健側相比,特定的軸突損傷導致了逆行繼發(fā)性神經退行性變,患側CST 喪失了微結構完整性。此外,用概率性追蹤或確定性追蹤方法進行纖維成像,追蹤全腦纖維構建腦網絡,如引入一個結合梗死面積和大腦網絡拓撲結構信息的損傷影響評分可預測卒中后的認知功能的長期恢復情況[20]。
DTI 的缺點:自由水的運動不符合高斯分布,且體素內纖維分布具有異質性,加上部分容積效應影響,DTI 的定量參數的準確性及特異性值得探討[21],且DTI 纖維追蹤并不能準確顯示交叉、匯聚和擴散纖維的走行[22]。因此,基于高階模型和無模型理論的擴散成像方法得到發(fā)展,如磁共振峰度成像、神經突起方向離散度與密度成像[23]、高角分辨率擴散磁共振成像、磁共振擴散譜成像等。
1.2 磁共振峰度成像
2005 年,Jensen 等[24]提出峰度模型,可檢測水分子非高斯分布情況。“峰度”(kurtosis)一詞是指過量峰度,是水位移分布標化的第四中心矩(引入四階張量,用對稱三維四階張量3×3×3×3表示峰度的方向性),用于量化水擴散位移曲線與高斯分布的偏差,反映組織結構的受限與組織成分混雜。構建磁共振峰度成像(diffusion kurtosis imaging,DKI)模型至少要兩個非零b 值(頭顱中b 值>2000)和15 個非線性梯度方向。除了提供DTI 的參數外,DKI 的主要參數為:平均彌散峰度(mean kurtosis,MK)、軸向峰度(axial kurtosis,Ka)、縱向峰度(radial kurtosis,Kr),分別代表組織內異質性和軸突、髓鞘的完整性。
與DTI相比,DKI使用了較大的b值,增加的量化非高斯擴散的指標提供了組織異質性信息,研究表明,峰度指標對CST早期微結構變化的檢測具有更高的敏感性[9,25],且有潛力表征不同位置急性缺血性中風腦組織的微結構變化差異,特別是MK,都優(yōu)于普通擴散指標[26]。此外,Wu等[27]在常規(guī)DKI的基礎上,介紹了一種快速DKI 協(xié)議(可直接映射MD 和MK),在急性腦卒中可對組織損傷快速進行分級并評估可挽救性。將DKI 與擴散加權成像(diffusion weighted imaging,DWI)互補用于缺血性卒中也有很大的臨床價值,基于DWI 顯示病變,有峰度變化的損傷更嚴重,而沒有峰度異常損傷較輕[28-29],且峰度-擴散失配有助于識別DWI 病變中較有可能在早期再灌注后恢復的部分[30]。
DKI 的缺點:①在模型假設的基礎上,它描述水分子的擴散并非十分全面,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②DKI的定量值不穩(wěn)定,因檢測部位的不同和研究設計的不同而有很大的變化[31]。③由于使用比DTI 更高的b 值,噪聲問題值得注意,不充分的信噪比可能會導致峰度值的過高估計。
1.3 擴散譜成像
2005 年,Wedeen 等[32]提出擴散譜成像(diffusion spectrum imaging,DSI),在不建立先驗模型的前提下,不對擴散過程進行假設,描述水分子在任意幾何空間內的擴散特征,能夠觀測單體素內多方向的纖維束,并追蹤重建出真實而復雜的纖維組織結構。目前基于q-space 進行的重建模型主要包括球棍(Q-ball imaging,QBI)、DSI 以及廣義q 空間采樣(generalized Q-sampling imaging,GQI)。QBI[[33]常使用Funk-Randon 變換或球諧函數來計算取向分布函數(orientation distribution function,ODF),適用于殼樣擴散采樣方案(即HARDI 采集方式,單個b 值多個方向)。DSI 基于擴散信號和氫質子擴散位移之間的傅立葉關系計算概率密度函數(probability density function,PDF),代表體素內平均相對自旋位移密度,再對轉換后的網格數據進行數值積分得到ODF,表示擴散的角度方向信息,傅立葉變換需要特定的網格擴散采樣方案(多個b 值多個方向)。GQI[34]主要探索質子自旋分布函數(spin distribution function,SDF)與MR 信號之間的關系,與ODF 不同的是,SDF 反映不同方向上水分子擴散的密度,是一種擴散ODF,且能在不同體素內進行分析,適用于任何擴散采樣方案數據。QBI 和DSI 僅提供擴散ODF 的數值估計,而GQI 直接計算SDF,從而避免數值估計中的誤差。這些重建方法都可對纖維交叉及走行進行評估,反映潛在的組織各向異性。比如,由ODF 函數得出的通用各向異性值(generalized fractional anisotropy,GFA) 或者擴散各向異性值(diffusion anisotropy,DA)可評估組織微結構的特征。但GFA 和FA 是高度相關的,會受到部分容積效應的影響,因此Yeh 等[34]提出了一種新的定量指標各項異性值(quantitative anisotropy,QA),量化各項異性水分子自旋分布的密度(對每個纖維束方向定義)。FA 和GFA 是針對每個體素定義的,體素內的所有纖維群共享相同的度量,這是它們最大的差異。針對比較QA 值時存在的一致性問題,提出標準定量各項異性值(normalized quantitative anisotropy,NQA)以及各向同性擴散分量指標(isotropic diffusion component,ISO)。
此外,2013 年Ozarslan 等[35]提出一種基于q 空間采樣觀察腦白質微結構相關恢復特征的算法——平均表觀傳播子(mean apparent propagator,MAP)MRI,由簡諧波振蕩SHORE模型延伸而來。 衍生參數包括:原點回歸率(the return-to-origin,RTOP)、返回到軸概率(return-to-plane,RTAP)、返回平面概率(return-to-axis,RTPP)、傳播各項異性(propagator anisotropy,PA)等,分別量化擴散受限程度、軸向/徑向擴散受限程度和各項異性。研究證明,MAP-MRI 相關參數可以提示重要微結構組織變化,且參數穩(wěn)定,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大腦白質的微結構相關特征[36-37]。
在最近的研究中,采用DSI 對受試者建立擴散磁共振連接組數據,再與慢性卒中患者匹配檢測異常,提供了個體水平的大腦發(fā)育、可塑性和疾病的結構連接性信息[38]。以及證明DSI 分析指標作為缺血性卒中新的白質生物標記家族的可行性,以及在灰質中的潛在利用性,且與DTI 衍生指標(FA 及MD)的組合可提供與卒中病理相關的更詳細見解,如卒中后1 周病灶RTAP、RTPP 和MSD 的異質性有助于區(qū)分缺血核心區(qū)和半影區(qū)[39]。歸功于無模型假設,DSI 可提供高精度的測量,可作為中風后神經元可塑性變化的數字生物標志物,預測轉歸[40],且DSI_Studio(http://dsi-studio.labsolver.org/)提供了便捷的后處理方法,包括定量、纖維追蹤、連接學[38]、可視化及腦網絡等分析。
2 血氧水平依賴性功能磁共振成像
近年來,作為可評估腦組織活力和受損組織血流情況的神經影像學技術,血氧水平依賴性功能核磁共振成像(blood oxygen level-dependent 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BOLD-fMRI)漸漸被應用于實驗和臨床,提高了對腦灌注損傷和組織氧合損傷病理生理機制的認識。于中風患者而言,神經功能損害有時會超過中風程度的預期。因為卒中損傷不僅導致局灶性、位置依賴性的神經癥狀,還可以通過功能網絡在受影響和未受影響的半球偏遠區(qū)域引起廣泛影響[41]。fMRI 可以提供全腦覆蓋信息(提供功能性網絡的交互模式與中風結局的聯(lián)系)和血管功能時空變化信息(如使用校準BOLD提取氧攝取分數),進一步加深對急性、亞急性再灌注損傷機制的理解,這可能會延長安全有效使用溶栓劑的時間窗[42]。
考慮到任務態(tài)功能磁共振成像的特點以及缺血性卒中患者的臨床情況,本文主要陳述靜息態(tài)功能磁共振成像技術的應用。靜息狀態(tài)下大腦的自發(fā)波動在腦網絡中是有序和連貫的。評估神經的相互作用可分為統(tǒng)計相關性的量化方法[功能連接(function connectivity,FC)]和解釋因果模型中相關性的方法[有效連接(effective connectivity,EC)][2]。在fMRI 研究中,FC 最常用典型相關系數來量化,表示兩個腦區(qū)或體素之間血流動力學波動幅度的相似性。其次,獨立成分分析可以實現全腦幅度相似性分析,從而區(qū)分獨立空間成分,這些空間成分對應不同的功能網絡,即“靜息狀態(tài)網絡”。EC假設大腦區(qū)域之間的信息流有限,再將FC 的實驗方法嵌入到不同的交互模型中,再根據其統(tǒng)計結果進行比較。EC 的優(yōu)勢為多變量性,即考慮了腦第三區(qū)域發(fā)生的間接神經相互作用。此外,還可評估兩個區(qū)域之間的正反向連接,提供了每個方向的信息流強度。FC和EC的分析結果是多維的,圖論為常用的降維分析方法。
主要應用:(1)評估運動功能。在人類和動物中風模型中,運動區(qū)域之間大腦半球間連接的減少直接關系到中風后皮質脊髓束的完整性[43-44]。在運動恢復過程中,未受損的大腦半球對受損半球的抑制作用會減弱,重新平衡這種不平衡是改善患者預后的一種方法。此外,還可預測急性中風后的功能預后,顳下回前部和左額上回之間跨半球連通性降低以及左半球尾狀核和顳下回前部之間的連通性降低對急性中風后運動功能的影響最大[45]。(2)評估其他功能障礙。右半球(導致空間忽視的主導神經系統(tǒng))受損后,左右頂葉區(qū)域激活不平衡,頂葉皮質的半球間功能連接減少。此外,結構正常的左頂葉和右后頂葉區(qū)域之間的功能連接中斷與中風后的空間忽視程度相關[46]。總之,各種運動和非運動網絡(如執(zhí)行控制、感覺運動、視覺空間和語言網絡)的完整性與中風結局有關[41,47-48]。此外,在評估中風后抑郁等神經心理學的改變也有廣泛應用[44]。
總之,BOLD-fMRI 可以提供卒中不同時期的血管反應、神經元活性和代謝相關測量結果,以及功能網絡情況。但信號受病灶周圍血管病理改變或血流動力學變化的影響,比如中風導致失語的患者與原發(fā)進行性失語患者相比,血流動力學反應延遲[49]。且其參數解釋受很多因素影響,故將BOLD-fMRI 數據與其他更具體的細胞測量方法結合可能會提供獨特的見解,比如將體內谷氨酸和氧代謝的結果與直接評估血管狀態(tài)的BOLD-fMRI 相結合,為了解缺血性卒中進展過程中決定BOLD 對比變化的因素提供重要依據[42]。除去對血流動力學波動進行評估,在自發(fā)的固有電振蕩水平上工作的腦電圖和腦磁圖更直接地與神經元活動相關(犧牲解剖學的精確性)。此外,非侵入性腦刺激在中風領域也備受關注[14]。
綜上所述,神經影像學為非侵入性深入了解缺血性卒中患者功能恢復和腦網絡重組的神經機制鋪平了道路,且基于MRI的技術具有極好的空間分辨率,這使得有機會從皮層重組的概念基礎轉向對潛在過程的解剖學或神經生物學解釋,對卒中患者的分層十分有助。未來這些方面的進步將為卒中康復提供更深入的見解,從而增強康復機率。
作者利益沖突聲明:全體作者均聲明無利益沖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