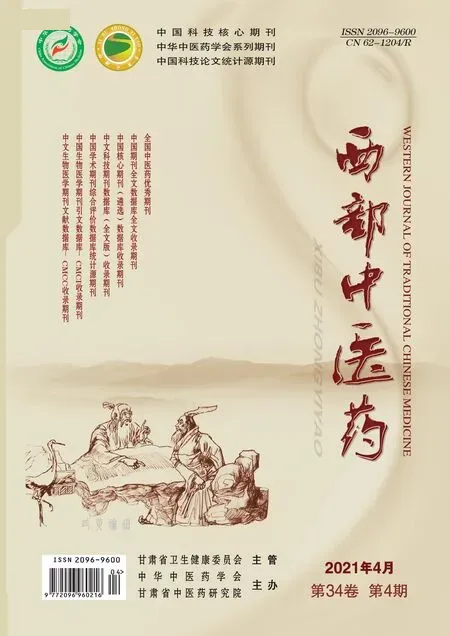《救荒本草》的歷史成就及海外傳播考略*
范延妮
山東中醫藥大學外國語學院,山東 濟南 250355
明代是我國古代植物學發展的重要時期,朱橚所撰的《救荒本草》就是這個時期的重要代表作之一,也是我國歷史上第一部以救荒為宗旨的植物學著作[1]。《救荒本草》共載有植物 414 種,書中詳細記錄了植物的食用部位、加工方法和食用方法,對我國明清時期農學、植物學和醫藥學的發展都產生了重要影響。它因內容翔實、特色鮮明而在我國植物學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國際植物學史上也具有深遠的影響。
1 《救荒本草》的歷史成就
《救荒本草》成書于明永樂四年(公元1406年),由明代朱元璋第五子朱橚撰,是15 世紀中國古代植物學代表著作。書中載有可供食用的植物414 種,其中源于舊本草者138 種,新增植物276種,每種植物均配精美插圖,文圖對照。《救荒本草》是我國歷史上最早的一部以救荒為宗旨的農學、植物學專著,它用簡明的文字和細致的繪圖,記錄了我國明代中原地區可食用的植物資源,總結了植物資源的利用、加工、炮制等方面內容,對我國植物學、農學、醫藥學等的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
2 朱橚其人
《救荒本草》的作者朱橚(公元1361—1425年),是明太祖朱元璋的第五個兒子,明成祖朱棣之弟。洪武十一年(公元1378 年),朱橚被封為周王,死后謚“定”。朱橚因受封或流放曾到過鳳陽、云南、開封、南京等地,親歷自然災害較多,深感于民間災荒及百姓缺醫少藥的疾苦,組織開展了多部醫藥書籍的編撰,為明代醫藥事業的發展和傳播作出了貢獻[2]。除《救荒本草》外,朱橚還撰有《普濟方》《保生余錄》《袖珍方》等醫學著作,《救荒本草》的歷史成就主要體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2.1 國內領先的植物學著作作為中國第一部專門記載可食用植物的植物學著作,《救荒本草》使中國古代植物學脫離了本草研究的束縛,以單純植物志的形式出現,開始了純粹的植物學研究。直到清代吳其濬著《植物名實圖考》的四百年間,中國古代植物學著作一直沿用《救荒本草》的體例,影響深遠[3]。
2.2 完整的植物描述體例《救荒本草》建立了一套比較完整的植物描述體例,與今天《中國植物志》的描述體例十分接近,包括學名、習性、根、莖、葉、花、果實、種子、物候、產地、生境和用途,其完整性超過了歷史上任何一部與植物相關的著作,是對歷代植物描述體例的一次大的提升[4]。此外,該書采用了類比方法來描述植物,如描述鼠菊“葉似菊花葉,微小而肥厚;又似野艾蒿葉而脆,色淡綠”,這種通俗易懂的描述方法,便于普通百姓掌握植物特征進行辨認。
2.3 精美的植物繪圖《救荒本草》載有414 幅植物繪圖,憑借這些繪圖,現代植物分類學家可以較為準確地鑒定大部分植物的類屬,其中一些繪圖和現代的植物科學繪圖相比也毫不遜色,包括花序、穗、花葶、枝杈等信息,如果沒有對真實植物進行仔細的形態學觀察,是很難描繪出這些特征的。事實上,當初繪制這些植物的初衷非常簡單,正如公元1525 年李濂在《救荒本草》第二版序言中所說,五方的土壤和氣候都不相同,因而各地的植物形狀和性質也大不相同。名稱繁多復雜,區別真假也很困難。如果沒有圖解和說明,人們會混淆蛇床和蘼蕪、薺苨和人參,這種錯誤足以置人于死地。這就是《救荒本草》用圖說明植物的形狀和記載其使用方法的原因。歐洲第一批自然意義的、清楚可鑒的植物繪圖是出現在公元1485 年德國的《植物品匯》,比《救荒本草》晚了79年[5],而且當時的繪圖還比較粗糙,只描繪了植物輪廓、葉子和花的粗略特征,這也是西方植物學家高度評價《救荒本草》繪圖的原因。
2.4 救荒植物研究的先驅《救荒本草》的普世價值使它廣受后世學者重視,特別是對于有毒植物,它詳細記載了加工方法和食用方法,深懷關愛民生之心。《救荒本草》引導了一場歷史上對救荒植物研究的浪潮,此后涌現出的一系列救荒植物專著,如王磐的《野菜譜》(公元1524 年)、周履靖的《茹草編》(公元1582 年)、屠本峻的《野菜箋》(約公元1600 年)、鮑山的《野菜博錄》(公元1622年)、姚可成的《救荒野譜》及顧景星的《野菜贊》等著作都受到《救荒本草》的影響。徐光啟的《農政全書》(公元1639 年)中的“荒政”部分,幾乎照搬了《救荒本草》的內容。明代本草學家李時珍、清代植物學家吳其溶的著作也都受到《救荒本草》的影響。可以說,《救荒本草》開創了中國古代經濟植物研究的新領域。英國李約瑟博士在其主編的《中國科學技術史》首卷中指出,《救荒本草》在當時的科學研究領域居世界前列[6],世界上其他國家對救荒可食植物的研究約在19世紀才起步。
《救荒本草》雖然代表了當時中國植物學的較高水平,但由于時代的局限性,朱橚僅客觀地記錄了植物觀察的結果,并沒有進行系統的理論總結和數字分析,此外還存在一些其他問題[7],例如理論概括性不足,部分本草與其他植物混淆,神仙方術思想沒有刪除等,但這些并不影響它在中國古代植物學史上的重要地位。《救荒本草》豐富和發展了我國古代植物學,在世界植物學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它相繼傳播到日本、美國、英國等歐美國家,因其救荒濟世的實用價值和植物學研究成就,得到國外植物學家和科學史家的認可和贊賞。
3 《救荒本草》在日本
17 世紀末,《救荒本草》東傳日本。當時日本在德川幕府統治下,經常發生自然災害,人民生活非常艱苦。《救荒本草》介紹的野生食用植物可以幫助百姓緩解糧食短缺問題,符合國情需要,所以很快引起日本學者的關注。公元1716 年,日本本草學家松崗恕庵(公元1668—1746)從《農政全書》中摘錄出《救荒本草》的內容,對所載植物進行了日名考證,刻成日本《救荒本草》第一個版本,書名是《周憲王救荒本草》。全書根據《農政全書》的編排,共十四卷,目錄一卷。隨后松崗恕庵的學生、本草學家小野蘭山(公元1729—1810)根據《救荒本草》嘉靖四年(公元1525 年)刻本對松崗恕庵本進行修正補遺,補充了果部,在公元1799年刊行了日本《救荒本草》第二個版本,書名為《救荒本草補遺》。同時他還以《救荒本草》為教材在日本傳授本草學知識,使該書在日本廣為人知。公元1842 年,小野蘭山的孫子小野惠畝(公元1774—1852)對《救荒本草》進行了注釋和解說,刊行了《救荒本草啟蒙》,該書文字簡明平易,主要目的是向日本人講解《救荒本草》,很適合日本讀者閱讀[8]。這三位日本學者為《救荒本草》在日本的傳播做出了積極貢獻。
隨著《救荒本草》在日本的傳播,日本植物學家和博物學界對它的研究興趣日增,成果顯著。據日本本草研究的權威人士岡西的統計,當時研究《救荒本草》的文獻達十五種之多,較為著名的當屬巖奇常正[9],他在自己多年研究的基礎上,于公元1816 年編撰了《救荒本草通解》,并效仿《救荒本草》作者朱橚的植物研究方法,在野外考察、收集、栽種野生植物二千余種,然后觀察、描述、繪制出植物的彩色圖譜,于公元1816 年撰寫成當時日本的植物學巨著《本草圖譜》。
日本近代植物學的奠基人牧野富太郎指出,日本第一部介紹近代植物學的譯著《植學啟原》中的一些果實分類術語,如“蓇葖、蕨”等就是源自《救荒本草》。日本植物學家上野益三指出:“《救荒本草》對植物產地、特征、記載簡潔,繪圖精確,有《本草綱目》等書所無的內容,這無疑對本草學的博物學化有很大的影響”[10]。在《救荒本草》的影響下,日本當時出現了類似的著作,包括《救荒略》《救荒植物數十種》《備荒草木圖》《荒年食糧志》《備荒圖譜》等。由此可見,《救荒本草》對于日本的植物學研究和博物學研究都發揮了極大的促進作用。
4 《救荒本草》在歐美
19 世紀以來,西方學者對《救荒本草》產生了濃厚興趣,開始對書中所載植物進行分析和整理。1881 年德國植物學家布賴特施耐德(E.Bret Schneider)在倫教出版《中國植物志》一書,對《救荒本草》中的176 種植物的學名進行了考證鑒定,認為書中優秀的木刻圖比歐洲要早70年[11]。
20 世紀美國著名的科學史家薩頓(George Sarton)在《科學史導論》一書中認為朱橚是個有成就的植物學家,他的著作不但是中國而且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研究野生食用植物的著作。因為朱橚自建園圃,親自種植、觀察400 多種植物,記錄植物生長、發育和成熟的全過程,并以畫工作圖,為書中圖文的準確性奠定了基礎,這在當時是很先進的植物學研究方法。薩頓在談到中世紀的植物園時說:“杰出的成就產生在中國,朱橚不僅設立了植物園,而且還有植物的實驗室……他的植物園是中世紀的杰出成就,他的《救荒本草》可能是中世紀最卓越的本草書”[10]。當時歐洲還沒有這樣的植物園,薩頓認為朱橚開創了實驗生物園的先河。對于《救荒本草》的插圖,薩頓評價說:“了解中國藝術家優秀的傳統,就不難理解《救荒本草》插圖的極端精美”[9]。
美國植物學家里德(A.S.Lead)在《植物學簡史》中對《救荒本草》作了高度評價,說它是“中國早期一部出類拔萃的植物學著作”[12],并指出這部著作在東方非常重要,它構成了野生植物利用馴化的重要源泉,是中國早期一本有價值的專著,由于其繪圖的優秀堪稱一部杰出的著作,遠勝當時的歐洲。
20 世紀30 年代,英國植物學家斯溫格爾指出,《救荒本草》在當時是研究救荒食用植物最好的書[13],他這樣說道:“已知最早并仍然是今天最好的這類著作,是由一位王子為努力減輕中國由于饑荒頻繁造成痛苦與死亡而經多年艱苦的研究之后寫下的……在很大程度上,中國人對食物和藥用植物沒有嚴格的區別;實際上,幾乎所有的食用植物同時也作為家用藥物,或是被醫生用于預防、治療、減輕疾病的處方之中”[5]。由此看出,斯溫格爾已經認識到中國藥食同源的傳統,并對《救荒本草》推崇備至。
到了20世紀40年代,英國藥物學家伊博恩開始對《救荒本草》展開研究,成為近代西方學者中研究《救荒本草》成就最高者[14]。伊博恩自1909年來華,先后就職于北平協和醫學院和上海雷士德研究院,一直從事藥物研究工作,以研究中國植物和藥品貢獻尤多。伊博恩深感《救荒本草》對于當時飽受戰亂和饑荒之苦的百姓意義重大,利用這些野生植物不僅可以充分發掘未開發的自然植物資源,更可以緩解因口岸封鎖、交通斷絕而帶來的食物不足,由此對《救荒本草》開展了全面研究。1946 年,伊博恩在上海以英文出版了《〈救荒本草〉所列的饑荒食物》一書,他以列表的形式對其中的358 種植物進行了研究。他標出了每種植物的漢語名字、拉丁學名、英文名字、化學成分以及在其他國家的食用情況,并用藥理分析方法對部分植物的化學成分做了測定,分析它們的營養價值,如他在該書的前言中指出葉子和根部所含的不同營養成分和熱量:“在葉子提供保護性元素、維生素、鹽的優良來源的同時,更重要的項目是根類、子類和豆類。關于根類,我們了解的熱值如下:每百克百合產生熱量140卡,麥門冬340卡,地栗159卡,山藥89卡……”[15]。
對于《救荒本草》的社會價值,伊博恩也有充分的認識,他在前言中說:“當人們面臨著由于饑餓而造成死亡的時刻,他們自然而然地轉向食用那些可以維持生命的東西,以樹皮野根野草來迎合他們的需要……所以,除了像周定王這樣的人編寫關于從野生植物中可得巨大資源的卓越著作外,我們極其需要他的精心之作,以指出如何把這些食品放在一起作出吸引人的飯食。這種飯食作為代食品,能夠吸取充足的熱量、維生素、鹽類以保護人們由于飲食的不平衡而造成的營養不良疾病。”在書的第一部分伊博恩還引用了原著的雁來紅、馬齒覓等十余幅插圖。伊博恩的編譯研究工作使《救荒本草》為西方更多學者所熟知,極大促進了該書的對外傳播進程。
英國的中國科技史專家李約瑟認為[5],朱橚的《救荒本草》在人道主義方面有很大的貢獻,他既是一個偉大的開拓者,又是一個偉大的人道主義者。對于朱橚設立的植物園,李約瑟給予高度評價,他指出這個植物園也是對可作食用的植物進行水土適應和研究的實驗場所,并猜測它肯定包含能進行生化和醫藥試驗與制備的實驗室。
5 結語
《救荒本草》對野生可食用植物的救荒作用以及本草療效進行了分析和研究,它因其通俗、實用和科學的特點在中國農學史和植物學史上占有重要地位。17 世紀以后《救荒本草》相繼傳到日本和歐美國家,不僅對緩解世界范圍內的饑荒發揮了重要作用,而且因其植物學上的成就贏得了國際學術界的重視和贊譽,值得更多學者對其展開更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