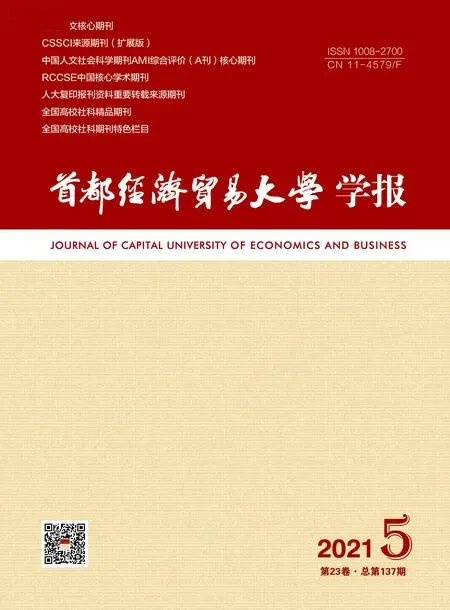對外開放概念的內涵及其客觀必然性的再探索
汪海波
(中國社會科學院,北京 100732)
一、對外開放概念的內涵分析
馬克思主義從來認為,人類社會的生產(1)這里說的“生產”是再生產過程中的“生產”,包括生產、交換(或流通)、分配和消費四方面,而不只是其中的“生產”。過程包括兩方面的內容:一是生產力,二是生產關系。
馬克思正是依據歷史唯物主義的這個基本原理,揭示了資本主義社會中商品交換這種物與物之間的交換關系形式的背后實質是人之人之間的生產關系。這包括作為市場主體的資產者之間的商品交換關系,以及作為市場主體的無產者的勞動力商品與資產者的作為商品價值一般價值形態的貨幣之間的交換關系。在資本主義自由競爭的條件下,前者是資產者作為依據價值規律要求的等價交換原則進行商品交換的平等的商品生產者之間的關系。后者在形式上也是依據這個原則產生的交換關系,但在實質上是資產者對無產者的剝削關系。問題在于,即使在自由競爭條件下,無產者獲得的也只是作為勞動力價值表現形態的工資,而無產者的勞動創造的價值大于勞動力價值。勞動者創造的剩余價值就被資產者無償地占有了。這樣,馬克思就揭示了資本主義社會中看來似乎平等的商品關系,實質卻是資產者對無產者的剝削關系。
資產階級學者在資本主義發展的各個階段,都對經濟科學的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這一點在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時代和當前經濟全球化獲得空前未有發展的時代,表現得尤為突出。但一般說來,資產階級學者出于階級本能的需要,總是有意無意地把資本主義經濟條件下的商品交換(包括無產者勞動力商品與資產者貨幣資本的交換)說成物與物的交換關系。這就掩蓋了資本主義的剝削關系。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把這種謬論稱之為“商品拜物教”“貨幣拜物教”和“資本拜物教”,深刻地揭示了其實質。
這里需要著重指出,從一般意義上說,馬克思指出的上述原理,對當代的對外開放研究也是完全適用的。就是說,在當代開放領域中,既有產品(包括服務)和生產要素(包括資金、技術、數字和勞動力等)在國家之間的流動,同時也存在雙方之間生產關系的交換。問題在于:對外開放不過是社會再生產過程(特別是其中的流通過程)在對外開放領域的延伸。這樣,對外開放領域就不只是產品和生產要素的流動,而不存在生產關系的交換。
但當前學者在論到當代中國對外開放時,注意力都是集中在前一方面,后一方面似乎并未進入他們的視線。從思想方法的根源來說,這種現象就是馬克思詳細批判過的“商品拜物教”在當前對外開放理論研究中的反映。
這種狀況,對判明各國對外開放的社會經濟性質(特別是中國對外開放的社會經濟性質),以及判斷當前對外開放的形勢及其發展趨勢,都是不利的。
還需要進一步指出,在對外開放領域中,不僅存在物與物之間的商品交換關系,也不僅存在交換雙方的生產關系,還存在作為基本經濟制度的生產關系的表現形式的經濟體制關系。
原來在歷史唯物主義理論中,最基本的有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以及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相互作用的理論,后來增加了一個經濟體制與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以及經濟體制與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相互關系的理論。在這方面,經濟體制的產生、發展和消失,都決定于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但又反作用于生產力,既可以成為生產力發展的巨大動力,又可以是發展生產力的桎梏。經濟體制既是基本經濟制度(生產關系或經濟基礎)的表現形式,但也反作用于基本經濟制度,既可以維護它,又可以導致它的滅亡。經濟體制既可以受到作為上層建筑的政府的維護,但也反作用于政府。在適應生產力發展要求而進行改革的情況下,經濟體制改革需要依靠政府來推動,反過來也鞏固政府。在違反生產力的要求而不進行改革的情況下,也能導致政府的滅亡。
基本經濟制度與經濟體制之間存在一些重要差別。一是前者能夠容納社會生產力的高度比后者要高得多。二是前者的延續時間比后者也要長得多。三是前者的根本變革在階級社會里一般都要經過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革命,而后者的根本變革是在政府維護基本經濟制度的前提下實現自我完善。
需要著重指出,經濟體制的上述作用,已經被古代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和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歷史所證明。
先以中國封建社會的發展而論,中國封建領主制度到封建地主制度的轉變,就可以從一個方面說明下列兩種歷史現象。第一,依據歷史資料,中國領主經濟從產生到消滅,大約只經歷了不到六百年的時間;而地主經濟從建立到滅亡,卻經歷了近兩千四百年的時間。后者經歷的時間約為前者的四倍。還要看到:盡管整個說來,封建社會生產力發展的重要特征是生產技術停滯,但地主經濟時代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比領主時代還是快得多。所以,這個歷史現象證明:地主經濟能夠容納的社會生產力的高度比領主經濟要高得多。第二,歐洲的封建莊園制度(類似中國的領主經濟制度)只綿延了一千年,而中國的封建經濟制度卻延續了將近三千年。決定這個差異的,當然有多方面的因素,但地主經濟比莊園經濟能夠容納更高的社會生產力,是一個基本因素。應當指出:中國許多史學論著在分析中國封建社會延續時間長的原因時,幾乎還未注意到這一點。因而這個問題似乎并未得到充分的說明。在這種情況下,提到這一點是特別重要的。
再以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而論。現在看來,無論是馬克思,還是列寧,他們揭示的資本主義制度和帝國主義制度滅亡規律都是正確的。但他們對資本主義社會存在的時間都估計短了,對它的滅亡時間估計早了。形成這一點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從理論上說,一個重要方面就是他們沒有看到(也不可能看到)現代的市場經濟體制所能容納的生產力的高度遠遠超過了古典的市場經濟體制。從根本上說來,這主要是由于馬克思和列寧所處的時代的限制。在他們所處的那個時代,不可能看到現代市場經濟體制在發展社會生產力方面的巨大作用。這種解釋既符合馬克思主義認識論,也符合歷史唯物論。馬克思對他創立的歷史唯物論作經典表述時明確說過:“無論哪一個社會形態,在它們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以前,是決不會滅亡的。”[1]所以,因為馬克思和列寧對資本主義存在時間和滅亡時間估計有誤差,就懷疑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正確性,是完全沒有根據的。
最后,以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而論。蘇聯在1991年解體,而中國在1978年以后經濟得到了飛速發展,社會主義制度得到了進一步鞏固。形成這種反差的原因,涉及諸多方面。蘇聯長期停留在計劃經濟體制,致使社會生產力發展很慢;而中國在1978年以后逐步走上了市場取向改革的道路,從而極大地推動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從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看,這無疑是一個根本的原因。
如果脫離了經濟體制在發展社會生產力方面的作用,中國封建社會的發展、現代資本主義的發展以及社會主義社會的曲折發展,都難以得到充分說明[2]。
那種把對外開放僅僅歸結為商品和生產要素在國家之間流動的觀點,其片面性不僅在它忽略了這種流動中存在的作為基本經濟制度的生產關系,而且在于它忽略了作為基本經濟制度表現形式的經濟體制的關系。
二、對外開放概念的內涵拓展
筆者認為,對外開放概念的內涵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實體型的對外開放,即產品(包括服務)和生產要素(包括資金、物資、人力資本、科技、信息、數字和產權等)以及作為消費者的旅游人員在國家之間的流動;二是制度型的對外開放,即體制的輸入和體制的輸出。
中國的經濟改革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是在堅持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前提下進行的。所以,這是說的制度型輸入,顯然不是指照搬國外的作為基本經濟制度的資本主義制度,而是依據中國改革發展進程的需要,逐步借鑒和吸納適合中國具體情況的作為經濟體制的市場經濟的某些方面。在這方面最突出的表現,就是改革初期創辦經濟特區。伴隨改革的發展,特區的范圍的擴大,也是屬于這種情況。
這里說的制度型輸出也不是指把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強行加在外國頭上,而是指依據平等合作、互利共贏的原則,通過共商共建共享,積極參與國際治理體系變革,逐步改革不合理的國際經濟政治秩序,建立合理的國際經濟政治秩序,最終實現人類命運共同體。當然,最終實現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一個數以百年甚至千年計的長期歷史過程。
在這里還需要說明兩點,第一,將中國對外開放區分為實體型對外開放和制度型對外開放,是從理論上說的。而在對外開放的實踐中,二者常常是結合在一起的。其突出例證有二:一是以創辦經濟特區為代表的國內地區開放。這顯然是制度型輸入,但伴有吸引外資這種實體型輸入。二是參與國際經濟合作。這顯然是制度型輸出,但伴有對外貿易這種實體型的輸出。兩種情況既包含實體型的對外開放,也包含制度型的對外開放。前者的主要特征是制度型輸入,后者的主要特征是實體型輸出。所以,在理論上將對外開放區分為實體型對外開放和制度型對外開放,是能夠成立的。第二,上述關于對外開放內涵的敘述,是依據當代對外開放實踐提出的。對外開放正在蓬勃發展,隨著對外開放實踐的發展,還會形成新的對外開放類型。
在系統分析對外開放科學內涵的基礎上,還需要對另一種觀點提出商榷意見。這種觀點認為對外援助也是中國對外開放的內容。
首先應當肯定,對外援助具有重大的政治意義。實際上,新中國成立后,就邁出并不斷加大了對外援助步伐。改革以來,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在這方面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據國務院新聞辦公室2016年發表的《發展權:中國的理念、實踐與貢獻》白皮書,60多年來,中國共向166個國家和國際組織提供了近4 000億元人民幣的援助,為發展中國家培訓各類人員1 200多萬人次,派遣60多萬援助人員[3]。另據商務部統計,2017年,中國政府承擔各類援助項目309個,境內外培訓各類人才近15萬名,惠及128個國家和地區及國際組織。其中,圍繞“一帶一路”建設,中國援建了農業、工業、交通運輸、能源電力、信息通信等領域的近60個重大基礎設施項目[4]。
特別是在世界性新冠肺炎疫情中,中國盡管也受到了疫情的嚴重傷害,但還是在力所能及的情況下向多個國家(主要是發展中國家)派出了醫療專家組和提供了防疫抗疫的物資。中國不僅在短時間內打贏了湖北和武漢抗疫人民戰爭阻擊戰,取得決定性勝利,為國際社會提供了寶貴經驗,還提供醫療人員和物資援助,被國際社會普遍譽為抗疫的典范。這是構建世界健康衛生命運共同體的一個重要步驟,是習近平總書記倡導的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偉大構想的一個重要方面。
但同時需要指出:對外援助和對外開放是有原則區別的兩種范疇。一般說來,前者是人類社會共同的價值追求(就中國來說,是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本質體現),遵循的是無償原則,是社會道義的范疇;而后者是在國家之間發展商品經濟的要求,遵循的是平等競爭和等價交換原則,是商品經濟的范疇。
三、世界各國對外開放的歷史過程
顯然,實行對外開放不僅取決于國內的條件和需要,而且取決于國外的條件和需要。因此,要論證對外開放的客觀必然性,就需要從國際和國內兩個方面入手。但當前學界僅著眼于國內這一方面,而忽視國際方面。為此,筆者在論證中國對外開放的客觀必然性時,先從國外方面論證這種客觀必然性,然后從國內方面論證這種客觀必然性。
在這方面,為了澄清當前學界廣為流行的對外開放古已有之的這種不完全符合對外開放歷史的觀點,還需要簡要地首先敘述世界各國對外開放的歷史,然后從當代世界對外開放的大潮中論證對外開放的客觀必然性。
馬克思主義創始人在十九世紀下半期依據當時的實際情況,曾經精辟地揭示了世界貿易中心的變化過程。他們指出:“世界貿易中心在古代是開羅、腓尼基和亞歷山大,在中世紀是熱那亞和威尼斯,在現代,……是倫敦和利物浦,而目前的世界貿易中心已是紐約和舊金山……”,與此相聯系,“世界交通樞紐在中世紀是意大利,在現代是英國,而目前已是北美半島南半部。”[5]
這個論述表明:
第一,在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就已經開始了世界貿易,因而才出現貿易中心。這也意味著在這兩個社會就已經出現了對外開放。
但這兩個社會的對外貿易只是局部性的世界貿易,對外開放也是局部性的對外開放。這主要是由當時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水平和生產關系的特點決定的。盡管封建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水平比奴隸社會要高得多,但僅以手工工具作為技術基礎的生產來說,二者基本上是相同的。因而這兩個社會的勞動生產率都不高,剩余產品也就不多。這樣,社會生產除了滿足奴隸主和封建主的生活需要以外,就沒有多少產品用于商品交換。而且,在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條件下,其生產目的主要也就是為了滿足奴隸主和封建主的生活需要。這樣,國內貿易不發展,國際貿易就更是如此。以手工工具為技術基礎的交通工具不僅限制了國內貿易的發展,更限制了國際貿易的發展。還需要指出:在那個時代,作為世界重要組成的美洲新大陸還沒有發現。這一切使得那個時代的對外貿易和對外開放,只能是局部性的世界貿易和對外開放。
第二,到了資本主義時代,對外貿易和對外開放開始發展成為世界性的對外貿易和對外開放。
對于世界市場形成的條件,馬克思和列寧多次做過詳細的論述。其中,最基本的論述主要有以下幾點:
“資本主義生產建立在價值上,……這一點只有在對外貿易和世界市場的基礎上才有可能。”[6]
“競爭迫使資本家不斷擴大生產并為自己尋找大量推銷產品的國外市場。”[7]
“彼此互為‘市場’的各個工業部門,不是均衡地發展著,而是互相超越著,因此較為發達的工業就尋求國外市場。”[7]
“大工業建立了由美洲的發現所準備好的世界市場。”[8]
“美洲和環繞非洲的航路的發現,給新興的資產階級開辟了新的活動場所。”[8]
“因此,對外貿易和世界市場既是資本主義生產的前提,又是它的結果。”[8]
作為世界對外開放起點和最基本內容的對外貿易,其形成條件是:
第一,旨在追求剩余價值的資本主義生產,并不滿足于國內市場,還必須開辟世界市場。只有這樣,其目的才能得到充分的滿足;否則是不可能的。在這方面,作為剝削者的資本家和封建主是有區別的。后者的生產目的是為了獲取滿足生活需要的使用價值,其追求的數量是有限的。而前者的生產目的是剩余價值,其追求的數量是無限的。為此,資本家并不滿足于發展國內市場,而是要在發展國內市場的同時,不斷地開拓國外市場。資本家之間的激烈競爭還使得這一點成為不可抗拒的強大的外在壓力,迫使資本家瘋狂地開拓國外市場。資本主義生產的盲目性必然導致各個生產部門不平衡的發展。這一點不僅加劇了資本爭奪國內市場的競爭,而且成為資本爭奪世界市場的另一個強有力的動力。當然,資本主義條件下各個生產部門發展的不均衡性,不只是由于資本主義制度固有的盲目性引起的,同各個生產部門形成和發展的條件差異也是有聯系的。
第二,以機械化生產作為技術基礎的大工業,為資本主義開拓世界市場提供了強有力的物質基礎;否則,世界市場的形成也不可能。
第三,美洲新大陸和環繞非洲的航路的發現,是形成完全意義上的世界市場的重要條件。顯然,沒有這兩個條件,也不可能有完整的世界市場。
上述三點表明:當前學界流行的對外開放自古有之的觀點是值得斟酌的。且不說上述的三個條件,只提其中的一點就可看得很清楚。在資本主義社會以前的古代社會,美洲新大陸還沒發現,何來世界市場之有?誠然,如前所述,在古代社會也確實存在過國與國之間的小規模、小范圍的商品交換。但它只是局部性的世界市場,而不是全局性的世界市場。而中國改革以后提出的對外開放正是全局性的世界市場和對外開放。這樣的世界市場和對外開放,在古代社會是不可能有的。這種流行的觀點,是混淆了古代的局部性的世界市場和對外開放與當代全局性的世界市場和對外開放。
需要進一步說明的是,由十八世紀下半期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時代開始的全局性的世界市場和對外開放,也只是它發展的第一個階段。
其第二個發展階段是:到了十九世紀末,資本主義的發展進入了壟斷資本主義時代。在這個時代,資本輸出上升到主要地位,取代了自由競爭資本主義時代商品輸出的主要地位。資本輸出又成為最有力的經濟杠桿,迫使落后國家淪為殖民地。帝國主義國家憑借其在殖民地的統治地位肆無忌憚地榨取壟斷利潤。這就驅使帝國主義國家在全世界到處掠奪殖民地。這樣,在這個時代,全世界的落后國家幾乎全部淪為殖民地,世界殖民體系也就最終形成了。這同時意味著這個時代全局性的世界市場和對外開放,又發展到第二個階段。
其第三個發展階段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取得勝利的偉大意義,不僅在于它使得世界殖民主義體系趨于瓦解,而且在于它促使歐洲和亞洲誕生了眾多的社會主義國家(其中包括世界人口最多的新中國)。在這種形勢下形成了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大陣營的對立,同時形成了以蘇聯為首的華沙條約軍事集團與以美國為首的北大西洋公約軍事集團的對立。于是就開啟了兩大軍事集團的冷戰局面。與此相聯系,蘇聯共產黨主要領導人又提出了社會主義市場與資本主義市場兩個平行市場的理論。這個理論對眾多的社會主義國家發生了重要影響。于是統一的世界市場就在很大程度上被分割為兩個平行市場。這樣,二戰以前全局性的世界市場發展受到了嚴重挫折。
但在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初,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相繼解體,兩大陣營對立的冷戰局面也隨之結束。全局性的世界市場又逐步得到了恢復。而且伴隨知識經濟的到來和經濟全球化的發展,世界市場無論在規模上還是在深度上都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這意味著全局性的世界市場又發展到第三個階段。
鑒于這個問題的重要性,這里做較為詳細的分析。
人類社會發展階段的劃分,從根本上說來,還是依據馬克思主義關于社會生產關系和生產力的理論。這里僅從生產要素在社會生產中的主導作用的視角,將人類社會生產區分為以下三個階段:一是除了原始社會,在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都是以手工工具為主的農業時代。二是在資本主義社會存在的長時期內,都是以機械化生產作為物質基礎的工業時代。三是從二十世紀下半期起,由信息和數字等因素構成的知識經濟逐步在社會生產中上升到主要地位。據有關資料,在二十世紀中葉知識經濟對經濟發達國家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還只有50%,但到二十世紀末就上升到60%至80%。這意味著人類社會已經步入了知識經濟時代。
知識經濟以其固有的優越性,從信息和物流等方面強有力地促進了經濟全球化,使得經濟全球化獲得了前所未有的大發展。
經濟全球化可以從多個視角去定義。一般認為,全球化包括自由市場、投資流動、貿易和信息的一體化。但從本質上說,經濟全球化似乎可以定義為貨物、服務、生產要素更加自由地跨國界流動,各國經濟更加相互依存的一體化過程。
這個過程突出表現在對外貿易和對外投資兩方面。
在對外貿易方面,其主要表現是:
就對外貿易規模看,1950年世界貿易的出口額僅為610億美元,2000年增加到64 540億美元,2019年進一步上升到188 887億美元。按現價計算,2000年比1950年增長了104.8倍,2019年又比2000年增長了2.93倍。
就對外貿易系數(即進出口總額對國內生產總值的依存度)看,進出口額與國內生產總值的比值,在1980—1996年期間,高收入國家由38%上升到42%,中低收入國家由42%上升到53%,低收入國家由30%上升到42%。
就對外貿易內部結構看,在1980—1993年期間,貨物貿易比重下降,服務貿易比重上升。按現價計算,在1980—1993年期間,前者占比由83%下降到78%,后者占比由17%上升到22%;到2016年,前者占比進一步下降到75.3%,后者進一步上升到24.7%。
就對外貨物貿易內部結構看,初級產品在貨物出口貿易中的占比迅速下降,工業制成品的占比迅速上升。在工業制成品中,高附加值新興工業品(如信息化的工業產品)的占比迅速上升,而低附加值的傳統工業品(如紡織工業品和食品)的占比迅速下降。在1937年、1973年和1987年這三個時間段中,初級產品的占比由63%下降到38%,再下降到18%;而工業制成品的占比由37%上升到62%,再上升到82%。21世紀以來,仍然呈現相同的發展趨勢。
就對外服務貿易內部結構看,傳統的勞動力密集型服務業出口的占比下降,而新興的以金融、通信等為代表的資本密集型和知識密集型服務業的出口占比上升,從20世紀末到21世紀以來,一直是這種發展趨勢。
就對外貿易的類型看,則呈現出傳統的產業之間的貿易比重下降,產業內部的貿易比重上升。這一點在經濟發達國家之間的貨物貿易方面表現得尤為明顯。在20世紀90年代以前,經濟發達國家一般都是出口工業制成品,進口原材料。而在此后,在經濟發達國家之間的貿易中,產業內的貿易占比上升,高的達到80%以上。這意味著國際產業分工已經發生了由垂直分工向水平分工的轉變。
在對外投資方面,其主要表現是:
就對外直接投資的規模看,流入存量從1960年的680億美元,增加到1992年的19 480億美元,再增加到1997年的34 560億美元。在投資流量方面,在1970年、1989年和1997年這三個時間段,分別為400億美元、2 320億美元、4 000億美元。
就對外投資的國家分布看,第二次世界大戰前,資產是從帝國主義宗主國流入殖民地。而在戰后,特別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經濟發達國家之間的相互直接投資迅速增長。1996年,經濟發達國家之間的相互投資流出量達到2 950億美元,占到世界投資流出量總額的85%;流入量達到2 080億美元,占到世界流入量總額的66%。
就對外投資的地區分布看,第二次世界大戰后,主要在北美和歐洲。而20世紀90年代以來,主要集中在北美、歐洲以及東南亞。
就對外投資的產業流向看,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初期,對外投資主要集中在自然資源的開采上,20世紀60年代以來主要轉向制造業,80年代以來主要流向服務業,1996年其占比已經達到50%以上[9]。
上述數據表明,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經濟全球化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發展高度。與此相聯系,全局性的世界市場也發展到第三階段。
可見,對外開放古已有之的觀點,不僅在于它混淆了局部性的世界市場和對外開放與全局性的世界市場和對外開放,而且在于它忽略了全局性的世界市場和對外開放的三個發展階段的差別。中國1978年以后提出的對外開放,正是指的全局性世界市場和對外開放發展的第三個階段。
習近平總書記多次提出:“歷史地看,經濟全球化是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客觀要求和科技進步的必然結果,不是哪些人、哪些國家人為造出來的。”“全球市場已經形成一個整體,我國經濟和世界經濟深度融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世界經濟的大海,你要還是不要,都在那兒,是回避不了的。想人為切斷各國經濟的資金流、技術流、產品流、產業流、人員流,讓世界經濟的大國退回到一個一個孤立的小湖泊、小河流,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符合歷史潮流的。”“縱觀國際經貿發展史,深刻驗證了‘相同則共進,相閉則各退’的規律。”[10-11]
習近平總書記的這些科學論述,從國際視角,依據對世界經濟發展規律的揭示,論證了對外開放的客觀必然性。
四、中國由半封閉、封閉向全面開放轉變的歷史過程
這里再從國內方面論證中國對外開放的客觀必然性。
簡要概括地說,僅從封閉或者開放這個視角看,可將1949年新中國成立直到1978年底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做出對外開放決策區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包括新民主主義社會時期(1949—1952年)、從新民主主義社會到社會主義社會的過渡時期(1953—1957年)和計劃經濟體制強化時期的開始階段(1958—1959年)。第一個階段的特點是半開放、半封閉。但需著重指出的是:這期間之所以只能實行半開放,其原因并不在國內,而是在國外,即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國家對中國實行封鎖禁運政策。
就國內來說,黨的經濟綱領一直是主張在自力更生的前提下,積極實行對外開放的。
1948年3月,在新中國建立前夕召開了黨的七屆二中全會。毛澤東主席在這次全會上的報告中,提出了黨在新中國建立后經濟、政治和文化等方面的發展綱領。全會報告在提出徹底摧毀帝國主義對中國控制權和實行對外貿易統治的同時,還提出:“關于同外國人做生意,那是沒有問題的,有生意就得做,并且現在已經開始做,幾個資本主義國家的商人在互相競爭。我們必須盡可能地首先同社會主義國家和人民民主國家做生意,同時也要同資本主義國家做生意。”[12]
1949年9月,在毛澤東思想指導下制定的起臨時憲法作用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可在平等和互利的基礎上,與外國的政府和人民恢復并發展通商貿易關系。”[14]
1956年9月,中共中央副主席劉少奇在《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向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政治報告》中明確提出:“同一切愿意同我們建立外交關系和經濟文化關系的國家建立和發展正常的外交關系和經濟文化關系,這是我國在國際事務中的方針。”[14]
周恩來總理在這次大會上做了《關于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建議的報告》(1958—1962年),還著重批判了關起門來搞建設的錯誤思想。他說:“不用說,我們要建設起一個完整的工業體系,在長時期內還需要蘇聯和各人民民主國家的援助,同時也需要同其他國家發展和擴大經濟、技術、文化的交流。而且即使我們在將來建成了社會主義工業國之后,也不可能設想,我們就可以關起門來萬事不求人了。……因此,在建設社會主義事業中的孤立思想,也是錯誤的。”[14]
上述歷史文獻確鑿證明:從新中國建立之初直到20世紀50年代末,中國實行對外開放的方針是十分明確的。這期間之所以只能實行半開放,完全是由于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國家對中國實行封鎖禁運造成的。
即使是實行半開放,在發展對外貿易方面仍然取得了重要成就。1950—1959年,中國進出口總額由11.4億美元增長到43.8億美元,增長2.84倍,年均增速為12.3%[15]。
這期間在這方面的成就突出表現在同蘇聯和東歐人民民主國家發展對外經濟貿易方面。
就國民經濟恢復時期來說,這方面的成就主要表現如下:
開展對外貿易,主要是開展對蘇聯和東歐人民民主國家的貿易。(1)1950—1952年,進出口總額由11.3億美元增長到19.4億美元,1952年比1950年增長了71.68%,其中,進口總額由5.8億美元增長到11.2億美元,增長了93.1%,出口總額由5.5億美元增長到8.2億美元,增長了49.1%。(2)在這期間,進口的生產資料為24.56億美元,增長了1.06倍,占進口總額的比重由83.4%上升到89.4%,特別是進口設備等增長了3.75倍,占進口總額的比重由22.5%上升到55.7%。(3) 在這期間,出口的農副產品及其加工品為18.28億美元,增長了34.93%,出口的工礦產品為3.04億美元,增長了1.88倍,前者的比重由90.7%下降到67.2%,后者的比重由9.3% 上升到17.9%。(4)1950年美國等國對中國實行禁運以后,中國同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貿易額,無論是絕對量還是相對量都大幅度下降了,比重由1950年的74.06%下降到1952年的34.11%。在這期間,中國同蘇聯和東歐人民民主國家的貿易額比重由25.94%上升到65.89%[16]。
從蘇聯引進資金。依據1950年2月14日中蘇兩國簽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和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政府關于貸款給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協定》,從1950年1月1日起的5年內,蘇聯政府給予中國政府3億美元的貸款,按35美元等于一盎司純金計算,貸款年息為1%。貸款用以償付蘇聯提供的機器設備等。機器設備等的價格按世界市場的價格計算。中國政府將以原料、茶、美元等支付上述貸款和利息。原料和茶的價格也按世界市場價格計算。貸款將在1954 年12月31日—1963 年12月31日10年內歸還,每年還貸款總額的1/10。貸款利息按使用貸款實數并自使用之日起計算,每半年交付一次[17]。
需要著重指出,蘇聯的資金援助是在帝國主義封鎖禁運、中國資金供給異常困難的情況下提供的;貸款利息和還款期限等方面的條件都是很優惠的,特別是這項資金對中國社會主義工業化建設增添技術設備具有極為重要的作用。這筆貸款盡管在新中國成立初期基本建設投資方面占的比重不是很大,但其意義是很大的。蘇聯的3億美元貸款按1950年匯率折算成人民幣,約合9億元,相當于3年恢復時期政府基本建設投資總額62.99億元的14.3%[18]。中國將蘇聯貸款集中使用在能源、原材料、機械工業和國防工業等重點項目的建設上。
從蘇聯和東歐國家引進設計技術人員。這一點,對于新中國在成立初期進行工業基本建設具有重大意義。1950年至1952年初,蘇聯幫助設計的項目共42個,在42個項目中,東北30個,關內6個,新疆5個,內蒙古1個。在東北的30個項目中,電力、鋼鐵、煤炭、制鋁等項目占20個,其他10個項目是機械、化學、造紙等。關內6個項目是太原、重慶、西安、鄭州4個電站及太原肥料廠、染料廠,新疆5個項目是電廠和醫院。至1952年1月,已作出初步設計并已經批準的項目有15個。
與蘇聯和東歐國家合辦股份公司。1950年3月27日,中蘇兩國政府簽訂了創辦三個股份公司的協定:《關于在新疆創辦中蘇石油股份公司的協定》《關于在新疆創辦中蘇有色及稀有金屬股份公司的協定》和《關于建立中蘇民用航空股份公司的協定》。依照協定,1950年,中國與蘇聯在新疆創建了中蘇石油股份公司、中蘇有色及稀有金屬股份公司和中蘇民用航空公司。1951年,又與蘇聯合資創辦了中蘇輪船修理建造股份公司。
這些公司的資本一般為雙方各占一半。中國是以開采石油的地段,獨山子石油公司建筑物、設備以及未來所需要的建筑材料折算;蘇聯是以提供公司設備、器材和運輸工具折算。
這些公司實行的經營管理體制是:(1)中外雙方平股平權,雙方各擁有50%的股份,在企業經營管理和收益方面具有同等的權力。(2)經營管理機構采取管理委員會領導下的經理制,管委會委員由股東大會選舉產生,每屆任期3年,委員會由雙方派出相同數量人員組成。管委會主任和總經理由雙方輪流擔任,3年一換。管委會不能達成協議的問題,交由公司雙方股東審查,如雙方股東不能達成協議時,由締約雙方政府審定。(3)公司經營活動以雙方政府所簽訂規定的范圍為限。公司經營活動條件,包括納稅,與中國國營企業所享受的條件相同。公司的產品,根據世界價格,雙方有權各購買50%。一方如愿意出賣其所得產品時,應首先向另一方提出。蘇聯方面所購買的50%的產品,可免納關稅及捐稅運回國;如果蘇聯方面購買中國方面應得的50%的產品時,這部分產品應交納關稅。(4)雙方股東應將他們所得紅利的30%交予中國。
1950年,中蘇合辦的股份公司為38個,占企業總數(包括國營、公私合營和中蘇合營企業,總計為2 815個)的3.3%;職工人數為34 150人,占職工總人數(1 189 569人)的2.9%;工業產值為15 704億元,占工業總產值(459 729億元)的3.4%[19]。需要指出,這些公司雖然比重不大,但也起了重要作用。
總之,在國民經濟恢復時期,主要發展對蘇聯的經濟貿易關系,在擴展進出口商品、籌集資金、引進技術設備和技術人才以及管理經驗方面,為恢復經濟創造了重要條件。
在國民經濟恢復時期,政府還注意吸引海外華僑到國內投資。1951年經政務院批準,設立了華僑回國投資輔導委員會。這個時期,在這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1950年僑匯為1.18億美元,1951年為1.68億美元,1952年約為1.7億美元。僑匯主要用于僑眷的養家費,但也有一部分用于輕紡工業的投資[18]。
在“一五”時期仍然十分重視從蘇聯和東歐國家引進設備、技術、人才、資金和管理經驗,發展這方面的對外經濟關系。
“一五”期間,在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國家對中國實行經濟封鎖、物資禁運的條件下,中國主要從蘇聯和東歐人民民主國家引進成套設備、科學技術、人才、資金和管理經驗,這對建立社會主義工業化基礎起過特殊重要的作用。
引進成套設備。蘇聯援建的成套供應設備的項目經過多次商談最后確定為154項。因為公布156項項目計劃在先,所以仍稱“156 項工程”。如果再加上1958年和1959年中蘇商定的項目,在整個20世紀50年代,由蘇聯援建的成套供應設備的項目共計304項,單獨車間和裝置64項。但由于1960年蘇聯單方面撕毀合同,成套供應設備的304項中,全部建成的只有120項,基本建成29項,廢止合同89項,由中國自力更生續建66項; 在64項單獨車間和裝置中,建成29項,廢止35項。
在整個20世紀50年代(主要是“一五”時期),由東歐各國(包括民主德國、捷克、波蘭、羅馬尼亞、匈牙利和保加利亞)援建的供應成套設備的建設項目共116項,其中完成和基本完成的項,解除合同8項;單項設備88項,完成和基本完成81項,解除合同7項。
按引進的設備投資計算,1950—1959年,從蘇聯共引進76.9億舊盧布(折合人民幣73億元),其中,1950—1952年引進2.4億舊盧布,占3.2%;1953—1957年引進44億舊盧布,占57.1%;1958—1959年引進30.5億舊盧布,占39.6%。同期,從東歐各國共引進設備投資30.8億舊盧布(折合人民幣29.3億元)。
從蘇聯和東歐各國引進的成套設備幾乎都是建立社會主義工業化初步基礎所必需的重工業項目,分別占97%和80%,主要是基礎工業。就引進的設備投資構成看,從蘇聯引進的總額中,能源工業占34.3%,冶金工業占22%,化學工業占7.9%,機械工業占15.7%,軍事工業占12%左右,以上合計占92%左右;其中,“一五”時期實際引進的44億舊盧布中,能源工業占28.6%,冶金工業占22%,化學工業占7.8%,機械工業占18.5%,軍事工業占14%左右,以上合計占91%左右[20]。
蘇聯對中國建設的援助是全面的,技術是先進的。蘇聯援助建設156個項目,從勘察地質,選擇廠址,收集設計基礎資料,進行設計,供應設備,指導建筑安裝和開工運轉,供應新種類產品的技術資料,一直到指導新產品的制造,是從頭到尾全面地給予援助。
從蘇聯和東歐各國引進成套設備的建設項目中,“一五”期間實際施工的分別為146個和64個,全部和部分投產的分別為68個和27個。這些項目的投產,在建立中國社會主義工業化初步基礎方面起了極為重要的作用。
“一五”時期不僅重視引進技術裝備,同時重視在科研、設計、施工和管理等各個環節上進行全面的學習和培訓,使得研究、設計、生產工藝和設備制造等環節上技術水平的提高基本上是同步的,因而比較快地提高了使用能力、消化能力和創新能力。例如,哈爾濱電機廠是“一五”時期蘇聯幫助建設的156個項目之一,在“一五”時期以后的1958年、1959年和1960年這3年,分別相繼制造出2.5萬千瓦、5萬千瓦和10萬千瓦的發電機組。隨后又制造出20萬千瓦的發電機組。
引進技術。1954年10月,中國和蘇聯簽訂了科學技術合作協定;之后,又分別與東歐各國簽訂了科學技術合作協定。到1959年,中國從蘇聯和東歐獲得的關于能源、原材料和機械工業(包括民用和軍用)的技術資料達到4 000多項。另外,在中國掌握尖端科學技術與和平利用原子能技術方面,蘇聯也給予了一定的援助。
引進人才。20世紀50年代(主要是“一五”時期)蘇聯和東歐各國來華工作的技術專家達到8 000多人,同時還為中國培養技術人員和管理干部7 000多人。
引進資金。1950年2月14日,中蘇兩國政府簽訂了蘇聯政府向中國政府提供3億美元貸款的協定。這筆貸款用于支付蘇聯供應中國的設備器材費用,年息1%,中國從1953年起10年內用商品和外匯等償還本息。1951—1955年,中蘇兩國政府又簽訂了10筆貸款協議,其中1筆為無息,9筆年息2%,償還期2~10年,用于支付從蘇聯購買抗美援朝戰爭和加強國防所需的軍事裝備物資、經濟建設所需的設備物資以及蘇聯移交中國的設施、物資等費用。上述11筆貸款金額共計56.6億舊盧布(折合人民幣53.68億元),其中,用于購買軍事裝備物資和支付蘇聯移交旅大軍事基地設施、物資的費用占76.1%;用于購買經濟建設設備物資的費用占23.9%。到1964年,即比協定規定提前一年,償還全部貸款,并付利息5.8億舊盧布,本息折合人民幣55.5億元。償付蘇聯貸款本息主要是靠直接向蘇聯出口商品支付的。這一部分約占歸還貸款金額的82%[20]。而且,中國對蘇聯出口的商品,有相當一部分是蘇聯發展工業(包括軍事工業)急需的重要戰略物資。比如,在1953年5月15日中蘇兩國政府簽訂的協定中,就規定在1954年至1959年間,中方向蘇聯提供鎢砂16萬噸、銅11萬噸、銻3萬噸、橡膠9萬噸等戰略物資作為蘇聯援建項目的部分補償[21]。
學習管理經驗。新中國在成立初期(包括“一五”時期)從蘇聯學習的經濟管理和企業管理的經驗,在建設中國社會主義經濟管理制度和企業管理制度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
總體來說,“一五”時期從蘇聯引進成套設備、技術、人才、資金和學習管理經驗,對中國建立社會主義工業化初步基礎,起了重要的促進作用。
但在1959年7月16日,蘇聯政府突然照會中國政府,單方面決定在一個月內撤回全部在華專家,撕毀專家合同,廢除科技合作項目;同時撕毀經濟援助合同,停止對中國的設備供應。所有這些都給新中國建立以后在中國對外經濟貿易關系占有極重要地位的中國與蘇聯和東歐各國的關系造成了極其嚴重的損失!所以,從國際視角看,這是中國由原來的半開放走向封閉的一個轉折點。這也是第二個階段的開始。
就國內來說,1958年開始實行“左”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這條總路線完全撇開了發展對外經濟貿易關系,把原本正確的自力更生為主的方針推到了一個極端,搞成了完全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
這樣,如果不說1961—1965年的經濟調整時期,在1958—1976年近20年時間里,先是執行了“左”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1958—1960年),后是執行了處于主導地位的“左”的黨在社會主義階段的基本路線,同時繼續執行了“左”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1966—1976年)。
這兩條路線的區別,僅就其中某些共同點來說,就是完全忽視發展對外經濟貿易關系的重要性。實際上,在黨的第九次和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也是只字不提發展對外經濟貿易關系。只要同黨的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文件在這方面的論述做一下對比,就可以更清楚地看出這一點。
所以,僅從國內視角說,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和社會主義歷史階段基本路線的先后提出,以及這兩條路線的實踐,是中國由新中國建立后實行的半開放到全封閉的根本標志。
這樣,僅就發展對外經濟貿易關系而言,就造成了極為嚴重的損失!在對外貿易方面,1960—1976年進出口總額、出口額和進口額三者的年均增速分別只有6.0%、6.4%和5.6%,三者分別比1949—1959年下降了6.3、7.0和8.9百分點。
需要說明:后者比前者增速的下降,有基數增大的因素,但主要因素還是后者在發展對外經貿經濟貿易方面遠遠遲后于前者。
在接下的1977—1978年,中國對外經濟貿易關系的發展又呈現出某種特點。一方面這期間仍然明確宣布要繼續執行之前提出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和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1977年8月召開的黨的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就明確提出,“堅持黨的基本路線”“要認真貫徹執行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22]1978年2月召開的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又一次強調:“堅持黨的基本路線,堅持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總路線。”[23]這些文件表明:導致封閉的對外經濟貿易關系的路線并沒有改變。但這只是問題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又正是在建設社會主義總路線指引下,從1977年開始掀起了一次“大躍進”。
1977年8月召開的黨的十一大提出:“一個國民經濟新躍進的局面正在出現。”“到一九八○年,要建立我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22]1978年2月召開的五屆人大一次會議又進一步提出:“一個新的躍進形勢已經到來了。”到1985年,要“建成全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糧食產量達到八千億斤,鋼產量六千萬噸”[23]。這個“躍進”的計劃,象1958年“大躍進”一樣,是一個不可能實現的空想。
與1958年開始的“大躍進”不同,這次“躍進”計劃的實現,在很大程度上,是寄希望于放手利用外資,大量引進先進技術設備。企圖在較短的時間內,通過大規模的技術引進來實現工業現代化。僅1978年,就和國外簽訂了22個大型的引進項目,共需外匯130億美元,折合人民幣390億元,加上國內配套工程投資200多億元,共需600多億元。在22個成套引進項目中,約占成交額一半的項目是在1978年12月20日到年底的10天內搶簽的。不少項目是屬于計劃外工程,既沒有經過認真的調查研究,進行必要的技術經濟論證,也沒有經過計劃部門綜合平衡,甚至連最簡單的計劃任務書也沒有,因此帶有很大盲目性。史稱的“洋躍進”,即由此而來。
1976年,國民經濟比例失調的問題已經十分嚴重。此后繼續推行的 “洋躍進”,更加劇了國民經濟比例失調。
但與這次“大躍進”的特點相聯系,在拓展對外經濟貿易關系上卻有很大的發展。僅以發展對外貿易為例,1977—1978年中國進出口總額、出口額和進口額的年均增速分別達到了24.0%、19.2%和28.0%;三者分別比1960—1976年的年均增速高出18個、12.8個和22.4個百分點。
顯然,與1960—1976年實行的封閉政策相比,這兩年可以看作是在實際上邁向半開放,但在體制上仍然是封閉的。
1977—1978年這個特殊的時期,就新中國成立后大多數年份來說,這期間中國在對外開放方面經歷了全封閉和半開放半封閉兩個階段(2)本文在這方面的表述,都是在這個意義上說的。。
1978年底召開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在這方面實現了歷史性的根本轉變,做出了實行對外開放的偉大決策。這也是第三個階段的開始。
這次全會重新確立了馬克思主義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提出以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為中心,對經濟管理體制進行改革,以及積極發展同世界各國平等互利的經濟合作的基本指導思想。
1982年2月召開的黨的十二大進一步提出:“實行對外開放,按照平等互利的原則擴大對外經濟技術交流,是我國堅定不移的戰略方針。”[24]
同年12月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明確規定:“中國堅持獨立自主的對外政策,堅持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發展同各國的外交關系和經濟文化的交流”[25]。從此,作為中國基本國策的對外開放,就由作為國家根本大法的憲法規定下來。
由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發端的對外開放政策,是由半封閉到開放的根本轉折的一個主要標志。這是由歷史唯物主義的一系列根本原理決定的。
歷史唯物主義認為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但生產關系對生產力,上層建筑對經濟基礎都有反作用(包括促進作用和阻礙作用)。
新中國建立后的長期實踐已經充分證明,作為上層建筑重要組成部分的半封閉到封閉政策,不利于社會生產資源在國內的有效配置,更不利于社會生產資源在國際的配置,因而不利于社會生產力發展,不利于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鞏固。
為了說明這一點,只要把新中國建立后的半開放、封閉、實際上再半開放這三個階段的經濟增長速度作一對比,就可以看得很清楚。1952—1959年實行半開放政策時,年均增速為10.9%。而在1960—1976年實行封閉政策,年均增速僅為3.9%,比上一個階段下降了7百分點。1977—1978年在實際上又回歸到半開放時,年均增速達到9.6百分點,比第二階段上升了5.7百分點[26]。
當然,決定這種差異的有多方因素。但與先后相繼實行的半開放政策、封閉政策和實際上再半開放政策也有很大關系。上述數據已經清楚地證明了這一點。因此,為了促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以鞏固社會主義制度,必須根本改變封閉政策,實行對外開放的基本國策。
黨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做出的對外開放的偉大決策,不僅正確反映了中國經濟發展的經驗,而且正確反映了世界各國經濟發展的經驗。第二次世界大戰后,世界各國經濟獲得了前所未有的大發展。如果僅就對外開放來說,這種大發展的因素主要有以下三個特點。
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帝國主義殖民體系趨于瓦解。這樣,原來經濟發達的帝國主義國家不可能再依靠殘酷掠奪殖民地半殖民地來獲取高額壟斷利潤。當然,二戰以前留下的不合理的舊的經濟、政治秩序仍然是它們獲取高額壟斷利潤的條件。但這一點已經不占主要地位了。這時他們主要依靠對現代的生產技術的壟斷地位來獲取壟斷利潤。需要著重強調的一點是:它們這時實行的對外開放呈現出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經濟發達國家相互之間的對外開放已經上升到重要地位,僅就對外直接投資來說還上升到了主要地位。實踐表明:二戰以后經濟發達國家相互之間的直接投資已經占到對外直接投資的大部分。這是促進二戰以后經濟發達國家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
第二,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在帝國主義殖民體系瓦解的基礎上,產生了一大批新興市場經濟國家。它們的興起也有眾多因素。其中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它們利用后發優勢和比較優勢,實行對經濟發達國家的開放,以便引進先進的生產技術以及與此相聯系的大量資金,加速與現代化相結合的工業化,從而迅速成長為新興工業化國家,迅速實現了由低收入國家到高收入國家的跨越。
第三,如前所述,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在歐亞兩洲產生了一系列社會主義國家,形成了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與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陣營的對立。與此相聯系,還形成了北大西洋公約的軍事集團與華沙條約的軍事集團的對立。與此同時,蘇聯共產黨主要領導人還提出了社會主義世界市場與資本主義世界市場兩個平衡市場的理論。這樣,統一的世界體系就被分割為兩個平行的市場體系。但到20世紀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社會主義的蘇聯和東歐人民民主國家先后解體。這些國家經濟得到復蘇以后,也紛紛加入世界市場體系。這樣,統一的世界市場體系又得以恢復,并促進了世界市場的發展。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世界市場的大發展以及由此促進的世界經濟的大發展只是事物的主流,如同任何事物的主流一樣,與它同時存在的必然還有一股逆流。二戰以后不時涌現的貿易保護主義就是這方面的逆流。近幾年來,美國一些政客頑固推行的單邊主義和貿易保護主義,就是這方面最突出的代表。但這畢竟只是一股逆流。在當今經濟全球化和世界多極化大發展時代,它不可能再成為主流。
上述的二戰以后世界市場的大發展及其促進的經濟大發展,是極為重要的經驗。這表明: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做出的對外開放的偉大決策,是以中國經濟發展和世界經濟發展的經驗為客觀依據的,是一個完全科學的決策。
這里需要著重指出,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改革開放四十周年大會上的講話》從國內國際兩方面的情況全面地深刻地說明了對外開放的客觀必然性。他說,“我們黨作出實行改革開放的歷史性決策,是基于對黨和國家前途的深刻把握,是基于對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實踐的深刻總結,是基于對世界潮流的深刻洞察,是基于對人民群眾期盼和需要的深刻體悟。”[27]
綜上所述,本文分別從國內和國際兩方面論述了中國在改革以后由原來的封閉、半封閉轉向開放的客觀必然性。因此,那種忽視對國際環境的分析,只從國內環境來論證對外開放的必然性,也不能認為是全面的。同時需要指出,中國實行對外開放有國際方面的原因,也有國內方面的原因。但這兩方面在啟動對外開放方面的作用是不能等量齊觀的。“唯物辯證法認為外因是變化的條件,內因是變化的根據,外因通過內因而起作用。”[28]就這里論述的問題也是這樣。1978年之所以能夠成為中國對外開放的起點,最關鍵的原因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在這方面做出了對外開放的決策,國際環境只是其形成和實施的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