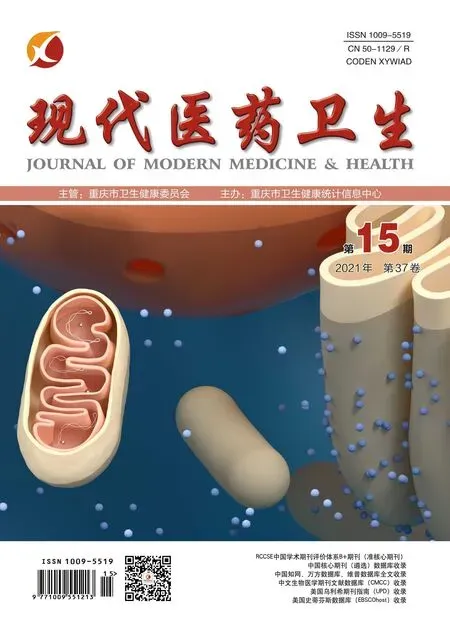子宮內膜容受性評估方法研究進展*
朱麒宇,黃 瑩 綜述,傅惠佳,劉西茹 審校
(重慶醫科大學,重慶 400016)
胚胎成功著床是成功妊娠的決定性因素,而胚胎著床是一個子宮內膜和胚泡之間相互作用的復雜過程。子宮內膜允許胚胎正常植入的能力稱為子宮內膜容受性,子宮內膜處于最佳容受狀態才能使胚胎正常植入,這是妊娠的基礎[1]。據統計,在體外受精(IVF)中胚胎自身缺陷占植入失敗原因的1/3,而子宮內膜容受性和胚胎-子宮內膜間的相互作用改變占2/3[2]。近年來,子宮內膜容受性已成為生殖醫學專家的研究熱點。盡管經大量基礎與臨床研究已對胚胎-子宮內膜間的相互作用過程有了深入了解,但在子宮內膜容受性評估和治療方面的臨床綜合應用進展甚微。目前,最常用的子宮內膜容受性評估方法是婦科超聲檢查,也有如子宮內膜活檢、宮腔內液體分析、內分泌指標及宮腔鏡等新興方法。但還沒有預測子宮內膜容受性的“金標準”,亟須研究更準確地評估子宮內膜容受性的方法。
1 超聲評價子宮內膜容受性
超聲的應用在婦科器質性疾病和產檢方面發揮了特異性價值,甚至成為許多疾病診斷的“金標準”。通過超聲檢查得到的子宮內膜厚度、子宮內膜類型、子宮內膜容積及內膜下血流信號等指標已廣泛用于評估子宮內膜容受性,而且超聲具有無創性、可重復性、可預測性及能夠實時監測等特點,使超聲診斷更具有臨床應用和研究價值,目前,大多數生殖醫學專家均選擇超聲作為評估子內膜容受性的首選檢查方法。
1.1子宮內膜厚度 子宮內膜厚度隨女性月經周期呈周期性變化,是目前評估子宮內膜容受性最常見指標,因其最簡單也最可重復。一項回顧性研究在子宮內膜厚度每毫米處評估臨床妊娠率、活產率和自然流產率,新鮮胚胎移植周期取卵日的子宮內膜厚度小于或等于6 mm的患者臨床妊娠率為50.00%,子宮內膜厚度大于16 mm的患者臨床妊娠率為84.20%,活產率則分別為33.30%、63.20%;凍融胚胎移植周期開始補充孕酮當天子宮內膜厚度從小于或等于6 mm增加到大于14 mm,臨床妊娠率為34.80%~69.20%,活產率為26.10%~46.20%;自然流產率的變化與子宮內膜厚度變化無明顯關系[3]。然而,一項薈萃分析結果顯示,在宮腔內人工授精和體外受精中妊娠組研究對象子宮內膜厚度與非妊娠組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此外,該薈萃分析中高精度研究的高質量證據顯示,子宮內膜厚度預測臨床妊娠的能力較差[4]。該項薈萃分析中的19項研究提供了人絨毛膜促性腺激素(hCG)注射當天子宮內膜厚度截止值為6~17 mm和新鮮胚胎移植后的臨床妊娠之間關聯分析的數據顯示,臨床妊娠與每一個子宮內膜厚度截止值增高呈正相關[4]。許健[5]還發現,部分患者因有人流史,子宮內膜厚度不均,僅測量內膜厚度不能如實反映內膜情況,需與其他超聲檢查指標結合才能評估子宮內膜容受性。總之,子宮內膜厚度對子宮內膜容受性和臨床妊娠的預測準確性均較低。
1.2子宮內膜容積 近十年來,人們開始采用子宮內膜容積參數預測IVF周期中的妊娠率,通過3D陰道超聲技術測量體積并進行重建從而得到子宮內膜容積。子宮內膜容積也會隨月經周期呈周期性變化,并與子宮內膜厚度顯著相關。但子宮內膜容積能否用于預測妊娠目前仍有爭議。一項研究分析了取卵當天子宮內膜容積和子宮內膜厚度,結果顯示,子宮內膜厚度、子宮內膜容積與最終的著床率并無相關性,但該研究結果也顯示,妊娠需要的最小子宮內膜厚度、容積分別為0.69 cm、1.5 mL[6]。另有研究表明,子宮內膜容積小于2 mL者妊娠的可能性較小,提示子宮內膜容積小于2 mL可能作為預測子宮內膜容受性的觀察指標[7]。一項前瞻性試驗在卵泡期長方案中,在給藥當天囑患者排空膀胱后進行5D經陰道超聲測量子宮內膜體積,結果顯示,子宮內膜體積大于或等于5 mL在預測卵胞漿單精子注射患者子宮內膜容受性中具有較高的靈敏度和較低的特異度;在個體應用中預測陰性值較好,預測陽性率較差[8]。總之,子宮內膜體積對子宮內膜容受性的預測性較低,難以用這個單一指標對子宮內膜容受性做出準確判斷。
1.3子宮內膜模式 根據超聲下子宮內膜和肌層的相對回聲狀態可將子宮內膜模式分為3型,即GONEN分型的A、B、C型子宮內膜。A型指外層和中層均為強回聲,內層為低回聲,宮腔的中線回聲最明顯,即通常所說的三線征;B型指子宮內膜呈一種均勻的相對高回聲,子宮內膜與肌層圖像基本一致,宮腔中線的回聲不明顯;C型指整個子宮呈一種均質強回聲,其內基本不可分辨宮腔中線的回聲[9]。在雌二醇和孕酮的周期性作用下,子宮內膜模式理論上會呈現從A到B再到C的周期性變化;在體外受精治療過程中絕大多數研究表明,A型子宮內膜對胚胎著床最有利。一項研究表明,在hCG扳機日將A型子宮內膜形態、7~14 mm子宮內膜厚度加上內膜下血管舒張末期血流信號共同預測胚胎著床的可能性時,其靈敏度和特異度均達到了80.00%以上[10]。另外一項薈萃分析結果顯示,三線模式(A型子宮內膜)與較高的臨床妊娠率相關[4]。但最近的一項研究表明,在控制潛在混雜變量后當子宮內膜為半三線性或單線性時活產率與三線性子宮內膜比較并沒有變化;當分別分析新鮮和冷凍周期及評估與臨床宮內妊娠和流產率的相關性時,其結果相似。子宮內膜類型似乎對輔助生殖技術的活產沒有顯著影響,該試驗數據不支持如果子宮內膜不是三線性就取消輔助生殖周期[11]。
1.4超聲多普勒信號 在應用子宮動脈各種超聲多普勒信號參數評價子宮內膜容受性方面,大量研究表明,子宮動脈的超聲檢查參數評估子宮內膜容受性具有一定的臨床意義。子宮肌層血流主要由子宮動脈供應,子宮內膜血流灌注則來源于子宮動脈終末支螺旋動脈,所以,子宮動脈搏動指數(PI)和阻力指數(RI)并不能準確反映子宮內膜血流灌注[12]。但子宮動脈終末螺旋動脈太細,難以用超聲直接探測其PI、RI,目前,較常使用的比較準確的測量子宮內膜下血流灌注的指標有收縮/舒張比值(S/D)、血流指數(FI)、子宮內膜區域的血管化指數和血管化血流指數。一項薈萃分析的結果顯示,hCG注射當天出現的子宮內膜下FI與較高的臨床妊娠率相關,在新鮮胚胎移植當天測量的子宮內膜下FI中,2組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新鮮胚胎移植當天測量的子宮動脈PI<3時臨床妊娠率較高[4]。一項回顧性分析發現,在凍融胚胎移植周期中非妊娠組研究對象螺旋動脈RI、PI均低于妊娠組,且妊娠組研究對象子宮動脈S/D之和低于非妊娠組,子宮動脈S/D之和的截止值為14.47[13]。子宮內膜及內膜下血流可能對子宮內膜容受性具有一定的預測意義,但仍需更多高質量、大樣本臨床研究驗證其預測子宮內膜容受性的價值,以更好地將這些指標用于臨床實踐。
1.5子宮內膜波狀活動 子宮內膜本身不具備運動功能,子宮內膜下肌層卻一直處于自發收縮和舒張狀態,子宮內膜蠕動在本質上反映的是子宮平滑肌運動。子宮內膜在卵巢周期不同時間段會呈現不同的蠕動方式,且內膜蠕動幅度與頻率之比也一定程度影響著胚胎著床[14]。KIM等[15]對241個IVF周期在宮腔內人工授精當天子宮內膜活動進行了3 min的評估,臨床妊娠婦女總體子宮內膜活動減少,但宮頸-宮底活動率升高。CHUNG等[16]評估了286例新鮮胚胎移植婦女子宮收縮的變化規律,分別于胚胎移植前5 min,移植后5、60 min進行超聲檢查,結果顯示,臨床妊娠組研究對象胚胎移植前5 min子宮收縮力與非妊娠組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臨床妊娠組研究對象胚胎移植后5 min測量的收縮頻率降低。但影響子宮內膜運動的因素很多,包括女性生理狀態、病理狀態、情緒波動等,而且子宮內膜運動檢查過程中受操作者主觀判斷的影響,準確度、精確度均需要提高。所以,子宮內膜運動尚不能作為一個可靠的預測子宮內膜容受性的指標。
2 子宮內膜活檢
2.1組織學和細胞學 子宮內膜組織是一種動態組織,在循環的雌二醇和孕酮作用下經周期性增殖、分化和細胞運輸,尤其是免疫系統細胞。胚胎著床過程中子宮內膜重塑受蛻膜細胞衰老及免疫破壞的有效性控制[17]。子宮自然殺傷(uNK)細胞是一類CD56+的NK細胞。LIU等[18]將組織學標準與uNK細胞計數結合,預測83例復發性流產或反復著床失敗婦女的未來妊娠結局,結果顯示,uNK細胞計數與后續妊娠結局無關,“延遲相”子宮內膜流產率(68.00%)較“同相”子宮內膜(35.00%)更高,結合uNK細胞計數和組織學分期增加了預測個體預后的價值。胞飲突是一項組織形態學指標,需要在內膜活檢后通過掃描電鏡才能完成。胞飲突是特異性出現于種植窗子宮內膜的腔上皮與腺上皮的大而平滑的膜狀凸起,其發育過程包括發育、成熟和退化3個階段。胞飲突一般在排卵后第6~9天出現,相當于正常月經周期的第20天左右,表達時間持續不超過48 h,與子宮內膜種植窗一致,因此,可準確地反映子宮內膜容受性。JIN等[19]報道了126例接受凍融胚胎移植婦女的胞飲突并形成評分系統,胞飲突指數評分較高者與評分較低者比較有較高的臨床妊娠率。一項隨機對照試驗在黃體中期對受試者子宮內膜進行電鏡掃描,再將其隨機分為個體化胚胎移植(iET)組和常規凍融胚胎移植組(對照組),發現胞飲突指數評分大于85分者臨床妊娠率(分別為74.29%、19.77%)和持續妊娠率(分別為62.86%、11.86%)明顯增高,而且個體化胚胎移植組研究對象臨床妊娠率明顯高于對照組(分別為33.82%、8.11%)[20]。通過掃描電鏡檢測反復著床失敗者子宮內膜表面胞飲突預測子宮內膜容受性具有重要的臨床意義,但由于其檢測存在有創性,成本高昂,在臨床工作中應用很少。
2.2子宮內膜容受性陣列(ERA) ERA是一種基于微陣列技術的分子診斷試驗。以238個選定基因的表達將子宮內膜活檢結果分為接受性、接受性前或增殖性內膜[21],根據ERA結果行個體化胚胎移植。ROBERT[22]認為,ERA是一種極好的診斷測試,因其具有良好的靈敏度和特異度。DVORAN等[17]進行的一項系統綜述認為,可通過ERA系統的子宮內膜活檢轉錄組學分析評估子宮內膜容受性。ERA不僅對IVF中反復種植失敗患者的植入時機選擇十分有利,而且能比較客觀和個體化地判斷復發性流產患者和薄型子宮內膜患者的子宮內膜種植窗,但由于該檢測的有創性、回顧性和費用高昂,而且通過子宮內膜活檢評估子宮內膜容受性由于手術的侵入性會推遲生育治療進程,所以,在誘導排卵和控制性超促排卵周期中應用十分有限,目前,在臨床工作中尚未廣泛應用。
3 子宮內膜液體
通過子宮內膜活檢量化子宮內膜容受性由于手術的侵入性推遲了生育治療的完成,子宮內膜液體抽吸的侵入性較低,幾乎是無創的,可在胚胎移植前進行,且不會對妊娠結局產生負面影響[23]。宮腔分泌物中存在多種蛋白反應帶,其中胎盤蛋白14、妊娠相關α2球蛋白、黃體酮相關蛋白、白細胞介素(IL)-1α、IL-1β、分泌蛋白等均與子宮內膜容受性相關[24]。這些蛋白質的作用可能是轉運維生素或其他重要物質到早期孕體,可能還具有免疫抑制作用[25]。一項薈萃分析中的3項研究評估了生育治療后不同結局研究對象各種細胞因子、糖肽、富含亮氨酸的α2糖蛋白的亞型、白血病抑制因子、腫瘤壞死因子、IL-1β、腫瘤壞死因子-α、干擾素γ誘導蛋白10、單核細胞趨化因子的平均水平,結果顯示,對妊娠結局并無臨床指導價值[4]。宮腔分泌物中的蛋白質分析對評價子宮內膜容受性的作用尚不明確,宮腔分泌物是否能用于預測子宮內膜容受性尚需更多高質量、大樣本的臨床研究佐證。
以前認為,人類子宮內膜是無菌的,但近年來的研究表明,子宮內膜中存在微生物,且與宮頸陰道菌群具有一致性[26]。雖然子宮內膜微生物群不受激素的調節,不隨月經周期變化,但在ERA診斷的接受性子宮內膜中存在非乳酸菌為主的微生物群患者的著床率、妊娠率及活產率均顯著降低[27]。宮腔內微生物群與人類子宮內膜細胞的關系,以及在生殖疾病治療中作用的研究才剛剛起步,尚需要更多研究闡明子宮內膜微生物群落多樣性對生殖的影響[28]。
4 內分泌指標
孕酮和雌激素在胚泡植入過程中具有主導作用,二者主要對子宮內膜產生作用并相互協調實現子宮內膜和胚泡同步發育。孕酮/雌二醇比值較孕酮與雌二醇絕對值對胚胎著床來說更重要,孕酮水平過低或雌二醇水平過高導致孕酮/雌二醇比值失調可能降低子宮內膜容受性,導致胚泡植入失敗[2]。在實際臨床工作中IVF的某些關鍵時間點,如hCG扳機日、胚胎移植日等均會常規檢查血液中雌激素、孕激素水平,作為粗略估計子宮內膜容受性的指標,同時,也可指導調整用藥,但其準確性尚有待于商榷,只能作為參考。
5 宮腔鏡
宮腔鏡能在直視下觀察宮腔表面形態,包括宮腔大小、形狀和內膜狀態,不易遺漏宮腔內微小占位和內膜病變,同時,還能在直視下定位活檢及在檢查的同時進行治療。子宮先天性或獲得性病變造成的宮腔形態變化均可在宮腔鏡下體現,子宮內膜息肉、縱隔子宮、宮腔粘連是最常見的宮腔內畸形,均是宮腔鏡檢查的適應證。最近的一項多中心隨機對照試驗結果顯示,子宮腔超聲檢查正常且IVF治療周期不成功的婦女在IVF前進行門診宮腔鏡檢查并不能提高活產率[29]。宮腔鏡檢查雖然是侵入性,但費用并不低,現在臨床上宮腔鏡的應用越來越廣泛,對有特殊病史的患者如自然流產史、反復著床失敗等,宮腔鏡檢查仍是有意義且必要的。宮腔鏡檢查可作為診斷某些宮內疾病的“金標準”,并且在與生殖相關的宮腔內疾病手術中越來越得到重視,但僅對預測子宮內膜容受性這一方面的應用十分有限。
總之,胚胎著床是一個十分復雜的過程,其成功與否由胚胎的植入能力及子宮內膜容受性共同決定。自然周期、誘導排卵周期和人工周期中的子宮內膜容受性可能存在差異,但在臨床工作中尚缺乏判斷子宮內膜容受性的“金標準”。在這種情況下通常將臨床妊娠作為確定容受性子宮內膜的替代結果。然而,影響臨床妊娠的因素很多,可能是胚胎質量或其他因素,不一定能反映子宮內膜容受性。因此,對子宮內膜容受性的研究一直是廣大生殖醫學專家的關注熱點。
本綜述中所描述的子宮內膜容受性的檢測方法,雖然目前被廣泛用于評估子宮內膜容受性及其他生殖工作中,但其價值不足以準確判斷子宮內膜容受性,從而預測臨床妊娠結局。在未來的科研中,希望能有更精心設計的研究明確子宮內膜容受性的影響因素,以期尋找到預測判斷子宮內膜容受性的最佳方法,提高胚胎著床率和妊娠率,從而改善IVF患者預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