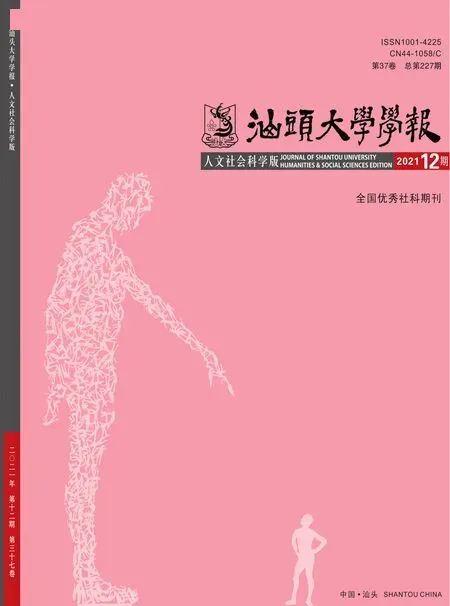愛(ài)之欲其善:趨向自我實(shí)現(xiàn)的自愛(ài)
原魁社
(太原科技大學(xué)馬克思主義學(xué)院,山西 太原 030024)
張岱年先生曾寫(xiě)道:“自愛(ài),這是一個(gè)永恒的題目。古往今來(lái),許多思想家都在探討自愛(ài)問(wèn)題。人人都懂得愛(ài)自己,究竟如何才是真正的自愛(ài)呢?”[1]從本體論的維度把自愛(ài)理解為趨利避害,雖賦予了自愛(ài)以存在論上的合法性,但容易使自愛(ài)陷入自利的窠臼,從而導(dǎo)致自愛(ài)的本體論困境。正如恩格斯在《在愛(ài)北斐特的演說(shuō)》中講到的:“我們大家辛勤勞動(dòng)的目的只是為了追求一己之利,根本不關(guān)心別人的福利。可是,每一個(gè)人的利益、福利和幸福同其他人的福利有不可分割的聯(lián)系,這一事實(shí)卻是一個(gè)顯而易見(jiàn)的不言而喻的真理。”[2]顯然,從本體論維度將自愛(ài)理解為趨利避害并付諸于實(shí)踐,則實(shí)際上犯了恩格斯所批評(píng)過(guò)的那種錯(cuò)誤,即將自愛(ài)主體的個(gè)人利益與他人和社會(huì)的利益相分割,而忽視了每一個(gè)人的利益與他人和社會(huì)利益不可分割的聯(lián)系。而從價(jià)值論的維度理解自愛(ài),把自愛(ài)理解為愛(ài)自己就不斷地滿足自己的需要,而自己的需要是分層次的,最高層次的需要是自我實(shí)現(xiàn)的需要。自我實(shí)現(xiàn)就是以自己本質(zhì)力量的對(duì)象化為社會(huì)和他人做貢獻(xiàn),是一個(gè)人充分發(fā)揮他的潛力,盡力成為他能夠成為的人。自我實(shí)現(xiàn)的勞動(dòng)就達(dá)到了馬克思所說(shuō)的“自由的生命表現(xiàn)”那種程度,通過(guò)這種“自由的生命表現(xiàn)”,“在我個(gè)人的活動(dòng)中,我直接證實(shí)和實(shí)現(xiàn)了我的真正的本質(zhì),即我的人的本質(zhì),我的社會(huì)的本質(zhì)”[3]。因此,從價(jià)值論維度理解的自愛(ài)就是:愛(ài)自己就希望自己越來(lái)越有價(jià)值(這種價(jià)值是社會(huì)價(jià)值和自我價(jià)值的統(tǒng)一),如此則可以使自愛(ài)擺脫本體論困境,獲得道德領(lǐng)域的崇高。
一、自愛(ài)不是趨利避害,而是“愛(ài)之欲其善”
亞里士多德在談到自愛(ài)的時(shí)候曾進(jìn)行了區(qū)分,他說(shuō)人們之所以從貶義的角度使用自愛(ài)這個(gè)詞,是因?yàn)樗麄儼褜?duì)錢財(cái)?shù)呢澯妥非笕怏w快樂(lè)的人稱為自愛(ài)的人,對(duì)此,亞里士多德說(shuō)道:“大多數(shù)人都是這類人。并且從這樣眾多的丑惡事實(shí),就產(chǎn)生了這樣的稱謂,這樣來(lái)譴責(zé)那些自愛(ài)者是公正的。”[4]200在指出這些自愛(ài)應(yīng)該受到譴責(zé)的時(shí)候,亞里士多德同時(shí)也談到了另外一種情況,比如有人追求的是比別人行事更加公正,比別人更加節(jié)制等社會(huì)公認(rèn)的德性。那么,就不能說(shuō)他是一個(gè)自愛(ài)者,從而說(shuō)他是錯(cuò)的,而應(yīng)當(dāng)對(duì)他的追求予以肯定。“這種人似乎是個(gè)更大的自愛(ài)者,他分配給自己的全都是最美好的東西。”[4]200在亞里士多德看來(lái),是否應(yīng)該對(duì)自愛(ài)者進(jìn)行譴責(zé),關(guān)鍵是要看自愛(ài)者想要為自己追求的是什么東西,“人們責(zé)備那些最為熱愛(ài)自己的人……壞人被認(rèn)為做一切都是為了自己,并且為自己所做的越多,他也就越壞。人們斥責(zé)他,說(shuō)他從不為別人做任何事情。而人做事出于高尚,所做的越多,他也就越好”[4]199。我們可以看到,亞里士多德實(shí)際上把自愛(ài)分為兩種情況,一種是以多占錢財(cái)、榮譽(yù)和肉體快樂(lè)為追求目標(biāo)的自愛(ài),一種是以公正、節(jié)制等高尚美好的東西為追求目標(biāo)的自愛(ài)。前者在他看來(lái)“譴責(zé)那些自愛(ài)者是公正的”,而后者卻“是個(gè)更大的自愛(ài)者”。因此應(yīng)該譴責(zé)前者而提倡后者。在亞里士多德看來(lái),后者才是真正的自愛(ài),兩者的區(qū)別在于“一個(gè)按照理性來(lái)生活,另一個(gè)則是按照情感來(lái)生活。一個(gè)所向往的是高尚的行為,一個(gè)所向往的看來(lái)是有利的東西。那些對(duì)高尚行為特別熱心的人受到普遍的贊揚(yáng)和尊敬。如若所有的人都在高尚方面競(jìng)賽,爭(zhēng)著去做高尚的事情,那么共同事業(yè)就會(huì)圓滿實(shí)現(xiàn)。每個(gè)人自身也得到最大的善,因?yàn)榈滦跃褪亲畲蟮纳啤K裕屏嫉娜耍瑧?yīng)該是一個(gè)熱愛(ài)自己的人,他做高尚的事情,幫助他人,同時(shí)也都是有利于自己的。邪惡的人就不應(yīng)該是個(gè)愛(ài)自己的人,他跟隨著自己邪惡的感情,既傷害了自己,又傷害了他人。邪惡人的所為之事和所應(yīng)為之事相背馳,而善良之人所做的一切都是他所應(yīng)該做的”[4]200-201。可以看出,亞里士多德賦予了追求“高尚”目標(biāo)的自愛(ài)以“善”的屬性,而卻賦予了追求私欲目標(biāo)的自愛(ài)以“惡”的屬性。
20 世紀(jì)30 年代,浙江大學(xué)的嚴(yán)群先生在介紹亞里士多德的倫理思想時(shí)說(shuō):“愛(ài)之欲其善,人之情也。”[5]163他在論述亞里士多德的自愛(ài)思想時(shí)說(shuō):“惟君子能自愛(ài),小人不能也。”[5]173君子是成德之人,有明確的人生目標(biāo),“成德之人,莫非自愛(ài)之徒。故惟有德者,乃能好生;其好生也誼,以其能自愛(ài)——能自愛(ài),然后知所以生也”[5]172。君子能夠通過(guò)忠恕之道把“愛(ài)己”推心置腹于“愛(ài)人”,君子的“愛(ài)己”“非飽食暖衣,愛(ài)我肉體之謂。乃愛(ài)我理性,不獨(dú)保之毋失,且培育之,使其滋長(zhǎng),以至于成德之謂也。”[5]174因此君子的自愛(ài)當(dāng)然具有“善”的屬性,而小人則不配擁有這種自愛(ài)。“小人不能自愛(ài),其故由二:(一)小人好惡無(wú)常,同一物也,或朝好而夕惡之,或朝惡而夕好之。非止此也,其好惡毫無(wú)標(biāo)準(zhǔn),應(yīng)好之物,或反惡之,應(yīng)惡之物,或反好之,以致是非顛倒。故其行事,益己者不為,損己者為之,終致敗德壞身,無(wú)異自戕。(二)小人不知有己。何則?其心志不定,好惡無(wú)常;明日所行之事,或與今日迥然不同,而不自知其所以。前后矛盾,儼然二人。”[5]173-174嚴(yán)群先生把亞里士多德的兩種自愛(ài)的主體解釋為小人和君子,實(shí)際上也就在提倡以“高尚”為追求目標(biāo)的自愛(ài)的同時(shí),否定了“以多占錢財(cái)、榮譽(yù)和肉體快樂(lè)為追求目標(biāo)的自愛(ài)”的倫理屬性。
實(shí)際上,趨樂(lè)避苦是人的一種本能,而本能具有亞里士多德關(guān)于“功用”的“善”,還不能說(shuō)具有倫理維度上的“善”。只有滿足本能的方式以及本能得到滿足后的主體的行為才具有倫理上的善惡之分。如果主體的行為是“善”的,那么為了維護(hù)“善”的主體的趨樂(lè)避苦的行為就具有增強(qiáng)主體的行善能力的性質(zhì)。而如果主體的行為是“惡”的,則“惡”的主體的趨樂(lè)避苦的行為就具有“為虎作倀”的性質(zhì)。因此,趨樂(lè)避苦的行為與倫理的“善”沒(méi)有必然的聯(lián)系,“當(dāng)說(shuō)一切快樂(lè)皆為善的,一切善皆為快樂(lè)的。然此不合事實(shí)者。如吾人承認(rèn)幸災(zāi)樂(lè)禍的人,亦有一種快樂(lè),偷盜殺人之人,偷得了食物,與殺了人,亦有一快樂(lè)。然吾人并不以之為善。而犧牲自己,以為他人而吃苦之人,吾人卻以之為善,可見(jiàn)樂(lè)與善非同義語(yǔ),吃苦亦可以是善”[6]。因此,我們說(shuō)以趨樂(lè)避苦為特征的自愛(ài)不具有倫理上“善”的屬性。把自愛(ài)理解為趨樂(lè)避苦并與人的本能相聯(lián)系,并不能賦予自愛(ài)以倫理合法性,關(guān)鍵要看滿足本能后的主體的行為所具有的意義。
保存生命是一種本能,而飲食顯然是保存生命最基本的活動(dòng),飲食是人與動(dòng)物都有的,但人的飲食不同于動(dòng)物的維持自己生命存在的飲食,唐君毅先生把飲食稱為低級(jí)價(jià)值,而把追求生命的意義稱為高級(jí)價(jià)值,他說(shuō):“人飲食,是為的使他的生命的意義,貫注到事物里面。”[7]45人的飲食活動(dòng)是為了實(shí)現(xiàn)主體客體化,是以客體的屬性來(lái)增強(qiáng)主體的力量,“飲食之實(shí)現(xiàn)價(jià)值,與人生之一切活動(dòng)之實(shí)現(xiàn)價(jià)值,在本質(zhì)是同類的”[7]46。低級(jí)價(jià)值的實(shí)現(xiàn)是高級(jí)價(jià)值實(shí)現(xiàn)的基礎(chǔ),在這個(gè)意義上,低級(jí)價(jià)值和高級(jí)價(jià)值都是應(yīng)當(dāng)實(shí)現(xiàn)的。該譴責(zé)是為了低級(jí)價(jià)值而放棄高級(jí)價(jià)值的行為和選擇。顯然,在唐君毅先生看來(lái),飲食的善惡在于飲食本身淹沒(méi)了高級(jí)價(jià)值,還是飲食幫助我們上通至高級(jí)價(jià)值,也就是說(shuō),飲食的意義取決于飲食后主體的行為的意義。
由此,本體論維度的自愛(ài)僅僅關(guān)注了趨利避害作為人的本能的合理性,而不能關(guān)注趨利避害的主體行為的意義。那些道德冷漠的主體之所以選擇了冷漠,其出發(fā)點(diǎn)就是他們認(rèn)為的“自我保護(hù)”。這種逃避“麻煩”的行為也是符合趨利避害的行為,如果這樣的行為是一種自愛(ài)的行為的話,那么這樣的自愛(ài)我們不要也罷。那些拒絕讓醫(yī)護(hù)人員回家的小區(qū)和居民“按自愛(ài)之心的暗示來(lái)行動(dòng)”,他們的行為使流汗者流淚,使盡心者寒心,他們以其“自愛(ài)之心的暗示”而損害了“眾人的利益”。他們的利益不僅要受到被他們損害的道德文明的間接損害,而且他們的行為本身也會(huì)受到社會(huì)群體強(qiáng)烈的譴責(zé),而使他們內(nèi)心承受巨大的壓力。“只要想起,他就為自己的行為感到羞愧和恐慌。倘若他的行為弄得眾人皆知,他定然會(huì)覺(jué)得自己要將遭受到奇恥大辱。”[8]123也就是說(shuō),冷漠的主體選擇這種“躲避麻煩”的“自愛(ài)”行為,終究要損害這些主體自身的利益。
本體論維度的自愛(ài)無(wú)法解決愛(ài)人與愛(ài)己的矛盾,而自愛(ài)的主體是離不開(kāi)自己所存在的群體的,離開(kāi)了整體而僅僅關(guān)注于自己本能的所謂“自愛(ài)”,不僅不能自愛(ài),而且最終還會(huì)造成自我利益的損害。而要從自愛(ài)的本體論困境中走出來(lái),我們可以從價(jià)值論的角度去理解自愛(ài)。
從價(jià)值哲學(xué)的視野中去理解自愛(ài),自愛(ài)是在自我價(jià)值感基礎(chǔ)上產(chǎn)生的對(duì)“我”的愛(ài)的情感。也就是說(shuō),在自我的存在和行為有價(jià)值的基礎(chǔ)上才產(chǎn)生了自愛(ài)的情感。自愛(ài)是自我對(duì)有價(jià)值的“我”的愛(ài)、是對(duì)“好”“我”的愛(ài),這樣的自愛(ài)才能被視作是一種美德,這就是“愛(ài)之欲其善”。
二、“愛(ài)之欲其善”的自愛(ài)與自我實(shí)現(xiàn)的需要聯(lián)系在一起
十七歲的馬克思在中學(xué)畢業(yè)時(shí)就寫(xiě)下:“在選擇職業(yè)時(shí),我們應(yīng)該遵循的主要指針是人類的幸福和我們自身的完美。……如果一個(gè)人只為自己勞動(dòng),他也許能夠成為著名的學(xué)者、偉大的哲人、卓越的詩(shī)人,然而他永遠(yuǎn)不能成為完美的、真正偉大的人物。”[9]459在重大疫情防控過(guò)程中,除了奮戰(zhàn)在一線的醫(yī)護(hù)人員外,依然有相當(dāng)多的人選擇了免費(fèi)接送醫(yī)護(hù)人員上下班、為醫(yī)護(hù)人員送餐、為疫情防控捐款捐物、為抗擊疫情運(yùn)送物資等。他們拒絕了趨利避害,他們將自身置于容易被感染的環(huán)境中,他們正在以奉獻(xiàn)的方式滿足自我實(shí)現(xiàn)的需要,他們正以滿足自己最高需要的方式創(chuàng)造著的自我價(jià)值,同時(shí)也體驗(yàn)著一種“愛(ài)之欲其善”的崇高的自愛(ài)。
自我作為價(jià)值客體,無(wú)論是滿足了自我主體的需要,還是滿足了他人和社會(huì)的需要,都將使“我”產(chǎn)生自我價(jià)值感,都將使“我”感覺(jué)到“我”是“好”的、有用的、有意義的社會(huì)存在,從而產(chǎn)生對(duì)“我”的愛(ài)的情感。“愛(ài)則欲善之心生”[5]163,自愛(ài)不僅是對(duì)“善”“我”的愛(ài),而且也包含著使“我”成為“善”的期待,即我們?cè)谇懊嬲f(shuō)過(guò)的“愛(ài)之欲其善”[5]163,愛(ài)一個(gè)人就會(huì)希望他“善”,愛(ài)自己當(dāng)然也包含著希望我“善”。“善”顯然超越了“我”的個(gè)體的利益,對(duì)使“我”成為“善”的期待,當(dāng)然離不開(kāi)對(duì)他人和社會(huì)的愛(ài),因此自愛(ài)實(shí)際上是利他和利己的統(tǒng)一。
在表征人的最高價(jià)值的價(jià)值關(guān)系中,價(jià)值主體的需要是自我實(shí)現(xiàn)的需要,價(jià)值客體是自我的本質(zhì)力量。客體屬性滿足主體需要的過(guò)程就是自我在社會(huì)實(shí)踐中通過(guò)本質(zhì)力量的對(duì)象化實(shí)現(xiàn)了自我。對(duì)價(jià)值關(guān)系的深刻理解離不開(kāi)評(píng)價(jià),“我”對(duì)自我實(shí)現(xiàn)的需要與自我本質(zhì)力量之間的價(jià)值關(guān)系的評(píng)價(jià)也是一種自我評(píng)價(jià)。在對(duì)自我最高價(jià)值的評(píng)價(jià)活動(dòng)中,主體選擇的需要就是自我實(shí)現(xiàn)這種最高層次的需要,此時(shí)所反映的價(jià)值關(guān)系就是主體自我實(shí)現(xiàn)的需要和自我的本質(zhì)力量之間的關(guān)系。“我”的本質(zhì)力量對(duì)“我”的自我實(shí)現(xiàn)需要的意義就在于,“我”通過(guò)“我”的社會(huì)實(shí)踐將“我”的本質(zhì)力量對(duì)象化,而這個(gè)過(guò)程就是為他人和社會(huì)做貢獻(xiàn)的過(guò)程,也就是“我”的人生意義的展開(kāi)過(guò)程。
人生價(jià)值表現(xiàn)為對(duì)人類發(fā)展的承上啟下、承前啟后的責(zé)任感,實(shí)際上就是以我的人生為價(jià)值客體,以他人和社會(huì)為價(jià)值主體,人生價(jià)值也就是不斷地以自己的人生展開(kāi)過(guò)程不斷滿足他人和社會(huì)的需要。“我”的人生過(guò)程滿足了他人和社會(huì)的需要,則“我”的人生就有價(jià)值,滿足他人和社會(huì)的需要越大,則“我”的人生價(jià)值越大。每個(gè)人都希望自己的人生有意義、有價(jià)值,“我們有對(duì)自我感覺(jué)良好的人類基本需求。心理學(xué)將此稱為自我增強(qiáng)的動(dòng)機(jī)……他們想努力擴(kuò)大并保護(hù)自己的自我價(jià)值感”[10]169。這種自我增強(qiáng)的動(dòng)機(jī)促使人們不斷提高自我價(jià)值,想方設(shè)法以己為榮,極力避免以己為恥。“擴(kuò)大并保護(hù)自己的自我價(jià)值感”的主要途徑就是增強(qiáng)自我實(shí)現(xiàn)的能力,發(fā)展和表現(xiàn)自己的體力和智力,在自己能力展現(xiàn)的過(guò)程中滿足他人和社會(huì)的需要。自我價(jià)值感是自愛(ài)的基石,自愛(ài)的情感伴隨著自我價(jià)值感的增強(qiáng)而增強(qiáng)。
在自我實(shí)現(xiàn)的過(guò)程中,雖然就行為的目標(biāo)指向和結(jié)果來(lái)說(shuō),是為了滿足他人和社會(huì)的需要,是一種“他愛(ài)”。但就行為所產(chǎn)生的價(jià)值感受來(lái)說(shuō),是對(duì)主體高層次需要的滿足,是一種自愛(ài)。自愛(ài)與愛(ài)他人和社會(huì)相統(tǒng)一,在盡自己的努力滿足他人和社會(huì)需要的過(guò)程中,自我不斷地體驗(yàn)著自愛(ài)的情感,斯賓諾莎說(shuō):“假如某人曾做一事,他想象著這事將引起他人快樂(lè),則他也將快樂(lè),而且意識(shí)著他自己是快樂(lè)的原因,這就是說(shuō),他將反省自己,感覺(jué)快樂(lè)。反之,假如他曾做一事,而他想象著這事將引起他人的痛苦,則他反省自己,也將感到痛苦。”[11]122自己引起他人快樂(lè),自己也快樂(lè),他人快樂(lè)是自己快樂(lè)的原因,但自己又是他人快樂(lè)的原因,因此是自己通過(guò)他人而使自己快樂(lè),也就是自己在滿足他人需要中體驗(yàn)著快樂(lè)。在這個(gè)意義上說(shuō),重大疫情防控中的“最美逆行者們”,他們的付出給社會(huì)和他人帶來(lái)了快樂(lè),而他們自己也體會(huì)著這種快樂(lè)。這正是青年馬克思所頌揚(yáng)的:“歷史把那些為共同目標(biāo)工作因而自己變得高尚的人稱為最偉大的人物;經(jīng)驗(yàn)贊美那些為大多數(shù)人帶來(lái)幸福的人是最幸福的人”[9]459。
通過(guò)以上的論述,我們已經(jīng)知道,對(duì)自我最高價(jià)值的肯定性評(píng)價(jià)產(chǎn)生了不斷增強(qiáng)的自我價(jià)值感,而不斷增強(qiáng)的自我價(jià)值感在強(qiáng)化著主體的自愛(ài)情感。“愛(ài)之欲其善,人之情也。”[5]163不斷強(qiáng)化的自愛(ài)情感又促使著主體進(jìn)一步增強(qiáng)自我實(shí)現(xiàn)的能力,從而在社會(huì)實(shí)踐中創(chuàng)造更大的人生價(jià)值。因此,在重大疫情防控中,“最美逆行者們”在“我”的最高價(jià)值的基礎(chǔ)上產(chǎn)生的自愛(ài)情感,不斷地豐富著他們的人生意義,激勵(lì)著他們的人生價(jià)值。
三、“愛(ài)之欲其善”的自愛(ài)是“愛(ài)他”與自愛(ài)的統(tǒng)一
馬斯洛認(rèn)為人的自我實(shí)現(xiàn)是一種使人的潛力得以充分實(shí)現(xiàn)的傾向,是一個(gè)人無(wú)止境的自我發(fā)揮和自我完成。自我實(shí)現(xiàn)是人不斷趨向于成為他能夠成為的一切,這就要求自我要盡可能地發(fā)展自己的體力和智力,并在社會(huì)實(shí)踐中尋找到最適合展現(xiàn)自己能力的職業(yè)崗位。自我實(shí)現(xiàn)的人必須處于最能展現(xiàn)自我價(jià)值的崗位上,否則,他就不能稱作是在滿足自我實(shí)現(xiàn)的需要。馬斯洛寫(xiě)道:“一位作曲家必須作曲,一位畫(huà)家必須繪畫(huà),一位詩(shī)人必須寫(xiě)詩(shī),否則他始終都難安靜。一個(gè)人能夠成為什么,他就必須成為什么,他必須忠實(shí)于他自己的本性。這一需要我們可以稱之為自我實(shí)現(xiàn)的需要。”[12]29對(duì)于真正的自我實(shí)現(xiàn)的過(guò)程,其同時(shí)也是主體享受快樂(lè)的過(guò)程。因?yàn)樽晕覍?shí)現(xiàn)的人不僅在做對(duì)他人和社會(huì)有益的事,而且他們正在做的事也是對(duì)自己有益的事。他們自覺(jué)自愿地實(shí)現(xiàn)自己的社會(huì)價(jià)值,同時(shí)也實(shí)現(xiàn)了自己的自我價(jià)值,他們是在奉獻(xiàn)中享受著自己的審美人生。這種自覺(jué)自愿實(shí)現(xiàn)自我人生價(jià)值的勞動(dòng),也就是馬克思所說(shuō)的“自由的生命表現(xiàn)”:“我的勞動(dòng)是自由的生命表現(xiàn),因此是生活的樂(lè)趣。”[3]38以自我實(shí)現(xiàn)為享受,也就是以滿足他人和社會(huì)的需要為享受,這就是把自己的需要與他人和社會(huì)的需要有機(jī)整合為一個(gè)統(tǒng)一體。
主體的自愛(ài)情感依賴于自己的人生價(jià)值,而自己的人生價(jià)值又取決于他的自我實(shí)現(xiàn)的程度,也就是取決于“我”對(duì)他人和社會(huì)所做貢獻(xiàn)的大小。“我”在為他人和社會(huì)做貢獻(xiàn)的自我實(shí)現(xiàn)過(guò)程中增強(qiáng)了“我”的自愛(ài)情感。從價(jià)值論的維度理解,滿足自我實(shí)現(xiàn)的需要是滿足自己最高層次的需要。在這個(gè)意義上說(shuō),尋求自我實(shí)現(xiàn)的自愛(ài)主體,其為他人和社會(huì)做貢獻(xiàn)是手段,而自我實(shí)現(xiàn)才是目的,自愛(ài)的主體出于自我實(shí)現(xiàn)的目的而為他人和社會(huì)做貢獻(xiàn)。為他人和社會(huì)做貢獻(xiàn)的同時(shí)使自己達(dá)到完美,這也正是馬克思在中學(xué)畢業(yè)論文里表達(dá)的觀點(diǎn):“人只有為同時(shí)代人的完美、為他們的幸福而工作,自己才能達(dá)到完美”[9]459。
從價(jià)值論的維度將自愛(ài)理解為“愛(ài)之欲其善”,自愛(ài)的主體因?yàn)樽詯?ài)而希望自我“好”,也就是希望自己的人生能創(chuàng)造出更大的價(jià)值。因此自我實(shí)現(xiàn)就成為“我”的目的,而通過(guò)自我實(shí)現(xiàn)為他人和社會(huì)做貢獻(xiàn)就成為滿足自我實(shí)現(xiàn)需要的手段。我們之所以在社會(huì)實(shí)踐中盡己所能地為他人和社會(huì)做貢獻(xiàn),是因?yàn)槲覀儫嶂杂谖覀冏约鹤晕覍?shí)現(xiàn)的需要。漸漸地,我們就把我們的熱衷從滿足自己自我實(shí)現(xiàn)的需要,轉(zhuǎn)移到了盡己所能為他人和社會(huì)做貢獻(xiàn)上來(lái)。經(jīng)過(guò)在社會(huì)實(shí)踐活動(dòng)中不斷地重復(fù)、反復(fù)地積淀,自愛(ài)的主體也逐漸地為了滿足他人和社會(huì)的需要而為他人和社會(huì)做貢獻(xiàn),那原始的滿足自我需要的動(dòng)機(jī)也不再出現(xiàn)在心中,為他人和社會(huì)的利益成為“我”的目的。
由此,我們可以看到,從滿足自我實(shí)現(xiàn)的過(guò)程中體驗(yàn)到的自愛(ài)情感可以生長(zhǎng)出為他人和社會(huì)做貢獻(xiàn)的崇高精神;以自我實(shí)現(xiàn)為出發(fā)點(diǎn),能夠把他人和社會(huì)的利益作為“我”的責(zé)任。當(dāng)“我”把他人和社會(huì)的利益作為“我”的責(zé)任時(shí),“我”的行為就有了道德的意義,因?yàn)椤拔摇钡淖晕覍?shí)現(xiàn)不再是出于自我的偏好,而是出于對(duì)他人和社會(huì)的責(zé)任。自愛(ài)的主體,最初的自我實(shí)現(xiàn)只是為了滿足自己的最高需要,但當(dāng)為他人和社會(huì)的利益由手段轉(zhuǎn)化為目的時(shí),如何為他人和社會(huì)服務(wù)就成為“我”的出發(fā)點(diǎn)和行為的準(zhǔn)則,也就是說(shuō),當(dāng)為他人和社會(huì)做貢獻(xiàn)成為“我”的行為的準(zhǔn)則時(shí),“我”的自我實(shí)現(xiàn)的行為就具有了崇高的道德價(jià)值。
“在17—18 世紀(jì)所謂的崇高,大都指的是外在事物,如宇宙的無(wú)限等等。而康德則在此之上加入了人的自身。人性自身的美麗和尊嚴(yán),就在引導(dǎo)著自己的道德生活,這本身就是崇高的體現(xiàn),它就是崇高。”[13]6在自我實(shí)現(xiàn)基礎(chǔ)上產(chǎn)生的自愛(ài)情感是崇高的,因?yàn)樵跐M足自我需要的過(guò)程中,展現(xiàn)著人性自身的美麗和尊嚴(yán)。
四、包含犧牲精神的自我實(shí)現(xiàn)是崇高的自愛(ài)
自我實(shí)現(xiàn)一般有兩種情況:第一種情況是主體以自己的職業(yè)本身為快樂(lè),在自己所從事的工作或職業(yè)既滿足了他人和社會(huì)的需要,又使自己的本質(zhì)力量通過(guò)對(duì)象性的實(shí)踐活動(dòng)順利實(shí)現(xiàn)了對(duì)象化,也可稱之為一種理想的樂(lè)業(yè)狀態(tài)。馬斯洛在對(duì)自我實(shí)現(xiàn)的人進(jìn)行考察后,他發(fā)現(xiàn)這些自我實(shí)現(xiàn)的人都是忠于自己的事業(yè),而且在自己心愛(ài)的工作中獻(xiàn)身精神非常突出。馬斯洛用“獻(xiàn)身”“使命”等詞匯來(lái)說(shuō)明自我實(shí)現(xiàn)的人身上那種激情和熱忱[14]271。馬斯洛的研究表明,在自我實(shí)現(xiàn)的人身上,貢獻(xiàn)和愉快是統(tǒng)一的,他說(shuō),在自我實(shí)現(xiàn)的人身上,“我們發(fā)現(xiàn)責(zé)任和愉快是一回事,同樣,工作和娛樂(lè)、自私和利他、個(gè)人主義和忘我無(wú)私,也是一回事”[14]176-177。
第二種情況是主體從事自己本身并不喜歡的工作,但不得不從事這份工作是因?yàn)橹黧w在追求一個(gè)崇高的目標(biāo)。比如感動(dòng)中國(guó)人物中的“暴走媽媽”式的母親,她們不是喜歡“暴走”,而是為了子女不得不選擇這種方式。他們?cè)谧鲆环N自我犧牲,但通過(guò)自我犧牲式的付出,他們能夠在子女身上看到自身人生價(jià)值的體現(xiàn),類似的例子我們可以舉出很多。自我犧牲的人在他們所從事的工作或選擇的生活中確實(shí)是在吃苦,他們選擇的不是他們喜歡的工作或他們想要的生活,無(wú)疑,是他們主動(dòng)選擇了自我犧牲。但他們所付出的犧牲是為了一種崇高的價(jià)值,是為了滿足自我實(shí)現(xiàn)的需要,因此這種自我犧牲是自愛(ài)的升華,自我犧牲的主體正是在追求著最高價(jià)值的自愛(ài)而做出的自我犧牲。
在重大疫情防控中,那些“最美逆行者”們不是喜歡冒險(xiǎn),而是通過(guò)自我犧牲的方式為社會(huì)和他人做貢獻(xiàn),以自我犧牲的方式實(shí)現(xiàn)自己的人生價(jià)值。
自我犧牲不是自討苦吃,而是為了體現(xiàn)自我更大的價(jià)值,是那種自我實(shí)現(xiàn)過(guò)程中更大的價(jià)值在吸引著他們做出自我犧牲。石里克為了論述“明顯的最大克己(seemingly-greatestrenunciation)或自我犧牲(self-sacrifice)的情況”[15]47專門舉了個(gè)例子:一個(gè)小孩子在幾塊糕點(diǎn)中進(jìn)行選擇,如果小孩子拿了最小的一塊,而把較大的糕點(diǎn)留給他的同伴,在他看來(lái),這個(gè)小孩子做出了這樣的自我犧牲,卻獲得了最大的快樂(lè),“很明顯,在其他情況下,想吃較大糕點(diǎn)的思想比想吃較小糕點(diǎn)的思想更加快樂(lè)。但是這里的情況有所不同,放棄吃大糕點(diǎn)的孩子由于他所受的教育或由于其天性,他的心中正發(fā)生著某種在其他孩子心中所沒(méi)有的事件。這些事件起作用的結(jié)果,使得互相沖突的目的原先所具有的情感色調(diào)完全改變了。”[15]46事實(shí)上,通過(guò)自我犧牲,在很大程度上使得主體增強(qiáng)了自我價(jià)值感,因?yàn)橥ㄟ^(guò)自我犧牲,“我”滿足了他人和社會(huì)的利益。而同時(shí),主體做出的這種自我犧牲也會(huì)得到他人和社會(huì)的認(rèn)可,受到他人和社會(huì)的贊賞與鼓舞,“鼓舞,這是可能影響人們命運(yùn)的最大快樂(lè)。受到某個(gè)東西的鼓舞意味著被這種思想引起的最大的歡樂(lè)所征服。一個(gè)人,當(dāng)他因?yàn)槭艿焦奈瓒幌б磺械厝椭笥眩蛉フ人擞谕纯嗪蜌缰械臅r(shí)候,他就會(huì)感到,促使他去完成這一行動(dòng)的思想使他如此深切地感到歡欣,如此強(qiáng)烈地感到快樂(lè),以致在此時(shí)此刻,保存自己生命以及避免痛苦的思想,是不可與之比擬的”[15]48-49。在石里克看來(lái),自我犧牲所獲得的快樂(lè),不是趨利避害的方式所能夠比擬的,而為了避免忍受痛苦而放棄崇高的目標(biāo),才是讓人難以接受的。
由此可見(jiàn),自我犧牲是自我實(shí)現(xiàn)的一種方式,實(shí)際上是主體對(duì)自我不同價(jià)值的權(quán)衡而做出的選擇。價(jià)值是分層次的,自我實(shí)現(xiàn)的人士為了高層次價(jià)值的實(shí)現(xiàn)而放棄了較低層次的價(jià)值。在有些情況下,他們追求的價(jià)值其崇高性甚至超過(guò)了生命本身,為了這種崇高的價(jià)值,他們?cè)敢飧冻觥⒃敢鉅奚瑢?duì)于這種自我實(shí)現(xiàn)的人所追求的“終極價(jià)值”,馬斯洛深情地論述道:“這些價(jià)值對(duì)于自我實(shí)現(xiàn)的人不是抽象的,它們是自我實(shí)現(xiàn)的人的一部分,正如他們的骨骼和血管一樣。永恒的真實(shí)、存在價(jià)值、純真和完美不斷地激勵(lì)著自我實(shí)現(xiàn)的人。”[14]257通過(guò)自我犧牲,他們放棄了低層次需要和滿足,他們不是受到了損失,而是獲得了更高程度的自愛(ài)體驗(yàn)。通過(guò)自我犧牲方式實(shí)現(xiàn)的自我價(jià)值,更能體現(xiàn)出人生的壯美,豐富著自愛(ài)主體的審美人生。
在突發(fā)性社會(huì)災(zāi)難救助過(guò)程中,那些“最美逆行者”們將自己置身于危險(xiǎn)的境地,他們沒(méi)有選擇趨利避害。在自身健康上他們犧牲了自己的安全感,他們?yōu)槿嗣竦慕】岛桶踩冻隽诵羷诤秃顾蔀槿嗣竦墨@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守護(hù)者,獲得了社會(huì)的崇高評(píng)價(jià)。同時(shí),他們也在滿足著自身的需要,但他們滿足的不是低層次的需要,他們直指最高層次的需要,即自我實(shí)現(xiàn)的需要。毋庸置疑,“愛(ài)之欲其善”的自愛(ài)情感賦予了自愛(ài)的主體在自我實(shí)現(xiàn)和人生價(jià)值上的獲得感,這種情感和精神上的魅力對(duì)一個(gè)人的人生永遠(yuǎn)具有吸引力,激勵(lì)著人永遠(yuǎn)前進(jìn),不斷地創(chuàng)造更大的人生價(jià)值。同時(shí),也為社會(huì)公眾樹(shù)立了崇高的榜樣和提供了一個(gè)正確的價(jià)值引領(lǐ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