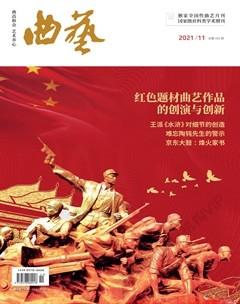“通俗”并非“媚俗”
毛巧暉
文藝的“雅”“俗”之辯古已有之。如晚明時期文藝活動中的以“俗”化“雅”,以“俗”為“雅”,是個性解放思想在文藝創作中的具體實踐。口傳的、新鮮的、生機勃勃的“俗”文學在時代發展中,凝結著民眾的共同價值、經驗、期望和理解。19、20世紀之交,隨著文學觀念的變革,民間的、通俗的文學進入了文學史的書寫。尤其在現代“民族―國家”觀念、性別意識、革命意識等不同時代話語的影響下,它成為文化普及、革命宣傳的有力工具。
從廣義上來說,一切生發于民間,散發著泥土氣息的藝術形式應可以被稱作民眾文藝。曲藝是最接地氣的藝術形式,自然也會受到“雅”“俗”之變的種種影響。
文藝的“雅”與“俗”,并無一個既定的標準可以評判,它源于民眾的生存經驗和生存智慧,并在交流與交融中不斷煥發新的生機,但這也并不意味著當下的大眾文藝發展就可以一味“媚俗”,如受經濟利益驅動,以一些“偽民俗”“惡民俗”“丑民俗”破壞民眾文藝原本的自然與淳樸。
文藝需要“俗”,這個“俗”,并非“低俗”“庸俗”“惡俗”,而是“通俗”,且這種“俗”的實踐在民族危亡之際曾經承擔著教化民眾,激發革命意識之重要作用。如延安文藝運動中民眾文藝以“極高的民眾參與度”“極深的社會影響力”逐漸成為革命動員的理想路徑。如說書藝人韓起祥創作的《張家莊祈雨》《劉巧團圓》《張玉蘭參加選舉會》等作品,譴責了迷信及傳統的買賣婚姻等陋習,提倡了婦女參與政治的權利。延安時期的“新年畫”也以“抗日”與“生產”為主題,將“麒麟送子”“加官進祿”“五子奪魁”等題材逐漸轉變為“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相結合的“做軍鞋”“學文化”“兒童勞軍”“解放軍攻城戰”等。
放眼當下,那些民眾喜聞樂見的文藝形式多“寓俗于雅”,以源自民間的勃勃生機感染世人,以人為本,以文化人。那些流行于人民大眾中間的各種曲藝形式和民間文藝形式,如快板、河南墜子、評書貫口、相聲小段、民謠、民歌、謎語、年畫、門神、剪紙等在抖音、快手、嗶哩嗶哩這樣的短視頻或直播平臺上大量出現,熱門話題的設置帶來的高度關注和情感共享極大程度地帶動民眾對文藝的關注度和參與度,從而強化人們的文化認同、共同信念等精神意識。
如今,“互聯網+文藝”成為了民眾文藝發展的“大勢”,越來越多的文藝家正在通過開設網站、微信公眾號、微博賬號、網絡直播等多樣化的方式宣傳推廣自己的作品。同時,數字化手段也對文藝工作者搶救保護文藝資料提供了更為可持續的途徑。但是其發展過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現重“術”輕“道”的現象,甚至出現“媚俗”的趨勢。這就需要我們堅持交流互鑒、開放包容,關注民眾文藝新的時代內涵和現代表達形式,回歸到文藝賴以生存的土壤中去,面向日常生活,聚焦民眾文藝的當代性。
“人民是文藝創作的源頭活水,一旦離開人民,文藝就會變成無根的浮萍、無病的呻吟、無魂的軀殼。”對于“雅”的追求,更多的是一種氣質、品格與精神,但如果過于追求“陽春白雪”,而對文藝的“人民性”熟視無睹,就會使文藝與人民大眾的關系日漸疏遠,喪失活力與生機。如傳統藝術形式總體衰落,逐年減少,傳承后繼無人。民眾文藝事象轉化創新乏力,生存空間不斷被壓縮,正在遭遇“邊緣化”危機。
民眾文藝也要在“大俗”中見“大雅”,走“雅俗共賞”之路。這就需要重視文藝的“人民性”,關注人民的主體性和創造性,堅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直面社會發展的趨勢,在尊重、繼承和弘揚傳統精神的基礎上,重塑文藝的當代性和時代性。如南音、四川清音、粵曲以及各種少數民族曲藝曲種的傳唱,剪紙、唐卡、刺繡、蠟染、木雕、泥塑等民間文藝的傳承,嫦娥奔月神話、白蛇傳故事、楊家將傳說等的傳播等。文藝在“雅”“俗”之間不斷注入新的時代精神與文化內涵,在“生成”和“互動”中呈現為一種表層生活形態與深層文化意蘊相重合的獨特審美表征。
民眾文藝是接地氣的,曲藝及各類民間文藝無不來源于民眾的日常生活。天橋底下的相聲,小橋流水間的評彈,中州大地上的鼓曲,以及泥塑、面塑、皮影、民歌等民間文藝形式,既展示了地域文化特色,更體現了時代賦予民眾文藝的精神內涵和價值理念。如2020年,曲藝工作者充分發揮曲藝藝術“短、平、快”的優勢,以《秀發》《鐘院士,百姓心中的一座山》《等你回來》等一大批抗“疫”作品鼓舞士氣,凝聚人心,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楊柳青木版年畫作品《抗擊疫情 中國必勝》,用可愛嬌憨的哪吒形象結合“抗疫”主題,發揮民間文藝凝心聚力的重要作用,表達戰“疫”必勝的信心。
民眾文藝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中華民族寶貴的精神財富。它植根于民眾的日常生活實踐,在“雅”“俗”的交流與交融及歷史與現實的傳承與超越中為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凝鑄提供了生命經驗和情感紐帶。
(作者: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文學研究所研究員)(責任編輯/馬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