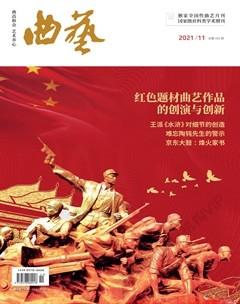書歸正傳
王聲
田連元先生所著的《評書表演藝術》出版之后,作為弟子,我近水樓臺,早早得到了一本。這是中國第一部評書藝術的高教教材,書到手后,我囫圇吞棗,先解饞再說。匆匆翻過一遍,有了個大概的印象;再細細精讀一遍,盡量一字一句都不輕易放過。怎奈知見不足,天資有限,書中精妙幽微處還是不能盡得。讓我談一談這部書,也只能是把自以為會心處記下來,略說一說我的一點淺見。
一、偉辭自鑄
我第一遍翻讀先生這部教材的時候,欣喜,甚至可以說驚喜異常。喜從何來?就是書里這些文字,字字規矩,句句老實,沒有絲毫賣弄顯擺。說句實在話,在學校的時候,讀教材對我來說,是一件苦差事。用大量的學術名詞和多重復句構成的學術化語言,實在是容易讓人眼直心亂,昏昏欲睡。而先生這部教材,一讀之下,不夸張地說,有一種身在雨后春山,大口吸氧的快意。金圣嘆說不亦快哉,此亦其一也。
不過,細細想來,做到這一點,實在不容易。
各位請想,寫成一部教材,第一步,先是掌握海量的資料。評書一道,大書如天。大書者,長篇書之謂也。在如恒河沙數的長篇書里,選出材料,或可用來厘清源頭,或可用來分析結構,或可用來示范表演。僅這一步,需時需識,尤見鑒別之力,剪裁之功。
二一步,把揀選好的材料進行分析歸納,一般來說,把總結好的內容分條列項,依次擺出,勾連彌縫,穿靴戴帽,一部高頭講章,也就算基本完成了。可是先生這部教材,又往前進了一步,難就難在這一步上。
這三一步,把這總結出來的一條一條,取意去形,從書中來,回書里去。怎么講呢?就是把從大量的書本資料中得來的東西,用評書式的語言表達出來。看似信手拈來,實則凝練傳神。咱們都知道作文章應當“我手寫我口”,真要做到這一點,何其難也。先生這一部教材,風格一以貫之,娓娓道來,如在目前。看這部教材,就好像當面聆訓的相仿,沒有絲毫接受上的障礙和困難。
不過,話雖平常,理卻不平常。洋洋灑灑一部大書真正是平中見奇,那么?奇在哪里呢?請您接著往下看。
二、現身說法
都說田連元先生的評書,不光要聽,更要看。手眼身法步,心神意念足。抬手動腳,都大有文章。我拜師之后,也多次聽先生講過評書藝術“一人多角,現身說法”的特點。一人多角好理解一些,分飾角色,一人千面。那何謂現身說法呢?請您往書中看。
“魯智深在五臺山喝醉了酒,醉打山門,大鬧五臺山。五臺山老方丈對他沒有辦法,給他寫了一封信,派他下山,到東京汴梁大相國寺投靠智清長老。花和尚魯智深,提包裹挎戒刀,肩扛著禪杖,懷揣著老住持寫的信,下山直奔東京。饑餐渴飲曉行夜住,非只一日,這天走到了桃花莊。一進這個莊子,就看見護莊河隔著洋護水。過了護莊橋,進了莊子之后才發現旁邊有個酒館。魯智深覺得有些饑餓,于是就進去吃飯喝酒,而且還想住一夜再走。”
這一段,是評書《桃花莊》的開篇。為什么教材里引用了這一段呢?因為袁闊成先生對這一部分,做了修改。怎么修改的呢?
“花和尚魯智深來到了桃花莊,肚子餓了。他一看,把著莊口這個地方有一個酒館,高挑著酒幌但是插著門。魯智深心想,怎么挑著酒幌還插著門呢?走到門前推一推,門里面插著呢。梆梆梆敲門沒人應,魯智深就問了一句,‘酒家開門來。酒家沒有搭聲,但是仔細一聽,里面好像有人哭。魯智深一聽這是怎么回事?怎么這個門不開,里面還有人哭啊?所以魯智深就漲了調門了:‘酒家,開門來,開門來。這個功夫就聽見院子里有腳步聲。腳步聲近后把門一開,里面出來個老頭,手里拿把菜刀,二話不說,照著魯智深迎面就劈過來了。魯智深拿月牙鏟往起一扛,當的一聲把菜刀給磕飛了,緊接著老頭一腦袋就撞在魯智深的肚子上。魯智深站在這一腆肚子,一動沒動。可是老頭噔噔噔倒退幾步,咕咚一下坐地上了,給來一腚蹲。”
兩篇引文之后,先生有一段評述。
“這兩個開頭是截然不同的。‘魯智深到桃花莊肚子餓了。這一句話就說明了幾個問題:魯智深是人物;桃花莊是地點;肚子餓了是事情起因;看見一個酒館插著門,這就是一個矛盾展示。之后,魯智深敲門,老頭拿菜刀劈他等接連發生的事情就引人入勝。”
先生多次跟我說過,袁老在世的時候,倆人聊天,袁老常說:“連元,咱們這評書,應該歸作協,咱這是文學創作啊。”話是玩笑,卻有深意。這兩篇引文對照,看似是說結構一部書,何處起,怎么個起法。實則還有布局謀篇的時候,怎么能把事情交代清楚的同時還不乏抓人的情節,既“過溝”,又不“松扣”。能做到這樣,就不是藝人照書背書,已經是身兼作者職能的二度創作了。
在此節講完之后,先生有一段總結:“敘事,最忌諱的是泛泛而談,怎么才能避免呢?這就需要在處理敘事過程的時候多動腦子,勤思考,多用心。在開頭、結尾和中間細節銜接的地方,都應該設想出幾個方案來,說出來之后,自己聽一聽,想一想,哪個方案最好,最后來確定采用哪個方案。這就是讓敘事保持生動和引人入勝的一個先決條件。”您看,辦法也給出來了,照計施行即可。
且住,那位說了,這也沒看見田先生現身說法啊?我以為,這才是真正的現身說法。說書時,人在角色里說表,一事將盡,說書人跳出角色評點一番,揭出意義,是為“現身說法”。連元先生是評書創作表演的大家,用自己的經典節目作為課例進行分析講授是再方便不過的了。而他把闊成先生的作品作為課例進行講授,就是把自己學習其他藝術家的方法和心得拿出來與大家分享,出技入道,詳見得失。這大概也是這部教材,與傳統教材,最不同的地方。
三、金針度人
我2018年10月2號,拜連元先生為師。拜師當天,我跟先生說,我打小聽楊家將的時候就想拜您為師,結果兜兜轉轉30年,36歲才完成了這樁心愿。等到教材出版,我看完之后,心里一陣酸,還是后來人有福,我等了30年,他們現在,買本教材就有了。
傳統曲藝的教授,講得是口傳心授,一師一徒。這個特性也決定了曲藝教學很難推廣擴大,因為一個老師的精力畢竟有限。而連元先生這部教材,基本上解決了這個問題。條分縷析,出技入道。就好像先生站在面前,掰開了揉碎了給你親自授課一般。
先是方法。在第三章第一節《評書表演要素》里,先生給出了一個敘事練習,把唐詩宋詞中自己熟知的一首詩,改成敘事文。舉出的課例是《早發白帝城》。詩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了,那么如何改呢?先從作者李白的性格特點,人物生平入手,把這首詩與他平生經歷結合,何時所寫,寫的時候李白什么歲數,什么身份,什么心境。把這些都弄明白了,詩里的“朝辭”“輕舟”“萬重山”好像都有了新的意思,有了不一樣的境界。
其次是技巧。在第三章第三節里所講的“撥口”,讓我如開茅塞。先生講“撥口”有“余興未盡”“欲罷不能”“浮想聯翩”“繼續思考”這么幾樣藝術特點,舉的課例是水滸傳第一回《高俅發跡》。書里說高俅因為踢球而高升,最后榮升太尉。首次升堂,在點名簿上發現了與自己有矛盾的人,不禁勃然大怒,到此已經是一回書了,后面兩句撥口就非常重要,有畫龍點睛之意:這才是,一個無賴登高位,千萬良善盡遭殃!
接著先生分析道:“這兩句話是概括總結這一集的內容,也包括了《水滸》這部書的點題之句:像高俅這樣一個人,靠著踢球的一技之長攀附上了端王趙佶這樣的人物。而趙佶當上皇帝之后,憑個人的好惡,把他這個昔日球友提拔為官。當聽到有人非議時,趙佶為了顯示自己的皇權不可侵犯,把高俅提拔成了更大的軍官—— 太尉。而正因高俅成了高官,才氣走了京都禁軍總教頭,林沖被逼上梁山。這兩句話點出了《水滸傳》‘亂自上做的主題。”
先生跟我講過,他在創作電視評書《楊家將》的時候,做到了每一回都能“小貓吃魚,有頭有尾”。如何做到有頭有尾呢?看完上述這段課例和分析,就明白了“撥口”不光能收束本回,引起下回,還能評點人物,突出主題。善加運用,妙用無窮。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就是書中無處不言道。先生一點不藏私,不虛飾。把自己多年總結出的經驗,散在表演要素、藝術特色、藝訣藝諺各項當中,開卷如入寶山,令人目不暇接,俯拾皆是。
這部教材的出版,讓評書普及化教育邁出了堅實的第一步,讓評書的傳承與發展有了更多的可能性。這正是,藝海長天,書歸正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