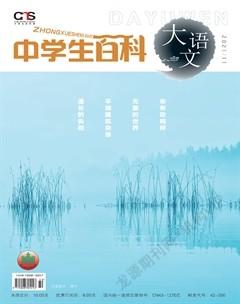給新人的跑馬經驗和個人傷病教訓(一)
目田君
作為一個(偽)跑步愛好者,我非常敬佩百公里越野跑的選手們,也很早就聽過梁晶老師的大名。常做運動尤其是戶外運動的人都知道,戶外運動有兩大殺手——失溫和中暑。據梁老師的教練說,看到梁晶老師的遺體雙膝都已經磨爛了,估計是失溫后人跌跌撞撞受傷所致,而跑友在群里發送的那一條條絕望的消息,更是讓人不忍卒讀。
看到悲劇發生,我深感4年前能完成馬拉松是何等幸運,在賽中遇到的情況和我愚蠢的舉動也讓自己后怕。除了悼念逝者、保持追責外,我想分享一些我個人的跑步、跑馬歷程,給想跑步、想參加馬拉松的同學一些經驗,也希望同學們吸取我的教訓,量力而行,健康運動。
我的跑步歷程
我從小體育很弱,小初高時的體育常年不及格。我幼年得過哮喘和慢性支氣管炎,即使跑200米都要喘半天。
我的體能比一般人弱很多——人生的前二十年我一直是接受這個設定的,但在2013年初開始了一直渴望嘗試的劍道練習,去了道館幾次后發現自己連橫舉竹刀抬手5分鐘都支撐不下去,更別談連續揮刀了。
“這樣不行。”但心里著急沒用,只能一步步訓練最基礎的運動能力。
初期我在健身房跑步機上鍛煉,目標不是跑多少公里或者1公里多少配速,而是先解決困擾我多年的一運動口里就出現血腥味的問題。
因為心肺能力太差,呼吸道的毛細血管極容易破裂,呼吸會帶血氣,很刺鼻。
大概經過2個月的平緩訓練后,我嘴里的血腥味問題好轉了很多,恰巧室友郭哥那時候受殷子大神(中文大學一位著名跑友)的感召,也在練習跑步。
在他的攛掇下,我開始了第一次路跑。
第一次路跑的路線是從逸夫書院走環徊路下山經二號橋到吐露灣,然后沿著白石角海濱長廊跑到大埔墟街市附近。
下山路太陡,跑步很傷膝蓋,所以先走下山當熱身,主要的跑步道是沿海的那段,全長大約5公里。
這里不得不提郭哥當時怕我堅持不下去,告訴我這條路2~3公里,當時我在跑步機上已經能完成4公里,心想3公里路跑應該沒問題。
結果開始跑之后,我才發現不對勁。
路跑和在跑步機上的感覺很不一樣,地面不平整,路上有障礙,跑步要轉彎,需要時刻調整步頻和留意周圍環境,同時我跟著他的速度跑,達不到他的配速,心肺負擔很重。
我中途一度想放棄,但一想3公里路跑都堅持不下來,以后怎么練習劍道。咬牙跑完了,回去拿地圖一查才發現上了當。
第一次路跑就是標準的錯誤示范,正確的是:
其一,跑步最好按照自己熟悉的配速來跑,逐步挑戰,別用別人的速度要求自己。
其二,不要為了完成跑量或逞能,超過自己的預期路程,身體很容易不適應,容易受傷甚至發生危險。
當然,第一次路跑跑完5公里也給了我很大的自信,郭哥用安慰新手的語調給我打氣,說他也是看到第一次上路就能跑完5公里的。
后續我迷上了跑步時那種身體的輕盈感和操控感,什么都不想,只是跑,或者什么都在想,繼續跑。
2013—2015年我劍道和跑步雙練并行,這兩項是我的日常修行和娛樂,持續進步時還把我從精神躁郁中拖了出來(這是另外一段故事)。
我跑了紅磡的海、科大的山、沙田的河、中大的路。10公里逐漸變成了日常訓練,并且在2015年底,我在深圳完賽了第一次半馬(21km)。
可能歸功于我兩年的基本功訓練,跑半馬沒有什么壓力,而且配速超過我的預期。從一個體育廢柴,到能完賽半馬,這個成績我還是很驕傲的。
但隱約感覺到腿腳有些問題。
我是扁平足,平時站立、走路久了會很累(所以我非常非常非常羨慕有足弓的人),跑步訓練的時候腳踝出現了一些疼痛癥狀,我認為是扁平足的問題,沒有太在意,就按照平時的護理抹一些活絡油,按摩一下就完了,最多用熱水泡腳放松——這為我的傷病埋下了伏筆。
跑完半馬,下一個目標自然是全馬了。
香港每年1—2月都有渣打馬拉松賽,因為2015年在準備深圳半馬,沒有報2016年的渣馬,所以挑戰放在了下一年,給自己充足的準備時間。
報名很順利,比賽時間是2017年2月12日,除了得到官方馬拉松大禮包外,我還從中大薅得了一件CUHK馬拉松隊的背心,心情很是激動。
在報名全馬前我還是有些猶豫,畢竟首位馬拉松跑者斐迪庇第斯跑完立撲。
但心里還是癢癢的:完成42.195公里,是什么感覺?
從上大學開始,我已經習慣于和自己搏斗了。同時也因重讀了那本很有名的《當我談跑步時我談些什么》,受了村上春樹的激勵——剛進大學的時候就翻過這本書,但那時候只是看字,真正自己開始跑步了,才明白有的感受只有跑者方能理解,有的感覺只有身體跑過才能體會。
我相信肯定還是有很多人看到甘肅越野馬拉松跑者遇難的事,心里會想這幫人閑著沒事干自討苦吃,就算不那么刻薄,也可能不太理解為什么會有人去參加這種明顯是摧殘自己、挑戰極限的比賽。
除了爭取名次和微不足道的獎金,我想很多跑者也都會被問到,也經常會自問:為什么去跑步呢?
我自己的答案很簡單:
因為路就在那里,而我在這里。
我還能跑,我想去試試。
我想知道我能跑多久。
我想看我能跑多遠。
(未完待續)
——評《休閑體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