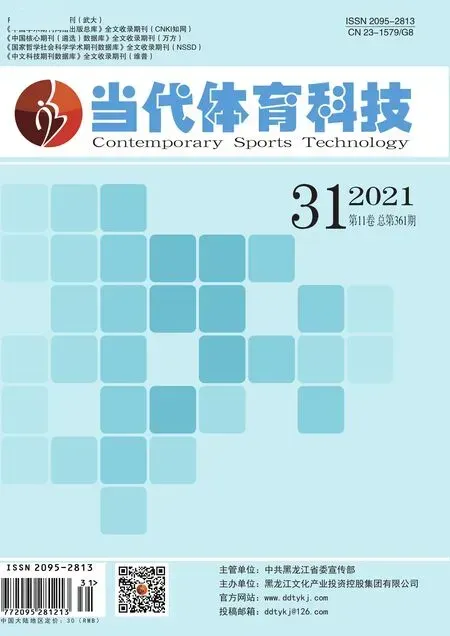德國校園足球利益群體的關系博弈及其啟示
張莉莉
(濱州職業學院 山東濱州 256603)
校園足球是中國足球人才培養的塔基,更是促進青少年身心健康、推動足球強國建設的有效抓手。截至2017年7月,教育部提前3年完成2萬所中小學特色學校、102個試點縣(區)、12個綜合改革實驗區的全國布局,校園足球普及工程取得階段性成果。然而,要想開展可持續的校園足球活動,僅靠教育系統單方面支撐是遠遠不夠的,有必要盤活學校閑置資源,整合社會資源,其中必然涉及不同利益群體的關系博弈。因此,如何處理好他們之間的關系是我國校園足球進一步發展所必須要應對的問題。大量文獻表明,德國校園足球與社會組織合作關系密切,以巴伐利亞州為例,多達406所中小學與俱樂部或基地簽署合作協議,使學生有條件在課內外接受專業教練員的指導,并有通暢的上升渠道,德國足球也因此從世紀之交的沉淪中成功復興。因此,該文試從合作博弈的視角出發,探析德國校園足球成功開展的機制,以期為我國校園足球發展提供積極的啟示。
1 德國校園足球發展歷史沿革
1.1 德國足球發軔于校園,發跡于社會(18世紀末至1990年)
18世紀末,得益于德國眾多的英語學校,足球運動傳入德國,并迅速取代德國體操成為最受歡迎的學校體育運動,隨后足球運動又從教育系統向外蔓延[1]。然而在成長初期,足球運動由于對代表德國中產階級的體操運動產生強烈的沖擊,因而在許多學校被禁止開展,體操選手Karl Planck更是將足球運動形容為“類似猴子的活動”[2]。但是,這項生命力強大的運動仍然在艱難中前行,并在1900年成立德國足球協會(DFB),以“使足球成為德國一項受尊敬的運動”為一項特定目標。建立過程的坎坷令足球協會更加注重基層足球運動的開展,加之德國工業化、城市化、生活碎片化趨勢使工人階級對足球這項激情、解壓的室外運動興趣發酵,以1954年“伯爾尼奇跡”德國世界杯奪冠為契機,德國人民對足球運動的熱情徹底釋放,逐漸形成以俱樂部為基礎的社會治理體制,足球人口迅速擴大。至1990年兩德統一前,聯邦德國足協注冊俱樂部超過2萬家,會員多達482萬人次,占總人口的6%,成為國際足聯中足球人口最多的成員協會。
1.2 德國校園足球計劃(1990—)
從歷史的視野去追溯,重視校園足球是當前德國足球走上健康發展道路的基礎認知。1990年兩德統一,足球人才培養受教育體制、社會組織磨合的影響出現明顯斷層,直接導致國家隊青黃不接、聯賽中外籍球員比例逐年遞增[3]。為此,德國足協制定了“校園足球攻勢”和“Doublepass2020”兩個校園足球計劃,因此“校園足球攻勢”對開展基礎進行全面的規劃,共分為1000個迷你足球場地的建設、學校體育教師的足球培訓、學校足球聯賽的組織、學校與俱樂部的合作、女子足球隊的建設5個部分,以培養學生對足球的興趣為主要目標,讓盡可能多的幼兒和青少年參與足球運動中。為此,德國足協在2012年出臺“Doublepass2020”計劃,要求參與的學校每周至少開設一堂足球課,由合作的俱樂部配套教練員,足協為合作提供資金、宣傳上的支持。這種模式使學校和俱樂部的聯系從課外擴展到課內,讓更多學生有機會接受專業的足球培訓。從德國校園足球計劃中可以看出,社會力量能夠彌補校園足球欠缺的師資力量,另外,業余俱樂部中有許多教練員是志愿服務的,這種文化氛圍在減少俱樂部的經營壓力的同時,為學校提供優質的服務。除此之外,俱樂部能夠改善學校醫療條件、硬件設施,也豐富了學校體育活動的外延,因此,明確社會、學校互動發展的相關利益群體,并厘清他們之間的關系將有助于理解德國校園足球成功開展的內在邏輯。
2 德國校園足球關聯的利益群體構成
利益相關者指任何可以影響組織目標或被該目標影響的群體或個人。“Doublepass2020”計劃所推行的社區俱樂部與學校間合作模式是德國足球協會在既有利益沖突下的積極回應,以及利益各方博弈的結果。顯然,學校和社區俱樂部的合作意向直接影響計劃目標的實現,合作結果又同時作用于多個利益群體,因此,德國校園足球關聯的利益群體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一是中小學校和幼兒園。得益于德國12年義務教育體制,每一個孩子都有機會接受幼兒教育和中小學教育,學校自然成為孩子成長過程中主要的活動場所和關鍵的利益訴求方。這種訴求主要體現在德國素質教育的發展目標以及終身鍛煉的宗旨上,這要求體育充分發揮其教育功能,而學校的體育教育資源遠遠達不到素質教育的要求,為社會足球走進校園創造了條件。
二是社區俱樂部。首先,德國社區俱樂部的性質是非營利性社會組織,其目標是讓盡可能多的人群參與體育運動,組織行為學強調,組織行為由組織形態及目標決定,因此社區俱樂部有積極性去吸納青少年群體,比如德國社區俱樂部推行成年人和青少年的差異定價,針對青少年會員僅收取成年人1/3的會費。然而從實施效果來看,仍然有許多青少年沒有參加課外體育活動,這使得校園內開展的體育活動具有更重要的意義。其次,社區俱樂部與學校相比處于缺少資源的一方,從博弈論的角度分析,缺少資源的一方往往處于“智豬模型”中搭便車的“小豬”角色,難以成為合作的推動者[4]。這就要求一個全新的第三方出現以促進學校和俱樂部間的合作。
三是足球協會。德國足球協會成為第三方出現的必然性體現在3個方面:(1)德國足球協會兼具普及和提高兩方面目標,普及是足球發展的邏輯起點,從課外延伸至課內的足球參與有助于擴大德國足球人才培養的“量”;(2)提高是足球發展的必然要求,只有形成高水平運動員到高水平聯賽,再到增加足協收入、增加青少年足球投入的良性循環,足球才能形成內生性發展,因此從校內足球課程的專業性出發有助于提升德國足球人才培養的“質”;(3)德國足球在2010年后受應試教育的沖擊,學生群體中放棄課外足球訓練的人數劇增,必然伴隨青少年體質下降等問題,迫使足球協會設法將足球推向校園內;(4)從德國足球發展歷程可以看出,歷經低迷的德國足球國家隊亟需成績來重振形象,具有時代迫切性。
四是政府。“足球是和平時期的戰爭”,足球往往代表著國家形象和文化,德國人對于足球的關注和熱愛更是凸顯其重要的社會價值。顯然,德國政府和足協,一個作為政策的制定者,一個作為政策的執行者,都是有動機促成合作的第三方,因此可以歸為一類。
3 德國校園足球相關利益群體的博弈分析
公共服務和市場服務的交叉領域常常權責不清晰,因此存在許多短板[5]。學校和社區俱樂部的合作恰好屬于這種情況,足球教育的供給不可避免伴隨社區俱樂部對學校資源的索取,容易造成市場缺乏動力、政府沒有改革需求,因此雙方往往難以形成合作。
假設不存在第三方組織介入,學校的成本為文化課導致學習滯后、學校安全問題、學校足球場地使用權、與俱樂部溝通的交易成本,收益為體育活動外延擴展、專業足球師資提供、足球配套服務完善、體育教師足球教學拓展;俱樂部的成本為師資力量薪酬、交通成本、管理成本、與學校溝通的交易成本,收益為學生會員的加入、拓展教練員的教學方法、俱樂部實力提升、學校足球場地使用權。學校往往是俱樂部爭取人才和體現社會責任的主要對象,學校出于對學生多元教育目標的考量也希望突破校園邊界,加強與社會組織的合作,然而雙方在尋找合作伙伴、促成合作協議中會產生大量交易成本。預期收益的高低決定了合作能否達成[6]。在此博弈中,博弈模型的參與人是學校和俱樂部。假定學校得到的足球教育資源(即學校收益)為E,代表體育教育目標占學校教育總目標的重要性系數為I,俱樂部可能帶來的安全風險為R,學校交易成本為C1,俱樂部交易成本為C2,學生會員加入所增加的收入為S,俱樂部多付出的人員成本為T。那么學校選擇合作的支付為E·I-R-C1,選擇不合作則支付為A;俱樂部選擇合作的支付為S-T-C2,選擇不合作則支付為P,雙方的支付矩陣如表1。

表1 學校與俱樂部合作博弈
當E·I-R-C1≥0時,學校選擇合作,可以發現,現實中學校不選擇合作的主要原因有兩點:(1)I偏小,體育教育不受學校重視,因此學校不愿意付出成本促成合作,場地資源使用權的歸屬也會影響既得利益者;(2)R的存在,R的大小取決于風險發生概率及不利影響的大小,由于安全風險導致的后果嚴重,學校本身又是保守的風險偏好者,即使風險發生概率只有0.01%,學校也可能不會選擇合作。當S-T-C2≥0時,俱樂部選擇合作,雖然俱樂部性質為社會組織,但校園足球不是俱樂部責任的情況下,經濟動因仍然是合作開展的必要條件。
雙方博弈中選擇合作的一方存在對方不合作的風險,需要支付交易成本,因此只有雙方條件同時滿足的情況下合作才會發生。在這種情況下,德國足協為雙方提供資金及宣傳上的支持,使博弈方選擇(合作,合作)策略并成功實踐。假定德國足協為學校和俱樂部提供的資金支持分別為F1和F2,宣傳支持為D,那么學校和俱樂部選擇合作的支付分別增加至E·I+F1+DR-C1和S+F2+D-T-C2,雙方的支付矩陣如表2所示。

表2 德國足協支持下的學校與俱樂部合作博弈
從實施效果來看,顯然E·I+F1+D-R-C1≥0且S+F2+D-T-C2≥0,宣傳上的支持和政策效應使學校獲得知名度和美譽度提升的同時促進生源,有助于達成學校的教育目標,資金支持則幫助俱樂部分擔業務拓展的經營成本壓力,因此德國足協的介入促使博弈雙方預期收益提高,從而達到納什均衡。
從成本收益的角度分析計劃實施的必然性,資金支出由德國足協和聯邦健康教育中心(BfGA)共同承擔,阿迪達斯贊助實物,足協結合BfGA的形象強調足球教育兒童和青少年的價值觀和超越體育教育的社交技能,BfGA則完成相應的體育教育目標,阿迪達斯給予學生實物的同時培養他們的品牌認知,最重要的是計劃培育大量足球人口,使整個德國足球受益。
4 德國校園足球關系博弈的啟示
4.1 三者之間的目的價值取向
學校、俱樂部、足協是德國校園足球相關的三方利益群體,學校以學生身心健康成長為主要目標,俱樂部有普及足球運動的社會責任,同時存在經營壓力,足協兼具足球運動普及與提高的社會責任。學校需要俱樂部的師資力量豐富學生教育內涵和足協的宣傳提升學校美譽度;俱樂部需要學校的生源增加俱樂部收入和足協的資金支持;足協需要俱樂部輸送專業足球人才,也需要學校培育潛在足球人口。
從上述需求關系可以看到,三者之間相互依存,有各自利益的同時必然存在共同利益促成合作,因此有必要明確德國校園足球誰來獲益。顯然,學生是校園足球的主體,也是三者共同的出發點。足協在培養學生身心健康的基礎上也存在選材的目的,俱樂部學校同樣需要學生會員的收入維持經營,柏林SV Empor俱樂部的體育競技總監Carsten Maa?認為與學校合作是俱樂部爭取學生會員的好方法,學校則重視足球團隊協作中體現出的多元價值。
4.2 德國足協作為第三方激勵合作行為
在德國足協介入學校、俱樂部合作前,雙方合作行為較少,以巴伐利亞州為例,合作的足球俱樂部和學校從2007/2008學期的164組增長至2016/2017學期的406組,全國大約18%的俱樂部與全日制學校合作,并呈上升趨勢,說明“Doublepass2020”計劃激勵了合作行為,激勵的方式分為物質激勵和精神激勵,一方面德國足協為合作提供資金支持,另一方面德國足協的宣傳使社會形成熱愛足球的文化氛圍,進一步促使學校和俱樂部有意愿與對方合作,因此第三方的激勵行為是促使社會與學校融合的重要途徑[7]。在合作過程中,德國足協只提供服務,具體合同范圍等方面均由雙方協商決定,州政府則建立相應的配套服務,例如巴伐利亞州學校體育辦公室專門成立了sport-nach-1機構,以幫助資金落實和協調工作。
4.3 專業的教練員體系
從博弈模型中可以看出,足球教育資源的實力是影響學校選擇與俱樂部合作的關鍵因素。德國作為世界上教練員體系最完善的國家,擁有1070名職業教練員、5500名A級教練員以及數以萬計針對青少年和兒童的E、F級教練員,他們大量服務于社區俱樂部中,在發掘學員潛力、培養對足球興趣等方面的作用不可替代,正因如此,學校考量學生多元培養目標時會選擇俱樂部的足球教育資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