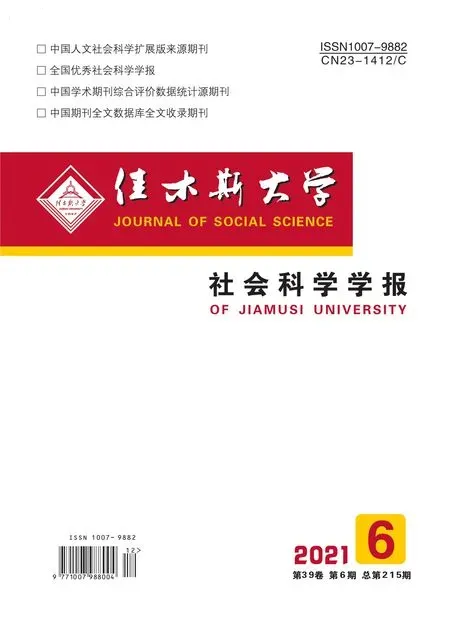杜爾伯特蒙古族音樂類非遺的傳統與變遷*
杜 洋
(東北石油大學 藝術學院,黑龍江 大慶 163318)
社會發展、文化置入、民俗意味,總是伴隨于杜爾伯特蒙古族人民的生活之中,賦予生活于杜爾伯特蒙古族自治區的每一個個體生命及族群生命以不同程度的關懷與眷顧。作為杜爾伯特蒙古族自治區重要的非遺存在,代表性音樂類非物質文化遺產早已深深涵化于杜爾伯特蒙古族文化生成與延續當中。杜爾伯特蒙古族音樂類非遺,是蒙古族文化的具體呈現,是我國少數民族音樂寶庫中民間傳統藝術的沉淀,更是傳統文化變遷中民間藝術不斷生長的支撐。深入認知杜爾伯特蒙古族音樂類非遺,不僅說明了其研究意義的闡釋,亦明確了其現存的生存態勢,是為杜爾伯特蒙古族后代給予深層族群認同感的“高級”方式。
一、有關杜爾伯特蒙古族音樂類非遺的相關敘述
杜爾伯特蒙古族自治縣,多年來一直以突出民族文化特色為重點,以深化民族藝術體制為發展動力,在音樂藝術的創新與傳承方面始終堅持傳統與變遷中不斷融合的構建方式。杜爾伯特蒙古族自治縣在多年來藝術遺產的保護工作中,大力強調極富本土特色的音樂類遺產,杜爾伯特蒙古族音樂類非遺給予當地人們以不同程度的肯定,是人們茶余飯后文藝生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杜爾伯特蒙古族是我國北方少數民族中的一個重要分支,其音樂類非遺所屬中國傳統音樂概念內的少數民族音樂體系。傳統化體系中的杜爾伯特蒙古族音樂體系包容于東方音樂體系框架之內,調式音階屬中國傳統五聲調式。在調式安排上,主要以羽調式為主,其次調式常用的是徵調式,角調式和其他調式偶爾也會使用,但是較為少見。蒙古族音樂旋律有其自身的代表性特點,均是以級進為主,在音程的跨度上經常出現四五度跳進,甚至六度、七度、八度以上大跳也很常見。[1]可見,杜爾伯特蒙古族音樂形態自由且可延伸發展,音樂旋律中總是透著某種“單純性”。
杜爾伯特蒙古族音樂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之歷史溯源并不十分久遠,在遺產生成、延續過程中,其發酵卻是實實在在存在的。陳毓博、任廣明的《杜爾伯特蒙古族音樂文化研究綜述》中,“通過對杜爾伯特蒙古族音樂文化相關文獻的匯總,從儀式音樂、民歌、曲藝、器樂和音樂文化融合幾個方面整理出對杜蒙蒙古族音樂文化研究的幾個要點和相關文獻的若干內容”[2],側重于對杜爾伯特蒙古族音樂文化的整體敘述。邵萱的《杜爾伯特蒙古族民間音樂調查研究》一文中,在內容安排上主要側重于對杜爾伯特蒙古族民間音樂文化的田野考察研究,通過分析杜爾伯特蒙古族音樂及其與生存環境之間的共融關系,分析杜爾伯特蒙古族音樂。[3]趙月梅的《黑龍江省杜爾伯特地區的“蒙古四胡”藝術》,以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蒙古四胡”的國家級代表性傳承人包杰作為研究切入點,分析“蒙古四胡”所生存的藝術現狀,對杜爾伯特蒙古族國家級非遺“蒙古四胡”目前所存在的問題及今后的保護對策進行了闡釋。[4]除此之外,劉喜寶、王鑫的《弘揚民族文化,促進經濟社會全面協調發展——關于杜爾伯特蒙古族自治縣民族文化建設的調查》一文中,介紹了杜爾伯特蒙古族自治縣民族文化建設的整體情況,為有關杜爾伯特蒙古族非遺的生成與發展給予了有力的文化背景,為弘揚及發展所屬杜爾伯特蒙古族自治縣的民族文化給出了三點建議。[5]
參考相關杜爾伯特蒙古族音樂類非遺的探討脈絡,相關資料中的論及方向并非從非遺的角度進行考慮,在有關杜爾伯特蒙古族音樂類非遺的涉入性提及中,多是對其音樂文化的總體綜述,可見有關杜爾伯特蒙古族音樂類非遺的研究只是這一區域內音樂文化大框架范疇內的潛在性涉及,可謂是簡單而“淺層”的探討。因此,本文將跳出原有研究范疇,以一種較明確的形式對杜爾伯特蒙古族代表性音樂類非物質文化遺產融入深度考量,遺產內容中不僅有杜爾伯特蒙古族自治縣的國家級代表性音樂類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還有所屬杜爾伯特蒙古族自治縣的黑龍江省省級代表性音樂類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及大慶市市級音樂類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明確杜爾伯特蒙古族音樂類國家級、省級、市級非遺項目,透過其變遷明確其留存,在社會變遷、文化變遷、民俗變遷背景中對其進行描述,以思量其傳統范圍內的認同應在哪些“外力”的助推下才能夠得以延續。
二、游走于民間的杜爾伯特蒙古族音樂類非遺
(一)代表性國家級音樂類非遺項目
2008年3月,杜爾伯特“蒙古族四胡音樂”被批準為黑龍江省第一批省級非遺名錄,6月,入選第二批國家級非遺名錄。2008年6月,杜爾伯特蒙古族自治縣江灣鄉永豐村包杰被評為第一批黑龍江省省級非遺項目“蒙古族四胡音樂”代表性傳承人。2018年,包杰“升級”為“蒙古族四胡音樂”的代表性國家級傳承人。在杜爾伯特地區,早于元代就已有“蒙古四胡”的出現,“蒙古四胡音樂”在漫長的杜爾伯特歷史發展過程中始終堅持著傳統的變遷與變遷后的創新,杜爾伯特“蒙古族四胡音樂”以其鮮明的民族特色與區域風格在豐富多彩的少數民族文化中獨樹一幟。
杜爾伯特蒙古族四胡是杜爾伯特蒙古族地區所特有的弓弦樂器,別名“胡日”“四弦”“侯勒”和“胡兒”,是杜爾伯特蒙古族自治縣每個個體與族群之間較常見的樂器,幾乎家家戶戶都有一把四胡,屬于蒙古族的特色樂器之一,現如今已成功被列入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之中。杜爾伯特蒙古族四胡音樂,主要反映了居住于杜爾伯特蒙古族自治縣牧民們的生活形態,展現了杜爾伯特蒙古民族音樂特有的藝術韻味,蒙古族四胡主要有高音四胡、中音四胡和低音四胡之分。杜爾伯特蒙古族四胡音樂的演奏者熟練操作四胡,具有深厚的藝術文化感知力、理解力和創造力,對音樂具有超高的情感共鳴。不同的演奏者,往往對曲子的理解力截然不同,鑒于演奏形式之不同,觀眾往往感受到的音色必然存在某種差異。杜爾伯特蒙古族低音四胡常用被用于伴奏蒙古族演唱及好來寶,音色柔美和諧,且深沉動聽,代表性曲目有《八音》《八音梆子》《趕路》等。杜爾伯特蒙古族中音四胡不同于低音四胡,音色更加圓潤且清爽明亮,不僅可以用來伴奏,也可用于獨奏,常與高音四胡、馬頭琴等樂器進行合作演奏,代表作品有《阿斯爾》《老八板》和《蒙古八音》等。杜爾伯特蒙古族高音四胡音色清脆,音量較大,主要用于獨奏、重奏和合奏等形式,代表作品有《花腰調》《諾恩吉雅》《歡樂的草原》等。
(二)代表性省級音樂類非遺項目
杜爾伯特蒙古族民歌,經黑龍江省人民政府于2009年6月正式批準被列入黑龍江省省級非遺代表性項目。2011年,包文章被評為杜爾伯特蒙古族民歌的代表性傳承人。楊振軍,作為大慶市杜爾伯特蒙古族自治縣縣文化館副館長,多年來一直系統的學習蒙古族長調音樂和短調音樂,在蒙古族民歌的演唱方面始終堅持著自己特有的演唱風格。包文章及楊振軍,在杜爾伯特蒙古族民歌的音樂中滲透著蒙古族元素,二人堅持著對蒙古族民歌的熱愛與瞻仰,以“口傳心授”的方式將杜爾伯特蒙古族民歌以最積極的熱忱在進行著遺產的傳承與延續。
杜爾伯特蒙古族民歌現已成功被列入黑龍江省省級非遺項目之一,以其獨特的演唱方式與極具民族特色的樂器相結合充斥著濃厚的蒙古族草原化氣息。杜爾伯特人民根據其所居住的社會環境不斷地與區域文化加以交流并整合,最后形成了濃厚鮮明特色的杜爾伯特蒙古族民歌音樂。取材范圍廣泛,格調氛圍雄渾,杜爾伯特蒙古族民歌一般分為“長調”和“短調”。杜爾伯特蒙古族長調,篇幅較長,氣息寬廣,情感沉郁,具有獨特而細膩的顫音式表達。而杜爾伯特蒙古族短調則篇幅較小,曲調緊湊,節奏和節拍相對限定化,歌詞簡單,更像是一種即興歌唱,演唱具有一定程度上的靈活性。杜爾伯特蒙古族民歌聲音洪亮深沉,曲調高亢悠揚,充分展示了杜爾伯特蒙古族人民開朗爽快的性格。杜爾伯特蒙古族民歌創作主要來源于日常生活、愛情友誼、山川草地等體裁內容,較為著名的杜爾伯特蒙古族民歌有《桑塞瑪》《遼闊的草原》《牧歌》等優美動聽的代表性作品。杜爾伯特蒙古族民歌以當地民間文化內容作為創作題材,較為真實地描繪了杜爾伯特蒙古族人民的風俗生活以及對家鄉的熱愛之情。早于1987年,便出版了流行于杜爾伯特蒙古族自治區民歌的《杜爾伯特蒙古族傳統民歌集》,其中收錄了民歌共計96首,涵蓋內容較廣,包括宗教習俗、婚喪嫁娶、祝酒宴會、勞工生活、思鄉念親、歌頌英雄等內容,構成了杜爾伯特蒙古族優美的民歌文化。
(三)代表性市級音樂類非遺項目
2018年,經大慶市市政府批準,大慶市文廣局確定,大慶市非遺專家評議小組、專家評審委員會審議并通過了有關第五批大慶市市級非遺名錄共計17項。傳統音樂類項目兩項,其中一項為蒙古族“馬頭琴音樂”。杜爾伯特蒙古族“馬頭琴音樂”作為入選市級非遺傳承項目,代表性傳承人包洪聲(蒙古名阿斯汗),就職于大慶市杜爾伯特蒙古族自治縣歌舞團,黑龍江省省級馬頭琴代表性傳承人,中國第五代馬頭琴代表性傳承人。白青山(蒙古名阿古拉),杜爾伯特蒙古族馬頭琴音樂青年演奏家,現就職于杜爾伯特蒙古族歌舞團,馬頭琴首席。
杜爾伯特蒙古族市級非遺項目馬頭琴是一種兩弦樂器,梯形長琴身,馬頭形狀雕刻的琴柄,根據這一特色被稱為“馬頭琴”,別名“潮爾”。馬頭琴與四胡在杜爾伯特蒙古族人民心中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馬頭琴與四胡的發展軌跡與流行范圍幾近相同,同屬于杜爾伯特蒙古族音樂類非遺的樂器項目。二者亦有區別,首先是具有不同的外形結構,音色自然存在著一定的明顯差異性。馬頭琴具有聲音圓潤,低音蕩氣回腸,音量弱的特點,演奏的曲目通常是氣韻粗狂而寬廣的。馬頭琴音樂在杜爾伯特蒙古族是區域音樂特色的彰顯,經世代演變與傳習,馬頭琴音樂已建構了屬于本土特色的演奏方式,且逐漸有了屬于杜爾伯特蒙古族自治縣的一套系統演奏法。馬頭琴音樂擅長演奏杜爾伯特蒙古族長調音樂,馬頭琴的傳統樂曲大部分是根據草原生活的蒙古族民歌改編而成的,以反映蒙古族牧民的生活情景及生活環境,具有強烈的感染力,深受杜爾伯特乃至全國人們的喜愛。杜爾伯特蒙古族馬頭琴音樂的演奏方式主要分為獨奏、伴奏、重奏及合奏,演奏形式較為多樣化。在現代文化的變遷與沖擊下,傳統的杜爾伯特蒙古族馬頭琴音樂演奏在維系傳統內容的基礎上,逐漸融匯了現代音樂形式、音樂類型,創作方式更加多樣化、豐富化。杜爾伯特蒙古族馬頭琴音樂著名的代表作品:《水靈》《八音》《歡樂的牧場》《秋雁》《烏利格爾敘事》等。除此之外,還有包洪聲(阿斯汗)與多蘭桌格共同以黑龍江扎龍境內的珰奈濕地為創作背景,基于回歸濕地大自然美的意蘊,融合當地的民間傳說與神話故事,創作了馬頭琴曲《女神湖》。
三、變遷中的杜爾伯特蒙古族音樂類非遺
杜爾伯特蒙古族自治縣是黑龍江省唯一的少數民族自治縣,有蒙古族、漢族、滿族、回族等21個民族,其中蒙古族人口占總人口的18.2%。不同的《蒙古秘史》以不同的形式記載著關于杜爾伯特蒙古族的遷徙史記,早見于年成書的「蒙古」策·達姆丁蘇榮蒙文本《蒙古秘史》稱“都蛙鎖豁兒有四子,都蛙鎖豁兒死后,其四子對朵奔蔑兒干不以親叔來看待,棄而遷之,成為杜爾伯特氏。”巴雅爾蒙漢合壁卷本《蒙古秘史》記為“朵奔蔑兒干的哥哥都蛙鎖豁兒有四子,同住的中間,都蛙鎖豁兒死了。他的四個孩子,將叔叔朵奔蔑兒干不做叔叔般看待,撇下了他,自分離去了,做了朵兒邊姓。”[6]在蒙語里,杜爾伯特意譯為“四”,成吉思汗的十二世祖道布莫爾根之兄道蛙鎖豁兒有四個兒子,因此被稱為杜爾伯特氏,世代傳承。
黑龍江省大慶市杜爾伯特蒙古族自治縣,是黑龍江省唯一一個以少數民族蒙古族為主體的自治縣。杜爾伯特蒙古族歷史悠久,清初時期,清順治五年,將杜爾伯特部改為杜爾伯特旗,隸屬哲里木盟,此時期隸屬于黑龍江省管轄;民國時期,1927年設置泰康設治局,1946年4月,旗和縣分設,泰康縣政府駐泰康鎮,同年5月,改由嫩江省管轄,1949年5月,撤銷嫩江省,劃歸為黑龍江省管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期,1954年8月,改屬新設之嫩江專區,到1992年8月21日,杜爾伯特蒙古族劃歸為大慶市領導,是清代衛拉特蒙古四部之一,由額爾齊斯河畔遷徙布多北境,當前已遷徙到黑龍江省杜爾伯特蒙古族自治縣。2001年后,杜爾伯特蒙古族自治縣包含4鎮、7鄉。現今杜爾伯特蒙古族自治縣在黑龍江省的西部,北鄰林甸縣與齊齊哈爾接壤處,東靠大慶市,南臨肇源縣,總面積高達6054平方千米。在歷史長河的推進中,歷史變遷,所屬杜爾伯特蒙古族的音樂類非遺在歷史進程中生成、發展,不斷尋找著未來可得以認可的某種延續。歷史變遷的推動,使杜爾伯特蒙古族音樂類非遺在歷史長河中分散且留存。
秦漢時期,漢族人民向黑龍江省遷徙,黑龍江地區有了漢族文化,與中原進行頻繁的人文交流。清王朝時期,大量人民被驅逐黑龍江流域這種極寒冷的荒地地帶,眾多人們為了生計開始狩獵、淘金等活動,并以此謀生。時至清末,更多流民例如像來自于河南省、山東省、山西省等地的人民闖關東遷徙到了黑龍江省流域,漢族人民的遷入,使得蒙漢兩族之間在物質文化、生活方式、音樂舞蹈等方面開始相互結合,為黑龍江省流域杜爾伯特蒙古族音樂文化的形成給予了充分的參考。越來越多的漢族人民遷徙至黑龍江省流域,原本只是使用蒙古語言的杜爾伯特蒙古族人民,在漢族人民的同質下使得漢語對杜爾伯特蒙古族人民產生了重要影響,蒙古族人們的音樂依賴于語言文化,漢語勢必對杜爾伯特蒙古族的音樂類型產生了較大范圍內的交融和影響,逐漸產生了蒙漢兩種語言交叉演唱的形式,即“風攪雪”的藝術形式,例如在杜爾伯特蒙古族民歌《劃拳》中便是如此。由此可見,傳統文化形式已無法滿足蒙漢民族的融合,文化形式在變遷中總是尋求某種中和,杜爾伯特蒙古族音樂文化的變遷是隨著文化環境的某種遷移而逐步完善的。文化的變遷,同化了杜爾伯特蒙古族音樂類非遺的存在。
歷史變遷、文化變遷,無不使得杜爾伯特蒙古族音樂類非遺在不斷的“漢化”邊緣中危險地存活著。杜爾伯特蒙古族人民在生活中總是將音樂藝術放置于較高的位置,不管是從樂器的角度考慮,還是民歌的角度涉及,音樂藝術總是伴隨著杜爾伯特蒙古族人民的生產生活。然而,在“漢化”影響下,使得杜爾伯特蒙古族音樂類非遺項目出現了“走樣”和“變味”的傾向。以大慶市杜爾伯特蒙古族音樂類非遺代表性國家級項目“蒙古四胡音樂”為例,國家級傳承人包杰作為一位樸實本分的農民,其所有的工作重心還是農間耕作,因此在遺產的保護與傳承工作上難以給予充分的考慮和思量。在不同民族的融合下,語言環境、民俗環境、教育環境皆發生了質的變化,杜爾伯特蒙古族的音樂類遺產在嚴重喪失母語的環境下,受眾環境的積極性并不樂觀。
四、對杜爾伯特蒙古族音樂類非遺未來發展的思考
根據上述所論,人們的交通工具越發便利,人口流動更為頻繁,整個社會的個體與群體間相互流動廣泛,杜爾伯特各民族或者族群之間開始學習漢語,這在促進區域文化發展的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杜爾伯特蒙古族的文化特性,使得杜爾伯特蒙語的使用環境氛圍逐漸降低。那么,對于杜爾伯特蒙古族人們來講,講蒙古語進行交流的機會大大減少,依賴于蒙語的杜爾伯特蒙古族音樂勢必會收到重大創傷,在某種程度上面臨著技藝失傳的危險,甚至有些音樂技藝已經在悄無聲息中離開了人們的視域。因此,國家范圍、社會范圍、民間組織、教育范疇當前皆應對杜爾伯特蒙古族音樂類非遺的未來發展問題加以重視,并采取相應措施為保護中華民族留存于人們的共同的人類財富做出積極努力。
首先,國家范圍不僅要在相關法律范疇內為杜爾伯特蒙古族音樂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保駕護航,而且還要做到“快準狠”,發揮一切可調動的力量積極尋找杜爾伯特蒙古族音樂類非遺的可傳之人,在保證傳承人家庭溫飽的基礎上,對傳人給予某種激勵機制,提供精神獎勵與物質獎勵,倡導更多的人加入到保護杜爾伯特蒙古族音樂類非遺的活動中來。現今,杜爾伯特蒙古族文化傳承積極性較低,包括蒙古族本族人民,對漢語的學習激情高漲,所以十分容易忽略蒙語的魅力與特色。國家層面,可在廣播電視、影視廣告中普及蒙古族音樂,以便于更多人能夠接觸到獨具少數民族地域特色的杜爾伯特蒙古族音樂類非遺。促進非遺文化與本土經濟建設相結合,充分利用經濟勢頭為杜爾伯特蒙古族音樂類非遺帶來的優勢,設置相關杜爾伯特蒙古族音樂文化播放劇場等,以獨特的音樂表現形式演繹杜爾伯特蒙古族的特色文化、民俗風情、人文情懷、音樂技藝等。
其次,對于社會范圍來說,在杜爾伯特蒙古族自治縣區域內推動民間文化、文藝活動是廣泛宣傳杜爾伯特蒙古族音樂類非遺的一項重要舉措。社會中的個體、群體等應積極搜集杜爾伯特蒙古族音樂類非遺的相關文物、可參考資料,合理有序的進行相關社會活動的安排。強調杜爾伯特蒙古族區域社會文化活動,有助于提升廣大人民群眾對杜爾伯特蒙古族音樂類非遺的社會需求和娛樂需求,形成相對穩定的文化產業以擴大本土文化的社會傳播范圍。同時,社會層面應設立杜爾伯特蒙古族自治縣公益非遺協會,以促進杜爾伯特蒙古族音樂類非遺的全面發展與保護。社會組織可建立相關社團,不同的參與人員應具有不同的工作分工,不僅要深入探究杜爾伯特蒙古族音樂非遺的相關文化、史記等整合內容的問題,還應深入學習杜爾伯特蒙古族音樂,培養越來越多的社會人士精通杜爾伯特蒙古族樂器和樂理,定期開展相關民歌演唱活動,在社會范圍的協助下擴大主動學習杜爾伯特蒙古族音樂類非遺人口總數。
另外,重視民間組織對于杜爾伯特蒙古族音樂類非遺的重要作用顯得十分重要。其中的民間組織包括一些非政府組織、社會群體或者由人民自由組織起來的一系列群體民間組織。杜爾伯特蒙古族非物質文化遺產源自于民間,且扎根于民間而生存,對民間組織來講,給予非遺于充分的保護是其自身使命與責任感的體現。民間組織應精心設計排練音樂類非遺項目的相關民俗活動、音樂演奏,精湛的技藝表現能夠充分感染杜爾伯特蒙古族群眾們保護遺產的情緒與心情。充分調動普通百姓參與拯救杜爾伯特蒙古族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積極性,喚醒普通大眾對稀缺音樂類文化遺產的興趣,營造濃厚的藝術遺產氛圍,使杜爾伯特蒙古族音樂遺產技藝得以發揚。杜爾伯特蒙古族音樂類非遺是杜爾伯特蒙古族人們共同創造的精神財富,為使民間技藝能夠永久留存,民間組織應緊跟國家保護非遺相關政策,通過引導社會大眾進行搶救與保護,確保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與繼承工作得以順利開展。
最后,從教育范疇考慮,最直接的方式是在學校范圍內開展杜爾伯特蒙古族音樂文化相關涉入活動。如此,既可以通過教育手段普及杜爾伯特蒙古族音樂文化內容,又完善了在學校范圍內對這類遺產的音樂教育活動。只有學生對少數民族優秀非物質文化遺產有了潛在認識和深層接觸,才可以更好的傳播、繼承和創新杜爾伯特蒙古族音樂類非物質文化遺產。當前,杜爾伯特蒙古族文化并沒有廣泛普及,存在分布不均衡的傳承現實。因此,可以通過在學校舉辦蒙古族文化歌舞比賽、器樂競賽等活動,以激發校園內教師與學生對相關領域的求知欲望和參賽信念。杜爾伯特蒙古族音樂類非遺傳承人才培養是推進杜爾伯特蒙古族音樂非遺傳承工作的直接方法,加大遺產教育力度,改變傳統音樂文化的固有認知,產生學生們對杜爾伯特蒙古族音樂文化內涵的深刻解讀,用科學直觀而系統的視角審視杜爾伯特蒙古族音樂類非遺。杜爾伯特蒙古族音樂類非遺民間傳承藝人可以走進校園,以“教育者”的身份搶救杜爾伯特蒙古族音樂類非遺是每位遺產傳承人的責任。
五、結語
在杜爾伯特蒙古族自治縣這片秀麗而古老的土地上,蒙古族音樂文化于民間禮俗中浸潤且遍布。盡管傳統的杜爾伯特蒙古族音樂文化在“漢化”的涉入下已褪去原有鎧甲,但杜爾伯特蒙古族音樂類非遺仍始終貫穿于杜爾伯特人民的衣食住行、價值觀念、審美趣味、習俗風尚當中。對于人類瑰寶之一的杜爾伯特蒙古族音樂類非遺,不單純應依靠國家、社會、民間組織等單方面的努力,而是應該團結所有能夠團結在一起的力量去共同維護杜爾伯特蒙古族音樂類非遺,給杜爾伯特蒙古族音樂類非遺帶來鮮活的生命活力,在和平美好的時代里,使其經久不衰且綻放無限魅力。杜爾伯特蒙古族音樂類非遺在歲月的洗禮中,綻放其濃郁的蒙古韻味,匯聚了蒙古族的民族氣息,承載著豐厚的文化底蘊。保護杜爾伯特蒙古族音樂類非遺,全社會皆應形成共同認識,用行動去拯救。追蹤杜爾伯特蒙古族音樂類非遺,可以跨越已有研究成果,在已有相關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加以重新認知,思考變遷之后杜爾伯特蒙古族音樂類非遺的未來發展之路,以便于今后有關本論題的相關探討和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