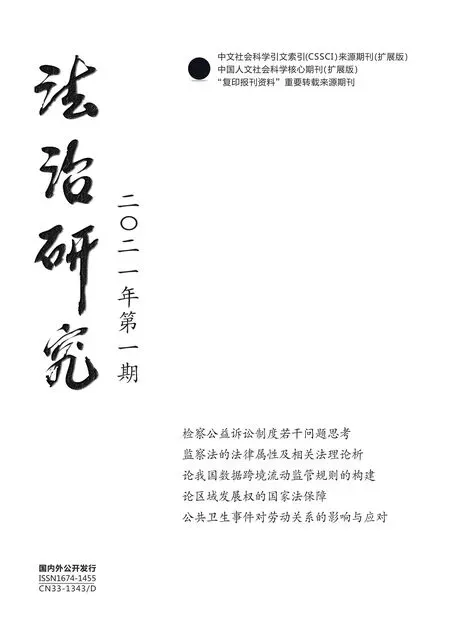國際經(jīng)貿(mào)條約的安全例外條款及其解釋問題
張乃根
一、條約法上的安全例外:觀念與條款的由來及發(fā)展
“安全”是國際關系中一個極為重要的觀念。當代歐美國際關系學理論較多討論“集體安全”“國際安全”問題。①如英尼斯·克勞德的“均勢、集體安全和世界政府”理論,參見倪世雄、金應忠主編:《當代美國國際關系理論流派文選》,學林出版社1987年版,第163頁;又如“國際安全新論”,參見倪世雄主編:《當代西方國際關系理論》,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434頁。其實,現(xiàn)代國際關系和國際法形成之初,“安全”就是一個基本觀念。對于每一個現(xiàn)代主權國家而言,相對安全的生存環(huán)境或條件必不可少。因此,國家的“安全”觀具有本國不受他國武力侵犯或威脅和獨立生存而避免根本上依賴他國的基本內(nèi)涵。格勞秀斯在最初探討現(xiàn)代國際法原理時曾提出兩項包含“安全”觀念的自然法戒律:“第一,應當允許保護(人們自己的)生命并避免可能造成其傷害的威脅;第二,應當允許為自己取得并保有那些對生存有用的東西。”②[荷]格勞秀斯:《捕獲法》,張乃根等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4頁。他在《戰(zhàn)爭與和平法》中將這兩項戒律運用于論證正義戰(zhàn)爭的合法性:“就戰(zhàn)爭之目的與宗旨在于保全生命與身體完整,并保存或取得對于生活有用的東西而言,戰(zhàn)爭完全符合這些自然的基本原則。”③Hugo Grotius, The Law of War and Peace, translated by Francis W. Kelsey, the Clarendon Press, 1925, p.52.這在傳統(tǒng)國際法上被稱為每個國家的“自我保全”原則,涵蓋自衛(wèi)和自存兩方面的固有權利。④See Amos S. Hershey, The Essentials of International Law,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19, p.144; “自衛(wèi)”又稱“自保”,參見[英]勞特派特修訂:《奧本海國際法》,上卷第一分冊,王鐵崖、陳體強譯,商務印書館1971年版,第224頁。
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之后,《聯(lián)合國憲章》第2條第4款原則上規(guī)定“各會員國在其國際關系上不得使用威脅或武力,或以與聯(lián)合國宗旨不符之任何其他方法,侵害任何會員國或國家之領土完整或政治獨立。”同時第51條允許“聯(lián)合國任何會員國受武力攻擊時,在安全理事會采取必要辦法,以維護國際和平及安全以前,本憲章不得認為禁止行使單獨或集體自衛(wèi)之自然權利。”⑤《聯(lián)合國憲章》(1945年6月26日),載《國際條約集》(1945-1947),世界知識出版社1961年版,第35頁。這是相對禁止使用武力原則的例外,⑥See Kenneth Manusama, The 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Martinuis Nijhoff Publishers, 2011, p.299;又參見黃瑤:《論禁止使用武力原則》,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278頁。可以說,這是現(xiàn)代具有普遍約束力的多邊條約第一次規(guī)定自衛(wèi)權的安全例外條款。此前,《威斯特伐利亞條約》第124條規(guī)定對于違約者,受害者應首先采取“溫和的手段和法律措施”,經(jīng)三年無法解決爭端,可使用武力。⑦《威斯特伐利亞條約》(1648年10月24日),載《國際條約集》(1648-1871),世界知識出版社1984年版,第31頁。其實質(zhì)在于允許一個國家使用武力解決與他國的爭端,因而不是禁止使用武力的安全例外。這一支配現(xiàn)代國際關系數(shù)百年的法則直到聯(lián)合國成立才得以改變。
在《聯(lián)合國憲章》問世后不久,1947年10月30日簽署并于翌年1月1日起臨時生效的《關稅與貿(mào)易總協(xié)定》(GATT)⑧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 55. U.N.T.S. 94; Protocol of Provisional Application of the GATT, 55. U.N.S.T. 308.第21條以“安全例外”為標題,明確規(guī)定:“本協(xié)定的任何規(guī)定不得解釋為:(a)要求締約方提供其認為如披露會違背其基本安全利益的任何信息;或(b)阻止任何締約方采取其認為對保護其基本國家安全利益所必需的任何行動:(i)與裂變和聚變或衍生這些物質(zhì)有關的行動;(ii)與武器、彈藥和作戰(zhàn)物資的貿(mào)易有關的行動,及與此類貿(mào)易所運輸?shù)闹苯踊蜷g接供應軍事機關的其他貨物或物資有關的行動;(iii)在戰(zhàn)時或國際關系中的緊急情況下采取的行動;或(c)阻止任何締約方為履行《聯(lián)合國憲章》項下的維護國際和平與安全的義務而采取的任何行動。”⑨《關稅與貿(mào)易總協(xié)定》(GATT1947),載《世界貿(mào)易組織烏拉圭回合多邊貿(mào)易談判結果法律文本》[中英文對照],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456頁。這是多邊條約首次明確規(guī)定的安全例外條款。這不僅對此后國際經(jīng)貿(mào)關系的調(diào)整具有重大意義,而且作為嚴格意義的條約法上安全例外條款,在一般國際法上也堪稱先例。
GATT烏拉圭回合多邊貿(mào)易談判達成的一攬子協(xié)定隨著1995年1月1日WTO的成立而生效實施,其中,《貨物貿(mào)易多邊協(xié)定》包括1947年GATT,上述第21條安全例外條款不僅原封不動地保留,而且一字不差地被復制到新的《服務貿(mào)易總協(xié)定》 (GATS)第14條之二和《與貿(mào)易有關的知識產(chǎn)權協(xié)定》(TRIPS)第73條,成為WTO三大實體性貿(mào)易協(xié)定下安全例外的共同條款。
不同于多邊貿(mào)易條約的安全例外條款之由來和發(fā)展,自上世紀50年代末,尤其70年代興起,迄今已達數(shù)千項的雙邊投資保護條約或協(xié)定(BITs),⑩1959年德國與巴基斯坦《投資促進與保護協(xié)定》是第一項BIT,截止2020年1月25日,全球共有2899項BITs,其中已生效為2340項。此外,含有投資條款的經(jīng)貿(mào)協(xié)定共有389項,319項已生效。參見UNCTAD網(wǎng)站:https://investmentpolicy.unctad.org/internationalinvestment-agreements,2020年9月2日訪問。起初的安全例外實質(zhì)上是“公共秩序”范疇下的投資待遇例外,如1973年德國與馬耳他BIT的議定書補充第2條(a)款規(guī)定:“基于公共安全與秩序、公共健康或道德而不得不采取的措施不應視為第2條含義下‘低于優(yōu)惠的待遇’。”?Protocol to treaty between Malta and the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concerning the encouragement and reciprocal protection of investment.7 April 1973.此后的BITs將“公共秩序”例外延伸到“基本安全利益”,形成比較明確的安全例外條款,如1983年美國與塞內(nèi)加爾BIT第10條標題“本條約不得調(diào)整的措施”下第1款規(guī)定:“本條約不得排除締約任何一方采取必要措施以維持其公共秩序與道德,履行其有關維持或恢復國際和平或安全的義務,或保護自己基本安全利益。”?Treaty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he Republic of Senegal concerning the reciprocal encouragement and protection of investment, 6 December 1983. 這成為美國與其他國家BITs的條款范本。其他國家間部分BITs逐漸采納了這樣的做法,并參照了多邊貿(mào)易協(xié)定的安全例外條款。如2008年日本與烏茲別克斯坦BIT第17條第1款規(guī)定:“本協(xié)定任何條款不得解讀為阻止一締約方采取或?qū)嵤┐胧╠)對其認為有必要保護基本安全利益,(i)在戰(zhàn)時或武裝沖突,或其他該締約方或國際關系中的緊急情況”。?Agreement between Japan and the Republic of Uzbekistan for the Liberalization, Promotion and Protection of Investment, 15 August 2008.與多邊貿(mào)易協(xié)定不同,BITs安全例外條款尚無統(tǒng)一表述。
盡管在國際關系中,安全對于每個國家都是至關重要,但是,除了安全保障或核安全等領域極少數(shù)條約,?如《日本和美國共同合作和安全條約》(1960年1月19日),載《國際條約集》(1960-1962),商務印書館1975年版,第27頁;《關于核子能方面建立安全管制的公約》(1957年12月20日),載《國際條約集》(1956-1957),世界知識出版社1962年版,第662頁。一般而言,條約本身很少冠以“安全”。貿(mào)易、投資等國際經(jīng)貿(mào)條約僅包含安全例外條款。其原因在于安全事關國家主權,通常由各國自行處置,毋庸以條約與他國約定。國際經(jīng)貿(mào)條約的安全例外條款特指對締約方承擔的國際貿(mào)易或投資方面義務而言,可基于國家安全理由,例外地不履行。因此,安全例外的實質(zhì)是正當行使國家主權的體現(xiàn)。鑒于“條約必須遵守”?這既是“舉世所承認”的習慣國際法,也是條約法的基本規(guī)定。參見《維也納條約法公約》(1969年5月23日),載《國際條約集》(1969-1971),商務印書館1980年版,第42頁,序言和第26條。,有關締約方通過安全例外條款作為履行條約義務之例外,僅限于涉及基本安全利益或發(fā)生戰(zhàn)爭及國際關系中的緊急情況。可以說,這是條約義務的履行與締約方“自我保全”相沖突或發(fā)生武裝沖突致使以和平為宗旨的條約?格勞秀斯在《戰(zhàn)爭與和平法》中將整個條約范疇一概歸為希臘人所謂“狹義的和平”,條約亦即和平。參見前注④,p.394.及其義務無法履行等極端情況下適用的。相對《聯(lián)合國憲章》下維護或恢復國際和平與安全的“集體安全”“國際安全”而言,國際經(jīng)貿(mào)條約的安全例外條款主要以單個締約方例外地不履行其條約義務的自身“基本安全利益”或發(fā)生武裝沖突等危及國家安全的極端情況為適用對象。下文分析的國際貿(mào)易、投資條約中安全例外的解釋問題都與此類適用有關。
二、 國際貿(mào)易條約的安全例外條款解釋問題
如上所述,1947年GATT以及1995年WTO三大實體性貿(mào)易協(xié)定早就有了安全例外條款,在GATT時期也有過涉及安全例外條款的爭端解決,但均未對GATT第21條作過條約解釋。?如,捷克斯洛伐克訴美國出口控制案,GATT/CP.3/SR.22 (1949),參見GATT Disputes:1948-1995, Volume 1: Overview and one-page case summaries, Geneva: WTO Publications 2018, p.3;又如,尼加拉瓜訴美國禁運案,L/6053,專家組報告未通過(1986年10月13日),參見[美]約翰·H·杰克遜:《世界貿(mào)易體制:國際經(jīng)濟關系的法律與政策》,張乃根譯,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257頁。WTO成立至今,直到晚近才接連發(fā)生兩起有關貨物貿(mào)易和貿(mào)易相關知識產(chǎn)權的安全例外爭端解決案件,即,“俄羅斯有關過境運輸措施案”(俄羅斯過境案)和“沙特阿拉伯有關知識產(chǎn)權保護措施案”(沙特知識產(chǎn)權案)。?Russia-Measures Concerning Traffic in Transit, WT/DS512/R, 5 April 2019;該案未提起上訴,已通過專家組報告。Saudi Arabia-Measures Concerning the Protec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WT/DS567/R, 16 June 2020, 該案已提起上訴。通過WTO爭端解決專家組對涉案安全例外條款的條約解釋,使人們對國際貿(mào)易中安全例外的內(nèi)涵以及適用條件有了進一步理解。在當前美國肆意濫用其所謂“安全例外”,頻頻挑起國際經(jīng)貿(mào)爭端的情況下,?如,2018年3月美國以安全例外為由對進口至美國的鋼鋁制品采取加征關稅措施,中國率先向WTO起訴美國實質(zhì)上是采取違反WTO規(guī)則的保障措施。US-Steel and Aluminium Products (China), DS544/1, 9 April 2018. 隨后,歐盟等8個成員相繼以同樣理由訴告美國。如何運用條約解釋的國際法,?參見張乃根:《條約解釋的國際法》(上下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正確理解和適用國際貿(mào)易條約中安全例外條款,顯得格外重要。
(一)“國際關系中的緊急情況”:解釋含義之一“一般是指武裝沖突或潛在的武裝沖突”
俄羅斯過境案是“第一起WTO爭端解決專家組被要求解釋GATT第21條(或GATS與TRIPS的相同條款)。”21同前注?,WT/DS512/R,para.7.20.該案起因于俄羅斯以國家安全例外為由,禁止烏克蘭貨物經(jīng)由俄羅斯公路和鐵路過境至哈薩克斯坦等國。
專家組首先對俄羅斯主張安全例外的“自裁性”進行分析,認為包括WTO爭端解決專家組在內(nèi)的國際裁判庭都擁有履行其職能所需的“內(nèi)在管轄權”,包括對其行使“實體管轄權”有關所有事項的裁定權。22同前注?,WT/DS512/R,para.7.53.根據(jù)WTO《關于爭端解決規(guī)則與程序的諒解》(DSU)第1條第2款,WTO爭端解決的規(guī)則與程序適用于包括GATT第21條在內(nèi)一攬子協(xié)定的諸條款,DSU附錄2所規(guī)定適用特殊或附加規(guī)則與程序也不包括GATT第21條,因此,俄羅斯援引該第21條作為其違反GATT第5條過境自由規(guī)定的“安全例外”,屬于適用DSU一般規(guī)則與程序的專家組管轄權范圍。
然后,專家組側重于該第21條(b)款(iii)項的解釋,并明確依照DSU第3條第2款,應適用作為“國際公法的解釋慣例”之《維也納條約法公約》(VCLT)第31條、第32條。該第21條引言句規(guī)定:“本協(xié)定的任何規(guī)定不得解釋為”,接著三款(a)、(b)、(c)均以“或者”分開規(guī)定WTO成員履行GATT義務的安全例外。第21條(b)款也有引言句:[不得解釋為]“阻止任何締約方采取其認為對保護其基本國家安全利益所必需的任何行為”。該引言句可以不同方式解讀,得出多種解釋。特別是“其認為”可解釋為:其一,僅對“必需”這一用語而言;其二,也包括對“其基本國家安全利益”而言;其三,對第21條(b)款的三種情況而言。專家組認為對于同一條約用語可有不同解釋,但沒有明確根據(jù)VCLT解釋規(guī)則,是否允許多種解釋的并存。在WTO的規(guī)則體系中,只有《反傾銷協(xié)定》第17條第6款(ii)項明確規(guī)定專家組依據(jù)國際公法的解釋慣例,“認為本協(xié)定的有關規(guī)定可以作出一種以上允許的解釋”,并可選擇其一。根據(jù)DSU附錄2,這屬于特殊規(guī)則,僅適用于《反傾銷協(xié)定》。換言之,第21條(b)款可有多種解釋,但并沒有協(xié)定依據(jù)允許并存的情況下選擇其一。更何況對于《反傾銷協(xié)定》第17條6款(ii)項,上訴機構始終否認多種解釋的并存。23在“美國洗衣機案”中,一位上訴機構成員對上訴機構有關《反傾銷協(xié)定》第2條第4款第2項下W-T比較方法不允許歸零法的多數(shù)意見表示異議,并認為這也是《反傾銷協(xié)定》第17條第6款(ii)項所允許的解釋。US-Washing Machines, DS464/AB/R, 7 September 2016, paras.5.191-5.203.
專家組對這三種可能的解釋,逐一展開,但重點在于第三種。第21條(b)款的(i)、(ii)、(iii)項分列的情況實質(zhì)不同,且不是累加的,而是“替換的”。但是,專家組認為,其中任何行動必須滿足其中之一的要求,“以便落入第21條(b)款的范圍內(nèi)”。24同前注?,WT/DS512/R,para.7.67.這是該解釋的關鍵,即,盡管三種可替換的情況不同,但都屬于第21條(b)款,因而具有一定的共性。這是將(iii)項的“國際關系中的其他緊急情況”放在整個(b)款的上下文中,加以解釋。
就(iii)項的“國際關系中的其他緊急情況”之詞義而言,專家組解釋:“在戰(zhàn)時或國際關系中的其他緊急情況”這一規(guī)定提示戰(zhàn)爭是“國際關系中的緊急情況”這一大范疇下一種情況。戰(zhàn)爭通常指的是武裝沖突;緊急情況包括“危險或沖突的情況,系未曾遇見的起因并要求采取緊急行動”;國際關系一般指“世界政治”或“全球政治,主要是主權國家的關系”。
就(iii)項的“國際關系中的其他緊急情況”之上下文而言,專家組認為(i)和(ii)項的事項,即“裂變物質(zhì)”和“武器運輸”,與(iii)項的戰(zhàn)爭均與國防、軍事的利益有關。因此,“‘在國際關系中的緊急情況’必須理解為是從第21條(b)款所規(guī)定的其他事項引起的同樣利益中引申而出的。”25同前注?,WT/DS512/R,para.7.74.亦即,第21條(b)款引言的“基本國家安全利益”具有相同性。“因此,國際關系中的緊急情況看來一般是指武裝沖突或潛在的武裝沖突,或高度緊張或危機,或一個國家內(nèi)或周邊普遍的不穩(wěn)定狀態(tài)。這種情況引起有關國家的特定利益,即,國防或軍事利益,或維持法律或公共秩序的利益。”26同前注?,WT/DS512/R,para.7.76.這類利益存在與否,屬于可經(jīng)專家組“客觀認定的客觀事實”,而不是主張安全例外的WTO成員自己主觀“認為”即可。這與專家組認為安全例外不是主張者“自裁”事項是相吻合的。也就是說,第21條安全例外的成立與否,既不是主張安全例外的成員自己決定,也不是其主觀認定,而是在專家組的管轄范圍,并應該經(jīng)由專家組的客觀認定。
就(iii)項的“國際關系中的其他緊急情況”之目的及宗旨而言,《建立WTO協(xié)定》及GATT之總目的及宗旨在于促進互惠互利安排的安全性、可預見性以及實質(zhì)減少關稅與非關稅壁壘,同時在特定情況下,成員可偏離其GATT和WTO項下義務,以便在最大限度接受此類義務時保持一定靈活性,但是將這專家組的上述解釋更多依賴于該條款的起草史。這包括美國于1946年提交的始初文本包含如今GATT第20條、第21條的例外條款,1947年5月的起草本將一般例外與安全例外分開。美國代表團對“或國際關系中的其他緊急情況”作了如此解釋:“我們特別記得上次戰(zhàn)爭結束前的情況,在1941年底我們參戰(zhàn)前,戰(zhàn)爭在歐洲已進行了兩年,我們即將參戰(zhàn)時,為保護自己,要求可采取許多如今憲章已禁止的措施。我們的進出口在嚴格管控下,原因在于戰(zhàn)爭在進行著。”27同前注?,WT/DS512/R,para.7.92.也就是說,在美國參戰(zhàn)前夕,所采取的進出口管制措施屬于“國際關系中的其他緊急情況”,但與戰(zhàn)爭直接相關。正是在該起草史的印證下,專家組認為“國際關系中的其他緊急情況”包括潛在的武裝沖突。這一解釋符合第21條(b)款(iii)項的初衷。
但是,按照如今在條約解釋的國際法實踐中得到普遍認可的“演進”解釋規(guī)則,即,對締約的時代較久遠且依然有效的條約所具有的一般性用語,“作為一項基本規(guī)則,必須假定締約方有意使這些術語具有演變的含義。”28Dispute Regarding Navigational and Related Rights, ICJ Reports 2009, p.243, para.66.“國際關系”和“緊急情況”都屬于一般性用語。在當代,除了戰(zhàn)爭這一國際關系中的緊急情況,還有其他不屬于武裝沖突范疇的緊急情況。尤其應指出,根據(jù)當代的一般國際法,調(diào)整傳統(tǒng)的主權國家間戰(zhàn)爭法已發(fā)展為包括主權國家下內(nèi)戰(zhàn)(非國際性武裝沖突29參見《1949年8月12日日內(nèi)瓦四公約關于保護非國際性武裝沖突受難者的附加議定書》(第二議定書),1977年6月8日訂于日內(nèi)瓦。)的武裝沖突法。根據(jù)VCLT第31條第3款(c)項,作為“適用于當事國間關系之任何有關國際法規(guī)則”的當代武裝沖突法,應與解釋第21條(b)款(iii)項的上下文一并考慮,從而避免像本案專家組將“國際關系中的其他緊急情況”首先解釋為“武裝沖突”,與當代武裝沖突法下的“戰(zhàn)爭”重疊,使得“國際關系中的其他緊急情況”在很大程度上變得多余,與條約的有效解釋相悖。些偏離僅作為某成員單邊意愿的表示,則有悖于這些目的及宗旨。專家組在解釋第21條(b)款之目的及宗旨時,似乎并未緊扣“國際關系中的其他緊急情況”,而是指該條款項下的客觀認定問題。進言之,如第21條(b)款(iii)項下“國際關系中的其他情況”首先也是“武裝沖突或潛在的武裝沖突”,與作為武裝沖突的“戰(zhàn)爭”又有什么區(qū)別呢?如果這樣幾乎同義反復,第21條(b)款(iii)項只需規(guī)定“戰(zhàn)時”,即可。
綜上專家組關于GATT第20條(b)款(iii)項的解釋,一方面將該款項放在(b)款的整體中解釋,認為“基本國家安全利益”涵蓋(b)款三項的共性,都具有“國防或軍事利益,或維持法律或公共秩序的利益”,一方面強調(diào)(b)款引言“其認為”針對每一項而言,必須滿足每一項的要求方可成立,而(iii)項首先須與武裝沖突或潛在武裝沖突有關。30該案專家組認定俄羅斯援引安全例外的情況包括2014年3月至2016年底烏克蘭與俄邊境接壤的東部地區(qū)武裝沖突構成國際關系中的緊急情況。同前注?,WT/DS512/R,para.7.123.
(二)“國際關系中的緊急情況”:解釋含義之二“高度緊張或危機”
沙特知識產(chǎn)權案所解釋的TRIPS第73條本身與GATT第21條完全相同,但涉及貿(mào)易有關知識產(chǎn)權,因而條約解釋的語境不同于俄羅斯過境案。該案起由是近年來沙特及其他海灣地區(qū)部分國家與卡塔爾的關系惡化,直至2017年6月沙特宣布與卡塔爾斷絕外交及領事關系,關閉與卡塔爾有關所有陸海空通道,禁止卡塔爾國民進入沙特。卡塔爾訴稱沙特同時禁止總部設在卡塔爾的一家全球性體育娛樂公司(beIN)繼續(xù)在沙特從事該公司擁有專有轉(zhuǎn)播權的體育賽事廣播業(yè)務,并允許沙特本地一家廣播公司(beoutQ)未經(jīng)許可廣播beIN的所有體育賽事,構成TRIPS第61條下“具有商業(yè)規(guī)模的蓄意盜版”而不采取任何刑事措施。沙特雖未明確以安全例外為該盜版行為抗辯,但辯稱斷絕與卡塔爾的外交關系等全面措施是在國際關系中緊急情況下采取必要的安全例外措施。實際上,此類盜版行為是實施這些措施之后發(fā)生的。因此,專家組認為一旦認定盜版行為存在,沙特也沒有適用相應的刑事程序和刑罰,就應根據(jù)沙特為其全面措施抗辯所援引的安全例外,分析此類不適用TRIPS第61條的刑事措施是否屬于TRIPS第73條(b)款(iii)項的安全例外。31該案專家組最終裁定沙特對于beoutQ商業(yè)規(guī)模的盜版行為不采取任何刑事程序和刑罰違反TRIPS第61條,并與沙特斷絕與卡塔爾外交等關系而終止或阻止與卡塔爾國民有任何交往的安全例外措施無關。同前注?,WT/DS567/R,paras.7.294.
該案專家組以俄羅斯過境案為指導,闡明了評估援引TRIPS第73條(b)款(iii)項的四步驟:1. 是否確實存在該款項下“在戰(zhàn)時或國際關系中的其他緊急情況”;2. 是否“在戰(zhàn)時或國際關系中的其他緊急情況下采取的行動”;3. 援引安全例外的一方是否形成相關“根本安全利益”并足以能夠判斷所采取的行動與之相關性;4. 所采取的行動對于保護緊急情況下的根本安全利益是否必要。32同前注?,WT/DS567/R,paras.7.242.下文限于評析專家組對第一步驟中有關“國際關系中的其他緊急情況”的條約解釋。
該案專家組基于俄羅斯過境案對“國際關系中的緊急情況”的條約解釋,即,包含“武裝沖突或潛在的武裝沖突”,或“高度緊張或危機”,或“一個國家內(nèi)或周邊普遍的不穩(wěn)定狀態(tài)”,認為沙特援引安全例外的“國際關系中的緊急情況”屬于“高度緊張或危機”。33同前注?,WT/DS567/R,paras.7.257.專家組同意沙特主張WTO某成員斷絕與另一成員的所有外交及經(jīng)濟關系可視為“存在國際關系中緊急情況的國家最終表示”,并以聯(lián)合國國際法委員會關于VCLT第63條“斷絕外交或領事關系”的評注為依據(jù),認為這是一個國家“單邊和自由裁量的行動,通常是派出國與接受國關系出現(xiàn)嚴重危機時采取的最后手段”。34同前注?,WT/DS567/R,paras.7.260.該案專家組還認為應將這一“高度緊張或危機”放在沙特斷絕與卡塔爾外交及其他關系的背景下考察,即,沙特一再聲稱卡塔爾“破壞地區(qū)穩(wěn)定與安全”,而卡塔爾強烈拒絕此類指控。專家組表示對雙方此類爭執(zhí)不持任何立場,只是認為“這本身反映了與安全利益有關的高度緊張或危機的情況”。35同前注?,WT/DS567/R,paras.7.263.
值得留意,沙特知識產(chǎn)權案專家組對“國際關系中的緊急情況”含義與其說是條約解釋,不如說是對俄羅斯過境案有關條約解釋用語的進一步解釋,也就是說,將當事方之間“斷絕外交或領事關系”作為體現(xiàn)國家間關系“高度緊張或危機”的含義所在。問題在于:“高度緊急或危機”用語本身不是安全例外條款的條約用語,而是先前專家組的條約解釋用語。這種類似遵循先例的做法,在條約解釋的國際法實踐中十分普遍,也是保持同類案件對相同條約款項的解釋“判理穩(wěn)定性”36參見前注?,第106頁。之習慣做法。尤其是俄羅斯過境案專家組報告未經(jīng)上訴而通過后,其條約解釋的判理指導嗣后專家組作出進一步解釋,充分體現(xiàn)了當前在WTO爭端解決上訴機構無法運行的情況下,已通過的專家組報告具有很強的類似先例作用。37沙特雖對專家組報告提起上訴,但并不涉及專家組對安全例外條款的解釋。這表明該解釋已得到當事方的認可。參見沙特上訴通知,Notification of an Appeal, WT/DS567/7, 30 July 2020.
還應進一步留意,沙特知識產(chǎn)權案不存在俄羅斯過境案中的武裝沖突情況,因而不必涉及上文提及將“國際關系中的緊急情況”首先解釋為“武裝沖突或潛在武裝沖突”,會產(chǎn)生與當代武裝沖突法包含戰(zhàn)爭的含義重疊問題。但是,“國際關系中的緊急情況”下“高度緊張或危機”不限于斷絕外交關系等情況,因而如何進一步解釋安全例外條款,尤其是“國際關系中的緊急情況”仍是值得深入探討的國際法問題。
(三)全球貿(mào)易戰(zhàn)的背景下安全例外條款解釋問題
上述兩起案件的專家組在當前全球貿(mào)易戰(zhàn)的背景下對國際貿(mào)易條約安全例外條款的解釋,具有特殊意義。兩起案件本身與貿(mào)易戰(zhàn)沒有任何關系。俄羅斯過境案是由于烏克蘭與俄羅斯關系惡化,尤其是克里米亞公投并入俄羅斯和烏克蘭東部地區(qū)武裝沖突,導致美國、歐盟等對俄羅斯的經(jīng)濟制裁與俄羅斯的反制裁,包括俄羅斯以國家安全為由禁止烏克蘭貨物經(jīng)由俄羅斯公路和鐵路過境至哈薩克斯坦等國而引起的貿(mào)易爭端。沙特知識產(chǎn)權案則是在中東地區(qū)復雜的國際關系中因部分國家與卡塔爾斷交引起的貿(mào)易相關知識產(chǎn)權爭端。
然而,2018年3月美國以安全例外為由對進口至美國的鋼鋁制品采取加征關稅措施,中國率先向WTO起訴美國實質(zhì)上是采取違反WTO規(guī)則的保障措施。38同前注?。美國辯稱:“國家安全是政治問題,不屬于WTO爭端解決的事項。每一個WTO成員均有權自己決定對于其重大安全利益的保護必要性,如同這體現(xiàn)于1994年GATT第21條規(guī)定。”39US-Steel and Aluminium Products (China), DS544/2, 17 April 2018.在專家組審理俄羅斯過境案時,美國作為第三方強調(diào)安全例外的自裁權是“GATT締約方和WTO成員反復承認的‘固有權利’。”40同前注?,WT/DS512/R,para.7.51.盡管該案專家組通過條約解釋,已明確在WTO的國際貿(mào)易條約下安全例外問題一旦進入爭端解決程序,就不是其成員自行主觀判定的事項,而應由專家組基于個案事實的客觀評估加以認定,但是,美國作為沙特知識產(chǎn)權案的第三方,再次提出TRIPS“第73條(b)款是一項自裁性條款”。41同前注?,WT/DS567/R,para.7.238.沙特知識產(chǎn)權案專家組重申認定安全例外屬于適用DSU一般規(guī)則與程序的專家組管轄權范圍。這對WTO爭端解決機構處理此類貿(mào)易爭端的正當性和權威性,具有重大意義。
值得進一步探析的是“國際關系中的緊急情況”究竟涵蓋哪些情況?俄羅斯過境案專家組的解釋至少涵蓋三種情況:“武裝沖突或潛在的武裝沖突”,或“高度緊張或危機”,或“一個國家內(nèi)或周邊普遍的不穩(wěn)定狀態(tài)”。沙特知識產(chǎn)權案專家組又將“高度緊張或危機”進一步解釋為至少涵蓋國家間“斷絕外交與領事關系”。如上文評析時認為,從演進的條約解釋來看,“武裝沖突或潛在的武裝沖突”的涵義與如今武裝沖突法涵蓋戰(zhàn)爭的情況重疊,有悖條約有效解釋規(guī)則。“高度緊張或危機”涵義寬泛,本身不是條約用語,嗣后專家組按照類似遵循先例的做法,將先前專家組解釋延伸的用語當作進一步解釋的基礎。已故著名WTO法學者杰克遜教授曾擔憂安全例外條款“這一規(guī)定的表述是如此寬泛、自我判斷和含糊,以致顯然會被濫用。”42同前注?,第256頁。晚近WTO成員在國際貿(mào)易爭端解決中接二連三地援引安全例外條款,作為其違反WTO法規(guī)則的正當性抗辯理由。美國根據(jù)國內(nèi)法,在對外經(jīng)貿(mào)關系中濫用安全例外,對其他WTO成員的進口產(chǎn)品單邊加征關稅,或封殺他國企業(yè)的產(chǎn)品或投資等,更是無所不及。
目前在全球貿(mào)易戰(zhàn)的背景下安全例外條款的解釋,涉及GATT第21條(b)款(iii)項下“國際關系中的其他緊急情況”的兩個關聯(lián)問題。其一,在中國等訴美國鋼鋁制品案中,美國聲稱的安全例外是否構成國際關系中的“緊急情況”或更具體地說,“高度緊張或危機”?其二,美國以所謂不公平貿(mào)易的301調(diào)查結果為由對數(shù)以千億美元中國輸美產(chǎn)品實施加征關稅的單邊貿(mào)易措施。對于美國挑起的貿(mào)易戰(zhàn),中國不得不被迫進行必要反擊。這樣的貿(mào)易戰(zhàn)是否屬于該第21(b)(iii)條下“國際關系中的其他緊急情況”,以致中國可以采取反制措施以維護自己的重大安全利益?
就第一個問題而言,美國辯稱:根據(jù)其1962年《貿(mào)易擴展法》第232節(jié)采取加征關稅措施“對于調(diào)整威脅損害美國國家安全的鋼鋁制品進口是必要的。國家安全問題是不屬于由WTO爭端解決來審查或能夠處理的政治問題。WTO各成員保留自己決定那些它所認為有必要保護基本安全利益,正如GATT第21條所體現(xiàn)的那樣。”43US-Steel and Aluminium Products (China), DS544/2, 17 April 2018.美國明確援引了該第21條作為其違反WTO規(guī)則加征關稅的安全例外依據(jù)。如果參照俄羅斯過境案的解釋,所謂“威脅損害美國國家安全的鋼鋁制品進口”顯然與戰(zhàn)爭無關,也不屬于“國際關系中緊急情況”的“武裝沖突或潛在的武裝沖突”,或“高度緊張或危機”,或“一個國家內(nèi)或周邊普遍的不穩(wěn)定狀態(tài)”,而是與美國鋼鋁制品產(chǎn)業(yè)因進口過多而受損有關。中國等諸多WTO成員因而訴告美國假借國家安全例外,實質(zhì)是針對短時期內(nèi)某類產(chǎn)品進口激增而采取的保障措施。正如杰克遜教授曾比喻:如果濫用安全例外,“甚至有人提出保留制鞋行業(yè)作為例外,因為軍隊必須有鞋穿。”44同前注?,第256頁。如將因進口過多而影響其產(chǎn)業(yè)等經(jīng)濟安全也作為“國際關系中緊急情況”,那么在俄羅斯過境案所列三種情況之外,或者沙特知識產(chǎn)權案所解釋的“高度緊張或危機”涵蓋“斷絕外交與領事關系”之外,至少還要增加“國家經(jīng)濟安全”這一更加寬泛的情況,從而極大地擴展安全例外的范圍。從條約解釋的角度看,一國的產(chǎn)業(yè)存廢或發(fā)展程度主要不是國際關系的問題。國際關系的通常涵義是在世界政治或全球政治中的主權國家間關系。在GATT第21條(b)款的上下文中,“緊急情況”一般指的是危險或沖突的情況,未曾遇見的起因并要求采取緊急行動的情況。美國鋼鋁制品產(chǎn)業(yè)的相對停滯或減弱是其本身經(jīng)濟結構調(diào)整的結果,與2002年美國對進口鋼材采取保障措施時碰到其鋼鐵產(chǎn)業(yè)衰退的情況,如出一轍。當時歐盟為主包括中國等多個WTO成員訴告美國違反WTO保障措施的規(guī)則,并勝訴。45參見楊國華:《中國入世第一案:美國鋼鐵保障措施案研究》,中信出版社2004年版。如今美國打著安全例外的旗號,實際上采取保障措施。在GATT包括保障措施的條款等上下文看,美國單方加征進口鋼鋁制品關稅的所謂國家安全例外難以歸入第21條(b)款(iii)項的“國際關系中的其他緊急情況”。
就第二個問題而言,美國挑起對中國的貿(mào)易戰(zhàn)可歸入“國際關系中的緊急情況”涵蓋國際關系的“高度緊張或危機”。從演進的條約解釋看,GATT第21條(b)款(iii)項的“國際關系中的其他緊急情況”的通常涵義應該是相對于“戰(zhàn)時”,也就是當代武裝沖突法所涵蓋的兩個或數(shù)個國家之間,或一國內(nèi)部的武裝沖突等軍事行動而言,和平條件下的國際關系中的政治(如斷絕外交與領事關系)、經(jīng)濟(如所謂貿(mào)易戰(zhàn)之類特別重大的經(jīng)貿(mào)摩擦)等方面突發(fā)事件,或鄰國突發(fā)重大事變等危及本國安全的情況。因此,中國面臨美國強加的史無前例、超大規(guī)模的雙邊貿(mào)易戰(zhàn),兩國經(jīng)貿(mào)關系處于“高度緊張或危機”的緊急狀態(tài),為了維護自身經(jīng)濟方面的國家安全,只得對來自美國的進口產(chǎn)品采取實質(zhì)等同的加征關稅措施。這是真正的安全例外措施。或許正是如此,美國迄今未在WTO訴告中國采取此類關稅措施違反WTO規(guī)則。46相比之下,對于中國等反制美國加征鋼鋁制品關稅而采取WTO《保障措施協(xié)定》第8條第2款項下的措施,美國在WTO提起爭端解決。參見China-Additional Duties on Certain Product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WT/DS558, 16 July 2018. 同類案件還有美國訴告歐盟等,WT/DS557, 559, 560, 561, 566, 585. 這些案件目前均處于專家組審理階段。
簡言之,相比泛泛而論的“國家經(jīng)濟安全”,“貿(mào)易戰(zhàn)”涉及國際經(jīng)貿(mào)關系,構成“高度緊張或危機”的情況。因此,進一步解釋GATT第21條(b)款(iii)項的“國際關系中的其他緊急情況”,至少可增加諸如中美“貿(mào)易戰(zhàn)”此類情況。誠然,美國并未就此啟動涉及條約解釋的爭端解決,這只是本文的假設性解釋。但是,中國等訴告美國鋼鋁制品案的專家組將無法回避解釋產(chǎn)業(yè)相關“國家經(jīng)濟安全”是否構成“國際關系中的其他緊急情況”。47該案原定在2020年底前完成專家組審理。參見US-Steel and Aluminium Products (China), DS544/10, 10 September 2019.讓我們拭目以待。
三、 國際投資協(xié)定中安全例外的解釋問題
(一)國際投資協(xié)定中安全例外條款的“自裁性”
由于阿根廷國內(nèi)經(jīng)濟危機導致政府頒布《緊急狀態(tài)法》等相關措施與外國投資者的利益發(fā)生沖突,因此在2000年之后有數(shù)十起有關投資爭端仲裁案件,48自2001年Enron Creditors v. Argentina, ICSID Case No. ARB/01/3起,截止2019年12月,有57起訴告阿根廷政府的投資爭端仲裁案,參見聯(lián)合國貿(mào)發(fā)會議官網(wǎng):https://investmentpolicy.unctad.org/investment-dispute-settlement/country/8/argentina,2020年9月8日訪問。其中不乏涉及BITs安全例外條款的案件。如,安然公司訴阿根廷案所涉阿根廷與美國BIT第11條的解釋。該第11條規(guī)定:“本條約不得排除締約任何一方適用必要措施以維持公共秩序,履行有關維持或恢復國際和平或安全的義務,或保護自己基本安全利益。”49轉(zhuǎn)引自上注48,ARB/01/3,para.323.該案仲裁庭表示在審理中對于該第11條的討論顯得特別復雜,除了當事雙方提出了各自許多主張,該仲裁庭還聽取了有關專家學者的法律意見。
關于安全例外是否為“自裁性”條款,阿根廷認為美國對此一貫持肯定立場,基于BITs的互惠性,阿根廷也應從相同的理解中受惠,也就是說,可以自行判斷采取應對國內(nèi)經(jīng)濟危機以保護其基本安全利益的必要措施。該案的外國投資者認為如將安全例外解釋為“自裁性”條款,“將創(chuàng)設條約下義務的寬泛例外,并削弱此類條約之目的及宗旨。”50同前注48,ARB/01/3,para.330.該案仲裁庭傾向于保護外國投資者的利益,認為:“首先必須關注該條約之目的及宗旨,作為一般的立場,是適用于經(jīng)濟困難情況時也要求保護國際保障的受益者權利。在這一范圍,任何導致擺脫既定義務的解釋均難以與該目的及宗旨相吻合。因而必需采取限制解釋。在承認允許將經(jīng)濟緊急狀況納入該第11條上下文的解釋同時,將該條款解釋為自裁性條款肯定與該條約之目的及宗旨相悖。實際上,該條約會被失去其任何實體意義。”51同前注48,ARB/01/3,para.332.從條約解釋角度看,該案仲裁庭基于條約之目的及宗旨解釋涉案BITs第11條,并不完全符合VCLT第31條解釋通則所要求條約用語的通常含義應在其上下文中兼顧條約之目的及宗旨,加以善意解釋。該案仲裁庭除了通過上述限制解釋而強調(diào)涉案BIT的安全例外條款不應由投資東道國“自裁”,沒有對該第11條作更多的解釋。
正是因為該案仲裁庭一味偏向外國投資者,所以阿根廷不服該案裁決,尤其是對第11條的解釋,請求撤銷該案裁決。阿根廷訴稱:“即便該第11條不是自裁的,該案仲裁庭也未適用涉案BIT第11條,因為它未作實體性審議,而是簡單地以有關習慣國際法對必要性分析代替了該第11條,從而有悖于條約的有效解釋規(guī)則。”52Enron Creditors v. Argentina, ICSID Case No. ARB/01/3 (Annulment Proceeding), 26 January 2010, para.353(e).審理該請求撤銷的臨時委員會認為該案仲裁庭對涉案BIT第11條有關“必要措施”的解釋不充分,構成可撤銷裁決的“未充分闡明理由”這一錯誤。53根據(jù)《解決國家與他國國民間投資爭端公約》(ICSID)第52條(1)款(e)項,“裁決未陳述其依據(jù)的理由”,可予以撤銷。參見Antonio R. Parra, the History of ICSI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p.360.該委員會針對仲裁庭要求阿根廷的安全例外抗辯須滿足“必要措施”是“國家保障其陷入嚴重和迫在眉睫的災難之根本利益的唯一方法”,且在論證阿根廷采取的措施并非“唯一方法”時,未充分闡明理由。比如,該仲裁庭沒有充分闡釋“唯一方法”的含義。“該表述有多種可能的解釋。一種潛在的字面解釋為在諸如本案的情況下,阿根廷所依賴的必要性原則是它確實不可能采取其他措施應對經(jīng)濟危機。”54同前注52,para.369.誠然,一國政府面臨經(jīng)濟危機可能有多種應對方法,然而,這并不意味這就是正確的解釋。政府可能考慮有必要采取不違反或最少違反其國際義務的措施,而這可能正是“唯一方法”。再如,可替代的方法是否有效,等等。該案仲裁庭過于依賴支持外國投資者的專家有關阿根廷采取的并非“唯一方法”意見,而徑直作出相關認定。該委員會通過多方面分析,指出該案仲裁庭沒有充分陳述理由,決定撤銷該裁決。55同前注52,para.395.
(二)國際投資協(xié)定中安全例外條款的“基本安全利益”
CMS煤氣輸送公司訴阿根廷案也涉及阿根廷與美國BIT第11條的解釋。在該案中,阿根廷政府首先否認該公司的投資損失與其經(jīng)濟管制措施有關,其次作為可替代的實體性抗辯理由,援引了應對當時經(jīng)濟危機的《緊急狀態(tài)法》,“作為豁免國際法與條約項下責任的依據(jù)”。56CMS Gas Transmission Co., v. Argentina, ICSID Case No. ARB/01/8, Award, May 12, 2005, para.99.阿根廷政府認為該危機所涉經(jīng)濟利益構成“嚴重和迫在眉睫的災難所威脅的國家基本利益”,“《緊急狀態(tài)法》出臺的唯一目的在于控制阿根廷面臨的經(jīng)濟社會崩潰的混亂局勢。基于該危機的必要性應排除政府采取措施的非法性,尤其是不負賠償責任。”57同上注56,paras.305-306.
首先,該案仲裁庭認為:涉案BIT“顯然旨在保護經(jīng)濟困難或政府采取具有負面作用的措施之情形下的投資。然而,問題在于這些經(jīng)濟困難可能嚴重到什么地步。嚴重危機不一定等于完全崩潰的情況。”58同前注56,para.353.這并不是解釋“基本安全利益”本身,而是解釋在什么情況下必須采取例外措施保護基本安全利益。換言之,基本安全利益取決于經(jīng)濟困難的程度,如果到了“完全崩潰”的地步,一個國家難以維持生存,那就涉及基本安全利益了。“在缺少此類根本性嚴重條件的情況下,很清楚,條約[保護投資]將優(yōu)先于任何[例外措施]必要性的抗辯。”59同前注56,para.354.根據(jù)該仲裁庭的評估,阿根廷的經(jīng)濟危機尚未到“完全的經(jīng)濟及社會崩潰”,因此,還缺乏援引涉案BIT安全例外條款的理由。其次,該仲裁庭以聯(lián)合國國際法委員會起草《國際責任》條款第25條第1款(a)項為依據(jù),認為一國僅在應對國家基本利益處于嚴重迫切危險的措施為“唯一”時,方可豁免由此違反其國際義務的責任。在本案“并沒有顯示相應義務存在的國家基本利益或國際社會作為整體的利益受到損害。”60同前注56,para.358.再次,該案仲裁庭認為涉案BIT第11條雖未提及任何種類的經(jīng)濟危機或困難,但也不能排除該條款包含主要的經(jīng)濟危機。這實際上間接地解釋了該條款“基本安全利益”包括經(jīng)濟危機所觸及的國家基本安全。“如果基本安全利益的概念限于直接的政治和國家安全關注,尤其具有國際特點。并排除其他利益,比如主要的經(jīng)濟緊急狀況,這會導致對該第11條的失衡理解。”61同前注56,para.360.在承認基本安全利益涵蓋“主要的經(jīng)濟緊急情況”的基礎上,該案仲裁庭認為關鍵在于如何認定經(jīng)濟危機的程度以及構成可采取例外措施的基本安全利益,并最終否定阿根廷的抗辯。總之,涉案安全例外條款下基本安全利益雖包括經(jīng)濟危機,但該危機須達到國內(nèi)經(jīng)濟崩潰的地位方可采取例外措施,且沒有其他可選擇的方法。
值得留意,阿根廷對該案裁決不服,請求予以撤銷,理由包括該裁決沒有充分陳述涉案安全例外措施未滿足“唯一”性要求。審理該撤銷請求的臨時委員會承認:“該仲裁庭沒有提供任何有關第11條的決定之進一步理由。……在本委員會看來,雖然該裁決的[說理]動機可以更清楚一些,但是,仔細的讀者可以理解該仲裁庭隱含的理由”。62CMS Gas Transmission Co., v. Argentina, ICSID Case No. ARB/01/8(Annulment Proceeding),September 25, 2007, paras. 123,127.與前案撤銷委員會對這一問題的復審不同,該撤銷委員會顯然對此敷衍了事,偏袒外國投資者。
(三)比較國際貿(mào)易協(xié)定安全例外條款的解釋判理
比較國際貿(mào)易、投資協(xié)定的安全例外條款及其解釋,可見,雖然有關條款均有“其認為”或“不得排除”等具有“自裁性”含義的用語,且上文所分析的案例都反映美國(雖都不是涉案當事方)主張適用安全例外條款的“自裁性”,但是,WTO國際貿(mào)易協(xié)定和至少本文分析所涉美國與阿根廷BIT的安全例外條款經(jīng)解釋均不具有“自裁性”。值得比較的是其不同的解釋判理。
比如,俄羅斯過境案專家組將GATT第21條(b)款引言句的“其認為”與涉案(iii)項的“國際關系中的其他緊急情況”作為整體解釋,認為采取安全例外措施的成員主觀上“其認為”的前提是發(fā)生了需要爭端解決專家組經(jīng)過客觀評估,加以認定的此類緊急情況。由此推理,該案專家組首先解釋什么是此類緊急情況,并將解釋澄清的此類情況中的第一類“武裝沖突或潛在的武裝沖突”適用于涉案事實,認定在該案中確實存在此類緊急情況;然后,再回到解釋“其認為”保護的“基本國家安全利益”含義及其采取措施的必要性,并認為援引安全例外的成員有權對此判斷,但應秉承善意,避免將安全例外“作為規(guī)避其義務的手段”。63同前注?,WT/DS512/R,para.7.133.沙特知識產(chǎn)權案將此類措施的“必要性”解釋為需滿足援引安全例外的一方是否形成相關“根本安全利益”并足以能夠判斷所采取的行動與之相關性。
再如,安然公司訴阿根廷案在承認允許將經(jīng)濟緊急狀況納入涉案BIT第11條上下文的解釋同時,強調(diào)將該條款解釋為自裁性條款肯定與該條約之目的及宗旨相悖。在該案仲裁庭看來,BITs目的就是保護外國投資者,如聽任東道國自行判斷可否采取安全例外措施,就難以實現(xiàn)該目的。CMS煤氣輸送公司訴阿根廷案從另一角度駁回了阿根廷主張的安全例外條款“自裁性”,認為東道國可自行判斷和采取相關措施,但是,“如果此類措施的合法性在國際法庭受到質(zhì)疑,那么就不是涉案國家,而是有管轄權的國際法庭決定必要性抗辯可否排除非法性。”64同前注56,para.373.這種看法已超出了條約解釋范疇,認為一旦進入國際爭端解決程序,就不存在安全例外條款的“自裁性”。至少這兩起國際投資仲裁庭站在外國投資者一邊,都沒有對安全例外條款“自裁性”進行符合條約解釋慣例的充分解釋。
無論人們怎樣看待國際經(jīng)貿(mào)協(xié)定的安全例外條款“自裁性”,國際經(jīng)貿(mào)爭端的否定性實踐表明相關的爭端解決專家組或仲裁庭均擁有管轄權,已是不爭的現(xiàn)實。比較而言,國際貿(mào)易協(xié)定的安全例外條款比較完備,包括“其認為”采取必要措施的“國際關系中的緊急情況”通過解釋延伸為“武裝沖突或潛在的武裝沖突”“高度緊張或危機”和“一個國家內(nèi)或周邊普遍的不穩(wěn)定狀態(tài)”,以及援引安全例外的一方須形成相關“根本安全利益”并足以能夠判斷所采取的行動與之相關性。也正是這樣的緣故,如今一些BITs的安全例外條款,如上文提及日本與烏茲別克斯坦BIT,更接近于國際貿(mào)易協(xié)定安全例外條款的共同模式。
總括全文,可以得出初步結論:條約法上的安全例外觀念出自于一般國際法上的“自我保全”原則;《聯(lián)合國憲章》的自衛(wèi)條款是條約法上第一次明確規(guī)定相對于禁止使用武力原則而言的國家安全例外條款;在國際經(jīng)貿(mào)條約方面,GATT第21條是最初的安全例外條款,并發(fā)展為WTO貨物和服務貿(mào)易以及貿(mào)易相關知識產(chǎn)權三大實體性條約共同的安全例外條款;國際投資條約的安全例外條款從隸屬公共秩序例外逐步延伸并發(fā)展為單獨的條款,與國際貿(mào)易條約的安全例外條款趨同,但尚無統(tǒng)一表述。國際經(jīng)貿(mào)條約的安全例外條款在有關爭端解決的適用中經(jīng)過條約解釋,大致可以進一步理解為:援引一方主張自行判斷可否采取安全例外措施的“自裁性”已被否定;安全例外的抗辯一方可自行決定采取相關措施,但一旦進入國際爭端解決程序,其必要性以及“基本安全利益”的認定則不具有“自裁性”;國際貿(mào)易條約安全例外條款中有關“國際關系中的緊急情況”涵蓋的范圍有所擴大,國際投資條約安全例外條款中的“基本安全利益”的界定傾向于相對保護外國投資者的利益而言,限于因經(jīng)濟危機導致國家經(jīng)濟社會崩潰此類極端情況引起的東道國安全利益。對于我國目前參與國際貿(mào)易爭端解決相關安全例外條款的適用與解釋,以及今后可能參與國際投資仲裁涉及的安全例外問題而言,65比如,《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加拿大政府關于促進和相互保護投資的協(xié)定》(2012年9月9日簽署,2014年10月1日生效)第33條第5款規(guī)定了安全例外。期待本文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