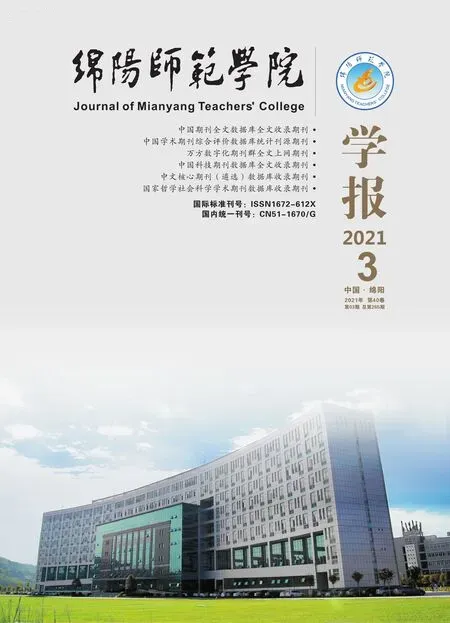論《媽閣是座城》的創作思想
——從遺傳學談起
童穎瑤,杜明業
(淮北師范大學外國語學院,安徽淮北 235000)
長篇小說《媽閣是座城》單行本出版于2014年,這是嚴歌苓赴美25年之后,在兩國文化的縫隙中對人性冷峻觀摩的書寫,真正做到了用“異國方式(以自然科學的方式)講述中國故事”。嚴歌苓于1989年11月到美國哥倫比亞藝術學院攻讀文學寫作學碩士學位,這也是她寫作呈現轉型態勢的重要因素之一,此后,她的文學寫作大致從以往的宏大敘事轉向以世界為眼光、以跨學科的模式繼續從事文學創作。這正如她本人所說:“出國之后,有了國外生活的對比,對人性有了新的認識,再后來接觸心理學、人類行為學,很多事情會往那方面聯想,會把善惡的界限看的寬泛一些。”[1]
《媽閣是座城》的寫作正是這一創作思想的感性再現,即將自然科學理論(遺傳學)運用于文學創作之中。該小說是嚴歌苓繼《拉斯維加斯的謎語》之后,又一部深度刻畫賭徒的文學作品。兩部小說對賭徒的塑造,在情節(賭博—追債)以及人物形象的塑造上(老薛、段凱文等人在成為賭徒之后從正派人物變成老賴)顯然打上了嚴歌苓鮮明的個人痕跡,兩者之間具有一脈相承之處。相比之下,《媽閣是座城》是在歲月流轉中沉淀后的產物,其以遺傳學理論為創作基點,從家族遺傳角度、種族遺傳角度以及遺傳的辯證角度,深入關照了遺傳之于人性的意義。
一、遺傳基因:烙印在家族后代的記憶符號
《媽閣是座城》是將自然科學理念熔鑄于文學創作之中的產物,遺傳學說理論是開啟該部小說創作的鑰匙。1892年,德國生物學家魏斯曼提出了有關遺傳物質的種質學說,這一學說有兩個基本論點:其一,生物世代間遺傳物質只有通過細胞分裂和雌雄生殖細胞的受精才能得到傳遞;其二,生物體可以截然區分為種質和體質兩類細胞,其中只有種質細胞才能把親代的遺傳物質傳遞給后代[2]。也就是說,生物的遺傳主要在于種質細胞在家族世代的傳承中呈現出不可磨滅的連續性影響,內在的種質通過外在的體質表現為遺傳,這種遺傳不會被后天環境所影響,具有不可更改性。
小說首先運用的就是遺傳基因對后代產生影響的思想。這種影響就像是一種記憶符號深深地烙印在家族后代的靈魂深處,不會隨著經年久遠而消失殆盡,反而在一代又一代的傳承中深化這種遺傳因子,使得某個家族呈現出具有相似性的人格亦或是形貌特征。魏斯曼提出的種質學說強調的是人體外在的生理特征具有遺傳性,這也就能夠從遺傳的角度合理解釋家族中所產生的生理遺傳現象。那么個體經過內化而形成的性格特征與這種遺傳也具有緊密聯系,俗話說“有其父必有其子”強調的不僅是外貌特征的相似性,也有內在個性的相似性。魏斯曼從科學的角度為這種說法提供了相對合理的解釋。《媽閣是座城》顯然呈現了后者所反映的內容,即遺傳基因在家族之中使得后代成員在命運、本性等方面皆具有傳承性,這就是遺傳基因作為一種家族的記憶符號深深地烙印在后代身上的外在顯現。
敘述者通過回顧性敘述以及全知視角使得基因具有遺傳性這條主線清晰可見:梅大榕——梅亞農——梅曉鷗——梅曉鷗的兒子,前三代人雖然生活的年代相距甚遠(不包括梅曉鷗兒子,因為他與母親生活于同一時代),但賭性卻是綿綿相傳、更延不迭,尤為深刻的是小說將這種賭性以一種隱形的方式傳承到了梅曉鷗的身上:梅曉鷗本身就有一種特殊的能力,她能夠從混跡于茫茫人海的賭徒里面挑選出最具有潛力的客戶。這種特殊能力原來“是他祖先梅大榕把這雙眼給她的......是它給了曉鷗好眼光去辨認有發展前途的賭客”[3]91。在揭露梅曉鷗骨子里的賭徒形象時,嚴歌苓并未使用任何文字來描寫梅曉鷗是怎樣沉迷于賭博的,而是以一種不動聲色的隱含立場將梅曉鷗骨子里的賭性刻畫得絲絲入扣。她雖然沒有直接在活色生香的澳門賭場與形形色色的賭徒、游客賭博,但是這并不意味著梅曉鷗的血液中沒有留下梅大榕身上的賭徒血脈,反之她更愛賭,也更敢賭:她敢于去賭誰會成為她最有潛力的客戶,而且她還會站在段凱文的背后通過間接參與賭博的方式,享受著輸贏那一剎的歡暢;此外,梅曉鷗與那些只賭金錢的賭徒不一樣,她賭的是賭徒人性背后的善惡美丑。因此她賭得更大膽、更奧妙。
另一條遺傳線索是以梅曉鷗為核心的暗線。這條線索展現了她與梅吳娘及其母親之間極為相似的命運。梅曉鷗(靠著愛賭博的富翁獲得抽成積累財富)與梅吳娘(因梅大榕嗜賭如命而開辟出自己的繅絲事業)都是被惡習滋養的人。她們依靠他人的惡習成就了自己的事業,實現了個體經濟能力。在幫助孩子戒賭這件事上兩位母親所采取的方法也呈現出驚人的一致,她們都試圖通過地理位置的遷移來改變賭風盛行的生存環境,從而讓自己的孩子遠離賭博:梅吳娘為了戒掉梅亞農的賭癮從廣東搬到了上海,梅曉鷗為了戒掉自家孩子的賭癮從媽閣搬到了溫哥華。這一舉動頗似歷史上著名的“孟母三遷”。
除此之外,她們也都曾生發過殺死自己孩子的念頭。梅吳娘使在梅亞農出生之前的男孩子都失去了生命,而梅亞農幸存是因為他的爺爺奶奶在他剛出生快要被梅吳娘掐死的時候,從她母親的手中搶下來的。梅吳娘與梅曉鷗的殺子行為包含了二元對立的矛盾沖突,其中不僅內含了“具有原罪性質的宿命設計”,即宿命與現世的對立,而且還帶有顛覆倫理的“殺子復仇”思想(將梅吳娘異化成美狄亞)[4],也就是父親與兒子之間的對立。嚴歌苓將西方文化因子融入到“中國故事”的講述中,以特有的敘事方式,表達了命運不可抗的特性。在《媽閣是座城》中,對于梅曉鷗來說命運仍然具有不可抗力,只不過前者是受西方文化中宿命論的影響,而后者強調的是遺傳在個人命運中所起到的作用。
而梅曉鷗同她母親命運的相似之處在于:她們都在中年重新邂逅愛情但卻遭到自己孩子的排斥。因年代以及整個文化氛圍、具體事件的復雜程度不同,曉鷗母親的第二次愛情有了結果,而曉鷗卻沒有如此幸運。這部分的情節在文本中是以第三人稱全知敘述視角展開的敘述,縱觀全文來看,除了梅姓氏族有著驚人相似的遺傳基因之外,盧姓氏族也同樣如此,“這個中級干部的兒子從父輩就脫貧了呀,而這體態從他餓死的祖輩通過精血秘密流到他身體里,在這一刻返祖,活靈活現”[3]56。如果說梅姓氏族遺傳下來的是賭性,那么盧姓氏族遺傳下來的就是窮性。兩大不同家族的遺傳因子根深蒂固地溶進了后代血脈之中,也溶進了后代的秉性。這樣的傳承彰顯出基因遺傳之于家族后代命運、本性的意義。
就文本本身來看,該小說敘事手法異常復雜,全知視角、回顧性敘述視角、固定式人物有限視角等敘事手法流轉于全文,在繁復瑣雜中仍然有跡可循、有條可捋,且呈現出一定的敘事規律:嚴歌苓在創作之際采用了具有延續性的敘事手法,即將梅曉鷗置于核心地位,開枝散葉于過去和現在,將其對往事的回憶交融進當下的語境中,使得過去與現在連接,這樣的敘事方式(過去與現實相交融)吻合了其創作思想,即強調遺傳基因(包含過去與現實)在家族中的傳承性。正是過去與現在的情節交織才使得小說敘事手法看上去是繁復的,而這樣時空交錯的表現手法呈現出了時間的延續性,繼而關涉到遺傳的延續性,在一定程度上表現了遺傳基因對于家族后代品性塑成的影響。
整體而言,《媽閣是座城》創作思想呈現的是“骨”與“肉”交融的結果。其以敘述技巧作為“骨”有機地連接了作為文字內容的“肉”,以這樣相互匯通的架構文字的方式使得小說具備了洞悉人物心靈、透視人物靈魂的獨特價值,以此種方式區別了其他媒介(電影、音樂等)塑造人物精神、表達主題思想的作用,將人性最微妙的那一縷浮動絲絲呈現出來。敘述者在體現遺傳思想的時候往往以第一人稱回顧性敘述視角來展望曾經的人(主要是梅曉鷗回顧自己家族中的人),然后再以血緣或種族一脈相承的關系為紐帶,使得過去與現在的人性相通,進一步佐證了遺傳理論思想在小說中運用的合理性。
二、遺傳基因:塑成了種族特有的國民性
遺傳理論思想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小說中人物性格塑成的原因,如若讓這樣的遺傳思想走出個體小家族來到整個社會,這種遺傳基因的影響會將一個種族內部的人格特點相互勾連。也就是說當遺傳因子從家族范圍擴展到整個種族范圍的時候,就解釋了為何同一種族的人擁有相似的性格特征,這樣的特征又被稱為國民性。因此,《媽閣是座城》除了強調家族根性對后代的影響之外,還凸顯了種族遺傳對國民性的影響。在種族問題上,丹納將“種族”定性為是影響一國文學風貌、精神的最重要因素(相較于環境、時代而言)。他認為種族“是指天生的和遺傳的那些傾向,人帶著它們來到這個世界,而且它們通常更和身體的氣質與結構所含的明顯差別相結合。這些傾向因民族的不同而不同”[5]12。簡而言之,各民族是不相同的,而民族之內的民族性卻具有相似性。種族遺傳就發生在其內部,也就是在特定、具體的社會環境中所生成的國民性。這種脾性在浩蕩的歷史長河中、紛繁的人事悵惘中不易更改。
丹納定義的種族更重要的是指建立在共同地域、心理、血緣關系之上的民族精神,是一種民族性格與民族特征的復合物[6]。另外,丹納在提出“種族——環境——時代”三因素學說的時候,也是將自然科學的研究模式應用于人文科學之中,這正如他本人所說的那樣,“美學本身便是一種實用植物學,不過對象不是植物,而是人的作品”[5]28。丹納這種將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相結合的路子,與嚴歌苓將遺傳學理念應用于文學的創作有著異曲同工之處。
將丹納的“種族”概念遷移到《媽閣是座城》中,則詮釋了種族遺傳對于國民性塑成具有不可磨滅的影響。從科學角度定義的種族概念與小說文本所運用遺傳學理論的創作思想之間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即小說中的人物在面對賭博時,不同姓氏的中國人有著高度相似的行為。至于國人為何會如此狂熱于賭博,在小說中已有表示。敘述者將人們對賭博的熱衷追溯到中國自古以來世代相傳的“災民意識”,即“我們在集體潛意識中,對財富的渴望是那么熱切、危急、致命,之所以如此是因為連年戰亂饑荒,天災人禍”[7]。也就是說想要發財就要抓住戰爭與戰爭之間的短暫和平,這就造成了國人的國民性中留下了根深蒂固的致富原則,即速度要快、金額要大,而賭博正是符合這一原則的謀獲金錢行為的外在表現形式。
在這短暫的和平間隙,可以暫時告別戰亂。窮人想著致富,但是富人卻想著要追求及時的快樂,在戰亂之時即便是家財萬貫也可能隨著一聲轟炸在頃刻間化為灰燼,而賭博在分秒之內給人所帶來的快感卻是其他娛樂活動無法與之相媲美的。因此,賭博也就具有了雙重屬性:一方面滿足了人們在短時間內求富的愿望;另一方面也迎合了一部分人追求刺激的娛樂心理。這里揭示了構成特定國民性是由地域外部與個體內部共同導致的。而種族特有的屬性正是由這內外兩重因素相互交匯的結果,由此來看,賭性在國民性的生成中有著特定的內部條件以及外部環境。
此外,小說中出現“中國人”“華夏子孫”這樣指向確切的限定詞,還有為數不多的“美國人”。只有通過“他者”看“我者”,在比較關照之下才能更好突出“我者”的國民性。文本不僅通過固定式人物(梅曉鷗)有限視角稱贊美國人是全世界最愛兒童的,而且還以全知視角稱贊美國醫護人員的救人心切。嚴歌苓筆下不乏此類書寫,在《金陵十三釵》中也有對美國傳教士的善美書寫,這些都可以看出嚴歌苓正以其跨文化的視域將美國人烏托邦化。而在《媽閣是座城》中嚴歌苓運用的遺傳學創作思想所關照的正是國人國民性中特有的賭性,而并非世界人民共有的賭性。
賭性,固然也是人性,《媽閣是座城》中所鐫刻的賭性是作為國民性的一部分來呈現的。首先,梅大榕與盧晉桐是沒有任何血緣關系的,當他們賭輸了之后,卻不約而同地選擇割手指這樣殘忍的方式試圖麻痹自己;其次,梅大榕最后以跳海結束了自己的生命,而在媽閣海灘上也時常打撈起一個又一個前“豪杰”。割手指與跳海仿佛成為了賭徒們解脫自我的慣用手法,直到今天,這樣的行為也在不同的地方屢屢上演。這里種族遺傳的表現之一就在于面對同樣事情的時候,該種族的內部人群往往會有相似的行為舉止。關于國人對于賭博的熱衷,嚴歌苓在《拉斯維加斯的謎語》(1997)中早有體現:將中國人熱愛賭博、享受著輸贏那一剎所帶來的快感的國民形象活靈活現地溢于紙上,其中尤以老薛最為典型。在生活中,老薛寧愿拿簡單的三明治充饑,對于日常所用的大部分物品也都能夠想辦法使其循環使用。可在生活中如此節儉的老薛卻毫不吝嗇地將大把的錢幣一次又一次投進老虎機中,對賭博的癡迷竟達到如此程度。可見,嚴歌苓早就意識到了賭性是國民性中具有典型性的特點之一,然而在《拉斯維加斯的謎語》中所呈現的賭性還不夠復雜,還不夠深刻,更不夠宏遠。以一種更為成熟和全面的眼光完整呈現國民性中的“賭性”,還要以17年后的《媽閣是座城》的完本落下帷幕。
可以說,人性經種族遺傳而外化為國民性的思想是嚴歌苓在該小說中運用的一個重要創作理念,其理論支撐就在于丹納的“種族”理論。小說突出強調了種族遺傳對國民性的塑成具有深遠的影響。這不僅能夠深度剖析嚴歌苓本人的創作思想,而且還升華文本更深一層次的內涵,從而以一種全局視野進一步觀摩中國國民性在歲月的洗禮中經轉百變所留下的痕跡。《媽閣是座城》揭示了遺傳因子與種族之間具有不可磨滅的關系,貼近任何一個時代、任何一個社會中人性的發展以及演化。
三、遺傳基因:在人性發展進程中具有辯證屬性
《媽閣是座城》一方面彰顯了遺傳之于家族的影響及其對于國民性塑成的重要意義,另一方面又將這樣的主題予以了更深一層的升華,即并未將遺傳對人格的影響絕對化認定,反而合乎情理的對既定的具有一成不變的遺傳準則提出了挑戰,即承認了遺傳的辯證性。遺傳基因的確會影響人們的行為甚至是心理,根據這一現實情況,一門叫做“行為遺傳學”的科學應運而生,行為遺傳學是一門探討行為的起源、基因對人類行為發展的影響,以及在行為形成的過程中,遺傳和環境之間的交互作用的學科[8]。行為遺傳學研究的爭議止于20世紀70年代,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尤其是90年代,行為科學家們越來越接受基因的影響的觀點[9]。由此可見,遺傳基因對人的諸多行為及其心理狀態均會產生不同程度的影響,然而遺傳基因對后天行為的影響并不具有絕對性。著名遺傳學家普洛明(Plomin)就將個體心理體質的差異歸為遺傳、共享環境以及非共享環境三個方面[10],也就是說除了遺傳基因這種內部原因,外部因素對人性的塑成也具有不可磨滅的重要作用,甚至后天環境對人性的影響更為突出、顯著。
小說通過極為隱蔽的兩處情節巧設體現了嚴歌苓本人關于遺傳的辯證思想,這種思想并非完全肯定遺傳在家族以及種族中所扮演的不可更變的角色,反而質疑了遺傳的絕對性,使得遺傳這一創作思想褪去了扁平化、單一化且不可更改的屬性,為其重新罩上了一層立體化、不確定性的面紗。梅大榕是梅姓家族中被賭博戕害最深的人,他付出的代價也是最為慘痛的,這一脈流淌著“頑劣賭性”的血液一直綿延到梅曉鷗的兒子身上。然而就整個家族而言,這一脈血緣中所攜帶的“賭性”基因卻騰空越過了梅亞農。雖然梅亞農在小時候也有賭博的傾向,但是在梅吳娘的努力下將其骨子里僅存的賭性清除得干干凈凈。他本是梅吳娘想要掐死卻被梅家的公婆拯救下來的唯一的兒子,在他十二歲的時候就已經學會了和幾個小同學一起賭繭的雌雄,梅吳娘知道后不惜賣掉自己的繅絲坊帶梅亞農從廣東來到上海,試圖使兒子遠離賭博的環境;來到上海之后,梅亞農又和孩子們賭些小玩意兒——“賭馬,賭狗,賭蟋蟀”[3]145,梅吳娘得知他又參與賭博后將爐子通心條放在梅亞農的手心上,以此懲戒梅亞農的賭博行為,以慘痛的代價在他心中刻下終身難忘的記憶,自此之后梅亞農再也不賭博了,還考取了北京的京師大學堂,可謂是學業有成。
從基因遺傳的角度來看,梅亞農身上攜帶著梅大榕的“賭性”,但是其人格的變化是后天養成的。以普洛明為代表的一些學者非常強調非共享環境的作用,即強調后天教養及個體在家庭內外的獨特經驗對人格發展的重要作用[11]。因此,從情節設置來看,梅亞農戒賭這一情節安排質疑了遺傳不可更改的價值準則,質疑了一般意義之下具有普世性質的遺傳準則。
除了質疑遺傳在血緣關系中不具有絕對化意義之外,嚴歌苓在另一情節的安排中也挑戰了賭性在國民性中不可更改的客觀印象。小說中的三個男性賭徒——盧晉桐、史奇瀾和段凱文,可以說流連賭場、沉湎賭博、頹唐消殆的賭性同樣根深蒂固,他們三個之間沒有任何血緣關系,唯一的共性就是他們都是華夏子孫。他們基因里的賭性代表了國民性中特有的賭性,然而賭性并非不能戒,也就是說國民性也不是永遠不會被更改的。這一情節巧妙穿插在梅曉鷗對史奇瀾說的一句話中,曉鷗說:“不沾就證明還沒有真正戒賭。為什么?因為戒賭就像戒酒,一滴酒不沾不叫真戒,沾了不醉才叫真戒。”[3]406史奇瀾為了向梅曉鷗證明自己真的戒賭了,身體力行地從賭臺邊站起來,走出賭場。所以說即便是沾染上賭癮也不是不能戒掉的,國民性雖是由特定的歷史文化環境等諸多因素塑成的,但是這也不是一直扣在某類人身上永遠也撕不掉的標簽。
在既定的價值評判中,遺傳是不可更改的,所謂“江山易改,本性難移”即是這樣思想的外現。《媽閣是座城》對這樣絕對化的遺傳思想予以了有力的質疑,從科學的角度來看,這種質疑也存在合理之處。遺傳本來就具有復雜性、不確定性以及非絕對化,正如達爾文在《物種起源》中所認為的那樣:“控制遺傳的法則還不太清楚;沒人能說出為什么同一物種的不同個體和不同物種的個體,它們之間的共同特性有時候遺傳,有時候又不遺傳。”[12]13因此,遺傳無論是在家族中還是在種族中,其產生的效用都不是絕對化的,要因人、因時、因地,將具體情況匯聚一起進一步探析,這也就打破了人們慣有的關于遺傳具有不可更改性的認知標準。而賭性如此深厚的梅氏家族中的梅亞農戒了賭,這一情節與之后史奇瀾也戒了賭形成了強烈的互文。前者回擊了家族遺傳的不可更改性,后者回擊了國民性的一成不變。這種呼應與整個文本中其他遺傳思想相互對立,使得嚴歌苓本人的創作思想顯得更為復雜且深奧。最后,通過這樣的情節設計使得文本的思想不拘泥于傳統且更為開闊地展現了遺傳基因在人類的發展中具有發展變化的屬性。
對遺傳的絕對性提出質疑符合各個時代運行、進步的潮流。如果一直秉持遺傳是不可更改的這種自封自閉、停滯不前的思想,那么人類進步的動力也終將枯竭。正如約翰·穆勒所說的那樣:“當前有一種普遍的傾向,認為人的性格中一切突出的特征都是先天固有的,基本上是不可消除的。這種看法是理性處理社會問題的最主要的障礙之一,是人類完善提升最大的絆腳石之一。”[13]184這段話直接否定了人性不可更改這一常規意義上的論斷,也就是否定了遺傳絕對化的思想,為人類主體的進步、發展提供了理論依據。嚴歌苓將這樣繁復多樣、博大精深的創作理念運用于小說的創作中,極大地豐富了小說的思想主題及其現實意義。
四、結語
《媽閣是座城》這部長篇小說關于人性中“賭性”的豐富思考離不開嚴歌苓本人中西交融的雙重文化背景。她以其特有的生活體驗及其廣博的跨文化、跨學科的學識素養,做到了用“異國方式”講出“中國故事”。小說對于“賭性”的刻畫是以燈紅酒綠的澳門賭場為背景的。她不僅從血緣的角度聚焦了梅氏家族賭性的流傳以及變異,還關注了非血緣關系的段凱文、史奇瀾等具有個體特質的“賭性”演化,最后通過“賭性”在梅亞農以及史奇瀾身上的異化(戒賭)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人類個體具備自我發展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