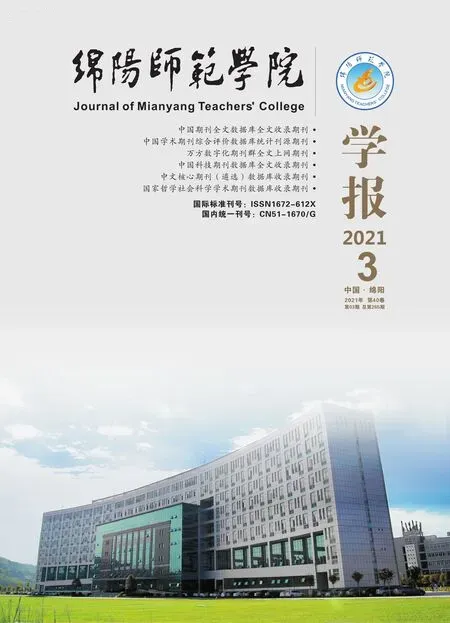館閣文臣王士熙的詩歌創作與大元氣象的書寫
戴歡歡,任聲楠
(1.合肥師范學院文學院,安徽合肥 230601;2.江蘇師范大學文學院,江蘇徐州 221116)
王士熙(約1266—1343)字繼學,東平(今屬山東)人。其父王構,仕元為翰林學士。王士熙早年師從鄧文原。至治初任翰林待制,泰定四年(1327)累官至中書參政。泰定帝薨后,卷入皇位爭奪,失勢后下獄。文宗即位后,便被流放至遠州,次年得以還鄉。順帝即位,起任江東廉訪使,于后至元二年(1336)遷南臺侍御史,至正二年(1342)升南臺御史中丞,未幾卒。追封為趙國公。《圖繪寶鑒》卷五載其“善畫山水”[1] 154。王士熙與其弟王士點以文學世其家,士熙原有詩集,惜未傳,清顧嗣立《元詩選》二集輯其詩116首,用原集名為《江亭集》。王士熙詩,長于樂府歌行,且其詩歌多為唱和之作,其唱和對象主要是袁桷、馬祖常、虞集、揭傒斯、宋本等館閣文臣。
一、王士熙的生平與思想
王士熙出身于文學仕宦之家,其父王構“少穎悟,風度凝厚。學問該博,文章典雅,弱冠以詞賦中選,為東平行臺掌書記。參政賈居貞一見器重,俾其子受學焉”[2]3855。世祖時期,王構入翰林,為侍講學士。成宗即位,纂修實錄,書成,為參議中書省事,生平事跡詳見于《元史》。在《元史·王構傳》后尚有對其二子的簡介:“子士熙,仕至中書參政,卒官南臺御史中丞;士點,淮西廉訪司僉事,皆能以文學世其家。”[2]3856王士熙的家庭是傳統的業儒之家,他在仕宦之路上雖歷經沉浮,但也有一段時間得到重用,并有扈從皇帝巡幸兩都的經歷,這對漢族文臣來說是難得的。王士熙一方面延續了其家庭出仕的傳統,另一方面也以文學世其家。對此,元人胡助在其《挽王繼學中丞》詩中寫道:“玉堂揮翰瀉珠璣,家學光華世所稀。但覺高才無滯事,安知平地有危機。妙年臺閣祥麟出,晚節江淮退鹢飛。惆悵百身曾莫贖,生芻一束淚沾衣。”[3]610第一句,胡助就對王士熙的文學才能予以稱贊,并且分析了其背后的家學影響因素。而“妙年”“晚節”二句寫出了王士熙的身世浮沉之境況。王士熙自小受儒家思想影響,所以有儒家典型的入仕之精神。但是對于儒家思想的學習,他有自己的看法:“生平不愿為慵書,亦不愿作章句儒。”(《贈廣東憲使張漢英之南臺掾》)[4]4,在王士熙看來,他是不齒于死讀書的,也不愿作只拘泥于辨析章句的儒生,但是對于儒學大師許謙,王士熙還是頗為推崇的,曾“訪謙于山中,謂謙清氣逼人,可畏既退,論薦于朝”[5]40。王士熙作為北方儒士,在元代入仕相較南人容易許多,他對自身的才能亦較為自信,“才高不用長嘆息,四海彌天豈無識”(《贈廣東憲使張漢英之南臺掾》)[4]4。王士熙至治初年時即任翰林待制,供職京師,后于泰定四年(1327)累官至中書參政,達到了人生的巔峰,可謂“圣主敷皇極,元臣建上臺”(楊載《寄王繼學二十韻》)[6]27,進入了統治階級的高層。但是他的仕途并非一帆風順,由于他之后卷入皇位爭奪之中,因此下獄,后慘遭流放。元順帝即位之時,雖又起用王士熙為江東廉訪使,并于至正二年(1342)升南臺御史中丞。但經歷過宦海沉浮之后的他,不禁感慨“飄然閱浮世,獨立寂無語”(《石人峰》)[4]15。王士熙沒有了年少之時的豪情壯志,而是產生了“燕市塵深拂衣去,海門何處問魚蓑”的想法,歸隱的念頭縈繞心中。對于王士熙的形象,柳貫有《王繼學畫像贊》:“粹然冰玉之英展也,星凰之瑞,用則盛之鸞臺鳳閣,不用則置之朱崖儋耳。老智慮于多艱,觀夷險于一致,固將挾玉局之飛仙,以游夫鴻濛溟涬之際。所謂瑯瑘之宗魯公之子,而盛德之世者也。”[7]397此中多為溢美之詞,可見王士熙在當時頗具名望,其落難時,比之于李德裕(貶朱崖)、蘇軾(貶儋耳),其升官時,張翥有《王繼學廉使遷南臺侍御史詩以賀之》。
入朝為官是王士熙的主要人生追求,這是其在儒家思想影響下形成的強烈的用世精神。元代社會,思想文化政策相對寬松,儒、釋、道等各家思想對士人都或多或少的產生影響。王士熙一生并非只受儒家思想影響,還有較為明顯的道家思想痕跡,在其行為上主要表現為求仙問道,這在其詩歌中有較為普遍的反映。王士熙在仕途上有起有落,面對如此的人生經歷,心里難免有對閑逸生活的向往,這在其《題幽居》詩中有所抒發:
最愛幽居好,青山在屋邊。竹窗留宿霧,石檻接飛泉。
采藥蟾奔月,吹笙鶴上天。 世途塵擾擾,裁句詠神仙[4]7。
整首詩句語言淺近,易于理解,詩人表達了對紛紛擾擾的塵世的厭倦。他想深居簡出,與自然為伍,過著神仙般逍遙自在的生活。因此,在王士熙的思想中,儒家的用世和道家的出世思想是并存的,積極用世是其現實之舉,但當詩人仕途失意之時,道家出世想法又為其提供了精神慰藉。王士熙身為元代的館閣文臣,與馬祖常、虞集等同僚唱和館閣,他交游對象的身份并不單一,與道士也有往來。如元代道士吳全節,同樣出身于儒門,得到元朝廷的重用,時朝中儒臣如高昉、賈鈞、王士熙諸人“多所咨訪”(《河圖仙壇之碑》)[8]365。另其有詩《送袁道士二首》其一:“五公舊譜漢廷傳,之子飄飄去學仙。山里牧羊成白石,云間騎鶴上青天。黃庭夜月迎三疊,綠綺秋風度七弦。拂袖京城留不住,別離可奈落花前。”[4]10朋友袁道士要離京學仙去了,王士熙想象其學仙的場景,字句中透露出羨慕之情,對朋友的離別也十分不舍。王士熙所受的道教思想,其中的求仙行為對他有較大影響力,這在其詩歌中有多次書寫。最能表達其求仙心切的有《送華山歸隱西湖》:
方士求仙入滄海,十二城樓定何在。金銅移盤露滿天,琪樹離離人不采。
軒轅高拱圣明居,群仙真人左右趨。青牛谷口迎紫氣,白鶴洞中傳素書。
珊珊鳴佩星辰遠,寂寂珠庭云霧虛。修髯如漆古仙子,玉林芙蓉染秋水。
九關高塞不可留,歸去江湖種蘭芷。山頭宮殿風玲瓏,玄猱飛來千尺松。
閑房誦經鐘磬響,石壁題詩苔蘚封。欲向君王乞祠祿,安排杖屨來相從[4]3。
此詩一開始便用大半篇幅描寫神仙所處之仙境,最后詩人自己不免心動,想要就此罷職,而去管理道教宮觀,去追求神仙般的生活。其求仙的思想,多半是其在仕途中遇到挫折之時所尋求的精神解脫。
二、詩畫創作的互通
王士熙現存詩歌130首,諸體兼備,有五律、七律、五絕、七絕、五排等,此皆近體詩作,占現存詩歌數量的一半以上。就創作成就來說,他的樂府古詩水平更高。樂府始創于秦,兩漢時期的樂府詩多出自民間,是創作者有感而發的結果,因此,樂府古詩多本性情。《漢書·藝文志》有載:“自孝武立樂府而采歌謠,于是有代趙之謳,秦楚之風,皆感于哀樂,緣事而發……”[9]1756可知,樂府詩是詩人為具體事物所觸動,激發了創作熱情,不是為文造情的空洞之語。對于古樂府的發展歷程,元人楊維楨在其《玉笥集敘》中有所論述:“《三百篇》后有《騷》,《騷》之流有古樂府。《三百篇》本情性,一出于禮義。《騷》本情性,亦不離于忠。古樂府,雅之流、風之派也,情性近也。漢魏人本興象,晉人本室度,情性尚未遠也。南北人本體裁,本偶對聲病,情性遂遠矣。盛唐高者追漢魏,晚唐律之敝極。宋人或本事實,或本道學禪唱,而情性益遠矣。”[10]42冊309楊維楨論樂府古詩注重書寫情性,但自南北朝以來,尤其是宋詩的本之事實,重于說理,致使古樂府去性情甚遠。至元代,“吟詠性情”成為詩人和詩論家們討論的熱點,其含義泛化,其中劉將孫主張性情得之自然,認為詩是“一時自然之趣”。王士熙的樂府詩創作也是注重吟詠性情、本之自然的。如其《青青河畔草》一詩:
青青河畔草,江上春來早。春來不見人,思君千里道。
千里君當還,夙夕奉容顏。青樓獨居妾,含情山上山。
白雁歸塞北,一行千萬億。團團月出云,卻使妾見君[4]2。
此詩沿用古題,在詩歌內容上表現的是代思婦所寫的閨怨之作。詩歌前兩句描寫早春時節江河兩岸小草青青的景象,開頭就描繪了清新自然的環境。寫景不是目的,而是為表現人物服務的,一方面可以引出人物,另一方面為人物提供了活動場所。在這樣美好的季節,本來應該和自己思念的郎君踏春游玩,而現實卻是不見故人歸來,獨居的女子只能含情遠望,期待與所思之人相見。詩歌語言淺近直白,但句子之間連接緊密。首先詩人由河畔青青小草的萌發,意識到早春已經來到,可是在這春回大地之時,卻不見游子歸來。那人應在千里之外,等待歸來之日。閨中人定日夜守望,以美好的容顏來迎接心上人。可是,現在她只能遙望遠處的高山,將自己的思念寄托給北歸的大雁。當夜晚月亮出來的時候,她想象著和心上人共同欣賞這輪圓月。這首詩處處都體現著女子對遠游之人深深的思念之情,語言不加雕琢,自然真切,一如其感情真摯,感人至深。除了此類柔情之作,王士熙也用樂府吟詠豪情之歌,如其《行路難二首》,前一首寫了自然環境的險惡:
請君莫縱珊瑚鞭,山高泥滑馬不前。請君莫駕木蘭船,長江大浪高觸天。瞿塘之口鐵鎖絡,石棧縈紆木排閣。朝朝日日有人行,歇棹停韉驚險惡。饑虎坐嘯哀猿猱,林深霧重風又凄。
在行路途中面對如此多的困難,第二首便寫了“男兒有志在四方”。雖然前景迷茫,路途險惡,依然要能“雞鳴函谷云縱橫,志士長歌中夜起”[4]4-5。這是一種不畏艱險的精神。此二首《行路難》,雖然在氣勢上不如李白的同題詩作,但是感情真摯自然,也能體現出其堅忍不拔之志。
竹枝詞的主要特色在于吟詠風土俗尚,從而達到“志土風而詳習尚”的目的。王士熙創作了《竹枝詞十首》,其一“居庸山前澗水多,白榆林下石坡陀。后來才度槍竿嶺,前車昨日到灤河”[4]17。此詩共四句,勾勒了北方的一段行車路程:出居庸,過白榆林,度槍竿嶺,直到灤河。北方的一些地名出現在詩人的詩歌中,為人所知。其四“車簾都卷錦流蘇,自控金鞍撚仆姑。草間白雀能言語,莫學江南唱鷓鴣”[4]18。此詩的后兩句寫了北方的鳥類白雀能夠言語,發音不同于江南的鳥類,有自己的特點。此二首,載入楊維楨《西湖竹枝詞》,序云:“竹枝本灤陽所作者,其山川風景,雖與南國異焉,而竹枝之聲則無不同矣。”[11]554竹枝詞由巴蜀民歌演變而成,其表現的內容多為江南風土人情。王士熙所作的竹枝詞多用來表現北方的風土,對我們了解北方的地理和人文環境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王士熙所作的竹枝詞,是其在去往上都的途中或在上都時的所見所感,表現的內容也具有北方特色。同時詩人也表達了自己的書寫目的,即“要使竹枝傳上國,正是皇家四海同”(《竹枝詞十首》其十)[4]18。關于王士熙此十首竹枝詞的創作背景,袁桷有言:“(至治元年)四月甲子扈蹕開平,與東平王繼學待制、陳景仁都事同行,不任鞍馬,八月始達,留開平一百有五日,繼學同邸,八月甲寅還大都,得詩凡六十二首。”[12]206繼王士熙之后,袁桷作《次韻繼學途中竹枝詞》十首。王士熙、袁桷等人在有意識地拓展竹枝詞的表現內容,將其表現范圍由江南推向北方。此外,王士熙所作的《上都柳枝詞七首》也應值得我們關注。柳枝詞作為一種歌曲流行于中唐以后,歌辭通常是詩人借詠柳而抒寫別情。上都是元朝的首都之一,為元世祖忽必烈所建,城址現在內蒙古境內。其一:“曾見上都楊柳枝,龍江女兒好腰肢。西錦纏頭急催酒,舞到秋來人去時。”[4]18每年四月,元朝皇帝都要去上都避暑,等八九月份天氣轉涼時才返回大都。皇帝在此除了進行狩獵,還會舉行傳統的祭祀活動。因此,一些隨行的漢族文臣也得以見識北方的風俗,而上都也因之發展了起來。王士熙的此首詩以上都的楊柳枝詠起,寫到了所見到的北方女子,而最后一句從側面反映了元代統治者上都之行的歸期,也就是秋來之時,上都的發展旺季也就面臨結束了。又其四:“儂在南都見柳花,花紅柳綠有人家。如今四月猶飛絮,沙磧蕭蕭映草芽。”[4]18南方的春天花紅柳綠,欣欣向榮;而北方的四月卻是風沙多發的季節,一片蕭瑟。王士熙的竹枝詞與楊柳詞是其作為館閣文臣扈從皇帝至上京時所作,所吟詠的皆是北方風土人情,在其表現內容上有所創新,同時具有紀時紀地之特色。這在元代詩壇中也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元人吳當就有《王繼學賦柳枝詞十首書于省壁至正十有三年扈蹕灤陽左司諸公同追次其韻》十首。
詩歌和繪畫是兩種不同的藝術形式,但二者存在緊密的聯系。在元代,詩歌與繪畫實現了高度的融合,這與能詩善畫的文人的大量出現有關。王士熙作為一名文士,書畫兼長,在繪畫方面,《圖繪寶鑒》載其“善畫山水”。在詩歌創作上,王士熙也留下了他的題畫詩作,如《題高房山青山白云圖》《虞秘監山林小像》《題郭忠恕九成宮圖二首》《驪山宮圖》等。其中《題高房山青山白云圖》一詩前有序文稱高克恭:“能畫山水,詩甚有唐人意度。……其作山水,人家多有之,珍藏什襲,其價甚高,為大元能畫者第一。青山白云,甚有遠致。”[4]22可見,王士熙對高克恭的山水畫作極為推崇。詩云:
吳山重疊粉團高,有客晨興灑墨毫。
百兩珍珠難買得,越峰壓倒涌金濤[4]22。
此詩的首句和末句將高克恭的青山白云圖描繪出來:吳山一座座重疊在一起,粉團似的白云越過高峰,在陽光的照耀下如波濤般洶涌。“壓倒”一詞顯得氣勢頗為磅礴,雖只兩句,但將原本靜態的畫作十分靈動地呈現了出來,從而實現了詩畫之間的相互補充。
三、以清壯偉麗之筆寫大元盛世氣象
關于王士熙的詩歌創作水平及風格,其友馬祖常稱贊其與袁桷的畫松聯句之作:“清壯偉麗,備體諸家,祖常實不能及后塵也。”[13]684此中雖不免有馬祖常的過謙之辭,但清壯偉麗,確是王士熙詩歌的主要風格。王士熙清壯風格的實現,主要與其人生經歷及性格有關。他出身于儒學世家,且有自己家傳的文學創作經驗,加上師承文學家鄧文原,增長了其學識,又喜交朋友,有了文學創作上相互切磋的機會。王士熙頗為自信樂觀,豪情壯志常充其胸間。這在《贈廣東憲使張漢英之南臺掾》一詩有所反映:
生平不愿為傭書,亦不愿作章句儒。酒酣詩成吐素霓,意氣凜凜吞千夫。
前年排云叫閶闔,出門一夜車四角。去年海嶠席未溫,一舸乘潮又催發。
大江之西日本東,廬陵文物常稱雄。決科歲占十八九,君當努力提詞鋒。
才高不用長嘆息,四海彌天豈無識。壯年懷居亦何有,著眼帶礪開胸臆。
巖巖柏府凌高寒,豪士傾蓋宜交歡。我知屠龍不屠豨,食馬政欲食馬肝。
吳姬壓酒飄香絮,謫仙神游歌白纻。敬亭惟有孤云閑,欲雨人間亦飛去[4]4。
王士熙對自己的未來充滿信心,他不愿意做一個皓首窮經的白面儒冠,意氣風發,滿腹的豪情壯志溢于言表。在揮毫作詩時,他的情感表達常是噴發式的,一氣呵成。無論何時何地,只要有了創作的沖動,就直接予以抒發。而其詩歌的偉麗風格,與當時詩壇的風氣有關。元初北方詩壇“承金氏之風,作者尚質樸而鮮辭致”,而后來值“延祐、天歷,豐亨豫大之時”,隨著元朝國力的日益強盛,文人士大夫們熱衷于歌詠盛世,而“范、虞、揭以及楊仲宏、元復初、柳道傳、王繼學、馬伯庸、黃晉卿”(《練伯上詩序》)[10]55冊287諸人就是其中的代表。他們實現了詩風的轉變,一改以往質樸的詩風,而多綺麗之語。王士熙的詩歌也正是如此,如其《送巨德新》:
渭城秋水泛紅蓮,白雪梁園作賦年。金馬朝回門似水,碧雞人去路如天。
揚雄宅古平蕪雨,諸葛祠空老樹煙。小隊出游春色里,滿蹊花朵正娟娟[4]9。
此詩中雖提到古跡,如揚雄宅和諸葛祠,但詩中并沒有懷古感傷的情緒,轉而表達的是游春的快樂和春天的美好場景。身為畫家,王士熙擅于構圖,且十分注重顏色詞的搭配使用。他在詩中大量使用顏色詞,有紅色的蓮花,有白色的云朵,亦有金馬,有碧雞,有顏色鮮艷的花兒,加上空間的幾度轉換,讓人目不暇接,僅用詩歌語言就呈現出了極強的畫面感,營造出一種色彩明艷、景色秀美的清麗之境。又《寄上都分省僚友二首》其二:
畫省熏風松樹陰,合歡花下日沉沉。腐儒無補漫獨坐,故人不來勞寸心。
紫極三臺光景接,洪鈞萬象歲年深。 灤江回首九天上,誰傍香爐聽舜琴[4]11。
此詩采用了欲揚先抑的寫法。前四句描寫詩人在松樹陰里、合歡樹下終日無所事事,表達了一種百無聊賴的情緒,與下文回憶與僚友在上都的美好生活形成對比;后四句通過描寫“紫極”“洪鈞”“香爐”“舜琴”等意象頗顯綺麗,通過今昔對比來表現對過往生活的懷念和對友人的思念。
文學有其自身發展的規律,同時也與朝代的更替、國家的盛衰有著密切關系。元朝是個大一統的時代,文學發展上也出現了“文運向明,文體為之一變”(《胡孟成文集序》)[14]68的現象。在元代,宗唐之聲一直此起彼伏,元代文人將盛唐氣象作為他們所崇尚的文學風貌。文學與世運之間的關系,在一個朝代的盛世和末世有更好的體現,盛世通常會伴隨著“盛世之音”的出現,元代即是如此。歐陽玄曾說:“我元延祐以來,彌文日盛,京師諸名公咸宗魏晉唐,一去金宋季世之弊,而趨于雅正。”(《羅舜美詩序》)[15]64元朝國力日趨強盛之時,在詩歌創作上也有了詩風轉變的需要。元人有意要去宋金末世詩歌創作的弊端,追求雅正之風。“蓋方是時,祖宗以深仁厚德涵養天下垂五六十年之久,而戴白之老、垂髫之童,相與歡呼鼓舞于閭巷間,熙熙然有非漢、唐、宋之所可及。”(《皇元風雅序》)[16]588追慕盛世,鳴國家之盛,頌時代之美,這是典型的歌詠盛世的雅正之風。在詩歌中具體表現為:注重于歌頌,頗為崇尚“盛世之音”,多“鳴太平之盛治”,不同于“風雅”有批判現實的精神。而王士熙作為至治、泰定年間較為活躍的館閣之臣,在元代館閣詩人發展的進程中有著承前啟后的作用。正如楊鐮在《元詩史》中所說:“元代的臺閣詩人真正產生影響,就是在這一時期,由袁桷、王士熙、馬祖常等人唱和在前,‘元四家’虞楊范揭繼起于后。”[17]29館閣詩人在詩歌創作上有相同的特點,即對“雅正”之風的追求、對盛世的歌頌。如其《次霍狀元接駕韻》:
關頭曉日瑞光蟠,隱隱駝鈴隔薄寒。金殿巧當雙嶺合,繡旌遙指五云看。
軍裝騕褭開馳道,仙仗麒麟簇從官。詞苑恩波供染翰,秋風歲歲候鳴鑾[4]8。
前四句寫邊關安定,國家內外一片祥和興盛;后四句寫皇帝身邊百官擁戴,供奉翰林之士得以發揮自己的才能,并年年等候隨從皇帝出行。每句都可見其對國家盛世的歌頌。這樣盛世里館閣文臣的生活在王士熙詩中有亦所體現,《上京次李學士韻五首》其二:“金燭承恩出院遲,玉堂學士草麻時。明朝出國新端午,彩筆供奉帖子詩。”[4]19臣子們往往需要議定國事、擬定詔書到很晚才能“出院”,但他們對國家和君主心懷感激。詩中稱皇帝賜予他們的蠟燭為“金燭”,并感受到皇帝對他們的恩澤,在節日來臨之時,他們也會用富麗的辭藻去創作帖子詩來歌頌太平。
王士熙作為館閣文臣,與其同僚交往密切,也留下了為數不少的唱和之作。對此類詩,顧嗣立評價較高:“繼學為詩……與袁伯長、馬伯庸、虞伯生、揭曼碩、宋誠夫輩唱和館閣,雕章麗句,膾炙人口。如杜、王、岑、賈之在唐,楊、劉、錢、李之在宋,論者以為有元盛世之音也。”[11]537此外,楊鐮的《元詩史》說“就存詩歌量而言,王士熙并不算多,但在元代詩壇,特別是北方臺閣詩人傳承過程中,他卻占據著比較關鍵的位置”[17]294。在楊鐮看來,王士熙的詩歌創作不僅是館閣文臣的代表,而且還有傳承之功。對于王士熙在臺閣詩人中的地位,元人傅若金在《呈王繼學大參特領江東憲二首》中寫道:“丈人文律擅風騷,往昔朝中屬望勞。宣室近聞征賈傳,漢庭重見遣王褒。”[18]239可見,王士熙在館閣文臣中的地位較高,影響力很大。王士熙也在詩中多次寫到在元代都城的各種見聞。如其《早朝行》:
石城啼鳥翻曙光,千門萬戶開未央。丞相珂馬沙堤長,奏章催喚東曹郎。
燕山驛騎朝來到,雨澤十分九州報。輦金馱帛分遠行,龍沙士飽無鼓聲。
閣中龍床琢白玉,瑟瑟圍屏海波綠。曲闌五月櫻桃紅,舜琴日日彈薰風[4]5-6。
此詩前八句記述了百官早朝的情景,渲染了一種嚴肅而緊張的氣氛,但是后四句轉向對宮廷建筑、環境的描寫,寫了用白玉雕琢的龍床、綠如海波的屏風、紅似櫻桃的闌干以及彌彌的琴聲,視野一下子縮小了許多,具有館閣詩的特點。此外,王士熙在館閣之時,與袁桷、馬祖常、虞集、揭傒斯、宋本諸人的唱和之作不在少數,他們都是元代館閣詩人的代表。《石洲詩話》卷五就有相關論述:“至治、天歷之間,館閣諸公如虞伯生、袁伯長、王繼學、馬伯庸,每多唱和,如代祀西岳、上京雜詠之類。”[19]163這在其詩歌創作中有較多體現,如《送虞伯生祭祠還蜀用袁待制韻》:
蜀道揚鞭舊險摧,家山遙認碧崔巍。奉香暫別金鑾去,題柱真乘駟馬來。
祠罷汾陰迎漢鼎,路經驪谷吊秦灰。歸釐宣室須前席,不似長沙遠召回[4]7。
此詩用袁桷的韻來寫對虞集的送別。袁桷在元廷頗受統治者的重視,“朝廷制冊,勛臣碑銘,多出其手”。當袁桷為祭祠還蜀之時,王士熙作此詩有不少恭維之辭,如“題柱”“前席”等。另王士熙有《上京次伯庸學士韻二首》,其二:
長堤芳草遍灤河,誰買扁舟系樹槎。金帳薰風生殿角,畫樓晴霧宿檐阿。
萬年枝上烏啼早,九奏階前鳳舞多。供奉老來文采盡,詩壇昨夜又投戈[4]11。
此詩作于詩人上京扈從之時,前兩句寫景,描寫灤河芳草萋萋的景色,中間四句多寫皇帝臨時駐扎之時的景象,最后兩句寫文臣的供奉職責與不易。此詩乃次韻之作,伯庸即馬祖常寫了多首上京詩作,而元詩人柳貫在他們的影響之下,也創作出了《次伯長待制韻送王繼學修撰馬伯庸應奉扈從上京二首》。由此,元代館閣文臣所倡導的“治世之音”詩風逐漸形成,并且影響深遠,成為元代早期北方詩壇的特色。
隨著人生境遇的變化,中國多數知識分子在出世與入仕之間猶豫徘徊,不論最終是否付諸行動,但是不同的思想在一個人身上也會實現思想上的和諧狀態。王士熙出身于儒臣之家,從小接受儒家思想,走上仕途是必然的。作為北方的儒士,王士熙在仕途上有持續晉升的時候,雖中間有流放的經歷,但總的來說,他屬于統治階級,其豐富的人生見聞使他留下了具有元代特色的上京組詩,又因其在館閣之時,積極與同僚唱和,為元代館閣詩的發展作出了貢獻,是元代“盛世之音”的代表詩人。王士熙又兼畫家身份,其繪畫創作的思路在其詩歌中也有所體現。不論是他的紀行詩,還是送別詩,都注重對環境的描寫,其所描繪的景象在構圖與色彩的組合上,均呈現一定的畫面感,給人以美的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