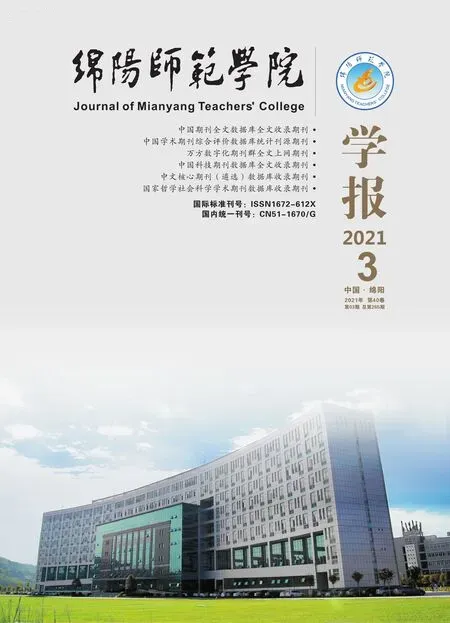論李白山水詩“本真自然”的審美風格
楊文洪,嚴雯韜
(四川文化傳媒職業學院,四川成都 611230)
一、引言
李白山水詩具有“本真自然”的詩學風范。詩人向往自由、尋仙問道等詩意棲居活動,詩歌創作寫景繪形、描物抒情、表情達意、刻寫心性,詩風自然純樸、平實淡泊,盡顯其熱愛自然、喜愛山林之審美情趣。詩作質樸而不粗陋,本真自然,想象奇妙,意向非凡。李白山水詩或隱逸清雅,純然自由,或樸素巧妙,或自然雄奇、磅礴大氣。并且,其性情真實、真誠、真摯、本真,流露自然,為詩人自我情懷的呈現,是詩人自己本身心性的顯露,自己的本心本性,生存存在傾向澄明;其詩情來自詩人內心的個性追求,對生命意義的領悟,至誠至真,至深至切,感人肺腑。就其山水自然詩作看,鳥飛魚游、犬吠鳴雞、樹叢村落、房屋炊煙,充滿生機活力。所謂“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1]97。天然、本然、坦蕩細膩,美妙深情,曠遠悠揚,情懷樸素,其中蘊藉著強烈的生命意識和對生命的深沉思考,生命意識的流露鮮活、細膩,包蘊著一種生命的原力與生存意念。本文希望通過現象學美學理論,來探討李白山水詩“本真自然”的審美品格。
二、“本真自然”的審美品格與詩意呈現
李白的山水自然詩作,審美風格樸實無華,清新淡遠,自然天成,具有一種“本真自然”之美。就人格操守看,李白具有仙風道骨,他崇尚獨立與自由,人生觀念通達,喜愛山林自然等詩意棲居活動,優游于名山大川,投身于山山水水、自然大化之中,以怡情隨性。如《下終南山過解斯山人宿置酒》詩云:“暮從碧山下,山月隨人歸。顧卻所來徑,蒼蒼橫翠微。相攜及田家,童稚開荊扉。綠竹入幽徑,青蘿拂行衣。歡言得所憩,美酒聊共揮。長歌吟松風,曲盡河星稀。我醉君復樂,陶然共忘機。”[1]169這首抒寫山林意趣的詩,就呈現出一種“本真自然”的詩意棲居之美。詩人月夜下山,過訪問訊解斯山人,沿途賞玩碧山,觀賞山月、山徑、蒼翠山色;造訪田家,綠竹、幽徑、青蘿、松風、優美景色。童稚、美酒、山人、幽居、飲酒、吟詩,山光林影與“人”一路相伴,任運自然,既“歡言得所憩”,又“陶然共忘機”,天人合一、情景交融,詩風自然真率、渾樸平淡。審美情趣與藝術風貌幽淡清新,與山林諧協交融。又如其《山中問答》詩云:“問余何事棲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閑。桃花流水杳然去,別有天地非人間。”[1]157詩人隱居于山間林野,棲住于林之山中,心境舒坦,情緒悠閑,心靈淡泊清遠,與山水自然相伴,物我交融,混融一體。詩人寫景抒情,借當下之景,抒心中之感。高飛遠去的鳥兒,越飛越遠,直至無影無蹤;寥廓無有盡頭的長空,悠悠白云,清靜幽然平靜的心靈,莫名的悵惘與孤獨,淡淡的寂寞與憂傷。閑靜寧謐的山林,空山中婉轉鳴啼的鳥兒,內心的不忍和無奈。清新明凈的詩意化、藝術化意境。情景相交,物與親和,天人一體,諧適超逸,深情真摯,其詩作乃生命最自然的體現。深情厚意,成為了生命情感的重要組成,既五彩斑斕又樸實純凈,承載著生命的歡樂,表現那積極向上的生命活力與生命不屈的力量,是生命意義與生命希望的生動自然抒寫,是平凡生活、平凡生命的“此在”。本真存在是此在與共在的存在及其意蘊的一種呈現,是“此在”“去在”,在存在,是本我、本己、本心、本性的顯露、顯現。又如其《秋思》詩云:“春陽如昨日,碧樹鳴黃鸝。”[1]55春日里,春光明媚,黃鸝鳥在婉轉地鳴唱,悠然淡然;《山人勸酒》詩云:“春風爾來為阿誰,蝴蝶忽然滿芳草。”[1]34翩翩飛舞的蝴蝶,輕盈可愛;《秋浦歌》其三詩云:“秋浦錦駝鳥,人間天上稀。山雞羞淥水,不敢照毛衣。”[1]67珍貴、美麗的錦鴕鳥,世間罕見,舉世無雙。禽鳥天真可喜、自在自由,與心性純真、品性高潔的“人”之心靈契合。詩歌中,詩人生動形象地展現了禽鳥的美麗。能與禽鳥相伴,忘世忘我,超越世俗的一切,游走徜徉于山間林野、碧山綠水中,自得自樂。因自然萬物觸動,而自然生發靜謐恬淡,靜觀萬象,萬象如在鏡中,光明瑩潔,而各得其所,詩歌呈現山水自然自在、充實內在的存在意義,自我的內心得到凈化與升華,至善至美。
李白的山水詩,風貌靜穆澄明、恬淡自然,景物與人渾然一體,靜動相生,和諧自然。應景觸發所生之情,源于心靈的自然流泄。詩人內在之“情”與山川景物融通,“人”與自然和諧相生。詩興詩情本乎天成,詩境詩意妙手偶得,率真直達,靈動飛揚,無阻無礙。詩歌的情感表達來自其生命的本真體悟,人與自然本然圓通,無有障礙。詩歌意境的熔鑄為本真心靈的顯露,藝術與生命融合,物態與心態妙合無垠,意味無窮,鑄就了“本真自然”的審美精神。詩學風范是人與自然一體交融、情景合一、物我一體、相依相存。
李白的山水詩審美創作追求“本真自然”的抒寫與詩意棲居的呈現,其詩歌作品則鮮明地表現出“本真自然”的審美風格。這種“本真自然”是由其真摯之情的凝結熔鑄而成,是芙蓉出清水,具有一種清新、淡雅、天然、本然的生命之美;曠達、超然、澄澈、空明,平淡流轉。李白的山水詩審美創作正是出自“本真自然”且集天地英靈之氣,奇險壯麗,靈氣所鐘,乃詩人個性與氣質才性的呈現。李白曠世逸才,天賦天成,縱情任性,放蕩驕恣,豪放野性。空山白云,清溪繞屋,溪堂醉臥,落花如雪,超妙奇絕,山鳥不鳴,隨意取來為己所用,并不真正地信仰,而是已融入了自己的生命,情有獨鐘。這種“本真自然”審美品格,“素樸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美”[2]130。所謂“真者,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圣人法天貴真,不拘于俗”[2]323。“天真之美”“素樸之美”,都是一種“自然之美”,縱橫多變,體似湖海。李白以其一生去追求“本真自然”這一審美品格,認為“自從建安來,綺麗不足珍”[1]12。在山水詩審美創作實踐中,他追求“清”之審美風貌,標舉“清新”“天真”“清真”等審美品格。基于此,他強調“圣代復玄古,垂衣貴清真”[1]12,又指出“俄成萬里別,立德貴清真”[1]272。因此,可以說,李白的詩歌是源于詩心的自然流露,是至真之情、至誠之心的表達與表白,質樸無華、靜謐恬淡、通透無礙。其詩作是詩人本真的體悟、詩意化生存的呈現。藝術與生命合而為一,是最自然、真實的生存狀態。審美風格厚樸、明朗、雋永。山水自然與情感、物態、心態妙合無垠,意味無窮,詠物中寄托著詩人的情志,達到了物我一體的藝術境界。“天光物色”表現出詩人真情實感,情感熾熱,蘊藉深厚,祥和寧靜。詩人情懷高潔,對自然、對生活極其珍視。他胸懷闊大,本真的情愫與天光物色融為一體,活潑率真。“我”之“本真”源于胸中造化,所謂“右軍本清真,瀟灑在風塵”[1]190。“右軍”,即王羲之。李白傾服崇敬王羲之,認為其書法神妙自然,為人瀟灑率真,人品與書法達到神妙的境界,風貌純潔質樸,灑脫無拘束,超脫塵世。李白詩歌創作“天真自然”,內蘊“自然本真”審美精神,其最深層內核為“天然去雕飾”。自我、自性、本色一體化于獨立不可復制的“真我”中。他極其強調“真我”,詩歌創作“天然去雕飾”。
三、對道家美學的傳承與詩性發揚
李白山水詩所體現的“本真自然”審美品格與道家美學主張的“道法自然”“以天合天”“法天貴真”“歸樸反真”等審美主張密切相關。在詩歌創作風貌追求方面,李白推崇“天然去雕飾”“清新純真”的審美意趣,詩歌創作追求“天然”“純然”“本色”“自然”,就是對道家美學的一種運用與詩性發揚。李白的山水詩審美創作顛覆傳統、突破傳統,呈現為一種個體自性的審美化、詩意化,表現出一種“本真自然”的審美風貌和“天然去雕飾”的山水詩創作風味,獨樹一幟,生發出一種自然情致,自由自在的蘊致和蕭散,性情交織纏繞,為其詩歌的清純、清新化審美增添了亮色,給予可資的價值意義。李白詩歌創作崇尚本色和真情,尊重事物自然本性,“本真自然”,“求真性”“求真情”“求真色”“求真事”,走進生活與山間林野,去激發才情詩興,暢懷歌詠,釋放精神,傳遞著積極的情感。清代學者王夫之對李白推崇備至,如評李白的《金陵酒肆留別》詩時就強調指出,“供奉一味本色”[3]130。王夫之認為李白繼承了南北朝的鮑照,發揚了漢魏樂府的優良傳統。李白其詩云:“金陵子弟來相送,欲行不行各盡觴。請君試問東流水,別意與之誰短長?”[1]192這首話別詩雖短,卻情意深長。開頭兩句“風吹柳花滿店香,吳姬壓酒喚客嘗”,寫春風、柳絮、吳姬、客人,春風吹起柳絮,酒店滿屋飄香,侍女捧出美酒,勸客人細細品嘗。楊花飄絮,江南水村,山郭酒家,駘蕩的春風,卷起了垂垂欲下的楊花,輕飛亂舞,撲滿店中。別緒滿懷將要離去的詩人,獨坐小酌。當壚的姑娘,捧出剛剛釀造的美酒,勸客品嘗。柳絮濛濛,酒香郁郁,春光春色,生動自然,灑脫超逸,情長意盛。別情與流水,悠然無盡,惜別之情,飽滿酣暢,悠揚跌宕,青春的風采與風流瀟灑的情懷浸透詩句,力透紙背。同樣,由于李白的五言古詩繼承了從《詩經》《古詩十九首》以來的詩歌傳統,而且加以提煉,其詩歌創作風格,更具詩人自我的特色,將歷史典故、當下寓目之景、心中的感受,熔鑄在一起,抒發自己的情懷,寫出了詩人的感想,其意旨深遠。王夫之非常推崇李白詩作“本真自然”、不事雕琢之特點,如評李白詩《送張舍人之江東》詩,點評云“讀太白詩,乃悟風光不由粉黛”[3]323;評其詩《侍從宜春苑奉詔賦龍池柳色初青聽新鶯百囀歌》云“虧他以光響合成一片,到頭本色”[3]323;又點評言其“李獨用本色,則為《金陵送別》一流詩,然自是合作”[4]130。他認為,李白的山水詩審美創作乃“天授非人力”,這些地方所謂的“本色”,也就是“本真自然”。在王夫之看來,李白詩歌創作“本色”“自然”,不靠“粉黛”,沒有刻意修飾的痕跡,把“天然”“巧化參工”作為詩歌審美標準和藝術理想,崇尚自然,清新秀美。的確,誠如斯言,李白詩歌“風神清遠”,清新飄逸,超拔自然,“內極才情,外周物理”[3]325,為他人難以企及。清代詩歌批評家趙翼也認為李白的山水詩審美創作不事雕琢,“神識超邁”,“不勞勞于縷心刻骨”,本真自然,“自有天馬行空,不可羈勒之勢”[5]18。這可以說是李白詩作呈現出的共同特色。杜甫在其《春日憶李白》中也曾經指出,李白詩歌創作獨具特色,“無敵”“飄然思不群”,兼具庾信詩的清新與鮑照的俊逸風采。宋代嚴羽在對李白詩的評論中,也不止一次地以“本真自然”來評點,如其評《梁園吟》中的“掛席欲進波險山”句,就指出此句詩“壯險語,卻自然,非造非矯”[6]117,認為其具有奇麗壯險的風貌特色,然而內蘊自然,沒有刻意地去施為與雕琢,呈現出“自然本真”的審美特色;又如其評《春日游羅敷潭》“云從石上起,客到花間迷”詩句,多加贊譽,言其“自然如此,拈出卻生動”[7]323。指出其詩歌風韻清新,風格自然,浩浩落落,自然而成,不假人力;再如評《勞勞亭》“春風知別苦,不道楊柳青”句,認為其具有“自然拈出,卻使造揉者知丑”[6]180的審美風貌。李白自己也推舉“本真自然”的審美訴求,在《經亂離后,天恩流夜郎,憶舊游懷贈江夏韋太守良宰》中,他自己的兩句詩——“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可以說是夫子自道,為其詩歌風格的一種生動寫照,也是其詩歌“本真自然”風格的最好評語。應該說,李白詩歌創作一直以“清水出芙蓉”“本真自然”為審美追求,如其《古風》其三十五所批評的“雕蟲喪天真”,就反對人為的“雕蟲”“雕飾”,標舉“天真”。所謂“天然”“天真”,即天生、天賦、天稟、生就、原生、天然、自然、天成,就是道家美學所主張的“法天貴真”“道法自然”。在李白看來,狀寫自然風貌的詩歌創作與繪畫審美旨趣相同,以生其所生、自其所自、自然而然為工,寫景狀貌,應該順其自然,不事雕琢,以自得、自然、自在為最佳審美創作訴求。所謂“清新”,也即自然,自然生成,天然造就,清新清爽,新穎新鮮,嶄新清澈。具有自然清新審美風格的詩歌作品,都是詩人澄心靜懷,于空明心地中自然流出來的。因此,看似全不著力,卻無心耦合,本然油然,自然而然,不假修飾,沁人心脾。詩歌創作不以鍛煉為工而自能獨特,信手拈來,氣象宏闊,鋪敘宛轉。所謂常行于所當行,止于不可不止,靈心慧性,隨手拈來,天工自成。李白詩歌創作,往往“言在口頭,想在天外”[8]58,自然拈出,自達妙絕。得自然之數,不差毫末,天才縱恣,妙語天成,融法度于內,化鍛煉于天然。而其詩歌作品風格則情感率真,直抒己胸,興酣淋漓。他在詩歌創作構想活動中,高興時則興高采烈、歡呼雀躍,“仰天大笑”;憂愁時則“抽刀斷水”“舉杯澆愁”,所謂“五花馬,千金裘,呼兒將出換美酒,與爾同銷萬古愁”;胸中激情滿懷,沖口而出,肺腑情愫一泄胸臆,情真意切,天然率真,隨物賦形,恰如一朵出自清水的“芙蓉”,出水綻放,清香四溢,洗盡繁華與鉛塵,亭亭玉立,充滿生命力。詩人生性曠達,心境澄明,同時,其胸懷睿智,于世俗生活超脫、平淡,詩如其人。因此,在詩歌創作手法上,李白往往觸目興懷,仰觀俯察,信手拈來,直抒胸臆,進退自若,字里行間皆是一種曠達之氣,體現出了詩人對人生的體悟,揭示了至深的哲理。
李白樂于山水泉林之中,心清氣正,以山水造境。李白的自然林泉生活所體現出的曠達怡樂的審美旨趣,觸景生情,即景成詠,將自然山水景色與心性融合,熔鑄于藝術意境之中,營造出心物、情景、意象一體交融的詩意化境域。這種詩意化境域與旨趣是李白借由虛實相生、情景相融、動靜結合構筑出來的。李白就在這之中達成其人生抱負,游樂于山水自然之間,居高臨下,俯覽全景,觀松賞杉,視野開闊,景象壯闊,投身于自然山水之中,而超然山水外,心神早已與山水融為一體,無懼悲喜,悅耳、悅目、悅心,心胸得以開闊暢然。李白詩歌之自然審美意識的形成受到老莊美學的深刻影響。在他的詩歌中,“人”與自然物我一體、和諧共生。他尊重生命、仁愛萬物,把人的自然化和自然的人格化和諧地統一在一起,表現出對自由閑適生活的向往。
李白的一生充滿了出世與入世、積極與消極、清高與世俗之間的矛盾。他遺世獨立、狂放不羈、求仙訪道、嘯傲山林。李白詩歌之自然審美意識的形成離不開老莊美學說的影響。自然萬物皆生于“無”,“人”與萬物都是萬有大化的有機組成部分,應相互親和,彼此尊重,相互融合,一體渾然。“人”與自然萬物互依互存、協調一致、和睦相處、不分彼我,“天地與我并生,而萬物與我為一”。“人”要進入詩意化、審美化境域,只有忘卻人世的一切煩惱,修身養性,保持自然恬淡的審美心態,澄心靜意,虛明心境,最終達到“天人”相與相和、人心與物意相交相融的境界。李白詩歌就體現了這種“意象一如”“情景一體”“天人交與合一”的生態審美意趣,以仁心仁性愛護天地自然間的萬有萬物。樹木、花草、林野、星辰、端木、茅草、枯株、朽木、香草、美人、瑤草、奇花都入其詩作,如其《贈江油尉》詩云“嵐光深院里,傍砌水泠泠。野燕巢官舍,溪云入古廳。日斜孤吏過,簾卷亂峰青。五色神仙尉,焚香讀道經”[1]279,無限的生機與活力,與人和諧相處,其樂融融;又如《山人勸酒》云“春風爾來為阿誰,蝴蝶忽然滿芳草”[1]190,詩歌描寫了蝴蝶翩翩飛舞的輕盈可愛;又如“春陽如昨日,碧樹鳴黃鸝。蕪然蕙草暮,颯爾涼風吹。天秋木葉下,月冷莎雞悲。坐愁群芳歇,白露凋華滋”[1]55,春光明媚中,黃鸝鳥在婉轉地鳴唱;《秋浦歌(其三)》云“秋浦錦駝鳥,人間天上稀。山雞羞淥水,不敢照毛衣”[1]67,美麗的錦鴕鳥極其珍貴,舉世無雙;又如《荊門浮舟望蜀江》詩云“迤巴山盡,遙曳楚云行。雪照聚沙雁,花飛出谷鶯。芳洲卻已轉,碧樹森森迎。流目浦煙夕,揚帆海月生”[1]188,人靜源于心靜,山澗流水,寂靜無人,花自開落,景色繁多,空靈嫻靜,花落鳥鳴,寧靜淡泊,有聲有色,生意盎然。一片化機,非復人力,詩情畫意。心真意閑,超越世俗雜念,留下了想象的空白,心境灑脫,本自天成,妙手偶得,清幽絕俗,萬籟都醉,富有生機。雪白的大雁,美麗猶如花兒一般的黃鶯。天真可愛、如童稚嬉戲似的禽鳥,與詩人酷望自由與熱愛自然之心契合。詩人懷著一顆仁民愛物之心,平等地對待世間的一切生靈。如其《留別王司馬嵩》詩所云:“鳥愛碧山遠,魚游滄海深。”[1]126鳶飛魚躍,各得其所。如其《春日醉起言志》詩所云:“覺來盼庭前,一鳥花間鳴。借問此何時,春風語流鶯。”[1]201在自然山水中,詩人尋覓到了心靈的家園,找到了避風港與憩息所在。李白以其自然本真的詩性精神在詩壇上獨樹一幟,尤其是他獨特的審美旨趣與訴求,或“本色清純”“本真自然”,或豪放俊宇,呈現了其特有的情趣指向和意趣情愫。從其自然本真的詩性精神中,我們可以體會到詩人的胸懷與仁心仁性。
這種以“本真自然”的審美品格為詩歌創作追求的意識,體現了李白真摯熱切的心性、正直的人品、人格尊嚴的獨立,其山水自然詩構筑“天人合一”詩性意境。詩人置身于大自然的懷抱中,感受到空明澄碧的自然山水景觀,陶冶了詩人的性情,凈化了詩人的凡心,使詩人的精神得到超越和升華。李白山水詩中,大自然的清麗明凈與人的恬淡雅潔融為一體,達到了“不知何者為我,何者為物”的審美藝術境域。在山水詩審美創作構想方面李白“以氣為主,以自然為宗”[9]349。詩人往往情感激越奔放,如天上的白云,舒卷自如,沒有定形,以呈現詩人性格上的狂狷,緩解其內心深處的躁動,獲得情感乃至心靈的釋然與慰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