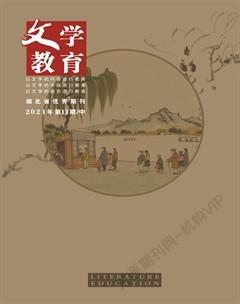論亞里士多德《政治學(xué)》中的平等觀念
龔成康
內(nèi)容摘要:不同于政體中各個(gè)群體的平等主張,亞里士多德對(duì)平等做出了他自己的解釋,即無(wú)論何種平等觀念,都應(yīng)符合城邦的目的、城邦所追求的最終的“善”。這種形而上的平等觀念將具體而現(xiàn)實(shí)的平等觀念引向倫理層面而變得抽象化,由此帶來(lái)的影響是兩方面的,一方面它可以彌合不同政治團(tuán)體間因價(jià)值理念偏差而可能引起的社會(huì)分裂;另一方面則使平等問(wèn)題邊緣化,讓平等觀念被懸置。當(dāng)人們對(duì)平等的追求成為對(duì)城邦最終的“善”的追求,那么對(duì)不平等的反抗就會(huì)由行為層面的暴動(dòng)轉(zhuǎn)向道德層面的譴責(zé),由此將會(huì)使不平等的表現(xiàn)變得越發(fā)隱晦、不平等的程度變得越發(fā)深刻,但亞里士多德沒(méi)有考慮這些,他所想要做的是為奴隸制國(guó)家辯護(hù),使其能長(zhǎng)久地存在。
關(guān)鍵詞:亞里士多德 平等觀念 善 不平等
亞里士多德在《政治學(xué)》中多處論及了他的平等思想,依據(jù)的方式是“夾敘夾議”,也就是通過(guò)對(duì)各個(gè)政體進(jìn)行分析,指出他們是持怎樣的平等觀念,然后在這個(gè)基礎(chǔ)上將他們進(jìn)行對(duì)比,評(píng)判不同的平等觀念。由此,對(duì)亞里士多德《政治學(xué)》中的平等觀念的分析,也可以從其在著作中關(guān)于平等是什么的討論,到關(guān)于什么的平等的討論,再到亞里士多德是怎樣化解并統(tǒng)一不同政體間平等觀念的沖突來(lái)進(jìn)行。
一.亞里士多德《政治學(xué)》中關(guān)于平等是什么的討論
古希臘是以城邦組成的社會(huì)。所謂城邦,是指為了完成某一善業(yè)的社會(huì)團(tuán)體,亞里士多德認(rèn)為城邦是因人類生活的發(fā)展而自然產(chǎn)生的,依次從家庭發(fā)展到村落再進(jìn)化到城邦[1]10,城邦是社會(huì)的本性、極因。作為奴隸主社會(huì)的古希臘,把處在這個(gè)社會(huì)中的人們,分成三六九等,就算具有公民身份的公民也不例外,奴隸則被完全排斥在城邦之外,甚至被當(dāng)做是一宗有生命的財(cái)產(chǎn)、行為工具[2]12。
古希臘社會(huì)中的平等是通過(guò)各個(gè)政治團(tuán)體在對(duì)自己利益的追求的過(guò)程中得到體現(xiàn)的。書中亞里士多德在多處論述了何為平等,其中有論及寡頭政體和平民政體的平等觀念。平民政體作為共和政體的變態(tài),人數(shù)眾多的平民控制著治權(quán),以窮人的利益依歸,把“平等”作為超過(guò)一切的無(wú)上要義[2]169,這里的平等具體體現(xiàn)在分配政治職司的平等,他們認(rèn)為人們?cè)谧杂缮矸葸@一個(gè)條件上相等就應(yīng)該在所有方面都相等。在他看來(lái),這樣的確實(shí)是一種平等,但只限于同等擁有自由身份的人們之間,并沒(méi)有考慮擔(dān)任這些政治職司的人是否具有相應(yīng)的才德,且不是普及全體的正義[2]149。而在寡頭政體中,平等體現(xiàn)在政治職司的不平等分配,在寡頭統(tǒng)治者看來(lái),不平等分配是正義的,他們認(rèn)為資財(cái)多的人在所有方面都應(yīng)該優(yōu)先,這樣才是真正的平等,因?yàn)檫@樣保證了他們作為優(yōu)越群體的優(yōu)先權(quán),而亞里士多德認(rèn)為,這種正義同樣不是普及全體的正義[2]149,忽略了城邦存在的目的,即追求最高的“善”。寡頭派和平民派主張的平等都是事物的平等,并未追求人身的平等,如能力、品德的平等。
那么誰(shuí)追求的平等觀念才是真正的平等觀念呢?在亞里士多德看來(lái),他們的平等觀念都是帶有偏見(jiàn)的,一味地追求權(quán)利的平等而忽略人們?cè)谀芰Α⒇?cái)富上面的差別,或者一味地追求自身的階級(jí)利益而忽略其他階級(jí)的利益都是不“正義”的。而想要克服這種偏見(jiàn),則需要樹立一個(gè)前提條件即符合正義,那何所謂正義呢?“正義即公平”[2]153,在亞里士多德看來(lái),正義是某些事物的平等觀念[3],寡頭派和平民派都忽略了的組成方式:城邦是若干生活良好的家庭或部族為了追求自足而且至善的生活,才行結(jié)合而構(gòu)成的[2]153,也就是說(shuō)城邦的目的在于促進(jìn)善德和自給自足,城邦中的執(zhí)政者應(yīng)該帶領(lǐng)全城邦的人們追尋高高在上的美善的生活,而不是落入塵世的社會(huì)生活[2]153。那么在進(jìn)行分配的時(shí)候,誰(shuí)做的貢獻(xiàn)多,就擁有更為優(yōu)越的政治品德,故而應(yīng)該在這個(gè)城邦中享受到更多的東西,這與亞里士多德“人生來(lái)便是政治的動(dòng)物”的觀念相呼應(yīng),當(dāng)人擁有優(yōu)越的政治品德成為城邦的一分子時(shí),便優(yōu)于其他人,這異于寡頭派和平民派那樣將正義單純求諸于外在的利益品的分配。依此來(lái)看,在亞里士多德眼中,無(wú)論何種平等觀念,只有符合城邦的目的,和城邦追尋的最終的善保持一致,才是他認(rèn)為所應(yīng)有的平等觀念。
二.亞里士多德《政治學(xué)》中關(guān)于什么是平等的討論
亞里士多德認(rèn)為城邦的一般含義是為了要維持自給生活而具有足夠人數(shù)的一個(gè)公民集團(tuán)[2]124,城邦的終極目的就是“優(yōu)良生活”[2]153,對(duì)平等觀念而言,它是城邦意識(shí)形態(tài)的一種體現(xiàn),也需符合城邦的終極目的,也就是說(shuō)平等觀念也要以“優(yōu)良生活”作為追求。此時(shí)就需要面對(duì)一個(gè)問(wèn)題:怎樣才算“優(yōu)良生活”?這里就不得不結(jié)合當(dāng)時(shí)古希臘具體的社會(huì)狀況來(lái)說(shuō)明。
作為以奴隸主強(qiáng)迫奴隸進(jìn)行集體勞動(dòng),并占有他們的一切勞動(dòng)成果為特征的奴隸制生產(chǎn)方式的社會(huì),自由人與奴隸的劃分不足以概括古希臘整個(gè)社會(huì)的階級(jí)特點(diǎn),最好的劃分是公民和非公民。公民身份是古希臘各城邦得以良好運(yùn)轉(zhuǎn),追求良好生活的核心,此處的公民是指全稱意義上的[2]122,之所以是核心其原因有兩點(diǎn):第一,公民身份是奴隸主維持奴隸主生產(chǎn)方式的手段。以財(cái)富限額作為接收一個(gè)人是否成為公民的條件,過(guò)濾掉了生產(chǎn)上不以奴役別人而自給自足的人,這種門檻使得人們之間的分別被人為地建立起來(lái);第二,具有公民身份的人才可能被稱為是具有“善”品格的人。這里的“善”是相對(duì)于不具有公民身份的人以及自由公民中的下層多數(shù)人來(lái)講,“善”是指具備好的道德品質(zhì)的公民,在卷四章十二中亞里士多德講到城邦的“質(zhì)”和“量”,質(zhì)即代表著自由身份、財(cái)富、文化(教育)和門望,而“量”是指人數(shù)的多少[2]229,質(zhì)、量?jī)煞矫嫫胶馐亲非髢?yōu)良生活的現(xiàn)實(shí)基礎(chǔ),所以亞里士多德認(rèn)為,如果一個(gè)政體中有中性的仲裁,其中各個(gè)階層混合平衡,這個(gè)政體就可以存在很久[2]230,這便是城邦追求“優(yōu)良的生活”的基礎(chǔ)。
作為政治動(dòng)物的人,只有在政治生活中才能追求“優(yōu)良生活”。在古代,只有富的人才有“閑暇”,而窮的人整日忙于生計(jì),正如第一點(diǎn)所講,具有一定財(cái)富限額的人才有資格成為公民,進(jìn)而參與到政治生活中去,為什么多數(shù)的城邦都選擇用一定的財(cái)富去限制人們成為公民呢?亞里士多德講到,富人由于富有恒產(chǎn),比較能夠信守契約[2]165,還能圈養(yǎng)戰(zhàn)馬,使城邦之間為戰(zhàn)時(shí)能以騎兵制勝[2]198,而且他們衣食無(wú)憂,不生盜心,不會(huì)因迫于饑寒而犯刑法[2]216,富人較窮人體現(xiàn)出來(lái)的優(yōu)勢(shì)使得富人更適于作為公民來(lái)治理城邦,這些“自然的”差別便帶來(lái)了人與人之間的差距與不平等。
由此我們可以看到,人們一般對(duì)平等的追求,主要涉及到財(cái)富、權(quán)利和榮譽(yù)等方面,亞里士多德也指出,人間的爭(zhēng)端或城邦間的內(nèi)訌一方面是因?yàn)樨?cái)富的失調(diào);另一方面是因?yàn)槊缓蜆s譽(yù)的不平[2]76。普通民眾會(huì)因財(cái)貨的不平而吵鬧,有才能的人則因名位的過(guò)分平等而產(chǎn)生憎恨之情,這些只是涉及到上層公民和下層公民之間對(duì)平等的不同追求,然而這里忽略了奴隸:被壓迫在社會(huì)最底層的奴隸也是人,但被排除在城邦之外,作為一種有生命的工具完全以附屬別人而存在。雖然對(duì)古希臘時(shí)期奴隸運(yùn)動(dòng)的記載極少,但那時(shí)因奴隸主和奴隸之間的基本矛盾而產(chǎn)生的奴隸起義,造成過(guò)每個(gè)希臘城市社會(huì)的動(dòng)蕩不安。
三.亞里士多德《政治學(xué)》中對(duì)平等觀念間沖突的化解
前面已經(jīng)敘述不同階級(jí)人們之間會(huì)因?qū)Ω髯岳娴淖非螅a(chǎn)生矛盾,統(tǒng)治階層可以利用自己的權(quán)利盡最大可能維護(hù)自己的利益,被統(tǒng)治階層可以利用自己的語(yǔ)言、行動(dòng)來(lái)爭(zhēng)取自己的利益,而不管以什么樣的方式,在亞里士多德看來(lái)都是不能達(dá)到真正的平等原則[2]149,因?yàn)槿藗兛倳?huì)對(duì)平等與正義做出有偏見(jiàn)的解釋。平等觀念間的沖突起源于不同階級(jí)對(duì)平等觀念的認(rèn)知差異,人們只能在一方面上做到正義,不可能絕對(duì)全面地合乎正義[2]165。當(dāng)人們心中對(duì)平等持不同的看法,關(guān)于平等的沖突就產(chǎn)生了。不同人群對(duì)平等的追求影響著城邦的統(tǒng)治權(quán),那么當(dāng)一個(gè)城邦擁有多種成分的人們時(shí),應(yīng)如何對(duì)各個(gè)成分進(jìn)行利益的合理分配呢?
亞里士多德解決這個(gè)因平等觀念而起的沖突的方式是依據(jù)“平等的公正”。在他看來(lái),“最為正宗”也就是“最為公正”的政體,最為公正的政體就應(yīng)該既不偏袒少數(shù)也不偏袒多數(shù),而應(yīng)以全邦公民利益為依歸[2]167,此時(shí)平等問(wèn)題便轉(zhuǎn)向有關(guān)于平等自身——我的平等追求是否符合全邦公民利益?對(duì)平等的外在追求變?yōu)閷?duì)平等的內(nèi)在考察,將不同平等觀念間的矛盾統(tǒng)一了起來(lái),對(duì)平等的追求不再是從追求少數(shù)或多數(shù)的平等,不再是追求主體或客體的平等,而是追求什么樣性質(zhì)的平等。
亞里士多德的思維從不同平等觀念間沖突的表面,轉(zhuǎn)到平等觀念內(nèi)部,將有可能引起現(xiàn)實(shí)問(wèn)題的平等間的沖突從觀念層面化解掉,這種做法既平息了富人因以善德為標(biāo)準(zhǔn)進(jìn)行城邦的利益分配而可能引起的平民階層的憤慨,又減少了平民因以自由身份為標(biāo)準(zhǔn)追求各種權(quán)利的均等而可能引起的富有人群的不滿。亞里士多德正是靠著這一“中庸”的方式[1]14,向矛盾著的多方推行著他的平等觀念,維護(hù)著奴隸主階級(jí)的統(tǒng)治。但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亞里士多德將由生產(chǎn)力和生產(chǎn)方式的矛盾造成的現(xiàn)實(shí)的平等問(wèn)題,抽象為形而上的倫理問(wèn)題,雖然可以弱化人們因平等而起的矛盾沖突,但生產(chǎn)力和生產(chǎn)方式之間的沖突卻不是那么容易能夠被掩蓋起來(lái)的,生產(chǎn)力和生產(chǎn)方式之間的沖突只有通過(guò)對(duì)政體性質(zhì)的變革才能達(dá)到,而顯然這并不是亞里士多德想要采取的方法和手段。亞里士多德作為中等階層的代表,是奴隸主國(guó)家的忠實(shí)擁護(hù)者[1]6,在書中我們可以看到,他稱贊中等階級(jí)是穩(wěn)定的、優(yōu)勝的,而且最好的立法家都出生于中產(chǎn)家庭[2]226,他所想要做的就是利用中等階層來(lái)平衡整個(gè)城邦,使政體保持在一個(gè)中間形式,只有這樣才能免除城邦的黨派之爭(zhēng),城邦才可以去追求終極的善,使城邦中的公民過(guò)上“優(yōu)良的生活”。
參考文獻(xiàn)
[1]吳恩裕.論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學(xué)》[M]//亞里士多德.政治學(xué)[M].吳壽彭,譯.北京:商務(wù)印書館,1965.
[2]亞里士多德.政治學(xué)[M].吳壽彭,譯.北京:商務(wù)印書館,1965.
[3]亞里士多德.尼各馬可倫理學(xué)[M].廖申白,譯.北京:商務(wù)印書館,2003.
基金項(xiàng)目:本文系江蘇大學(xué)第20批大學(xué)生科研課題立項(xiàng)資助項(xiàng)目,項(xiàng)目編號(hào):20CA0002
(作者單位:江蘇大學(xué)馬克思主義學(xué)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