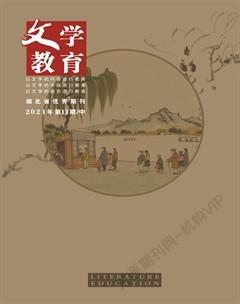文學闡釋學的形態反思
張玲
內容摘要:文章要探討的是文學闡釋學這種比較重要的思想理論形態,同時也是一種經典的文學研究方法。首先梳理其發展過程,也就是分為傳統文學解釋學、現代文學解釋學和后現代文學解釋學有三種思維方式。這三種觀點的解釋學有其自身的合法性和局限性,經過對其的分析和總結,實現對這三種詮釋學的整體超越。由此,主張一種新的文學闡釋模式:保衛作者。提倡對作者的回歸,辯證的揚棄和提升,是對后現代理論模型的反駁。
關鍵詞:作者 文學闡釋 意義 確定性
人們在接觸一部文學作品的時候,必然要涉及到對其意義的思考,這就是解釋學要研究的課題:從作品的文本出發,對意義進行更貼切的解讀。一般來說,要確定文學作品的意義,離不開作者與讀者。因此,有史以來出現的文學闡釋模式分為了傳統文學解釋學、現代文學解釋學和后現代文學解釋學有三種思維方式。本文通過分析這三種模式的利弊,最終提出保衛作者的文學闡釋模式,以期理順目前的文學闡釋學的理論狀態。
闡釋學(hermeneutics)最早出現于古希臘時代,有一位信使叫赫爾墨斯(Hermes),負責向人們傳達主神宙斯的旨意,以及其他翻譯工作,比如把神界語言轉換為人間語言。發展到中世紀的時候,闡釋學成為研究《圣經》的一種方法,也就是說將上帝的旨意通過闡釋的方式傳達給人類,所以這種學科在當時又被稱為“神學闡釋學”。闡釋學的第三個發展階段是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時期,此時的闡釋學不僅用來對典藏做注解,還擴展為對所有的古代文化的做闡釋。20世紀60年代之后,闡釋學作為一種哲學及文化思潮,在西方廣泛流行,是西方的重要文藝理論。語言在“闡釋”這門學問中非常關鍵,因為語言是作用于人類社會的一種特殊的介質,只有人類才有語言,只有人類才能進行思考。人們通過語言這種特殊媒介表達自我需求,所以有一種需求應運而生,是語言無限接近于內心真實的表達,于是便出現了闡釋學。
一.文學闡釋學的核心問題
當今的文化語境錯綜復雜,對文學意義的進行闡釋,其確定性問題逐漸成為人文學科的重要問題。該問題包含兩方面:一方面,也就是在理論層面,涉及的是文學觀的問題;另一方面,即實踐層面上,涉及的是文學行動的問題。我們需要分別對這兩個方面進行梳理分析。
我們常說:“千位讀者有千位哈姆雷特。”哪些是可行的,哪些是不可行的?在這一千個Hamlet當中,哪種最符合作者的自身的設計?這些Hamlet,如果按照價值區分,有三六九等嗎?等等……不管怎么解讀,其實都是涉及到對文學意義的解讀的確定性問題。這一問題又可以分成兩個方面:一是解釋文學意義的確定性問題。那就是,誰產生了文學意義,這些意義是怎么形成的?二是如何評價對文學意義做出闡釋的這種確定性。如果能解決這兩個子問題,就有可能對文學闡釋的確定性達成共識。
二.核心問題的解決思路
目前,解決上述問題有三種方法。不是每一種詮釋學都只有一種聲音,沒有區別。事實上,每一種詮釋學觀念都有一種復雜的存在,這種存在是“和諧而不同”的,略有不同。
第一種,傳統闡釋學的思路。
特里·伊格爾頓的《文學理論導論》中指出,德國哲學家胡塞爾的現象學是文學闡釋學的淵源。胡塞爾認為人們可以完整地認識客觀世界并得出結論,不需要外在的歷史或者社會條件輔助。胡塞爾假設出一種能表達作者真實意圖的特殊語言,這種語言沒有實際的存在形式,是一種存在于意識的語言。這種情況可以運用繪畫、音樂等藝術手段進行表達,可是音樂和繪畫并不能等同于文學。
第二種,現代闡釋學的思路。
基于上述問題的矛盾性,胡塞爾的學生Martin Heidegger在其哲學著作《存在與時間》從存在主義的角度對該問題進行了梳理,采取了與胡塞爾的“本質主義”截然相反的立場。他認為人認識事物不能孤立存在,它屬于人類存在,而人類的存在離不開其構成要素——歷史或時間。但Heidegger認為人類對世界的理解是完全被動的。Heidegger的觀點比Huseerl更加進步,肯定了歷史和語言在文學闡釋學中發揮的作用。然而,他的論斷也存在一個矛盾之處:如果說人類的理解只能是被動的,那又如何做到在歷史層面上進行分析?
第三種,后現代闡釋學思路。
后現代闡釋學是比較極端的。主體不存在,人們生活在一個毫無意義的世界。后現代主義主張生活脫離風格、個性和藝術。Ffdedei,djffw在后現代主義的世界觀下,后現代闡釋學認為,可以忽略作者的存在。人們不必過分糾結闡釋者提供的理解是否可行,只需要從中體驗閱讀的快感即可。在這個混亂的世界里,權力賦予了他這種力量,但讀者還不知道,他仍然享受著戲劇般的幻想中詮釋所帶來的肉體上的快樂,作者淪為一種擺設性的存在。更有甚者,后現代詮釋學甚至反對交流。
經過一輪探討梳理,開頭提出的問題用后現代文學闡釋學理解就會成為“一千位讀者有一千位Hamlet”。這一千個Hamlets是在極樂的游戲中創造出來的功能性讀者,對于顯著性評價機制等問題是沒有意義的。
三.反思文學闡釋學的思路
這三種解釋學形式都是合法的,應該整合到新的解釋學中。在此,我們嘗試運用布迪厄的反思性社會學研究,對文學詮釋學進行一些思考:其一,保證知識獲取科學性的工具是反思。反思性社會學認為,需要用兩種反思保證人類獲取知識的科學性。正如布迪厄所說:“第一個要確定的是,把握研究對象的社會建構過程。這是把握認知科學性的關鍵。”第二,研究主體要不斷進行反思,以獲取知識之間的區別與相互聯系。只有這樣,才能產生科學知識。回到文學闡釋問題,一方面,文學闡釋需要解釋一種文本的意義,反思性文學詮釋學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要找到知識的來源,幫助人們更好地獲取知識,更好地對意義進行闡釋。
現在要解決的就是怎樣設置評價的標準問題,有三點需要注意:首先,作者創制文學意義的過程要獨立完成,作品發表后意義的傳播過程也要獨立進行,解釋者拿到手中后對意義的接受過程應該也是獨立的。第二,解釋者將意義確定后公之于眾,這樣一來,意義實現的價值就可以作為某一段時間內的相對固定的選擇。這種固定的價值形式會影響行動者的現實行為。第三,當一段時間過后,相對固定的意義可能被新產生的確定的意義取代,那么舊的意義就可以退出大的公共領域,不過仍然可以存在于個別的小型領域中。這樣就可以繼續發揮對個體的作用,避免個體產生形而上學等思想問題。
四.超越傳統思路:回歸作者
E.D.Hirsch提出客觀闡釋學的理念,以客觀主義精神為指引,主張通過闡釋行為使讀者對作品的原來意義有所了解,進而理解作者意圖,這樣就可以將誤讀降最低點。
現在讓我們來看看Hirsch是如何逐步擊破現代解釋學的論點的。第一,Hirsch提出作品的含義和作品的意義兩種不同的概念。他認為,“文本含義是作者運用各種符號表達各種事物……,而文本意義是文本含義和某個具體的個體、情景、任意事物之間的關聯。”從作者的角度來說,作品的意義(significance)會變化,作品的含義(meaning)是固定的。第二,針對作品意義中的確定性和不確定性這對矛盾,Hirsch創設了范型的概念。將范型運用于闡釋學領域,是為了將作品的含義的確定性與它自身的范型相關聯。不過Hirsch沒有將確定性偏激的固定住,而把確定性視為作者想要的范型的確定性,這種范型的確定性不是一成不變的,既能顯示確定性的存在,也包含差異性。這樣一來,范型就把文本的含義的個別性與解釋的社會性結合起來了,合理地解開了文學作品意義的確定性與不確定性的謎團。第三,Hirsch還區分了解釋與批評。Hirsch拿傳記做例子進行了詳盡的闡述:“解釋,是與個人的生活息息相關的,比如這個人的個人閱歷等等;批評,范疇要更大一些,就是將個人的生活納入更大的范圍去討論。”所以說,文本意義的確定性是文本意義的不確定性的前提。鑒于此,Hirsch提倡保衛作者,其實就是保衛一部著作的意義的確定性。
綜上所述,本文主張在文學闡釋的過程里,履行一種較為新穎的文學闡釋規則:再次回歸作者,目的是糾正目前出現在文學批評界的一些謬誤。今天,我們要倡導的新的理論——保衛作者,就是對后現代理論的質疑,也是一種超越。而文學理論的進步正是在無數次質疑和超越中迂回前進。
參考文獻
[1]傅美蓉.從烏托邦到異托邦:婦女主題博物館的空間實踐[J].東南文化,2018(05):121-126.
[2]趙柔柔.身體的抵抗——20世紀西方烏托邦轉向與反烏托邦敘事[J].江蘇社會科學,2018(03):230-237.
[3]桑明旭.如何看待“作者之死”[J].哲學研究,2017(05):99-108.
[4]A.埃倫,孫秀麗.非烏托邦的解放——臣服、現代性以及女性主義批判理論的規范性訴求[J].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16(02):147-156.
(作者單位:山東師范大學外國語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