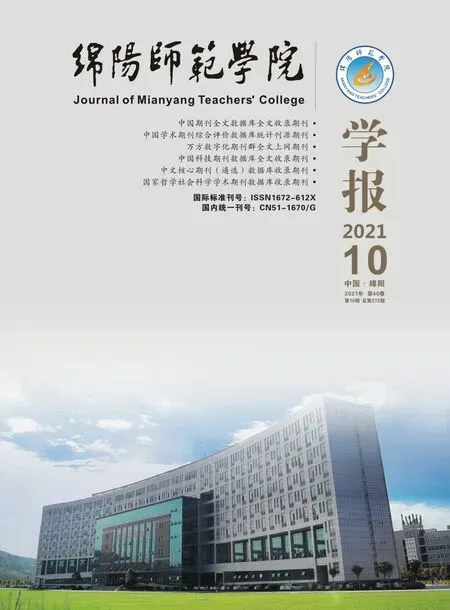網絡歷史書寫中的女性自我意識
——以米蘭Lady為例
鄧韻娜
(西南科技大學文學與藝術學院,四川綿陽 621010)
女性歷史小說作為中國網絡小說中的一個重要類型,與將男性作為主體的中國史學與史傳傳統之間存在著天然的對抗關系。如何在男性話語所記載的歷史中尋覓、拾取女性的模糊面影,并賦予其飽滿的人格與血肉之軀,重塑女性在歷史舞臺上應有的身份與意義,成為網絡女性歷史書寫所追索的共同主題。其中,桐華的《步步驚心》采取穿越的形式,以現代女性的眼光審視男性宮廷黨爭;流瀲紫的《后宮·甄嬛傳》和海宴的《瑯琊榜》則選擇了架空歷史,為女性的生存斗爭虛構出全新時空;蔣勝男的《鳳霸九天》《羋月傳》等作品以基本史實為綱,用女性日常生活經歷填補史傳空缺。總的來說,以上作品都是將歷史作為“釘子”,據此充分發揮個人的創作與想象。有“宋史言情天后”之稱的米蘭Lady則與前者不同,她深耕宋史,對兩宋歷史人物及其事跡了如指掌,因此在她的女性歷史書寫中時常穿插著大段的正史記載,并與女主人公的個人際遇嚴絲合縫地綴為一體。在此基礎之上,對于宋代宮廷禮制、政治風云、物質文化與風土民俗的細致考證和展示也成為米蘭Lady的寫作特色,讓她的作品擁有了磅礴氣象與厚重底蘊,也讓讀者切身體驗到了歷史長河中的陣陣漣漪。
長篇歷史小說《孤城閉》和《柔福帝姬》是米蘭Lady 最負盛名的代表作。其中,《孤城閉》圍繞《宋史》中關于仁宗朝福康公主與宦官梁懷吉的記載,以公主與懷吉的愛情悲劇為主脈,展開了一幅北宋仁宗時期國家昌盛、名臣輩出、百姓安樂的歷史、政治與風俗畫卷。包拯、司馬光等名臣的直言敢諫,歐陽修、蘇軾、宋祁、晏殊等文人墨客的千古詞章,由范仲淹、富弼、韓琦、歐陽修等人所倡導的慶歷新政,通通有史可依。因此,由《孤城閉》所改編的電視劇《清平樂》在對仁宗朝整體歷史背景的把握上獲得了宋史專家虞國云的高度贊譽。《柔福帝姬》也改編為電視劇《柔福》,女主人公同樣出自宋史。柔福帝姬是宋徽宗的愛女,宋欽宗和宋高宗的異母妹妹,在靖康之難中與徽欽二宗一同被擄至金國,受盡磨難后逃回臨安。徽欽二宗被俘后,高宗建立南宋,遭到金兵數次奔襲,苗傅、劉正彥趁機發動兵變,逼迫高宗退位,呂頤浩、張浚、韓世忠、劉光世、張俊等名臣迅速趕來勤王復辟。內憂外患中的宋高宗不得不對金國采取求和的姿態,在主戰派韓世忠、岳飛和主和派秦檜之間舉棋不定,這讓一心收復失地、報仇雪恥的柔福帝姬大為不齒。兩宋之際的風云變幻成為柔福帝姬一生飄零的時代背景,也因為一個女子的愛恨情仇而具有了更為細致可感的溫度與肌理。
由此可見,翔實的史料搜集整理與女性細膩的個人體驗之間的平衡成為了米蘭Lady歷史小說創作所要解決的一大難題。筆者認為,米蘭Lady主要通過女性自我意識的穿針引線實現了宏大歷史與幽微心事之間的巧妙彌合。美國耶魯學派學者杰弗里·哈特曼認為,自我意識不同于歐陸學派所提出的理性“主體”概念。主體完全隸屬于理性范疇,立足于理性與感性、主體與客體、永恒與短暫之間的二元對立。自我意識則打破了西方思維框架中的一系列二元對立,并在二元對立的兩極之間來回流動。米蘭Lady筆下的女性自我意識同樣打破了歷史書寫中的二元對立,在整體性的歷史與個人化的體驗之間往來無間。總的來說,米蘭Lady的歷史書寫中可以找到以下一系列的二元對立兩極:中國古代宮廷生活與西方柏拉圖式的精神戀愛、歷史記載與小說技法、上國風光與情感悲劇、儒家傳統與現代意識。在女性自我意識的流淌與連綴之下,這些原本二元對立的兩極之間實現了互通有無與彼此勾連,使得米蘭Lady的小說同時呈現出細膩的心理揣摩與恢弘的氣魄、純粹美好的人格與驚世駭俗的情感糾葛,以及濃郁的古典風韻與現代性的思索。
一、天家兒女與精神戀愛的雙峰對峙
《孤城閉》與《柔福帝姬》中都能梳理出兩條貫穿始終的主線:生在帝王家的無奈與柏拉圖式的精神戀愛。兩條主線如同雙峰對峙交映,故事則在夾岸間跌宕起伏。《孤城閉》中男主人公梁懷吉八歲凈身入宮,幾經輾轉后得以侍奉最受仁宗寵愛的長公主徽柔。仁宗生母李氏本是侍女,生下仁宗后交由劉德妃撫養,至死無緣母子相認。仁宗得知真相后極力提拔出生卑賤的母舅李用和,并將李用和的兒子李瑋立為駙馬。李瑋生性愚魯,母親楊氏為人粗鄙,徽柔下嫁后苦不堪言,更與懷吉暗生情愫。皇后與仁宗、宦官張茂則之間的暗流涌動則成為旁枝暗線。皇后是開國元勛曹彬的孫女,對仁宗用情極深,但仁宗忌憚曹家勢力,再加上皇后同情新政大臣,有干政之嫌,因此對皇后滿心猜疑,常年冷落;張茂則是皇后身邊的內侍,愿意用一生去守護皇后。皇后對于仁宗、張茂則對于皇后,都抱有柏拉圖式的隱忍情感。
《柔福帝姬》中,按照朝中定例,不同妃嬪所生的子嗣異殿而居,皇子長大則要離宮另建居所,因此異母所生的兄妹幾乎沒有見面的機會。康王趙構在宮中偶遇假扮為宮女的柔福帝姬瑗瑗,并對瑗瑗一見傾心。多年后,被金人擄走的瑗瑗逃回臨安,已經登基稱帝的高宗趙構仍然對瑗瑗抱有一份隱秘的男女之情;另一條暗線則是瑗瑗的侍女吳嬰茀對于趙構的愛慕。嬰茀在靖康之亂中出逃,成為趙構的侍女,在苗劉兵變中拼死護駕,終于被納入后宮。就在侍寢的當晚,金兵突襲,趙構受驚過度,失去了男性能力。因此趙構、瑗瑗和嬰茀之間的感情與陪伴都止步于精神層面。
與傳統史傳中對于“帝王將相”的艷羨與歌頌不同,在米蘭Lady的女性自我意識燭照下,手握天家權柄的仁宗與高宗顯得十分悲哀和無奈。仁宗立身謹嚴,禮遇言官,當他因為朝中諍言而不得不鉗制囂張跋扈的張貴妃時,徽柔的自我意識對于仁宗的態度流向了尊敬和認可的一極。徽柔下嫁后,因為與懷吉走得太近引發婆媳爭執,一怒之下夜開宮禁,犯下大忌。在言官的死諫之下,仁宗不得不一次次地讓徽柔與懷吉分開,徽柔的自我意識也流向了失望和同情的對立一極。徽柔與懷吉訣別之前,承諾每年都會在宮外的桃枝上掛上花勝,以慰相思。此時徽柔的自我意識從天家兒女的無奈流向了柏拉圖式的精神超越。趙構還是康王時,曾經主動請纓,前往金營做人質,并因泰然自若的氣度而令金主嘆服。在此時的瑗瑗眼中,她的九哥是一個頂天立地的男子漢,即使被擄北上,被迫委身完顏宗雋,瑗瑗也堅信九哥一定會為她報仇。當瑗瑗終于逃回臨安時,卻發現此時的趙構已經變得懦弱退縮,一心求和,瑗瑗的自我意識流從希冀、憧憬流向了鄙夷和怨恨的一極。嬰茀覺察出趙構對于瑗瑗的愛意,在韋太后的授意下指認瑗瑗是假冒的,并在瑗瑗死后被立為王后。經過漫長的歲月磨蝕,趙構在臨終前仍然緊握著瑗瑗生前留下的團扇,嬰茀的自我意識從渴望流向了幻滅,她費盡心機常伴趙構身邊,卻僅僅見證了趙構對于瑗瑗一生的追憶。如果說《孤城閉》與《柔福帝姬》中的皇宮分別象征封禁與放逐,那么男女主人公至死不渝的靈魂之愛則超越了肉體的禁錮與流離,小說中的自我意識也從女性短暫的肉體生命流向了男性永久的精神皈依。
二、歷史記載與小說技法的經緯交織
金圣嘆認為史書撰寫屬于“以文運事”,小說創作則是“因文生事”,米蘭Lady歷史書寫的核心問題之一就在于如何將史傳中固有的“事”與作者虛構鋪排的“文”巧妙結合。《孤城閉》小說開頭,女主人公呼喚“爹娘”,哭向西華門,被禁衛當作瘋婦阻攔,其中一位禁衛認出她身邊的男子是常入宮門的宦官,才開始詢問女子身份,得知對方竟是兗國公主。她的自我意識從癲狂不經流向了對立一極的尊貴無匹,渲染出令讀者惋惜不已的慘痛結局,也為后文設置了足夠的懸念。該情節出自《宋史》中關于“周、陳國大長公主”的記載:“嘉佑二年,進封兗國。……帝念章懿太后不及享天下養,故擇其兄子李瑋使尚主。瑋樸陋,與主積不相能。主中夜扣皇城門入訴。”[1]8776作者為此還特地撰寫《宋代皇室成員的稱謂》,引用《四朝見聞錄》《鐵圍山叢談》等史料筆記,論證宋代皇子皇女稱父皇為“爹爹”,稱嫡母為“孃孃”或“娘娘”,后妃、內侍與臣民則稱皇帝為“官家”。以倒敘手法打開全篇,故事繼續以懷吉的視角從頭展開。懷吉送畫入中宮,皇后命懷吉回去挑選幾幅以呈圣覽。懷吉在返程途中偶然看見一位小姑娘在月下為生病的爹爹祝禱,不惜以身代父。再度送畫之日,張貴妃污蔑長公主徽柔夜行巫蠱,詛咒八公主幼悟,懷吉挺身而出,說出實情。公主為父祝禱同樣出自《宋史》:“主幼警慧,性純孝。帝嘗不豫,主侍左右,徒跣吁天,乞以身代。帝隆愛之。”[1]8776送畫入宮這一情節安排讓史筆記載成為公主與懷吉的初見。公主單衣赤足,符合史實,也讓懷吉在不知對方是誰的情況下感動于其拳拳孝心,從一開始就拋開世俗身份,洞見靈魂,暗示了兩人的柏拉圖之戀。公主的“性純孝”也為她日后為仁宗所做出的犧牲伏脈千里。
《柔福帝姬》中瑗瑗的生平經歷同樣見于《宋史》。《宋史·宦官列傳·馮益》中記載,柔福帝姬北歸后,大太監馮益負責驗明正身。“紹興議和” 后,高宗迎回生母韋太后,韋太后卻一口咬定真正的柔福帝姬已經死在金國,眼前的柔福帝姬的真實身份是尼姑靜善,馮益也被發配昭州。《宋史·列傳第七·公主》則隱晦地提到“靜善遂伏誅”,暗示假扮柔福帝姬的靜善經受嚴刑拷打之后招供,被高宗賜死。《鶴林玉露》《四朝見聞錄》《隨國隨筆》等典制文獻和史料筆記則認為,逃回故國的柔福帝姬是真正的公主,韋太后之所以要致其于死地,是因為擔心柔福帝姬會泄露自己在金國所遭受的種種不堪經歷。在米蘭Lady筆下,瑗瑗被金國八太子完顏宗雋所霸占,韋太后和高宗的原配邢夫人則委身于景國公完顏宗賢。在一次宴會上,完顏宗賢讓韋太后與徽宗相見,并表示愿意把韋太后還給徽宗,韋太后卻拒絕了,在場的瑗瑗直言不諱地指責韋太后,也為自己埋下了禍根。逃回南宋的柔福帝姬不僅身受凌辱,還目睹了其他皇室宗親的不幸遭遇,性情大變,也讓部分舊宮人生疑,這是在立足史實基礎上創造出的一個剛烈、孤傲、偏執的浪漫主義悲劇形象。《建炎以來朝野雜記》記載,柔福帝姬下嫁高世榮,嫁妝有二十萬緡,這不但明顯違背了當時崇尚節儉的風尚,而且超出了南朝定例的數十倍。宋史中宋高宗為養子賜名一個“瑗”字,與瑗瑗同名,這都成為小說里趙構愛慕瑗瑗的佐證。
《孤城閉》與《柔福帝姬》中的主要人物雖然出自史傳,卻被作者賦予了獨立的自我意識與完整的精神世界,他們各踞立場,時有激烈辯論。《孤城閉》中張貴妃借用皇后車輿上的紅傘而不得,暴怒如狂,徽柔指責她欲望太過,她卻認為徽柔也一定有看似尋常卻不為世人所容的愿望;面對諫官廷諍,仁宗請求群臣念及一個父親的骨肉親情,司馬光反駁:“世人皆稱陛下為‘官家’,是取‘三皇官天下,五帝家天下’之意。皇帝以天下為家,天下萬民無不是陛下兒女。陛下豈可獨愛公主而將其余子民拋諸腦后?”[2]歐陽修屢遭臺官彈劾,一生坎坷,請辭離京前卻說很慶幸“我遇到的君主仰懼天變,俯畏人言,嚴于律己,又并不乏辨識力,知人善任,禮賢下士,從諫如流,國家言路開明,所有人都受到言者監督,無人可肆意妄為、獨斷專行”[3]。《柔福帝姬》中瑗瑗、玉箱和韋太后三人的態度與觀點之間時常產生對比與沖突。瑗瑗毫不掩飾對宗雋的仇恨,吃盡苦頭;玉箱忍辱負重,對金主假意承歡;韋太后則對宗賢感激婉順,安于現狀。一日瑗瑗偶遇韋太后,發現她已經懷有身孕,憤怒地指責她毫不顧及高宗的顏面與南朝的尊嚴,玉箱卻認為韋太后常年受到徽宗的冷落,彼此之間根本談不上情義,宗賢卻對韋太后呵護備至,因此韋太后的選擇合乎人情。而且韋太后既然已經嫁給了宗賢,就算勉強回到徽宗身邊,也同樣難以自處。宋金議和后,歸國在即,韋太后問邢夫人:如果瑗瑗把她們婆媳共事一夫的丑事說出去該怎么辦?邢夫人當晚就懸梁自盡,用行動回答了韋太后的疑慮,韋太后也對瑗瑗起了殺心。
與傳統史書中或隱或現地表達作者對史實的態度與評議不同,米蘭Lady的歷史書寫中無意判定不同人物的是非曲直,只是為他們提供各抒己見的舞臺,讓人物各自的心曲匯成多聲部的合唱。這一人物塑造技法與巴赫金復調小說理論暗暗相通。復調小說人物不像獨白小說人物那樣是作者的客體對象,而是獨立于作者的平等自我意識,“應該揭示的……是他的意識和自我意識的最終總結,歸根到底是主人公對自己和對世界的最終看法。”[4]60復調小說主人公所擁有的獨立自我意識使得他們不再被作者所規定和限制,而是發出完全屬于自己的聲音,與其他人物甚至作者進行對話與辯論。與復調小說不同的是,《孤城閉》與《柔福帝姬》主人公不被作者所掌控,還因為他們早已被歷史寫下結局,充滿自我意識的血肉之軀與無情的歷史車輪相碰撞,綻放出動人心魄的孤勇與凄絕。
三、上國風光與情感悲劇的鮮明對比
米蘭Lady閱讀了大量宋代相關史料與文獻,其作品也對當時的民風民俗、市井風光和宮廷文化進行了濃墨重彩的細細鋪排。《孤城閉》中,徽柔初入公主館閣時,兩人都是總角之年,徽柔正與玩伴做簸錢之戲,屢屢戰敗的徽柔為了不讓對手猜出掌下銅錢的正負,故意把銅錢夾在虎口之間,懷吉從公主手背拱起的形狀猜出銅錢非正非負,公主的母親苗昭儀責備公主“壞了規矩”。豎立的銅錢非正非負,處于靈與肉的交界點,正是懷吉與公主這段精神戀愛的象征,“壞了規矩”更是一語成讖。簸錢的典故出自歐陽修《望江南》:“十四五,閑抱琵琶尋,堂上簸錢堂下走,恁時相見已留心,何況到如今。”七夕之夜,仁宗與六宮嬪妃彩樓乞巧,供奉彩衣泥塑玩偶“磨喝樂”、穿針、焚香等儀式皆從民間而來。皇后提及出閣前的閨中游戲,許愿后轉動銅錢,如果正面朝天,心愿就能實現。徽柔連試了三次都是負面,于是用蠟油將兩枚銅錢的背面粘在一起,轉動之后,銅錢側立不倒。皇后說自己十八歲時用一枚銅錢許愿,也得到了同樣的結果。豎立的銅錢成為作品中的代表意象。皇后母儀天下,卻始終得不到仁宗的信任,夫妻關系徒有其名,含而未吐的情感,正如豎立的銅錢,成為煢煢獨立于有情與無情之間的界線。
《柔福帝姬》中,“紹興議和”后,趙構命修內司官窯燒制了一個花瓶送給瑗瑗,瓶身上雕著兩人初遇時瑗瑗蕩秋千的倩影。瑗瑗卻因為趙構向金人一再退讓而悲憤不已,不但砸碎了花瓶,而且還企圖用碎片割腕自盡。修內司官窯又稱南宋官窯,燒制出的宮廷瓷器有“厚釉薄胎”“紫口鐵足”的特征,且多有紋片。紋路精美又胎薄易碎的官窯瓷瓶象征了宋室皇女的命運,沾上瑗瑗的鮮血之后顯得更為觸目驚心,其背后的女性自我意識從典雅華貴流向了無限悲辛。中秋之夜,臨安城中徹夜華燈,歌舞升平,士人淑女紛紛把“一點紅”羊皮小燈放入錢塘江祈福。宮人摹仿民間風俗,也在御池中點燈。當晚,趙構告訴瑗瑗,完顏宗雋已經因為通宋的罪名被金主所殺,瑗瑗立刻猜到是趙構用了離間計。瑗瑗一心希望高宗揮兵北上,堂堂正正地殺死宗雋,為自己、也為千千萬萬的大宋子民報仇雪恥,沒想到趙構只能偏安一隅,玩弄權術與陰謀。與趙構相比,英武豁達、苦學中原文化的宗雋反而高大了起來。瑗瑗對宗雋的態度從切齒痛恨流向了同情與追懷。滿池星河的輝映下,她的心中只有寂滅的悲哀:曾經的英雄成了小人,曾經的仇恨又化作云煙。米蘭Lady所塑造的女性自我意識總是從上國風光的繁華流向無所依憑的落寞。
四、儒家傳統與現代意識的遙相輝映
《孤城閉》集中探討了不同儒學流派之間的交鋒。仁宗給徽柔布置命題文章論“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于心”[5]309,該句出自《孟子》。孟子認為,人心天然就具有“仁義禮智”,“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也。”[5]259對苦難的同情、對邪惡的反感,對天地君親師的恭敬,以及對是非的判斷,是人心中固有的“良知”“良能”。因此,“學問之道無他,求放其心而已矣。”[5]267儒家修習的要義就是找回遺失的善良之心。明代王守仁在此基礎上發展出與程朱理學相抗衡的心學。“知是心之本體。心自然會知:見父自然知孝,見兄自然知弟,見孺子入井自然知惻隱,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6]7如果說孟子強調“放其心”,王陽明心學就更偏重“心自然會知”“不假外求”。可以說,仁宗代表了孟子的觀念,他心懷仁厚,仍時刻警醒自己不要遺落“良知”。一晚仁宗想吃燒羊,卻擔心百姓跟風模仿,屠戮羊群,寧愿忍饑挨餓;想喝水時隨侍不在身邊,為了不讓隨侍遭到責罰,就算口渴也不發一言;把最珍愛的長女嫁給母弟之子,既為母家盡孝,也為天下做出表率,令百姓相勸以孝。徽柔得知仁宗將自己許嫁李瑋,哀嘆:“如果我真是個珠寶也就罷了,任他送給誰都無怨言,因為沒有眼睛,也沒有心,分不出美丑,辨不出賢愚。可是誰讓我生為一個有知覺的人……。”[7]對“心”與“知覺”的強調暗中契合了王陽明“知是心之本體”。徽柔眼見仁宗病倒,自然就愿意以身代父,替爹爹承受痛苦;張貴妃放誕無禮,貪得無厭,她從小就對此心生反感;明明已經說服仁宗留下了懷吉,只因仁宗為她送來幼時最愛吃的釀酶,令她感知到一片愛女之心,就立刻做出讓步,兌現了幼時替爹爹承受痛苦的諾言。對于徽柔來說,一切懲惡揚善的行為都是發自內心的自然流露,不需要任何外在的規訓與約束。仁宗一味注重心中固有的先天道德,忽略了心的“知覺”,造成了徽柔的悲劇。
司馬光與北宋“理學五子”——周敦頤、邵雍、張載、程顥、程頤來往密切,在書中成為程朱理學的象征。程朱理學將三綱五常與天理結合起來,與王陽明“心外無理”針鋒相對,認為“理”外在于“心”。由此提倡“存天理滅人欲”,不是像孟子和王陽明那樣向內尋求先天道德,而是用外在的綱常倫理規范和制約行為與內心。程顥強調:“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學者當學顏子,入圣人為近,有用力處。”[8]48其立足點就在于,不是人人都像孟子、王陽明那樣天生具備“仁義禮智”與“良知良能”,并非圣人的凡夫俗子應當效法顏淵的“克己復禮”即“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9]123,通過恪守外在禮制滅除內心的非道德欲望。徽柔、仁宗與司馬光之間極具復調小說特征的論辯投射出王陽明心學、孟子心本體論與程朱理學三派儒家學說的交鋒。徽柔摹仿蘇軾杜撰典故,稱《太宗實錄》記載,太宗上元節賞燈,路遇女子相撲,馮拯指責女相撲衣著暴露,理應禁止,太宗問馮拯是否記得誰勝誰負,馮拯答不出,太宗笑稱馮拯只在乎女子裸露,不顧賽事,“所見即所思。人性無染,本身圓成,只要保持清凈心性,那么那些虛幻皮相豈會引起淫邪之念?卿憂心至此,是把天下萬民全看成淫邪的小人了。”[10]“人性無染,本身圓成”即是王陽明的“心外無理”,徽柔與懷吉發乎情止乎禮,不懼市井間流言蜚語;仁宗在朝上以骨肉之情打動眾臣,是基于孟子“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司馬光則站在蕓蕓眾生的角度,堅持用外在的道德準則約束內在的舐犢之情,他雖然不至于將天下萬民看成“淫邪小人”,卻也堅持他們并非人人都具備仁宗、徽柔那樣的“清凈心性”,因此必須讓他們“非禮勿視、非禮勿聽”,為維護綱常倫理的有效性,徽柔與懷吉決不能在一起。神宗即位后,在宦官的挑撥下與皇太后曹氏不睦,司馬光多次直諫,終于令神宗態度緩和,這一情節從側面認可了程朱理學積極的一面。
《柔福帝姬》則借趙構的養子趙璩之口探討了范沖與王安石圍繞《明妃曲》所產生的儒學思想碰撞。趙璩的啟蒙老師范沖認為,王昭君作為漢宮女子,遠嫁胡虜,心中應當懷有無窮的怨恨,因此大多數詩人所做的《明妃曲》都是悲愴凄涼的調子,王安石的《明妃曲》卻稱“漢恩自淺胡恩深,人生樂在相知心”,將“胡恩”置于“漢恩”之上,違背了三綱五常中的君父之道,也壞了天下人的心術。趙璩卻說,王安石《明妃曲》強調的是君王用人之道,所謂“胡恩深”與“漢恩淺”,是對于明君與昏君的暗喻,因此該詩真正想表達的是作者對于慧眼識珠的知己的渴望之情,以及愿為知人善任的明君鞠躬盡瘁的赤子之心。范沖是宋朝著名史學家,對于司馬光極為推崇,他強調綱常對天下人的約束,也與司馬光的立場一致。王安石的儒學思想則被稱為荊公新學,他對孟子極為推崇,認為孟子是可與孔子比肩的圣人。在治經方面,王安石摒棄章句訓詁,倡導以義理解經,尤其重視道德性命之理。他的性命之說與孟子的心學是一脈相承的。《柔福帝姬》中的韋太后在宮中極不得寵,地位卑微,到了金國之后卻被完顏宗賢賞愛。宗賢不但給了她尊榮的地位,還忍痛讓她回歸故里。韋太后聽到趙璩論《明妃曲》,觸動心事,感慨萬千,儒家義理與小說創作巧妙地結合了起來。
《孤城閉》雖然講述的北宋年間的宮廷軼事,其中所塑造的人物卻與車爾尼雪夫斯基的《怎么辦》具有精神上的勾連。《怎么辦》中的女主人公巴夫洛夫娜從小被母親控制,得不到婚姻自由,在醫科學生洛普霍夫的幫助下逃離了舊家庭。此后,她建立了專收女工的縫紉工廠,贏利全歸女工所有,目的就是幫助盡可能多的女性獲得經濟與生活上的自由;她在兩段婚姻中都堅持禁欲主義,認為愛情并非肉欲上的滿足,而是生活中的陪伴與相處。在第二段婚姻中,她與丈夫討論詩歌、愛情與男女平等問題,認為這是永葆愛情的良方。《孤城閉》中徽柔自己婚姻不幸,卻支持和鼓勵身邊的女性追求自由。國舅夫人楊氏為駙馬納妾,選中侍女春桃,春桃執意不肯,遭楊氏打罵,公主站出來為春桃贖身,促成她與意中人的姻緣。之后公主召集身邊所有的侍女,承諾但凡想要離開的都賜金放還,幫助她們沖破禁錮,追尋心中的幸福,自己卻在公主宅承受孤獨。《柔福帝姬》中的瑗瑗幼時被迫纏足,她對此激烈反抗,并希望所有的女子都能自由選擇自己的名字、夫婿,并自行決定是否纏足。在愛情觀方面,徽柔與懷吉、瑗瑗與趙構之間,都存在著精神之間的吸引與靈魂上的契合。
米蘭Lady筆下的人物大多在秉承儒家心學的基礎上具有犧牲奉獻的精神。徽柔自己被縛于皇女的身份,卻能因為幫助其他女性獲得幸福而快樂;懷吉與張茂則都將守護徽柔或皇后作為自己一生的心愿;趙玉箱為了救出父親和徽欽二宗,假意迎合金主,即使遭到眾人的唾棄與誤解也在所不惜;瑗瑗更是為了天下萬民和國家的尊嚴一次又一次地激怒當權者,最后死于獄中。對于他們來說,一切犧牲都是發自本心的自然流露,這與《怎么辦》中的“利己主義”暗暗相通。洛普霍夫認為,如果為他人犧牲能夠讓他人幸福,從而讓自己快樂,這種表面的犧牲就是一種“利己”。基爾薩諾夫也說:“總數大于部分,人之情理比你的任何個別欲望對你更為重要、更為有力量,如果這兩者發生矛盾,那么與其滿足你的任何個別欲望,不如順乎人之情理,只有這樣,才能保全住一切。簡而言之:為人正直,一切都會圓滿的。”[11]195“人之情理”超越個人欲望對正直的人具有重大力量,正是王陽明“心外無理”的另一種表述。
綜上,米蘭Lady的女性歷史書寫一方面扎根歷史,為中國傳統文化注入了鮮活靈動的生命力,另一方面又在人物塑造上體現出車爾尼雪夫斯基筆下“新人”的特質,呈現了新時代的精神風貌。人物在精神上所承襲的儒家心學內涵與《怎么辦》中“利己主義”的呼應,也是在文學創作上對于守正創新的一種探索:通過西方優秀作品與思想的比較與映照,在博大精深的中國傳統文化中挖掘出鮮明的時代意義。這對中國網絡小說在創作上的健康發展提供了積極的引導與借鑒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