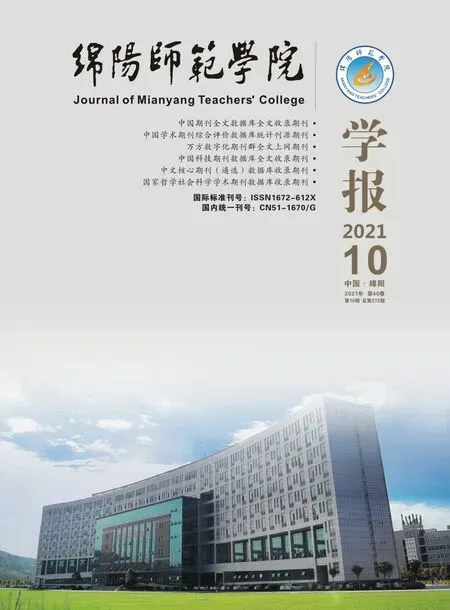論《民法典》第146條第1款的司法適用
——以房屋買賣合同為視角
畢明珠
(鄭州大學法學院,河南鄭州 450000)
2017 年3月15日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總則》(以下簡稱《民法總則》)在第 146 條首次規定了“虛假行為”, 進一步完善了民事法律行為相關制度,也是對民事法律行為效力問題的一大創新。2020年5月28日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以下簡稱《民法典》)延續這一制度。在司法實踐中,當事人主要是通過簽訂虛假房屋買賣的方式進行逃避稅款或者是騙取銀行貸款。人民法院在審理虛假房屋買賣相關案例時,主要是從當事人雙方是否有真實意思表示以及是否有通謀來具體認定虛假行為的存在與否。但是,人民法院在審理相關案件時,對虛假行為規則和惡意串通規則的適用相當混亂。本文主要從房屋買賣合同中虛假行為的具體類型、具體認定入手,分析人民法院在審理時適用虛假行為和惡意串通規則的原因以及對善意第三人的保護,在此基礎上認為法院應當明確虛假行為與惡意串通規則的關系,并且應當出臺虛假行為不得對抗規則的司法解釋來真正保護善意第三人的合理信賴。
一、具體類型
近年來,我國房地產市場發展迅猛,房屋交易量增長迅速,法院受理的房屋買賣糾紛日益增多,其中“虛假房屋買賣”糾紛數量巨大。以虛假房屋買賣形式獲得銀行貸款、逃避債務、規避稅款、獲取他人借款等現象屢見不鮮。本文主要探討虛假房屋買賣逃避稅款和騙取貸款的情形。
(一)名為買賣,實為躲避稅款
由于房屋買賣需要支付一定的稅款和手續費,交易雙方為了節省稅費而采取簽訂“陰陽合同”的方式來實現當事人利益的最大化[1]。通過案例的搜集研究,可以發現主要有兩種情形來逃避稅款。
1.以買賣合同代替贈與合同
由于贈與的房屋需要繳納契稅,如果再次出售的話還需要繳納個人所得稅,因此相對于贈與合同來說,買賣合同繳納的稅款會相對少一些。如在“李某等訴張某等房屋買賣合同糾紛上訴案”①中,李寶柱、祁淑惠夫妻二人立下遺囑將房子遺留給兒子李秋平,但為避稅,李秋平與其母親祁淑惠簽訂房屋買賣合同并辦理登記手續,但李秋平沒有向祁淑惠支付房屋價款。法院認為祁淑惠本意是贈與房子給兒子李秋平,而不是二人之間進行房屋買賣,雙方構成通謀虛偽行為,合同無效。
2.以低價格的合同代替高價格的房屋買賣合同
在這一情形中,為了掩飾不想繳納稅款的意圖,當事人一般會簽訂兩份價格不同的買賣合同,將約定的真正想要成交的高價格合同隱藏,以低價格的房屋買賣合同進行行政登記備案,以達到避稅的目的。如在“王菲與龍建國房屋買賣合同糾紛上訴案”②中,王菲因不能償還到期債務,將其本人所有的位于長沙市××山路××號盛世東方大院2期2-3棟101房的房屋作價出售給龍建國以抵銷部分債務,二人在2015年4月27日共簽訂兩份房屋買賣合同,其中由王菲本人簽字的合同約定的成交價格為800萬元,由王菲委托代理人陳柏文簽字的合同約定的成交價格為500萬元,該成交價格為500萬元的合同為在長沙市房產檔案館備案的合同。法院認為,綜合本案來看,成交價格為800萬元的合同才是雙方當事人的真實意思表示,龍建國稱成交價為500萬元的合同系為避稅而簽訂符合情理,二人所簽訂的交易價格為500萬元的《房屋買賣合同》系雙方惡意串通為避稅而簽訂,進而認定該合同無效。
在上述兩種情形中,法院不論是根據惡意串通還是根據通謀虛偽表示來進行判斷,行為人與相對人以虛假的意思表示簽訂的房屋買賣合同都是無效的。對于隱藏行為的效力,祁淑惠與李秋平之間隱藏的贈與意思符合法律規定,合法有效;而龍建國與王菲之間的隱藏行為己經違反了稅法相關的法律強制性法規,損害了國家、集體的利益,因此隱藏行為也是絕對無效的。
(二)名為買賣,實為借貸
由于房屋買賣涉及大筆的金錢交易,因此,在實踐中常常有以通謀虛偽的方式簽訂虛假房屋買賣合同來達到騙取銀行貸款的目的。根據當事人的不同,主要分為兩種類型。
1.房地產開發商與虛假買房人之間
這一類型又被稱作“虛假按揭”,即指開發商在建設房產的過程中,與并無購房意愿的名義上的購房人進行虛假房屋買賣以套取銀行的貸款,最終由房地產開發商使用貸款并還款的行為[2]。如在“呂秋秋、上海浦東發展銀行南昌分行金融借款合同糾紛案”③中,2010年2月26日,呂秋秋先是與天地公司簽訂《商品房買賣合同》,約定呂秋秋購買天地公司開發的別墅一棟,后又與浦發銀行南昌分行簽訂《借款合同》,約定浦發銀行南昌分行向呂秋秋貸款180萬元用于購房,但該180萬元實際上是由天地公司使用的。法院認為,《商品房買賣合同》是為套取銀行貸款而簽訂的虛假合同,天地公司與呂秋秋實施的行為屬于以合法形式掩蓋非法目的的行為,該合同為無效合同。
2.虛假買房人和賣房人之間
這一類型存在于二手房買賣中,買房人與賣房人之間通謀,虛構房屋買賣合同,并根據該合同騙取銀行貸款。在“劉淑娟與李明灝房屋買賣合同糾紛案”④中,劉淑娟與李明灝簽訂涉案房屋買賣合同后,劉淑娟在取得銀行貸款的第二天即將135萬元的款項全部給付李榮春。貸款期限內,李明灝從未償還過銀行貸款,所有貸款均由李榮春償還。涉案房屋買賣合同簽訂后,李明灝并未實際居住使用涉案房屋,亦未向居住、使用涉案房屋的他人收取租金,因此其并未實際掌控涉案房屋。法院認定劉淑娟與李明灝之間并無實際發生涉案房屋所有權轉移的真實意思表示,李明灝也無向劉淑娟支付涉案房屋購房款的真實意思表示。
無論是房地產開發商與虛假買房人之間,還是虛假買房人和賣方人之間,都會涉及到銀行利益的保護。對于第三人銀行利益的保護,有的法院認為名義購房人依約承擔還款責任,開發商承擔連帶保證責任③;有的法院認為開發商作為貸款實際使用人承擔還款責任,名義購房人不承擔責任⑤;有的法院則未提及⑥。
二、具體認定
虛假行為是指表意人和相對人為了實現自己的目的而營造訂立某項法律行為的假象,其內心并不想使該行為發生法律效果的行為[3]。針對虛假行為的構成要件,學術界主要有“三要說”和“四要件說”兩個觀點。“三要件說”認為虛假行為的構成要件包括存在意思表示、意思表示不真實、行為人與相對人通謀三要件[4]285。“四要件說”在“三要件說”的基礎上增加了“行為人內心明知表意不真實”這一要件。筆者比較贊同“四要件說”,它更能體現表意人與相對人之間欠缺效果意思,不希望法律行為發生法律效果的意圖。在司法實踐中,審判機關對于案件是否屬于虛假行為從以下幾方面來認定。
(一)判斷雙方是否為真實意思表示
意思表示是民事法律行為的核心要素,它包括目的意思、效果意思和表示行為,真實的意思表示是表意人希望其內心意思發生法律效果。虛假行為是表意人內心效果意思與外在表示出來的行為不一致產生的,是非真意的意思表示。如在“程琳與程趙忠房屋買賣合同糾紛案”⑦中,法院認為本案的核心爭議焦點就在于上訴人程琳與被上訴人程趙忠之間就系爭房屋簽訂的《上海市房地產買賣合同》是否為雙方真實的房屋買賣意思表示。法院分別從房屋買賣合同的簽訂原因、房屋本身狀況和交易的背景三方面來判斷雙方之間簽訂的房屋買賣合同并非雙方真實意思表示,屬于無效合同。又如在“謝超文、尚書房屋買賣合同糾紛案”⑧中,法院分別從原、被告之間的簽約情況、交易價格、履行情況、稅費支付情況四個方面來證明簽約雙方之間并無房屋買賣的真實合意,案涉《溫江區存量房買賣合同》應屬無效。
(二)判斷雙方是否有通謀
通謀是指當事人之間存在虛假意思表示聯絡,這也是虛假行為的核心所在。如果雙方的通謀只是一方自知而非真意的行為,那么只能構成“單獨虛偽表示”或“真意保留”。在司法實踐中,審判機關對“通謀”的判定主要有兩種方式。
1.雙方共同策劃
雙方共同策劃是指在簽訂房屋買賣合同時,當事人雙方為了掩蓋自己的真實目的,雙方共謀達成非真實的意思表示。如在“王紅與張濤房屋買賣合同糾紛案”⑨中,張濤為了獲得銀行的貸款,與王紅共謀,約定將房屋出售給王紅,然后以王紅名義向銀行申辦抵押貸款,銀行放款至張濤賬戶。
2. 一方策劃,另一方明知
有時一方當事人雖然沒有參與謀劃,但對另一方當事人非真意的表示行為明知且不加阻攔也屬于“通謀”的一種。例如,在“袁先暢、彭會蘭房屋買賣合同糾紛案”⑩中,被上訴人袁先暢為了騙取銀行的高額貸款,在和房地產中介服務機構簽訂合同時,虛構真實交易價格,而上訴人彭會蘭述稱沒有看清楚該虛構交易價格就簽字。但是,若按照涉案房屋真實交易價格是無法取得175萬元貸款的,即使不是雙方共同謀劃,至少彭會蘭也明知袁先暢虛構交易價格的真實原因是騙取銀行貸款,所以雙方通過虛構交易價格來實現合同目的。
三、裁判標準
“惡意串通”規則最早規定于《民法通則》第58條第1款第4項,即“惡意串通,損害國家、集體或者第三人利益的民事行為無效”,后《合同法》第52 條第 2 項采用了《民法通則》的上述規定。在制定《民法典》的過程中,多數學者認為不應保留惡意串通行為的規定。例如,學者楊代雄認為我國的《民法典》總則只要明確規定濫用代理權意義上的惡意串通行為的法律效果即可,不需對一般意義上的惡意串通行為予以規定[5];學者冉克平認為 “惡意串通”規范應當完全廢除,以“通謀虛偽表示”取而代之[6]。
通過在中國裁判文書網查找房屋買賣中虛假行為的適用相關案例,發現法院在理解和適用虛假行為的相關規定上比較混亂,法官在裁判文書中使用了“惡意串通”“通謀虛偽表示”“以合法形式掩蓋非法目的”或者它們之間的結合等裁判理由進行裁判。由于《民法典》將“以合法形式掩蓋非法目的”的規定刪去,因此本文只重點論述惡意串通與虛假行為之間的適用問題。
在司法實踐中,法院在審理房屋買賣合同糾紛時,針對相同情形,有的法院適用“虛假行為”,如在“濱州市技術學院與趙平平房屋買賣合同糾紛案”中,法院認為,涉案住房購置合同為聯展公司與被告趙平平為騙取銀行貸款而簽訂,并非合同雙方當事人的真實意思表示,根據《民法典》第146條第1款規定,涉案住房購置合同為聯展公司與被告趙平平的虛假意思表示,該合同無效;有的法院適用“惡意串通”規則,如在“呂平與呂晶房屋買賣合同糾紛案”中,法院認為,呂晶將訴爭房屋過戶給呂平,并非真實的房屋買賣意思表示,而是借訂立買賣合同之名,以達到套取銀行貸款的目的。當事人惡意串通,損害第三人利益的,合同當屬無效。另外還有的法院將二者結合適用,如在“胡輝虎與彭影、彭婧等確認合同無效糾紛案”中,法院認為,彭鋼、宋詩霞、曾濤作為法定代理人代彭某、彭某某與彭宗容簽訂的《重慶市房屋買賣合同》,彭鋼與彭宗容認可未實際支付價款,且簽合同的真實意思并非出售房屋,而是為了以彭宗容的名義獲取貸款,其意思表示虛假,且屬于惡意串通,其行為損害了原告的合法權益,故合同無效。
惡意串通是指行為人和相對人以損害他人利益為目的,而作出的相互勾結、串通的意思表示。在虛假行為規范規定之前,惡意串通制度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部分虛假行為的作用。然而,《民法典》在第146條和154條同時規定了虛假行為和惡意串通。那么如何在司法中區別 “虛假行為”和“惡意串通”的適用呢?
筆者認為,應當厘清虛假行為與惡意串通的關系。首先,惡意串通和虛假行為有一定的相似性。例如,“惡意串通”中的“串通”和“虛假行為”中的“通謀”均指行為人和相對人之間具有意思聯絡和溝通,但二者之間更多的是區別。第一,是否存在“惡意”不同。惡意串通中,雙方當事人存在損害他人利益的故意;虛假行為中,行為人和相對人并不是以存在此故意為必須。第二,意思表示是否真實不同。惡意串通中,當事人之間只需要存在共同意思聯絡;虛假行為是行為人與相對人之間意思表示與行為必須不一致。第三,規范目的不同。惡意串通更加強調當事人共謀,損害他人的合法權益,是由于其目的不合法對其予以規制;虛假行為主要是從意思表示出發,從意思表示是否真實來判定行為是否有效。第四,是否損害他人利益不同。惡意串通中以損害他人利益為必須,而虛假行為不以損害他人利益為必要。
在司法實踐中,法院在審理房屋買賣合同相關案例時,首先應當考慮涉案當事人的共同意思聯絡是否是真實意思表示。如果雙方當事人惡意串通為虛假意思表示的情形,則應按照虛假行為規則處理,而無須考慮是否損害他人利益。如果當事人惡意串通為真實意思表示且有損害他人利益的目的,則按照惡意串通規則處理。
四、對善意第三人的保護
從世界各國立法規定來看,虛假行為的效力存在兩種模式:絕對無效和相對無效。絕對無效是指雙方當事人、第三人都可以主張無效,即是絕對、當然無效,這種模式以德國、瑞士為代表;相對無效是指虛假行為的效力不能對抗善意的第三人,這種模式以日本為代表[7]。我國《民法總則》在制定過程中,在草案的審議稿中均規定了“行為人與相對人通謀虛偽表示無效,不得對抗善意第三人”。 但正式通過的《民法總則》刪除了“不得對抗善意第三人”的規定。虛假行為無效是因為當事人雙方意思表示與表示行為不一致造成的,因而該無效僅在當事人之間發生,但由于虛假行為有時會涉及到第三人的利益,如何保護善意第三人的合理信賴成為一個問題。
在司法實踐中,房屋買賣合同中關于善意第三人的利益保護,法院一般是利用善意取得制度來保護。如在“王淑芹與王濤、第三人中國郵政儲蓄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平谷區支行房屋買賣合同糾紛案”中,法院認為,王淑芹、王濤簽訂的房屋買賣合同,其目的僅在于套取郵政儲蓄銀行平谷支行的貸款,雙方簽訂的《存量房屋買賣合同》系通謀虛假意思表示,應屬無效。但是,郵政儲蓄銀行平谷支行基于借貸關系善意取得的訴爭房屋的抵押權,應當受法律保護。因此,判決原告王淑芹償還第三人郵政儲蓄銀行平谷支行全部剩余借款本息,以消滅對房屋享有的抵押權。
但是在司法實踐中,對房屋買賣合同中“善意第三人”中的“善意”認定標準不一。例如,在“王珍珍、中國工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濱州濱城支行房屋買賣合同糾紛案”中,一審法院與二審法院對第三人王珍珍及工商銀行濱城支行未對涉案房屋進行實地考察,其是否是“善意"存在不一樣的看法。一審法院認為,王珍珍未能盡到謹慎注意義務,存在重大過失,系非善意,王珍珍對涉案房產不構成善意取得,工商銀行濱城支行對抵押權不能構成善意取得。二審法院認為,王珍珍未入戶查看,系一般過失,構不成重大過失,故一審認定王珍珍未構成善意取得不當。工商銀行濱城支行在辦理貸款審批時,已按照規定對抵押物進行實地勘察,手續也無不當之處,故該抵押合同有效。
有學者認為,在形式主義領域,對于善意取得規定足以保護形式主義下的善意第三人,而不必適用虛假行為不得對抗規則[8]。筆者表示贊同。在我國,大多數物權變動實行的是以交付、登記為權利變動生效要件的物權變動模式,但是針對其他領域,比如意思主義、債權讓與領域,善意取得制度不能適用。因此筆者認為,善意取得制度和虛假行為不得對抗規則是相互補充的,但出臺相應的司法解釋規定虛假行為無效不得對抗善意第三人的規定也是必要的。
首先,應當明確“善意”的判斷標準。第三人善意是第三人不知道、也不應當知道房屋買賣雙方當事人之間的虛假意思表示。對于一般過失應納入“善意”的范疇,而重大過失存在故意、惡意的主觀惡性,其不能適用不得對抗規則。其次,應當明確善意取得制度和虛假行為不得對抗規則的適用范圍。善意取得適用于具有權利公示方式的物權領域,在房屋買賣合同中,善意的第三人可以根據善意取得制度主張將房屋登記于自己名下。在不具有權利公示方式的其他領域則可以適用虛假行為不得對抗規則,如作為善意第三人的銀行的債權如何獲得救濟。在同一個案件中如果同時需要適用善意取得制度和虛假行為不得對抗規則時,應當給予善意第三人選擇權,法院也應當綜合考慮案情,作出有利于協調各方利益的判決。
注釋:
① 參見北京市第三中級人民法院(2016)京03民終7576號。
② 參見湖南省長沙市中級人民法院(2016)湘01民終6878號。
③ 參見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民申2109號。
④ 參見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2020)京02民終9943號。
⑤ 參見北京市西城區人民法院(2020)京0102民初6449號。
⑥ 參見湖北省武漢市武昌區人民法院(2016)鄂0106 民初4773 號。
⑦ 參見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2020)滬01民終7783號。
⑧ 參見四川省成都市中級人民法院(2019)川01民終16690號。
⑨ 參見北京市第三中級人民法院(2021)京03民終722號。
⑩ 參見廣東省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2020)粵01民終8395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