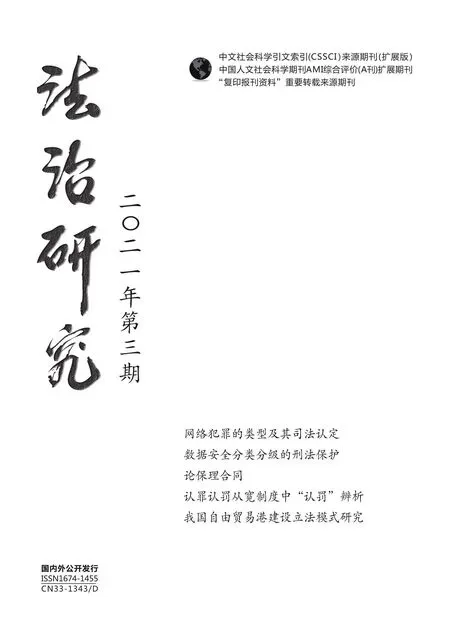我國自由貿易港建設立法模式研究*
胡加祥
一、時代的呼喚與現實的課題
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賦予自由貿易區更大改革自主權,探索建設自由貿易港。”2018 年4 月13 日,在海南經濟特區成立30 周年慶祝大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宣布:“設立海南自由貿易試驗區,支持海南逐步探索、穩步推進中國特色自由貿易港建設,分步驟、分階段建立自由貿易港政策和制度體系。”2019 年3月,李克強總理在第十三屆全國人大第二次會議上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明確:“推進海南自貿試驗區建設,探索建設中國特色自由貿易港”。2019 年11 月5 日,習近平總書記在第二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開幕式上發表的主旨演講中重申“加快推進海南自由貿易港建設”。2020 年6 月1 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了《海南自由貿易港建設總體方案》。2021 年1 月4 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向社會公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海南自由貿易港法(草案)》(以下簡稱《海南自由貿易港法(草案)》)。自此,我國建設自由貿易港已經由規劃變為現實。
探索建設自由貿易港是繼2013 年決定成立自由貿易試驗區之后黨中央作出的又一重大戰略部署,標志著我國將進一步深化改革,以更加開放的心態迎接經濟全球化和貿易投資自由化。雖然自由貿易港與迄今獲批的21 個自由貿易試驗區都是以“制度創新”為核心,以構建現代開放型營商環境為目標,但是它們有本質區別。自由貿易港建設是“立法先行”,以完善的法制對接國際最自由的貿易和投資規則;自由貿易試驗區旨在“創新先行”,在國家沒有明確規定的情況下,突破現有行政體制,創新市場準入機制,這其中有成功,也有失敗。有學者將自由貿易試驗區建設的法治理念比喻為“守法改革”,即“先實踐、后立法”①例如,上海自貿區2014 版“負面清單”的序言部分開宗明義:“以有關法律法規、國務院批準的《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總體方案》《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進一步擴大開放的措施》《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2011 年修訂)》等為依據”。;而將自由貿易港建設的法治理念比喻為“給法改革”,即“先立法、后實踐”。②參見龔柏華:《中國自由貿易試驗區到自由貿易港法治理念的轉變》,載《政法論叢》2019 年第3 期。
從自由貿易試驗區到自由貿易港,法治理念的轉變是由被動的“法律特區”試法到主動的“特區法律”立法。自由貿易試驗區的制度創新是在為自由貿易港建設投石問路、積累經驗,而自由貿易港建設則需要對自由貿易試驗區積累的經驗及時加以總結完善。
自由貿易港是建在一國(地區)境內、海關監管之外允許境外貨物、服務、資金等生產要素自由進出的港口,可以是海港,也可以是陸港。外方船只、飛機等交通運輸工具可以自由往來,但仍需遵守當地衛生、移民等政策法令。世界海關組織(WCO)1974 年生效的《關于簡化和協調海關業務制度的國際公約》(簡稱《京都公約》)對“自由區”(free zone)是這樣定義的:“締約方境內的一個區域,在那里,進口的任何貨物關稅和其它稅收享受其在關稅區以外一樣的待遇”。③參見Kyoto Convention,Chapter 2 (free zones),E1./F1。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時任國務院副總理汪洋2017 年11 月10 日在《人民日報》上撰文時也指出,“自由港是設在一國(地區)境內關外、貨物資金人員進出自由、絕大多數商品免征關稅的特定區域,是目前全球開放水平最高的特殊經濟功能區。”④汪洋:《推動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載《人民日報》2017 年11 月10 日,第4 版。這既是我國高層對自由貿易港的權威解讀,也預示著我國自由貿易港建設的發展方向。
縱觀世界各地的自由貿易港,除了像香港這樣整個區域就是自由貿易港外,更多的是在一國(地區)內劃出一塊特定區域。它們有以下四個共同特征:一是境內關外開放,在劃出的特定區域內享受優惠政策和待遇,受特別法律保護;二是經濟自由化,經濟交往不僅稅負較低,而且手續簡便;三是經濟關系國際化,與全球經濟融為一體,資金、人才、生產要素全球流動和配置;四是港區功能綜合性,在貿易、投資、金融各領域以及物流、商貿等配套服務方面都給予充分的便利。
自由貿易港是一片投資熱土,但不是法外之地。越是自由的市場,法制建設越是完善。盡管世界各地的自由貿易港在其功能上有很大的相似性,但是彼此的開放程度和管制方式卻各不相同,沒有統一的范式和樣板可以借鑒。我國建設自由貿易港要立足中國,制定出符合我們自身發展特點的一套制度規范。2014 年2 月28 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深改組第二次會議的講話中強調:“凡屬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據。在整個改革的過程中,都要高度重視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發揮法治的引領和推動作用,加強對相關立法工作的協調,確保在法治軌道上推進改革。”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對于如何處理改革與法治的關系給出了明確思路:“實現立法和改革決策相銜接,做到重大改革于法有據,立法主動適應改革和經濟社會發展需要。”
作為改革開放的重大舉措和全面融入世界經濟一體化的重要組成部分,自由貿易港建設的過程也是不斷完善我國法制建設的過程。既然“法制先行”是建設自由貿易港的前提和基礎,如何立法便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一個現實課題。是國家立法為主,還是地方立法為主?抑或選擇兩者之間的平衡?需要基于我國當下的憲政體制和立法架構去分析這三種模式的利弊得失。
二、國家單一立法模式
從自由貿易試驗區到自由貿易港,我國學界一直有一種觀點,認為應該制定“自由貿易園(港)區法”這樣一部基本法。陳俊在《我國自貿區發展中的立法保障探討》一文中談到,立法制度的培育有助于構建法治化的營商環境,規范和引導自貿區的有序發展;立法制度的保障可以規范自貿區發展面臨的各種社會關系;立法制度的支持可以推動自貿區公平競爭法治環境的形成。這些觀點無疑是正確的,但是作者似乎沒有準確把握國家設立自貿區的要旨,認為“自貿區所涉的國家事項首先應由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通過制定法律或作出相關規定,從而在法律層面提供合法性依據”。⑤參見陳俊:《我國自貿區發展中的立法保障探討》,載《甘肅政法學院學報》2016 年第2 期。作者把國家設立自由貿易試驗區作為“政策實驗室”的意圖曲解為中央政府在給地方政府布置“命題作文”。
李猛在《中國自貿區國家立法問題研究》一文中也呼吁及時出臺《中國自貿區法》作為法律代替各地自貿區《總體方案》,充分發揮國家立法引領規劃、統籌協調自貿區建設的功能和作用,為我國自貿區戰略順利推進提供最為專業有效、穩定可靠的頂層法治保障。⑥參見李猛:《中國自貿區國家立法問題研究》,載《理論月刊》2017 年第1 期。陳利強則提出,在自由貿易試驗區法制構建的“應然模式”(國家層面統一立法的基本法模式)與“實然模式”(國家授權、部委規章、地方立法三層次聯動推進模式)之間應該有一種“過渡性模式”——由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中華人民共和國自由貿易園(港)區特別授權法》作為統領我國自由貿易試驗區和自由貿易港建設的統一立法。⑦參見陳利強:《中國自由貿易試驗區法治構建論》,載《國際貿易問題》2017 年第1 期。
上述觀點背后的邏輯是自由貿易試驗區是一項國家戰略,國家在出臺這項戰略之前已經(或者說應該)有預設的目標,各自貿區在國家立法的前提下去一一實現這些目標。上述論斷與國家的發展方向不符。創立自由貿易試驗區是黨中央、國務院作出的重大決策,是新形勢下推進改革開放的重要舉措,其目的在于將自由貿易試驗區打造成為推進改革和提高開放型經濟水平的“試驗田”,形成可復制、可推廣經驗,發揮示范帶動、服務全國的引領作用。2014 年10 月27 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深改組第六次會議中強調:“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取得的經驗,是我們在這塊試驗田上試驗培育出的種子,要把這些種子在更大范圍內播種擴散,盡快開花結果,對試驗取得的可復制可推廣的經驗,能在其他地區推廣的要盡快推廣,能在全國推廣的要推廣到全國。”
自貿區的功能就像國家政策實驗室,創新有成功,也會有失敗。只有那些經過自貿區先行先試之后被證明是切實可行的,才可以在其他地方復制,國家才會把這些做法上升為法律加以固化。在這方面,2020年1 月1 日起施行的《外商投資法》便是一個鮮明例子。對外商投資企業采用“準入前國民待遇+負面清單”的管理模式是在自貿區成功實踐之后迅速在全國推廣的。在自貿區設立之初,沒有人對這一創新做法有絕對把握,更不用說一開始就把它上升到國家立法高度。我國的改革開放已經過了“摸著石子過河”階段,就像習近平總書記所說的:“容易的、皆大歡喜的改革已經完成了,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難啃的硬骨頭。”⑧《習近平接受俄羅斯電視臺專訪》,載新華網2014 年2 月9 日,www.xinhuanet.com。通過自貿區“先行先試”后出臺國家政策和法律,這將是我國今后制度構建的一條基本路徑。
我國不宜制定自由貿易試驗區國家立法的另一個原因是國家設立這么多自貿區都是經過慎重考慮的,不是簡單的數量疊加,而是有所側重。例如,除上海自貿區外,第二批的廣東自貿區總體方案強調“促進內地與港澳經濟深度合作”“成為粵港澳深度合作示范區、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重要樞紐”;天津自貿區總體方案強調“努力成為京津冀協同發展高水平對外開放平臺”;福建自貿區總體方案強調“率先推進與臺灣地區投資貿易自由化進程”。可見,每一個自貿區背后都承載著一個重大國家戰略決策。國務院2019 年8 月6 日批復的《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臨港新片區總體方案》則提出“選擇國家戰略需要、國際市場需求大、對開放度要求高但其他地區尚不具備實施條件的重點領域……打造更具國際市場影響力和競爭力的特殊經濟功能區”。
不僅如此,差異化發展的特征還將會隨著自由貿易試驗區數量的增加變得更加明顯。目前批準設立的21 個自由貿易試驗區分布在大半個中國,既有位于沿海、沿邊,也有位于內陸,面對的問題除了改革開放這個大方向外,更多的是帶有本地特征的發展難題。各個自貿區的改革場景共同繪就了當下中國改革的一幅整體畫卷。國家希望先在一定范圍、以一種可控的方式來一個一個化解這些難題,使得出臺的政策和制定的法律更具有針對性和可操作性。因此,國家層面的自由貿易(園)區立法根本無法詳盡如此眾多的問題,立法的滯后與現實發展之間的矛盾有時會成為推動自貿區創新的桎梏。
與自由貿易試驗區不同,自由貿易港國家立法的現實意義似乎更加明確。目前,我國自由貿易港建設還面臨著制度層面和技術層面的一些障礙。制度層面的障礙包括政府管理制度和理念尚不完全適應高度市場化的運行機制,難以避免政府過度干預市場的現象;港口運營管理部門與周邊地區管理部門、主要口岸管理機構(海關、出入境檢驗檢疫、出入境邊防檢查和海事管理等)難以適應完全市場經濟的運營;多重政府目標影響自由貿易港政策實施效果。技術層面的障礙包括現有自貿區基礎設施及其配套服務功能達不到自由貿易港要求;主要口岸管理機構的監管方式與監管水平離國際慣例還有一定差距;⑨參見黃志勇、李京文:《實施自由貿易港戰略研究》,載《宏觀經濟管理》2012 年第5 期。宏觀上雖有建設自由貿易港的總體方案,但是微觀上缺乏具體、精細和透明的操作性規章和流程。
上述問題在我國自由貿易港建設中具有現實意義,不可能靠當年自貿區成立之初通過“暫停”實施某些法律來解決,而必須針對自由貿易港制定專門的法律。作為一項全新事物,自由貿易港建設也要遵循當初建自貿區的做法,分批、分階段推進。“分批”是指從現有的自貿區中選擇條件最成熟的建自由貿易港,“分階段”是指自由貿易港建設是一個逐步推進的過程。根據總體方案,海南自由貿易港建設的目標是:2025 年之前全面封關,2035 年之前全面建成,到本世紀中葉成為國際上有影響力的自由貿易港。之所以這樣安排,原因有以下兩點:
第一,自由貿易港建設是一個不斷探索的過程,沒有現成的模式可以照搬和借鑒。許多問題都是在實踐中發現的,無法在立法時考慮得那么充分。例如,香港作為自由貿易港,除特區政府監管的行業(金融、通訊等)外,對外資不設任何限制,也沒有制定投資產業政策及相關目錄。除了對煙、酒等少量進口商品征收關稅外,其它大部分進口商品都免征關稅,市場流通環節的稅負也不高。⑩參見范宏云、孫永光:《香港建設自由貿易港的經驗》,載《特區實踐與理論》2008 年第3 期;崔文良:《香港:自由貿易區的典范——成思危副委員長赴港調研散記》,載《港口經濟》2002 年第5 期。迪拜自由貿易港更是對公司的營業收入和個人所得實行零稅率。?參見Dubai Airport Freezone 網站,https://www.dafz.ae/en/corporate/why-dafza/#incentives,2021 年1 月8 日訪問。這樣的開放程度,海南自由貿易港是無法做到的。?根據《海南自由貿易港建設總體方案》,對注冊在海南自由貿易港并實質性運營的鼓勵類產業企業,減按15%征收企業所得稅。對在海南自由貿易港設立的旅游業、現代服務業、高新技術產業企業,其2025 年前新增境外直接投資取得的所得,免征企業所得稅。對企業符合條件的資本性支出,允許在支出發生當期一次性稅前扣除或加速折舊和攤銷。對在海南自由貿易港工作的高端人才和緊缺人才,其個人所得稅實際稅負超過15%的部分,予以免征。
第二,從長遠看,我國的自由貿易港有可能不止一個。除海南之外,上海、浙江舟山都有條件建自由貿易港,其他一些自貿區也在積極準備。?參見胡加祥:《我國自由貿易港建設的法治意義》,載《東方法學》2018 年第3 期。除了開放程度相似之外,不同的自由貿易港應各具特色,發揮不同的功能。例如,海南建自由貿易港與上海建自由貿易港的側重點就有很大的差異,內地的自由貿易港與沿海的自由貿易港也在開放領域會有所不同。因此,無法“畢其功于一役”,用一部基本法去適應形式多樣的自由貿易港。這次頒布的《海南自由貿易港法(草案)》就是為海南自由貿易港“量身定做”的。今后若要建別的自由貿易港,是整合出臺一部全國統一的自由貿易港法,還是再單獨制定?這是立法部門下一步考慮的問題。
“國家單一立法模式”不可取并不意味自由貿易港建設不需要國家立法,而是指單靠這樣一部國家立法還遠遠不夠。自由貿易港建設的“前瞻性”和“穩定性”特點表明,自由貿易港建設需要“立法先行”。因此,國家立法要解決的是自由貿易港的法律地位和國家立法與地方立法之間的關系。如果將立法視為一個體系,那么《自由貿易港法》就是其中的基本法,此外還包括眾多特別法和地方立法。?參見《海南自由貿易港法(草案)》第24 條、25 條、26 條、27 條、28 條、29 條、48 條等。當其它自由貿易試驗區轉型為自由貿易港后,相應地,包括負面清單在內的市場準入制度也將與別的自貿區有所不同,從而建立起與世界上大多數自由貿易港相類似的開放市場。可見,我國自由貿易港法制建設是一項系統工程,單一的《自由貿易港法》立法模式不是最佳選擇。
三、授權立法+地方立法模式
在明確了自由貿易港建設需要國家立法這個基本定位之后,隨之而來的是這個“國家法”是“人大立法”還是“授權立法”這樣的立法形式探討。授權立法是指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專門作出決定,授權國務院根據授權決定行使立法權的活動。?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中華人民共和國立法法釋義》,法律出版社2015 年版,第31 頁。國內學界有一種觀點將授權立法分為“立法機關專門作出授權決定的授權”和“法律中的授權”兩種形式,前者是指在法律沒有規定或者現行法律有不同規定的情況下,立法機關針對某一特定事項、在特定區域和特定時間內作出的立法變通決定,后者是指“通過法律中的條款明確授予國務院制定規范性文件的權力”。?參見陳文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授權立法的現狀分析》,載《行政論壇》2018 年第2 期。對此,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編寫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立法法釋義》已經明確否定了這一觀點,理由如下:
第一,法律規定要求有關機關作出規定的,性質不盡一樣。有些本來是屬于應由法律規定的,因為制定該法律時,由法律作出統一規定的條件還不太成熟,所以授權有關機關作出相關規定。也有一些本來就不應該由法律作出規定的,而是為了保證法律的貫徹執行,要求有關機關制定相應的規定,這種情況并不是一種授權,而是一種義務性規定。所以,如何區分法律中哪些規定屬于授權,哪些不屬于授權,這比較困難。
第二,根據法律的授權制定有關規定,就是執行法律,不作為授權立法看待。這樣的解釋有利于加強對專門決定的授權的規范。?參見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中華人民共和國立法法釋義》,法律出版社2015 年版,第31 頁。
上述解釋符合《立法法》的本意。根據《立法法》規定,只有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才能成為授權主體,因為《憲法》規定,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行使國家立法權。國家立法權具有最高性、主權性、獨立性的特點,因此,它可以派生其他立法權,包括授權立法。雖然國務院及其直屬部門可以制定行政法規和規章,省、自治區、直轄市人大及其常委會可以制定和批準地方性法規,民族自治地區人民代表大會可以制定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但是機構制定法規和規章不是在行使國家立法權。國務院和省、自治區、直轄市人大及其常委會、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會、國務院各部門和有關地方政府制定法規和規章的權力是國家授予的,它們不能成為授權主體。
2013 年8 月26 日,第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四次會議決定:授權國務院在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暫停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外資企業法》《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外合作經營企業法》有關行政審批的部分規定,這是國家實施自由貿易試驗區戰略之后啟動的第一次授權立法。雖然在當時《立法法》尚未修改的情況下作出這樣的決定曾一度引發學者的熱議,?參見傅蔚岡、蔣紅珍:《上海自貿區設立與變法模式思考——以“暫停法律實施”的授權合法性為焦點》,載《東方法學》2014 年第1 期;范進學:《授權與解釋: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變法模式之分析》,載《東方法學》2014 年第2 期。但是實踐證明,全國人大這一授權決定對于自由貿易試驗區第一階段的探索是非常重要的。正是基于這一授權,我們嘗試了“準入前國民待遇+負面清單”的市場準入管理模式,進而為《外商投資法》的出臺奠定了基礎。
自由貿易港建設將沿襲自由貿易試驗區的發展思路,但改革創新的力度會更大。因此,與現有法律制度相沖突的現象將更加頻繁地出現。雖然新修訂的《立法法》第13 條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可以根據改革發展的需要,決定就行政管理等領域的特定事項授權在一定期限內在部分地方暫時調整或者暫時停止適用法律的部分規定,但是《立法法》第10 條“授權的期限不得超過五年”的規定仍需遵守。這一規定對于自由貿易試驗區也許可行,因為自由貿易試驗區的創新本身就是一個不斷探索的過程,制度更新較快,但是對于自由貿易港未必可行,因為人們對自由貿易港的法治環境會有一個穩定的預期。
自由貿易試驗區的使命是突破現有的行政體制和法律規定,創新和簡化市場準入的行政審批手續,充當的是立法的“探路者”。自貿區的改革一旦成熟,國家就會及時將這些做法上升為法律在全國推廣。如果改革不成功,就可以暫時停止甚至放棄。更為重要的是,自由貿易試驗區改革的重點的是“簡化行政審批手續”,而對于市場主體需要承擔的各種稅負則不是改革的重點,這也是為什么自貿區被稱之為“政策高地”,而非“稅收洼地”。自由貿易港不僅是“政策高地”,同時也是“稅收洼地”。自由貿易港吸引各類市場主體,靠的不僅僅是良好的營商環境,更重要的是低廉的運營成本,因為其他地區的營商環境會隨著法制的健全而逐漸改善,而優惠的稅收則需要由法律明確規定。
自由貿易港的優惠稅收靠授權立法無法實現,因為自由貿易港建設不是一項權宜之計,而是一項長期國策,需要有健全的法治環境和寬松的營商環境。自由貿易港各類優惠政策不能朝令夕改,必須通過法律加以明確。授權立法雖然能解決一些迫切的問題,但是它的時效性決定其無法為自由貿易港提供穩定的政策與法治環境,而地方立法又無權改變由國家立法規定的內容。《立法法》第8 條規定,下列部分事項只能通過制定法律作出規范:……(六)稅種的設立、稅率的確定和稅收征收管理等稅收基本制度;(七)對非國有財產的征收、征用;(八)民事基本制度;(九)基本經濟制度以及財政、海關、金融和外貿的基本制度;(十)訴訟和仲裁制度;(十一)必須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制定法律的其他事項。上述內容涉及自由貿易港建設最核心的事項,也是決定一個自由貿易港“自由”與“開放”程度的重要標志。
可見,授權立法的“臨時性”特征和地方立法的“地方性”特點無法為我國自由貿易港建設提供完整、有效的法律支撐,這也不是我國自由貿易港建設立法的理想模式。
四、全國立法、授權立法+地方立法并行模式
根據以往自由貿易港建設的經驗,發達國家往往采用“先立法、后設區”的做法;發展中國家或地區立法和設區順序雖不完全相同,但是都制定了自由貿易園(港)區的專門法律,明確規定自由貿易園(港)區的區域性質、法律地位和監管模式。?參見肖林:《自貿區“國際水準”全對標(一)——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之國際標桿研究》,載《國際金融報》2013 年9 月30 日,第8 版。通過比較“國家單一立法模式”和“授權立法+地方立法模式”,我們不難發現,上述兩種模式都不適合我國自由貿易港的法制建設。我國自由貿易港的立法模式宜采取“全國立法、授權立法+地方立法并行”的模式,充分發揮國家立法、授權立法和地方立法的各自優勢,形成國家立法有格局、授權立法有側重、地方立法有內容的特點。
全國立法是指由國家立法機關專門制定一部《自由貿易港法》,它不同于授權立法,具有相對的穩定性。作為海南自由貿易港建設的“基本法”,《海南自由貿易港法(草案)》除了明確我國建設自由貿易港的意義、宗旨、目標和需要遵循的基本原則外,重點是對《立法法》第8 條的完善和補充,因為該條款禁止地方立法的內容恰恰是自由貿易港賴以生存的地方。作為稅收洼地,自由貿易港在沒有國家法律明文規定的情況下,無權擅自降低稅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韓正在海南主持召開推進海南全面深化改革開放領導小組全體會議時指出,海南自由貿易港的法制建設要“以自由貿易港法為基礎,以地方性法規和商事糾紛解決機制為重要組成的自由貿易港法治體系”。自由貿易港要形成“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特殊稅收制度”。?參見《韓正在推進海南全面深化改革開放領導小組全體會議上強調:對標世界最高水平的開放形態、加快推進海南自由貿易港建設》,載《人民日報》2019 年11 月10 日,第1 版。這表明海南自由貿易港建設需要國家立法這一頂層設計。
《海南自由貿易港法(草案)》以國家立法的形式明確自由貿易港在“稅率的確定和稅收征收管理等稅收基本制度”(第四章)、“基本經濟制度以及財政、海關、金融和外貿的基本制度”(第一、二、三章)、“仲裁制度”(第七章)等領域實行與全國其他地區不同的制度。為此,《海南自由貿易港法(草案)》需要厘清以下三層關系:
第一,《海南自由貿易港法(草案)》與其它立法的關系。《海南自由貿易港法(草案)》只解決了自由貿易港享有比別的地方更加優惠的稅收、財政、金融和外貿制度的法理基礎問題,至于這些領域的制度在自由貿易港具體怎么落實,還需要其他相關法律加以明細。作為“境內關外”的海關特殊管理區,自由貿易港的保稅和免稅制度怎么執行,這需要《海關法》等專門法來規定。自由貿易港區域內的經濟管理需要由國家財稅、金融、外貿等相關法律來調整。作為全球商貿中心,自由貿易港應建立起與之相配套的經濟糾紛解決機制,包括適當放開臨時仲裁,吸引外國投資仲裁機構將仲裁放在自由貿易港內。21參見《海南自由貿易港法(草案)》第53 條。這些創新做法只有在修改了財稅法、海關法、合同法以及民事訴訟法、仲裁法等法律之后才能實現。當然,就《立法法》第8 條而言,修改《立法法》也能解決上述現行法律制約的問題,但是《海南自由貿易港法(草案)》的功能不限于此,它還要明確自由貿易港的法律地位、中央和地方的立法權限劃分等重要事項。
第二,《海南自由貿易港法(草案)》與行政法規和規章的關系。除了配套法律,我國自由貿易港法制建設也離不開必要的行政法規和部門規章,以適應自由貿易港的快速發展和立法的相對滯后。自由貿易港建設包括硬件和軟件兩個方面,離不開基礎設施建設和相關人員培訓。國家沒有這方面的投入,只能通過社會途徑籌集資金,滿足港區建設發展需要。中央應及時出臺鼓勵社會資金投入自由貿易港基礎設施建設和運營的政策法規。如果是政府經營自由貿易港的港區業務,建設資金可以通過發行政府債券籌集;如果是通過BOT、PPP 等形式管理自由貿易港,22BOT(Build-Operate-Transfer),即建設-經營-轉讓,是私營企業參與基礎設施建設,向社會提供公共服務的一種方式。PPP(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即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是公共基礎設施中的一種項目運作模式。則允許條件具備的非政府運營機構上市融資,23的貨物都是由香港空運貨站有限公司(HACTL)和亞洲空運公司(AAT)負責處理。這兩家公司都是私營機構,與香港機場管理局簽署經營管理合同。香港的海港物流也都外包給四家民營企業經營。這些企業通過公開招投標從政府獲得港口經營權后,在自己經營的范圍投入巨資改造基礎設施,提升物流水平。參見趙愛玲:《建設自由貿易港助力全面開放新格局》,載《中國對外貿易》2017 年第11 期;范宏云、孫永光:《香港建設自由貿易港的經驗》,載《特區實踐與理論》2008 年第3 期。政府在其中主要是行使監管職能。從這次全國人大常委會公布的草案看,立法部門已經注意這個問題,并在草案中作了相應規定,24參見《海南自由貿易港法(草案)》第25 條。現在需要的是具體的配套措施。
第三,《海南自由貿易港法(草案)》與國際法的關系。作為世貿組織一員,我國的法制建設需要與WTO 規則相一致。WTO 規則的一個基本要求是成員國的市場準入門檻不能高于其入世時所作的承諾。自由貿易港是在我國現有對外開放的基礎上進一步放寬市場準入標準、擴大開放領域。與我國在貨物貿易領域設定的關稅幅度和服務貿易領域所作的開放承諾相比,自由貿易港的貨物貿易關稅更低、服務貿易限制更少。在國內稅方面,與自由貿易港區外相比,外國投資者和貿易經營者享受的也是“超國民待遇”。因此,自由貿易港的法制建設符合WTO 的“合規性”要求。
《海南自由貿易港法(草案)》是對包括海南自由貿易港在內我國所有自由貿易港具有普遍意義的國家立法。相比之下,授權立法則兼具“國家法”和“地方性”的特點。換言之,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出的授權都是針對某一特定地區的特定事項。2020 年4 月29 日,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七次會議授權國務院在海南自由貿易試驗區暫時調整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中華人民共和國種子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海商法》有關規定,期限至2024 年12 月31 日。這一授權就是針對海南自由貿易試驗區探索建設自由貿易港作出的,具有明顯的地方特色。它們將被生效后的《海南自由貿易港法》所取代。
在國家立法和授權立法指導下,自由貿易港所在地的立法機構也需要出臺相應的地方性法規。《憲法》第3 條規定:“中央和地方的國家機構職權的劃分,遵循在中央的統一領導下,充分發揮地方的主動性、積極性的原則。”新修訂的《立法法》第73 條也規定:“地方性法規可以就下列事項作出規定:(一)為執行法律、行政法規的規定,需要根據本行政區域的實際情況作具體規定的事項;(二)屬于地方性事務需要制定地方性法規的事項。除本法第八條規定的事項外,其他事項國家尚未制定法律或者行政法規的,省、自治區、直轄市和設區的市、自治州根據本地方的具體情況和實際需要,可以先制定地方性法規。在國家制定的法律或者行政法規生效后,地方性法規同法律或者行政法規相抵觸的規定無效,制定機關應當及時予以修改或者廢止。”這些是我國地方立法的憲法和法律淵源,它不同于早期全國人大特別授予經濟特區的立法權。251981 年全國人大常委會授權廣東省、福建省人大及其常委會,根據有關的法律、法令、政策規定的原則,按照該省經濟特區的具體情況和實際需要,制定經濟特區的各項單行經濟法規,并報全國人大常委會和國務院備案。1988 年、1992 年、1994 年和1996 年全國人大先后四次分別授權海南省、深圳市、廈門市、汕頭市、珠海市人大及其常委會,根據經濟特區的具體情況和實際需要,遵循憲法的規定以及法律和行政法規的基本原則,制定法規,在各自的經濟特區實施,并報全國人大常委會、國務院或所在省的人大常委會備案。經濟特區的特別立法權雖然也得到了《立法法》的肯定,26《立法法》第74 條規定:“經濟特區所在地的省、市的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根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授權決定,制定法規,在經濟特區范圍內實施”。第90 條規定:“經濟特區法規根據授權對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作變通規定的,在本經濟特區適用經濟特區法規的規定”。第98 條第5 項規定:“根據授權制定的法規應當報授權決定規定的機關備案;經濟特區法規報送備案時,應當說明對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作出變通的情況”。但是國內學界對此一直有爭議,27參見吳鵬:《經濟特區授權立法制度應被廢除》,載《云南大學學報(法學版)》2007 年第1 期;何家華:《經濟特區立法權繼續存在的正當性論證》,載《地方立法研究》2018 年第2 期。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觀點認為,不同地方對特區立法權的運用情況差異很大,立法實踐中也存在偏離特區法規制定初衷和核心功能的現象,混淆特區法規與地方性法規的界限,增加了立法體系的復雜性,尤其在位階及適用規則方面。28參見林彥:《經濟特區立法再審視》,載《中國法律評論》2019 年第5 期。
自由貿易港不同于以往的經濟特區,它是一個國家的特殊經濟區,它的存在具有明確的法律地位,也有長期的穩定預期;自由貿易港也不同于當下的自由貿易試驗區,它是稅收洼地,它的功能不在于向其他地區輸出可復制、可推廣經驗,而是吸引全世界的貨物、資金、人才匯集于此,形成“磁場”效應。《海南自由貿易港法(草案)》只是解決了自由貿易港的法律地位問題,而自由貿易港如何發展,這是事關自由貿易港建設成功與否的關鍵。授權立法解決的是自由貿易港建設迫切需要解決的制度性問題,地方立法是完善自由貿易港法治環境的基礎保障。從法律位階講,海南省地方立法的上位法既有《海南自由貿易港法(草案)》,也包括全國人大作出的授權立法。從法律內容看,海南地方立法對應授權立法的程度高于《海南自由貿易港法(草案)》。29參見《海南自由貿易港法(草案)》第10 條、21 條、24 條。地方立法與國家立法和授權立法共同構成我國自由貿易港法制體系的有機組成部分。
五、結語
我國自由貿易港法制建設應按照“循序漸進、按需立法”的思路推進。“循序漸進”是指立法將是一個長期過程,不能指望一蹴而就、一勞永逸;“按需立法”是指在《海南自由貿易港法(草案)》的總體框架下,根據實際需要逐個修改現有法律,地方人大相應地制定地方性立法。自由貿易港應該是當今中國制度更加健全的特殊經濟區,它不僅有較低的市場準入門檻和優良的營商環境,還有規范的市場秩序,是我國全面融入經濟全球化的“橋頭堡”。法制建設對于國家發展來說是一個長期課題,對于自由貿易港建設而言則是一個迫切而又具體的任務,因為健全的法律制度是自由貿易港市場化機制有效運轉的根本保障。
我國自由貿易試驗區建設依靠的是“行政推動加地方創新”聯動模式,沒有國家層面的立法規范,而是通過政府不同部門下發文件解決實踐中的具體問題。自貿區這種“自上而下”的法制建設特點難免會形成交叉管理局面,缺乏統一的制度安排,從而導致企業經營過程中面臨“多部門監管,問題卻無人解決”的現象。30參見李凱杰:《中國自由貿易試驗區向自由貿易港轉變研究》,載《國際經濟合作》2017 年第12 期。更有甚者,各自貿區的總體方案須經國務院批準,而各地立法機構和政府又相繼制定本地區自貿區管理條例和管理辦法。這些規范性文件在實際運用中的法律位階問題也存爭議。31同前注⑥。上述問題都需要在自由貿易港的法制建設中逐步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