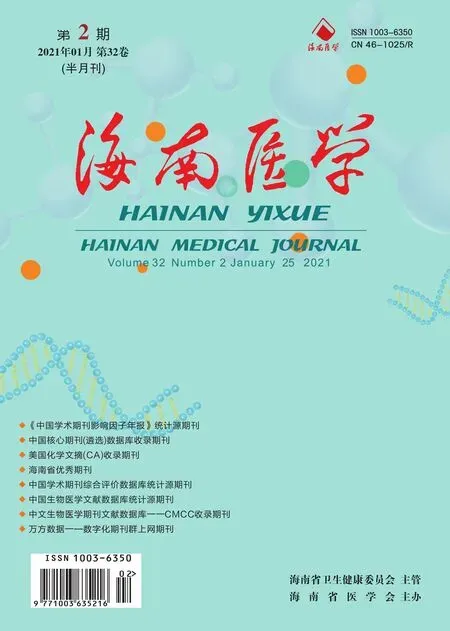間充質干細胞源性外泌體促進軸突再生和突觸重塑的研究進展
王倩 綜述 余昌胤 審校
遵義醫科大學,貴州 遵義 563000
神經突觸參與了大腦信息的處理及傳輸,是神經元細胞之間交換信息的重要紐帶。大腦中神經元突觸損害可引發認知功能障礙等一系列神經系統疾病。近年來發現MSCs外泌體由于其自身的性質和特點作用于中樞神經系統,在神經細胞軸突再生和突觸重塑中發揮重要作用。
1 外泌體的概念
外泌體初次在成熟網織紅細胞中發現,被認為是細胞向外界排放廢物的載體。后續研究鑒定出外泌體中含有mRNA、miRNA、DNA、蛋白質和信號復合物等物質,并證實外泌體可被靶細胞攝取傳遞細胞信息并產生一系列生物學活性[1]。
1.1 外泌體的起源、結構 外泌體來源于晚期胞內體,是胞外囊泡的一種類型。作為囊泡運輸的載體,外泌體的形成主要經歷3個過程:首先形成早期內涵體(early endosome),隨后以內生芽的方式形成囊泡小體(multivesicular bodies,MVBs),最后部分MVBs與細胞膜融合釋放到胞外,形成大小均一的囊泡,即外泌體[2]。電鏡下,外泌體大小30~100 nm,呈雙凹圓盤狀或杯口狀,并能在細胞間相互運輸,介導相鄰細胞或全身范圍內細胞之間的信息交換[3]。體內多數細胞及神經細胞均能分泌外泌體,且普遍存在于腦脊液、尿液、乳汁和血液等多種體液中。
1.2 外泌體的分子組成與生物功能 外泌體內富含多種類型蛋白質及脂質,如蛋白膜轉運、融合蛋白、跨膜蛋白、熱休克蛋白以及脂質蛋白等。其外層為脂質雙分子結構,富含多種脂類,可以保護其內含物不被降解,從而維持外泌體的形態。外泌體還攜帶多種RNA,通過與細胞受體結合或與質膜融合的方式作用于靶細胞并發揮其功能。STATELLO等[4]研究證實,外泌體RNA可以在受體細胞和調節基因中表達,從而發揮一定的生物效應。
1.3 外泌體可通過血腦屏障 中樞神經血管單元(neurovascular unit,NVU)由細胞外基質、周細胞、星形膠質細胞、少突膠質細胞、小膠質細胞和神經元組成,維持血腦屏障(blood-brain barrier,BBB)的功能。外泌體在NVU細胞間起著關鍵作用,以影響神經發生、神經血管生成和少突膠質細胞發生,調節NVU中的細胞通信。外泌體能夠通過BBB從中樞神經系統到外周或外周到中樞神經系統并調節細胞信號傳導[5]。研究發現,外泌體進入中樞神經系統有兩種可能機制:被內皮細胞攝取,通過細胞間的轉運最后轉移到大腦內的受體細胞;或跨越內皮細胞之間的細胞間連接,直接進入中樞神經系統。LIU等[6]證實外泌體可將腦脊液中的miR-135a通過血腦屏障傳遞至外周血,在循環血液中發揮生物學作用。在大鼠脊髓損傷模型中,研究發現BMSCs外泌體也可以影響中樞系統周細胞的NFκB通路活性,減少VEGF分泌,從而穩定血腦屏障,減輕神經功能損害,改善預后[7]。
1.4 間充質干細胞(MSC)源性外泌體 MSCs是一群具有自我更新、多向分化和免疫調節功能的成體干細胞群。由于其來源廣、再生能力強、多向分化能力及免疫抑制性,近年來廣泛應用于多種疾病。目前,人們普遍傾向于間充質干細胞通過旁分泌發揮其主要作用,可通過吞噬、胞膜融合、受體接觸等方式將內容物釋放到細胞質內。可在許多實驗中觀察到MSCs的旁分泌作用[8]。
MSCs源性外泌體是攜帶和傳遞分子到靶向細胞的理想載體,包括治療基因、藥物、酶或RNA[9]。同其他細胞類型的外泌體,MSCs源性外泌體也可運輸蛋白質和miRNA,參與細胞的信號傳導及周期調控。相比,MSCs具有更為廣泛的組織分化能力,可分化為神經膠質細胞、神經元等;其來源廣泛,可以從骨髓、脂肪組織、牙髓及妊娠組織(胎盤、羊水、臍帶膠質、臍血、絨毛膜)等獲取;因其缺乏HLA-DR的表達,其免疫原性明顯低于其他細胞類型;且MSCs源性外泌體可通過血腦屏障,參與生物活性分子的傳遞。目前研究發現間充質干細胞分泌外泌體能力最強,并且可通過Fas/Fap-1/Cav-1復合物來調控間充質干細胞外泌體的分泌,加速傷口創面愈合[10]。還可以調節多種細胞參與從而發揮其免疫作用,抑制炎癥反應,促進組織修復,以維持組織穩態和平衡。
此外,MSCs外泌體的治療效果已在多種疾病中得到證實。在神經系統疾病中,研究證明MSCs在體外特定條件誘導下或機體受損后可以分化為雪旺氏樣細胞,與其他細胞來源外泌體相比,MSCs源性外泌體更能介導受損神經元組織的修復,促進細胞間的信息傳遞和抗原呈遞、調節機體免疫應答[11-12]。在一項缺血模型研究中,骨髓來源MSCs的外泌體通過抑制促凋亡蛋白Bcl-2相關蛋白、腫瘤壞死因子(TNF)-α和白細胞介素(IL)-1β的表達,增強抗凋亡蛋白的表達,改善神經行為表現,并通過調節小膠質細胞/巨噬細胞極化而表現出神經保護作用[13]。RUPPERT等[14]還報道了MSCs源性外泌體可以減輕脊髓組織中星形膠質細胞和小膠質細胞的神經炎癥并改善功能恢復。這些結果表明,MSCs源性外泌體可以改善神經系統疾病癥狀。
2 MSCs外泌體介導軸突再生與突觸重塑
神經元不可再生,神經突起(包括軸突和樹突)再生是神經系統損傷后功能恢復的主要方式。神經元和膠質細胞之間互相作用,協調軸突和髓鞘形成。神經元和膠質細胞釋放的外泌體參與了這些過程,分泌多種神經營養因子以維持受損的神經元存活并促進軸突生長。對間充質干細胞分泌物刺激靶細胞進行研究,包括骨和軟骨再生、神經疾病、肝臟損傷、急性腎臟損傷和心血管疾病等都證實間充質干細胞所分泌的分子既可以直接激活靶細胞又能刺激臨近細胞分泌活性因子,并且在動物疾病模型中發揮神經元保護、神經元再生、神經元形成、突觸可塑性等重要作用。此外,研究證實外泌體除含有遺傳物質、多種蛋白質外,還含有對軸突生長有著關鍵性作用的肌動蛋白、微管蛋白細胞等骨架蛋白[15]。
CHIVET等[16]發現,當中樞神經系統受損時,突觸離子型谷氨酸受體亞型N-甲基-D-天冬氨酸受體被激活,神經細胞釋放的外泌體含有Synaptotagmin蛋白,作用于其他神經元后可以調節軸突生長的逆行信號,且這些囊泡體優先在突觸前部位結合,證實外泌體參與突觸功能的調節。此外,經視黃酸受體β2(RARβ)激動劑處理的神經元外泌體對神經元和星形膠質細胞失活PTEN信號具有雙重作用,導致突觸生長增強,抑制星形膠質細胞的增殖[17]。TANG等[18]研究證明外泌體可以通過PTEN-mTOR通路增強損傷神經元軸突再生。從寡糖樹狀細胞瘤中提取的攜帶髓鞘相關蛋白的外泌體,有助于髓鞘化和維持神經元的完整性[19]。因此,神經元外泌體通過神經元之間的突觸轉運及與細胞之間的聯系,介導突觸和軸突的可塑性。
2.1 MSCs外泌體與卒中后神經細胞突觸重塑 腦卒中是影響人類健康的重大疾病,外泌體在其病理生理過程中傳遞細胞物質,調節卒中后細胞信號傳導。成熟的少突膠質細胞產生的髓鞘蛋白與髓鞘的正常形態和功能密切相關。因此,腦損傷后少突膠質細胞的分化成熟以及軸突的生長對神經功能的修復起著重要作用。研究證實外泌體可以促進軸突再生以及少突膠質細胞的增殖、分化,并促進軸突的髓鞘形成,改善腦損傷后的神經功能。在大鼠模型中,富含miR-219的外泌體刺激少突膠質細胞前體分化成髓鞘細胞,并促進髓鞘在CNS中的形成[20]。研究證實腦卒中時將顯著下調腦中miR-133b,通過使用過表達miR-133b的MSCs外泌體,可以促進短暫性腦缺血模型小鼠星形膠質細胞外泌體的二次釋放,顯著增加大腦動脈閉塞小鼠大腦神經突分支數量和神經元的長度[21]。ZHANG等[22]發現來源于間充質干細胞的外泌體促進神經細胞軸突的生長,可能與miRNA-17-92有關:他們轉染miRNA-17-92至MSC后發現,外泌體中高表達的miRNA-17-92可進一步促進軸突生長。
同樣,也有研究報道miRNA-17-92可靶向作用于信號通路蛋白AKT、mTOR、GSK-3β,促進其磷酸化,激活相應的信號通路,促進軸突重建。CHEN等[23]研究結果顯示,脂肪MSCs外泌體內含有的神經因子能促進受損神經元軸突再生。這些研究表明,MSCs外泌體通過神經元之間的突觸轉移和與星形膠質細胞的通信來介導腦卒中神經細胞軸突和突觸重塑。
2.2 MSCs源性外泌體與阿爾茲海默病神經細胞突觸重塑 阿爾茨海默病(AD)是一種高致殘率和普遍流行的神經退行性疾病。其病理特征主要是β淀粉樣蛋白(amyloidβ,Aβ)形成淀粉樣斑塊和tau蛋白高度磷酸化形成神經纖維纏結。淀粉樣β肽的可溶性寡聚體(AβOs)被認為是參與早期神經元氧化應激和突觸損傷的神經毒素,最終導致AD的神經變性和記憶障礙。MARIANA等[24]實驗結果顯示,MSCs及其外泌體能夠保護神經元免受AβOs引起的氧化應激和突觸損傷,從而保護海馬區神經元和突觸,減少腦內Aβ斑塊沉積和水平。ZHAO等[25]研究表明,通過MSC傳遞外源蛋白可以調節APP/PS1轉基因AD模型小鼠小膠質細胞功能,增強海馬神經發生,改善突觸相關蛋白表達,顯著減輕學習記憶障礙。ZALDIVAR等[26]研究還評估了MSCs外泌體和MSCs在側腦室室下區促進神經發生的作用,與AD組相比,用MSCs和MSCs外泌體處理的小鼠增加了SVA唾液酸神經細胞黏附分子(PSA-NCAM)和雙皮質素/微管相關蛋白(DCX)陽性細胞的數量,其中PSA-NCAM和DCX被廣泛應用于新生未成熟神經元和神經元前體的鑒定,評價神經發生,表明MSCs和MSC外泌體都可以有效地促進阿爾茨海默病模型腦室下區的神經發生。
2.3 MSCs源性外泌體與周圍神經損傷后細胞突觸重塑 MSC源性外泌體作為細胞旁分泌產物,可能在周圍神經損傷(PNI)后的恢復中起主要作用。VERRILLI等[27]報道了不同來源的MSC外泌體,包括人月經間充質干細胞(MenSCs)和骨髓間充質干細胞(BMMSCs),都可以促進背根神經節神經元和皮層神經元的突起生長。另一項研究表明,人脂肪干細胞源性外泌體(ASC-exos)在被雪旺細胞(SCs)內化后,通過優化SCs功能,減少SCs凋亡、減輕自噬作用,體外上調相應的基因促進周圍神經軸突再生[28]。同時,ZHANG等[29]證明大鼠注射骨髓干細胞源性外泌體(BMSC-Exosome)可激活ERK1/2、STAT3 和CREB信號通路蛋白,這些信號通路蛋白參與神經損傷后的神經元生長和軸突再生。在大鼠脊髓損傷模型中,損傷區域NF200染色少于遠端區域。注射BMSC-外泌體組損傷區NF200染色減少遠低于對照組,Western blot也顯示BMSC-外泌體組NF200的表達水平明顯高于對照組,表明BMSC-外泌體促進外傷性脊髓損傷后的軸突再生[30]。此外,特異性表達的miRNA參與MSC的增殖和表型轉換、神經發生、軸突外生長和巨噬細胞遷移。例如,特異性miRNA的過表達(miR-23a,miR-200,miR-133b,miR-17-92簇)可以促進軸突基因的發生和髓鞘化[31-34]。同時最近的研究表明,MSCs源性外泌體分泌的miRNA-126也可以保護脊髓損傷大鼠神經元,從而介導神經的可塑性,改善損傷后神經的恢復[35]。MSCs源性外泌體可能通過傳遞外泌體miRNA來靶向神經源生態位中的神經細胞,從而促進突起的生長。除了傳遞遺傳成分外,MSCs外泌體還含有許多神經營養因子,在軸突再生中也起著關鍵作用。因此,MSCs外泌體中與神經修復相關的生物活性分子的存在提供了調節去神經肌肉萎縮、神經存活和軸突生長恢復的可能性。
3 外泌體治療應用的當前挑戰
由于人群的異質性和神經系統疾病機制的復雜性,只有少數藥物在臨床試驗中取得了成功,適合治療患者。外源性給藥具有嚴重副作用的風險,如惡性轉化、腫瘤產生或微血管阻塞[36]。基于MSC細胞治療的治療效果可以通過分泌可溶性因子,如外泌體等來介導。LAURA等[37]證明MSCs外泌體的治療效果與MSCs一致,并且通過增強腦修復機制和發揮免疫調節作用來治療神經疾病。MSCs外泌體的低免疫原性、低毒性、生物降解性和跨越血腦屏障的能力是作為外源性疾病治療的優點。盡管如此,一些問題必須解決,才能在臨床試驗中應用MSCs外泌體:一是開發技術,以低成本大規模獲得外泌體;二是需要標準的分離技術來獲得高純度的外泌體;三是如何通過外泌體遞送來提高靶向藥物治療的準確性。
4 展望
綜上,外泌體在神經系統疾病病理和生理過程及治療中發揮重要作用。間充質干細胞源性外泌體可以通過調節基因、蛋白質和RNA在靶細胞和組織中的表達來誘導神經細胞突觸再生和重塑發揮神經保護作用。在不同分泌外泌體的細胞類型中,MSCs外泌體較其他細胞來源外泌體介導神經細胞突觸再生功能在神經系統疾病中的應用潛力受到了廣泛關注,其大致具有以下幾個優點:免疫原性,降低了免疫細胞對受體細胞的識別及吞噬;可自由通過血腦屏障;脂質雙分子層可以運輸和保護腔內的物質免受細胞外環境的破壞;外泌體治療為無細胞治療,降低了MSC移植所引起的致瘤及栓塞的風險。但是,MSCs外泌體的研究還面臨諸多挑戰,在神經系統疾病的診斷和治療方面的研究仍任重道遠,需要進一步探尋其臨床治療的研究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