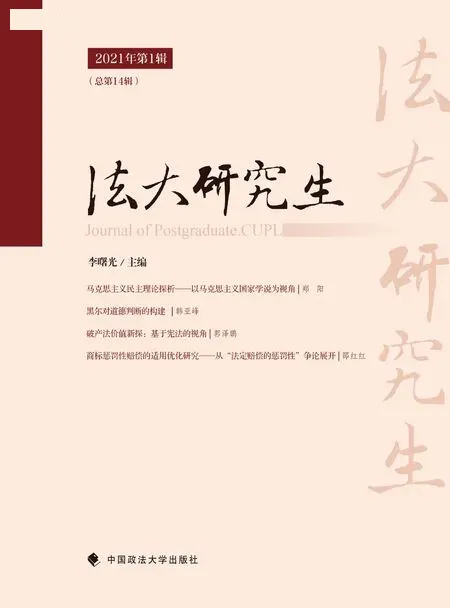關于中國法典評注寫作的若干思考
李 昊
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于2021 年1 月1 日起施行,中國正式步入了“民法典時代”,而新近發布的《法治中國建設規劃(2020—2025 年)》也提出“對某一領域有多部法律的,條件成熟時進行法典編纂”。可以說,中國很快也將進入“法典化時代”。法典可以說是立法體系化的典范,而與之相配的學理的典范則是被稱為“法教義學巔峰”的法典評注。法典評注不僅是德國法系下法教義學衍生的集成作品,在其他有著成文法典的大陸法系國家,如意大利、法國、日本等也存在著體例不一的法典評注作品,甚至以普通法為根基的美國和英國也存在著體系化的法律重述。可以說,法典評注及類似的體系化的作品是法學理論和法律實踐高度發展的產物和表征。
以德國民法典評注為例,其主要特征在于,基于現行法的體系呈現法學理論和司法實踐融合發展而形成的通說。因此,隨著立法的更改以及法學理論和司法實踐的發展,法典評注也將隨之進行頻度不等的變動。以德國最大型的Staudinger 民法典評注為例,近年來隨著《德國民法典》的頻繁修訂,也不斷加快了修訂的進度。因此,評注的內容需要及時更新,反映最新的立法、司法和學說。在某種程度上,這種更新也表明評注并不僅僅是呈現通說,還起到了在沒有成熟的理論和實踐支撐時,對新頒布或修訂的內容進行學理構建和規范指引的功能。這也是法典頒布之初法典評注需要發揮的主要功能,即總結以往理論和實踐經驗,促進通說的形成,法典評注所提出的觀點如果為高層級法院的典型案例所采納,即可能成為之后的通說。中國民法典評注目前階段所要發揮的功能即在于此。在通說形成前,則應避免采用通說這種表達,而應對各種代表性的學說觀點進行總結,并以觀點持有者的學術地位和支持者的數量進行大體的分類,不妨采用多數說、少數說、有力說、新近觀點等表達;對于新設制度,還需要提出適用的方向,凝練共識,而這也為撰寫者個人思想發揮提供了較大的空間,尤其是單篇評注作品,但對于集合性的整體的法典評注,撰寫者的個性則需要與整個法典評注的理論基調相協調,在一定程度上需要收斂。
與法典原創國家不同,中國作為典型的法律多元繼受的國家,在法典評注中還需要注重發掘法律條文和制度的來源,嘗試探究法律繼受的路徑,為體系化的梳理提供歷史的視角。當然,我們無需像德國的HKK (德國民法典歷史評注) 那樣都追溯到古羅馬法。雖然新中國的立法資料大多隱而不彰,但立法機關的法律釋義、參與立法者的著述中仍可以爬梳出法律繼受的蛛絲馬跡,并為法典條文的體系化解釋和司法適用提供方向,但法典評注并不一定要受到繼受來源的拘束,在一定意義上,甚至需要反思糾偏,避免多元繼受所帶來的解釋適用上的體系矛盾。
在中國,法典評注所面臨的主要障礙并不僅僅是繼受來源的不確定和不明晰,更為棘手的是對既往司法實踐的梳理,也即對海量的司法案例的分類歸納整理。目前雖然已經有諸多案例數據庫提供了大量的司法案例數據,但中國的案例公開在一定時期內缺乏制度保障,判決的寫作缺乏整體框架,尤其是缺乏學理的展開;相應地,案例研究起步晚,缺乏體系化的梳理,沒有對大量的同類司法案例進行總結歸納,因此也直接影響了評注寫作的精度,加大了評注寫作的難度。這也和中國法教義學和法學方法論不夠發達有著內在的關聯。在這一背景下,中國的法典評注在一定程度上也承擔了以法典條文為綱,總結司法實踐中出現的類案的功能。目前,考慮到海量數據尚缺乏有效的同案擇選技術,根據案例的來源進行分類梳理可以適當減輕評注的工作難度,其中指導案例、《最高人民法院公報》、《民事審判指導與參考》、《人民法院案例選》、《審判案例要覽》、各地方高級法院公布的典型案例等可以作為重點的案例選擇來源,而對于尚缺乏高層級案例引用的法條,則可以摘選具有典型示范意義的低層級法院公開的案例。
現階段,中國的法典化程度低,尤其在民法典中存在著部分的宣示性法條、重復規定法條,有學者甚至將之稱為僵尸法條,而且部分法條的結構不完全、參引技術不規范、條文之間存在矛盾,也沒有充分考慮證明責任的分配,使得法典評注的寫作需要對法條的體系功能加以闡述,區分請求和抗辯規范以及相應的輔助性規范并指明證明責任的分配。對于具有重要適用意義的法條,評注可以分為條文宗旨、條文性質(請求規范還是抗辯規范或者輔助性規范)、條文的比較法和歷史考察、條文的體系關聯、條文結構(構成要件和法律效果)、證明責任等幾個主要部分,并需要充分運用法教義學和法學方法論對條文進行體系化和解剖式的闡明。而對于用益不大的法條則可以簡略評注,甚至多條聯合評注。
法典評注除了可以對學理發展加以總結,為司法實踐提供指引,呈現或逐步形成通說外,也有重要的教學意義。對于高校的法學教育而言,重要的即是教授學習活法(living law),并引導學生形成體系思維,而法典評注的功能和特點恰恰使其適合作為主要的教學資料。對于國內目前風頭正盛的鑒定式案例研習而言,評注所凝練或提出的觀點也是案例寫作中重要的引證來源,并可以逐步推動案例分析結論的穩定化。當然,更為妥適的做法是為學生專門編寫小型的適于學習的評注。鑒定式案例寫作形成的體系化思維也有助于對司法案例的深入研究,形成較為穩定的研究路徑和結構。在法科生將來進入實務領域后,這又可以進一步推動司法判決寫作的規范化,注重和學理觀點的互動,推進通說的形成,為評注提供滋養。可以說,鑒定式案例研習、判例研究、司法裁判和學理研究是相輔相成、互為促進的一套完整的機制,法典評注則是可以將數者勾連起來的良器,最終促進法律人共同體的形成。
對于中國的法典評注來說,這個時代提供了機遇,提供了對法學理論和司法審判進行整合和反思的機會,但同時也存在著重大的挑戰,目前,無論是法教義學的研究、法學方法論的運用還是司法審判的技術都尚不足以支撐理想的法典評注的實現。我們所做的就是以同情的和學習的眼光,逐步探究中國法典評注應有的姿態和路徑,或許在不遠的一天能夠形成自己的風格和豐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