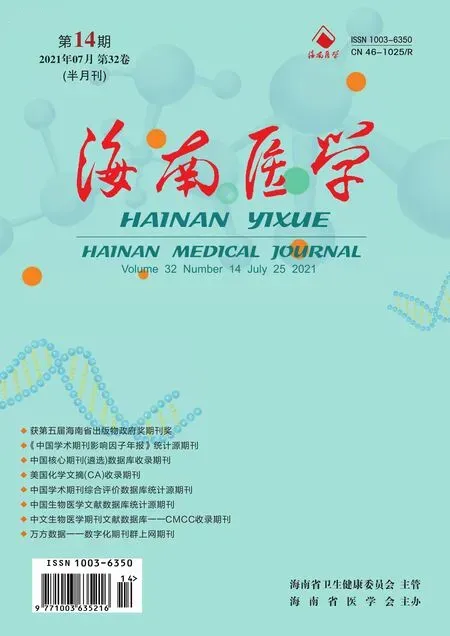血腦屏障與進展性缺血性卒中相關性的研究進展
張燁平 綜述 秦濤,劉安祥,張駿審校
1.遵義醫科大學第三附屬醫院老年病科,貴州 遵義 563000;2.遵義醫科大學附屬醫院神經內科,貴州 遵義 563000
目前進展性缺血性卒中(progressive ischemic stroke,PIS)在國內外均暫無統一定義及診斷標準,其通常是指發生卒中后經過積極臨床治療后,癥狀在7 d內仍進行性加重的缺血性卒中(ischemic stroke,IS),其危險因素多、發病機制復雜、致殘率及致死率高。但目前關于PIS的機制上尚不清楚,近年來的研究顯示IS發生后會破壞血腦屏障(blood-brain barrier,BBB)結構及功能,而BBB損害將進一步使IS病情惡化,繼而發展為PIS。因此,進一步了解BBB與PIS的相關性,對改善患者預后非常重要。本文將對BBB與PIS相關機制的研究現狀進行綜述,為PIS的研究提供一定的理論基礎。
1 BBB
BBB是中樞神經系統和血液之間的生理及功能的屏障,為腦組織提供必需的營養物質,并有效地控制廢物從大腦中排出[1]。它表達多種離子轉運蛋白和通道,調節中樞神經系統離子濃度,控制腦組織中水和電解質平衡,從而在腦實質中產生細胞外環境,為神經元和神經膠質功能提供最佳的介質[2]。腦微血管內皮細胞(brain microvascular endothelial cell,BMECs)、星形膠質細胞、周細胞等是BBB的重要組成細胞[3],它們在保護BBB完整性以及維持BBB正常生理功能中發揮著重要作用。BBB的破壞是IS的病理特征之一[4]。當IS發生后,上述BBB的重要組成細胞會被激活,并通過分泌炎性因子從而引發炎癥損傷等機制,直接或間接地破壞BBB的完整性[2],從而導致BBB功能障礙,并發展成血管源性水腫,以及IS損傷的進一步加重[5]。
2 PIS
PIS尚無明確的定義及診斷標準,一般是指卒中發病后經臨床積極治療,病情仍呈進行性加重,表現為原有神經功能缺損的加重或出現同一血管供血區受損的新癥狀與發病7 d內繼續惡化的IS[6]。PIS的診斷標準主要采用2004年歐洲進展性卒中工作組(European Progressing Stroke Study Group,EPSS)提出的斯堪地那維亞評分(Scandinavian Stroke Scale,SSS),即意識水平、上下肢活動、眼球運動中任意一項評分≥2分或語言評分≥3分,在此診斷標準下若神經功能惡化發生在發病3 d內的患者被定義為早發進展性卒中,發病在3~7 d者則為晚發進展性卒中[7]。PIS的發病率占卒中患者的12%~42%,國內PIS的發病率約為30%,國外為9.8%~43%[8]。PIS的發病機制未明確,可能與多病因及多病理改變共同作用有關:(1)血流動力機制,包括:血栓進展、腦灌注壓降低、側支循環建立障礙、血液流變學異常[9];(2)腦部機制:局部有毒物質堆積(興奮性氨基酸毒性作用、氧自由基生成過多和清除能力下降、酸中毒、炎癥損傷和微循環障礙等)、腦組織水腫、再灌注損傷、遲發性腦損傷等[10];(3)其他系統機制:如患者的心肺功能、感染情況、血壓變化及水電解質紊亂等影響患者腦組織代謝,進一步加重神經功能損傷。而BBB的破壞也會導致上述幾種病理改變,故BBB的破壞可能促進了PIS的發生。
3 BBB損傷與PIS
當IS發生后,BBB結構和功能受到破壞。而在這一過程中,BBB主要組成結構(BMECs、周細胞和星形膠質細胞等)也參與了BBB相關損傷機制及病理改變,并可能直接或間接參與了血流動力機制、腦部機制或其他系統機制,從而導致IS進一步惡化,發展為PIS。
3.1 周細胞 周細胞由中胚層的神經周圍血管叢和外胚層的神經脊細胞而來,進一步發育成中樞和外周的血管網絡。周細胞于體內幾乎所有的微血管上,然而它們在中樞神經系統和視網膜中的密度最高,這與它在微循環血流的精細調節和BBB的維持中的作用有關[11]。在大腦中,周細胞、BMECs、星形膠質細胞以及神經元構成了神經血管單元[12]。神經血管單元內的周細胞能夠調節許多神經血管功能,這些功能包括BBB結構的發展和維持,血管穩定性和血管生成,以及毛細血管水平的血流調節[13]。周細胞通過與神經血管單元的內皮細胞和其他細胞的直接接觸或通過自分泌和旁分泌信號通路發揮其生理功能[14]。周細胞既表達肌動蛋白、原肌球蛋白、結蛋白等收縮蛋白,也表達兒茶酚胺、內皮素-1、血管加壓素和血管緊張素Ⅱ等血管活性分子的受體,從而具有調節血管直徑和血流的潛力[15]。在IS發生初期,周細胞可以變得非常活躍。它們在大腦中動脈阻塞后的短暫腦缺血后收縮毛細血管。相關研究發現,過氧亞硝酸鹽的形成可能是IS時周細胞收縮毛細血管的基礎,從而導致大腦能量供應的減少和神經損傷的加劇[16]。同時在發生IS損傷后,周細胞強烈遷移到壞死組織周圍的梗死區域[17-18]。之后出現收縮僵硬,導致毛細血管節段性變窄、血細胞滯留以及周細胞死亡[17-18]。而周細胞死亡及BBB破壞會導致持續性收縮[16,18]造成毛細血管血流量的長期減少,這兩者都會導致IS后持續的神經元損傷。因此,在短暫的局灶性缺血初期,周細胞的收縮可能是減少腦血流和增加神經元損傷的重要因素。周細胞覆蓋是血管通透性的一個決定性因素,每個內皮細胞的周細胞數和被周細胞覆蓋的血管壁表面積決定了毛細血管的相對通透性[19-20]。周細胞通過調節緊密連接蛋白的表達,抑制跨內皮細胞運輸和免疫細胞外滲進入中樞神經系統,從而維持BBB低血管通透性[21-22]。當IS發生后,周細胞功能障礙和缺陷會導致BBB通透性增加[23],引起缺血區腦水腫和微循環的損害。并且在梗死周圍區域,周細胞在缺血后從微血管遷移。這種遷移可能通過為梗死周圍血管生成提供指導起到保護作用,但也可能是有害的,因為它可能通過破壞周細胞和緊密連接的相互作用而增加微血管的通透性[24]。周細胞覆蓋的缺失導致血管不穩定,引起BBB通透性增加,進一步可發展成腦水腫,加重IS損傷。
3.2 星形膠質細胞 星形膠質細胞占大腦膠質細胞總數的20%~40%,是具有腦區特異性的高度異質性細胞群[25]。星形膠質細胞通過廣泛的縫隙連接耦合,形成星形細胞合胞體,起支持和分隔神經細胞的作用,并參與BBB的形成[26]。正常生理情況下星形細胞功能包括:突觸的形成或消除[27]、突觸可塑性[28]、神經營養因子釋放、吸收和循環神經遞質、維持BBB、調控腦血流量[29]、清除和維持離子和細胞外神經遞質[30]、葡萄糖代謝和底物傳遞給神經元等功能[31]。星形膠質細胞在神經發病機制和病理條件中也有重要作用,因為它們參與先天和適應性免疫反應,是大腦先天免疫系統的主要組成部分[32]。IS發生后,損傷部位的神經元和膠質細胞立即通過釋放損傷相關分子模式分子(DAMPs)等產物激活星形膠質細胞[32]。星形膠質細胞的形態和功能特征在病理條件下發生改變,這一過程被稱為“反應性星形膠質細胞病”,包括它們的增殖、中間絲蛋白、細胞因子和趨化因子的表達以及免疫反應的調節[33]。反應性星形膠質細胞分泌炎癥因子,如血管內皮生長因子(VEGF-A)、基質金屬蛋白酶(MMPs)、趨化因子和細胞因子,這些因素直接或間接加重BBB的破壞,并從外周血中吸收白細胞,這會導致繼發性腦組織損傷[34]。在IS過程中,MMP-2和MMP-9水平升高,主要與BBB完整性的破壞有關[35]。雖然小膠質細胞和中性粒細胞是MMPs的主要來源,但也有報道稱星形膠質細胞在病理條件下表達MMPs[36]。此外,星形膠質細胞是趨化因子單核細胞趨化蛋白-1(MCP-1)和趨化因子C-X-C motif配體1(CXCL-1)的來源[37]。MCP-1不僅影響星形膠質細胞分泌細胞因子(IL-1β、IL-6和TNF-α),在缺血后小膠質細胞活化中也扮演關鍵的角色[38]。另一方面,作為一種中性粒細胞趨化劑,CXCL-1水平的降低會影響腦缺血后中性粒細胞的募集[39]。因此,星形膠質細胞參與IS后炎癥環境的復雜形成和BBB破壞的機制,并推動IS進一步發展。星形膠質細胞可釋放谷氨酸,并主動調節神經元的興奮性、突觸傳遞和可塑性[40]。而在IS后,星形膠質細胞的損傷會導致BBB完整性的破壞,從而影響腦組織的能量供應,導致神經元和星形膠質細胞離子梯度和膜電位去極化的丟失[41-42]。這誘導谷氨酸和其他神經遞質從突觸前末端釋放到細胞外空間。能量消耗進一步導致星狀細胞和神經元谷氨酸轉運蛋白的功能障礙,不能清除釋放到突觸間隙的谷氨酸,使大量谷氨酸聚集在突觸間隙,過度刺激谷氨酸受體(尤其是NMDARs)導致Ca2+的內流和胞內超載[42],繼而激活下游磷脂酶和蛋白酶,降解細胞膜和蛋白質,最終導致急性神經元死亡[43]。此外,大量谷氨酸也會引發分子事件,導致神經元的延遲死亡和腦損傷[44]。
3.3 BMECs BMECs是一薄層介于循環血液和血管壁平滑肌中間的細胞,依賴化學、物理和機械刺激而發生相應改變[45]。BMECs保證BBB的緊密性,并具有許多區別于其他血管內皮細胞的獨特元素,如BMECs胞飲極少,甚至沒有;胞內線粒體含量豐富;細胞膜表面的窗孔結構較少;存在緊密連接[46]。BMECs中豐富的線粒體可以產生生物能量,驅動溶質進出大腦[2]。缺乏開孔的BMECs可非特異性地阻止血源性親水分子和細胞通過血管壁進入神經組織[45]。BMECs之間的緊密連接是BBB的主要結構和功能成分,在細胞外空間的封閉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47]。在生理條件下,BMECs維持BBB結構和功能的完整性,但隨IS進展而改變。受損的BMECs會引發一系列腦血管損傷,進而加重BMECs損傷[48]。在IS的發展過程中,BMECs通過制造促炎狀態參與BBB的破壞,諸如CCL5和MCP-1等炎性細胞因子從腦微血管中釋放出來[49]。這些細胞因子通過血液循環到達免疫系統的各個器官,在那里它們開始激活免疫細胞,并觸發中性粒細胞的釋放[50]。活化的中性粒細胞遷移到損傷部位,在24 h內達到峰值[51],使局部微血管環境惡化,導致其他細胞因子的產生,最終從周圍招募單核細胞、巨噬細胞和細胞毒性T細胞[52]。此外,BMECs的病理改變會激活中樞神經系統中的小膠質細胞,導致周細胞脫離,進一步破壞BBB[20,53]。在卒中后最初的幾個小時和幾天,所有這些炎癥過程都集中在腦內皮細胞上,這些細胞已經被缺氧和再灌注損傷,開始減弱和死亡,促進了免疫細胞浸潤和中樞神經系統的膠質激活,推動IS的進展,加重缺血損傷[54]。BMECs緊密連接是調節細胞旁通透性主要的介質,限制了溶質、離子和水的脫細胞運動[45]。在缺血再灌注情況下,通過增加14C-蔗糖的腦積累可看出,緊密連接的中斷會破壞BBB的完整性[55]。此外,再灌注會增加BBB對海馬和皮層微血管中右旋糖酐(分子量在4~10 kDa之間)的泄漏,表明細胞旁對大小溶質的通透性增強[55]。腦組織中14C-蔗糖和葡聚糖積累的變化與Occludin、Claudin-5、ZO-1等組成的緊密連接蛋白的修飾和表達有關[56]。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缺血再灌注破壞了二硫鍵合的Occludin寡聚物組裝,從而阻止單體Occludin形成對細胞旁擴散的物理屏障[2]。這些緊密連接組織和BBB溶質泄漏的變化也與再灌注后腦含水量的顯著增加有關。進一步證明,在腦缺血的環境下,BBB的破壞會導致血管源性水腫,導致IS損害加重,進一步發展為PIS。
4 結語
卒中是世界致死及致殘的主要疾病之一,其中PIS作為難治性腦血管疾病,較一般卒中有著更高的致殘率及死亡率,需引起警惕。本文通過BBB的完整性因IS受到破壞后,其主要組成細胞(周細胞、星形膠質細胞、BMECs)的生理功能變化和病理變化,來闡述BBB與PIS發生的相關性。由此為PIS的預防、發生機制、診療及預后提供新的思路,也讓PIS的相關研究應受到更多重視。防止IS發展對改善患者神經功能恢復、PIS的預防以及減少PIS引起的病殘甚至死亡都具有重要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