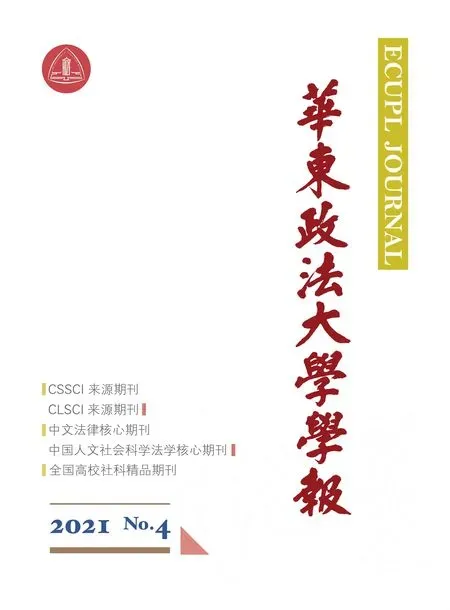我國企業(yè)合規(guī)研究的階段性梳理與反思
李本燦
一、問題的提出
作為新興的學(xué)術(shù)概念,“合規(guī)”之“規(guī)”的范圍不限于國內(nèi)法與商業(yè)倫理規(guī)則,還可能涵蓋公司業(yè)務(wù)所能觸及的其他國家或國際性組織的法律或規(guī)則。某種意義上講,規(guī)則的疏密與企業(yè)可能面臨的制裁風(fēng)險成正比。“必須遵守的規(guī)定越多,員工被監(jiān)督的行為構(gòu)成犯罪的危險就越高。”〔1〕[德]丹尼斯?伯克:《論作為降低涉企犯罪損害預(yù)期值措施的刑法上要求的企業(yè)監(jiān)督——界定合規(guī)責(zé)任的基本問題》,黃禮登譯,載李本燦等編譯:《合規(guī)與刑法:全球視野的考察》,中國政法大學(xué)出版社2018 年版,第300 頁。經(jīng)濟的全球化意味著企業(yè)所需遵守規(guī)則的全球化,這無疑加劇了企業(yè)面臨的制裁風(fēng)險。〔2〕參見[德]洛塔爾?庫倫:《德國的合規(guī)與刑法》,馬寅翔譯,載趙秉志主編:《走向科學(xué)的刑事法學(xué)——刑科院建院10 周年國際合作伙伴祝賀文集》,法律出版社2015 年版,第430 頁。為了應(yīng)對全球化的合規(guī)風(fēng)險,世界主要經(jīng)濟體紛紛效仿美國,通過立法方式促進企業(yè)合規(guī)。最典型的是2018 年5 月25日生效的《歐洲通用數(shù)據(jù)保護條例》(GDPR),其對于企業(yè)數(shù)據(jù)合規(guī)的全球化具有不可估量的意義。2018 年年底,國務(wù)院國有資產(chǎn)監(jiān)督管理委員會發(fā)布了《中央企業(yè)合規(guī)管理指引》,商務(wù)部等六部委發(fā)布了《企業(yè)境外經(jīng)營合規(guī)管理指引》,以此應(yīng)對逐步凸顯的企業(yè)合規(guī)風(fēng)險。
作為源自域外的新興學(xué)術(shù)現(xiàn)象,國內(nèi)學(xué)術(shù)界早在十年前就零星地關(guān)注到了企業(yè)(刑事)合規(guī)問題,中興通訊事件、華為事件則進一步激發(fā)了學(xué)界的研究興趣。從2018 年開始,已經(jīng)有數(shù)十篇相關(guān)論著發(fā)表。應(yīng)當(dāng)說,在企業(yè)合規(guī)問題上,學(xué)術(shù)研究已經(jīng)邁出了堅實的一步。然而,現(xiàn)有的研究也出現(xiàn)了諸多問題。第一,研究的碎片化與視角分離。例如,國家視角與企業(yè)視角的研究缺乏學(xué)術(shù)溝通,甚至互相攻擊;實體法與程序法的研究也并未合理對接,或者有加以混淆的嫌疑,或者以為以認(rèn)罪認(rèn)罰從寬處理機制為切入口的程序機制可以獨當(dāng)一面,甚至排斥實體法上的合規(guī)機制。第二,研究方法單一。最突出的問題是,學(xué)界對合規(guī)的教義學(xué)研究方法關(guān)注不夠,甚至有學(xué)者極力阻止合規(guī)問題的教義學(xué)化。第三,現(xiàn)有的學(xué)術(shù)觀點中,尚有值得商榷之處。例如,刑事合規(guī)制度以替代責(zé)任為前提,從而否定中國引入該制度的正當(dāng)性?刑事合規(guī)制度以嚴(yán)格責(zé)任為前提,為了引入該制度,應(yīng)當(dāng)將嚴(yán)格責(zé)任原則引入我國刑法?企業(yè)刑事合規(guī)的研究是否以單位犯罪立法化為前提?為了推動企業(yè)合規(guī),是否需要通過立法強化單位處罰?單一刑罰威懾框架下合規(guī)計劃是否必然無效?如此等等,還有很多問題有待澄清。
二、學(xué)術(shù)研究現(xiàn)狀的梳理
(一)學(xué)科與視角的分化
1. 學(xué)科的分化
“合規(guī)”概念起源于醫(yī)學(xué)領(lǐng)域〔3〕例如,Weber 等德國學(xué)者1977 年即以“Patienten-Compliance”(患者合規(guī))為題以專著形式系統(tǒng)討論了醫(yī)療領(lǐng)域的合規(guī)問題。,表達的是遵循醫(yī)囑之意。現(xiàn)如今,合規(guī)概念已經(jīng)擴展到企業(yè)經(jīng)濟學(xué)、法學(xué)等領(lǐng)域。作為一種公司治理形式,合規(guī)問題自然是企業(yè)經(jīng)濟學(xué)的研究范疇。在法學(xué)領(lǐng)域內(nèi),它首先是公司法的研究內(nèi)容,旨在探索公司自律機制。例如,我國學(xué)者對于證券服務(wù)機構(gòu)自律機制的研究,〔4〕參見侯東德:《證券服務(wù)機構(gòu)自律治理機制研究》,載《法商研究》 2020 年第1 期,第129-142 頁。實際上,在更久遠(yuǎn)的1981 年,國內(nèi)已經(jīng)開始了對公司內(nèi)部控制理論的研究(通過CNKI 檢索獲得信息)。以及對于合規(guī)制度的公司法實現(xiàn)路徑的研究。〔5〕參見趙萬一:《合規(guī)制度的公司法設(shè)計及其實現(xiàn)路徑》,載《中國法學(xué)》2020 年第2 期,第69-88 頁。公司治理機制的轉(zhuǎn)變,一定程度上依賴于作為更大命題的規(guī)制理念的調(diào)整。例如,我國學(xué)者對于社會自我規(guī)制理論的研究〔6〕參見高秦偉:《社會自我規(guī)制與行政法的任務(wù)》,載《中國法學(xué)》2015 年第5 期,第73-98 頁;高全喜:《協(xié)商民主、數(shù)字網(wǎng)絡(luò)社會與合作治理》,載《上海政法學(xué)院學(xué)報(法治論叢)》2019 年第1 期,第113-119 頁。,以及個別領(lǐng)域內(nèi)自我規(guī)制實踐的研究。〔7〕參見王旭:《中國新〈食品安全法〉中的自我規(guī)制》,載《中共浙江省委黨校學(xué)報》2016 年第1 期,第115-121 頁;周佑勇:《契約行政理念下的企業(yè)合規(guī)協(xié)議制度建構(gòu)——以工程建設(shè)領(lǐng)域為視角》,載《法學(xué)論壇》2021 年第3 期,第49-61 頁。這些都屬于行政法的研究范疇。
隨著企業(yè)犯罪增多,合規(guī)漸漸與刑法發(fā)生關(guān)聯(lián),公私共治成為犯罪治理的替代性措施。這就意味著,在廣義的刑事法領(lǐng)域內(nèi),合規(guī)首先是犯罪學(xué)的研究范疇。例如,國內(nèi)學(xué)者對于民營企業(yè)(家)犯罪的情境預(yù)防的研究。〔8〕參見張遠(yuǎn)煌、邵超:《民營企業(yè)家犯罪及其情境預(yù)防》,載《江西社會科學(xué)》2016 年第4 期,第164-169 頁;國外學(xué)者對于合規(guī)治理與傳統(tǒng)社會控制方式的對比研究是更為典型的犯罪學(xué)研究范式。See Sally S. Simpson, Corporate Crime, Law, and Social Control,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作為一種新的犯罪治理理念,合規(guī)治理進入刑事法的前提是系列立法和司法政策的調(diào)整。《美國聯(lián)邦量刑指南》通過兩極化刑事政策的設(shè)定推動企業(yè)合規(guī)的立法實踐說明了這一點。〔9〕具體可參見我國學(xué)者對美國量刑改革背景和進程的詳細(xì)介紹,參見崔仕繡:《美國量刑改革的源起、發(fā)展及對我國的啟示借鑒》,載《上海政法學(xué)院學(xué)報(法治論叢)》2020 年第1 期,第11-20 頁。我國學(xué)者以合規(guī)理念為指導(dǎo),圍繞企業(yè)犯罪治理政策的研究即屬于刑事政策學(xué)的范疇。〔10〕參見李本燦:《企業(yè)犯罪預(yù)防中合規(guī)計劃制度的借鑒》,載《中國法學(xué)》2015 年第5 期,第177-205 頁。作為新的犯罪治理制度,合規(guī)制度的有效性離不開對刑事實體法的準(zhǔn)確理解。例如,缺乏對實體刑法的準(zhǔn)確把握,風(fēng)險識別就難免疏漏,這對于企業(yè)是毀滅性的。現(xiàn)代企業(yè)對于犯罪行為的敏感性決定,“合規(guī)”之“規(guī)”的核心即是刑事實體法規(guī)范。從這個意義上講,刑事合規(guī)是企業(yè)合規(guī)制度的核心。孫國祥〔11〕參見孫國祥:《刑事合規(guī)的理念、機能和中國的構(gòu)建》,載《中國刑事法雜志》2019 年第2 期,第3-24 頁。、黎宏〔12〕參見黎宏:《合規(guī)計劃與企業(yè)刑事責(zé)任》,載《法學(xué)雜志》2019 年第9 期,第9-19 頁。、時延安〔13〕參見時延安:《合規(guī)計劃實施與單位的刑事歸責(zé)》,載《法學(xué)雜志》2019 年第9 期,第20-33 頁。的研究即歸屬于刑事實體法范疇。
作為刑事合規(guī)制度的集大成之地,美國的對抗制訴訟文化及其嚴(yán)苛的公司歸責(zé)模式所導(dǎo)致的激勵不足共同引導(dǎo)出通過起訴激勵方式推動公司合規(guī)的刑事合規(guī)類型。由此,合規(guī)成為刑事訴訟法的研究范疇。我國學(xué)者以認(rèn)罪認(rèn)罰為切入點〔14〕參見李本燦:《認(rèn)罪認(rèn)罰從寬處理機制的完善:企業(yè)犯罪視角的展開》,載《法學(xué)評論》2018 年第3 期,第111-121 頁。,或者從比較法〔15〕參見陳瑞華:《企業(yè)合規(guī)視野下的暫緩起訴協(xié)議制度》,載《比較法研究》2020 年第1 期,第1-18 頁。的角度對企業(yè)合規(guī)的訴訟法機制進行的研究,就歸屬于刑事訴訟法范疇。企業(yè)合規(guī)問題是多學(xué)科的交叉問題,呈現(xiàn)顯著的學(xué)科分化形態(tài)。但總體上,刑事法角度的研究是主流,也是合規(guī)的核心。
2. 視角的分化
某種意義上講,學(xué)科的分化意味著視角的分化。然而,不同學(xué)科也可能屬于同一個視角。刑事實體法學(xué)科視角下的刑事合規(guī)制度,主要討論如何用刑法手段推動組織體自我管理。〔16〕Vgl. Thomas Rotsch, ZStW 2013, S. 494.刑事訴訟法學(xué)科視角下的刑事合規(guī)制度,主要討論如何建構(gòu)旨在推動組織體自我管理的外部程序性激勵機制。〔17〕參見李玉華:《我國企業(yè)合規(guī)的刑事訴訟激勵》,載《比較法研究》2020 年第1 期,第21-29 頁。不管是程序性激勵機制,還是實體性激勵機制,對于企業(yè)合規(guī)而言,都是一種外部視角,更確切地說,都是站在國家視角探索如何推動企業(yè)合規(guī)的問題。從這個角度說,兩種不同的學(xué)科視角均歸屬于國家視角。刑事政策學(xué)、犯罪學(xué)、行政法學(xué)的研究也都可以歸屬于國家視角。與此相對的是從企業(yè)視角展開的討論,即探索如何建構(gòu)有效的合規(guī)計劃制度,以避免可能面臨的合規(guī)風(fēng)險。這就意味著,企業(yè)合規(guī)呈現(xiàn)出國家視角與企業(yè)視角的分化。國家視角的合規(guī)是指,保證企業(yè)守法的、促進法益保護的法制度工具。〔18〕Vgl. Dennis Bock, Criminal Compliance, Nomos, 2011, S. 21.與此相對,企業(yè)視角的合規(guī)是指,企業(yè)為了保證所有職員行為合法的整體性組織措施。〔19〕Vgl. Thorsten Alexander, Die strafrechtliche Verantwortlichkeit für die Wahrung der Verkehrssicherungspflichten in Unternehmen, Centaurus Verlag, 2005, S. 316.
回顧我國現(xiàn)有的企業(yè)合規(guī)研究不難發(fā)現(xiàn),研究視角也大致遵循了國家與企業(yè)視角的二元區(qū)分。孫國祥對于企業(yè)合規(guī)與刑罰論(積極一般預(yù)防理論)、單位刑事責(zé)任論關(guān)系的研究,〔20〕參見孫國祥:《刑事合規(guī)的理念、機能和中國的構(gòu)建》,載《中國刑事法雜志》2019 年第2 期,第3-24 頁。陳瑞華〔21〕參見陳瑞華:《合規(guī)視野下的企業(yè)刑事責(zé)任問題》,載《環(huán)球法律評論》2020 年第1 期,第23-40 頁。、黎宏〔22〕參見黎宏:《合規(guī)計劃與企業(yè)刑事責(zé)任》,載《法學(xué)雜志》2019 年第9 期,第9-19 頁。、時延安〔23〕參見時延安:《合規(guī)計劃實施與單位的刑事歸責(zé)》,載《法學(xué)雜志》2019 年第9 期,第20-33 頁。對企業(yè)合規(guī)與單位刑事責(zé)任論關(guān)系的研究,陳瑞華〔24〕參見陳瑞華:《企業(yè)合規(guī)視野下的暫緩起訴協(xié)議制度》,載《比較法研究》2020 年第1 期,第1-18 頁。、李玉華〔25〕參見李玉華:《我國企業(yè)合規(guī)的刑事訴訟激勵》,載《比較法研究》2020 年第1 期,第19-33 頁。對企業(yè)緩起訴制度與企業(yè)合規(guī)關(guān)系的研究,都可以歸屬于國家視角的研究。區(qū)別于上述研究,韓軼在企業(yè)刑事合規(guī)風(fēng)險的類型化基礎(chǔ)上,對于企業(yè)刑事合規(guī)的基本內(nèi)容和一般方案進行了探討,這是典型的企業(yè)視角的研究。〔26〕參見韓軼:《企業(yè)刑事合規(guī)的風(fēng)險防控與建構(gòu)路徑》,載《法學(xué)雜志》2019 年第9 期,第1-8 頁。其他文獻還包括李本燦:《企業(yè)視角下的合規(guī)計劃的建構(gòu)方法》,載《法學(xué)雜志》2020 年第7 期,第76-83 頁。盧勤忠對于民營企業(yè)具體刑事合規(guī)風(fēng)險及其防范的研究,也部分地涉及企業(yè)視角的研究。〔27〕參見盧勤忠:《民營企業(yè)的刑事合規(guī)及刑事法風(fēng)險防范探析》,載《法學(xué)論壇》2020 年第4 期,第127-137 頁。
最后需要特別交代的是,視角的區(qū)分不意味著內(nèi)容上的絕對分離。兩種視角彼此都需要對方的知識補給。例如,企業(yè)視角下,預(yù)防風(fēng)險的組織性措施需要參照刑事立法中的有效性標(biāo)準(zhǔn);作為風(fēng)險預(yù)防的前提,風(fēng)險識別尤其需要準(zhǔn)確理解實體法的內(nèi)容;國家視角下,有效性合規(guī)標(biāo)準(zhǔn)具有證據(jù)法上的決定性意義,其確定離不開企業(yè)視角下公司治理的基本理論。這就意味著,盡管國內(nèi)的研究出現(xiàn)明顯的視角分化,但各自的研究并無方法上的優(yōu)劣,都是有效刑事合規(guī)制度建構(gòu)所必需的。在這個意義上,陳瑞華提出的“從整體視角對合規(guī)問題的全新研究”〔28〕陳瑞華:《企業(yè)合規(guī)制度的三個維度——比較法視野下的分析》,載《比較法研究》2019 年第3 期,第62 頁。確有必要。
(二)范圍的拓展
對于刑事合規(guī)研究范疇的劃定,Bock 曾經(jīng)提出:刑事合規(guī)應(yīng)當(dāng)避免的是“與企業(yè)有關(guān)”的經(jīng)濟犯罪,換言之,刑事合規(guī)是公司刑法的研究范疇。〔29〕Vgl. Dennis Bock, Criminal Compliance, Nomos, 2011, S.23.Rotsch 則認(rèn)為,從“組織關(guān)聯(lián)性”來看,任何組織體都需要合規(guī)制度。〔30〕Vgl. Thomas Rotsch, ZStW 2013, S. 489f.Hilgendorf 也認(rèn)為,將合規(guī)措施理解為組織機構(gòu)(機關(guān)、高校、國家研究機構(gòu)等)內(nèi)部采取的措施更有意義。〔31〕參見[德]希爾根多夫:《刑法合規(guī)中的基本問題:以反腐為例》,江溯譯,載希爾根多夫:《德國刑法學(xué):從傳統(tǒng)到現(xiàn)代》,江溯、黃笑巖等譯,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15 年版,第506 頁。Blassl 認(rèn)為:越發(fā)復(fù)雜的工作程序以及通過資源集中形成的集權(quán),使得在自成體系的組織結(jié)構(gòu)中建構(gòu)組織措施成為必要;合規(guī)不應(yīng)限于企業(yè)合規(guī),否定政黨內(nèi)合規(guī)結(jié)構(gòu)存在的必要性,就等于否定了合規(guī)自身的必要性與正當(dāng)性。〔32〕Vgl. Johannes Sebastian Blassl, Zur Garantenpflicht des Compliance-Beauftragten, Peter Lang, 2017, S. 44f.從國外的研究與實踐情況看,合規(guī)已經(jīng)超出企業(yè)合規(guī)的范圍,政黨、公共機構(gòu)、軍隊合規(guī)都是合規(guī)研究的重要議題。
國內(nèi)研究也實現(xiàn)了從公司合規(guī)到組織體合規(guī)的跨越。魏昌東教授提出了建構(gòu)公共權(quán)力領(lǐng)域合規(guī)計劃的建議和具體方案。〔33〕參見魏昌東:《國家監(jiān)察委員會改革方案之辯正:屬性、職能與職責(zé)定位》,載《法學(xué)》2017 年第3 期,第14 頁;《監(jiān)督職能是國家監(jiān)察委員會的第一職能:理論邏輯與實現(xiàn)路徑——兼論中國特色監(jiān)察監(jiān)督系統(tǒng)的規(guī)范性創(chuàng)建》,載《法學(xué)論壇》2019 年第1 期,第32-33 頁。筆者以我國《刑法》第397 條為中心建構(gòu)公共機構(gòu)腐敗治理合規(guī)路徑的觀點〔34〕參見李本燦:《公共機構(gòu)腐敗治理合規(guī)路徑的構(gòu)建——以〈刑法〉第397 條的解釋為中心》,載《中國刑事法雜志》2019 年第2 期,第25-46 頁。,也是對企業(yè)合規(guī)研究范圍的拓展。
(三)合規(guī)與刑事法的主要學(xué)術(shù)聯(lián)結(jié)點
盡管近幾年的合規(guī)制度研究涉及多個學(xué)科,但隨著國外對刑事合規(guī)制度立法與執(zhí)法的強化,國內(nèi)的研究也主要圍繞合規(guī)與刑事法的關(guān)系展開。鑒于此,此處僅對合規(guī)與刑事法的學(xué)術(shù)聯(lián)結(jié)點加以簡要歸納。
1. 合規(guī)、犯罪預(yù)防與刑事政策
從國家視角來看,合規(guī)被理解為保證組織體守法的制度性工具。也就是說,合規(guī)制度首先是作為一種政策工具與刑法發(fā)生關(guān)聯(lián)。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合規(guī)被稱為“打擊經(jīng)濟犯罪的替代模式”。〔35〕[德]烏爾里希?齊白:《全球風(fēng)險社會與信息社會中的刑法:二十一世紀(jì)刑法模式的轉(zhuǎn)換》,周遵友、江溯等譯,中國法制出版社2011 年版,第236 頁。經(jīng)濟犯罪“替代模式”的提出,源于傳統(tǒng)單一國家規(guī)制路徑效果不彰,因此需要其他模式的功能補給。合規(guī)模式實際上是將外部規(guī)則(國家法)內(nèi)化為組織體的行為守則,并通過系列組織性措施保證規(guī)則的貫徹執(zhí)行。也就是說,組織體自身被成功拖進了傳統(tǒng)“國家—行為人”規(guī)制鏈條之中,構(gòu)造出新型的規(guī)制模式,即“國家—組織體—行為人”的二元規(guī)制模式。相比于國家,組織體距離犯罪行為更近,對于內(nèi)部風(fēng)險更為熟悉,其制定的內(nèi)部規(guī)則與組織性措施也更具適應(yīng)性。因此,在一個“規(guī)制的自治”的框架內(nèi),更好的犯罪預(yù)防效果是可以期待的。國外學(xué)者的實證研究也證實了這一點。〔36〕See Ulrich Sieber, Marc Engelhart, Compliance Programs for the Prevention of Economic Crimes——An Empirical Survey of German Companies, Duncker & Humblot, 2014, p.132.
回顧國內(nèi)的研究歷程,第一個研究視角即是犯罪學(xué)視角。犯罪學(xué)視角的研究套路相對固定,即首先對我國當(dāng)前的企業(yè)犯罪治理現(xiàn)狀進行梳理,以此提出問題;其次是引出外國法中的企業(yè)合規(guī)制度,并對其全球化趨勢與制度優(yōu)勢進行比較研究;最后是提出引入合規(guī)治理模式的建議及具體進路。犯罪學(xué)視角的研究往往涉及刑事政策的學(xué)科內(nèi)容,即作為犯罪預(yù)防政策,合規(guī)進入刑法需要具體路徑,該路徑就涉及立法與司法政策的調(diào)整問題。例如,在上述“國家—組織體—行為人”的規(guī)制鏈條中,政策制定者希望看到的,也是合規(guī)機制發(fā)揮作用的前提是,組織體選擇站在國家這一邊,共同對抗不法行為人。然而,現(xiàn)實情況是,組織體及其內(nèi)部職員是利益共同體,其往往共同對抗國家調(diào)查。這種情況下,合規(guī)機制要想發(fā)揮實際作用,就需要刑事政策上的配合,打破組織體和具體行為人的共同利益關(guān)系。例如,通過立法強化單位及自然人責(zé)任,同時引入合規(guī)激勵機制,嚴(yán)厲單位犯罪司法政策,為合規(guī)機制發(fā)揮作用創(chuàng)造機會和足夠激勵空間。〔37〕參見李本燦:《企業(yè)犯罪預(yù)防中合規(guī)計劃制度的借鑒》,載《中國法學(xué)》2015 年第5 期,第177-205 頁。以美國為代表的合規(guī)實踐已經(jīng)印證了這種路徑的合理性。國內(nèi)對于分則個罪與合規(guī)關(guān)系的研究,也主要涉及犯罪學(xué)與刑事政策的學(xué)科內(nèi)容。例如,于沖對于網(wǎng)絡(luò)平臺刑事合規(guī)問題以及人工智能刑事風(fēng)險規(guī)制問題的研究;〔38〕參見于沖:《網(wǎng)絡(luò)平臺刑事合規(guī)的基礎(chǔ)、功能與路徑》,載《中國刑事法雜志》2019 年第6 期,第94-109 頁;于沖:《刑事合規(guī)視野下人工智能的刑法評價進路》,載《環(huán)球法律評論》2019 年第6 期,第44-57 頁。陳冉對于公害犯罪治理問題的研究,都涉及上述內(nèi)容。〔39〕參見陳冉:《企業(yè)公害犯罪治理的刑事合規(guī)引入》,載《法學(xué)雜志》2019 年第11 期,第108-119 頁。
2. 合規(guī)、單位責(zé)任與刑罰論
為了從內(nèi)部瓦解組織體與員工的利益共同體關(guān)系,美國《聯(lián)邦量刑指南》通過量刑激勵的方式鼓勵組織體實施合規(guī)管理。也就是說,合規(guī)借助于其與單位刑事責(zé)任理論的關(guān)系實現(xiàn)了刑事化。〔40〕參見萬方:《企業(yè)合規(guī)刑事化的發(fā)展及啟示》,載《中國刑事法雜志》2019 年第2 期,第55-57 頁。
單位是刑法上的擬制實體,其實施行為與履行注意義務(wù)的方式不同于自然生命體。從單位故意犯的角度說,單位只能通過自然人實施行為。這只能說明,自然人行為是單位犯罪的必要非充分條件,并不能由職員行為必然推導(dǎo)出該行為歸屬于單位。于是就產(chǎn)生了如何區(qū)分單位行為與自然人行為的問題。從單位過失犯的角度講,單位履行注意義務(wù)與結(jié)果回避義務(wù)的方式也不同于自然人,于是,當(dāng)發(fā)生職員違規(guī)行為之后,就產(chǎn)生了如何認(rèn)定單位是否履行注意或回避義務(wù)的問題。作為犯罪預(yù)防的組織性措施,合規(guī)計劃代表著單位對違規(guī)行為的態(tài)度及其履行監(jiān)管義務(wù)的方式。當(dāng)故意違規(guī)行為發(fā)生后,當(dāng)然可以據(jù)此區(qū)分開自然人行為與單位行為。在單位過失犯罪的場合,有效的公司合規(guī)計劃意味著其盡到了注意與回避義務(wù),自然不應(yīng)承擔(dān)過失責(zé)任。以妨害動植物防疫、檢疫罪為例,如果單位為防疫、檢疫工作制訂了詳細(xì)的合規(guī)方案,即便結(jié)果依然發(fā)生了,也應(yīng)當(dāng)排除單位責(zé)任。國內(nèi)對合規(guī)與單位責(zé)任論關(guān)系的研究已經(jīng)比較充分,相對統(tǒng)一的觀點是,合規(guī)應(yīng)當(dāng)成為單位責(zé)任認(rèn)定的核心要素。〔41〕參見黎宏:《合規(guī)計劃與企業(yè)刑事責(zé)任》,載《法學(xué)雜志》2019 年第9 期,第9-19 頁;孫國祥:《刑事合規(guī)的理念、機能和中國的構(gòu)建》,載《中國刑事法雜志》2019 年第2 期,第3-24 頁。
合規(guī)不僅可以成為責(zé)任刑的考量因素,還可能對預(yù)防刑產(chǎn)生影響。具體來說,在消極的一般預(yù)防理論中,企業(yè)合規(guī)意味著預(yù)防必要性降低;在積極的一般預(yù)防論中,預(yù)防效果的實現(xiàn)受三個因素的影響,即懲罰概率、刑罰種類與幅度以及民眾對刑罰的感知度。〔42〕參見陳金林:《積極的一般預(yù)防理論研究》,武漢大學(xué)出版社2013 年版,第226 頁。在民眾對刑罰的感知度相對穩(wěn)定的情況下,預(yù)防效果取決于刑罰種類、幅度以及懲罰概率。企業(yè)合規(guī)機制包含事前預(yù)防、事中運行以及事后及時報告違規(guī)事件等機制,可以顯著提高違規(guī)行為的發(fā)現(xiàn)概率,從而降低預(yù)防效果對刑罰種類和幅度的依賴。也就是說,在積極的一般預(yù)防理論中,合規(guī)也起到對預(yù)防刑的調(diào)節(jié)作用。國外的立法例積極踐行了這一點,〔43〕例如,奧地利法對于違規(guī)行為發(fā)生后建構(gòu)合規(guī)機制的積極認(rèn)可,vgl. Thomas Rotsch, ZStW 2013, S. 486.國內(nèi)學(xué)者的研究也已經(jīng)涉及這個問題。〔44〕參見李本燦:《刑事合規(guī)制度的法理根基》,載《東方法學(xué)》2020 年第5 期,第39-41 頁。
3. 合規(guī)與起訴激勵
國外的實踐中,除了通過出罪、量刑激勵方式推動企業(yè)合規(guī)之外,起訴激勵機制(緩/不起訴制度)也被廣泛使用。起訴激勵機制也成為合規(guī)制度研究的重要理論陣地。
盡管我國刑訴法尚未規(guī)定企業(yè)緩起訴或不起訴制度,但從2020 年3 月開始,最高人民檢察院開始試點推行實質(zhì)意義上的企業(yè)暫緩起訴制度。隨著試點工作的深入推進,學(xué)術(shù)界也開始廣泛關(guān)注合規(guī)與起訴制度之間的關(guān)系。企業(yè)緩起訴制度之所以越來越多地被提倡和適用,原因在于,傳統(tǒng)的刑罰激勵不足以推動企業(yè)合規(guī)。對于企業(yè)而言,一旦進入刑事訴訟程序,即可能產(chǎn)生企業(yè)污名化,進而產(chǎn)生嚴(yán)重負(fù)外部效應(yīng)。有罪判決更是無異于間接宣告企業(yè)“死刑”,因此,企業(yè)合規(guī)制度的推行需要更強有力的外部激勵機制。企業(yè)緩/不起訴制度即充當(dāng)了這種外部激勵機制。從理論上說,起訴激勵機制對于企業(yè)具有如下意義:負(fù)外部效應(yīng)的克服;報應(yīng)正義的實現(xiàn)與社會關(guān)系的修復(fù);〔45〕通過罰款、補償金等類似制裁方式(Similar Sanction)實現(xiàn)報應(yīng)正義,恢復(fù)被破壞的社會關(guān)系。在處罰方式上,盡管存在作為刑罰措施的“罰金”與作為行政罰的“罰款”的區(qū)別,但二者都表現(xiàn)為對企業(yè)的經(jīng)濟制裁,具有相同的效果。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國外學(xué)者將“企業(yè)罰款”制度稱作“標(biāo)簽性欺詐”(Etiketenschwindel),它只是立法者為規(guī)避企業(yè)刑罰與傳統(tǒng)刑法中的罪責(zé)原則之間矛盾的鬼把戲而已。See Markus D. Dubber, “The Comparative History and Theory of Corporate Criminal Liability”, 16 New Criminal Law Review 203, 216(2013).推動企業(yè)合規(guī)管理,預(yù)防未然之罪。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國內(nèi)現(xiàn)有的研究都普遍認(rèn)為,應(yīng)當(dāng)以認(rèn)罪認(rèn)罰從寬處理機制為制度切入口,引入企業(yè)合規(guī)起訴激勵機制。〔46〕參見陳瑞華:《企業(yè)合規(guī)視野下的暫緩起訴協(xié)議制度》,載《比較法研究》2020 年第1 期,第17-18 頁;李本燦:《認(rèn)罪認(rèn)罰從寬處理機制的完善:企業(yè)犯罪視角的展開》,載《法學(xué)評論》2018 年第3 期,第111 頁。
三、學(xué)術(shù)研究方法與方向的反思
(一)研究方法上的反思
1. 立法論抑或司法論?
學(xué)界對合規(guī)計劃問題的研究剛剛起步。對于如何推動企業(yè)合規(guī),學(xué)界有代表性的觀點是,通過立法方式將合規(guī)寫入刑法以及刑事訴訟法。例如,萬方提出了合規(guī)進入刑法的具體方案;〔47〕參見萬方:《企業(yè)合規(guī)刑事化的發(fā)展及啟示》,載《中國刑事法雜志》2019 年第2 期,第66 頁。李玉華則提出了合規(guī)進入刑事訴訟法的方案。〔48〕參見李玉華:《我國企業(yè)合規(guī)的刑事訴訟激勵》,載《比較法研究》2020 年第1 期,第28 頁。
客觀說,在司法機械主義較為嚴(yán)重的中國當(dāng)下,通過立法方式引入合規(guī)計劃是較為合適的方式。這種方式不僅可以為企業(yè)提供行為指引,還可以為司法判決提供直接的裁判指引。然而,現(xiàn)在面臨的實際情況是,我國企業(yè)在“走出去”過程中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合規(guī)風(fēng)險。可以說,如何促進我國企業(yè)的合規(guī)經(jīng)營已經(jīng)迫在眉睫。在立法尚需時日而風(fēng)險已經(jīng)逼近的情況下,最合適的辦法或許是,通過刑事司法活動推動企業(yè)合規(guī)。
問題是,如何將合規(guī)理念融入公司犯罪司法?這取決于企業(yè)合規(guī)在傳統(tǒng)刑法體系中的理論定位以及我國當(dāng)前的刑事訴訟制度。從實體法的角度講,企業(yè)合規(guī)是單位刑事責(zé)任認(rèn)定的核心要素。尚有疑問的是,合規(guī)計劃應(yīng)當(dāng)在單位責(zé)任認(rèn)定中起到什么作用?盡管在我國的刑事司法實踐中,合規(guī)在部分判決中起到罪與非罪的區(qū)分作用,或者減輕企業(yè)罪責(zé)的作用,但這并未形成穩(wěn)定的裁判規(guī)則。事實上,司法實踐中的諸多判決已經(jīng)考量了“合規(guī)理念”,但并未直接使用“合規(guī)”字眼。穩(wěn)定的裁判規(guī)則取決于合規(guī)與單位責(zé)任理論的關(guān)系。結(jié)合我國《刑法》第30 條以及責(zé)任主義原則可知,單位犯罪是單位自身的犯罪,相應(yīng)地,單位刑事責(zé)任是單位因自己行為需承擔(dān)的責(zé)任,并不是單位代員工受罰。這就意味著,企業(yè)合規(guī)具有排除單位責(zé)任的制度空間;即使合規(guī)責(zé)任未完全履行,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責(zé)任刑。也就是說,通過解釋學(xué)的方法,可以推導(dǎo)出,在我國現(xiàn)行的立法框架下,合規(guī)可能起到降低乃至排除單位責(zé)任的作用。合規(guī)在傳統(tǒng)理論中的定位客觀上為司法提供了穩(wěn)定的裁判根據(jù),這也是合規(guī)計劃中國化最現(xiàn)實、便捷的路徑。
從程序法的角度講,企業(yè)合規(guī)是緩起訴或者不起訴考量的核心要素。盡管我國刑訴法缺乏企業(yè)緩起訴制度,但不起訴制度可以部分承擔(dān)合規(guī)激勵作用。法定不起訴和酌定不起訴都包含了對“情節(jié)顯著輕微”情形下的不起訴。對于外國實踐中通過不起訴協(xié)議促進企業(yè)構(gòu)建或完善合規(guī)計劃的相關(guān)內(nèi)容,完全可以通過檢察建議加以解決。《最高人民檢察院關(guān)于充分履行檢察職能加強產(chǎn)權(quán)司法保護的意見》第8 條規(guī)定:檢察機關(guān)應(yīng)當(dāng)“積極參與社會治安防控體系建設(shè),采取檢察建議等形式,幫助各類產(chǎn)權(quán)主體強化產(chǎn)權(quán)保護意識,促進國有企業(yè)健全內(nèi)部監(jiān)督制度和內(nèi)控機制、規(guī)范國有資產(chǎn)流轉(zhuǎn)程序和交易行為,促進集體經(jīng)濟組織建立健全集體資產(chǎn)管理制度和財務(wù)管理監(jiān)督制度”。實際上,“內(nèi)部監(jiān)督制度”“內(nèi)控機制”等都是企業(yè)合規(guī)機制的重要內(nèi)容。這里尤其需要強調(diào)法定不起訴的運用,原因在于,行刑交叉案件中以刑代罰的情況大量存在,〔49〕參見孫國祥:《行政犯違法性判斷的從屬性和獨立性研究》,載《法學(xué)家》2017 年第1 期,第49 頁。加上司法考評機制的影響,使得大量本不應(yīng)作為犯罪的案件進入刑事審判程序,難以回轉(zhuǎn)。此時,對于行政違法的案件,應(yīng)當(dāng)大膽適用法定不起訴制度,附加“強化內(nèi)部管理機制”的檢察建議,并對檢察建議的實際執(zhí)行情況加以監(jiān)督。
2. 反教義學(xué)化?
從方法論上說,國內(nèi)學(xué)界對合規(guī)問題的研究實現(xiàn)了從現(xiàn)象描述、制度引介到規(guī)范化闡釋的跨越。然而,學(xué)界仍有不少學(xué)者排斥用教義學(xué)方法研究合規(guī)問題,原因在于,中國刑法中沒有形式上的企業(yè)合規(guī)制度。不得不說,這是對刑事合規(guī)制度的誤讀。中國的合規(guī)問題研究已經(jīng)過了觀念倡導(dǎo)期,未來的研究應(yīng)當(dāng)堅持教義學(xué)方法的主導(dǎo)地位。原因如下。
第一,刑事合規(guī)以刑事法規(guī)范為基礎(chǔ)。從刑事合規(guī)的基本功能和概念可知,其在前置領(lǐng)域預(yù)先對刑事實體法的規(guī)定加以具體落實。〔50〕Vgl. Uwe H. Schneider, ZIP 2003, S. 645f.刑事實體法規(guī)定的具體落實實際上是風(fēng)險識別過程,這是組織體內(nèi)部行為守則確定以及結(jié)構(gòu)化的前提。〔51〕Vgl. Marc Engelhart, Sanktionierung von Unternehmen und Compliance: Eine rechtsvergleichende Analyse des Straf- und Ordnungswidrigkeitenrechts in Deutschland und den USA, Duncker & Humblot, 2010, S. 167ff.某種意義上說,刑事風(fēng)險的識別與刑事法規(guī)范的發(fā)現(xiàn)和解釋工作同步,解釋的準(zhǔn)確性直接決定著企業(yè)未來可能面臨風(fēng)險的大小。例如,在騙取貸款罪逐步口袋化的今天,騙貸風(fēng)險幾乎存在于每一個企業(yè)。有效避免騙貸風(fēng)險的前提是對騙取貸款罪構(gòu)造的準(zhǔn)確把握。典型的問題是,存在足額擔(dān)保的情況下,虛構(gòu)或者任意改變貸款用途的行為是否構(gòu)成騙取貸款罪?學(xué)理上存在較為有力的無罪說〔52〕參見孫國祥:《騙取貸款罪司法認(rèn)定的誤識與匡正》,載《法商研究》2016 年第5 期,第56 頁;王新:《騙取貸款罪的適用問題和教義學(xué)解析》,載《政治與法律》2019 年第10 期,第46 頁。,實踐中亦可見無罪判決。〔53〕參見湖北省高級人民法院(2014)鄂刑一終字00076 號刑事判決書。可是,在《刑法修正案(十一)》之前,這種解釋可能脫離了司法解釋對本罪“其他嚴(yán)重情節(jié)”的規(guī)定,因而得出了不合適的結(jié)論。〔54〕參見張明楷:《騙取貸款罪的保護法益及其運用》,載《當(dāng)代法學(xué)》2020 年第1 期,第59-62 頁。以個案為例證立自己無罪說的觀點也不盡合理,事實上,司法實踐也存在大量有罪判決。〔55〕參見江西省橫峰縣人民法院(2018)贛1125 刑初71 號刑事判決書。簡言之,離開了刑法教義學(xué),作為合規(guī)機制建構(gòu)基礎(chǔ)的風(fēng)險識別工作都難以完成,更不用說合規(guī)機制的有效建構(gòu)和運行。
第二,刑事合規(guī)制度邊界的劃定離不開教義學(xué)。作為風(fēng)險刑法與經(jīng)濟全球化的產(chǎn)物,刑事合規(guī)制度具有明顯的時代性。迎合時代需求不意味著對傳統(tǒng)教義學(xué)的背離。“法教義學(xué)的當(dāng)代發(fā)展,已經(jīng)從過去那種科學(xué)面向的、唯體系化的、純粹依靠概念和邏輯推理構(gòu)建起來的法教義學(xué),轉(zhuǎn)向為實踐和經(jīng)驗面向的、融合了多學(xué)科知識、包含了目的、利益和價值判斷的法教義學(xué)。”〔56〕車浩:《理解當(dāng)代中國刑法教義學(xué)》,載《中外法學(xué)》2017 年第6 期,第1423 頁。刑事合規(guī)制度不僅具有單位刑事責(zé)任論與保證人義務(wù)理論上的根據(jù),也順利將刑事政策上的預(yù)防目的融入規(guī)則體系。從刑事合規(guī)的出罪與責(zé)任減輕功能看,其并不違背罪刑法定原則。然而,在合規(guī)監(jiān)管的問題上,則出現(xiàn)了問題:法定可罰性范圍的前置領(lǐng)域在結(jié)構(gòu)上是開放的,其后果是,對于規(guī)則的構(gòu)建,刑事合規(guī)并不包含任何的內(nèi)部界限,從自由的角度看,這是存在問題的。〔57〕Vgl. Thomas Rotsch, ZIS 2010, S. 616.部分案件中,合規(guī)規(guī)則為刑事責(zé)任創(chuàng)設(shè)了新的連接點,例如,德國達姆施塔特地方法院從對內(nèi)部合規(guī)規(guī)則的違反中推導(dǎo)出職員背信罪的義務(wù)違反性。〔58〕Vgl. Frank Saliger, Karsten Gaede, HRRS 2008, S. 57.一些國家,不合規(guī)甚至成為加重處罰的事由。〔59〕See Jonathan A Clough, Carmel Mulhern, The Prosecution of Corporation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188.在本文看來,這些觀點或立法例都將合規(guī)制度過于政策化、工具化,逾越了應(yīng)有的制度邊界。也就是說,刑事合規(guī)應(yīng)當(dāng)有制度邊界,而制度邊界的劃定離不開傳統(tǒng)教義學(xué)的支持。〔60〕參見孫國祥:《刑事合規(guī)的刑法教義學(xué)思考》,載《東方法學(xué)》2020 年第5 期,第24-25 頁。
第三,單位責(zé)任論本身就是教義學(xué)的重要范疇。單位犯罪并非傳統(tǒng)刑法學(xué)的命題,但自從單位犯罪普遍進入各國刑法(尤其是大陸法國家)之后,如何解決單位責(zé)任與傳統(tǒng)責(zé)任主義原則之間的沖突就成為核心問題。從單位罪責(zé)理論的學(xué)術(shù)史可以看出,其經(jīng)歷了自然路徑向規(guī)范路徑的轉(zhuǎn)變。研究路徑轉(zhuǎn)變的根源就在于,傳統(tǒng)以自然人為媒介建構(gòu)單位責(zé)任的路徑有背離罪責(zé)自負(fù)原則的嫌疑,因此有必要重新認(rèn)識單位責(zé)任。由此可見,進入刑法之后,單位責(zé)任論就成為教義學(xué)的重要范疇。作為單位責(zé)任認(rèn)定的重要參考要素,合規(guī)計劃問題的研究自然離不開教義學(xué)方法。
第四,合規(guī)官保證人義務(wù)問題亦是教義學(xué)的重要范疇。我國當(dāng)前的合規(guī)制度研究深受英美法的影響,都是在單位犯罪的語境中展開。然而有疑問的是,在沒有單位犯罪的國家(例如德國)如何構(gòu)建刑事合規(guī)制度?如果從“利用刑事法手段推動企業(yè)自我管理”的角度理解刑事合規(guī)制度,那么,就沒有理由將刑事合規(guī)限定在單位犯罪的語境。實際上,通過賦予特定自然人(例如公司領(lǐng)導(dǎo)以及合規(guī)官)對于職員的業(yè)務(wù)關(guān)聯(lián)行為的監(jiān)督者保證人義務(wù)的方式推動企業(yè)合規(guī),也是一種有效的建構(gòu)路徑。然而,在強調(diào)自我答責(zé)的現(xiàn)代刑法中,如何證立“為他人行為負(fù)責(zé)”這一命題就成為問題。這恰恰是教義學(xué)的重要范疇。需要特別指出的是,現(xiàn)在主要是德國學(xué)者在討論這個問題,但這絕不意味著這種討論對我們國家沒有任何意義。原因在于,盡管我們國家存在單位犯罪制度,但其具有顯著片段性。在非單位犯罪的領(lǐng)域,這種討論就具有補充性意義。
(二)研究方向上的反思
過去十年,世界范圍內(nèi)經(jīng)濟刑法研究沒有哪一個議題比刑事合規(guī)得到更多關(guān)注。國內(nèi)現(xiàn)有的研究也多以肯定為主,并從實體和程序法兩個角度分別發(fā)表了制度引介的建議。然而,從國外的實際運行情況看,并不容樂觀。總體上說,對企業(yè)而言,合規(guī)計劃開始成為負(fù)擔(dān),并且制度初衷是否達到也值得懷疑;從學(xué)理上說,它已經(jīng)逾越了自由法治國應(yīng)有的制度邊界,構(gòu)成對企業(yè)經(jīng)營自由的侵害。
據(jù)介紹,2009 年至2015 年7 月間,美國監(jiān)管機構(gòu)對在美經(jīng)營的銀行罰款1610 億美元,其中不乏百億美元的巨額罰單。〔61〕參見余永定:《美巨額罰款公正還是勒索?》,來源:http://opinion.caixin.com/2018-05-09/101246420.html,2020 年3 月20 日訪問。這些處罰大都與合規(guī)機制瑕疵有關(guān)。除巨額罰款外,企業(yè)還面臨重構(gòu)合規(guī)計劃的巨額經(jīng)濟壓力。更值得關(guān)注的是,通過長臂管轄進行全球執(zhí)法的做法正在被效仿,例如,自GDPR 生效以來,歐盟執(zhí)法機構(gòu)已經(jīng)對谷歌、英國航空、萬豪集團等公司做出了數(shù)億歐元的罰款。此外,合規(guī)還可能使自己遭受“起訴困境”,即合規(guī)計劃的信息被訴訟當(dāng)事人用于攻擊企業(yè)。鑒于此,企業(yè)僅具有采用“次優(yōu)合規(guī)計劃”的動機,這也就很難保證犯罪預(yù)防目的的實現(xiàn)。〔62〕參見[美]菲利普?韋勒:《有效的合規(guī)計劃與企業(yè)刑事訴訟》,萬方譯,載《財經(jīng)法學(xué)》2018 年第3 期,第150-152 頁。
通過對多國立法及實踐的考察,也可以發(fā)現(xiàn)合規(guī)計劃帶來的過度規(guī)制等侵害企業(yè)經(jīng)營自由權(quán)或職員基本訴訟權(quán)利的問題。例如,在預(yù)防措施的問題上,普遍采取的是標(biāo)準(zhǔn)化的方法。標(biāo)準(zhǔn)化對于合規(guī)制度的推行以及有效性評估固然有益,但也會產(chǎn)生與基本權(quán)的沖突問題:合規(guī)標(biāo)準(zhǔn)化是否可能與企業(yè)經(jīng)營自由權(quán)相沖突?事實上,在很多國家,企業(yè)的經(jīng)營自由受到憲法的嚴(yán)格保護,企業(yè)組織結(jié)構(gòu)形式應(yīng)以有效促進經(jīng)濟活力為宗旨,不應(yīng)當(dāng)受制于嚴(yán)苛的官僚式的規(guī)則。〔63〕See Günter Heine,“ New Developments in Corporate Criminal Liability in Europe: Can Europeans Learn from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or Vice Versa”, 1998 Saint Louis-Warsaw Transatlantic Law Journal 173, 178(1998).“合規(guī)計劃的程序十分復(fù)雜,難以滿足各行業(yè)的獨特需求。量刑委員會提供的設(shè)計說明越詳細(xì),則越可能出現(xiàn)部分企業(yè)的合規(guī)需求偏離《聯(lián)邦量刑指南》規(guī)定的情況……必須允許企業(yè)設(shè)計滿足獨特需求的合規(guī)計劃,這些需求是法律無法預(yù)期的;要實現(xiàn)這個目標(biāo)(預(yù)防犯罪),需采納另一條去結(jié)構(gòu)化的途徑。”〔64〕[美]菲利普?韋勒:《有效的合規(guī)計劃與企業(yè)刑事訴訟》,萬方譯,載《財經(jīng)法學(xué)》2018 年第3 期,第151 頁、第156 頁。“對所有法人進行一攬子司法指導(dǎo)是幾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務(wù)。能夠滿足處于不同行業(yè)、體量差異巨大、內(nèi)控制度眾相紛呈的法人所需求的合規(guī)計劃實際上并不存在。這樣的現(xiàn)實情況就要求立法與司法機關(guān)必須一次又一次經(jīng)過繁雜的程序,不斷推出新的內(nèi)容以滿足各個行業(yè)的獨特需求,但這樣不僅會對罪刑法定原則的安定性產(chǎn)生不良影響,而且從實用主義的角度來看也并不明智。”〔65〕宋頤陽:《企業(yè)合規(guī)計劃有效性與舉報人保護制度之構(gòu)建——澳大利亞路徑及其對中國的啟示》,載《比較法研究》2019 年第4 期,第89 頁。又如,在預(yù)防措施的強度問題上,國外實踐中緩/不起訴協(xié)議的達成多以承諾構(gòu)建或強化合規(guī)計劃為前提,為此企業(yè)投入了巨大資源,問題是,邊界在哪里?從對企業(yè)經(jīng)營自由的憲法性權(quán)利保障出發(fā),內(nèi)部控制措施應(yīng)當(dāng)符合比例原則,以可能、必要、可期待為準(zhǔn)則來衡量內(nèi)控措施。〔66〕Vgl. BGH NStZ 1997, S. 545f.再比如,公司自己實施的內(nèi)部調(diào)查形成的證據(jù)能否直接在法庭中使用?漢堡地方法院曾經(jīng)將公司內(nèi)部調(diào)查形成的證據(jù)材料,直接針對內(nèi)部被詢問者使用。〔67〕Vgl. Matthias Jahn, ZIS 2011, S.453; Hans Joachim Fritz, CCZ 2011, S.155.可是,這難道不是對不得自證其罪原則的間接侵害嗎?如此等等,還有很多問題。這些問題提示我們,對刑事合規(guī)不能只唱贊歌,冷思考也十分必要。
四、對具體問題的批判性反思
(一)以程序法抑或?qū)嶓w法為切入點?
上文已指出,從國家的角度講,刑事合規(guī)是旨在推動組織體合規(guī)管理的法制度工具。從這個概念出發(fā),實體法上的定罪、量刑激勵以及程序法上的起訴激勵機制都是合適的制度工具。不同于此處的邏輯推論的是,國內(nèi)有學(xué)者提出,在我國已經(jīng)確立認(rèn)罪認(rèn)罰從寬制度的背景下,沒有必要引入域外的刑事合規(guī)計劃;總體上可以將認(rèn)罪認(rèn)罰從寬制度作為載體,完善我國企業(yè)犯罪案件辦理工作機制。〔68〕參見趙恒:《涉罪企業(yè)認(rèn)罪認(rèn)罰從寬制度研究》,載《法學(xué)》2020 年第4 期,第121-124 頁。也就是說,該論者認(rèn)為,我們應(yīng)當(dāng)以程序法而非實體法為切入點建構(gòu)刑事合規(guī)制度。這種觀點看似合理,實則是對刑事合規(guī)概念的誤解,也混淆了實體法和程序法上的合規(guī)激勵機制的關(guān)系。
第一,刑事合規(guī)包含程序法上的激勵機制,但程序法上的機制并非刑事合規(guī)制度的全部。趙恒博士在論文中反復(fù)提及:“刑事合規(guī)計劃以企業(yè)認(rèn)罪答辯為顯著特點;刑事合規(guī)計劃是以認(rèn)罪答辯為核心的犯罪案件快速處理機制從自然人犯罪領(lǐng)域擴張至單位犯罪領(lǐng)域的結(jié)果。”〔69〕趙恒:《涉罪企業(yè)認(rèn)罪認(rèn)罰從寬制度研究》,載《法學(xué)》2020 年第4 期,第123-124 頁。這種觀點顯然是對刑事合規(guī)制度的誤解。首先,既然刑事合規(guī)是旨在推動企業(yè)內(nèi)部管理的制度工具,那么,實體法上的定罪激勵、量刑激勵或者以個人責(zé)任作為聯(lián)結(jié)點推動企業(yè)實施合規(guī)管理的激勵機制都是適格的制度工具。既然實體法上的激勵機制適格,則不能認(rèn)為認(rèn)罪答辯是刑事合規(guī)制度的核心。其次,刑事合規(guī)也不一定以認(rèn)罪為前提。例如,英國法明確規(guī)定,認(rèn)罪并非緩起訴的前提;〔70〕Deferred Prosecution Agreements Code of Practice(2013), para. 6.3.據(jù)學(xué)者介紹,法國法中的企業(yè)緩起訴也不以認(rèn)罪為前提;〔71〕參見陳瑞華:《法國〈薩賓第二法案〉與刑事合規(guī)問題》,載《中國律師》2019 年第5 期,第83 頁。即便在企業(yè)緩起訴大量適用的美國,很多企業(yè)緩/不起訴案件中,涉案企業(yè)并不認(rèn)罪,協(xié)議甚至不要求企業(yè)承認(rèn)涉案事實。〔72〕See Peter Spivack, Sujit Ramen,“ Regulating the New Regulators: Current Trends in Deferred Prosecution Agreements”, 45 American Criminal Law Review 159,177-178(2008).
第二,實體法上單位歸責(zé)模式以及訴訟文化的差異決定了,企業(yè)緩起訴的適用應(yīng)有限度,不可能成為推動企業(yè)合規(guī)的核心制度工具。刑事合規(guī)制度與單位歸責(zé)模式具有內(nèi)在關(guān)聯(lián),不同的單位歸責(zé)模式?jīng)Q定了不同的刑事合規(guī)制度。以美國為例,主流的單位歸責(zé)模式是代位責(zé)任。〔73〕參見李本燦:《域外企業(yè)緩起訴制度比較研究》,載《中國刑事法雜志》2020 年第3 期,第103 頁。代位責(zé)任的目的是激勵企業(yè)維持最高水平的內(nèi)部監(jiān)督和控制機制,以避免員工不法行為。〔74〕See Matt Senko,“ Prosecutorial Overreaching in Deferred Prosecution Agreements”, 19 Southern California Interdisciplinary Law Journal 163,190(2009).然而,代位責(zé)任的結(jié)果是,企業(yè)承擔(dān)了嚴(yán)格責(zé)任。在代位責(zé)任模式下,合規(guī)計劃不能避免,而僅能減輕企業(yè)責(zé)任。對于企業(yè)來講,其追求的是避免定罪而不僅僅是責(zé)任減輕,定罪本身即足以給企業(yè)帶來毀滅性災(zāi)難。也就是說,代位責(zé)任模式下的刑事合規(guī)制度存在激勵不足的缺陷,因此需要程序法上激勵機制的功能補給。美國大量適用企業(yè)緩/不起訴推動企業(yè)合規(guī)的實踐正是在這種深刻的制度背景下產(chǎn)生的。這個判斷也可以從文獻中得到印證:美國法的文獻中普遍存在一種聲音,“如果刑事司法不想繼續(xù)妥協(xié)的話,消除代位責(zé)任模式就是必要的”。〔75〕Matt Senko,“ Prosecutorial Overreaching in Deferred Prosecution Agreements”, 19 Southern California Interdisciplinary Law Journal 163,164(2009).作者表達的觀點正是,由于代位責(zé)任激勵不足,因而才有了緩起訴制度;如果要限制企業(yè)緩起訴(及其帶來的諸多弊端),就應(yīng)當(dāng)改變代位責(zé)任的歸責(zé)模式。回到我國,從《刑法》第30 條以及第14 條、第15 條可以推論出,單位責(zé)任是組織體自身的責(zé)任。〔76〕參見黎宏:《組織體刑事責(zé)任論及其應(yīng)用》,載《法學(xué)研究》2020 年第2 期,第87 頁。在組織體責(zé)任模式中,企業(yè)合規(guī)是單位履行注意或結(jié)果回避義務(wù)的方式,完全可以起到排除責(zé)任或者減輕責(zé)任的作用。這也就意味著,我國實體法中的出罪或責(zé)任減免機制完全可以在合規(guī)激勵上獨當(dāng)一面,對程序法上的暫緩起訴制度的功能補給需求并不強烈。此外,美國廣泛適用企業(yè)緩起訴制度也與其深厚的訴訟協(xié)商文化密不可分,盡管我國刑訴法中的認(rèn)罪認(rèn)罰從寬處理機制、附條件不起訴制度都體現(xiàn)了協(xié)商文化,但受制于整體訴訟協(xié)商文化氛圍稀薄,其適用有嚴(yán)格的限度。例如,盡管認(rèn)罪認(rèn)罰從寬并沒有在可適用罪名、訴訟階段等方面加以限制,但美國式的深度、廣泛協(xié)商根本不可能適用。概而言之,實體法上的單位歸責(zé)模式以及訴訟文化的差異決定了,以認(rèn)罪認(rèn)罰從寬處理機制為切入點的程序法上的合規(guī)激勵機制僅具有補充性作用,其不可能排除實體法上的合規(guī)激勵機制的適用。
(二)刑事合規(guī)的研究是否以單位犯罪的法定化為前提?
有學(xué)者提出,“企業(yè)合規(guī)進入法律實踐領(lǐng)域并呈現(xiàn)刑事化發(fā)展的前提是,企業(yè)能構(gòu)成犯罪,并承擔(dān)相應(yīng)的刑事責(zé)任。”〔77〕萬方:《企業(yè)合規(guī)刑事化的發(fā)展及啟示》,載《中國刑事法雜志》2019 年第2 期,第64 頁。近幾年,作者本人著重借鑒德國學(xué)者的規(guī)范研究方法,通過對德國的刑事合規(guī)制度的研究,來反思英美以及我國的合規(guī)實踐。對于這種研究方法,部分學(xué)者頗有微詞,其認(rèn)為,德國不承認(rèn)單位犯罪何談刑事合規(guī)?同樣的批判也針對本人在中國法語境下提出的“刑事合規(guī)的教義學(xué)化問題”,即中國刑法典中沒有合規(guī)概念,談何“教義學(xué)化”?本文對此稍加回應(yīng)。
以上兩個看似不相關(guān)的問題,實際有內(nèi)在關(guān)聯(lián)。對于刑事合規(guī)制度是否以單位犯罪的法定化為前提的問題,答案取決于我們?nèi)绾卫斫狻靶淌潞弦?guī)”的概念。上文也已經(jīng)提到,刑事合規(guī)是保證企業(yè)守法的、促進法益保護的法制度工具,或者說是如何運用外部激勵機制推動企業(yè)自我管理的制度。外部激勵手段并不是單一的,通過出罪可以最大限度激勵企業(yè)合規(guī);通過減輕罪責(zé)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激勵企業(yè)合規(guī);通過起訴激勵也可以促進企業(yè)合規(guī)。然而,這些都是針對企業(yè)自身的激勵機制,除此之外,還包括對自然人的激勵機制,例如,美國的合規(guī)計劃在2002 年之后加速發(fā)展的根本動力是《薩班斯法案》對于自然人責(zé)任的強化。2015 年經(jīng)司法部副部長薩利?耶茨簽署的《公司違法行為個人責(zé)任指令》進一步強化了個人責(zé)任。“耶茨備忘錄強調(diào)執(zhí)法過程中個人的配合,也要求涉案個人承擔(dān)相應(yīng)責(zé)任,這一指令表現(xiàn)出美國司法部欲將企業(yè)高層繩之以法的傾向。”〔78〕陳可倩、龔自力:《白領(lǐng)犯罪前沿問題——白領(lǐng)犯罪國際研討會會議綜述》,載《交大法學(xué)》2016 年第2 期,第8 頁。德國也恰恰是通過賦予公司領(lǐng)導(dǎo)、合規(guī)官等風(fēng)險控制人員監(jiān)督者保證人義務(wù)的方式〔79〕BGHSt 54, 44, Rn.3-6;BGH B. v. 06.02.2018 - 5 StR 629/17 - NStZ 2018, 648.推動企業(yè)合規(guī)。個人履行監(jiān)督者保證人義務(wù)的方式并非貼身盯防,而是建立組織性措施,保證公司領(lǐng)域內(nèi)不發(fā)生業(yè)務(wù)關(guān)聯(lián)性風(fēng)險。由此可見,刑事合規(guī)制度的建構(gòu)并不以單位犯罪的法定化為前提。既然通過賦予特定責(zé)任主體監(jiān)督者保證人義務(wù)的方式也是一種刑事合規(guī)制度,難道不需要教義學(xué)方法嗎?更何況,我國單位犯罪條款本身就是合規(guī)規(guī)則的設(shè)定,合規(guī)制度并不以明確的文字標(biāo)識為必要。
(三)單一的刑罰威懾與刑事合規(guī)制度是否存在邏輯悖論?
有論者提出,“礙于合規(guī)計劃與刑罰威懾效果之間固有的邏輯沖突,單一刑罰威懾框架下的合規(guī)計劃難以做到真實且有效”。〔80〕宋頤陽:《企業(yè)合規(guī)計劃有效性與舉報人保護制度之構(gòu)建——澳大利亞路徑及其對中國的啟示》,載《比較法研究》2019 年第4 期,第89 頁。這是對現(xiàn)行刑事合規(guī)制度的根本否定。這種觀點的核心論據(jù)是:法人組織是理性經(jīng)濟人,刑罰僅是法律提供給法人組織可供計算的眾多數(shù)據(jù)之一;合規(guī)計劃越有效,企業(yè)越有可能暴露在訴訟之下,甚至成為第三人起訴的證據(jù)。〔81〕參見宋頤陽:《企業(yè)合規(guī)計劃有效性與舉報人保護制度之構(gòu)建——澳大利亞路徑及其對中國的啟示》,載《比較法研究》2019 年第4 期,第89-92 頁。對此,本文做兩點回應(yīng)。第一,刑罰是企業(yè)理性計算的因素之一,但它也恰恰是最重要的要素。如果保證及時、足夠的刑罰供應(yīng),企業(yè)不可能僅采取具有裝潢意義的合規(guī)計劃,這也恰恰是其理性計算的體現(xiàn)。原因在于,相比于自我暴露的合規(guī)材料被第三方用以攻擊企業(yè)的危險,刑罰對于企業(yè)是更致命的打擊。現(xiàn)代企業(yè)對刑罰的敏感性已經(jīng)不止一次得到驗證,這也是美國企業(yè)犯罪司法中,無論需要付出多大的罰款、補償金等成本,企業(yè)都愿意與司法部達成緩起訴或不起訴協(xié)議的根本原因。第二,有效合規(guī)計劃產(chǎn)生的額外訴訟負(fù)擔(dān)削弱了企業(yè)自我揭發(fā)的動機,但這不足以從根本上否定刑事合規(guī)制度。在本文看來,這個問題暴露出了合規(guī)制度中配套性規(guī)則設(shè)置的缺陷,但不能據(jù)此否定制度本身。企業(yè)合規(guī)是刑事訴訟私有化的表現(xiàn),國家將自身的任務(wù)分配給了企業(yè),企業(yè)是在幫助國家行使國家職能。如果從這種“善良行動”中產(chǎn)生對企業(yè)的額外負(fù)擔(dān),有違基本的正義理念。因此,有必要設(shè)計輔助性規(guī)則,解決合規(guī)制度中的缺陷。一個可行的路徑是,引入“自我評估特免權(quán)制度”。美國俄勒岡州在1993 年的《環(huán)境犯罪法案》中已經(jīng)引入了“環(huán)境審計報告證據(jù)豁免規(guī)則”,以此鼓勵企業(yè)實施合規(guī)管理。〔82〕參見李本燦:《企業(yè)犯罪預(yù)防中國家規(guī)制向國家與企業(yè)共治轉(zhuǎn)型之提倡》,載《政治與法律》2016 年第2 期,第63-64 頁。總而言之,合規(guī)制度并非完美的,但不能據(jù)此徹底否定制度,單一的刑罰威懾與刑事合規(guī)制度并不存在無法解決的沖突。
(四)刑事合規(guī)制度的單位歸責(zé)模式基礎(chǔ):替代責(zé)任?組織體責(zé)任抑或嚴(yán)格責(zé)任?
上文也提到,刑事合規(guī)制度與單位歸責(zé)模式具有密不可分的內(nèi)在關(guān)聯(lián),可以說,不同的單位歸責(zé)模式塑造了不同的刑事合規(guī)制度。然而,這絕不意味著刑事合規(guī)制度單一地依附于哪一種單位歸責(zé)模式。在這個問題上,國內(nèi)存在如下兩點誤解。第一,在組織體責(zé)任與嚴(yán)格責(zé)任之間糾纏不清。陳瑞華教授在這個問題上就表現(xiàn)得非常糾結(jié)。一方面,他認(rèn)為,“唯有建立企業(yè)獨立意志理論,將單位視為一種獨立的生命有機體,承認(rèn)其具有實施獨立行為和具有獨立主觀意志的能力,才能將企業(yè)合規(guī)融入單位歸責(zé)原則之中。”〔83〕陳瑞華:《合規(guī)視野下的企業(yè)刑事責(zé)任問題》,載《環(huán)球法律評論》2020 年第1 期,第23 頁。另一方面,他又指出,“由于不承認(rèn)嚴(yán)格責(zé)任,我國刑法難以確立類似英國‘商業(yè)組織預(yù)防腐敗失職罪’那樣的罪名,無法為企業(yè)設(shè)定無過錯責(zé)任;嚴(yán)格責(zé)任的確立,在對企業(yè)犯罪嚴(yán)密法網(wǎng)的同時,也賦予企業(yè)通過建立合規(guī)計劃來進行積極抗辯的權(quán)利,從而使得企業(yè)具有建立和完善合規(guī)計劃的強大動力;在動輒強調(diào)主客觀相統(tǒng)一的中國刑法之中,嚴(yán)格責(zé)任沒有存在的空間,因此我們應(yīng)當(dāng)引入嚴(yán)格責(zé)任制度,并在此基礎(chǔ)上將企業(yè)合規(guī)確立為企業(yè)無罪抗辯事由和法定的減輕處罰情節(jié),由此在定罪量刑環(huán)節(jié)將合規(guī)激勵機制予以激活。”〔84〕陳瑞華:《論企業(yè)合規(guī)的中國化問題》,載《法律科學(xué)(西北政法大學(xué)學(xué)報)》2020 年第3 期,第45 頁、第47-48 頁。第二,以美國為單一的觀察對象,錯誤地認(rèn)為,既然美國的刑事合規(guī)制度產(chǎn)生于代位責(zé)任模式之下,那么代位責(zé)任就是刑事合規(guī)的制度根基。這種錯誤觀點的典型代表是田宏杰教授〔85〕參見田宏杰:《刑事合規(guī)的反思》,載《北京大學(xué)學(xué)報(哲學(xué)社會科學(xué)版)》2020 年第2 期,第120-121 頁。及其引以為據(jù)的萬方博士。〔86〕參見萬方:《企業(yè)合規(guī)刑事化的發(fā)展及啟示》,載《中國刑事法雜志》2019 年第2 期,第55 頁、第64-65 頁。
對于這些誤解的澄清如下。首先,嚴(yán)格責(zé)任不應(yīng)成為激勵企業(yè)合規(guī)的主要制度工具。關(guān)于嚴(yán)格責(zé)任的概念,學(xué)術(shù)上并未形成統(tǒng)一的觀點。一種觀點認(rèn)為,嚴(yán)格責(zé)任與絕對責(zé)任無意義上的區(qū)別,無論當(dāng)事人盡到怎樣的注意義務(wù)或采取何種預(yù)防措施,只要損害發(fā)生,其必須承擔(dān)責(zé)任;嚴(yán)格責(zé)任犯罪中無須包括犯罪心態(tài)(限于對公眾福利造成危害的行為)。〔87〕參見薛波主編:《元照英美法詞典》,載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17 年版,第1298 頁。美國《模范刑法典》采取了這種概念。〔88〕參見[美]約書亞?德雷斯勒:《美國刑法綱要》,姜敏譯,中國法制出版社2016 年版,第154-156 頁。一種觀點則將嚴(yán)格責(zé)任區(qū)分為實體性嚴(yán)格責(zé)任與程序性嚴(yán)格責(zé)任。實體性的嚴(yán)格責(zé)任即無過錯責(zé)任;程序性的嚴(yán)格責(zé)任則將犯罪意圖的舉證責(zé)任歸于被告,即控方無須就責(zé)任舉證即可推定犯意,被告可通過舉證加以反駁以擺脫責(zé)任。〔89〕參見[美]道格拉斯?胡薩克:《刑法哲學(xué)》,謝望原等譯,中國人民公安大學(xué)出版社1994 年版。勞東燕教授將嚴(yán)格責(zé)任區(qū)分為絕對的嚴(yán)格責(zé)任與相對的嚴(yán)格責(zé)任〔90〕參見勞東燕:《認(rèn)真對待刑事推定》,載《法學(xué)研究》2007 年第2 期,第23 頁。,也可以歸屬于這一類觀點。陳瑞華教授的論述未明確嚴(yán)格責(zé)任的概念,可分述如下。第一,觀點的自我矛盾。一方面,其認(rèn)為嚴(yán)格責(zé)任是無過錯責(zé)任,這是在絕對的意義上使用嚴(yán)格責(zé)任概念;另一方面,其又認(rèn)為,企業(yè)的嚴(yán)格責(zé)任可以通過合規(guī)計劃進行抗辯,這是在相對的意義上使用嚴(yán)格責(zé)任概念。兩種不同意義上的嚴(yán)格責(zé)任所產(chǎn)生的法律效果差異巨大,不能不加區(qū)分地使用。第二,如果其是在絕對的意義上使用概念,那么,通過嚴(yán)格責(zé)任激活合規(guī)機制的主張就很難實現(xiàn)。原因是,這個意義上的嚴(yán)格責(zé)任實際上與美國的替代責(zé)任無差異,在這種歸責(zé)模式中,企業(yè)合規(guī)無法排除責(zé)任,存在天然的激勵不足的缺陷,因此才需要上文討論的程序法上的企業(yè)緩/不起訴制度的功能補給。第三,如果其是在相對的意義上使用概念,則與組織體責(zé)任模式下控方負(fù)責(zé)證明合規(guī)計劃的無效性的情形相比,確實更有利于激勵企業(yè)合規(guī),問題是,刑事合規(guī)制度的推行應(yīng)在現(xiàn)有的法律框架內(nèi)展開,作為一種價值追求,企業(yè)合規(guī)不能凌駕于其他價值之上。這個層面的嚴(yán)格責(zé)任“在放松控方證明要求的同時又將存疑風(fēng)險轉(zhuǎn)移到被告人身上,背離了排除合理懷疑的證明標(biāo)準(zhǔn),直接危及無罪推定原則所保護的價值和利益。”〔91〕勞東燕:《認(rèn)真對待刑事推定》,載《法學(xué)研究》2007 年第2 期,第21 頁。因此,這個層面的嚴(yán)格責(zé)任下的刑事合規(guī)制度亦不值得過分主張。
其次,單位歸責(zé)模式與刑事合規(guī)制度的類型化。在嚴(yán)格責(zé)任的問題解決之后,剩下的問題是,刑事合規(guī)制度的歸責(zé)模式基礎(chǔ)是什么?組織體責(zé)任抑或代位責(zé)任?在這個問題上,觀點針鋒相對,但在本文看來,兩種觀點都存在疑問。很明顯的例子是,在替代責(zé)任主導(dǎo)的美國產(chǎn)生了刑事合規(guī)制度,并且成為合規(guī)制度的典范;在組織體責(zé)任模式下的我國,也可以發(fā)現(xiàn)刑事合規(guī)制度的影子;在倡導(dǎo)組織體文化責(zé)任的澳大利亞〔92〕See Criminal Code Act 1995, Chapter 2, Part 2.5, 12.3.,也廣泛推行了刑事合規(guī)制度。試問,對此應(yīng)如何解釋?在替代責(zé)任模式之下,哪怕是底層員工的行為,只要是在職權(quán)范圍內(nèi)部分為了企業(yè)利益實施,都應(yīng)當(dāng)歸屬于企業(yè)。也就是說,員工的行為就是企業(yè)的行為,不管企業(yè)對此是什么態(tài)度,采取了什么措施。這種歸責(zé)模式下,企業(yè)承擔(dān)的是絕對責(zé)任。因此,企業(yè)合規(guī)不能排除責(zé)任,只能降低責(zé)任,由此可以推導(dǎo)出量刑激勵類型的刑事合規(guī)制度。在組織體責(zé)任模式之下,員工的行為不一定是單位的行為,員工行為僅僅是認(rèn)定單位犯罪的“觀察資料”。〔93〕參見李本燦:《單位刑事責(zé)任論的反思與重構(gòu)》,載《環(huán)球法律評論》2020 年第4 期,第39 頁。單位責(zé)任是單位為自己的行為負(fù)責(zé)。企業(yè)合規(guī)表征了單位對于員工行為的態(tài)度,也是單位履行注意與回避義務(wù)的方式。在這種模式之下,有效的合規(guī)計劃可能排除企業(yè)責(zé)任;有瑕疵的合規(guī)計劃也代表了單位在履行責(zé)任上的努力,可以減輕企業(yè)罪責(zé);由此可以推導(dǎo)出排除或減輕責(zé)任類型的刑事合規(guī)制度。總而言之,刑事合規(guī)制度并不依存于哪一種單位歸責(zé)模式,不同歸責(zé)模式產(chǎn)生不同類型的刑事合規(guī)制度。
(五)對其他觀點的集中回應(yīng)
近期,田宏杰教授《刑事合規(guī)的反思》(下稱“田文”,不再一一標(biāo)注出處)一文對于國內(nèi)刑事合規(guī)制度的研究進行了反思性批判,其認(rèn)為國內(nèi)的研究存在諸多誤區(qū),進而從根本上否定了刑事合規(guī)制度。在本文看來,田文的批判多建立在對合規(guī)制度的片面解讀之上,因而有必要集中加以澄清。〔94〕關(guān)于代位責(zé)任與刑事合規(guī)的關(guān)系問題,本文已經(jīng)針對田宏杰教授的觀點做了回應(yīng),此處僅圍繞其他爭論點展開論述。
1. 立法定性與司法定量的立法模式造就了美國的刑事合規(guī)制度?
田文(121-122 頁)認(rèn)為,除了替代責(zé)任外,美國刑事合規(guī)制度得以發(fā)展的另一個理論背景是立法定性與司法定量的立法模式;這種立法模式產(chǎn)生了兩個方面的影響:從實體上來看,美國法語境下的刑事合規(guī)與中國法語境下的行政合規(guī)相對應(yīng);從程序上來看,司法定量的模式給予了司法機關(guān)更大的裁量權(quán),因此才有了暫緩起訴制度的廣泛適用。
在本文看來,這種觀點存在如下問題。第一,邏輯推論上的錯誤。即便“立法定性與司法定量”的基本判斷無誤,也不能據(jù)此認(rèn)為美國的刑事合規(guī)相當(dāng)于中國的行政合規(guī),因而中國不存在刑事合規(guī)的制度基礎(chǔ)。正確的邏輯推論應(yīng)當(dāng)是,“美國的刑事合規(guī)=中國的行政合規(guī)+刑事合規(guī)”。據(jù)此,中國的刑事合規(guī)的制度空間當(dāng)然不能被否定。第二,美國程序法上的合規(guī)激勵機制主要與實體法上的單位歸責(zé)模式以及濃厚的協(xié)商性訴訟文化相關(guān)聯(lián),與“立法定性與司法定量”的立法模式關(guān)聯(lián)微弱。
2. 理論界的誤解還是田文的誤解?
田文認(rèn)為,國內(nèi)學(xué)術(shù)界對刑事合規(guī)制度有如下多方面的誤解,下文逐一進行辯證。
(1)任意擴大刑事合規(guī)概念的外延。田文(122-123 頁)認(rèn)為,刑事合規(guī)制度只能要求企業(yè)采取適當(dāng)?shù)拇胧┓乐蛊鋬?nèi)部員工實施犯罪,而不能要求企業(yè)防止其客戶實施犯罪;刑事合規(guī)主要是一個國內(nèi)法問題,而非國際法問題,用國內(nèi)法要求本國企業(yè)遵守其他國家的國內(nèi)法,這種做法缺乏法理正當(dāng)性;隨著其他國家法律的修改而改變自己的合規(guī)標(biāo)準(zhǔn),實際上意味著我國企業(yè)的行為受到了他國的操縱。
在本文看來,田文的觀點存在如下問題。第一,企業(yè)不僅應(yīng)保證自身不對外輸出風(fēng)險,如果外部風(fēng)險(例如,客戶實施的犯罪)發(fā)生在自己的管轄范圍,其也應(yīng)當(dāng)保證風(fēng)險不發(fā)生。作者自己也承認(rèn),刑事合規(guī)的核心是預(yù)防犯罪。從國家的角度講,其將本應(yīng)由自身承擔(dān)的預(yù)防犯罪職責(zé)轉(zhuǎn)移給了企業(yè),以實現(xiàn)犯罪預(yù)防的情景化,同時節(jié)約司法資源。既然是概括的犯罪預(yù)防,單位就不僅要保證自身不對外輸出風(fēng)險,法定場合,其還應(yīng)當(dāng)保證自身管轄空間內(nèi)不發(fā)生風(fēng)險。以田文所舉網(wǎng)絡(luò)服務(wù)提供者為例,其不僅要防止員工犯罪,在刑法賦予其對自身管轄空間的安全保障義務(wù)的情況下,對于其他人員在平臺內(nèi)的犯罪(例如,傳播違法信息),其當(dāng)然具有管理義務(wù)。網(wǎng)絡(luò)服務(wù)提供者阻止客戶實施犯罪只不過是保證自身不發(fā)生風(fēng)險的手段。從企業(yè)的角度來說,刑事合規(guī)的基本功能是降低自身可能遭受的刑事風(fēng)險。〔95〕參見[德]弗蘭克?薩力格爾:《刑事合規(guī)的基本問題》,馬寅翔譯,載李本燦等編譯:《合規(guī)與刑法:全球視野的考察》,中國政法大學(xué)出版社2018 年版,第53 頁。這種風(fēng)險不僅包括自身不受刑事法制裁,還包括不成為犯罪侵害對象。例如,當(dāng)公司外的其他人員針對公司的財產(chǎn)實施犯罪時,負(fù)有安全保障職責(zé)者(例如,負(fù)有勤勉義務(wù)的公司領(lǐng)導(dǎo))當(dāng)然具有阻止義務(wù)。第二,合規(guī)制度是國內(nèi)法問題,但其要解決的問題包括規(guī)避海外經(jīng)營中的風(fēng)險。文獻中普遍性的認(rèn)知是,合規(guī)是經(jīng)濟全球化的產(chǎn)物。〔96〕Vgl. Thomas Rotsch, ZStW 2013, S. 495.經(jīng)濟的全球化意味著行為規(guī)則以及制裁風(fēng)險的全球化。作為全球經(jīng)濟的參與者,國家與企業(yè)具有利益的趨同性。如果我國企業(yè)在海外普遍遭受合規(guī)風(fēng)險,那么我們的經(jīng)濟安全也就無以保證,中興通訊事件就是最好的說明。為了培育企業(yè)的合規(guī)文化,避免海外經(jīng)營風(fēng)險,《中央企業(yè)合規(guī)管理指引》《企業(yè)境外經(jīng)營合規(guī)管理指引》的諸多條款都規(guī)定,企業(yè)應(yīng)當(dāng)遵守相關(guān)國家的法律規(guī)范,然而,這種做法并非缺乏法理正當(dāng)性,保護企業(yè)以及國家利益就是最大的正當(dāng)性根據(jù)。現(xiàn)代刑法不就是建立在法益(利益)保護的基礎(chǔ)之上嗎?更何況,對其他國家或國際組織規(guī)則的遵守,對于經(jīng)濟全球化浪潮中的所有參與者都同等適用。例如,為了適應(yīng)中國的法律規(guī)范和文化,多數(shù)美國企業(yè)也不得不改變自身在華經(jīng)營的合規(guī)標(biāo)準(zhǔn)。〔97〕See The US-China Business Council, Best Practices for Managing Compliance in China(2013).簡言之,遵守公司業(yè)務(wù)所在國的法律,根據(jù)其法律調(diào)整合規(guī)標(biāo)準(zhǔn)是經(jīng)濟全球化的必然要求,并非田文所言的“行為操縱”。
(2)在單位犯罪和自然人犯罪的關(guān)系上立場不一。田文(125 頁)認(rèn)為,以孫國祥教授為代表的學(xué)者具有自相矛盾的嫌疑:一方面,其認(rèn)為單位犯罪與自然人犯罪的法益侵害本質(zhì)相同,應(yīng)當(dāng)同罪同罰;另一方面,其又主張不同于自然人犯罪的歸責(zé)模式。
在本文看來,田文的觀點存在如下問題:從法益侵害的角度講,單位犯罪與自然人犯罪并無本質(zhì)差別,尤其是,單位犯罪無非是作為集合體的人的犯罪,因此,兩者同罪同罰本身并無不妥。問題是,同罪同罰與是否采取相同的歸責(zé)模式是兩個不同的問題。英美法系國家的刑事立法多不區(qū)分自然人犯罪與法人犯罪,即在大多數(shù)的犯罪中(強奸、重婚等除外),自然人與法人都同罪同罰。〔98〕參見聶立澤:《單位犯罪新論》,法律出版社2018 年版,第1 頁。然而,一方面,這些國家的單位歸責(zé)模式亦不同于自然人;另一方面,這些國家的單位歸責(zé)模式也不盡相同,例如,美國以代位責(zé)任為主流、英國以“同一視理論”為主流、澳大利亞則以法人文化責(zé)任為主流。〔99〕參見李文偉:《法人刑事責(zé)任比較研究》,中國檢察出版社2006 年版,第18 頁、第23 頁、第39 頁。在本文看來,無論是將法人作為擬制體或者實體,其都不同于作為自然生命體的自然人,相應(yīng)地,兩者的歸責(zé)模式也不可能相同;即便否定法人責(zé)任的規(guī)范化處理方法,將法人責(zé)任理解為領(lǐng)導(dǎo)的集體責(zé)任,但這種歸責(zé)方法也強調(diào)責(zé)任的整體性,〔100〕參見李本燦:《自然人刑事責(zé)任、公司刑事責(zé)任與機器人刑事責(zé)任》,載《當(dāng)代法學(xué)》2020 年第3 期,第107-109 頁。顯然區(qū)別于自然人。然而,否定自然人與法人歸責(zé)模式的相同性,并不意味著法人犯罪和自然人犯罪不能同罪同罰。
(3)過分夸大和片面強調(diào)刑事合規(guī)的優(yōu)點。田文(125-126 頁)認(rèn)為,用刑法手段要求企業(yè)必須建立合規(guī)計劃,加重了企業(yè)負(fù)擔(dān),違背了權(quán)責(zé)統(tǒng)一原則;刑事合規(guī)制度助推了企業(yè)犯罪的灰色化乃至黑色化;能否帶來長遠(yuǎn)利益存在疑問。
在本文看來,田文的觀點存在如下問題。第一,權(quán)責(zé)統(tǒng)一在刑事合規(guī)制度中已經(jīng)實現(xiàn)了。一方面,如果企業(yè)實施合規(guī)管理,那么作為回報,當(dāng)發(fā)生員工違法時,企業(yè)可以以此為據(jù),主張排除或者減輕自身責(zé)任,這也是權(quán)責(zé)統(tǒng)一的表現(xiàn)形式;另一方面,與合規(guī)義務(wù)相對的是,內(nèi)部調(diào)查的權(quán)利。例如,美國的合規(guī)計劃制度中,給予了企業(yè)在違法行為發(fā)生后的內(nèi)部調(diào)查權(quán),并且,由外部律師參與實施的內(nèi)部調(diào)查所形成的證據(jù)材料享有律師—客戶、工作成果特免權(quán)。企業(yè)內(nèi)部調(diào)查是刑事訴訟私有化的表現(xiàn),田宏杰教授當(dāng)然有權(quán)“不認(rèn)為這是一件很有魅力的事情”,但作為發(fā)展趨勢,刑事訴訟的私有化已不可避免。無論是刑事和解,還是認(rèn)罪認(rèn)罰從寬制度不都是刑事訴訟私有化的表現(xiàn)形式嗎?第二,無論是否存在刑事合規(guī)制度,企業(yè)內(nèi)部調(diào)查和制裁都普遍存在,相應(yīng)地,將犯罪行為進行內(nèi)部消化處理的現(xiàn)象也不可避免〔101〕我國學(xué)者對于民營企業(yè)內(nèi)腐敗犯罪的實證研究也證實了這一點,參見賈宇:《民營企業(yè)內(nèi)部腐敗犯罪治理的體系性建構(gòu)——以〈刑法修正案(十一)〉的相關(guān)修改為契機》,載《法學(xué)》2021 年第5 期,第75 頁。,反倒是合規(guī)激勵機制部分改善了這種情況,這尤其依賴于作為合規(guī)激勵前提的自我報告。例如,經(jīng)過對英國截止2020 年4 月發(fā)布的7 個企業(yè)緩起訴案〔102〕“SFO v. Standard Bank”(2015),“ SFO v. Sarclad Ltd”(2016),“ SFO v. Rolls-Royce”(2017),“ SFO v. Tesco”(2017),“ SFO v.Serco Geografix Ltd”(2019),“ SFO v. Güralp Systems Ltd”(2019),“ SFO v. Airbus SE”(2020)。這些緩起訴協(xié)議文本,可以從SFO 官網(wǎng)獲取。的協(xié)議文本及附屬材料的考察不難發(fā)現(xiàn),除Rolls-Royce 案沒有企業(yè)的自我報告之外,其他案件都是企業(yè)自我報告的結(jié)果。第三,合規(guī)確實給企業(yè)帶來了負(fù)擔(dān),但合規(guī)建設(shè)遵循個別化原則,對于中小企業(yè)并非遙不可及,長期利益也可以平衡經(jīng)濟負(fù)擔(dān)。學(xué)界已經(jīng)在合規(guī)建設(shè)的個別化原則上達成共識,〔103〕See Winthrop M. Swensen, Nolan E. Clark,“ The New Federal Sentencing Guidelines: Three Keys to Understanding the Credit for Compliance Programs”, 1 Corporate Conduct Quarterly 1, 1-2(1991).并不會產(chǎn)生田宏杰教授所說的“雪上加霜”的后果;合規(guī)計劃在預(yù)防犯罪上的有效性〔104〕See Ulrich Sieber, Marc Engelhart, Compliance Programs for the Prevention of Economic Crimes——An Empirical Survey of German Companies, Duncker & Humblot, 2014, p.132.以及對于法治化營商環(huán)境建設(shè)上的積極意義,都是對企業(yè)負(fù)擔(dān)的平衡。
(4)刑事合規(guī)對不法的影響問題。田文(127-128 頁)認(rèn)為,合規(guī)官的保證人義務(wù)不值得贊成;合規(guī)計劃的出罪功能將會落空,因為員工實施犯罪行為即表明合規(guī)無效。
在本文看來,田文的觀點存在如下問題。第一,合規(guī)官的保證人義務(wù)完全可以在學(xué)理上證成。篇幅所限,作者將對這個問題另行論述,此處僅擇要說明。首先,企業(yè)總負(fù)責(zé)人的保證人義務(wù)并非不言自明。“在單位犯罪中,企業(yè)總負(fù)責(zé)人本來就要承擔(dān)相應(yīng)責(zé)任,沒有必要專門論證其負(fù)有保證人義務(wù)”的觀點可以成立,問題是,在非單位犯罪的情況下呢?即便我國存在單位犯罪立法,可是單位犯罪也具有顯著片段性。在非單位犯罪領(lǐng)域,企業(yè)負(fù)責(zé)人對于職工行為的監(jiān)督者保證人義務(wù)需要小心求證,而非不言自明。其次,領(lǐng)導(dǎo)的多層級化僅改變義務(wù)履行方式,而不改變義務(wù)歸屬。從我國《公司法》第147 條可以推導(dǎo)出,合規(guī)義務(wù)是領(lǐng)導(dǎo)的集體性義務(wù),具有不可轉(zhuǎn)委托性,即便發(fā)生領(lǐng)導(dǎo)層內(nèi)水平方向的授權(quán)以及領(lǐng)導(dǎo)層下垂直方向的授權(quán),都不改變義務(wù)歸屬。經(jīng)過授權(quán),下級合規(guī)人員取得了保證人義務(wù),但由于命令指使權(quán)的缺失,其履行義務(wù)的方式僅表現(xiàn)為信息傳遞。實際上,田宏杰教授已經(jīng)隱約認(rèn)識到了這個問題,只是其對保證人義務(wù)的認(rèn)識再次發(fā)生了偏差:一方面,其認(rèn)為“合理的制度安排是要求部門經(jīng)理負(fù)有報告義務(wù)”;另一方面,其又否定了這些人員的保證人義務(wù),由此傳遞出的信息是,保證人義務(wù)的履行必須表現(xiàn)為親自制止不法行為,保證結(jié)果不發(fā)生。這顯然是對保證人義務(wù)的錯誤理解。試想,交通肇事人對于被害人的救助義務(wù)必須通過親自上手術(shù)臺才能履行嗎?實際上,無論是交通肇事人,還是公司合規(guī)人員,通過信息傳遞即可以履行保證人義務(wù)。最后,人確實不能被視為危險源,但這并不能否定建立在其他聯(lián)結(jié)點上的保證人義務(wù)。例如,從“未履行組織體結(jié)構(gòu)的合理塑造或運行義務(wù)”的危險前行為中,可以推導(dǎo)出監(jiān)督者保證人義務(wù)。需要說明的是,危險前行為僅提供了義務(wù)來源,而非義務(wù)及其履行方式本身,“保證人義務(wù)是一種結(jié)果防止義務(wù),而不僅僅是制度建設(shè)義務(wù)”顯然是對本人之前觀點的誤讀。第二,個案中犯罪預(yù)防的失效并不必然意味著合規(guī)計劃的無效,這一點無論是在典型立法例,〔105〕See U.S. Sentencing Guideline Manual(2018) §8 B2.1.(a).還是在學(xué)理上,〔106〕參見李本燦:《公共機構(gòu)腐敗治理合規(guī)路徑的構(gòu)建——以〈刑法〉第397 條的解釋為中心》,載《中國刑事法雜志》2019 年第2 期,第38 頁。都已經(jīng)得到了認(rèn)同。
(5)刑事合規(guī)對責(zé)任的影響問題。在合規(guī)與違法性認(rèn)識錯誤的關(guān)系問題上,田文(128-129 頁)認(rèn)為,“合規(guī)計劃是企業(yè)為了預(yù)防犯罪而建立的內(nèi)部控制機制,合規(guī)計劃的存在本身已表明,企業(yè)已經(jīng)認(rèn)識到了相關(guān)行為的違法性,而不存在違法性認(rèn)識錯誤,自然也談不上可以避免(責(zé)任)的問題。”
在本文看來,田文的觀點沒有正確認(rèn)識合規(guī)計劃的功能定位及限度:合規(guī)計劃是預(yù)防犯罪的制度工具,但絕不是消滅犯罪的法寶;合規(guī)計劃的構(gòu)建本身就遵守可能、必要、可期待的限度標(biāo)準(zhǔn)。這就意味著,合規(guī)計劃不可能識別(包括法律風(fēng)險在內(nèi)的)所有風(fēng)險。這種情況下,不可避免的違法性錯誤完全可能發(fā)生,此時,沒有理由不適用錯誤論排除企業(yè)責(zé)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