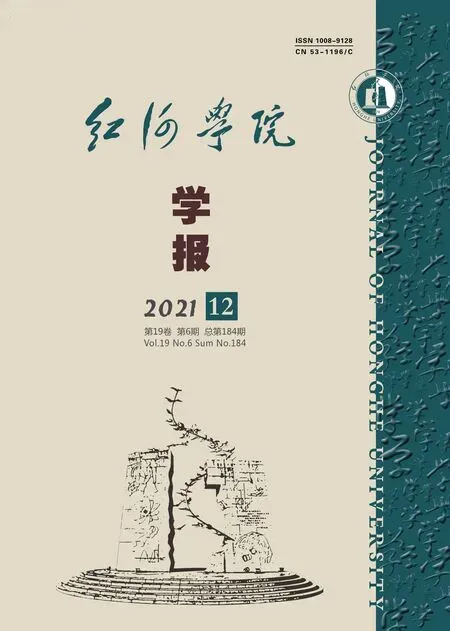移動支付發展對居民家庭金融資產結構的影響分析
——基于家庭金融調查數據的實證
陳 東
(中國人民銀行紅河州中心支行,云南蒙自 661100)
電子支付已快速融入到居民的日常生活之中,主要包括移動支付、自動柜員機交易網上支付、銷售終端交易等方式,移動支付逐步發展成為多元化支付方式,并對現金形成較大的替代效應。
根據艾媒咨詢數據統計顯示,2017年我國移動支付使用人數已達5.62億人,2019年突破7億,2年用戶數增長30.43%。2014年移動支付交易額僅為22.6億元,2017年交易額已達202.9億元,為2014年交易額的8倍,2014年以來移動支付發展進入快速通道。截至2019年末,我國移動支付的覆蓋率已超過80%,遠高于發達國家水平,移動支付已深入到居民日常生活的多個領域。
居民家庭資產逐步由單一性資產向多元化結構性資產轉變,根據西南財經大學中國家庭金融調查與研究中心的調查統計分析結果,我國居民家庭資產結構主要呈現以下特點:
1.居民家庭資產規模整體呈現分布不均的態勢,主要表現為東部與中西部、東北地區家庭資產規模分布差異較大,根據2013年CHFS調查數據分析結果,東部居民家庭資產中位數38.3萬元,為中西部地區的1.8倍,東部居民家庭資產占我國居民家庭總資產的66.6%,而中部和西部地區僅為18.4%和15.0%。
2.居民家庭資產增長顯著且存在向中等資產家庭聚焦的趨勢,居民家庭資產各年度均呈現穩步增長的態勢,特別是由于我國城鎮化進程加速等原因,導致我國城鎮地區的居民資產增長較快。同時,中等資產家庭占全國家庭總資產的比重呈逐年上升趨勢,2015年CHFS調查顯示,中等資產家庭占比已達37.6%。
3.現金等無風險資產占金融資產比例逐步下降,新興互聯網理財快速發展。根據2013年至2015年CHFS調查顯示,無風險資產呈現快速增長的趨勢,但是占金融資產的比例在持續下降,2013年CHFS調查中現金占金融資產的比例為7.4%,至2015年已下降至4.8%,特別是近年來由于移動支付科技的迅猛發展,現金資產持有量已呈逐步減少的趨勢,后續隨著人民銀行數字貨幣的推出,可預見數字貨幣將快速成為M0的重要組成部分并對現金紙幣形成替代效應。同時,理財產品不論從資產總量或是擁有率方面,均呈快速上升趨勢,根據CHFS調查顯示,僅2013年至2015年,銀行業金融機構理財擁有率從2013年的1.7%增長逐步升至2015年的4.5%,但2013年快速興起的互聯網理財擁有率到2015年已升至4.6%,超過傳統銀行理財擁有率,移動支付為居民無風險資產轉化為互聯網理財產品提供了便捷的通道。
本文的創新和貢獻主要在于:重點針對移動支付發展與居民家庭金融資產結構之間的關系開展分析研究,把前期獨立的移動支付發展與居民家庭金融資產結構研究聯系起來,深入探索兩者之間存在的關聯影響。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對移動支付與居民家庭金融資產的結構性特點進行分項研究,重點分析分地區和分年齡居民家庭情況。
一 文獻綜述
近年來中國家庭金融資產占比不斷提升。尹志超等[1]運用中國家庭金融調查數據分析研究發現,隨著中國金融市場的深度和廣度不斷擴張,金融資源和服務的可得性提升后,居民將更為積極地到正規金融市場中進行投融資,增加對股票、債券、衍生品等風險資產的配置,家庭風險資產占金融資產的比例顯著上升。研究發現,中國家庭金融資產出現了較大幅度的增長,投資性風險金融資產占比明顯提升,居民理財產品擁有率逐年上升,互聯網理財產品愈發受到青睞。
年齡、受教育程度和收入是影響家庭資產結構的重要因素。馬廣奇和楊靖[2]將我國宏觀經濟因素納入考慮,重點分析居民家庭資產結構影響的主要因素,并通過與美國居民家庭資產配置狀況進行比較,他們認為家庭金融資產結構與居民的收入水平、年齡和學歷水平存在著非常密切的關聯。余新平[3]利用2010年和2012年的中國家庭追蹤調查(CFPS)數據和《中國統計年鑒》數據,重點研究影響我國居民家庭固定資產配置的因素,年齡、教育、家庭收入是其中最重要的幾個因素。
移動支付的快速發展顯著減少了居民對實物現金需求。謝平和劉海二[4]認為,隨著金融科技發展,運用移動支付和電子貨幣的人數呈現快速增長趨勢,移動支付具有低交易成本的優勢,家庭居民現金需求量比例呈逐步降低趨勢,反映出居民貨幣需求的形式正在發生變化。朱琳琪和周弘[5]運用《中國統計年鑒》的宏觀經濟數據對家庭金融資產結構進行分析,發現由于銀行業和互聯網第三方支付的快速發展,相較于其他金融資產,家庭持有的現金比例大幅下降。王山[6]以我國1990至2015年的經濟數據建立現金需求模型,發現電子支付對居民現金資產有明顯的擠出效應。
移動支付對不同地區的影響程度存在較大差異。韓永和李成明[8]經過異質性分析發現,由于東部地區擁有更為發達的經濟和技術,移動支付的優勢得以更好地顯現,有助于家庭有效配置資源,移動支付的運用效率對東部地區的影響顯著高于我國其他地區。尹志超等[8]基于CHFS數據,研究發現移動支付對貨幣需求的影響在東中西部地區、城鄉地區存在顯著差異,驗證了地區發展水平對移動支付效用的發揮起到了關鍵作用。
二 數據、變量與模型
(一)數據
本文選擇的研究數據為西南財經大學中國家庭金融調查與研究中心開展的中國家庭金融調查數據(CHFS),其目的為收集我國居民家庭的微觀金融經濟數據信息,內容包括:房地產資產、金融投資資產、信貸債務資產、消費支出、社會保險保障、代際轉移支付、個人特征及職業情況、支付方式等方面。本文利用2017年CHFS數據,通過對數據進行清洗和整理,共計獲得全國(除港澳臺外)各省(直轄市、自治區)40,011戶家庭,127,012個人的微觀數據。
(二)變量
1.移動支付
本文研究的移動支付是指用戶利用移動終端對購買的商品或服務進行賬務支付的一種服務方式,移動支付終端主要包括移動電話、便攜式平板電腦等移動電子設備。2017年CHFS家庭金融調查問卷中關于支付方式的問題為:您和您家人在購物時(含網購),一般會使用下列哪種支付方式?(可多選):1.現金;2.刷卡(包括銀行卡、信用卡等);3.通過電腦支付(包括網銀、支付寶等);4.通過手機、Pad等移動終端支付包括(支付寶APP、微信支付、手機銀行、Applepay等);5.其他。為便于把移動支付與其他支付方式進行區分,本文將被調查者問卷中答案包含選項4的定義為擁有并使用移動支付工具,將其賦值為1,不包含選項4的則賦值為0。
2.居民資產及資產結構變量
根據2017年CHFS家庭金融調查數據結果,本文研究的居民家庭資產包括房地產資產、商業投資性資產、耐用品資產(主要為汽車)、其他非金融資產、投資性和非投資性金融資產,其中金融資產進一步細分為現金、股票賬戶中的可用資金、活期存款、定期存款、公開上市的股票、非公開上市的股票、基金、互聯網理財產品、傳統金融理財產品、債券、金融衍生品和借出款。本文所研究的互聯網理財產品為居民通過互聯網渠道購買的具有一定收益性的金融理財產品,既包含第三方線上支付公司提供的理財產品,也包含居民通過金融機構線上渠道購買的理財產品;而傳統理財產品主要是通過銀行業金融機構柜臺進行現場銷售,部分理財產品設置一定的投資門檻,期限普遍超過90日,針對普通居民家庭而言更類似于定期存款。對資產結構變量的研究,本文重點針對現金占流動性貨幣資產比例、金融資產占總資產比例和互聯網金融理財占投資性金融資產比例共計3項居家金融資產結構變量。同時,為排除極端值對計量結果的影響,本文在建模時已剔除資產總計最大和最小的各1%樣本,累計剔除2540個極端樣本值。
3.控制變量
參照文獻并結合CHFS問卷內容,本文選取的控制變量為:居民個人特征變量(含受訪者年齡、教育程度、婚姻狀況、是否為家庭戶主、最近是否工作并取得收入、上一年工作實際獲得的稅后貨幣工資、所在省份和地區、是否有網購經歷等)、家庭特征變量(含家庭擁有房產數量、是否參與涉及互聯網銷售的商業項目、家庭擁有汽車數量、家庭擁有汽車的價值等)。表1給出了各變量的描述性統計。

表1 描述性統計
(三)模型
本文估計移動支付對居民家庭資產結構影響的模型設定為:

在研究方法上,本文除使用普通最小二乘法進行計量研究外,還分別運用Tobit模型和分位數回歸進行研究,本文使用的Tobit模型為:

分位數回歸用于研究不同資產規模居民家庭的移動支付影響情況,利用解釋變量的不同階段分位數計算得到被解釋變量所對應的分位數方程,更為精準描述移動支付變量對資產規模情況的條件分布影響,有利于結構化分析不同居民資產規模的影響特征。
三 實證結果
(一)移動支付對居民家庭金融資產結構的影響
1.移動支付和居民金融資產
本文將金融資產占居民總資產的比例作為研究對象,金融資產主要包括現金、各項存款、股票、債券、基金、互聯網和傳統金融理財產品、金融衍生品和借出款。表2給出了移動支付對居民金融資產占總資產比例的影響。

表2 移動支付使用對金融資產占總資產比例的影響
表2(1)至(4)列反映出,移動支付的估計系數均為正值,且在1%的水平上顯著,說明移動支付的使用對提升居民金融資產占總資產比例具有促進效應。值得關注的是,第(1)至(3)列模型中,家庭擁有房產數量的估計系數均為負值,說明家庭擁有房產數量越多,其金融資產占總資產的比例越低,反映出現階段居民家庭資產結構中,房地產資產與金融資產之間呈現相互擠出的效應。
2.移動支付和居民持有現金資產
為研究移動支付發展對居民持有現金意愿的情況,本文將現金占流動性貨幣資產的比例作為研究對象,流動性貨幣資產主要包括現金、股票賬戶中的現金、活期存款和定期存款。表3給出了移動支付對居民持有現金占流動性貨幣資產比例的影響。

表3 移動支付使用對現金占流動性貨幣資產比例的影響
表3第(1)列給出在不考慮居民收入情況下,移動支付對現金持有比例的影響,在控制居民和家庭特征變量后,發現移動支付的估計系數為-0.096,且在1%的水平上顯著,說明利用移動支付的居民會降低其現金持有量,移動支付發展對現金需求存在一定的擠出效應。第(3)和(4)列分別為利用Tobit模型在是否考慮居民收入情況下的回歸結果,移動支付的估計系數分別為-0.151和-0.138,均在1%的水平上顯著,再次驗證移動支付對居民現金持有比例存在抑制作用,對居民持有現金存在替代效應。從人民銀行公布的現金凈投放量來看,2014年至2020年4月,年度現金凈投放量均不超過6,000億元人民幣,2017、2018和2019年現金凈投放量僅為2,342、2,563和3,981億元,反映出移動支付發展對現金使用的替代性正快速顯現。
3.移動支付和互聯網金融理財
為研究移動支付發展對互聯網金融理財資產結構分布狀況,將互聯網金融理財占投資性金融資產的比例作為研究對象。表4給出了移動支付對互聯網金融理財占投資性金融資產比例的影響。

表4 移動支付使用對互聯網金融理財占投資性金融資產比例的影響
表4(1)至(4)列反映出,移動支付的估計系數均為正值,且在1%的顯著水平上,說明移動支付的使用對提升互聯網金融理財占投資性金融資產比例具有促進作用。值得注意的是,表4(1)至(4)列均反映出,“是否具有購物經歷”的估計系數均為正值,且在1%的水平上顯著,而表2和表3的模型中“是否具有網購經歷”的估計系數均影響程度較小或不顯著,說明具有網購經歷的居民其互聯網金融資產配置傾向越高、互聯網金融資產占投資性金融資產的比例越高。
(二)移動支付對不同年齡層次居民金融資產結構的影響
本部分對移動支付對金融市場發展的影響程度,從居民家庭年齡結構開展研究,對CHFS的被調查居民按照年齡分為3部分,分別是40歲以下、40歲(含40歲)至60歲,60歲(含60歲)以上,為避免篇幅冗長,表5報告3個年齡層次與移動支付交叉項的估計系數值和穩健標準差,其余控制變量不再報告。

表5 移動支付使用對不同年齡層次居民金融資產占總資產比例的影響
表5從年齡結構的角度分析了移動支付對金融資產占總資產比例的影響程度,總體來看,各年齡層次的居民使用移動支付對金融資產占總資產比例均為正向影響,且所有估計系統在1%的水平上顯著,說明移動支付對金融資產占總資產比例的提升起到促進作用,該結論與表2給出的結論相一致。按不同年齡層次來看,在40至60歲的居民中,移動支付對金融資產占總資產比例的影響更為顯著,60歲以上居民的影響程度相對較低。
(三)基于不同地區視角下,移動支付對居民家庭資產和金資產結構的影響
分位數回歸:分地區來看移動支付和居民家庭資產關系。
本部分使用分位數回歸分析移動支付對居民家庭資產的影響,檢驗在不同地區移動支付對不同家庭資產規模的影響程度。本文將我國除港澳臺以外的省(直轄市、自治區)分為東部、中部、東北和西部共計4個地區,分位數回歸時對居民家庭資產所取分位點為20、40、60和80分位點,表6僅報告4個地區的移動支付估計系數值和穩健標準差,其余控制變量不再報告。

表6 移動支付使用對居民家庭資產影響的分位數回歸
由表6可知,東部地區居民使用移動支付對居民家庭資產總額具有促進作用,而中部、東北和西部地區居民所持資產總額相對較少。從各分位數的具體情況看,在20分位數上,移動支付的估計系數均為正值,且在1%的水平上顯著,說明在整體資產持有量較少的居民中,移動支付的發展對其資產增長具有促進作用。根據艾媒咨詢數據調查顯示,月收入1萬元以下的用戶已占移動支付總用戶數的87.1%,移動支付使用率在1萬元收入以下人群中覆蓋率更高,該調查結果與上述移動支付發展的普惠性特征結論相一致。在80分位數上,東部地區移動支付的估計系數為正,且1%的水平上顯著,反映東部地區移動支付發展對高資產凈值的人群提升資產規模具有促進作用,而在中部、東北和西部地區,移動支付發展對高資產凈值的人群提升資產規模反而有抑制作用。可以看出移動支付對居民家庭金融資產的影響程度顯著高于對居民家庭總資產的影響程度,特別是在80分位數水平上,移動支付發展對居民總資產和金融資產的影響程度差異性較大,高資產凈值的人群(80分位數水平)的金融資產水平與移動支付發展呈現正向關系,而在中部、西部和東北地區總資產水平與移動支付發展呈現負向關系。
五 結論與建議
以2017年CHFS中國金融家庭數據為研究標的,本文研究移動支付發展對居民家庭金融資產結構間的關系,并分別選擇普通最小二乘法(OLS)、Tobit模型、分位數回歸模型等方法。通過研究得出以下結論:
一是移動支付對居民金融資產結構產生重要而關鍵的影響。由于移動支付已在支付領域占據重要地位,對居民金融資產配置中產生較大影響,特別是對現金已經產生較大的替代作用,使用移動支付的居民會顯著減少持有現金的相對量。在移動支付快速發展的當今社會,隨著中央銀行數字貨幣的開展試點,下一步的推廣使用,可以預見現金資產整體持有量將大幅下降。
二是移動支付發展對提升金融資產的結構占比起到促進作用。移動支付有效提升了金融資產的整體流動性,使得居民可較為便捷地買賣金融資產,降低金融資產交易成本,特別是針對互聯網理財產品,移動支付的快速發展可有效提升居民家庭持有互聯網理財產品占投資性金融資產的比例,互聯網理財產品整體風險性較低、收益率具有一定比較優勢,使用移動支付的居民更傾向于將資產配置于互聯網理財產品。
三是移動支付在不同年齡段人群的運用和金融資產配置方面具有顯著的差異性。從年齡層次結構來看,各年齡層次中移動支付對居民金融資產占總資產的比例均呈現正向效應,但在40至60歲居民中,移動支付對金融資產占總資產比例的影響更為顯著,移動支付發展對中年居民更有效地配置金融資產提供了較大便利。
四是移動支付對促進不同地區金融資產流動縮小發展差距方面具有探索的價值。通過使用分位數回歸分析不同地區移動支付對居民資產結構的影響,我國東部、中部、東北和西部地區呈現較顯著的差異化特征,東部地區移動支付對居民總資產的影響呈顯著正效應,而中部、東北和西部地區影響相對較弱,特別是較富裕居民中呈現移動支付對總資產影響效應為負,反映出移動支付發展在我國各地區仍存在較大差異,東部地區移動支付整體發展較快,而其他地區移動支付發展空間仍存。同時,移動支付對不同地區金融資產的影響均呈正效應,說明相對于居民總資產而言,移動支付發展對金融資產的影響程度更大、影響范圍更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