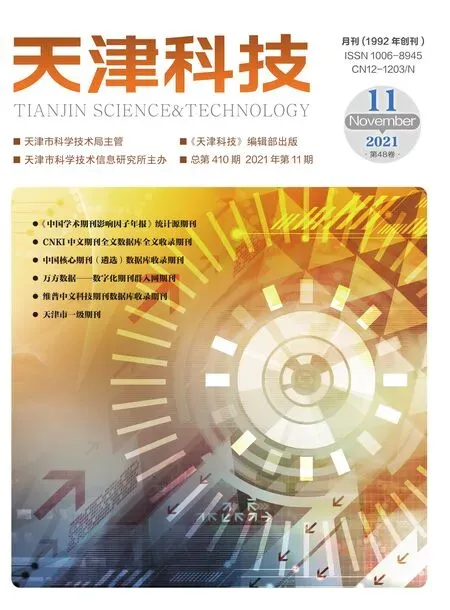天津城市發展與城市更新研究探索
楊唯一
(天津理工大學 天津 300384)
0 引言
隨著全球經濟和科技的快速發展,城市的快速擴張、人口聚集為城市的發展增加動力,但快速擴張和建設在為城市帶來便利和經濟利益的同時也會產生新的問題,如居住用地密集導致的潮汐交通壓力;傳統企業和工廠遷置城市邊緣,造成原址空置而產生的城市白地。如何合理利用這些區域并帶動周邊區域,成為近年來城市規劃中亟待解決的主要問題。
天津市作為我國直轄市之一,是連接首都和渤海灣的重要結點,地理位置優越,歷史文化悠久,陸路、水運交通便捷。如今在超一線城市的虹吸效應、環境保護等政策背景下,天津市各方面發展速度逐漸放緩,部分城區略顯蕭條。筆者曾以地中海沿線重要城市為例,對其發展中因快速擴張引起的諸多問題進行研究,并試圖借鑒謀求緩解天津市重點區域衰落的方法,進而運用城市更新理念復興該區域。本文以城市更新研究觀點結合天津雙城發展格局進行分析,并嘗試從規劃者和居住者角度進行探索和總結。
1 天津城市發展歷程
天津城市的發展歷史可分為4個主要時期,即:古代時期(581—1840年),商貿時期(1860— 1945年),繁盛時期(1949—2015年),轉折時期(2015—2020年)。
1.1 古代時期(581—1840年)
天津始建于隋朝大運河開通時期南北運河交匯處的三岔河口附近,唐朝中葉起成為南北糧、綢運輸的重要水陸碼頭,也成為軍事重鎮、鹽運稅收和漕糧轉運中心。
1.2 商貿時期(1860—1945年)
1860年天津作為北方開放的前沿城市和近代中國“洋務”運動的發源地,成為中國的金融商貿中心和當時北方第二大工商業城市。
1.3 繁盛時期(1949—2015年)
新中國成立后天津作為直轄市之一,鞏固了綜合性工業和商貿中心的地位。1994年濱海新區作為渤海地區的中心(含塘沽區、天津港、經濟技術開發區、保稅區),形成“一心三點”組合型城市布局結構[1]。并于2014年設立為自由貿易實驗區,實現海、鐵、空、陸多式聯運,成為當時北方最大的港口和華北第二大航空貨運基地。天津市雙城發展格局已顯現 雛形[2]。
1.4 轉折時期(2015—2020年)
在全球經濟下行的大背景影響下,天津的城市發展不可避免地難逃此劫。同時期天津市區居住、商業用地的更新和增加、大型交通設施的建設、大量的工廠從市區搬到郊區,在促進了城市快速擴張的同時,也使本就資金緊張的財政負擔初見端倪。
2 天津濱海新區發展歷程
天津市濱海新區在將近40年的發展中,從默默無聞的鹽灘變成北方經濟發展的重要口岸。其面積占天津的1/5,人口占天津的1/7,生產總值最高保持在環渤海地區的10%左右。天津濱海新區的發展歷程可分為3個主要時期。
2.1 開發建設時期(1984—2005年)
1994年的基本構想是“以天津港、開發區、保稅區為骨架,現代工業作為重要基礎,外向型經濟作為主要導向,著重發展商貿、金融、旅游,完善基礎設施配套,注重服務功能齊全,成為高度開發現代化經濟新區”。至2005年,已利用180多億美元外資,落戶世界500強企業70余家[3]。隨著新區的發展,開發了1199km2的農田、荒地和灘涂進行建設。
2.2 平穩增長時期(2005—2015年)
2005年,在“十一五”規劃中納入國家發展戰略,濱海新區成為國家重點支持開發的國家級新區。在《天津市城市總體規劃(2005—2020)》中,提出“一軸、一帶、三城區”的城市空間發展結構[4]。2009年國家投資1.5萬億元建設東疆港保稅區、南港工業區、于家堡和響螺灣中心商務區等重大項目。濱海新區于2014年12月獲批為北方第一個自貿區[5]。
隨著新區經濟的繁榮發展,城市快速擴張導致的城市資源浪費也略露端倪,于家堡、和響螺灣中心商務區處于停工狀態,空置建筑隨處可見。
2.3 雙城轉型時期(2016年至今)
受全球經濟下行和國內金融業進入收縮期的影響,濱海新區商貿發展逐漸減緩,2016年GDP縮水1/3,只剩6654億元。面對京津冀霧霾影響、環保限產、服務業疲軟等問題,GDP增長受到嚴重拖累。從于家堡和響螺灣的發展狀況來看,政府與房地產商的開發預期遠未達到,供需關系存在顯著落差。寫字樓無人租賃,投資負債無力償還。城市經濟結構以國企和重工業偏多,雖然新興產業增速較快,但實體重工業占比多,外資也以制造業為主,產業附加值較低,經濟結構轉型困難。
3 城市擴張及其問題分析
隨著時間的推移和快速發展,天津已處于市區與濱海新區兩地資源競爭和雙倍基礎設施建設的多重壓力之中。由于兩地邊界不斷向外擴張,忽略了交通不便捷、基礎設施負擔大的問題。當地政府意圖通過修建輕軌9號線作為公共交通,和兩條高速路將兩區連接起來,卻未能對9號線起始站點兩端的換乘交通予以足夠重視,導致兩地通勤不便、通勤成本增加和交通擁堵等問題,使看似相鄰僅40km的路程,平均單程通行的時間成本達到60min以上(可對比天津至北京120km路程通行30min時間)。
通過2019年底的客流統計,天津軌道交通運營的6條線路中,市區內主要貫穿主城區及各個重要交通樞紐的地鐵1、2、3號線平均每公里約1萬人次[6],而同期運營的地鐵9號線高峰時段客流與1、3號線相比,呈現明顯差距。首先,軌道交通站點周邊的土地開發配置不合理是影響客流偏低的主要因素;其次,站點與周邊道路、公交線路換乘銜接不暢(僅為9%),低于國內城市20%的平均水平[7];最后,導視系統、票務運營管理系統以及站點內外的配套設施不完善等。
由于天津城市更新是屬于存量地區的再次開發,與一般的城市開發建設不同,需要城市管理者具備較強的統籌和創新能力,但天津政府部門沒有獨立形成城市更新的管理部門,而是由市規劃部門歷史街區負責部門進行建設管理。國土主管部門不僅要負責歷史風貌建筑的保護,還承擔老舊區域的騰遷整理和房屋綜合整治、修繕等一系列繁雜的工作。城市更新類項目概念較新,牽扯各相關部門,以管理意式風情區為例,由于前期研究沒有充分考慮到原址居民為區域帶來基本活力的問題,將原址居民全部遷出,將原居住用地全部整合變更為商業用途,不僅增加了項目成本,而且對后續勞動力和交通上的需求增加了難度,加上招商和區域定位不夠明確等因素,使該區域人氣不足,商業空置,沒有取得預期的激活帶動效果。
在天津工業廠區的轉型改造中,高昂的搬遷費用和廠區改造項目的成本增加了后續運營難度,形成入駐門檻高的問題。由于城市更新政策的支持力度小,相應的投入資金少,導致多數工業廠區改造的功能策劃和主題運營是由政府部門委托開發商用周邊土地置換作為投資回報的形式進行改造投資,造成工業廠區的改造利用缺乏實用性或空置,甚至部分具有區域特色或歷史遺存建筑面臨被拆除命運。而改造完成的后續運營許可審批因缺乏政府系統性支持或運營限制過多,導致運營和發展受到局限,從而進入惡性循環的境地。
如果任其發展下去,短期內會形成兩區域相對孤立的城市發展結構,從長遠看來,將導致天津市區東部形成更多空置區域,影響城市有序發展。空置區域和廢棄建筑極易成為城市廢棄物堆放和安全不穩定因素頻發區域,成為社會問題惡化的主要誘因。
4 雙城發展現狀及其綜合解決方法
通過調研天津市區至濱海新區沿線的現狀,發現部分地區空置的形勢已存在相當長的時間。位于天津市中心城區和濱海新區核心區之間必經之地的東麗區,其地理位置和城市功能發展優勢突出[8]。
政府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試圖將沿路部分空置區域轉換為臨時防護綠地來提高該片區尷尬的境地。但想要緩解這些問題,還需對該區域進行改造,使其得到合理的利用。對該區域的城市更新項目還應從城市發展的角度進行分析,對城市邊緣區域的發展進行合理的配置,結合交通設施統籌解決。
近年來,新型以交通節點為核心的TOD綜合體(Transit-Oriented Development),在新一、二線城市的試點項目實施效果良好。TOD綜合體作為以公共交通為導向的樞紐綜合體,公共交通為核心結構,站點為中心,以5~10min步行路程(400~800m)為半徑合理滿足居民的全天候立體出行需求,形成復合、立體、便捷化的綜合型開發,能夠對站點周邊地塊產生有益的催化作用[9]。
天津市區公共交通設施逐漸完善的同時,考慮結合地理優勢和避免盲目擴張的形式解決。運用TOD綜合體設計要素,從城市更新的層面將城市資源進行整合,結合周邊業態交通流線和資源價值的整合等;高效合理利用土地,將空置區域進行合理置換或再利用,建設高品質、注重生態的宜居環境,從而帶來更加高效的土地價值和社會活力價值;通過對區域周邊業態的整合,著重體現空間和人行為的交互。合理配置多元交通換乘系統,設置私家車和共享單車等公共停車系統,結合公交巴士樞紐站和軌道交通,使周邊居民更便捷地換乘各種公交工具進入市中心或其他城區;完善立體步行系統,形成便捷的步行層級體系,合理組織各類交通流線,緩解因軌道交通站點而形成的城市割裂問題,加強區域持續發展動力;明確空間設計的精髓,設置開放空間作為休閑活動區域,成為公共空間的疏導集散器,形成區域的獨有特性。例如,可結合燈光、標識或構筑物,進行設計和包裝,在承擔立體交通的同時,成為吸睛和帶動流量的關注點,達到激活該區域的目的。通過此方法不僅可以保留當地特色,塑造區域的可識別性,而且可以為沿線的站點增加活力,同時完善商業配套,再通過立體步行連廊對接已有商業區域,緩解就業壓力,增加當地居民收入,從而構成具有區域文化的IP,匯聚人氣帶動周邊發展。
城市發展與擴張中,空置區域和荒廢建筑的存在是必然現象,無需直接消除負項資源。如何運用新興發展模式和理念合理利用城市資源,城市管理者和設計師需要了解、嘗試預測其發展趨勢,盡早發現問題并進行資源整合,以期對城市資源的有效衡量和利用,為其發展提供積極的建議。城市更新可為城市的發展帶來活力與新契機,應當把城市發展和城市更新作為一個整體考量,而不是孤立地發展部分區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