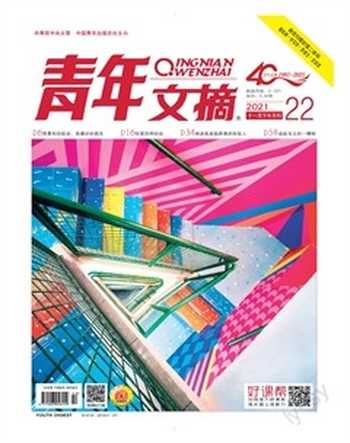祝君四種好運
萬維鋼

人人都希望能有好運氣,但是你知道嗎?好運有四種,你真正想要的,并不是最尋常的那一種。
這是神經科學家詹姆斯·奧斯丁提出來的一個分類法。他說的本來是搞科研這門業務中的運氣,但完全適用于從吃喝玩樂到功名利祿一切領域。
理解這四種運氣,你會對命運有更深的認識。
1
第一種好運可以叫作“盲目的隨機性”。四個人打牌,為什么你手里的牌最好?那么多人買彩票,為什么老王中了巨獎?這就是純隨機性。命運之神并不知道、也不在乎誰是誰,隨便一扔,誰收到就是誰的。
尋常人們追求的好運,在微博轉發錦鯉、到寺廟求賜福,求的就是這種隨機性。這種好運的特點在于它完全不可控,只能等著。可是真正的好東西怎么能這么被動地等著接收呢?你得能做點什么才行。
2
第二種好運是“跑出來的機會”。要是從來都不逛商場,當然就碰不上那波特價;要是平時很少能見到異性,當然就很難跟人自由戀愛;要是沒有出現在風口現場,當然就只能看著別的豬在那兒飛。
世人只知道盼望從天而降的第一種好運,殊不知這種自己跑出來的第二種好運才是最常用、最有用的。為什么那些最厲害的科學家、發明家和藝術家有那么多好想法?因為他們嘗試過很多很多,你看到的只不過是其中最好的那些。這就如同如果一個人去過很多地方,他自然就會去過好地方。那些好東西是他們“跑”出來的。
心理學家迪恩·西蒙頓專門研究各種創造性人物,他找到的統一結論是這些人其實都是用數量確保質量。一個人所能找到的有影響力的、成功的創意數量,同他想到的創意的總數成正比。巴赫有超過1000 部音樂作品,愛迪生有1093 項專利,畢加索創作過1800 幅油畫、1200 件雕塑、2800 件瓷器、1.2 萬張圖紙,還有數不清的版畫——其中你能記住的、被世人認可的,才有那么幾個而已。
創造的基礎是勤奮。一個想法行不行,你得做過才知道。你得嘗試過很多很多想法才能找到一個行的。不過搞創新并不是純體力勞動,你還需要第三種好運。
3
第三種好運是“有準備的頭腦”。微生物學家路易·巴斯德有句名言:“機遇只青睞有準備的頭腦。”關鍵詞是“頭腦”。同一個東西擺在所有人面前,只有有頭腦的人能看出來它的價值。
同樣看一場藝術展,外行只看到了熱鬧,內行卻能看到門道,有準備的頭腦才可能收獲下一個項目的靈感。如果頭腦里沒有相關知識和思維模型,再好的東西擺在面前,你也不知道該看哪里、該怎么看,你就不會跟它發生化學反應。
舉個例子,亞歷山大·弗萊明當初是怎么發現青霉素的呢?弗萊明想要觀察葡萄球菌的變異情況,把培養皿在室溫下放了幾天。中間可能是有一點霉菌偶然掉在培養皿里,他清洗培養皿的時候發現那一個小區域內的葡萄球菌沒有生長,于是判斷那個霉菌里有什么東西可以殺菌。
這聽起來很像是第一種好運,老天垂憐,給弗萊明演示了一遍青霉素的作用。然而這里的關鍵其實是第三種好運。在此之前,弗萊明就已經做過類似的實驗,他曾經以為自己感冒時候的鼻腔黏液里有能殺菌的物質,他一直在期待培養皿里發生那樣的變化。同樣的現象如果發生在別人面前,只會被當作污染。
第三種好運需要知識,而知識有個復利效應。就好像攢錢一樣,你的學問、經驗、生意、社交網絡越大,敏感度就會越高,就越有可能注意到新的機會。
那么積累到一定程度之后,你就會迎來第四種好運。
4
第四種好運可以稱之為“人設的吸引力”。它說的是因為你的特殊人設,不用你去找,而是自動來找你的好運。
比如,你的專業是考古學。當你還是個研究生的時候,你整天盼望能趕上一次重大考古現場,可是有大事根本用不到你,你連寫博士論文都找不到過硬的素材。但是如果有一天你已經成了西漢考古的頭面人物,這一塊全國就你最懂,那就不是你出去找素材,而是素材來找你了。哪里新發現一處漢代遺址、誰誰得到幾片竹簡,你想不看都不行,這篇論文你必須寫。
但是請注意,最有吸引力的人設,并不是資格和職位,也不是排名,而是你身上的某種特殊性。比別人做得好還不行,最有意思的人設是擁有別人沒有的東西。
第一種好運是人人都有的,最不可控,用處也最小。
第二種好運是由行動決定的,任何時候都可以爭取,用處也最多。
第三種好運取決于你的知識積累,不能臨時突擊得到,比的都是以前的功夫。
第四種好運卻是自我奮斗和歷史進程共同的產物,你不努力不行,光努力也不行,它取決于使命的召喚。
重大成就往往是四種好運綜合作用的結果,都要有一點隨機性,有一點主動性,有一點特殊性,有一點客觀性。想明白哪些是可以爭取的,哪些是必須等待的,哪些取決于別人,哪些取決于自己,我們也許會多一點對命運的主動權。
祝你取得四種好運。
(摘自“得到”app,張云開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