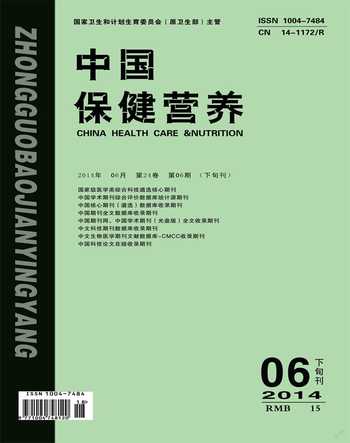CT室檢查中的護理干預分析
張鳳英
【摘要】 目的 探究護理干預手段在病人CT檢查中的有效性。方法 選取2012年11月——2013年11月期間于我院接受CT檢查的患者210例,采用隨機分組方式分為對照組和實驗組各105例。對照組患者接受一般護理,實驗組患者接受綜合護理。對比分析兩組患者的CT圖像質(zhì)量、掃描時間及患者滿意度。結(jié)果 經(jīng)綜合護理干預措施后,實驗組患者CT檢查的圖像質(zhì)量、患者滿意度明顯高于對照組,實驗組患者的掃描時間明顯少于對照組(P<0.05)。結(jié)論 應用綜合護理手段,對提高CT檢查效果及患者滿意度具有重要意義。
【關鍵詞】 CT室檢查;護理干預;有效性
文章編號:1004-7484(2014)-06-3270-01
近年來,隨著影像醫(yī)學技術的發(fā)展和進步,CT檢查在臨床診斷中應用日益廣泛[1-3]。CT檢查由于其成像快、效果安全且圖像精準清晰,所以CT影像成為臨床治療的可靠依據(jù)。然而,在患者實際的CT室檢查中,由于準備不足、配合不當或檢查時情緒狀態(tài)不穩(wěn)定,導致CT影像質(zhì)量欠佳,影像后期病癥的診斷。因此,本研究結(jié)合實際問題,對進行CT檢查的患者采取綜合護理措施,效果顯著,現(xiàn)將其詳細報道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選取2012年11月——2013年11月期間于我院進行CT檢查的患者210例,男性共144例,女性共66例;年齡分布:6-68歲;患者檢查部位為上腹部或頭顱,且均為首次進行CT檢查,采用隨機分組方式將樣本分為對照組和實驗組各105例。對照組患者男性76例,女性29例,平均年齡40.58.1歲;其中進行上腹部檢查患者83例,頭顱檢查22例。實驗組患者男性68例,女性37例,平均年齡43.67.17歲;上腹部檢查患者78例,頭顱檢查患者27例。經(jīng)統(tǒng)計學分析,對照組和實驗組的一般資料之間無統(tǒng)計學差異(P>0.05),符合進行本研究的條件。
1.2 護理方法 對于對照組CT檢查患者,護理人員給予常規(guī)護理;對于實驗組患者,護理人員給予綜合護理,具體護理措施如下。
第一、CT檢查前護理人員探視。由于患者均為首次接觸CT掃描,容易產(chǎn)生緊張焦慮心理和情緒,特別是擔心掃描設備對其身體的傷害或掃描后顯示病情嚴重而對CT掃描產(chǎn)生抵觸。因此,護理人員應該進行掃描前的探視,給患者講解CT檢查的意義和作用、掃描的過程及對身體的影響,讓患者減輕心理負擔,做好掃描前的充分準備。
第二、CT檢查室中護理。首先,護理人員詢問患者有無相關禁忌癥或者藥物過敏反應,向患者和醫(yī)生明確掃描部位,囑咐患者在掃描時遵從醫(yī)生指示并做好防輻射準備。進行CT掃描時,先定位平掃,然后注射靜脈對比劑[4]。注射時可能會使患者產(chǎn)生惡心等癥狀,護理人員應及時告知這是由于藥物濃度較高而引起的正常反應,不需要擔心。此外,護理人員注意患者體位是否移動、情緒和狀態(tài)是否正常,出現(xiàn)異常時及時告知醫(yī)生。
第三、CT檢查后護理。CT檢查完成后,由于藥效時間長,患者身體可能會出現(xiàn)一定的不適癥狀,護理人員應告知患者不可立即離開檢查室,而應在檢查室等待觀察月半個小時,在不適癥狀得到緩解或無明顯不適時方可回到病房。護理人員定時巡查病房,一旦患者出現(xiàn)胸悶、氣促、出冷汗等癥狀時,立即通知醫(yī)生前來診斷。
1.3 評價標準 本研究采用CT檢查圖像質(zhì)量、CT掃描時間及患者滿意度作為評估綜合護理措施有效性的評價指標。其中CT圖像質(zhì)量分三種:無移動偽影、單層移動偽影及多層移動偽影。CT掃描時間分上腹部掃描和頭顱掃描獨立統(tǒng)計,記錄各例患者掃描時間,最后以平均值表示。患者滿意度為CT掃描后護理人員在進行問卷或詢問得到結(jié)果后在進行統(tǒng)計的數(shù)據(jù),分值越高,滿意度越高。
1.4 統(tǒng)計學方法 運用SPSS19.0統(tǒng)計學軟件來處理統(tǒng)計數(shù)據(jù)。計數(shù)資料用百分率(%)來表示,采用x2驗,計量資料采用T檢驗,P<0.05時差異具有統(tǒng)計學意義。
2 結(jié) 果
2.1 兩組CT檢查圖像質(zhì)量比較分析 患者在接受綜合護理措施和,檢查圖像的無移動偽影例數(shù)達到87例,占83%,明顯高于對照組中的55例,P<0.01;經(jīng)綜合護理后,患者檢查圖像的多層偽影例數(shù)僅占10%,明顯少于對照組的20%,P<0.05。由此可見,經(jīng)綜合護理措施干預后,患者CT檢查圖像質(zhì)量明顯提高,見表1。
3 結(jié) 論
從表1和表2結(jié)果可以看出,CT室檢查中應用綜合護理干預手段,不僅能夠減少CT掃描時間,提高掃描圖像的質(zhì)量,還能夠提高患者對檢查過程體驗的滿意度,這即有利于病癥的臨床醫(yī)療診斷,也有利于提升醫(yī)院服務質(zhì)量和聲譽。
做好CT室護理工作,可使患者對結(jié)果滿意,同時對診斷也起著重要作用[5]。在CT室檢查中應用綜合護理干預手段之所以能取得良好的效果,原因在于綜合護理措施所具有的獨到的優(yōu)勢。一、通過護理手段可以幫助患者建立良好的心理狀態(tài)[6]。檢查前后對檢查過程及知識的講解、對患者不良心理狀態(tài)和情緒的疏導,能夠極大地改善患者在CT檢查時的表現(xiàn)。二、護理人員的全程護理能夠保證檢查的正常進行。及時有效地對患者采取有利手段,避免患者的不規(guī)范或異常行為影響掃描圖像的質(zhì)量。三、護理人員與患者建立的緊密聯(lián)系能夠提高患者應對疾病的信心,為檢查及檢查后的病情診治做好準備,同時提高患者在檢查過程中體驗的滿意度。
綜上所述,在CT室中應用護理干預措施是提高CT檢查質(zhì)量,為患者的診斷提供有效可靠依據(jù)的重要手段,值得臨床上更為廣泛的推廣和應用。
參考文獻
[1] 丁玉環(huán),孫瑞麗,陳暉,等.急診與危重患者CT掃描的護理對策[J].中國現(xiàn)代藥物應用,2010,04(17):204-205.
[2] Sadrozinski H F-W,Johnson R P,MacAfee S.et al.Development of a head scanner for proton CT(Conference Paper)[J].Nuclear Instruments and Methods in Physics Research,Section A,Accelerators,Spectrometers,Detectors and Associated Equipment,2013,699:205-210.
[3] 余春蓮.顱腦損傷438例CT掃描的護理[J].中國誤診學雜志,2012,12(16):4459-4460.
[4] 曾彩媚.CT增強檢查中的護理干預[J].中國醫(yī)藥科學,2012,02(7):122-123.
[5] 劉一筠.CT掃描的護理體會[J].臨床合理用藥雜志,2010,03(17):139-139.
[6] 左玲芝,何海洪,陳永莉,等.護理干預在CT增強掃描檢查中的效果觀察[J].國際護理學雜志,2013,32(8):1668-16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