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企不斷爆雷,購房者的最壞結果是什么
劉寶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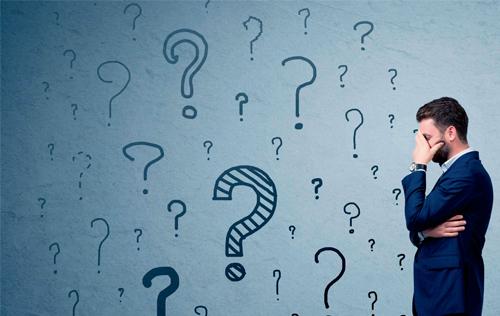
很多人都沒想過,地產行業有一天會變得如此風聲鶴唳。
國慶第四天,花樣年突然宣布債務違約。作為一家行業排名在60名左右的百強房企,這樣的消息令很多人感到詫異,而其未能償還的金額僅為2.05億美元。
違約額度并不算大,這也正是外界難以理解之處。
相較于花樣年的行業規模和資金實力,實在不應該出現這樣的失誤。然而更要命的是,花樣年承認在財報中漏報了有擔保的1.5億美元債券,這讓原本備受質疑的房企債務危機進一步加劇。花樣年、泰禾、華夏幸福、恒大……
債務違約的名單在不斷變長,業內外都在猜測下一個會是誰,抗風險能力較強的主流房企尚且如此,足以說明房地產行業真的進入了至暗時刻。
01房企深陷破產危機
破產意味著法律關系的終止,也意味著債權債務關系的終結,越來越多的房企出現債務違約或破產,無疑是一個行業陷入危機的最顯著特征。
根據人民法院數據,截至2021年10月11日,提交破產文件的房企數量高達310家,而這一數字去年是499家,2019年是528家。房地產行業從2017年開始進入深度調控以來,危機不斷暴露。
重慶市原市長黃奇帆早在2019年就說過,今后十幾年,基于房地產業高質量轉型要求和開發總量降低的趨勢,房地產開發企業必然會有一個大幅度減量萎縮的過程,會減掉三分之二。中小房企的抗風險能力本身就弱,如今房地產行業債務違約和破產的趨勢已經延伸到主流房企,且房企爆雷的速度正在加快。
9月以來,新力控股、花樣年、光耀集團先后爆雷或破產,爆雷速度明顯加快。“目前房企的現金流被全方位掐斷。”一位規模房企的北京負責人表示,海外資本市場都在拋售地產股和債,境內嚴控負債規模,唯一合法的融資渠道銷售回款受困于按揭額度,賣出去的房子收不回款。
中證鵬元房地產評級部高級分析師劉潔筠認為,短期來看,隨著違約房企的增加,特別是大型房企的違約,加大了房地產行業的融資難度,增大了房企的經營壓力和財務壓力。
在資金緊張的背景下,房地產企業明顯收縮了投資力度。同時,2021年下半年到2022年,房地產行業仍有較大規模的債券待償付。劉潔筠認為,若較為困難的融資環境持續,不排除有新的房企發生債務違約。
無論是債務違約還是破產,房企資金流斷裂,都將對行業產生巨大的危害,比如,導致樓盤停工,承包建設的農民工可能也拿不到工資,債券投資人以及銀行等機構更是面臨巨大的投資損失。
02債務違約意味著什么?
實際上,房企債務違約是風險暴露的第一步,也意味著房企進入生死存亡的待定狀態。
從法律上講,債務違約如果無法得到解決,后續面臨的結果有兩種,一種是各方都不愿意看到的破產。根據《破產法》的規定,企業不能清償到期債務,并且資不抵債,兩個條件同時具備才構成破產原因。
據北京某律師事務所高級聯席合伙人覃霖介紹,破產最大的特點是企業責任的終結,企業僅以它剩余的破產財產作為全部的責任財產來清償所有的債權人。另一個方向就是破產重組。
根據《破產法》,重整作為企業破產的一個程序,是指具有一定規模的企業出現破產原因,為防止企業破產,經企業債權人或者債務人向法院申請,對該企業實施強制治理,以使有復蘇希望的企業,通過重整程序,避免破產清算的法律制度。
覃霖表示,重組大概有三種方式,一是有望重組類,雖然債務違約,資金鏈斷裂,但公司手握核心資產,理論上資產大于債務。比如,泰禾這類企業能否成功要看市場、商機、談判、投資人和領導層預期。
二是比較艱難的一類重組,典型特征是資不抵債,企業也想走破產,但可能政府不希望,因為很多老百姓的問題不好解決,因此,還是要盡量救。
三是國企或央企介入,重組或者把企業變成國有化。覃霖認為,這種重組更多是一種形式,考慮的價值因素不光是財務本身,還會涉及社會穩定及地方經濟。
覃霖認為,滿足上述條件,重組成功的概率就大。但問題是,外界對當前樓市普遍缺乏信心。一位不愿具名的企業人事表示,現在有能力接手的企業非常少,大部分房企的資金都比較緊張。
融創中國董事長孫宏斌在8月的業績會上直言:“目前所有的企業無論你開什么價,我都是沒有辦法并購的,因為我還要同時并購你的債務。”“總結來看,一部分企業要進入破產,一部分進入重整,重整部分當中不排除有一部分最后重整不起來,又會再次進入到破產當中。”覃霖判斷,房地產會在2021年2022年再進行一輪洗牌和淘汰。
至于結局,則取決于房企自身的資產質量。覃霖認為,無論多么復雜的重組方案,最終一定是它的資產,包括各項資產,有形資產如土地房產,無形資產如商譽。上述負責人表示,當前很難判斷違約房企未來的走向,因為其資產質量有待第三方機構的排查和評估,需要時間才能最終清楚。
03購房者權益優先保護?
李斌是一名購房者,他原本特別開心的等待著2020年最后一天的到來,因為按照開發商的承諾,這天是他收房的日子。
為了買新房,李斌賣掉了僅有的一套房,全家人住進了出租屋,就在家人盼著收房的時候,項目開發商爆雷了,由于資金鏈斷裂,他的房子被迫停工。
眼看交房無望,李斌踏上了漫長的維權之路。一方面,他試圖厘清項目資金情況,比如項目抵押給了誰,還有多少資金,項目建設需要多少資金。
另一方面,他聯合其他業主,試圖跟政府溝通。然而,作為購房者,他的力量非常有限,時間過去了一年多,他的房子仍在坑里,沒有絲毫進展。
由于爆雷的房企陸續增多,像李斌這樣的購房者還有很多,如果他們房子的開發商出現債務違約,他們該怎么辦?還能否收到自己的房子?
這個問題并不好回答,大多數情況要因具體項目情況而定,但根據小編的調查和梳理,購房者可能面臨的情況有以下幾種:
首先,如果經過重組,違約房企恢復經營,那購房者就無需擔心,最多是項目交房時間拖延,但肯定可以收到房子。
其次,如果重組失敗,房企最終走向破產,那購房者能否拿到房子,就存在一定的未知。
尤其,由于破產重組是一項非常復雜的工程,而且,從法律上講沒有明確的時間線,針對債務違約,債權人可以上訴,但欠債多長時間進入到法定破產程序,在法律上沒有時間限制。
這也是令很多購房者感到無奈的地方,為此,很多購房者擔心,房企是否會故意拖延不復工。
覃霖認為,一般不會,資金成本其實就是時間成本,假如年化利息是8%,一旦逾期,就變成逾期利息,逾期罰息翻倍,所以大多違約房企的老板都特別著急。
實際上,雖然解決問題的時間因項目而已,但購房者的權益大多數情況下還是可以得到保障。
相對其他行業,房地產行業比較特殊,有購房人優先權。根據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釋,消費型購房者的優先權優于建設工程優先權,而建設工程優先權又高于抵押權。
對于款項的界定,最高人民法院將消費者購房人的支付比例限定在50%。覃霖表示,如果滿足條件,比如說已簽合同、付款超50%、名下唯一住房,就具備購房人優先權,需要最先保護購房者的權益。
04購房者可能面臨的最壞情況
雖然有法律權益,但執行程度還存在不確定性。
如果房子已經具備交付條件了,購房者的優先權就能落地;如果不具備交付條件,可能也沒有辦法,能否拿到房子,還要看具體的項目情況。
最壞的情況就是房企資產流拍,舉個例子,當年的鄂爾多斯被稱為鬼城,資產拍不出去,錢拿不回來,人也住不進去,這是最壞的情況,資產就在那爛著,相當于完全打水漂。
如果面臨最壞的情況,破產房企的資產無人接盤,無法籌措資金建房,購房者是否還有出路?
一位資深律師表示,拋除所有的法律法規,很多爛尾樓盤能否得到妥善解決,還有一個重要的影響因素就是依靠政策。
一般情況下,房地產項目爛尾,當地政府都會介入。
比如,根據媒體公開報道,自恒大流動性問題爆發以來,在監管層統一協調下,部分地方成立由省級政府牽頭、市縣級政府為主體的恒大風險化解專班小組,計劃幫恒大部分停工項目復工。
但政府最終能否承接,也要看當地政府的資金承載能力和違約房企的項目數量,也就是說,購房者能否收房,政府的實力也至關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