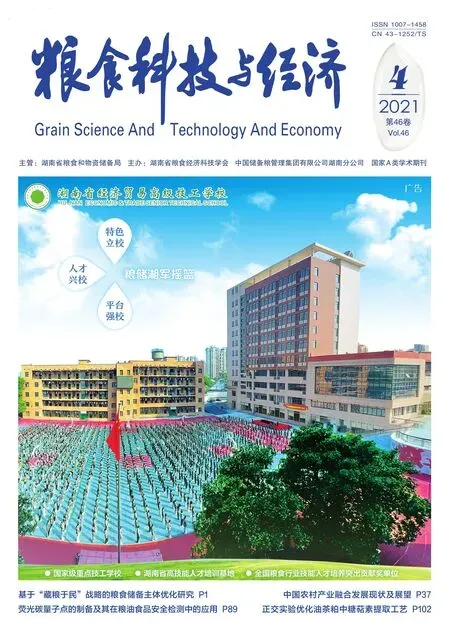新型職業農民培育政策需求與政策優化
吳易雄
(1.山西農業大學 公共管理學院,山西 晉中 030801;2.湖南開放大學 終身教育指導服務中心,湖南 長沙 410004)
2012年以來,湖南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視新型職業農民培育,每年的省委一號文件都強調要大力培育新型職業農民。目前,國內學者以湖南為例研究新型職業農民的成果較豐富,如鄭海燕等[1]提出了新型職業農民培訓的“湖南模式”;吳易雄[2]基于湖南株洲、湘鄉、平江三縣市的調查,探討了城鎮化進程中新型職業農民培養的困境與突破;米松華等[3]基于浙江、湖南、四川和安徽的調查,研究了新型職業農民的現狀特征、成長路徑與政策需求;王剛等[4]基于湖南涉農高職院校的實證分析,研究了涉農高職院校培訓新型職業農民的戰略路徑;湯旺利[5]基于湖南“湘農科教云”平臺運用與推廣,提出了開啟新型職業農民線上培育新時代;王靜怡[6]研究了基于高職教育資源共享的湖南新型職業農民培育機制;吳易雄等[7]基于湖南省平江縣的調研,分析了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下的新型職業農民培育問題;劉寶磊[8]研究了鄉村振興戰略視域下湖南新型職業農民培育體系的績效評價;譚星[9]探究了湖南農村電商新型職業農民勝任素質。但有關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背景下湖南新型職業農民培育狀況、政策需求及政策優化研究甚少。為此,筆者赴湖南省新型職業農民培育縣及培育機構開展深度調研,通過面對面與農民交流,走進農業農村部門、農業院校進行座談,深入鄉村了解情況,走訪農民合作社、家庭農場、農業企業等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組織217名新型職業農民開展問卷調查等方式,對新型職業農民培育狀況、政策需求和政策意見建議進行了調研,并作了深入思考。
1 湖南新型職業農民培育特征
1.1 新型職業農民培育個體特征
從年齡看,46~59歲最多,36~45歲次之,16~35歲較少,60歲以上最少。說明湖南農民以中老年為主,青少年為輔。從性別看,男性居多,女性較少。說明男性務農成為主力軍。從學歷看,大專以上較多,其中博士、碩士占了一定比例,高中以下居多,小學以下最少。說明湖南盡管學歷層次在不斷提高,但低學歷農民仍占多數。從從事的主要行業看,種養業是主業,其他行業是副業,加工、服務業比例低。說明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度低,農村加工業、服務業發展空間大。從現在掌握的主要技術看,懂種養技術的最多,懂其他技術的次之,懂信息技術、農產品銷售技術、農用機械技術、質量安全技術、貯藏加工技術的均較低。說明亟需提升農民的貯藏加工技術、質量安全技術、農用機械技術、農產品銷售技術、信息技術。從現在最缺的能力看,規模生產比例最高,經營管理和其他能力比例較少,媒體應用和組織溝通比例均最少。說明要加強農民規模生產和市場營銷能力提升。
1.2 新型職業農民培育制度特征
從對三農政策的了解情況看,不完全了解比例最高,完全了解比例居中,完全不了解比例最少。說明農民對三農政策的了解程度整體上不高,及時宣講三農政策需要提到重要日程上。從知道如何了解三農政策看,不完全知道比例最高,完全知道和完全不知道比例相當。說明農民對三農政策了解的渠道不暢通,需要開辟多種渠道讓農民了解三農政策。從所在地政府對三農政策落實情況看,沒完全落實比例最高,完全沒落實比例略高于完全落實。說明需要督促當地政府落實三農政策,才能保證黨中央、國務院和省委、省政府出臺的政策效果。從發展產業得到政府扶持看,超過半數的農民沒完全得到,完全沒得到的比例也較高,而完全得到的比例很少。說明政府扶持產業發展需要全覆蓋,廣大農民的產業發展積極性才能充分激發出來。
1.3 新型職業農民培育效果特征
從主要通過何種渠道獲取農業知識看,手機、電腦等媒體是首選,其次是自身實踐總結,再次是新型農業經營主體,而通過農技推廣部門、農業院校、親朋經驗交流、其他渠道獲取農業知識的很少。說明新媒體是農民獲取農業知識的主渠道,需要加大農技推廣部門、農業院校、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等優質資源傳播農業知識的力度。從當前教育培訓存在的主要問題看,最大的問題是理論與實踐脫節,其次是教育培訓次數較少,再次是教育培訓時間不適宜、監督檢查不到位、教育培訓質量差。說明農民傾向于理論結合實際的教育培訓,尤其需要的是能解決實際生產經營管理問題,通過增加教育培訓的次數和加強監督檢查,提升教育培訓的質量。從了解三農政策的主要渠道看,首選看新聞,其次是其他渠道,再次是參加教育培訓,聽別人說和讀報紙比例都很低。說明教育培訓不是農民了解三農政策的主渠道,因而在農民參加教育培訓中,需要加大三農政策宣講力度。從接受康養農業等農業新業態知識教育培訓看,超過半數完全接受,完全沒接受的比例較低,沒完全接受的比例次之。說明農民接受康養農業等農業新業態知識教育培訓的意愿強烈。從最希望通過教育培訓獲取的知識看,首先是生產技術,其次是社會化服務技術,再次是經營技術、管理技術、三農政策,最后是其他知識。說明農民將生產技術擺在第一位,將社會化服務技術擺在第二位,因為這兩項技術在農業產業鏈過程中至關重要,因而農民最希望通過教育培訓掌握這兩項技術。從最需要的教育培訓方式看,首選現場指導,其次是互動教學,再次是一對一咨詢、課堂講授,最后是網絡學習、專題講座及其他方式。說明農民最需要現場指導的教育培訓方式,農民遇到什么問題,教師就指導和解決什么問題,可收到立竿見影的效果。從希望通過教育培訓的目的看,最多的是引領農民創業致富,其次是掌握一門以上技術,而取得教育培訓證書及其他目的的比例很少。說明農民的大局意識很強,旨在助力鄉村產業振興。從新型職業農民培育最重要的教育培訓階段看,普遍認為社會教育和中等教育是最重要的階段,基礎教育次之,再次是高等教育,幼兒教育最少。說明抓好社會教育和中等教育對新型職業農民培育至關重要。
1.4 新型職業農民培育需求特征
從新型職業農民培育最需要的扶持政策看,首要的是技術跟蹤服務,其次是小額信用貸款、完善基礎設施、農產品統購統銷,再次是農業保險全覆蓋、土地集中流轉和其他扶持政策。說明農民最需要專技人員提供技術跟蹤服務,解決小額信用貸款、完善基礎設施、農產品統購統銷問題。從新型職業農民培育最需要政府購買服務的類型看,首選技術服務,其次是農產品,最后是人力資源。說明技術服務和農產品是農民在生產和銷售中遇到的兩大難題,最需要政府幫助解決。從新型職業農民培育最需要社會力量介入看,首選工商資本,其次是土地流轉,最后是績效評估。說明農民最關注的是工商資本和土地流轉,解決錢從哪里來,力往何處使的問題。從新型職業農民培育最需要的文化發展看,現代文化最多,農耕文化次之,而傳統文化和非遺文化最少。說明在新型職業農民文化發展中,農民對傳統文化和非遺文化的需要很少。從新型職業農民培育最需要的職業認同看,經濟效益好是首選,其次是勝任力強,最后是社會地位。說明農民追求的經濟效益高于社會效益,發展經濟是農民的硬核。從新型職業農民培育最需要的財政補貼類型看,種植補貼是首選,其次是社會化服務補貼,而養殖補貼與農產品加工補貼較少。說明農民亟需要全面解決的兩大補貼是種植補貼和社會化服務補貼。從新型職業農民培育最需要的社會保障看,創業保險居首,其次是養老保險,再次是醫療保險和教育保險。說明農民的創業熱情很高,但面臨的創業風險也很大,農民能擁有養老保險也是農民的心聲。從新型職業農民培育最需要的產業扶持看,產業項目最高,產業技術次之,產業設施最少。說明產業項目是農民發展產業的重要支撐。從新型職業農民培育最需要的土地流轉方式看,村“兩委”統一流轉比例最高,接近一半,其次是農民自主流轉,通過社會組織流轉土地比例較低。說明改革現有的土地流轉方式是農村土地制度完善的重要內容。從新型職業農民培育最需要的人才激勵看,物質激勵(獎金等)最多,精神激勵(榮譽等)、政治激勵(選任干部等)次之。說明農民看重的是實物,不太有精神和政治追求。從新型職業農民培育最需要的運行機制看,保障機制最高,其次是聯動機制,而領導機制和社會動員機制比例接近一致,監督機制、評價機制、獎懲機制比例很少。說明建立保障機制和聯動機制是新型職業農民培育的核心機制。
2 湖南新型職業農民培育困境分析
2.1 新型職業農民培育制度不夠健全
全面建立新型職業農民培育制度體系,是確保新型職業農民高質量發展和國家糧食安全的重要保障。目前湖南新型職業農民總量不到全省農村勞動力資源總量的2%,很難滿足湖南鄉村全面振興對人才的需求,其根本原因是湖南新型職業農民培育的制度體系不夠健全。與外省相比,天津、甘肅兩省就農民教育培訓事業發展均早已提供立法保障。雖然湖南也早已將農民教育培訓立法問題列入省人大農業立法計劃,并開展了立法調研和召開了立法聽證會,但迄今尚未出臺“農民教育培訓條例”,因而無法可依,難以有效有力保障農民教育培訓資金足額專款專用,導致新型職業農民培育緩慢,扶持新型職業農民培育的惠農政策落實督查制度執行力度不大,14.75%的農民反映所在地政府完全沒有落實三農政策,35.94%的農民反映發展產業完全沒得到政府扶持。
2.2 新型職業農民培育效果不太明顯
高質量高水平的教育培訓,是確保新型職業農民高質量發展的主要抓手,也是保證糧食安全人才供給的重要手段。盡管湖南農民教育培訓工作在審計調研和整體績效考核中得到國家審計署及中央財政農業相關轉移支付資金整體績效評估組的充分肯定,但調研反映新型職業農民教育培訓存在問題的現象依然存在,40.09%的農民反映理論與實踐脫節。此外,湖南農民參與高職擴招工作的積極性不高,全省僅衡陽市配合湖南環境生物職業技術學院完成了農學專業擴招錄取300人的任務。
2.3 新型職業農民培育需求不很充分
做好新型職業農民培育需求調研,充分挖掘新型職業農民培育的需求性,是確保新型職業農民高質量發展的前提條件。但湖南新型職業農民培育的需求性還沒有充分挖掘,58.53%的農民反映最需要的教育培訓方式是現場指導,66.82%的農民認為新型職業農民培育最需要的職業認同是經濟效益好,64.52%的農民認為新型職業農民培育最需要的人才激勵是物質激勵,63.59%的農民認為新型職業農民培育最需要的文化發展是現代文化,57.14%的農民完全接受康養農業等農業新業態知識教育培訓,52.53%的農民認為新型職業農民培育最需要的政府購買服務類型是技術服務。
3 湖南新型職業農民培育政策優化建議
3.1 完善新型職業農民培育制度
要重點加強高素質農民發展立法制度建設。將農民教育培訓立法列入省重點農業立法計劃,將認定管理、教育培訓、政策扶持、跟蹤服務、績效評價、社會保障和督查落實等相關方面以立法方式進行全面規范,盡快頒布實施。要重點加強高素質農民發展常態聯席會議制度建設。成立以政府分管農業的領導為組長,辦公、農業農村、財政、教育、科技、自然資源、人社、金融、婦聯、團委、工會等多方參與的高素質農民發展領導小組,明確領導小組成員單位各自職責,將高素質農民發展工作納入領導小組成員單位年度目標責任考核。
3.2 提升新型職業農民培育效果
要增強“雙師型”教師和“鄉土專家”兩支農民教育培訓師資力量的吸引力,提高農民教育培訓師資課酬,將課時計入職稱評審教學工作量,同等條件下優先評先、評優和晉升職稱。要采取“菜單式”“訂單式”確定教育培訓內容,按照產業小類分級實施教育培訓,對有教育培訓需求的農民不受參加次數限制。要按照農業生產周期和農時季節分段安排課程,農閑時間理論學習,農忙時間現場指導,加強理論與實踐緊密銜接,強化實際操作。要采取政府購買服務方式,委托第三方機構,通過線上線下雙向開展高素質農民教育培訓質量監督檢查和考核評估。要改革高職擴招高素質農民有關工作,實行注冊入學,免費就讀,食宿自理,嚴格過程和結果管理,畢業后與招干、晉升、社保、項目等政策待遇掛鉤。
3.3 適應新型職業農民培育需求
根據高素質農民創業需求,擴大土地承包經營權、林權、“四荒地”使用權和大型農用生產設備等抵押貸款覆蓋面。強力推進農村產業革命,每個產業投資1億元,每個省領導負責1個產業。按照農村產業基地規模大小,實行差別化扶持政策,嚴厲查處虛假申報產業規模套取國家惠農資金的行為,嚴審示范性農民合作社、家庭農場評選獎勵。參照定向免費培養醫學生的做法,實施“定向免費培養農科生計劃”,在農村服務期5年結束后在升學、晉升等方面享受優惠政策。堅決督查落實“誰種植、補貼誰、誰受益”的補貼政策,嚴厲查處虛報荒田騙取種植補貼的行為,取消已拋荒多年或根本沒種植的稻田糧食補貼,增加春耕補貼項目。出臺“農業生產資料規定”,保障農業生產資料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