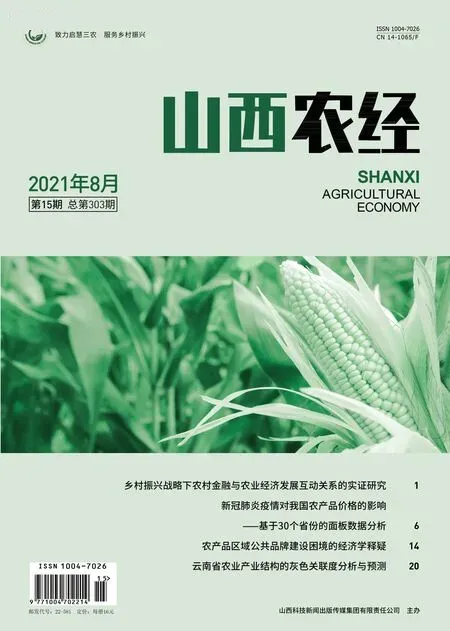旅游減貧理論下哈尼民族遺產區鄉村旅游的實踐效應研究
——以元陽縣阿者科村為例
□周恒麗
(四川大學旅游學院 四川 成都 610065)
我國2019 年啟動全國鄉村旅游重點村的評選工作,公布了第一批320 個鄉村旅游重點村名單。到目前為止,在全國已經有1 000 個鄉村旅游重點村。鄉村旅游重點村快速增長,說明我國鄉村旅游事業蓬勃發展,鄉村旅游已成為新時代鄉村經濟發展的增長點和減貧事業的著力點,通過發展旅游業來盤活市場經濟的作用不言而喻[1]。
1 文獻回顧
關于旅游減貧效應的研究開始于20 世紀70 年代。1999 年4 月,英國國際發展署(Department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在可持續發展委員會的報告中首次提出了PPT(Pro-Poor Tourism)的概念,即“可促進貧困者的旅游”。PPT 概念的核心觀點是通過發展旅游業來提高貧困人口的收益。
目前,國內外學者對旅游的減貧效應主要有以下3 種不同觀點。
第一種觀點是旅游發展可以促進減貧。在理論上,旅游發展可以促進減貧。外地游客的到來,為當地旅游及其相關產業提供了更多的需求市場,從而促進了當地經濟增長。一些研究發現,旅游業發展有助于給旅游地創造更多就業機會,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從而促進當地的經濟發展,減少貧困。目前,這一觀點在旅游減貧理論中占主流地位。如今實施的鄉村旅游減貧項目也都是基于這一假設開展,以期為當地的貧困人口帶來真正的經濟收益。很多實證研究從擴大就業角度分析旅游發展的減貧作用,一些研究發現旅游發展有助于給旅游地創造更多就業機會和提高居民經濟收入水平,從而減少貧困[2]。
第二種觀點與第一種觀點恰好相反,認為旅游業發展加劇了貧困。持該觀點的學者認為,旅游業會加大當地的不平等現象,還會擴大社區貧富差距。旅游業的發展對當地經濟和社會的影響并不全都是正面的,也可能對貧困地區居民造成負面影響。比如,旅游地的原始生態環境會遭到破壞;積極參與到旅游業的居民可以快速獲得經濟收益,從而變得更富足,而沒有參與其中的人則沒有獲得旅游發展帶來的利益,從而導致當地的貧富差距拉大,加劇了相對貧困。而且旅游業具有非常明顯的季節性,導致旅游業提供的就業崗位也存在很大的季節性波動,想通過發展旅游來促進當地減貧是不現實的。
第三種觀點是旅游發展與減少貧困之間沒有聯系。持該觀點的學者認為,旅游業發展不一定能夠減貧,旅游發展與減貧之間沒有必然聯系。由于許多旅游減貧項目沒有獲得預期成效,反而還引發了各種社會問題,因此許多學者對PPT 觀點產生了質疑,重新探討了旅游發展與貧困減緩之間的關系。許多研究發現,不同旅游活動類型對減少貧困的效果各異,缺乏統計學上的證據來判斷二者存在必然聯系。而且由于企業以盈利為目的,旅游業發展對減少貧困的作用僅限于旅游從業人員,但對旅游目的地的影響并不顯著。這些學者的實證研究成果有力證明了旅游發展與貧困減緩并無必然聯系這一觀點。
我國旅游減貧項目的長期效應有待實踐驗證。通過發展旅游業來實現減貧,在實踐中仍會出現許多不可避免的社會問題,特別是對偏遠的鄉村文化遺產區,更應該通過微觀視角驗證鄉村旅游減貧效應的持久性,從而厘清發展鄉村旅游對促進鄉村民族地區減貧效應之間的正確關系與影響機制,為鄉村旅游可持續發展及鄉村振興提供理論支持[3]。
2 旅游減貧理論下中國鄉村旅游的實踐效應
2.1 研究區域概況
元陽梯田位于云南省元陽縣哀牢山南部,是哈尼族人1 300 多年來的獨特創造。2013 年6 月22 日,在第37 屆世界遺產大會上,紅河哈尼梯田由于其符合遺產中心認定的第(Ⅲ)條和第(Ⅴ)條文化標準,以及具有真實性和完整性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成為我國第45 處世界遺產,是我國第一個以民族名稱命名的世界遺產。
阿者科村屬于典型的“富饒的貧困”,村莊交通不便,“空心化”非常嚴重,年輕人大部分外出打工。阿者科村總共64 戶、479 人。在鄉村旅游開發前,屬于典型的貧困村落,農民以種植業、畜牧業為主,人均年收入較低。村莊中有的村民將傳統民居出租給外地經營者,自己搬出村寨。如果不盡快改善阿者科村的經濟狀況,勞動力都外出打工,下一代外出上學,未來有很大可能棄耕,這不僅是世界文化遺產的極大損失,也會使哈尼族人民世世代代創造的文化奇觀失去保護與傳承。
2.2 旅游減貧理論的實踐效應分析
在鄉村扶貧政策支持下,阿者科村的鄉村旅游開發采用內源式發展模式。內源式發展模式最初源于經濟學理論的內源性增長理論,是指以區域內的資源、技術、產業和文化為基礎,以提高本地居民生活質量為目標,使區域經濟效益最大化。這一模式的內涵主要包含以下3 個方面:第一,一個地區開發的最終目的是培養其自身內部的生長能力,同時需要保持和維護好其本地的生態環境及文化傳統。第二,為了培養本地的自身發展能力,最好的途徑是以當地居民作為地區開發的主體,使當地居民成為地區開發的主要參與者和受益者。第三,為了保證當地居民的主體性地位,必須建立能體現當地居民的意志,而且有權干涉地區發展決策的有效基層組織。
內源式發展模式是從地區自身內部尋找發展的源泉和根本動力,強調發展最終必須從各自社會內部中創造出來的,而不是簡單從外部直接移植過來。近年來,在我國鄉村振興的背景下,這一發展模式被廣泛應用于鄉村發展之中[4]。
阿者科村民委員會、村民集體出資成立公司開發鄉村旅游業,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及生態效益都得到了很好的發展。實現穩定增收,群眾收入增加。2019 年3 月阿者科村第一次分紅,48 戶分得1 600 元,分紅最少的6 戶分得680 元。2019 年8 月第二次分紅,48 戶分得1 840 元,分紅最少的分得740 元。截至2019 年10 月,全村收入超40 萬元,村民分紅金額191 195 元;增加了就業崗位,群眾參與度提高;村民得到了實惠,對游客的態度由淡漠轉為熱情;提升了人居環境,旅游環境得到優化;村內除了村民日常打掃,還定期開展大掃除,順利完成公廁改建、水渠疏通、房屋室內宜居優化等。旅游業在阿者科村的興起,帶動了經濟社會生態良性循環,也使傳統村落得以保護。發展鄉村旅游后,阿者科村規定村民不得將房屋出租,否則視為放棄公司分紅權,傳統民居及其人文內涵得到保留。一些傳統民俗文化被市場認可,得以長久保護和傳承。中山大學團隊在駐村運營公司期間,不僅教村民使用計算機辦公和當地兒童學習普通話,而且還吸引了外出年輕村民返鄉創業,建設和保護家鄉。旅游的減貧效應不僅發揮在增加當地村民的經濟收入上,還體現在人居環境、村民教育水平、村民對民族文化的認同感提升等方面。
3 討論
阿者科村的鄉村旅游扶貧實踐是一次由政府、村集體以及學者團隊多方組織下的鄉村扶貧,是一次拉動經濟、提高村民收益以及民族村落保護的現實探索。這不僅是通過開發鄉村旅游來促進當地產業多元化發展,而且是哈尼族千年文化景觀遺產保護得到有效利用的良好契機,激發了村民主動保護民族村落和農耕文化的參與性和積極性。阿者科村民通過多方面參與,提升了哈尼族的傳統文化認同感,也增強了主動參與遺產保護的意愿,更直接的效應是村民的經濟收入增加,生活水平得到提高。村民更自愿參與旅游發展,這也是旅游減貧理論在阿者科村的應用,顯著印證了三大主流觀點之一的旅游發展有利于貧困減緩的理論,也是旅游減貧理論在中國的一次成功實踐。
此次研究仍然存在許多不足之處。首先,由于旅游發展的減貧持續效應還需要長期的動態研究來驗證其科學性,此次研究僅涉及一段時間內的實踐效應,因此還有待未來的研究擴充。其次,鄉村旅游發展模式選擇也會影響減貧效應研究的效果,主要是研究了內源式發展模式,未涉及外源式發展模式,因此研究結果也存在局限性。再次,由于中國民族遺產地區的多樣性和廣闊性,民族遺產地區的鄉村旅游減貧效應也應該在更多地方實踐,未來可以進行更多對比研究來印證旅游減貧的長期效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