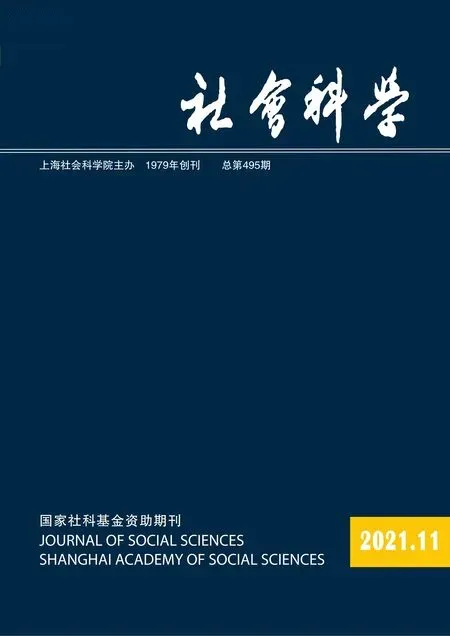身體、愛欲與倒錯*
——薩特與拉康學說中的身體問題
盧 毅
按照國內學者楊大春的觀點,“身體”不僅構成了當代法國哲學的三大主題之一(另外兩個主題分別是“語言”和“他者”),而且“身體問題在后期現代哲學中具有核心地位,……我們尤其從20世紀法國現象學存在主義運動中看出身體問題的極端重要性”。(1)楊大春:《語言·身體·他者:當代法國哲學的三大主題》,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7年版,第138頁。作為20世紀法國現象學存在主義運動的領軍人物,薩特盡管在這一運動中很早就對身體問題展開了專門探討,但他關于身體問題所進行的具有深度與原創性的思考,卻出于各種原因迄今未能得到應有的重視。與此同時,薩特對基于身體的愛欲以及由此衍生的倒錯現象(以施虐和受虐為典型)的關注,使得其對身體問題的分析跨越了現象學的界域,而與同樣聚焦相關問題的精神分析有了深度對話的可能。作為弗洛伊德思想最重要的后繼者與開拓者,拉康延續了弗洛伊德以來精神分析對身體問題的關注與強調,并通過其獨具特色的“三界”學說賦予了身體更為豐富的內涵,也由此揭示了基于身體的愛欲與倒錯問題可能具有的深層意蘊。在對身體、愛欲與倒錯問題進行分析和考察的過程中,我們發現,薩特與拉康在這些問題上既表現出值得關注的思想共鳴,也呈現出不容忽視的理論張力。對此加以梳理和總結,將有助于探索未來在現象學與精神分析交互視域下身體問題研究的方向。
一、薩特論身體、愛欲與倒錯
在身體現象學或現象學的身體研究領域,薩特無疑占據了一個關鍵位置。人們甚至有理由認為,正是薩特憑借其在《存在與虛無》中從現象學的存在論立場出發對身體之重要性的高度強調,及其對身體頗具原創性的多維分析,才真正開啟了現象學在法國的“身體轉向”。然而,在當今學界,薩特在身體問題上的貢獻,卻往往被梅洛-龐蒂、列維納斯、亨利等現象學家的光芒所掩蓋,這一點確實值得引起人們的重視與反思。根據當代著名現象學家德莫特·莫蘭的說法:“在《存在與虛無》中,薩特納入了關于身體的一個與眾不同的、具有開創性的章節,它在三個標題之下來探討身體:‘作為自為存在的身體:偶然事實性’,‘為他的身體’以及‘身體的第三個存在論維度’。盡管這一章對梅洛-龐蒂的影響已得到承認,但薩特的身體現象學從總體上看卻被忽視了。……我認為薩特甚至是比梅洛-龐蒂更杰出的關于肉身(la chair)以及關于主體際的身體際性(intersubjective intercorporeality)的現象學家。薩特強調觸摸自己僅僅是一個偶然特征而非‘身體性研究的基礎’。”(2)“根據薩特,觸摸與被觸摸,感到一個人在觸摸和感到一個人被觸摸,是被錯誤地歸于‘雙重感覺’下的兩種不同模式的現象。它們有根本的不同:觸摸為我們揭示了一種自為的身體的維度,而被觸摸的身體構成了薩特哲學中‘為他的身體’的身體性的維度。”(Marek Drwiega, “Dimensions of Human Corporeity in the Philosophy of Jean Paul Sartre”, Ph?nomenologische Forschungen , No.1/2, 2001,p.144.) Dermot Moran, “Husserl Sartre and Merleau-Ponty on Embodiment, Touch and the ‘Double Sensation’”, in Sartre on the Body, ed. by Katherine J. Morris,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0, p.41.莫蘭在另一處也表示:“應將‘肉身’這一關鍵概念的引入歸功于薩特。這一概念對梅洛-龐蒂后期的哲學而言非常根本,并且通常被認為源自于他。薩特論述的另一個原創性方面是他對‘身體際性’(梅洛-龐蒂在他后期工作中用這個詞來意指有生命的身體之間的身體性介入)的討論。”(Dermot Moran,“Sartre’s Treatment of the Body in Being and Nothingness: The‘Double Sensation’”, in Jean-Paul Sartre: Mind and Body, Word and Deed, ed. by Jean-Pierre Boulé and Benedict O’Donohoe, Newcastle: 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 2011, p.10.)并且“實際上,真的可以說薩特比其他任何現象學家(可能除了列維納斯之外)都更好地探討了對我的身體的這種主體際的共同構成”。(Ibid., p.14.)
在現象學傳統中,對身體問題的探討始于胡塞爾與舍勒,中間雖經海德格爾對此在之在世存在的分析,但直到現象學發展的“法國階段”,身體才在薩特與梅洛-龐蒂等人的學說中真正成為現象學的核心問題。值得注意的是,在這一傳統中,薩特與上述幾位代表人物都存在重要差異。與胡塞爾和梅洛-龐蒂探討身體問題的進路不同,“薩特并非從觀看或觸摸自己的身體開始,而是從被他者觀看或觸摸的身體開始。在我的身體與他者之存在一種持續的共同建構,這對尤其是在舍勒那里找到的通過共情構建他人身體的傳統路徑形成了挑戰”。(3)Dermot Moran, “Husserl Sartre and Merleau-Ponty on Embodiment, Touch and the ‘Double Sensation’”, in Sartre on the Body, ed. by Katherine J. Morris,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0, p.45.除此之外,盡管海德格爾對此在之在世存在的分析——尤其是他對此在之置身性(Befindlichkeit)與有死性即“向死而在”的分析——實際上指向身體問題,“然而,海德格爾對此在之在世存在的偶然事實性的分析并非是一種對肉身化存在的分析,而薩特的分析則是如此。通過這種方式,身體性成了對人之境況的一般性描述的基本元素”。(4)Marek Drwiega, “Dimensions of Human Corporeity in the Philosophy of Jean Paul Sartre”, Ph?nomenologische Forschungen , No.1/2, 2001, p.145.薩特對海德格爾的不滿不只是此在之身體性的缺失,還在于此在之性欲和性別的缺失,而性欲與性別在薩特看來乃是作為欲望的意識之具身性的基本體現,是理解此在即“人的實存”不可或缺的根本向度。按照薩特本人的說法:“特別是海德格爾,在他的存在分析中對性沒有一點暗示,以至于他的‘此在’顯得是無性(別)的。人們無疑可以認為‘人的實在’具體化為‘男性的’或‘女性的’實際上是一種偶然;人們無疑可以說性別分化的問題與存在的問題毫不相干,因為男人和女人一樣,不多不少剛好‘存在’。這些理由不能令人絕對信服。性別差異屬于偶然事實性的領域,這點我們嚴格接受。但這是否意味著‘自為’‘出于偶然’是有性(別)的,出于純粹的偶然而有了這樣一個身體?我們是否可以承認性生活這件大事對于人的境況而言是附加上去的?然而初看起來,欲望及其反面即性恐懼,都是為他存在的基本結構。”(Jean-Paul Sartre, L’être et le néant, Paris: Gallimard, 1943, p.424.)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薩特將身體描述為無處不在的,因為它是我們被納入處境的方式”。(5)Dermot Moran, “Husserl Sartre and Merleau-Ponty on Embodiment, Touch and the ‘Double Sensation’”, in Sartre on the Body, ed. by Katherine J. Morris,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0, p.52.
薩特對身體的討論是從意向性出發的,就此而言,他似乎比海德格爾和梅洛-龐蒂更容易被歸為胡塞爾式的現象學家。在薩特看來,“意向性是世界導向的。人的欲望和認識是朝向世界的并且已經在世界之中。薩特經常談論具身化的意識何以必須超出自身”。(6)Dermot Moran, “Husserl Sartre and Merleau-Ponty on Embodiment, Touch and the ‘Double Sensation’”, in Sartre on the Body, ed. by Katherine J. Morris,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0, p.49.例如,薩特曾表示:“作為要被超出在世存在的障礙,也就是我之于自己所是的障礙,身體再次是必要的。”(7)Jean-Paul Sartre, L’être et le néant, Paris: Gallimard, 1943, p.366.可見,作為意識的具身化,身體恰恰體現了意識不斷要求自我超越——超越自身以朝向世界,超越當下以朝向未來——而“不是其所是,是其所不是”的存在論屬性,并且實際上唯有憑借身體,意識的這種自我超越才能真正付諸實踐。“在這個意義上,身體代表著我介入世界的獨特性。我無法‘逃避’這一境況,因為這將等同于非存在。然而,根據薩特的觀點,這種存在又是偶然的。”(8)Marek Drwiega, “Dimensions of Human Corporeity in the Philosophy of Jean Paul Sartre”, Ph?nomenologische Forschungen , No.1/2, 2001, p.145.
可見,身體同時體現了人憑借身體在世的必然性以及憑借何種處境中的身體在世的偶然性。就其必然性而言,“出生、過去、偶然、一種觀點的必然、世上一切可能行動的事實條件:這就是我的身體,它是為我的。因此它絕非我靈魂之上的一種偶然的增添,而是我的存在的一種永久結構以及我的意識作為對世界的意識還有作為朝向我的未來超越的籌劃的永久條件”。(9)Jean-Paul Sartre, L’être et le néant, Paris: Gallimard, 1943, p.367.從這一角度來看,“身體因此是與世界之間意義關系的總和”。(10)Marek Drwiega, “Dimensions of Human Corporeity in the Philosophy of Jean Paul Sartre”, Ph?nomenologische Forschungen , No.1/2, 2001, p.157.然而,與他人的遭遇使我發現他人也有一個與我類似的身體,“隨之而來的便是他人的身體對我而言是一種整合的總體”。(11)Marek Drwiega, “Dimensions of Human Corporeity in the Philosophy of Jean Paul Sartre”, Ph?nomenologische Forschungen , No.1/2, 2001, pp.157-158.由于他人的身體總是在向我或為我呈現的處境中才作為他人的身體出場,“從這個意義上講,他人的身體是為我的綜合整體,因為首先我只能從指示他人的身體的整個處境出發才能把握他人的身體。……身體是從處境出發顯現為生命和行動的綜合整體”。(12)杜小真:《存在和自由的重負:解讀薩特〈存在與虛無〉》,山東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20頁。就其偶然性而言,身體以及具身化的欲望都體現出上述處境性,并且對他人身體之處境性的揭示,最終也揭示了作為揭示者的我自己身體的處境性。“在此意義上,欲望并非只是對他人身體的揭示,而是對我自己身體的揭示。而這不是就此身體是工具或觀點而言,而是就它是純粹的偶然事實性而言,亦即就我的偶然性之必然性的單純偶然形式而言。”(13)Jean-Paul Sartre, L’être et le néant, Paris: Gallimard, 1943, p.429.換言之,人的實存必然以偶然的方式具身化地存在,“所以,身體說到底是我的處境的偶然形態”。(14)杜小真:《存在和自由的重負:解讀薩特〈存在與虛無〉》,山東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11頁。
至此我們可以發現,在對身體的探討中,薩特非常關鍵地引入了他人的維度。在薩特看來,與他人的關系不僅是揭示身體的條件,而且也是對身體之揭示所印證的事實。“在《存在與虛無》中,薩特從‘與他人的具體關系’這一章開篇就宣稱沖突是為他存在的初始含義。”(15)Jean-Pierre Boulé, “érotisme, désir et sadisme chez Sartre”, Sartre Studies International Vol.23, Iss.1, 2017, p.40.換言之,作為自為存在本身所內在固有的為他存在這一結構,它與自為存在本身的內在張力必然在與他人的具體關系中表現出沖突與矛盾。“實際上,薩特堅持認為,我對他者可能采取的兩種原始態度都蘊含著這種沖突。在薩特將之與欲望/施虐聯系在一起的第一種態度中,我試圖超越他者的超越性,繼而將他者的自由統攝于我自己的自由之下。在薩特將之與愛/受虐聯系在一起的第二種態度中,我試圖將他者的超越性納入我之中而不取消其作為超越的特征。”(16)Betty Cannon, Sartre and Psychoanalysis, Lawrence: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1991, p.86.
由此可見,在與他人的具體關系中,薩特重點考察的是以身體為基礎和條件的愛欲以及作為其變體的性倒錯。首先是“愛”這種態度:在愛中,“愛者希望成為被愛者自由的‘對象-界限’。愛者并不希望成為世上眾多對象中的一個,而是希望成為被愛者的‘整個世界’或者說成為使被愛者的世界得以可能存在之物。愛者希望成為一個無法超越的、無法出于被愛者自身的目的而被工具性地使用的對象。(17)Betty Cannon, Sartre and Psychoanalysis, Lawrence: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1991, p.87.顯然,這一過于理想化的目標在現實中并無實現的可能。愛者無論如何提升自己的魅力或誘惑性,始終都會發現愛人難以被徹底限制的自由以及自身作為對象被超越的可能。“愛的籌劃無法避免的失敗可能導致以受虐的態度接受這種籌劃的降格。在受虐中,我放棄了通過將他者吸納為我作為對象的自由籌劃的見證者以為自己提供合理辯護的籌劃。我試圖讓自己成為一個純粹的對象、一個純粹的自在,而非一個超越性的對象。在羞恥中,我接受了我此前曾經拒絕的工具性的位置。”(18)Betty Cannon, Sartre and Psychoanalysis, Lawrence: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1991, p.89.
然而,吊詭的是,“我不得不承認,是作為主體的‘我’意圖將我化約為對他者而言的對象。因此我越是試圖體會我的對象化,就越是感受到我的主體性。例如,一個花錢讓妓女來鞭打他的男人,發現他一旦將這個女人作為工具來對待,則他在與她的關系中就占據了一個具有超越性的主體的位置。對她的對象性的這一發現因此解放了受虐狂的主體性,導致了整個受虐籌劃的瓦解”。(19)Betty Cannon, Sartre and Psychoanalysis, Lawrence: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1991, pp.89-90.換言之,“他(受虐狂——引者注)越是企圖領略自己的對象性,就越是被自己的主體性的意識所淹沒,直至淹沒在焦慮之中”。(20)杜小真:《存在和自由的重負:解讀薩特〈存在與虛無〉》,山東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32頁。因此,最終發現是主動設定自己被動對象地位的受虐狂主體陷入了對這一位置具有構成性的僵局中。正如愛一樣,受虐的籌劃因其自身的結構而注定失敗,主體必然無法通過將自身置于極端的對象地位而徹底擺脫其主體性與自由。
接下來便是另一組看似與此截然相反的態度,即欲望/施虐。“[在欲望中],我想要占據的當然不只是作為身體的他者的身體,我想要占據的是輪流將我作為一個對象來占據的意識所占據的他者的身體。我并不欲望作為身體的他者,而是欲望作為肉身的他者。……那么讓一個人變為肉身并進入欲望的世界意味著什么?……在欲望的狀態下,我放棄了我作為對我行動的工具性整合的組織,而以旨在純粹‘在此’的身體來取代它。”(21)Betty Cannon, Sartre and Psychoanalysis, Lawrence: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1991, pp.90-91.在薩特看來,愛撫是欲望最典型的具身化體現:“在愛撫他者的過程中,我讓他者的肉身作為具身化的意識在我的觸摸之下誕生。”(22)Betty Cannon, Sartre and Psychoanalysis, Lawrence: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1991, p.91.“不僅如此,在欲望的狀態下改變的不只是我相對于他者的定位,還有我的整個世界的定位。世界本身變成了一個欲望的世界,它向我揭示了對象‘肉身性的’一面。”(Ibid., p.92.)“如此一來,欲望就是占有一個身體的欲望,而這種占有將我的身體揭示為肉身。”(23)Jean-Paul Sartre, L’être et le néant, Paris: Gallimard, 1943, p.429.換言之,“欲望是讓身體脫離運動及衣著而讓其作為純粹肉身存在的一種企圖,是一種將他人的身體肉身化的企圖。……愛撫讓他人作為為我以及為他自己的肉身而誕生”。(24)Jean-Paul Sartre, L’être et le néant, Paris: Gallimard, 1943, p.430.
“然而,薩特式的性欲望,就像薩特式的愛一樣,是一個不穩定的位置,因為在‘雙方彼此肉身化’中達到的交互性無法持久。”(25)Betty Cannon, Sartre and Psychoanalysis, Lawrence: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1991, p.94.通過愛撫而顯現的肉身隨時可能因為被工具化而被重新還原為對象性的身體,而面對這一身體的我的身體也將難以作為肉身維系下去。“這種失敗可能導致受虐,假如我接下來試圖變成一個對象被納入作為意識的他者當中,由此變為在他者注視之下陶醉的肉身;也可能導致施虐,假如我由于試圖掌控和占有他者的肉身而破壞了肉身化的相互性。”(26)Betty Cannon, Sartre and Psychoanalysis, Lawrence: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1991, p.94.
貝蒂·坎農認為,從薩特的視角出發,“作為一個超越性的主體,施虐狂嘗試一種非相互性,他在其中‘面對著一種被肉身所捕獲的自由享有一種占用的權力’”。(27)Betty Cannon, Sartre and Psychoanalysis, Lawrence: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1991, p.95.杜小真則進一步明確道:“薩特指出,性虐待狂本身同盲目的冷漠和情欲一樣,也包含著它失敗的原則。首先是因為:把身體領會為肉體和對它的工具性使用之間,有一種深刻的不可共存性。”(28)杜小真:《存在和自由的重負:解讀薩特〈存在與虛無〉》,山東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38頁。具體而言,施虐這個位置的不穩定性體現在兩方面:“一方面,當施虐狂看似成功地將一種痛苦意識的他者化約為一種受奴役的自由時,他之前曾嘗試創造的‘作為工具的肉身’這一復合體便會消失,而他者的身體會重新出現。在這個時刻,施虐狂并不知道該怎么處理這個馴服的身體。”(29)Betty Cannon, Sartre and Psychoanalysis, Lawrence: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1991, p.95. 學者布雷也指出:“在《存在與虛無》中,薩特表示由于我想要侵占他人的自由,這種自由便在我的注視下瓦解,以至于我注定要通過他人之于我所是的對象來尋找他人的自由。”(Jean-Pierre Boulé, érotisme, désir et sadisme chez Sartre, Sartre Studies International Vol.23, Iss.1, 2017, p.42.)這種緣木求魚之舉,在薩特看來正是欲望和施虐都必然失敗的根本原因。另一方面,“施虐狂在受害者注視他的時刻,‘體驗到他的存在在他者自由中的絕對異化’,而正如我們可能已經預見到的那樣,他施虐的籌劃撞上他者主體性的礁石而沉沒”。(30)Betty Cannon, Sartre and Psychoanalysis, Lawrence: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1991, p.96.總之,無論是發現自己奴役的肉身淪為了工具性的身體而不知所措,還是發覺這身體依然能夠通過注視體現出自由,而自己只不過是他者的工具而驚慌失措,施虐狂的目標都終究遙不可及。
在表明上述兩種態度注定失敗之后,坎農表示:“我并不認為薩特的存在論要求我們采取一種消極的人際觀。這是因為,薩特后來承認在‘與他者的具體關系’中描述的所有互動都是在自欺之下進行的。……并且,薩特本人最終在一個具有挑釁意味的腳注中暗示,此前的論證并未排除從施虐-受虐的循環中‘獲得解放和救贖的一種倫理學的可能性’——基于對自由本身之重視的一種‘徹底轉換’的可能性。”(31)Betty Cannon, Sartre and Psychoanalysis, Lawrence: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1991, p.97.與之相似,布雷也認為:“《[道德]札記》的薩特,戰后的薩特,接近了波伏瓦在《該不該焚毀薩德?》中的立場。后者聲稱,由于受到干擾,存在在其自身及在他者那里同時作為主體性與被動性得到把握。結果就是‘通過這種含混的統一,伴侶雙方得以會合,每一方都擺脫對其自身的在場并達到與他者的一種直接溝通’,兩個主體得以在享受中共存。”(32)Jean-Pierre Boulé, “érotisme, désir et sadisme chez Sartre”, Sartre Studies International Vol.23, Iss.1, 2017, p.55. 另有學者指出,波伏瓦對薩特影響的有限性恰恰在身體問題上凸顯了出來:“如果說她在讓薩特放棄他嚴苛的絕對自由概念方面是成功的話,如果說她在讓他承認偶然事實性與處境的重要性方面是成功的話,我認為她在具身化問題上的成績則遠沒有那么醒目,如果不說徹底缺席的話。……盡管她更精致的具身觀揭示了人類基本的含混性,薩特卻依然執著于最終使其成為一位二元論者的觀點:僅就意識用其身體來朝向自己的籌劃而超越自己而言,意識才是具身化的。”(Christine Daigle, “Where Influence Fails: Embodiment in Beauvoir and Sartre”, in Beauvoir and Sartre : The Riddle of Influence, ed. by Christine Daigle and Jacob Golomb,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33-34.)
不過,也有學者表達了不同看法。例如,戴格樂認為:在薩特那里,“肉身的相遇是作為有性(別)的身體的意識的相遇。……在他看來,自為的性態度是其他一切態度的基礎。性欲和自為的涌現一樣根本。……薩特的確討論了性欲與性的關系。但即便如此,相遇似乎也發生在無性(別)的自為之間。當他討論與愛的概念聯系在一起的性關系時,他說的是一個意識試圖引誘并捕獲作為意識的他者。甚至性行為也是獲得他者意識的一種嘗試。”(33)Christine Daigle, “Where Influence Fails: Embodiment in Beauvoir and Sartre”, in Beauvoir and Sartre : The Riddle of Influence, ed. by Christine Daigle and Jacob Golomb,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9, p.37.換言之,在戴格樂看來,身體實際上在薩特學說中并未真正占據核心位置,對它的探討仍是在本質上作為一種意識哲學的薩特哲學的幌子:“自為缺乏存在的自身完整性并想要成為一種自在。意識用它的身體填充存在,使它自己成了存在的充盈。身體因此被視為并被用作自為試圖存在而非僅僅實存的一個工具。”(34)Christine Daigle, “Where Influence Fails: Embodiment in Beauvoir and Sartre”, in Beauvoir and Sartre : The Riddle of Influence, ed. by Christine Daigle and Jacob Golomb,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9, p.39.倘若果真如此,那么溫特格斯對薩特的下述點評便可謂直擊要害:“在《存在與虛無》中,薩特表示人類總是處境中的,并且意識并不獨立于它在世界上的身體性的位置而存在。然而,事實上,他卻強烈反對作為內在性因而作為自欺的一切身體性的化身,而主張明晰的、純粹的意識性的存在(即超越性)作為唯一本真的人的實存。”(35)Karen Vintges, “The Second Sex and Philosophy”, in Feminist Interpretations of Simone de Beauvoir, ed. by Margaret A. Simons,University Park: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50.
二、拉康論身體、愛欲與倒錯
薩特在現象學視域下深入考察的身體、愛欲與倒錯問題,也是與他同時代的拉康在精神分析領域重點關注的對象。正如迪迪耶·卡斯塔奈所言:“在拉康的教學中,如同在弗洛伊德那里一樣,身體占據了一個中心位置。雅克·拉康對身體感興趣,并且在弗洛伊德的眾多后繼者中,他是唯一知道如何給出一套與精神分析的發現相融貫的表述之人。”(36)Didier Castanet, “Le réel du corps : phénomènes psychosomatiques et symptme, Incidences cliniques”, L’en-je lacanien, 2004/2 N°3, p.107.拉康對身體問題的關注可謂貫徹始終,從其早期的鏡子階段理論關于人對其身體完形(Gestalt)的鏡像認同對“自我”之構建的考察,到其中期結構主義模型下關于語言能指對身體的符號化與結構化作用而生成欲望的思考,再到其后期對作為“享受的實體”的實在身體的揭示,身體實際上構成了貫穿拉康思想整體發展的一條重要線索。在此過程中,正如對其學說中的其他關鍵概念(如“他者”“無意識”)一樣,拉康也先后揭示了身體的想象、符號與實在三重維度,或者更確切地說,揭示了以想象的身體、符號的身體以及實在的身體這三重面向呈現的身體之“三位一體”的拓撲結構。
首先,就身體的想象之維而言,拉康認為,尚處在身體破碎而缺乏整合感狀態中的人類嬰兒,憑借其視覺能力相對于身體運動協調能力的超前性,出于對自身統一性的預期而將自身在鏡中的完整形象這一本質上異于自身的“他者”想象或誤認為“自我”,并由此奠定了人類認識的妄想狂結構。(37)Cf. Jacques Lacan, “Le stade du miroir comme formateur de la fonction du Je : telle qu’elle nous est révélée dans l’expérience psychanalytique”, in écrits, Paris: Seuil, 1966, p.94.換言之,想象的身體源于兒童所看到的鏡中的完整身體形象,“兒童對這一形象的原始認同將促進‘我’的結構化,而這將給拉康稱之為破碎身體之幻象的獨特精神體驗畫上句號。事實上,在鏡子階段之前,兒童起初并未對其身體有一種統一整體的體驗,而是有某種離散之物的體驗。這種關于破碎身體的幻想體驗——它的遺跡既在某些夢的構型中也在精神病性質的崩解過程中向我們顯現——在鏡子的辯證法中經過了考驗,而鏡子的功能正可以緩和身體令人焦慮的離散以有利于完整身體的統一”。(38)Jo?l Dor, Introduction à la lecture de Lacan, Paris: Deno?l, 2002, pp.99-100. 確切地說,在此得到揭示的不單是作為鏡像的想象的身體,其實也涉及破碎而缺乏整合感的實在的身體,或者不如說得到揭示的乃是處在(完形的)想象與(破碎的)實在張力之下的身體,只不過拉康在此更多強調的是身體的這一想象維度對于自我的構建作用,但并未真正忽視身體的實在維度,并且恰恰在其思想發展的后期重新聚焦并深入揭示了身體的這一實在維度。有學者據此認為,“鏡子階段是一個發展時段,孩子在該時段將自己作為一個處在與雙親力比多關系中的身體性的統一體來占據。……嬰兒在鏡子面前的狂喜因此是一個更深層地占據身體過程的跡象,而拉康通過賦予鏡子階段一種力比多含義暗示了這一過程”(39)Wilfried Ver Eecke, “Lacan, Sartre, Spitz On the Problem of the Body and Intersubjectivity”, Journal of Phenomenological Psychology, Vol.16, No.2, 1985, p.75.——在占據大他者(Autre)位置的雙親的許可下通過認同鏡像而形成原初的自我,這從力比多經濟學的角度來看也意味著形成原初的自戀——這表示“實際上,薩特將人視為一個身體,而拉康將人視為認同于并因此占據他的身體。拉康關于意識與身體之間關系的看法比薩特的看法更具動態性”。(40)Wilfried Ver Eecke, “Lacan, Sartre, Spitz: On the Problem of the Body and Intersubjectivity”, Journal of Phenomenological Psychology, Vol.16, No.2, 1985, p.74.
其次,就身體的符號之維而言,拉康主要涉及的是語言能指對身體的切割與構造,或者說是語言對身體的符號化與結構化,以及由此生成的欲望。盡管對鏡像的認同賦予人類個體一個想象的身體,為其提供一種想象的身份或同一性,但真正意義上人類主體性的確立還有賴于語言及其塑造出來的一個符號(化)的身體。正如梅奈所言:“實際上是語言將一個身體賦予主體。是肉身成道而非道成肉身。身體誕生于來自大他者的能指在有機體中制造的切割。”(41)Martine Menès, “Le corps objecteur d’inconscient ? ” , Champ lacanien, 2010/1 N°8, p.196.而按照芬克的說法:“在社會化的過程中,身體逐漸被能指所書寫和重寫,快感局限于特定區域,而其他區域則被言詞所中性化并被連哄帶騙地服從于社會的行為規范。”(42)Bruce Fink, The Lacanian Subjec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p.24.由此可見,身體的社會化意味著身體的符號化與結構化,也意味著基于身體的快感的合法化以及欲望的規范化,看似對立的“欲望”與“法則”由此便結合成為“合法的欲望”以及“欲望的法則”。然而,盡管經歷了社會化過程中語言的符號性異化以及此前鏡子階段中形象的想象性異化,身體依然沒有喪失其根本的實在性,“身體-實在保留著其有生命的狀態,處在語言的或鏡像的表征之外,并且對于任何言在(parlêtre)都是如此”。(43)Martine Menès, “Le corps objecteur d’inconscient ? ”, Champ lacanien, 2010/1 N°8, p.199.

至此,拉康語境下身體的三重維度便得到了初步揭示。然而,這三重維度之間的具體關系仍有待澄清。達米安·吉約內在探討拉康語境下的無意識主體與身體問題的一篇論文中,便試圖以拉康的思想演進為線索來把握相關問題。根據他的觀點,拉康在相關問題上的思想發展經歷了幾個關鍵節點。其一,在1957年的《無意識中字母的機制或弗洛伊德以來的理性》這篇重要論文中,拉康將主體確立為因能指的隱喻機制而被劃杠的無意識主體,這一主體在嚴格意義上沒有身體,或者說“身體(他使用了‘肉身’一詞)的領域作為創傷被納入了能指的行列”,(50)Damien Guyonnet, “Le sujet de l’inconscient et le corps”, in Lire Lacan au XXIe siècle, sous la direction de Fabienne Hulak, Paris: Champ social, 2019, p.250.即身體相對于主體而言恰恰構成了創傷性的、異質性的因素。其二,在1962-1963年的《研討班十:焦慮》中,身體被呈現為遭受能指切割的、洞開的身體,經這種切割而與身體相分離的實在部分即對象小a(objet petita)(51)拉康對對象小a(objet petit a)的探討較為復雜,相關分析可參見盧毅《存在的創傷與主體的發生——存在主義與精神分析交互視域下的焦慮問題》,《北京社會科學》2020年第2期。也成了主體焦慮的對象和欲望的原因,“因此,正如我們所言,是通過拉康逐步指出其實在地位的對象a,有生命的、享受的再加上性(別)化的身體的維度才在被劃杠主體的旁邊被重新引入。這正是幻想的代數式($◇a)所完美表明的:嚴格來說沒有身體的被劃杠的主體作為無意識主體通過拉康所說的一個菱形與對象a即享受的要素相連接,與有生命的身體建立了聯系”。(52)Damien Guyonnet, “Le sujet de l’inconscient et le corps”, in Lire Lacan au XXIe siècle, sous la direction de Fabienne Hulak, Paris: Champ social, 2019, p.254.其三,在1964年的《研討班十一:精神分析的四個基本概念》中,“拉康得出了沖動的環狀結構,該結構繞著作為中空、作為空的對象轉圈,而從邊緣、沖動的邊緣出發,身體的維度被喚起”。(53)Damien Guyonnet, “Le sujet de l’inconscient et le corps”, in Lire Lacan au XXIe siècle, sous la direction de Fabienne Hulak, Paris: Champ social, 2019, p.253.其四,在1964年修改完成的論文《無意識的位置》中,“拉康悄悄地‘用有生命的身體、有性(別)的身體替代了主體’,將對象a作為對力比多和生命體因有死和性(別)化所致的天然缺失的彌補”。(54)Damien Guyonnet, “Le sujet de l’inconscient et le corps”, in Lire Lacan au XXIe siècle, sous la direction de Fabienne Hulak, Paris: Champ social, 2019, p.253, n.720.其五,在1970年代,拉康則明確以享受的身體取代無意識主體作為其理論的首要參照,“這便是拉康晚年最后的教學所宣告的。‘無意識主體’的說法,被劃杠的主體,以某種方式被‘言說的身體’甚至‘言在’所取代,于是拉康得以賦予這被言說的和言說著的主體一個身體”。(55)Damien Guyonnet, “Le sujet de l’inconscient et le corps”, in Lire Lacan au XXIe siècle, sous la direction de Fabienne Hulak, Paris: Champ social, 2019, p.256.
通過以上梳理可以發現,暫時撇開作為“自我”這一想象的主體之基礎的想象的身體,在與嚴格拉康意義上的主體即無意識主體的關系中,拉康對身體的探討進路是從被能指切割的符號化的身體逐漸轉向作為享受的實體的實在的身體,并且不斷賦予身體更大的權重,以至于身體最終在某種程度上取代主體的理論地位。然而,倘若以拉康晚年的身體觀為定論,那么身體的實在維度顯然是最根本且最原初的,而這在某種意義上其實又回到了拉康起初在鏡子階段中所描述的破碎的實在身體。實在的身體的這種破碎性,一方面將通過想象的身體的理想完形而得到想象的修復與整合,另一方面也將由于語言能指的介入與切割而在符號的身體上被加倍改造。但正如上文所述,經歷想象與符號的雙重異化的身體并不會因此而喪失其實在性,反倒能夠將基于想象的幻想以及基于符號的言說本身呈現為身體實在的享受模式。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盡管“享受”似乎構成了拉康探討身體問題的關鍵與歸宿,但嚴格說來它卻并不能窮盡拉康語境下的身體和以之為基礎的愛欲及倒錯問題。正如芬克所指出的:在相關問題上,“人們可以認為實際上存在三個分開的層次:愛、欲望和享受”。(56)Bruce Fink, The Lacanian Subjec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p.196.
首先,就愛而言,“愛(與要求有關)有一個對象。當弗洛伊德談論‘對象選擇’時,涉及的是主體重復對同一類愛的對象的要求,或對愛的對象的同一類關系的要求。而拉康在早期作品中談論‘欲望的’或‘欲望中的’對象時(尤其是在《研討班六》中),這些對象明顯是愛的對象,是主體表達愛的要求的對象”。(57)Bruce Fink, The Lacanian Subjec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p.89.可見,在拉康看來,愛的對象在根本上是要求的對象,并因此與嚴格意義上欲望的對象相區別。“[拉康的]觀點是,在神經癥的幻想($◇D)而非($◇a)中,主體像其伴侶那樣采納了大他者的要求——也就是靜態的、不變的,圍繞著同一樣東西轉的某物(愛)——而非大他者的欲望,后者在根本上處于運動中,不斷尋求別的東西”。(58)Bruce Fink, The Lacanian Subjec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186-187.
其次,就欲望而言,如上所述,它與愛的關鍵區分就在于,它在根本上是一種無盡的換喻過程,總是指向別的東西,而這一換喻結構恰恰要歸因于上文提到的語言能指對身體的符號化與結構化作用。簡言之,經由能指切割和塑造的身體產生了具有可塑性的沖動,而沖動的組織化表達便體現為以能指為載體并按照語言規則運作的欲望。作為要求(demande)減去需要(besoin)所剩下的維度,欲望在根本上并不指向任何特定的對象及其可能帶來的滿足,而是憑借與為其奠基的需要和要求有關的對象a來維系自身即欲望的狀態。換言之,欲望所欲望的正是自身的不滿足,而這種不滿足在其對象上便體現為,欲望主體最終只能一再發現作為引發欲望之原因的對象a,而找不到能夠為其帶來徹底滿足的終極對象“物”(das Ding)。
最后,就享受而言,它在拉康那里并非總是與欲望截然相分,而是存在錯位的可能,并且薩特曾專門探討的倒錯態度正是這種錯位的體現。從拉康的視角出發,“倒錯者的欲望實際上表現為‘享受的意志’。它由一種幻想支撐,而在這種幻想中,享受通過關于對象、小他者的知識和權力而被達到”。(59)Christophe Louka, “Pourquoi Lacan introduit-il une disjonction dans le concept freudien de sado-masochisme? ”, Les Lettres de la SPF, 2011/2 N°26, p.94.作為精神分析師以及弗洛伊德思想的后繼者,同樣關注倒錯問題的拉康,其思考進路卻顯然有別于薩特。“以臨床為指導,他得以區分兩種主體性的結構,即一種受虐狂的結構和一種施虐狂的結構,而弗洛伊德則試圖將這兩種性倒錯合并為一種實體,即施虐-受虐癖。”(60)Christophe Louka, “Pourquoi Lacan introduit-il une disjonction dans le concept freudien de sado-masochisme? ”, Les Lettres de la SPF, 2011/2 N°26, p.89. 在弗洛伊德那里,“從《性欲三論》開始,施虐癖和受虐癖在他看來就構成了同一種性倒錯的兩面,在施虐癖中是主動的一面,在受虐癖中是被動的一面。在其后來的工作中,他依然強調施虐-受虐癖這種統一的構想”。(Ibid., p.90.)可見,在此問題上,弗洛伊德的觀點受到了明確的質疑與挑戰,“拉康最終確定的性倒錯理論實際上蘊含著主動性與被動性之對立以及作為施虐癖與受虐癖的沖動之聯結的消解”。(61)Christophe Louka, “Pourquoi Lacan introduit-il une disjonction dans le concept freudien de sado-masochisme? ”, Les Lettres de la SPF, 2011/2 N°26, p.91.
拉康對倒錯的探討同樣經歷了一個發展過程。確切地說,“受虐癖問題在1960年代才真正在拉康的教學中得到探討。從1955年開始,在第二年度的研討班上,他就表明在施虐癖和受虐癖之間不存在反向對稱性。這一言論是孤立的,沒有發展,也沒有直接的后續。等到1963年的研討班和1967年的研討班,受虐癖尤其在其與施虐癖的關系中才成為細致反思的對象。他在這一時期賦予了對象a概念一種新的含義,他從此將其設想為欲望的對象-原因,也就是說先于欲望的東西。在1963年,他從焦慮的方面來探討對象a,而在1967年,他的話題則涉及幻想”。(62)Christophe Louka, “Pourquoi Lacan introduit-il une disjonction dans le concept freudien de sado-masochisme? ”, Les Lettres de la SPF, 2011/2 N°26, pp.92-93.下面,本文便主要圍繞這兩個關鍵節點展開分析。(63)除上述兩個關鍵節點,拉康在《康德與薩德》一文中也探討了相關問題,值得一提的是,據托斯卡諾考證,拉康在兩個不同的文本中分別給出了兩種對薩德式享受準則的改寫,而這兩種改寫恰恰分別對應施虐與受虐兩種倒錯態度。(Cf. Rodrigo Toscano, “Lacan avec Sade: objet a et jouissances, sadique et masochiste”, Essaim, 2009/1 N°22, pp.84-89.)
首先,“在關于焦慮的研討班上,他表明受虐癖何以從構成兩種性倒錯結構的四項出發而有別于施虐癖。就性倒錯設定了一種與大他者的關系即主體向大他者傳達自己而言,主體、對象a、享受和焦慮實際上得以界定性倒錯的結構。……他在其中特別強調無意識幻想在倒錯欲望的目標方面發揮的作用。如此一來,受虐狂設想他通過占據交換的對象、拋棄的對象和殘余的對象的位置而尋求大他者的享受,然而他的幻想掩蓋了實際上他的目標在于大他者的焦慮。施虐狂看似通過讓自己成為大他者的工具來尋求大他者的焦慮,然而他的幻想卻隱藏了他實際的目標在于大他者的享受。(64)相似的論述亦可參見Erik Porge, Jacques Lacan,un psychanalyste, Toulouse: érès, 2014, p.263。我們發現如此設定的受虐癖和施虐癖的結構不再是一種相反的聯結,反向的對稱性消失了”。(65)Christophe Louka, “Pourquoi Lacan introduit-il une disjonction dans le concept freudien de sado-masochisme? ”, Les Lettres de la SPF, 2011/2 N°26, p.93.
其后,“1967年的研討班《幻想的邏輯》,對拉康而言是深化并完善其性倒錯理論的契機,他以‘享受’的概念作為中心”。(66)Christophe Louka, “Pourquoi Lacan introduit-il une disjonction dans le concept freudien de sado-masochisme? ”, Les Lettres de la SPF, 2011/2 N°26, p.93. “享受從1958年開始在拉康的工作中作為原創概念出現。它在一種雙重對立中得到界定。一方面,它區別于快樂,而指代例如一種難以忍受的過度的快樂,或身體的極度張力、痛苦或受苦狀態。另一方面,它對立于欲望。……除此之外,還要加上:在拉康看來,享受指涉作為大他者的身體,也就是說身體是肉身所接受的能指在肉身中所產生的效果。”(Ibid., pp.93-94.)他闡明施虐癖與受虐癖實際上構成了兩種彼此不同、不具有對稱性的享受模式。“在與享受的關系中,拉康再一次表明施虐癖與受虐癖沒有構成一個對立的對子,一個并非另一個的翻轉。……施虐狂看似享受大他者的身體,但依賴于知道人們所享受的身體是否自己在享受的問題,他不知道自己成了這種享受的工具。從知道他要從他相對于大他者作為殘余的位置上騙取的享受而在大他者的領域發生什么無關緊要之時起,受虐狂似乎沒有施虐狂那么幼稚。”(67)Christophe Louka, “Pourquoi Lacan introduit-il une disjonction dans le concept freudien de sado-masochisme? ”, Les Lettres de la SPF, 2011/2 N°26, p.95. 盧卡還指出:拉康“對受虐狂與施虐狂結構的這種拒絕其互補性、拒絕其表面上的反向對稱性的劃分,也在1967年出版的《介紹薩赫·馬索克》中得到德勒茲的支持”。(Ibid.)在布勞斯坦看來,包括施虐癖與受虐癖在內的諸性倒錯之間之所以不存在互補性,究其根本乃是因為“倒錯者愛情生活的本質在于一種‘去錯綜化’(désintrication),后者就在于不經由(大他者的)欲望而獲得享受”,(68)Nestor Braustein, La jouissance, un concept lacanien, Paris: Point hors ligne, 1992, p.241.而欲望與享受在拉康學說中的張力由此便凸顯了出來。概言之,倒錯的“倒錯性”便體現在其享受的“非欲望化”,并將這種“非欲望化”的享受的意志偽裝成自己的欲望,幻想不經由大他者的授意與中介而直接實現身體與享受的(重新)連接,以重建在大他者及其話語、法則和欲望介入之前實在的身體作為純粹享受實體的“自體愛欲”(auto-érotisme)的原初狀態。
三、交互視域下的身體問題
經過以上梳理可以發現,薩特與拉康在身體問題上既有共通之處,又存在重要差異。
首先,二者的共性主要體現在:第一,薩特與拉康都明確反對笛卡爾式的身心二元論,堅決拒絕將身體視為與心靈(無論是薩特關注的意識,還是拉康關注的無意識)完全異質的物,而都試圖以不同方式揭示心靈的具身性或身心的含混性,并將身體揭示為心靈得以存在的條件和基礎——在薩特那里,身體是作為人的意識向世界敞開并向未來籌劃的在世實存的條件;在拉康那里,身體作為無意識的實在乃是無意識主體之愛欲與享受的基礎。第二,薩特與拉康對身體問題的探討都彰顯了身體的愛欲性,二者都將性(別)以及愛欲視為身體的根本維度,在這點上二者都明顯有別于胡塞爾和海德格爾對既無性別也無愛欲的身體的現象學描述,而顯然都更接近于弗洛伊德對始終處在性沖動與愛欲投注關系中的身體的精神分析考察。第三,薩特與拉康關于身體與愛欲問題的論述不僅都涉及以施虐和受虐為代表的性倒錯問題,而且二者在將施虐與受虐這兩種極端的倒錯態度視為主體與他者間關系敗壞扭曲的反面典型的同時,也都嘗試將這兩種態度或立場作為理解包含身體際性在內的人的整個一般性的存在結構的關鍵突破口,并且都在某種程度上有意無意地將其刻畫為黑格爾式的主奴辯證法在愛欲領域的體現。(69)通過不同方式與進路,兩人最終都不同程度地揭示出,試圖以主人自居的施虐狂何以在虐待關系中淪為有賴于為其提供享受的受虐狂這一“奴隸的奴隸”,而試圖自愿降格為奴隸的受虐狂何以在此關系中憑借其辛勤的“勞作”而成了“主人的主人”。
其次,二者的差異主要體現在:第一,正如上文所提到的,有學者已經指出,薩特對身體問題的關注在某種程度上似乎仍是為其意識哲學服務的,因此盡管身體在發生學上可能為意識的實存奠定基礎,但身體在存在論上依然難以擺脫其作為“具身化的意識”這一基本定位;而拉康對身體問題的關注盡管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是為其無意識(主體)理論服務的,但其晚年的思想進展則表明身體最終可能取代了無意識的主體而成為其所聚焦的核心問題——關鍵不再是如何為主體尋找一個身體,而是身體如何生成一個主體。第二,薩特關注的是身體的肉身化,即原本為其自身存在且同時作為工具而被使用的身體,何以在他者的注視下尤其是愛撫下成為一個為他人存在同時也為我存在的身體;乍看起來似乎與此恰恰相反,拉康關注的是肉身的身體化,即處于原初享受狀態的實在的肉身何以在語言能指的切割與塑造下成為一個有欲望且能夠言說的身體。由此可見,在薩特與拉康各自的思想語境下,二者對身體與肉身的理解似乎存在某種理論錯位:被薩特視為真正人性化身體的肉身,恰恰被拉康說成是經過大他者的話語和欲望塑造的身體,而被薩特視為工具性存在的身體,則似乎更多對應于拉康所說的尚未具備人性的原初的實在肉身。第三,在對愛欲和倒錯問題的理解上,薩特似乎更多將愛/受虐和欲望/施虐視為兩組具有反向對稱性的態度,認為一組態度的失敗往往會轉向另一組態度,甚至由此陷入一個周而復始的惡性循環;拉康則旨在揭示并強調愛與欲望以及受虐與施虐之間的不對稱性與非互補性,愛的挫折有可能引發欲望,受虐的失敗也可能轉向施虐,但其中并不存在任何必然性甚至傾向性,因為對愛的請求完全有別于在根本上無所求的欲望,而施虐與受虐也各自對應于一種相互獨立的主體結構與享受模式。
基于對薩特與拉康在身體問題上主要觀點之異同的分析,最后不妨讓我們嘗試一下,對未來現象學與精神分析交互視域下探究身體問題的可能進路做一番初步勾勒:一方面,心靈的具身性或身心的含混性應得到進一步闡發,身體的愛欲性應得到進一步彰顯,倒錯問題的重要性應得到進一步重視;另一方面,身體之于主體的關系或許可以通過進一步的深入研究而得到澄清,對身體與肉身的理解與界定或許可以通過進一步的理論整合而趨于一致,對愛欲與倒錯的把握或許可以通過進一步的現實考察而接近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