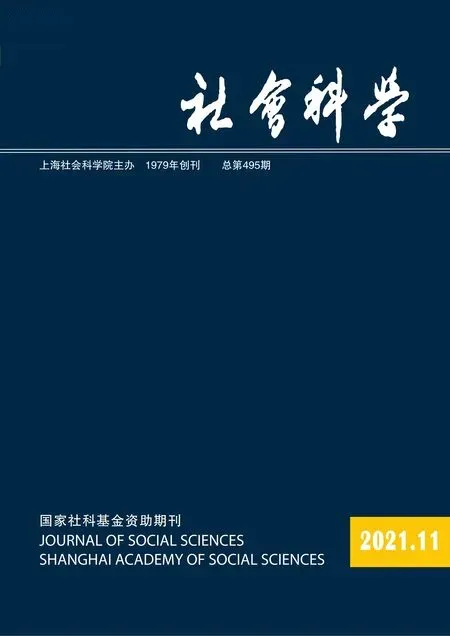有機體的破碎與無調時空的建構*
——德勒茲的電影思想資源
吳娛玉
作為現代科技支持下的新興藝術,電影與繪畫、攝影大異其趣。德勒茲認為,繪畫與攝影是一種特殊瞬間(instants privilégiés),強調某一瞬間的永久性和經典性,是一種理想的、綜合的、被定格時刻,以歐幾里得式的、以先驗的永恒姿勢(poses)來構建運動;而電影式的任意瞬間(équidistance das instantanés)將時間看作獨立變項,是笛卡爾式的、以內在的物質元素即以切面(coupes)來構建運動。盡管電影使用了靜態分切相片,每秒24格,選擇等距瞬間,制造連續感,是一種復制任意瞬間運動的系統,但電影給人們的印象不是相片集合,而是一種均衡畫面,運動作為一種直接條件(donnée immédiate)內在于這一均衡畫面,并直接提供一種運動-影像,所以電影不是“靜態分切+抽象時間”(coupes immobiles + temps abstrait),而是“真實運動-具體綿延”(mouvement réel→durée concrète)(1)Gilles Deleuze, CinémaI:L’image-mouvement, Paris: Les éditions de Minuit, 1983, p.10.,不是一種需要依據抽象時間計算的封閉集合,而是一種在運動中整體都發生過變化的開放綿延。于是,電影成為一種獨特的運動-影像。二戰后,一個有機的、系統的、虛構的運動-影像開始瓦解,取而代之的是一種更為真實的、荒蕪的、無力的時間-影像,尤其是1940年代的意大利新現實主義和1958年的法國新浪潮電影,以先鋒姿態襲擊并告別了傳統電影的生產模式和闡釋理論。已有電影理論無法解讀新的電影實踐,導致理論家一時失語,而德勒茲的兩部著作《電影Ⅰ:動作-影像》《電影Ⅱ:時間-影像》精準把握到這次變革的脈搏,恰如其分地闡釋了該轉型的內在理路和發展走向,也在中國學界產生了巨大影響。然而,現有研究多聚焦于運動-影像、時間-影像其一,少有追問德勒茲構建其從運動-影像到時間-影像演變的理論模型采用的思想資源。本文則試圖厘清在這次轉型中,德勒茲究竟針對了何種預設、采用了什么路徑,啟用了哪些資源,完成了從運動-影像到時間-影像的理論演變。
一、電影的定位與轉型:運動-影像的誕生與危機
(一)運動-影像即流動-物質
電影自誕生以來,常被作現象學解讀。胡塞爾認為人的意識總指向某個對象并以其為目標,意識活動的這種指向性和目的性即“意向性”,意向性是意識的本質特征,外部世界被人意向性光芒照亮之前是一片黑暗與混沌,只有當意向性投射于外部事物,外部事物成為意識的對象時,它們才有了意義與秩序。胡塞爾用意向性統一以往認識論中分裂的主客體。在他看來,人的意識不是對外界的被動記錄和復制,而是主動地認識和構造世界,它不僅通過意向性接受外界事物的性質,而是將這些性質組織成統一的意識對象。于是,意象對象不是客觀實體,意向作用不是經驗活動,而是對象在意識中的顯示方式,即對象的透視性變形以及意象關系體的統一化作用。電影鏡頭就是這樣一個意向活動。在此意義上,這種把握的“現象”不是事物對人類理性的作用,而是人類理性本身。
德勒茲認為真正的世界不是一個基于先驗意象和固定視域透視的世界,而是不斷運動變化的流動物質,無法確定基點和參照中心。這意味著知覺、意識不是先驗和預設的,而是外力給予某個流動的瞬間一個固定的視像中心,即柏格森意義上“被制造出來的”。電影如人的知覺一樣沒有基點和參照,它不是從無中心狀態進階到中心知覺,而在本身就處于無中心的狀態,柏格森認為運動影像是無限集合的物質世界,這種呈現物的集合即一種影像運動的世界。在這個呈現過程中,不是主體對客體的把握,而是所有影像、行動、反應的混合,是多種異質事物的相遇、影響和變化。“我們的身體接受的來自周圍實體的刺激,這些實體在其自身材質范圍內不斷決定著初期反射,因而在每個瞬間,大腦物質的這些內部運動都簡要地勾勒著我們可能對事物做出的行動。”(2)[法]亨利·柏格森:《物質與記憶》,姚晶晶譯,北京時代華文書局2018年版,第269頁。我們的身體就是行為和反應整體的影像。我們的眼睛、大腦就是我們身體局部的影像。大腦包含這些影像,同時也是其中的一個影像,即一個外在影像影響我,給我們傳遞、重構運動:這些影像存在于我們的意識之中,我們自己就是影像,即運動。在這種情況下,我不能談及我、我的眼睛、大腦和身體,只能視情形而定,一切都如無法確認的氣態。我的身體更像一個不斷更新的分子和原子的集合。這是一個普適變化、不斷波動、永遠動蕩的世界,沒有軸心、基點,沒有左右、高低,所有影像的無限集合構成一種內在性層面。影像即物質,影像與運動的同一性推演出影像與物質的同一性,如柏格森所說:“我的身體是物質,或者說是一個影像”。(3)[法]亨利·柏格森:《物質與記憶》,姚晶晶譯,北京時代華文書局2018年版,第4頁。
在此意義上,運動-影像即流動-物質,這不是機械論的物質世界,柏格森在《創造進化論》指出“機械論擺脫了那個準備去追求的目的,擺脫了那個理念上的模型。但它同樣認為:大自然像人一樣工作,將各個部分結合在一起;而只要對胚胎的發育瞥上一眼,便能知道生命運作與人的工作方式極為不同。生命的進展并非元素的聯合與相加,而是解體與分化。”(4)[法]亨利·柏格森:《創造進化論》,肖聿譯,華夏出版社2003年版,第75頁。盡管電影需要鏡頭剪裁、組合和某種外在性才能自洽,從而看似一個封閉系統、有限集合、靜態分切的機械論世界,但事實上,電影是一個無限集合,其鏡頭是運動的、內在的,它貫穿、融合并形成于每個系統的局部、系統與系統之間,運動擾亂這個封閉系統,使之無法絕對封閉。因此,它不是一個靜態時間分切,而是一種動態的時間透視、連續運動的整體,它自身形成的運動時間每次都屬于它,也即綿延。德勒茲認為:
鏡頭進行的運動動態分切并不只是表現一個變化整體的綿延,還在不斷地改變身體、局部、現象、維度、距離、身體的各個位置,因為它們構成影像中的某個集合。一個集合是由另一個集合生成的,這是因為純運動通過分割使集合的各種元素符合不同的分母,還因為它解構和重構這個集合,也因此連接一個基本開放的整體,而這個整體的本質是不斷地“合成”或變化、綿延。(5)Gilles Deleuze, CinémaI:L’image-mouvement, Paris: Les éditions de Minuit, 1983, p.38.
德勒茲繼承了柏格森生命哲學,將世界看作一個整體變化、不斷擴展的綿延狀態,德勒茲沒有從意向性這一固定中心、特殊立場對世界進行把握和交互,而是沿襲斯賓諾莎-柏格森傳統,將物質世界看作物與物隨機相遇、彼此關聯、無中心、無焦點的狀態。“封閉的形式是向心的,內在的;世界的整體包含在圖像框架內;開放式是離心的,向外的,作為移動窗口,代表潛在世界的可變部分。封閉式電影創造了一個世界,觀眾是一個受害者,屏幕中世界的完美一致性強加給觀眾,而開放式電影發現了一個世界,觀眾是一個客人,作為一個平等的人被邀請進電影”。(6)Thomas Eisaesser, Malte Hagener, Film Theory:An Introduction Through the Senses, New York and London:Routledge, 2010, p.16-17.
(二)運動影像的三種類型
德勒茲在讀解柏格森的運動命題中生成了電影的運動-影像問題:“通過電影,這個世界變成了自己的影像”。(7)Gilles Deleuze, CinémaI:L’image-mouvement, Paris: Les éditions de Minuit, 1983, p.10.電影不僅是運動的還原,還賦予了我們對運動的知覺,這樣的知覺呈現給我們一種主體視角下的純粹運動。德勒茲認為運動-影像是一個變化整體,在具體情況下分化為三種變型:知覺-影像、動作-影像和情感-影像。“有生命影像將成為在運動-影像的無中心世界中成形‘不確定性的中心’”。(8)Gilles Deleuze, CinémaI:L’image-mouvement, Paris: Les éditions de Minuit, 1983, p.91.人作為主體是這樣一個中心,會根據自己的實踐性利害原則,部分地接受來自外部的作用、部分地做出反作用,即運動的作用/反作用效應。
首先,根據柏格森的理論,人腦仿佛一張屏幕,物質的光投射在這一屏幕上,人腦依據利弊得失,選擇性的獲取一部分光粒子形成“像”(如圖1),這些“像”便形成了知覺,這是一道減法:“我們感知事物時,不太注意與我們需要無關的東西。應該從需要或利益上來理解我們從事物中保留的線與點,作為我們接收面和我們選擇的行為,作為我們可以回收的滯后反應。這是一種確定主觀性第一個物質時刻的方式:它是減法的,它從事物中減掉它不感興趣的部分。”(9)Gilles Deleuze, CinémaI:L’image-mouvement, Paris: Les éditions de Minuit, 1983, p.93.知覺被打了折扣,我們并非對所有的施加效果都會產生反應,感覺-運動回路已經形成了一個相對中心——即以人的利害、實踐性需要為依據,應對外部事物世界的一個相對的中心。德勒茲認為無數的運動-影像所組成的無中心的宇宙因生命知覺而形成“不確定的中心”。在所有作用/反作用層面上,知覺是被我們的身體“過濾和選擇出來的影像”,而身體占據著中心。被截流下來的部分形成為知覺,而部分接收了外部作用并獲得了知覺影像的人必然會做出其反作用,這個過程可以理解為外部把運動傳導給我的身體,身體通過外部觀察和內部情感的把握,向它們反射行動,這便是動作-影像的整個過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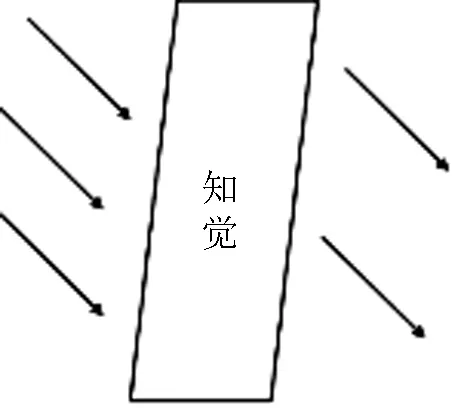
圖1 人腦影像與知覺作用圖
德勒茲認為情感是占據知覺和行動中間的間隔。反映在電影中是感覺神經中的一種運動傾向或運動努力,某種征兆和表情。情感-影像“是質或力量,是被表現物本身的潛在性。因此,其相應符號是表情,而不是呈現”,(10)Gilles Deleuze, CinémaI:L’image-mouvement, Paris: Les éditions de Minuit, 1983, p.139.情感-影像首先就是面部特寫、反應容貌,一張悲痛的臉,在大全景和特寫中給人的沖擊力是完全不同的。所謂知覺、情感、動作影像就在這樣的情況下出現,它們被稱之為運動-影像的三大類別。在運動-影像中的人總是做出積極的反應,這種模式體現在商業娛樂電影或戰前的傳統電影中,它們重復和強化了以人的實用、利害、實踐為前提的感覺-運動回路。在運動-影像中,時間是運動的附屬品、派生物,體現在剪輯環環相扣、空間銜接清晰、情境反應緊密結合,運動最終有一個結局。運動占據至高無上的地位,而時間是次要的,它被納入運動的體系之下,是“測量運動的數值”,并未成為鏡頭展示的對象。德勒茲指出這種依循運動的整體脈絡表現,形成了線性的因果鏈條,而這種線性時間構建是對自由時間的鎖閉。
德勒茲將生命運動-影像變換為電影運動-影像,電影視角代表了人的感知中心。人一方面把來自外部的作用反射回去,形成行動;另一方面在抗爭中吸收了作用的某些部分,形成情感。知覺與行動反映我們的反應能力,情感則反映我們的吸收能力。正是“知覺-情感-動作”的感知結構構成了德勒茲的運動-影像符號分類的依據:最初,呈現的是一個沒有中心的純粹運動-影像,但當它和人這個相對的中心發生關涉時,就生成分割為知覺/情感/動作這三種影像。作為相對中心的個人,從根本上就是這三種影像的組合。“運動-影像是電影的第一波,在這里攝影角度的運用穿越了可視的范圍,給予我們運動的直接印象,因此它開啟了我們對生命運動的思考。”(11)[英]科勒布魯克:《導讀德勒茲》,廖鴻飛譯,重慶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36頁。通過思考運動-影像背后知覺素材的深層運作機制,德勒茲開啟了一種新的電影哲學,電影不僅是一門藝術形式,更是重新理解事物的重要途徑。
(三)運動弱化與時間呈現
然而,電影誕生未久,德勒茲就宣告了運動-影像的危機。1958年法國新浪潮電影噴涌而出,以標新立異的理念、脫節虛無的節奏、緩慢無力的反應讓原先運動影像的理論啞然失語。具體來看,如果影像通過感知產生了情感,并隨之產生行動,感覺-運動環路順利進行,當感知-運動的鏈條停滯,感知-情感的環節將被無限延長,行動受阻便無法發生,這樣原本運行的環路就會發生斷裂。“無限開敞的時間先在于運動……當我們承認時間的先在性、時間的無限性與異質性(即個體內在的綿延不絕的異質時間),時間便成為運動的標準。”(12)司露:《電影影像:從運動到時間——德勒茲電影理論初探》,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30頁。也就是說,人在生活中感受到刺激時,會知覺到刺激作用,并做出某種應對行為。但如果一個人停留在被刺激并產生知覺的情境中,沒能促使人產生行動的意愿和動力,這時知覺的瞬間被無限拉長,在這種無力采取行動的情況下,人會在這個情感階段下無限停留,這也就意味著時間-影像的降臨。
與傳統情況不同,現代電影里更多的是人無法改變處境。德勒茲指出電影由運動-影像向時間-影像過渡與轉化,標志著二戰之后人們的“感知和情感進入了與‘經典’電影的感覺運動體系迥然不同的另一種體系”。(13)[法]吉爾·德勒茲:《哲學與權力的談判——德勒茲訪談錄》,劉漢全譯,商務印書館2001年版,第60頁。一開始人們認為運動-影像是合理的,但戰后人們的感覺系統與思維發生了微妙變化。二戰后的新影像使運動-影像陷入困境,感知-運動的回路失去作用,人物不再能對現實做出快速、直接的反應,電影中的人物表現為散漫、游移、靜止或僵化。感知-運動回路的耗竭代表了人們無法再對感知做出相應反饋,轉而沉浸在無力狀態,即所謂“不可思維”——面對被戰爭摧毀的世界和信仰,面對生活和情感的困境,人們只能出神。“純視聽情境取代了連貫的規則運動,對于那些游蕩的人們,不再表現他們有意識的動作,取而代之的是動作與動作之間充滿了斷裂的間隙,其中他們不再有改變處境的行動,精神和思維的運動超越了肢體的運動。”(14)周冬瑩:《影像與時間——德勒茲的影像理論與柏格森、尼采的時間哲學》,中國電影出版社2012年版,第172頁。純視聽影像的寫實不僅是環境的真實,更是情感和思維的真實。此時的時間已不再從屬于運動,而是運動從屬于時間。可以看出,運動影像發展到戰后已經面臨著巨大困境并亟待轉型,回到當時的歷史語境,會發現這一轉型駁雜、零碎,是一個不斷探索、實驗的過程,而德勒茲正從不同的理論家處尋找構建這一轉型理論的思想資源。
二、“思維的無力”:德勒茲對阿爾托的接受
(一)運動影像的危機:有機體的瓦解
在運動-影像中,剪輯(蒙太奇)是一種至關重要的組織情節、架構影片的方法,運動影像需要服從剪輯,而剪輯是一種“產品”,通過剪輯可以構建一個系統的有機整體。因此,電影也被說成是“智力電影”,而剪輯是“思維剪輯”。通過銜接、切換,蒙太奇可以確定出整體。愛森斯坦一直強調蒙太奇是影片的全體,即理念(idée)。
德勒茲認為格里菲斯把運動-影像的構成設計為一種組織、一個有機體(organisme),一個巨大有機單元(grande unite organique)。有機體包含各種變換的單元,即“一個包含了已分化局部的整體集合(ensemble de parties différenciée):其中有男女、貧富、城鄉、內外之分等等。這些局部被放在一種二元關系中,構成一個平行交替蒙太奇(montagéalterne paralléle),即一個局部的影像按照一定節奏連接另一個局部的影像”。(15)Gilles Deleuze, CinémaI:L’image-mouvement, Paris: Les éditions de Minuit, 1983, p.47.愛森斯坦受黑格爾辯證法的影響以對立蒙太奇取替格里菲斯的平行蒙太奇,用質的“跳躍蒙太奇”取代“協調蒙太奇”,作為擴延性(immensité)的整體不再是一個匯集所有組成部分的總和,而可以自行擴充、不斷增值。在這里,組成部分在所屬整體集合里相互作用、彼此相生,整體集合也會在組成部分中不斷生成、不斷改變,因此,這種交互因果、雙向關聯的螺旋不是從外部附加的規定,而是一種內部生產、不斷交錯的辯證方法。對立蒙太奇的意義在于兩個截然不同的影像并置所產生的并非簡單加和效果,而是疊加、交錯和相互作用中發生的質的飛躍,以冪的方式發生的意義增值。“事物才可以真正地在時間里伸展開,并因而變得更為廣闊,因為它們在時間里總是占據著一個比整體集合的組成部分或整體集合自身所據位置更大的位置。”(16)Gilles Deleuze, CinémaI:L’image-mouvement, Paris: Les éditions de Minuit, 1983, p.78.在此意義上,蒙太奇是思維的“智力程序”,一種刺激反射的活動。影像具有感覺特征的諧波,大腦皮層產生的諧波整體誘發思維,形成電影的我思:整體即主體。愛森斯坦在對立形態中設計刺激張力,以克服對立或轉換對立物的形式設計整體思維,影像應對思維形成刺激,迫使思維像思考整體那樣思考自己。愛森斯坦要證明剪輯的至高權力:電影的主體不是個體,它的對象也不是情節或故事;它的對象是自然,主體是大眾,在愛森斯坦看來電影而不是將其納入一個質量的同質性中,或將其限定在一個數量的不可分性中,而是將大眾個性化,這是戲劇、特別是歌劇一直嘗試而未獲得的東西。
然而,德勒茲指出:“當沖擊力不再屬于影像及其震撼,而是屬于被表現物的時候,人們就會被殘酷的專橫所左右;當崇高不再屬于創作,而變成被表現物的簡單吹捧時,何來大腦的刺激或思維的產生。這也許就是作者和觀眾的普遍缺陷。”(17)Gilles Deleuze, CinémaⅡ:L’image-temps, Paris: Les éditions de Minuit, 1985, p.214.大量的平庸作品導致了電影的滅亡,尤其是當大眾藝術被國家意識形態操控,淪為法西斯主義的宣傳工具時,早期電影的喪鐘被敲響。或許從一開始,運動-影像本質上就與戰爭結構、國家宣傳以及法西斯主義聯系在一起。
(二)思維的“無力”取代思維的“能力”
德勒茲從阿爾托那里獲得了批判的資源,在阿爾托相信電影的時期里,他認為電影涉及神經-生理的震撼,影像應該產生某種可以刺激思維的神經波。思維的運作體現在自身的產生、循環與重復中,影像需以思維運作為對象,只有這種思維運作把我們帶回影像的真正主體。從影像到思維,存在某種刺激或震撼,阿爾托看似與愛森斯坦觀點相似,但他很快放棄了這些主張并認為:“影像中的那些被騙來參加無數儀式的愚蠢人們永遠不可能使影像達到我們所期望于它的程度。詩已無力掙脫所有這一切,它只能是一種可能的詩,一種任人擺布的詩,它不用再期待電影什么了”。(18)[法]安托南·阿爾托:《電影的早衰》,載《作品全集》,伽利瑪出版社1990年版,第三卷,第99頁。這是阿爾托 1933 年與電影決裂的文章。轉引自 Gilles Deleuze, CinémaⅡ:L’image-temps, Paris: Les éditions de Minuit, 1985, p.215。事實上,阿爾托所說的電影真正的對象-主體不是思維的“能力”,而是思維的“無力”,他并非要電影從外部帶給我們一種單純的抑制,而是去追求一種內在崩潰,一種“思維偷竊”與脫軌。當電影只能制造抽象、形象或夢幻時,他不再相信電影;當電影呈現思維無力時,才值得相信。
精神的自動裝置不再由某種思維的邏輯可能性所限定,不再是形式上的逐一推理,精神自動裝置已成為木乃伊,并證明“思維即思維的不可能性”。表現主義的思維竊取、人格分裂、催眠的僵化、幻覺、狂躁的精神分裂似乎與此相似,但阿爾托的思維無力不是表現主義、超現實主義,不能同壓抑、無意識、夢幻、性或死亡混為一談,“阿爾托讓夢幻接受白晝治療,而表現主義則讓清醒接受夜間治療”。(19)Gilles Deleuze, CinémaⅡ:L’image-temps, Paris: Les éditions de Minuit, 1985, p.216.阿爾托認為電影同大腦的內在真實性相聯系,但這個內在真實性不是整體,而是一條斷痕,一條縫隙,電影的價值不是系統組織,整體架構,而是制造脫節、形成斷裂、分解力量、呈現漏洞。
阿爾托攪亂了電影-思維的關系,不再是由剪輯組成的一個可思考的整體,不再是由影像呈現的可陳述的內心獨白。思維取決于產生神經、骨髓的刺激,思維只能思考一件事情,就是我們尚未思考的事實,即思考整體的無力。“思維的無力”呈現出一個可被思考的整體的虛無形態或不存在性。正如布朗肖為文學作出的診斷:思維中的不可思考性的出場,既是思維的起源,又是它的障礙;思考者中另一個思考者的無限出場,可以摧毀一個正在思考的自我的獨白,這意味著“無法思考就有了思想”。(20)[法]莫里斯·布朗肖:《未來之書》,趙芩岑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49頁。阿爾托的構想是“假定一種思考沖動或思考強制力,其經過了各種各樣的分叉,從神經出發并與靈魂產生交流,其目的是達致思想。這樣一來,思想被迫思考的東西亦是思想自身的中樞的崩潰、斷裂、本性上的‘無力’,而這種無能力同時又是最大的強力-即作為未表明的力量的cogitanda[拉:思維存在],它們是形形色色的思想偷盜或思想的非法侵入”,(21)Gilles Deleuze, Différence et Répétition, Presses Univesitaires de France, 1968, pp.192-193.阿爾托追求一種無形象思想的啟示,他要奪取一種不聽任自己被表象的嶄新原則。他認為困難本身及其伴隨的問題與發問不是一種事實狀態,而是一種原則上的思想結構。“思想之中存在著無頭者,記憶中存在著失憶者,語言中存在著失語者,感性中存在著無辨覺能力者,思考不是先天的,而是在思想之中生發出來;問題不是先存著的思想,而是使尚未存在的東西誕生,思考不是回憶和天賦,而是創造,具有生殖性(génitalité)。”(22)Gilles Deleuze, Différence et Répétition, Presses Univesitaires de France,1968, pp.192-193.電影影像自它引發不規則運動起,就在操作一種世界懸念、表現一個混亂體的可見性。電影不像愛森斯坦所希望的那樣將思維可見化,而是探索一種不能被思考、不能被看到的潛在強力。在電影中思維雖被置于其自身不可能性的對面,卻能從中獲取一種更高級的再生力量。阿爾托認為電影不是夢幻,而是黑暗和失眠。
德勒茲認為“阿爾托是一位先驅,他使用‘真正的心理情境使走投無路的思維得以在它們之間找到一條可能的出路’,他還使用‘純視覺情境,讓劇情來自于視覺碰撞。甚至可以這樣講,這種碰撞來自于觀看的實體本身’”。(23)Gilles Deleuze, CinémaⅡ:L’image-temps, Paris: Les éditions de Minuit, 1985, p.220.不過,這種感知-運動的決裂需要較高條件,其本身也需要追溯人與世界關系的決裂。與感知-運動的決裂,令人既對難以容忍的事感到驚訝,又面對思維中不可思考者。不是思維以一個更美好或更真實的名義捕捉這個世界上的難以容忍,而是這個世界難以容忍才使思維不再思考世界和它自身。這種不可容忍性是日常生活庸俗性的永恒狀態。精神自動裝置處于預言者的心理情境之中,可以看得真,看得遠,但卻不能做出反應、不能思維。阿爾托的殘酷戲劇正是這樣:“我所說的殘酷,是指生的欲望、宇宙的嚴峻及無法改變的必然性,是指吞沒黑暗的、神秘的生命旋風,是指無情的必然性之外的痛苦,而沒有痛苦,生命就無法施展”,(24)[法]安托南·阿爾托:《殘酷戲劇:戲劇及其重影》,桂裕芳譯,中國戲劇出版社1993版,第93頁。這個“殘酷”從一開始就存在,是造成生存嚴峻、給人帶來痛苦的、不可改變的法則,但只有痛苦才能使生命施展。不論生活有多丑陋不堪,“殘酷戲劇”都敢于將生活的真實面目給觀眾剖開。
阿爾托并非把思維無力看作思維低能,而把它變成我們的思維方式,借用這種無力來相信生活并發現思維與生活的同一性。不是我們在制作電影,而是這個世界在我們的眼中形同一部電影。我們的感知并不全面,只能根據我們的經濟利益、意識形態、心理需求感知與我們有關或感興趣的部分。一旦我們的感知-運動模式發生故障、遭到破壞,就會出現另一個影像類型:純視聽影像,這是完整的、真實的、沒有隱喻的影像。它如實呈現事物的本質和無法辨識的特征,所以,戰后電影不再緊湊連貫,出現了漫無目的的構圖、脫節虛化的空間與空寂凝滯的靜物,這些影像某種程度上阻斷了運動的鏈條,發現了固定鏡頭的意義、呈現了直覺力量。純視聽影像成為直接表現時間的手段,把電影從規則運動中釋放出來。時間-影像引入了記憶、夢境等涉及意識與無意識的符號,影像不再形成邏輯序列。將人類感知世界的方式從線性因果聯系的敘事邏輯轉向一種非線性的、離散的和跳躍的思維方式,給予我們時間本身的影像,正是現代電影的價值。
三、音樂的獨立:尼采、巴赫金對德勒茲的啟示
(一)聲音的獨立與復調
在無聲電影到有聲電影的轉變中,聲音的位置和價值凸顯出來,但電影誕生以來就是一種視覺藝術,聲音被當作附屬和注釋。愛森斯坦的定位一直占據主流,他采用黑格爾辯證法,將視覺和聽覺統歸于一個更高更全面的“一”。這在無聲電影中已司空見慣,其雖然包含即興或計劃的音樂,但必須為描述、說明、敘事目的服務。當電影變成有聲的和有對白時,音樂從某種程度上獲得了自由,但德勒茲引用愛森斯坦通過分析普羅科菲耶夫的《亞歷山大·涅夫斯基》的音樂提出:“影像和音樂本身應該形成整體,從中提取一個視覺、聽覺共有的成分,找到一種既適合聽音樂又能閱讀視覺影像的方法,他認為整體應由超越高度統一的視覺和聽覺構成”。(25)Gilles Deleuze, CinémaⅡ:L’image-temps, Paris: Les éditions de Minuit, 1985, p.310.愛森斯坦試圖用一種更高的整體將視覺、聽覺合二為一,實際上是讓音樂臣服于視覺,為影片的統一性服務,這在新視聽電影中已不合時宜。
德勒茲轉向了尼采。尼采在《悲劇的誕生》中將古希臘文明描述為阿波羅與狄俄尼索斯的爭執。阿波羅屬于原則上的個人主義(principium individuationis),呈現優雅、冷靜、美麗的外觀,而狄俄尼索斯代表了迷醉、恣肆、非理性,是非理性成分主導的人類創造力。尼采認為概念所影響的視覺影像來自阿波羅,他按照某種尺度使影像運動起來,并通過田園詩或戲劇中介使之間接地表現整體;但整體也可被直接顯現,出現在與前影像不可公度的“直接影像”中,此即音樂的酒神影像。在酒神恣意的釋放中,人通向生命最深處體驗生命的激情與狂歡,美的外觀被打破,人面對的是生成和毀滅的痛苦,卻體會到和世界生命意志合一的歡樂。尼采認為悲劇始于薩蒂爾歌隊,是酒神智慧借他之口說話。“古希臘的薩蒂爾合唱歌隊(亦即原初悲劇的合唱歌隊)常常漫游其上的基地,正是一個‘理想的’基地,一個超拔于凡人之現實變化軌道的基地。希臘人為這種合唱歌隊建造了一座虛構的自然狀態的空中樓閣,并且把虛構的自然生靈(Naturwesen)置于它上面。”(26)[德]尼采:《悲劇的誕生》,孫周興等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46頁。尼采也贊同席勒的觀點,把歌隊的合唱看作隔絕現實,創造一個審美空間,保留自由詩意之地。在歌隊高唱酒神音樂時,人們由酒神刺激而感受到的與宇宙的生命本體合一的快感。尼采看來,音樂代表了一種酒神精神,音樂的直接影像是火的核心,周圍是阿波羅的視覺影像。
運動-影像要表現為一個變化的整體,視覺只是間接地表現,而音樂卻可以直接呈現。音樂是無形的、抽象的、純粹的形而上的,屬于非理性領域,只有音樂可以和世界的終極核心直接溝通交融。而尼采所謂直接顯現不是再現故事整體和時間秩序。音樂總以一種極不連貫狀態出場,也就是說,音樂與視覺不再是附屬關系而是處于不協調的對立狀態。在此意義上,新視聽影像中的音樂獨立了。那么,聲音又以何種方式存在?根據愛森斯坦的音樂觀,內心獨白構成帶有彼此協調或連貫的視聽表現特征,即每個影像具有一種決定調性,也具有限定其配合和隱喻可能性的諧波(當兩個影像具有相同諧波時,便產生隱喻)。因此,電影中存在一種統一性和整體性,可以囊括作者、世界和人物的復雜性和差異性。這種觀念一度是電影奉行的重要標準,但在新視聽電影中,內心獨白已被拆解地支離破碎,不再有完美的操作和配合,只有不協調與非理性分切,不再有影像的諧波,只有“脫節”的聲調。
德勒茲援引了巴赫金“復調”理論,“獨白”意味著眾多性格和命運構成的客觀世界,在作者統一的意志支配下層層展開,雖然主人公有自己的聲音,但他們的聲音都經過作者意志的過濾,只有刻畫性格和展開情節的功能,并沒有自己的獨立聲部;而復調意味著破碎的整體,作品中有眾多各自獨立而互不融合的聲音和意識,每個聲音和意識都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和價值,這些音調不是作者意識下功能性排布,而是平等地各抒己見。每個聲音都是主體,甚至可以被當作他人的意識,卻不成為作者意識的單純客體。巴赫金認為復調小說必須時而借用匿名的日常語言,或某一階級、集團、職業,人物的語言。因此,人物、階級、類型形成了作者的自由間接話語,如同作者形成它們的自由間接視角一樣。人物在作者的視角-話語中自由表達,而作者在人物的視角-話語中間接表達,匿名或擬人化的類型的反射構成多聲部的交融。戈達爾賦予電影以小說特有的力量,創造了許多諸如說情者的類型,我通過他們變成了另一個人成為連接作者、人物和世界的線索,并以斷線、折線、曲線地形式在其中不斷穿行。現代電影抹殺了影像的整體性,讓有機體發生破碎和瓦解,取消了連貫電影整體的內心獨白,成就了自由間接視角,于是,獨白的整一性變成了復調的破碎性和零散性,電影從單一的主旋律變成了眾聲喧嘩的多元體。
(二)現代電影中聲音的脫節
電影作為一種視覺主導的藝術,視覺影像通過聲音、說話、音樂、運動的循環維持整體性和統一性,無論有聲與否,內心獨白都不是一種獨立聲音而是一種視覺質料,它可以是間接陳述(字幕),也可以是直接陳述行為(說話和音樂)。聲音服從視覺,為影片整一性而服務。現代電影聲音力求脫離對視覺影像的依附而獲得自主性,如果說無聲片的字幕供人閱讀,采用了言語行為間接方式,有聲片使用言語行為的直接方式,現代電影則出現了特殊聲音的用法,即自由間接方式,它超越了直接與間接的對立,成為一個形式多樣的、獨特的、不可限制的維度。在布萊松的作品中,不是間接話語被當作直接話語,而是直接話語、對話被處理成出自另一個人之口,這就是著名的布萊松的聲音,即與戲劇演員的聲音對照的模特的聲音,在這里,人物的口氣就像他在聽別人說自己的話,以此獲得聲音的文學性,分割它的每一個直接反應,使之產生一種自由間接話語。這意味著感知-運動模式的完結,言語行為不再滲入行為和反應的連貫之中,不會呈現相互作用的脈絡。它不再是視覺影像的附屬或所屬,而是成為一個完整的聽覺影像。
當電影進入這種自由間接體制時,正是這些構成了所有新言語行為形式的一致性,因為這個行為,有聲片最終變成自生的。這種賦予言語自由間接價值的新結構隨處可見,與感知-運動決裂之后,聲音獲得了自主性,只涉及它自身和其他聲音。言語也掙脫出影像,成為一種創造行為,這表現在兩個方面:
一是從單一聲音變成多種聲音的融合。正如阿爾托提出的“物質化語言”,其最大作用不是制造統一性和附屬關系,而是營造一個詩意空間。阿爾托看來,戲劇不是生活的影子,而是要創造生活。“直接在舞臺上創造戲劇,蔑視演出和舞臺的種種障礙,這就要求發現一種積極的語言,積極和無秩序的語言,從而打破情感和字詞的通常界限”。(27)[法]安托南·阿爾托:《殘酷戲劇:戲劇及其重影》,桂裕芳譯,中國戲劇出版社1993年版,第 34 頁。當有聲和無聲的語言在戲劇空間中開始使用,觀眾會感覺到物體間、形式和意義間的一切關系都無法厘清,無秩序的語言造成空間混亂,而這種混亂使人們接近混沌,空間詩意由此誕生。而這些物質化語言、具有符號意義的語言刺激人們的感官造成直接刺激,削弱了戲劇的文學性,回到戲劇的本質——劇場性:不再是以劇作家為中心,而是呈現多聲部的復調效果,拉近觀眾和舞臺的心理距離,令觀眾沉浸在電影之中。
二是分解視覺和聽覺。小津安二郎在無聲片創造了空鏡、脫節空間與靜物,這表現了視覺影像的基礎,而“當他接觸有聲片時,雖然為時過晚,但仍成為這方面的先驅,他直接進入第二個階段……‘對顯現的影像和表現的聲音進行職能分解’”。(28)Gilles Deleuze, CinémaⅡ:L’image-temps, Paris: Les éditions de Minuit, 1985, p.322.他分解了兩種力量:視覺影像獲得一種新美學,視覺影像成為可讀的,具有無聲片沒有的力量;言語行為獲得獨立,創造了事件,呈現出有聲片第一階段所不具有的力量。不僅如此,戈達爾用“脫節”的方式讓電影具有無調性。影像間的關系不再是相互配合呈現諧波,而是非理性分切,不協調并置,脫節的界限。每個系列都涉及一種看或說的方式,可以是由標語反映的一般輿論的方式,可以是一個由觀點、假設、悖論或者甚至陰謀詭計和信口雌黃反映的一個階段、一種類型,一個典型人物的方式。每個系列是作者在可供其他作者使用的影像連貫中間接表達自己的方式,或與之相反,是某事或某人在被視為他人的作者視角中間接表達的方式。總之,不再有內心獨白串聯作者、人物和世界的同一性,只有自由間接話語、自由間接視角。作者要么通過某個自主的、獨立的、不同于作者的人物來表達,要么人物自己行動和說話,好像他自己的舉止和話語被帶給了第三個人。于是,視覺和聽覺的統一性被無調的、不和諧的間隙打破,聲音的特殊性和潛能就被盡可能釋放。
四、 “時空脫節”:小津安二郎對德勒茲的觸動
(一)空間的斷裂和虛無
德勒茲認為小津安二郎(1903-1963)是視覺符號和聽覺符號的發明者,是空間脫節的首倡者。他的作品借用游蕩(敘事詩)形式,而對象則是日本家庭的平凡日常生活。攝影機的運動越來越少:移動鏡頭是緩慢和低角度的“運動單元”,低位攝影機多是固定的,取正面或側面角度,淡出淡入鏡頭。剪輯的做法支配著現代電影,它是影像的過渡,或者純視覺停頓,直接產生或消除所有綜合效果。但現在特指情節——動作-影像——消失了,代之以純視覺影像和純聽覺影像,并以極其普通的對白構成劇本的主要內容。
首先,德勒茲認為在小津安二郎的作品中,“不存在溝口健二那條連接關鍵時刻和死與生者的宇宙自然線路,也不存在黑澤明包孕深邃問題的靈感-空間或并合空間,小津安二郎的空間是脫節的、虛無的,被升華到隨意空間狀態”。(29)Gilles Deleuze, CinémaⅡ:L’image-temps, Paris: Les éditions de Minuit, 1985, p.27.目光、方向,物品位置的假銜接鏡頭是經常性和系統性的。一個攝影機的運動情況可以提供脫節實例:在《初夏》中,女主人公踮腳前行,想給餐館中某人驚喜;這時攝影機后移,取主人公的中景;接著,攝影機在一個過道中前進,但這已不是餐館的過道,而是女主人公家中的過道。至于無角色、無運動的空鏡空間,它們都是沒有主人的內景、空靈的外景或自然風景。攝影機不被人物的運動和敘事節奏帶動,而是為靜止地呈現各種空間,這些空間在小津安二郎的作品中都具有一種自主性,它們實現了絕對的、純粹的靜觀,達到身心合一、虛實合一、主客合一、物我合一的境界。攝影機的運動制造了間隙,造成了影像的脫節,兩個影像的間隙非此非彼、不是和諧、匹配的,而是差異的、不均衡、不對稱的,銜接鏡頭是一種非理性的、相互獨立的分切,這意味著間隙比配合更為首要,間隙得到擴展,不再維護影像的連貫性,不惜跳越一些空白,脫離主線的控制。電影不再是“連貫的影像一個影像的、不間斷的連貫,影像奴隸”,在兩個動作、兩種情感、兩個視覺影像,兩個聽覺影像之間展示不可分辨性。正如布朗肖所言:“作品吸引著獻身于它的人走向它接受不可能性(30)朱玲玲在《走出“自我之獄”——布朗肖論死亡、文學以及他者》指出,可能性被布朗肖視為一種主體的同一化的權力和力量。參見朱玲玲:《走出“自我之獄”:布朗肖論死亡、文學以及他者》,《文藝理論研究》2013年第4期。考驗的地方。”(31)[法]莫里斯·布朗肖:《無盡的談話》,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162頁。布朗肖倡導的純粹文學宣告主體與文學的界限。在文學中,人們體會到無力,這種無力凸顯了主體認知能力的失效,文學是沉默、是虛無,是無用,它從不歸屬于穩定的真實。這種間隙不是影像運動產生的空白,而是對影像提出質疑的空白,沉默不再是話語的運動,而是對它的徹底質疑。
其次,事物“停滯”,突出“靜物”。一個空鏡空間的價值在于缺少可能的內容,而靜物不等于景物,靜物是由物品的在場和構成界定的,它們自身蘊涵或自成內容的載體,如德勒茲談到“《晚春》臨近結尾時,那個花瓶的長鏡頭。此類物品不必隱在空鏡中,但可以讓角色在某種朦朧狀態中生活和說話,如《東京女人》中那個花瓶和水果的靜物或者《夫人忘記了什么?》中那個水果和高爾夫球場的靜物”。(32)Gilles Deleuze, CinémaⅡ:L’image-temps, Paris: Les éditions de Minuit, 1985, p.27.這同塞尚的《靜物》異曲同工,幾枚蘋果凌亂地放在鋪著臺布的桌子或果盤里,就足以讓西方美術界震驚。在小津安二郎《浮萍物語》開頭,瓶子和燈塔參差對照是空與滿的差別,空鏡空間構建了純視覺和聽覺情境,靜物表現了命運、變化、過程。但所變之物的形式沒有變,沒有動,這就是時間。個人的時間是“片刻的純粹狀態時間”,是直接的時間-影像,它給所變之物以不變的形式,而在不變形式中又產生變化。夜變成晝或晝變成夜,如同一個光線時明時暗的靜物。(33)Gilles Deleuze, CinémaⅡ:L’image-temps, Paris: Les éditions de Minuit, 1985, p.27.這意味著靜物脫離了固有的、熟悉的解釋系統,自主地呈現著時間和自身,呈現出一種陌異感和獨異性。
德勒茲對小津安二郎的解讀正契合布朗肖的“黑夜”理論。布朗肖提出了二重黑夜。第一種夜是白晝的反面,與白晝對立卻共同構成圓圈式的循環,形成完整的世俗時間,如布朗肖所說:“夜終將被白日所驅散:白日在其帝國運作:它是自身的征服和經營;它朝向無限。……或者,白日不僅僅想要驅散黑夜,還欲侵占它。……黑夜變成白天,它讓光更豐饒,它賦予清晰膚淺的閃耀以一種更深的內在光輝。這樣,白日就是日和夜的統一體,辯證法的偉大允諾”。(34)[法]莫里斯·布朗肖:《文學空間》,顧嘉琛譯,商務印書館2003年版,第168頁。第一種夜恰恰是對真正夜的錯失與遺忘,它通過睡眠、靜息的方式積蓄自身迎接下一個白晝。與白晝的合謀和依附中,第一種夜被同化,成了白天的仆人與影子。在晝夜交替、日夜輪換中造就白晝的神話——并被冠以理性之名。白日強調人的主觀能動性,以一種外在暴力迫使事物歸屬于主體,而另一種夜跳脫了勞作的邏輯,對原有秩序進行顛覆和取消。布朗肖將另一種夜視為真正的晦暗體驗,它不作為人們自身權力實踐的空間存在而有著自律的原則。作為白晝的他者,夜是絕對的缺乏與虛無,消解了白晝的規律與秩序。靜物就是第二種夜,它跳脫了白晝的邏輯,確保了自身的真實,“讓事物向光投降,接受太陽的審判,就是對事物本身的晦暗性的剝奪,而驅迫事物成為‘形式’和‘意義’的存在”,(35)朱玲玲:《走出“自我之獄”》,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126頁。對靜物的凸顯不是按照白天的邏輯,即有用性、理性和功能性,而是按照黑夜的法則,是對一種陌異于主體的、事物本真的召喚,在對固有價值的懸置和拒絕中,靜物走向了自己的深處。
(二)從間接時間到直接時間
運動影像是一種有機敘事,是感知-運動模式的發展,人物根據它們對情境采取行動并做出反應,這個協調的抽象形式是直線式的歐幾里得空間。“它是人們根據節省原則,按照最小值和最大值的規律,釋放張力的范圍,比如:以最簡捷的途徑、最恰當的迂回、最有效的言語、最方便的方式獲得最大收效。這種敘事經濟學既體現在動作-影像和神經經絡空間的具象形態中,也體現于運動-影像和歐幾里得空間,運動和動作可以展現多種明顯的不規則形式,如斷裂、插入、重疊、拆解,但這些不規則的形式都服從那些屬于空間力量中心分配的規律。時間是被間接表現的對象,因為它來自于動作,從屬于運動,取決于空間。因此,不管時間多么混亂,原則上是有序時間。”(36)Gilles Deleuze, CinémaⅡ:L’image-temps, Paris: Les éditions de Minuit, 1985, p.167.
時間-影像則不同,它意味著感知-運動模式被純視聽情境取代。人物不能做出反應,只需“看到”情境中所發生的事。在小津安二郎的作品中,視覺為運動服務,代替動作占據一切位置,運動可以為零,人物可以靜止,鏡頭可以固定,這便是一種新的運動模式,即一種德勒茲口中的永不停頓的布朗運動,一種由不同規模運動構成而不再根據張力、目的、障礙、迂回來組織的多樣性、無規則運動。在此意義上,“布萊松的作品中,在新現實主義,新浪潮和紐約派的作品中存在著黎曼空間;在羅伯-格里耶作品中存在著量子空間;在雷乃作品中存在著概率和拓撲空間;在赫爾措格和塔爾可夫斯基作品中存在著結晶空間。”(37)Gilles Deleuze, CinémaⅡ:L’image-temps, Paris: Les éditions de Minuit, 1985, p.169.這些空間都是彎曲、流形的空間,其局部的接合不是預定的,可通過多種方式完成,從而構成一個脫節的、純視覺、聽覺乃至觸覺的空間。小津安二郎電影中是空虛的、無定形的、失去歐幾里得坐標的空間,這意味著這些空間是時間的直接呈現。我們不再面對來自運動的間接時間影像,而是面對產生運動的直接時間影像,我們不再面對可以被潛存不規則運動攪亂的有序時間,而是面對無序漫長時間產生注定是“不規則”的運動。剪輯不再以提取時間間接影像的方式組構運動影像,而是以提取所有可能運動的方式拆解直接時間影像的關系。
具體來看,超低機位構圖、凝滯鏡頭建構了小津安二郎獨特的視覺美學。其電影突出了沉寂的時間,鏡頭或對白可以在較長的空白中延伸,從而懸置了非凡與平庸之分,極端情境與普通情境之分,即使是死亡和死人,也只是自然遺忘的對象。德勒茲注意到小津安二郎作品中的特殊性:一切都是平凡、規律而日常性的。靜物就是對時間的直接呈現,小津安二郎的靜物具有一種綿延性,這種綿延表現了經歷一系列變化后的留存物。自行車、花瓶、靜物是時間的純粹的和直接的影像。每個影像都是時間,都是在時間所變之物的這樣或那樣的條件下的時間。“在平凡的日常生活中,動作-影像甚至運動-影像會讓位于純視覺情境,但它們發現了一種新型關系,它們不再是感知-運動的,不被納入時間與思維的直接關系之中。這就是視覺符號十分獨特的延伸:使時間和思維成為感覺的,讓它們有形有聲”。(38)Gilles Deleuze, CinémaⅡ:L’image-temps, Paris: Les éditions de Minuit, 1985, p.28.小津安二郎不是傳統的衛道士,也不是激進的先鋒派,而是日常生活的批評家。他以同情和體恤的方式書寫日常生活,“從無意義中發現不可忍受性,純視聽情境可以喚起某種預見功能,它既是幻覺的,又是證明的;既是批判的,又是同情的”。(39)Gilles Deleuze, CinémaⅡ:L’image-temps, Paris: Les éditions de Minuit, 1985, p.30.
五、運動-影像與時間-影像對照——建構一種新的電影表達模式
(一)有機體制與結晶體制
汲取多方思想資源后,德勒茲建構了兩種電影體制——有機的和結晶的。運動-影像是鏡頭獨立描述一個故事、一個對象的影像統一體,是一個外在視野對環境、人物的組織、排布和統攝,它預設了一個先存的真實敘事框架和價值觀念,運用與感知-運動模式組成了一個閉合的緊湊的回環,是一種表演者的電影,人物要對情境做出反應,觀眾的感覺被故事情節與視聽畫面組織,這就是動作事故帶來的束縛與限制。另一種即結晶體制,經常改變、違背、移動、肢解之前的描述。1940年代的意大利新現實主義、1958年法國新浪潮導演們采用低成本制作,啟用非職業演員,不用攝影棚而用實景拍攝,不追求場面刺激和戲劇化沖突。他們廣泛使用表達主觀感受和精神狀態的長鏡頭、移動攝影、畫外音、內心獨白、自然音響,甚至使用違反常規的晃動鏡頭,打破時空統一性的“跳接”“脫節”“跳剪”等,或采用一些以人物為對象的由輕便攝像機完成的跟拍,搶拍及長焦、變焦、定格、延續、同期錄音等紀實手法以結合主觀寫實與客觀寫實。他們從未經裝飾、真實樸質的現實環境中獲取素材,期待從中發掘一種具有破壞、重組、創造功能的純描述,這意味著運動反應的失效和脫節形成了一種純視聽情境。柴伐蒂尼把新現實主義界定為一種碰頭的藝術,即片段、瞬間、零散、失敗的相遇(recounter)。德勒茲認為希區柯克是顛覆這一觀點的首倡者,他把觀眾帶進了影片,角色在某種程度上成為了觀眾。角色徒勞地走動、奔跑、行動,所處的環境全面超越他的運動能力,看并聽到了他無法再用回答或行動判斷的東西,角色更像在記錄而非反應,他受制于某個視角,被它追蹤或追蹤它,而不是采取行動。觀眾如角色一樣,進入參與式沉浸式觀影體驗。
從動作-影像的危機到純視聽影像的演變:先從游蕩(敘事詩)影片開始,到脫節的感知-運動關系,然后獲得純視聽情境。有時兩者在同一部影片中并存,然而,傳統現實主義電影根據動作-影像的模式,事物與環境的真實性是一種功能性的真實性,受情境規定,接在動作中延伸。而純視聽情境中,電影不是故事,而是一種實錄、一種記錄精神。意大利新現實主義和法國新浪潮都試圖走出攝影棚,多拍實景和外景不用或少用人工搭制場景,取消舞臺化的照明技術和攝影陳規,讓演員去掉表演痕跡,保持自然狀態,充分調動演員的創造性,拋開浮夸形式轉向了真實的社會生活。
(二)連貫空間與任意空間
德勒茲認為:“有機描述假定真實是可以通過重建連續性的銜接鏡頭,通過確定這些連續性、同時性、永恒性的規律被識辨出來。這是一種可定位關系的體制,一種現時連貫的體制,一種合法、因果和邏輯聯系的體制,這個體制包納非真實、回憶、夢幻和想象,但只是作為它的對照物。想象實際上以頻繁變化和不連續性的形式表現出來,每個影像都與它所轉換的另一個影像互不銜接”。(40)Gilles Deleuze, CinémaⅡ:L’image-temps, Paris: Les éditions de Minuit, 1985, p.166.這種類型的影像作為現時現在或者真實危機的需要在意識中被現實化。一部影片可全部由夢幻-影像構成,這些影像將保存它們對抗真實-影像的脫節和不斷變形的能力。因此,有機體制包含這兩種存在方式,兩個彼此對立的端極,即真實視角上的現時連接和想象視角上意識的真實呈現。
結晶體制則截然不同:“現在脫離與其運動連接,真實脫離與其合法聯系,而潛在擺脫呈現表達真理的要求,開始呈現自身價值。這兩種存在方式在此合成一種循環,真實與想象、現時與潛在前承后繼,交換角色,難以識別。結晶影像是一個現時影像和它的潛在影像的聚合,兩種不同影像的不可識辨性”。(41)Gilles Deleuze, CinémaⅡ:L’image-temps, Paris: Les éditions de Minuit, 1985, p.166.從一個體制到另一個體制,從有機到結晶的過程可以不知不覺地形成,或者這些侵占行為可以無窮產生。這里存在著兩種性質不同的體制。在新現實主義作品(包括布景或外景)中,一切都是真實的,但有環境的真實與動作的真實之分,它不再是一種運動的延伸,而是一種通過不受約束的感覺器官獲得的夢一般的關系,動作似乎在情境中漂浮,而不是終結或控制這種情境。
新現實主義的視聽情境與傳統現實主義鮮明的感知-運動情境形成對立。感知-運動情境的空間是一個特定環境,包含一個揭示它的動作或引發某種適合它或改變它的反應。但一個純視聽情境則建立在“任意空間”之上,是脫節的、空蕩的。在新現實主義作品中,感知-運動關聯只能通過那些使其不安、脫節、失衡的意外發揮作用。視聽情境不再來自一個動作,也不在動作中延伸,而是一種新符號類型:視覺和聽覺符號。這些新符號涉及各種各樣的畫面:日常生活、特殊環境、主觀畫面、童年回憶、可視與可聽的夢境或幻覺,角色的行動不用被人看到,而觀眾用費里尼的方式——參與式的平面視角——實現一種“情感同化”。在最平凡或者日常性的情境釋放積蓄的“沉寂力量”。人們正面對一個不可確定性或不可區分性的原則,即人們不必區分想象與真實,身體與心理,德勒茲認為,在費里尼的作品里,如果主觀、心理畫面如回憶或幻覺不成為客觀,回憶就不能構成場景。“一個角色的內心世界包容著其他衍生角色,它因此變成了跨心理的,并憑借扁平的視點,獲得‘一個中性的、無個性的視象,即我們大家的世界’”。(42)Gilles Deleuze, CinémaⅡ:L’image-temps, Paris: Les éditions de Minuit, 1985, p.16.
又如,布萊松的視覺空間是一個散碎的和脫節的空間,但它的各個部分又被人為地重新緊密地銜接。德勒茲談到《扒手》中,三個問案犯的手如何以不同于拿東西的方式把巴黎里昂車站的零碎空間連接起來。影片主要表現手接近、放下、轉移、傳遞物品和物品在車站的流動,手具備了抓握(物品)和連接(空間)的雙重功能。(43)Gilles Deleuze, CinémaI:L’image-mouvement, Paris: Les éditions de Minuit, 1983, p.154.德勒茲表明,視覺符號和聽覺符號與真正的觸覺符號密不可分,純視聽情境不會在動作中延伸,更不由動作推演出來。它需要捕捉某些不可容忍、不可承受的東西。它不是人們在動作-影像的感知-運動關系中呈現的,而是超越感知-運動能力,將其意義擴至“不可承受”的地步。這時,“‘移動鏡頭變成拼貼手段,成為運動的非真實性證明’,而電影不再是辨認,而是認知的活動,即‘視覺印象的科學,強迫我們遺忘自己的邏輯和視網膜習慣’”。(44)Gilles Deleuze, CinémaⅡ:L’image-temps, Paris: Les éditions de Minuit, 1985, p.30.
(三)真實與潛在:線性時間與時間的分叉
德勒茲認為時間-電影不同于運動-電影,呈現了一種全新的時間觀。在運動-電影中,時間是一個隨著時刻流逝而展開的故事鏈條,運動是在線性時間基礎上計量的,但時間-電影中,時間不均質、等量、按照一個方向流逝,而是一種凝滯、凍結、閃回、重復、甚至綿延狀態,這意味著時間從單一線條變成多維晶體,原來在線性時間中不可能實現的事情在多維晶體時間中變成了可能。如果明天可能爆發一場海戰是真實的,如何解決下列悖論:要么承認不可能來自可能,即如果海戰爆發,它就不再有不爆發的可能,要么承認過去無需是真實的,海戰有可能沒爆發。人們很容易視其為詭辯,但它卻表明了思考真理與時間形式的直接關系的困難。德勒茲受萊布尼茲啟發,“他認為海戰可以發生也可以不發生,它不屬于同一世界,因為海戰可以在一個世界中發生,在另一個世界中沒發生,而這兩個世界都是可能的,但它們之間是不可‘并在’的。萊布尼茲因此應該杜撰不可并在性這個絕妙概念(與矛盾不同)以便既解決了這個悖論,拯救了真理。來自可能的,不是不可能,而是不可并在性,所以過去可以是真實的,無需真正發生。”(45)Gilles Deleuze, CinémaⅡ:L’image-temps, Paris: Les éditions de Minuit, 1985, p.171.
這意味著這個世界不是一個向量狀態,而是一個可能的、潛在的世界,不可并在物有可能在于同一宇宙。正如博爾赫斯描繪的,相互靠攏、分歧、交錯或永遠不干擾的時間織成的網絡包含了所有的可能性:
方君有個秘密;一個陌生人找上門來;方君決心殺掉他。很自然,有幾個可能的結局:方君可能殺死不速之客,可能被他殺死,兩人可能都安然無恙,也可能都死,等等。在彭家的作品里,各種結局都有;每一種結局是另一些分岔的起點。有時候,迷宮的小徑匯合了:比如說,您來到這里,但是某一個可能的過去,您是我的敵人,在另一個過去的時期,您又是我的朋友。(46)[阿根廷]豪·路·博爾赫斯:《小徑分岔的花園》,載《虛構集》,浙江文藝出版社2008年版,第79頁。
在時間影像中呈現的是時間的迷宮,是一條分叉線和一條不斷分叉的線,它經歷過不可并在的現在,又回到無需真實的過去。一種新敘事結構由此產生:敘事不再是真實的、實現的,而是呈現為一種潛在的強力,保存了不可并在現在的共時性或無需真實的過去的并存性。結晶描述已經獲得了真實與想象的不可辨識性,而與之相應的虛構敘事給現在提出了不可解釋的差別,給過去提出了真實與潛在的不可辨識的交替。長鏡頭不是呈現運動的單一與交替,攝影機不再滿足跟蹤角色的運動,電影避免對某一空間的描述隸屬于思維功能,拒絕主觀對客觀的呈現模式,放棄真實和想象的簡單區分,重塑一種不可辨識性,進而重新定義真實。正如巴贊不贊成按社會內容界定意大利新現實主義,他認為真實性的一種新形式,這種新形式被假定為離散、省略、游移或飄忽不定,并通過將浮動的事件與微弱的連帶關系凝成聚塊的形式,真實不再被重現或復制,而是被“直擊”(visé),不是表現一個已被破譯的真實,而是“直擊”一個有待破譯、曖昧的真實。(47)Gilles Deleuze, CinémaⅡ:L’image-temps, Paris: Les éditions de Minuit, 1985, p.7.于是,通過時間交叉和多維呈現,我們的世界就從單一、固定的判斷變成多元、復雜的可能,真理也不再是預設好的唯一解,而是待破譯的不同時間線中的問題。
結 語
在20世紀40、50年代意大利、法國電影出現巨大轉型后,德勒茲構建了兩種影像模式:運動-影像,即感覺、反應、運動模式被剪輯、組織起來的時間間接影像,與視覺符號、聽覺符號處于脫節、斷裂和游牧狀態,作為時間的直接影像的時間-影像,在此時間不是計量運動的尺度,而是運動變為時間的視角,整個影像不僅可看,而且可讀。這一轉變中德勒茲援引了阿爾托、巴赫金、尼采、布朗肖、小津安二郎等資源,從“無力的思維”“音樂的獨立”“時間的凸顯”等幾個方面勾勒這一轉型的理論脈絡。從有力到無力,從獨白到復調,從同一到差異。在這些思想資源的背后體現了一種新的解讀世界的方法,世界不是被有機組織的,而是一種偶然相遇;不是預設真理,而是“直擊”到的疑問;不是歐式直線空間,而是一種布朗運動、黎曼空間。盡管新浪潮電影的先鋒性在1964年之后逐漸衰退,但德勒茲的理論闡釋卻依然熠熠生輝,他詮釋的這一認知模式對后人類電影、科幻電影、當代先鋒電影仍葆有較強解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