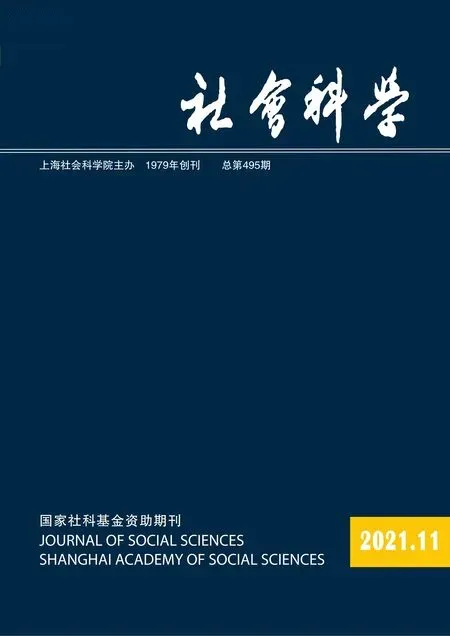生存分析與真理意識*
——在方法意識與思想本身之間行走
尚文華
思想是關(guān)于存在本身的“事情”,它能夠超出自身進(jìn)入存在并與存在共屬一體,這就是真理這個(gè)詞所指稱的基本意義。就此而言,真理的道路(即其在時(shí)間中的發(fā)生和運(yùn)行)本就是思想的道路和存在的道路。如何進(jìn)入這條道路乃是思想首先的任務(wù)——如果這一點(diǎn)保證不了,它可能就偏離了存在或真理本身。因此,思想如何切中真理(其實(shí)也是回到存在自身的意義)就成了檢驗(yàn)其能否作為自身而立的關(guān)鍵。這種“如何切中”乃是一種方法意識。因此,于思想而言,方法首先不是什么科學(xué)方法論,以及其他關(guān)于“什么”的方法論——它們以存在已經(jīng)被把握為“什么”為前提;它需要以如何“進(jìn)入”存在作為衡量自身的尺度:相對于已經(jīng)被把握的存在(者)而言,存在自身的超越性會引導(dǎo)思想的運(yùn)行;這種思,以及這種由存在引導(dǎo)而進(jìn)入存在的方法,是一切具體的思想、觀念、方法論等成立的前提。
西方近代思想史中出現(xiàn)過經(jīng)驗(yàn)的方法、數(shù)學(xué)的方法、自明證的方法、(1)斯賓諾莎、培根、洛克、笛卡爾等都為此做過努力,并在近代自然科學(xué)的進(jìn)展中發(fā)揮著關(guān)鍵作用。在科技哲學(xué)研究界與現(xiàn)象學(xué)研究界,經(jīng)驗(yàn)和數(shù)學(xué)的研究方法,(現(xiàn)象學(xué)性質(zhì)的)自明證方法得到相對充分的探討。先驗(yàn)論證的方法以及辯證法等。(2)先驗(yàn)論證的方法以及辯證法分別由康德和黑格爾推動。陳嘉明教授、黃裕生教授等充分注意到先驗(yàn)論證之于近代哲學(xué)的意義;辯證法則一度主導(dǎo)了馬克思和黑格爾的研究,其影響力至今猶在。故而,本文第一部分通過批判這兩種方法來展開對生存分析方法的探討。這些方法都是由尋求真理的動機(jī)所推動。盡管這些方法對真理或存在問題的切入點(diǎn)各不相同,但它們分享了一個(gè)共同的基礎(chǔ):尋求關(guān)于存在的真理性知識。問題是,存在能夠知識化嗎?能夠知識化的存在還是存在本身嗎?正是在知識與存在問題相聯(lián)結(jié)的關(guān)鍵之處,克爾凱郭爾開啟了全新的探討,他引入近代以來一直被忽視的生存問題,從而一種不同于尋求真理性知識的哲學(xué)方法被引導(dǎo)出來。(3)克爾凱郭爾對生存和生存分析方法的界定和分析是沿著基督徒的生存狀況展開的,不過他的研究被忽視了近半個(gè)世紀(jì),直到海德格爾的生存論分析出現(xiàn)才重新激活了克爾凱郭爾。這導(dǎo)致德文和英文學(xué)界的克爾凱郭爾研究被“強(qiáng)行”整合到海德格爾研究中。Paul Ricoeur、John Wild等學(xué)者的相關(guān)研究就是如此。20世紀(jì)后,克爾凱郭爾對生存和生存分析的研究才真正擺脫了海德格爾研究的束縛。這以C. Stephen Evens, George Pattison, M. Jamie Ferreira等學(xué)者的相關(guān)研究為代表。本文即是在生存分析與真理(意識)之間切入近代思想史,直面漢語學(xué)界所一直忽視的一個(gè)關(guān)鍵問題。
一、“生存”何以成為問題:一種方法論的視角
如何獲得一種(認(rèn)識性的)方法來切中真理問題(取代信仰的出發(fā)點(diǎn)位置),是近代以來思想家需要解決的基本問題。數(shù)學(xué)的方法、經(jīng)驗(yàn)的方法、見證的自明性等,都曾經(jīng)一度主導(dǎo)思想界,但它們面臨的共同問題是,自由無法在其中呈現(xiàn)——而自由恰是現(xiàn)代性確立自身的基準(zhǔn)。在自由這個(gè)問題上,康德邁出了關(guān)鍵一步,但他采納了先驗(yàn)論證的方法。(4)可見《純粹理性批判》“認(rèn)識論”分析部分。學(xué)界也有眾多文章討論先驗(yàn)論證問題。這種方法保證了知識的普遍性和必然性,并引導(dǎo)出無條件的絕對者的存在,或者說,正是無條件者的存在保障了知識的普遍必然性;同時(shí),自由因成為可能。相關(guān)于人的道德行為,自由與意志問題聯(lián)合起來,自由意志開始成為現(xiàn)代性和現(xiàn)代社會的奠基性原則。(5)這兩點(diǎn)分別是《純粹理性批判》和《實(shí)踐理性批判》的內(nèi)容。
可以說,這種先驗(yàn)論證的方法,一方面使經(jīng)驗(yàn)成為一切的起點(diǎn)——一切知識都源于經(jīng)驗(yàn);(6)《純粹理性批判》“導(dǎo)言”開篇。另一方面使知識能夠不停留于經(jīng)驗(yàn)而進(jìn)入先驗(yàn)甚至超越的存在領(lǐng)域——無條件者或絕對者的存在、物自體的存在、自由的存在意義(非選擇意義的自由)等,開始成為思想的對象。自笛卡爾開啟現(xiàn)代意義上的意識原則之后,康德實(shí)現(xiàn)了近代以來思想史的第一次大綜合,其關(guān)鍵就是這種方法(論)意識的突破。
但這種方法有內(nèi)在的無法克服的缺陷,它在經(jīng)驗(yàn)性的存在(意識的建構(gòu))和超越性的存在(存在本身)之間劃下了一個(gè)深深的無法跨越的鴻溝。“為知識劃定一個(gè)邊界,以為信仰留一個(gè)空間”,這句話證明了康德本人對此有深切的意識。非但信仰問題如此,存在問題也被懸置在經(jīng)驗(yàn)和知識之外。在《判斷力批判》中,康德意圖彌合兩者之間的巨大裂痕,但他給出的反思判斷力原則依然是主觀的原則。換言之,對于存在自身怎樣,意識只能給出一種主觀的形式的合目的性原理。(7)《判斷力批判》第二部分。可以說,在思想問題上,康德把人類的主觀性推到極致,這意味著真正的方法和思想原則呼之欲出。在《精神現(xiàn)象學(xué)》“導(dǎo)論”部分,黑格爾給出了一種新的方法原則:
意識之一般地具有關(guān)于一個(gè)對象的知識這一事實(shí),恰恰就已經(jīng)表明是有區(qū)別的:一個(gè)環(huán)節(jié)是某種自在于意識之外的東西,而另一個(gè)環(huán)節(jié)是知識。……根據(jù)這個(gè)現(xiàn)成存在著的區(qū)別,就能進(jìn)行比較考查。如果在這個(gè)比較中雙方不相符合,那么意識就必須改變它的知識,以便使之符合于對象;但在知識的改變過程中,對象自身事實(shí)上也與之相應(yīng)地發(fā)生變化;因?yàn)閺谋举|(zhì)上說現(xiàn)成存在著的知識本來是一種關(guān)于對象的知識:跟著知識的改變,對象也變成了另一個(gè)對象。……意識因而就發(fā)現(xiàn),它從前以為是自在之物的那種東西實(shí)際上并不是自在的。……意識對它自身——既對它的知識又對它的對象——所實(shí)行的這種辯證的運(yùn)動,就其替意識產(chǎn)生出新的真實(shí)對象這一點(diǎn)而言,恰恰就是人們稱之為經(jīng)驗(yàn)的那種東西。(8)[德]黑格爾:《精神現(xiàn)象學(xué)》上卷,賀麟、王玖興譯,商務(wù)印書館1997年版,第59-60頁。
這里,黑格爾重新界定了經(jīng)驗(yàn),這個(gè)界定意義深遠(yuǎn)。意識具有關(guān)于對象的知識本身證明,對象的存在與意識的建構(gòu)之間既存在現(xiàn)成的區(qū)別,也存在最內(nèi)在的比較性關(guān)聯(lián)。如果在比較中不相符合,意識會改變其建構(gòu)方式使其符合對象,同時(shí),對象的存在也發(fā)生了相應(yīng)改變,即并不存在意識之外的、與意識無關(guān)的自在存在。相反,意識與對象的存在本就是在辯證過程中相互成就。黑格爾把這種由辯證運(yùn)動而產(chǎn)生的真實(shí)的對象稱為經(jīng)驗(yàn)。換言之,經(jīng)驗(yàn)的對象不是現(xiàn)象,而是意識活動中產(chǎn)生的新的也是真實(shí)的對象。這個(gè)界定對康德式經(jīng)驗(yàn)的突破表現(xiàn)在兩點(diǎn):首先,它把意識認(rèn)識與對象存在的時(shí)間性甚至實(shí)踐性關(guān)系帶入思想的視野;其次,它把存在問題引導(dǎo)出來。據(jù)此,存在并非經(jīng)驗(yàn)之外的自在存在。相反,經(jīng)驗(yàn)若離開存在,就只能關(guān)注同一性建構(gòu),因而是受到了限制的經(jīng)驗(yàn);存在若離開經(jīng)驗(yàn),就只是一個(gè)思想的斷定或者論證,其與經(jīng)驗(yàn)的差異就是絕對的,因而無法成為思想對象。真實(shí)的情況乃是,存在與經(jīng)驗(yàn)之間是一個(gè)由同一性活動和差異性活動共同展開的辯證運(yùn)動過程。
這個(gè)辯證運(yùn)動過程(也是經(jīng)驗(yàn)過程)在方法上被領(lǐng)會為辯證法。辯證法是一種真實(shí)的思想方法,其起點(diǎn)是經(jīng)驗(yàn)(包括各種意識活動),其過程是經(jīng)驗(yàn)與存在的運(yùn)動,其終點(diǎn)則是存在本身。事實(shí)上,如果只關(guān)注這個(gè)運(yùn)動過程,與其說經(jīng)驗(yàn)的認(rèn)識在先,因而意識產(chǎn)生新對象(存在),不如說正是存在自身的發(fā)生和運(yùn)動引導(dǎo)了意識活動;因?yàn)槿魺o存在的自行發(fā)生和運(yùn)動,意識不會發(fā)現(xiàn)其同一性建構(gòu)不同于對象的存在。黑格爾之所以強(qiáng)調(diào),“意識產(chǎn)生出新的真實(shí)對象”,其本意在于意識活動窮盡存在的顯現(xiàn),因而使得存在本身成為思想,從而實(shí)現(xiàn)思想與存在的共屬一體的真理意義。這已經(jīng)預(yù)示了黑格爾思想體系指向的乃是真理本身,因此,除了在思想意義上說辯證法是一種指向真理的認(rèn)識方法外,在真理的終極意義之處,辯證法恰好不是一個(gè)認(rèn)識性的方法——認(rèn)識總是在時(shí)間和實(shí)踐進(jìn)程之中的,認(rèn)識總是時(shí)間中的“人”在認(rèn)識。
或許源于思想本身的形式性沖動,或許源于經(jīng)典的哲學(xué)思想范式,這種終極性訴求盡管完成了思想的基本要求,其起點(diǎn)和過程亦把時(shí)間和認(rèn)識活動作為重要的思想形式和內(nèi)容,但它也確實(shí)在關(guān)鍵的終極性位置根本性地錯(cuò)失了“時(shí)間中的‘人’”——克爾凱郭爾把這種時(shí)間中的“人”,以及“人”在時(shí)間中的展開(包含各種活動)稱為“生存”,并據(jù)此批評黑格爾那里沒有生存。(9)參見[丹麥]克爾凱郭爾:《最后的、非科學(xué)性的附言》,王齊譯,中國社會科學(xué)出版社2017年版,第77-89頁。對于黑格爾來說,思想與存在問題已經(jīng)如此地切身和本己(意識意義上的),怎么能從這里出發(fā)思考和界定生存呢——生存明明是個(gè)如此平常而“不哲學(xué)”的“事情”,它怎么能成為思想與存在的交匯點(diǎn)呢?
二、“生存”為何:一種信仰分析的思路
黑格爾的思想深度“先行”決定了生存的深度。或者說,如果生存能夠成為思想的出發(fā)點(diǎn),它能夠獲得的形式和內(nèi)容深度絕不能再倒退回去——如果不是有所添加的話,否則它無法確立自身的思想和存在意義,更不能保障一切對象的思想和存在意義(真理意義)。這也便為我們接下來的分析提供了基本的尺度:生存若能成為思想和哲學(xué)的主題,其運(yùn)作空間必定在存在與真理之間,而絕非任何單純主觀的事情。在克爾凱郭爾這里,信仰是切入生存問題的基點(diǎn):對信仰的分析揭示出生存所具有的絕對深度。
何謂信仰?讓我們從它的反面說起。無論數(shù)學(xué)的方法、經(jīng)驗(yàn)的方式,還是先驗(yàn)論證的方法、辯證的方法,獲得有關(guān)“真理”的知識都是其最終目的。這是一種理性的立場,這種理性立場有一個(gè)基礎(chǔ)預(yù)設(shè):存在是可認(rèn)識的;如果是不可認(rèn)識的——像康德做的那樣,它就與由認(rèn)識起點(diǎn)建構(gòu)起來的東西存在無法跨越的鴻溝,因而最終康德還是訴諸反思性的判斷力來解決這個(gè)問題。“存在是可認(rèn)識的”,這個(gè)預(yù)設(shè)的基本意義是:存在只能呈現(xiàn)在認(rèn)識的建構(gòu)中,或者說,本質(zhì)先于存在、也決定存在;若非如此,理性無法斷言,它的知識就是關(guān)于存在的知識。可以說,無論理性的知識建構(gòu)有多宏大,哪怕建構(gòu)出作為存在本身或者最高存在的“神”,這個(gè)“神”也是在一開始就被決定了的:它是一個(gè)出于本質(zhì),完成本質(zhì)的終結(jié)點(diǎn)而已。
理性要預(yù)設(shè)“存在是可認(rèn)識的”,并據(jù)此“建構(gòu)終極的存在或神”,這證明,存在對于理性乃是無法擺脫的首要問題;或者說,理性一開始面對的就是存在。正因?yàn)榇嬖诓粩嗟貨_擊著它,它才要把存在建構(gòu)起來;正因?yàn)槭鞘滓模乓A(yù)設(shè)其可認(rèn)識性。就此而言,存在乃是理性的界限,既是其起點(diǎn)的界限,亦是其終極的界限,因?yàn)檎J(rèn)識的終極性建構(gòu)來源于這個(gè)預(yù)設(shè)。在預(yù)設(shè)和建構(gòu)之前,作為理性之界限的存在乃是“不可知的”,不可知性才是理性不斷意圖跨越這個(gè)界限的動力。作為一種理性存在者、一種根據(jù)其理性存在而建構(gòu)知識的存在者,除了以理性的方式之外,“人”有無其他可能的“生存樣式”觸及理性的預(yù)設(shè)和建構(gòu)之前的存在呢?與理性面對存在,并總是意圖將之建構(gòu)起來的方式相比,這是怎樣的一種存在樣式呢?
在克爾凱郭爾的分析語境中,基督徒的信仰正是這樣一種生存樣式。首先,我們無法“理性地”給出信仰如何產(chǎn)生的答案,因?yàn)檫@樣做會讓信仰淪為理性的對象。其次,信仰是基督徒式生存的“事實(shí)”,是不是基督徒都無法拒絕這一事實(shí)。因此,接下來的任務(wù)是分析信仰如何切中理性必須面對,且在理性之前的存在(于信仰而言,是上帝的存在)。信仰這一切身且根本的生存現(xiàn)象所指向的存在(上帝)不是由理性建構(gòu)起來的,因而不是理性認(rèn)識的對象;但同時(shí),因其切身和根本,這種存在于生存而言是實(shí)實(shí)在在的。進(jìn)一步,因?yàn)樾叛鍪浅隼硇哉J(rèn)識的,所以這種存在才是最實(shí)在的,是真實(shí)本身,與之相對的生存則是“虛無”(有限性本身,罪);但因?yàn)樾牛婺軌蛟谶@種存在中被建立起來。在建立生存的過程中,理性雖然起作用,但它不是起點(diǎn),換言之,在信中領(lǐng)受多少,理性便能走多遠(yuǎn)。這便是由信仰和存在“組建起來”的生存,在時(shí)間中,它們共同組建起來一個(gè)生存過程。(10)信仰與理性的出發(fā)點(diǎn)之爭;根本有限性即罪性的意義,及其如何在理性的建構(gòu)的爭辯中“確證”自身;以及個(gè)體、共同生存的建構(gòu)等;筆者都有相應(yīng)分析。參見尚文華:《自由與處境——從理性分析到生存分析》,中國社會科學(xué)出版社2018年版,第三、四章。
我們需要進(jìn)一步追問的是,信仰是否是唯一的“讓”面對存在的生存建立起來的生存樣式?答案是否定的,因?yàn)橹辽偻ㄟ^對面對死亡的“畏”(Angst)的分析,海德格爾給出了一種更一般、更普遍的樣式,即每個(gè)個(gè)體的生存中都會出現(xiàn)的生存現(xiàn)象。死亡意味著終結(jié),能夠在“畏”中“先行”進(jìn)入死亡則意味著,在當(dāng)下的生存樣態(tài)中,終結(jié)一切可能性的完整可能性(含納了過去、未來和現(xiàn)在的整體結(jié)構(gòu)及其相關(guān)的生存內(nèi)容)能夠進(jìn)入生存之中——其實(shí)也便是生存的存在意義本身;并且,這種進(jìn)入讓生存已經(jīng)獲得的一切現(xiàn)實(shí)性都重新進(jìn)入可能性中,因而生存向著無限的可能性(即不受現(xiàn)實(shí)性限制)本身敞開,即向著自身同時(shí)也是整體的存在敞開。(11)參見尚文華:《真理中的生存與生存中的真理——一種基于可能性視角的分析》,《學(xué)術(shù)研究》2020年第10期。無疑,海德格爾的這一分析遭到了很多非議,但與理性的相關(guān)建構(gòu)相比,生存如何面對存在需要的乃是“親證”,只有在對存在或真理的親身見證發(fā)生之后,理性的進(jìn)一步建構(gòu)才是可能的——這是建構(gòu)和解構(gòu)發(fā)生交互運(yùn)作的空間,它們共同指向的是存在和真理問題,否則既不存在解構(gòu)問題,建構(gòu)也是無意義的。
無論是基督徒的信仰,還是一般意義的不期而至的“畏”,它們之所以能夠“讓”生存面對存在,并在其中重新組建自己,是因?yàn)樗鼈兇蚱屏死硇粤?xí)以為常的連續(xù)性和現(xiàn)實(shí)性,從而把自己“拋擲”到全然的出于存在的可能性中。如果把日常的連續(xù)性稱為時(shí)間的話——這種時(shí)間性更多是通過感覺、經(jīng)驗(yàn)、觀念等理性要素建構(gòu)起來的,那么信仰和“畏”中的生存則是一個(gè)又一個(gè)的時(shí)刻或瞬間。(12)在《基督信仰》中,施萊爾馬赫已經(jīng)注意到“時(shí)刻”對理性建構(gòu)的“反沖”,在該書中,“時(shí)刻”這個(gè)詞出現(xiàn)的頻率很高,但它并未成為主導(dǎo)性的“概念”,相比生存、信仰等問題的起點(diǎn)性意義,“時(shí)刻”的意義也不突出。克爾凱郭爾在《哲學(xué)片段》中正式將“時(shí)刻”確立為基礎(chǔ)性的概念,海德格爾早期的“現(xiàn)象學(xué)神學(xué)”亦建基于對 “時(shí)刻”的思考。在漢語學(xué)界中,謝文郁教授首次對“時(shí)刻”做出哲學(xué)性和思想性界定,筆者對此也有相關(guān)的討論。參見謝文郁:《自由與生存——西方思想史上的自由觀追蹤》,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五章;尚文華:《觀念抑或情感:一個(gè)關(guān)涉哲學(xué)和神學(xué)起點(diǎn)的爭論》,《學(xué)海》2019年第6期。時(shí)刻對時(shí)間的打破意味著理性建構(gòu)的中斷,意味著不同于理性建構(gòu)的“差異性”要素(作為可能性的存在)的進(jìn)駐;而理性建構(gòu)的中斷并不意味著它對生存不再有效,相反,它作為一種“曾經(jīng)的”現(xiàn)實(shí)性要素被保持在生存的可能性中,或者說,于生存而言,它只是諸多甚至無限的可能性中的一種而已,時(shí)刻中的生存在可能性中進(jìn)入下一個(gè)時(shí)刻。
很明顯,黑格爾對經(jīng)驗(yàn)的界定證明他已經(jīng)覺識到這一點(diǎn):新對象的進(jìn)駐本就是存在在意識中展示自身的一種方式。但是,這種新對象受制于意識既成的建構(gòu),因而只有相關(guān)于意識的知識,才有新對象的出現(xiàn),從而作為差異性要素的新對象并不意味著意識之連續(xù)性(時(shí)間)的中斷,充其量,它只是充實(shí)意識之時(shí)間性的“新要素”——這滿足了黑格爾的知識體系建構(gòu),但同時(shí)也使得時(shí)刻無法得到明晰的“自覺”,從而生存的時(shí)刻性,以及時(shí)刻性的生存在黑格爾體系中得不到應(yīng)有的出發(fā)點(diǎn)位置。從生存及其相關(guān)分析的視角看,黑格爾的見識意味著,哪怕是一位理性主義者,他在理性中也要“時(shí)刻”面對存在問題,即不只是在起點(diǎn)上,理性需要面對存在;理性建構(gòu)的整個(gè)過程都無法離開存在的展現(xiàn)。不同的是,究竟是理性的建構(gòu)在先,還是生存面臨的存在更加切身和本己,從而是生存在先,這是區(qū)分理性分析的生存分析的關(guān)鍵點(diǎn)。
總之,從理性立場看,存在是它不得不從一開始就要面對的問題,哪怕在其建構(gòu)有關(guān)存在的知識的過程中,存在亦是其不得不面對的;從生存的立場看,存在是它的起點(diǎn),在其組建自身的過程中,存在亦是起點(diǎn)性的。信仰、“畏”等“情緒”只是把生存不得不一直面對存在的“處境”揭示出來,其突破點(diǎn)在于對時(shí)刻的理解,這種理解既顛覆了理性傳統(tǒng)中的時(shí)間和永恒的思想,亦為重新面對存在問題和真理問題提供了契機(jī)。下面,讓我們進(jìn)入作為分析方法的生存分析。
三、生存分析何為:生存的結(jié)構(gòu)及其思想表達(dá)
無疑,克爾凱郭爾和海德格爾的相關(guān)思考是針對近代以來的理性哲學(xué)思路所陷入的困境而展開的,這個(gè)困境可以用一句話來表達(dá):理性的知識建構(gòu)思路遮蔽了存在問題,使思想與存在共屬一體的真理意義成為純粹建構(gòu)性的。而對信仰的分析、對“畏”的分析,則使存在重新成為生存所不得不面對的問題。這一步的踏出意味著,凡是能夠使存在進(jìn)入生存的要素都是需要思想重點(diǎn)關(guān)注的,所以情緒、生存傾向,包括古典思想中的功夫論、宗教的實(shí)踐活動等,凡是能夠解構(gòu)經(jīng)驗(yàn)或觀念建構(gòu),從而使生存能夠重新面對存在或真理的要素都成為重要的分析對象。
在生存要素的分析中,傳統(tǒng)的理性建構(gòu)并未被取消,只是不再作為“獨(dú)斷”的真理,不再作為遮蔽存在本身之顯現(xiàn)的要素;這并不意味著其存在沒有真理性,恰恰相反,它只是存在和真理本身的展示環(huán)節(jié),因而不斷地被解構(gòu),從而進(jìn)入存在在生存中的自身運(yùn)行之中。正如生存乃是一個(gè)不斷更替和運(yùn)行的過程,存在或真理本身的運(yùn)行亦是生存-理性不斷地被建構(gòu)和解構(gòu)的過程。這個(gè)過程的關(guān)鍵正是生存的時(shí)刻性,以及存在的自身發(fā)生性和運(yùn)行性。我們可以把生存在時(shí)刻中面對存在的自行發(fā)生和運(yùn)行稱為推動生存的一種真理沖動或真理意識。
因此,作為分析方法的生存分析,其方法論意識的首要因素乃是,把生存的真理沖動和真理意識充分接受下來。傳統(tǒng)理性的真理觀亦是由真理意識推動的,因而其同時(shí)也是生存分析所需要面對的題材;只是因其強(qiáng)大的建構(gòu)性,或者說,因其對理性的認(rèn)識性的強(qiáng)大確信,這種真理觀恰恰忽視了生存中時(shí)刻存在著的真理意識,忽視了這種真理意識乃是純粹面對存在的。換言之,正是存在自身在起點(diǎn)上的發(fā)生和運(yùn)行,引導(dǎo)了生存的真理意識,而非相反;同時(shí),因?yàn)樯娴恼胬硪庾R是由作為生存起點(diǎn)的存在發(fā)生和運(yùn)行推動,由這種真理意識所推動的理性的知識性建構(gòu)才是具有真理性的,否則它只是意見或觀念而已。
有了對生存內(nèi)在的真理沖動和真理意識的充分覺識之后,生存分析作為一種引導(dǎo)性的方法需要把生存自身置于時(shí)刻中,并能夠把一切現(xiàn)實(shí)性或由理性建構(gòu)起來的東西作為可能性而保持在自身之中。只有這樣,生存內(nèi)在的真理意識才能被激活,由這種意識建構(gòu)起來的文本系統(tǒng)才能進(jìn)入解構(gòu)自身的運(yùn)行邏輯中,從而不只是自身的生存意識被激活,文本系統(tǒng)所呈現(xiàn)的真理性意義,及其對存在或真理本身的進(jìn)一步指引意義才會顯示出來。即存在的自行發(fā)生性和運(yùn)行性進(jìn)入生存自身,進(jìn)入文本系統(tǒng);從而生存自身和文本系統(tǒng)的開放性或無限可能性才能彰顯出來。
因此,生存分析的對象不只是對自身生存的分析,同時(shí)亦是對眾多文本系統(tǒng),因而是對任何一個(gè)他者的分析。盡管存在著對象的無限差別——任何一個(gè)個(gè)體的生存意識及其相關(guān)建構(gòu)可能,必然相差殊異,但他們只是存在發(fā)生和運(yùn)行的工具或者渠道而已,是存在發(fā)生和運(yùn)行的無限豐富性和無限可能性的彰顯。這其中有斗爭與和平,有差異與同一,有相向而行與背道而馳。與理性建構(gòu)的同一性體系相比,生存分析揭示出來的存在的發(fā)生和運(yùn)行是一切的綜合體,它們有各自的真理性,亦都指向存在或真理本身。
因此,由生存分析所帶動的思想性寫作和解釋,以及對事物的揭示,既能夠讓思想在解構(gòu)自身中指向存在或真理,又能夠在既定的表達(dá)中建立自身的思想體系。無疑,無論是建立還是解構(gòu),都只是形式性的話語,其真實(shí)有力的內(nèi)容在于進(jìn)入事物的存在本身之中,因而是參與真理自身在大地上的發(fā)生和運(yùn)行。這種進(jìn)入和參與乃是一場關(guān)于存在顯現(xiàn)的“斗爭”。生存分析的意義在于:一方面,它在與他者(各種文本、各種“現(xiàn)實(shí)”的歷史等)的“爭辯”中,把這些事物的真理意義揭示出來,同時(shí)也把自身的存在意義以同一或差異的方式展示出來;另一方面,它面對的首先是自己的存在意義和真理意識,因而首先是在這種意義和意識中不斷地消融其個(gè)體性、特殊性、主觀性,使其展示為一種出于存在本身的真理性:它不僅為自己賦予存在意義,同時(shí)也為事物本身提供尺度,因?yàn)檫@種尺度出于存在自身,因而是一種絕對的尺度。
毫無疑問,作為一種哲學(xué)方法,我們對生存分析的界定或者言說具有某種形式性。這種形式性需要在具體內(nèi)容,即存在的諸多甚至無限豐富的展示領(lǐng)域中不斷地豐富,從而以自身的“實(shí)踐”方式,讓存在自身發(fā)生和運(yùn)行——這是克爾凱郭爾之后,作為方法的生存分析與“現(xiàn)實(shí)的”真理意識之運(yùn)作的空間:啟蒙之后,理論(思想)與實(shí)踐(行動)無論從哪個(gè)方面講,都深刻地耦合在一起。因此,沿著真理意識展開的生存分析,或者說,由生存分析引導(dǎo)的真理意識,使得理論和實(shí)踐這一傳統(tǒng)的哲學(xué)詞匯都具有真理意義,即我們需要在存在的發(fā)生和運(yùn)行,以及生存被賦予的可能性意識(自由)中重新思考理論和實(shí)踐所具有的原發(fā)性意義,即由思想和生存自身內(nèi)在的“建構(gòu)-解構(gòu)”張力所推動的真理意義。
在筆者看來,這種哲學(xué)的分析方法一旦得到確切的領(lǐng)會和理解,其迸發(fā)出來的力量既能夠?yàn)闈h語學(xué)界理解和闡釋西方文本和思想提供路徑,亦能夠?yàn)槲覀冎匦陆忉屩袊?jīng)典文本提供基礎(chǔ)。下面簡略闡釋其對于筆者解讀中國經(jīng)典的指引意義。
四、生存分析下的中國經(jīng)典重釋:以莊子的真理意識為例
與古希臘以來的西方哲學(xué)傳統(tǒng)相比,中國思想不重視嚴(yán)格的概念界定和形式性的邏輯推演,已經(jīng)在相當(dāng)程度上成為共識,但這不能抹殺中國思想內(nèi)在的思想意識和生存體驗(yàn)。作為現(xiàn)代意義上的學(xué)者,如何遵循界定和邏輯意識將中國思想的內(nèi)涵及其對存在的“經(jīng)驗(yàn)”闡釋出來,乃是漢語學(xué)人需要承擔(dān)的使命。我們發(fā)現(xiàn),中國經(jīng)典文本重視的生命體驗(yàn)及對超越者(天、道、佛等)的言說,更適合用生存分析的方法來進(jìn)行重釋。
有堅(jiān)實(shí)力量、有歷史穿透性的思想往往都是關(guān)乎存在或事情本身的,意圖在生存中切中存在的真理意識乃是推動經(jīng)典文本運(yùn)行的內(nèi)在動力。故而,采納生存分析方法對中國經(jīng)典文本進(jìn)行深度思想闡釋的要義在于,發(fā)掘其內(nèi)在的真理意識,并據(jù)此重構(gòu)文本的運(yùn)行邏輯。這個(gè)重構(gòu)的過程便是遵循嚴(yán)格的概念界定和形式邏輯而重演其對存在言說的“確-切”性過程。即使對于最主觀的情感問題,分析性的重構(gòu)過程亦是要在體驗(yàn)與對象之間展開:體驗(yàn)指向的是存在或?qū)ο螅瑢ο笞陨韯t由語境賦義,賦義即要確切地言說存在。因此,對于生存分析來說,真理意識和邏輯意識(包含界定)是進(jìn)入并重新闡釋中國經(jīng)典文本的兩把“解剖刀”,其目的在于揭示存在在漢語思想“時(shí)-空”中的發(fā)生和運(yùn)行。
在《齊物論》中,無論怎樣論述,似乎都不能說明“真宰”或“真君”即“吾喪我”中的“吾”的真實(shí)存在;同樣,在“死”面前,無論怎樣論說,似乎“人之生”和“心”隨著死都會過去;但莊子依然篤定地說:“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真。”(13)莊子:《齊物論》,載《莊子注疏》,郭象注,成玄英疏,中華書局2011年版,第31頁。此“論斷”實(shí)則出于一種最真切的現(xiàn)象(學(xué))意識,它既出乎最基礎(chǔ)的生存體察,也是一切“爭執(zhí)”產(chǎn)生的根源。試想,若非這種“真(理)”意識,儒墨之爭怎么可能?若非這種意識,思想性言說怎么可能?但若問這種真理意識是什么,能否被確實(shí)地把握和言說?答案是否定的:其切身性并不能保證其確實(shí)性(指:建構(gòu)出來)。亦是因此,對此“真意識”的一切言說,莊子明確地說:“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果有言邪?其未嘗有言邪?”(14)莊子:《齊物論》,載《莊子注疏》,郭象注,成玄英疏,中華書局2011年版,第33頁。換言之,如果說“真理意識”是“真-切”的,那么對真理的一切言說都“特未定也”,同樣是“真-切”的,兩者是同樣真實(shí)且基礎(chǔ)性的生存現(xiàn)象意識。
第一種生存現(xiàn)象意識保證了儒墨之爭,以及其他出于真理意識的言說都擁有某種程度的“真理性”;第二種生存現(xiàn)象則同時(shí)解構(gòu)了其真理性,從而思想能夠向著“更加”真實(shí)的存在狀況敞開。因此,既然深切地意識到這一點(diǎn),莊子對儒墨及其爭執(zhí)的態(tài)度絕非要在儒墨之外提供第三種“真理學(xué)說”——否則他就掉入自己要解構(gòu)的狀況中。這就引導(dǎo)解釋者深入反思,莊子要提供的是什么?沿著莊子本人的“真理意識”,即其對存在的“經(jīng)驗(yàn)”方式和“言說”方式來解讀《齊物論》,才是有思想意義的:這既是對莊子的思想闡釋,亦是闡釋者自身對存在的“經(jīng)驗(yàn)”和“言說”。由此,一個(gè)具有思想性和存在性的空間便隨之打開:這是思想的爭執(zhí),也是存在自身的爭執(zhí)。這種由存在引導(dǎo)所打開的“爭執(zhí)空間”既彰顯了存在在莊子、莊子的解釋者,以及眾多解釋者之間的發(fā)生和運(yùn)行,同時(shí)也彰顯了存在自身在“歷時(shí)”和“歷事”中間的發(fā)生和運(yùn)作。
非但《莊子》如是,眾多經(jīng)典文本都是如此。一旦生存的時(shí)刻性進(jìn)入我們的意識,存在自行的發(fā)生和運(yùn)行就成為主導(dǎo)性和引導(dǎo)性的;生存分析與真理意識也就成為學(xué)者自身,及其相互之間爭辯的分析起點(diǎn)和經(jīng)驗(yàn)起點(diǎn)。一個(gè)跨越時(shí)間和空間的存在的發(fā)生和運(yùn)行也便成為相互之間已經(jīng)發(fā)生、正在發(fā)生,也必將發(fā)生的有關(guān)“同一”(理性、邏輯等的建構(gòu))和“差異”(源于存在自身的發(fā)生和運(yùn)行)相互對峙、爭執(zhí),也相互融合、提升的“空間”——這是思想和存在自身的運(yùn)作空間:一個(gè)超越肉身和感性的超越性空間,但又是如此地本己和切身的空間。生存以及生存分析,正發(fā)生于這個(gè)空間之中。它是理性的知識性的建構(gòu)時(shí)代之后,思想尚有可能、尚有意義的關(guān)鍵契機(jī),亦是進(jìn)入漢語經(jīng)典、重塑漢語經(jīng)典的一把鑰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