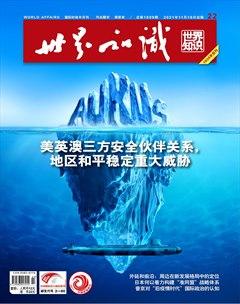對區(qū)域合作的思考(四)

張?zhí)N嶺
在對區(qū)域合作的研究中,有幾個常用詞,如區(qū)域主義(regionalism)、區(qū)域一體化(regional integration)、區(qū)域化(regionalization)、區(qū)域合作(regional cooperation),它們把具有不同含義和內(nèi)容的區(qū)域合作發(fā)展加以區(qū)別,并且賦予不同的含義。
區(qū)域主義一般是指區(qū)域制度化建設(shè)的合作,包括成立區(qū)域組織,賦予其以管理職能等。區(qū)域一體化或者區(qū)域化主要是針對經(jīng)濟(jì)上的高度鏈接,通過機制構(gòu)建,如自貿(mào)區(qū)(FTA)/經(jīng)濟(jì)伙伴關(guān)系(EPA),形成區(qū)域性產(chǎn)業(yè)鏈、供應(yīng)鏈網(wǎng)絡(luò)。
區(qū)域并非一個“想象的共同體”,而是所含國家的共處、共生之地。這些國家有著不可隔斷的歷史、現(xiàn)實聯(lián)系,存在著諸多共享的利益。即便如此,要開展合作,還是需要條件的,最基本的就是成員國的需要與共識。有種說法,即危機是推動合作的驅(qū)動力,但這只有部分道理,有時危機也會產(chǎn)生分裂。推動區(qū)域合作的需要和共識會因地區(qū)不同而有所差異,在合作內(nèi)容和方式上也是如此。
歐洲合作被認(rèn)為是在區(qū)域主義指導(dǎo)下的區(qū)域合作。歐洲有著歷史的區(qū)域主義基礎(chǔ),一戰(zhàn)后,出于構(gòu)建歐洲和平的需要,歐洲國家曾努力推動歐洲區(qū)域合作的制度構(gòu)建,但沒有成功。二戰(zhàn)后,歐洲國家推動區(qū)域合作的需要和共識更為強烈,獲得了成功。歐洲合作以創(chuàng)建地區(qū)和平為初衷,逐步建立了一套比較完整的區(qū)域管理體系。歐洲統(tǒng)一大市場的構(gòu)建是一個里程碑,實現(xiàn)了區(qū)域法律基礎(chǔ)上的高度開放與融合,使得區(qū)域制度構(gòu)建發(fā)展到一個很高的程度。
東南亞合作(東盟)被認(rèn)為是“準(zhǔn)區(qū)域主義”的構(gòu)建,或者說是東南亞特色的區(qū)域主義制度構(gòu)建。東南亞多數(shù)國家直到二戰(zhàn)后才逐步實現(xiàn)民族國家獨立,從殖民主義的枷鎖中解放出來。1967年部分國家出于政治動機,即聯(lián)合抵御所謂“共產(chǎn)主義擴張”的動機成立區(qū)域組織,此后,調(diào)整目標(biāo),把發(fā)展經(jīng)濟(jì)作為重點,力圖通過推動區(qū)域市場開放,促進(jìn)經(jīng)濟(jì)發(fā)展。東盟決定構(gòu)建“東盟共同體”,是區(qū)域主義制度構(gòu)建的一個大的發(fā)展,通過構(gòu)建東盟特色的經(jīng)濟(jì)、政治安全、社會文化共同體,凝聚區(qū)域合力,實現(xiàn)區(qū)域的合作、和平與發(fā)展。之所以說是“準(zhǔn)區(qū)域主義”,是因為東盟的共同體是以維護(hù)國家主權(quán)、治權(quán)為基礎(chǔ)的,區(qū)域?qū)哟蔚淖饔檬沁M(jìn)行目標(biāo)、議程、基本規(guī)則的設(shè)定與監(jiān)督,實施仍是以成員國的自主落實為基礎(chǔ),是一種基于政治約定與承諾和目標(biāo)導(dǎo)向的區(qū)域合作方式。
非洲聯(lián)盟(非盟)可以說是基于政治導(dǎo)向的區(qū)域主義,有著強烈的民族獨立的思想驅(qū)動。非盟的前身是1963年成立的非洲統(tǒng)一組織(非統(tǒng)),目標(biāo)設(shè)定是最終建立統(tǒng)一的“非洲合眾國”,實現(xiàn)非洲的獨立和自強,2001年改為非洲聯(lián)盟,并制定了非盟憲章。絕大多數(shù)非洲國家都參加了該組織,按照目標(biāo)設(shè)計,非盟將推動實現(xiàn)非洲自貿(mào)區(qū)、統(tǒng)一貨幣、聯(lián)合防御力量等。不過,由于非洲的復(fù)雜性和非盟缺乏執(zhí)行力,要實現(xiàn)這些遠(yuǎn)大目標(biāo)并非易事。
關(guān)于區(qū)域主義指導(dǎo)下的區(qū)域合作,以及區(qū)域主義本身,還是一個需要深入研究的問題。有學(xué)者從不同的構(gòu)建和動機進(jìn)行分類分析,比如基于政治安全的區(qū)域主義構(gòu)建,主要從政治利益考慮,在這方面,有非盟、泛美運動、阿拉伯聯(lián)盟(阿盟);基于經(jīng)濟(jì)的區(qū)域主義構(gòu)建,最為突出的是關(guān)稅同盟、貨幣區(qū)、共同市場,特別是經(jīng)濟(jì)共同體的構(gòu)建;基于文化的區(qū)域主義構(gòu)建,主要從加強文化的區(qū)域認(rèn)同性和獨立性考慮,被認(rèn)為是對“全球文化主義”的應(yīng)對,多以非政府合作的形式構(gòu)建。
在很多情況下,區(qū)域合作并不一定是區(qū)域主義的驅(qū)動,而是出于利益上的需要,是否能逐步發(fā)展到區(qū)域主義的認(rèn)知和共識,還需要許多條件。比如在東亞區(qū)域,亞洲金融危機曾催生東亞的區(qū)域主義意識和行動,相關(guān)國家提出了構(gòu)建東亞共同體的倡議,但因為受到諸多因素的制約,目前已很少提及。我出版過一本書,書名是《在理想與現(xiàn)實之間》,對東亞區(qū)域主義意識與行動進(jìn)行了比較詳盡的分析,感興趣者可細(xì)讀品味。
(未完待續(x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