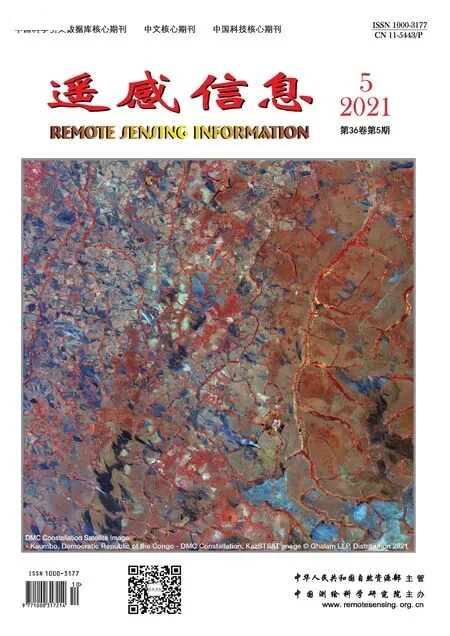大氣臭氧總量衛星反演產品地基驗證的空間異質性特征
呂春光,王玉萍,張悅,耿君,史云飛
(1.臨沂大學 資源環境學院,山東 臨沂 276000;2.山東省水土保持與環境保育重點實驗室,山東 臨沂 276000;3.合肥工業大學 土木與水利工程學院,合肥 230009)
0 引言
臭氧作為一種地球大氣中重要的痕量氣體,在全球氣候變化和地表生態效應中都扮演著重要的角色[1]。作為表征大氣臭氧狀況的重要指標,大氣臭氧總量可由搭載在地基和衛星平臺上的各類傳感器進行觀測,在相應的反演算法支持下,形成臭氧總量產品[2]。其中,地基觀測方式通常利用Dobson或Brewer紫外分光光度計等測量儀器,在一定空間范圍上,實現大氣臭氧總量的觀測[3-5]。地基儀器易于維護和標定,其觀測結果具有較高的穩定性和延續性,便于對其他觀測結果進行驗證,但在大范圍上表現臭氧總量的空間分布狀況時,受限于觀測站點的布局和數量等條件[6]。相比而言,衛星觀測臭氧總量具有大范圍同步優勢,可快速得到覆蓋全球的臭氧總量數據,已成為有效監測全球大氣臭氧時空分布和變化的重要手段[7]。然而,由于受到衛星傳感器壽命、遙感反演算法適用性以及氣象資料準確性等因素的影響,特定時間和區域的衛星反演臭氧總量會存在不同程度的觀測誤差[8]。因此,研究如何利用區域內地基觀測等可靠性強的數據資料,對衛星遙感臭氧總量產品進行對比驗證,掌握比對過程中存在的各類誤差來源、影響因素及其空間變異性,一直是遙感研究領域的熱點,具有重要的研究意義和實際價值。
在利用地基觀測數據對衛星反演臭氧總量產品驗證方面,國內外相關學者已針對各類不同的衛星傳感器,進行了大量的研究工作。根據反演產品的連續性和穩定性,選用的星載儀器以紫外高光譜傳感器為主,包括TOMS、GOME、OMI、SCIAMACHY、TOU以及SBUV/2等,而用以進行比對的地基站點,其空間分布范圍廣泛,多采用Dobson或Brewer臭氧總量觀測儀,具有較長的觀測歷史和數據積累,便于對數據進行篩選以及特征規律分析[9-18]。上述的比對研究,多采用衛星過境與地基觀測時間和空間距離接近、觀測角度偏差較小的樣本數據集,在保證充足數據量的情況下,對不同緯度不同區域的臭氧總量的線性相關性、年季和月季變化特征進行細致深入的論述。在分析測量誤差方面,則多關注臭氧總量偏差隨時間的長期變化趨勢,側重于從時序特征中提取輔助信息,圍繞太陽角度偏差、近地面狀況、觀測儀器靈敏度以及反演算法的設定參數等因素評估其對臭氧總量估算的影響[19-20]。值得注意的是,衛星傳感器對地觀測臭氧總量的像元范圍可能在十幾公里至上百公里,而地基觀測有效范圍僅限于站點附近,如此的觀測空間尺度差異,可能會使得像元內部的空間響應效應、大氣及地表狀況的空間可變性對衛星-地基臭氧總量觀測偏差產生影響,從而導致較為顯著的空間異質性特征。空間異質性是各類地物在空間分布中普遍存在的特征,也是生態環境領域較為關注的研究問題。在對其長期的研究過程中,形成了半變異函數、空間自相關系數以及熱點分析等豐富的研究方法,以揭示研究目標的空間異質性情況[21-25]。然而,在當前的相關研究中,針對大氣臭氧總量衛星反演產品在地基驗證過程中存在空間異質性特征的研究還不多見。
綜合上述情況,本研究嘗試選取多個典型的、具有較長臭氧總量觀測數據積累的地基站點及周邊范圍為研究區,開展對衛星-地基臭氧總量觀測結果的空間變化趨勢分析,以揭示其空間異質性特征。首先,以地基站點為基準點,構建其與各個樣本衛星觀測中心點的空間距離維度和空間方位維度,并在對應衛星觀測點位標記臭氧總量的觀測偏差;其次,結合探空站氣象資料,評估并識別風速風向因素對站點觀測結果空間變異的效應;在此基礎上,通過統計分析方法對各研究區觀測偏差的空間距離變異進行表達,并結合衛星和地基臭氧總量觀測結果相關性隨距離指標變化關系,分析其在空間距離維度上表現出的空間變化整體情況;進一步,借助空間聚類分析方法,對觀測偏差在空間距離和方位上表現出的梯度性和綴塊性進行表達,以揭示臭氧總量觀測的空間異質性差異及與基站類型等影響因素的關聯關系。該研究將有助于提升在生態環境領域中應用大氣臭氧總量衛星遙感產品的適用性,亦可為構建大氣臭氧總量遙感觀測的修正模型提供參考依據。
1 數據與研究區
1.1 數據資料
本研究使用的衛星反演臭氧總量產品來自于太陽紫外后向散射儀SBUV(solar backscatter ultraviolet instrument)/2。該衛星傳感器采用太陽同步軌道天底觀測方式,空間分辨率為170 km,具有12個光譜分辨率為1 nm的探測通道,其光譜覆蓋范圍在252~340 nm。搭載在NOAA19衛星的SBUV/2臭氧總量反演數據集,即SBUV2N19L2,采用類似TOMS算法的雙通道反演算法[26]。該算法經歷了幾十年的發展和訂正,是目前世界上使用最廣泛的臭氧總量衛星反演算法。在研究過程中,根據選定的地基臭氧總量樣本的觀測時間和空間位置,來確定SBUV2N19L2數據集中所需的具體像元。
臭氧總量地基觀測數據主要來自于世界臭氧與紫外輻射數據中心(World Ozone and Ultraviolet Radiation Data Centre,WOUDC)。WOUDC包含全球超過400個站點和80年的連續臭氧監測數據,可提供逐日/逐小時臭氧總量以及通過激光雷達、探空儀器等手段得到的臭氧廓線等豐富資料[27]。為了便于各地基站點同時期觀測的橫向比較,保證空間異質性分析的有效性,在研究中選取連續觀測時段內具有較為密集觀測樣本的逐小時臭氧總量觀測數據。根據選用的NOAA19 SBUV/2過境情況,進行綜合比較和篩選,最終確定了在2009—2010年內五個地基觀測站共計2 824組不同觀測時間的臭氧總量數據(表1)。
1.2 研究區概況
如表1所示,選取的五個典型地基觀測站分別是Aosta站、Churchill站、HongKong站、Kislovodsk站和Toronto站。根據站點所處的城市規模以及其周邊環境狀況,可將其分為都市型、城鎮型和鄉村型三種類型。其中,Aosta站、Kislovodsk站和Toronto站具有相近的緯度,均位于43.66°N~45.74°N。具體地,Aosta站和Kislovodsk站周邊多為度假勝地,附近沒有重要的大氣污染物源,冬季干燥,夏季溫暖,屬于典型的城鎮型站點。而Toronto站,位于國際著名大都市附近,人們的日常生活和工業活動會產生不同程度的對流層臭氧污染。Churchill站臨近高緯度地區(58.74°N),它的觀測儀器布設在加拿大哈德遜灣西緣的村鎮附近,氣候寒冷,人類活動極少,是鄉村型站點的代表。HongKong站位于22.21°N的熱帶低緯度地區,與Toronto站類似,臨近人口密集、生產活動頻繁的香港大都市區,是典型的都市型觀測站。

表1 地基觀測站信息
2 研究方法
2.1 數據預處理
分別提取2009—2010年內的NOAA19 SBUV/2衛星遙感臭氧總量產品以及WOUDC地基站點臭氧總量觀測資料,并在對應空間和時間范圍內對兩類數據進行匹配和篩選,共得到3 522組有效的比對樣本。它們具體包括:Aosta站613組、Churchill站1 043組、HongKong站547組、Kislovodsk站667組和Toronto站652組。在數據處理過程中,通過相對偏差對衛星反演和地基觀測的差異進行表達。
在預處理過程中,也同時記錄與之相關的輔助信息,包括衛星-地基太陽天頂角及其偏差、大氣質量、二氧化硫濃度、氣溫、地基儀器類型和觀測模式等參數值(表2)。

表2 相關輔助信息統計
此外,風速和風向等氣象觀測條件的顯著變化,可改變特定探測時間上地基觀測站點與衛星觀測像元所在實際空間范圍內的臭氧總量分布格局,進而對各個空間范圍內的衛星觀測偏差變化特征施加作用。為了能夠合理評價風速和風向影響,增強空間異質性分析的有效性,實驗選用了WOUDC現有的HongKong站和Churchill站同期臭氧探空數據178組,提取并統計了在臭氧總量中占主要比重的平流層臭氧峰值范圍上的平均風速和平均風向數據。
進一步為了表達風速風向情況、觀測偏差值與觀測空間位置之間的特定關系,定義可變距離百分比(percentage of drifting distance,pdd)如式(1)、式(2)所示。
(1)
(2)
式中:D表示地基站點至衛星觀測像元中心的空間距離,單位為km;ws表示平流層臭氧峰值范圍內的平均風速,單位為m/s;t表示衛星與地基站觀測時間點間隔,單位為s;α表示地基站點位和衛星觀測像元中心點形成的方位角φ(0°~360°),與平流層臭氧峰值范圍內平均風向wd(0°~360°)之間形成的夾角。當風速ws在方位角φ上的分量與地面站-衛星像元中心同方向時,cos(α)≥0,pdd表現風速風向對觀測點位之間實際空間距離的“縮近”作用;而當反向時,cos(α)<0,pdd則表現對實際空間距離的“拉伸”程度。
2.2 統計方法
在以往的研究中,線性相關性分析是對衛星反演值和地面站觀測值進行比對最常用的方法,可發掘其特征規律以及構建轉換模型。因此,在本研究中,首先對觀測樣本值進行相關性分析,以揭示觀測值隨空間距離偏離的基本情況。進一步,為了分析與衛星像元構成不同空間比例關系的樣本值整體偏離情況,借助半變異函數以空間距離因子為自變量的函數表達方式,構建空間距離變異曲線,從而形成更具適用性的評價指標。空間距離變異曲線可與相關性分析形成應證關系,進而用于表明觀測偏差隨觀測點空間距離偏移之間的內在關系。該曲線通過各空間范圍內的樣本計算平均相對偏差(mean relative deviation in the distance,mrdd),如式(3)所示。
(3)
式中:rd為相對偏差;i為樣本編號;N為一定空間距離范圍內的觀測樣本數量。空間距離范圍可由定義的空間距離因子d表示,如式(4)所示。
(4)
式中:D的含義同式(1);Rpixel為衛星傳感器像元的半徑,此處對于SBUV2傳感器為85 km。在觀測活動中,d為介于0~1的值表示地基站點位于對應衛星傳感器像元內部,而當d大于1時,表明地基觀測站點位于觀測像元范圍之外。
2.3 熱點分析方法

(5)
式中:rdj是要素j的統計值,即衛星臭氧總量觀測值與地基站點的第j組觀測的相對偏差;ωi,j是要素i和j之間的空間權重;n為要素總數;μ為所有要素統計值的均值;S為要素統計值的標準差。
根據上述熱點分析原理并應用相關分析工具,可構建關于rd的密度表面,表現其在各個空間方向上的不均勻程度,可視為由各距離上mrdd構成的空間變異曲線在二維空間平面上的拓展。
3 結果與討論
3.1 相關性分析
圖1展示了上述五個典型研究區的地基站與SBUV/2最鄰近像元在各對應觀測時間的臭氧總量的線性相關性,其中臭氧總量個數以多布森單位(Dobson unit,DU)表示。如圖1所示,通過對空間距離因子d≤1(圖1(a))、d≤2(圖1(b))、d≤3.5(圖1(c))以及d≤7(圖1(d))的樣本點統計情況,可以發現,在地基站位于衛星探測像元內部以及外部較大空間范圍上,普遍具有較為良好的線性擬合關系。其中,Churchill站的相關性整體最高,R2介于0.853~0.915,Toronto站和Aosta站的相關性略低于Churchill站,分別為0.799~0.924以及0.754~0.924。另外,Kislovodsk站點的相關性則穩定在0.800~0.857,而HongKong站的相關性最低,為0.353~0.504。為了進一步揭示臭氧總量相關關系在地基-衛星探測點空間距離變化過程中所表現出的特征和趨勢,對各個空間距離因子的線性相關性的擬合優度R2進行了加密計算,并在此基礎上展現其變化趨勢的整體性以及各研究區所體現的差異性。

圖1 地基站臭氧總量與各個空間距離范圍內衛星觀測值的相關性
如圖2(a)所示,各個研究區擬合優度的曲線形態及閾值范圍差異主要表現為:Churchill站的擬合程度最高,R2均值可達0.89,且在整個空間范圍上緩慢下降趨勢明顯。相比而言,Toronto站、Kislovodsk和Aosta站的擬合優度閾值波動范圍略低于Churchill站,分布在0.77~0.93之間,其擬合優度較大幅度的升降變化多出現在d<2的空間范圍。而HongKong站閾值與其他站點相比明顯偏低,介于0.35~0.53之間,且變化幅度較大,這可能是由于站點處于低緯度熱帶,光照時間相對較長,大氣較為活躍,使得風速風向等氣象因素對結果的影響較大;并且該區域臭氧總量閾值范圍小,對流層范圍特別是近地基臭氧濃度的變化對衛星觀測結果影響更為顯著,因而其在各距離范圍上表現出相對較低的線性相關程度。

圖2 臭氧總量觀測值擬合優度隨空間距離因子的變化趨勢
3.2 風速風向對觀測偏差的影響
臭氧探空數據的統計結果表明,在平流層各觀測樣本臭氧峰值范圍的高度區間,風速介于0.9~42 m/s,平均風速約為13.3 m/s,HongKong站和Churchill站由于緯度帶差異,兩地風速隨時間呈現較顯著的負相關,且具有典型的季節性變化。研究區內盛行東風(風向在45°~135°)和西風(風向在225°~315°),所占時間比重達到81%,且兩個觀測站風向具有較明顯的正相關特征。根據風速風向數據,結合地基站與衛星像元中心路徑,可進一步計算得到可變距離百分比(ppd)。由統計可知,ppd的均值在8.27附近,中位數為0.49,標準差約為37.9。如表3所示,ppd值域范圍在0~333.0之間,其中,小于1的樣本比重超過70%。ppd大于5的比重約為11.2%,結合均值和中位數來看,在該閾值范圍內,風速風向對地基-衛星觀測空間距離產生的擾動更為顯著。

表3 ppd值域分布情況 %
如圖3(a)所示,ppd指數在觀測rd增序區間上呈現出向rd高值區集聚的分布形態。當rd>4.45時,ppd>5的樣本出現頻次增加,數值升高明顯,可視為ppd指數的高頻分布區間。以上情況表明,風速風向與臭氧觀測偏差具有特定的響應關系,特別在觀測偏差較大的區間上,具有顯著效應。
研究表明,風速風向如對地基站與衛星的觀測結果施加作用,需要衛星與地基觀測具備必要的時間差。圖3(b)所示為地基站與衛星觀測時間差的增序區間上ppd指數的變化情況。在時間差負值范圍(衛星觀測時間早于地基站觀測)以及時間差正值范圍上,ppd高值均集中于時間差區間的兩端。同時,在區間中部,即時間差大于-9.4且小于6.5范圍內,形成了ppd指數均不超過5的穩定區間。

圖3 風速風向指數與臭氧總量觀測指標的關系
綜上所述,由于在時間差絕對值小于6.5的范圍,ppd處于穩定的低值區間。因此,采用該標準可分離風速風向對觀測偏差的作用,進而修正擬合優度以及觀測偏差等指標的空間變異曲線。如圖2(b)所示,在基于風速風向修正后的各研究區擬合優度中,HongKong站與Kislovodsk站出現了顯著的升高。其中,Kislovodsk站整體接近擬合優度最高的Churchill站,而HongKong站曲線閾值升至0.53以上。可以看到,修正后的HongKong站擬合優度仍然處于較低水平,這與站點區域的緯度帶和周邊環境關系密切。為了進一步有效識別因站點類型因素影響的觀測偏差空間異質性特征,對各研究區觀測偏差空間變異曲線進行繪制并對結果加以修正,具體論述請見3.3節。
3.3 觀測偏差空間變化的區域性特征
圖4展示了在采用時間差指標進行風速風向效應修正前后,各研究區臭氧總量觀測偏差隨著空間距離因子的變化情況。如圖5(b)所示,鄉村型Churchill站mrdd值在修正前后變化較小,整個空間距離的均值和標準差曲線都處于較低水平,極小值為2.73%和2.45%(修正后),其出現位置接近,分別在d=1.67和d=1.70處。作為都市型站點的HongKong站和Toronto站,修正前在整個空間距離上均值曲線分別大于5.3%和4%,表現出較高的相對偏差(圖4(c)和圖4(e))。修正后,HongKong站的均值曲線的下降較明顯,曲線平均值由5.79%降至4.46%,而標準差曲線值亦顯著減小,這可能是由于其所處低緯度熱帶地區,大氣層間流動作用更為顯著所致。作為城鎮型觀測站,Aosta站在修正前后其均值和標準差之間較為接近,均值的整體變動范圍略高于鄉村型站點(圖4(a))。而同為城鎮型觀測站的Kislovodsk站,在修正后均值和標準差曲線均出現下降,其平均值分別由4.02%和3.86%降至3.91%和3.20%。
從整體上看,各研究區修正后的空間距離變化曲線的閾值范圍均有不同程度的降低(圖4(a)~圖4(f))。在d<2的區間內,mrdd均值曲線的整體閾值由鄉村型->城鎮型->都市型而逐漸增大,表明其對地基觀測站點的類型具有指向性;而在d>3.5的范圍,各個研究區mrdd均值和標準差均有整體升高的趨勢。前人研究結果表明,在HongKong和Toronto等都市型站點,由于近地面人類生產和生活活動頻繁,使得對流層范圍的臭氧濃度顯著升高,衛星自頂向下觀測,易受太陽角度和反演算法的影響,對對流層臭氧濃度變化的敏感性較弱[29]。在這種情況下,對HongKong站和Toronto站為中心的區域進行衛星觀測,可能會使得臭氧總量觀測結果偏差增大(見圖4(c)和圖4(e)均值)。

圖4 臭氧總量相對偏差隨空間距離因子的變化趨勢
如圖4所示,研究區mrdd空間距離因子均值曲線主要表現了一定空間距離上的偏差整體大小,而標準差曲線可用于表現在具體空間范圍上觀測偏差分布的離散程度。如需對研究區域觀測偏差空間格局進行分析,表現空間平面內的距離性和方向性,則可通過熱點分析的密度分布圖予以展現。
3.4 熱點分析結果
如圖5所示,對各研究區域以地基站為中心,利用觀測偏差樣本數據表現的d<7(約600 km空間范圍)空間范圍熱點分布情況進行分析。可以發現,對于上述五個研究區,在整個空間上,觀測偏差均出現不同程度的空間綴塊和梯度變化,表現出顯著的空間異質性特征。以Churchill站為代表的鄉村型研究區,由地面基站至較大的空間范圍上,觀測樣本的空間梯度變化在所選研究區中最為明顯,低值區分布范圍廣,集中于地面基站附近,而高值斑塊面積較小且整體性好,分布在離中心較遠的區域。相比之下,在城鎮型Aosta站和Kislovodsk站附近區域,高值斑塊的數量較少,但覆蓋范圍有明顯的增加,在站點中心較近區域某些方位的高值有增加趨勢。以HongKong站和Toronto站為代表的都市型站點,其觀測偏差在空間上則表現出更為強烈的綴塊性,即高值斑塊的破碎程度加強,數量顯著增加,站點中心附近的高值在面積和強度上也較城鎮型站點區域有所加強。

圖5 各研究區空間異質性分布狀況
總體而言,地基站點由鄉村型-城鎮型-都市型的類型轉換,可使得衛星反演臭氧總量觀測偏差值的空間梯度性弱化,高值斑塊破碎化加強,并向SBUV/2的觀測像元尺度內(d<1)漂移,空間異質性程度得到加強。
在衛星傳感器和地基儀器觀測臭氧總量的觀測過程中,存在諸多因素,如輻射傳輸模型、臭氧垂向分布、大氣溫度狀況、下墊面狀況、數值內插誤差、太陽天頂角、觀測天頂角、雜散光以及儀器誤差等,都可能對臭氧總量估算結果產生影響[30]。不難發現,上述因素若對衛星-地基觀測偏差的空間分布格局產生影響必須滿足兩個條件:影響因子在空間上具有較為明顯的動態變化范圍;衛星-地基觀測時影響因子及其差異與觀測偏差之間隨著空間位置變化能夠具有顯著的相關性。在通常情況下,輻射傳輸模型、數值內插誤差、雜散光以及儀器誤差等類型的影響因素可作為系統性誤差,對空間距離因子變化并不敏感。
此外,如臭氧廓線、地表反射率等部分指標,由于地基站點觀測各種限制原因,較難得到同步觀測值的大量樣本,但可通過其他參量對其產生的觀測偏差影響進行粗略估計和定性分析。綜合上述考慮,根據觀測季節和觀測時間劃分時段,選取太陽天頂角及偏差、大氣質量、二氧化硫濃度、氣溫、地基儀器類型和觀測模式等幾個因素(表2),來進行其與空間異質性的相關性分析。
分析結果表明,隨空間距離和空間方位的變化,上述單一影響因素與觀測偏差之間不存在顯著的線性相關性(擬合優度均低于0.3)。另一方面,根據各研究區的空間異質性情況,其表現出的梯度性和綴塊性又與氣溫、緯度、對流層臭氧以及下墊面狀況等相關影響因素所確定的基站類型之間具有很強的指向性。由此可見,依照長時間序列不同觀測條件的樣本數據所得到的衛星-地基臭氧總量觀測偏差空間分布狀況,可能是上述多個影響因素對特定時間和空間臭氧總量觀測的綜合作用結果,從而形成了針對不同類型研究區固有的空間異質性格局。
4 結束語
本文以NOAA-19 SBUV/2衛星臭氧總量產品和WOUDC地基逐小時臭氧總量觀測數據為基礎,通過相關性分析、空間統計分析和熱點分析等方法,選取典型研究區開展了大氣臭氧總量衛星反演產品地基驗證的空間異質性研究。主要有以下結論。
1)對于衛星臭氧總量反演產品,在利用地基站點觀測數據進行驗證過程中,二者之間的臭氧總量觀測存在復雜的空間異質性特征,這使得觀測偏差并非隨衛星觀測中心點與地基站點之間空間距離因子的增大而呈現出簡單的遞增變化趨勢。
2)風速和風向氣象條件在觀測相對偏差大于4.45%的區間范圍上對臭氧總量觀測偏差具有不可忽略的效應,其在低緯度熱帶地區施加的影響更加顯著。風速和風向的影響作用較依賴于觀測時間差的大小,可利用時間差絕對值小于6.5分鐘指標確定非風速風向影響的穩定區間。在此基礎上,根據地基站點緯度帶及其周邊環境等因素確定的站點類型,對衛星-地基觀測臭氧總量的線性相關關系以及相對偏差,在空間距離上體現出較明顯的關聯性和分選性。其中,在d<2的范圍內,觀測相對偏差與站點類型的關聯度最強。隨著空間距離因子的增大,特別是在d>3.5的范圍內,能夠表現出總體上升趨勢。總體上,各個研究區空間距離變異曲線的閾值范圍和波動形態,是觀測偏差空間變化區域差異顯著性的反映。
3)通過熱點分析所得Gi*統計值范圍在0~0.018之間。根據其在空間距離維度和空間方位維度上的分布形態,可以發現,鄉村型站點區域的空間梯度性最強,而都市型站點區域具有的斑塊破碎化程度最高。指向不同地基站點類型的觀測偏差空間分布格局,受控于衛星傳感器的空間響應、觀測像元內部和外部氣象條件以及下墊面性質的均勻程度等因素,是氣溫和對流層臭氧濃度等對空間敏感的各類影響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
在未來有必要針對TOMS、OMI以及TOU等多種類型的紫外衛星傳感器,開展大氣臭氧總量地基驗證過程的空間異質性研究,以便更全面地掌握其觀測偏差在空間上的變異規律。同時,在后續的研究中,可選取更多類型的高光譜衛星傳感器大氣臭氧產品,通過與多種地面臭氧觀測數據的比對,嘗試對對流層臭氧總量觀測結果的空間異質性情況進行研究。